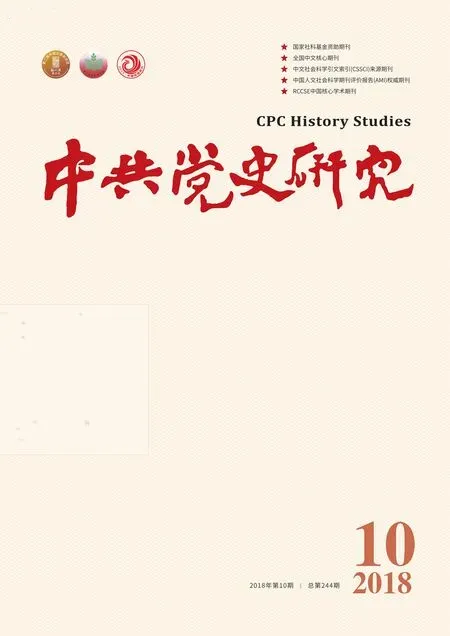解放戰爭時期晉綏邊區土改中私營工商業者的心態*張 曉 玲
〔〕解放戰爭時期,晉綏邊區土改中私營工商業者的心態經歷了由不滿、焦慮、恐慌到懷疑、信任,再到最終興奮的轉變過程。心態的轉變折射出中共在面對私營工商業者利益受侵犯時進行糾偏的決心和成效。顯然,侵犯私營工商業者利益并非中共土改的題中應有之義,糾偏亦非權宜之計。中共上層政策的模糊和基層干部素質偏低是私營工商業者利益受侵犯的深層原因。私營工商業者心態變遷反映出中共面對政策失誤時敢于承認、堅決糾正的作風,這也使中共最終贏得了民心。
土地改革中的私營工商業,是學界研究的重要問題,長期以來備受關注。但從已有成果看,多數研究注重探討中共的工商業政策,強調政策的運作及其執行效果,對私營工商業者本身的研究有所忽視,未能把其作為研究的主線*目前關于該方面的專門研究成果主要有黃兆康:《解放戰爭時期我黨對于民族資產階級及工商業的政策》,《黨史研究與教學》1991年第3期;徐秀春:《解放戰爭時期黨對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北京商學院學報》1993年第2期;楊國東:《解放戰爭時期黨的民族工商業政策的演進及其意義》,《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4年第6期;李良玉:《1948年前后土改中的工商業問題》,《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楊青:《解放戰爭時期黨的城市私營工商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黨的文獻》2005年第1期;楊奎松:《建國前后中國共產黨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李彩華:《解放戰爭時期黨的勞資兩利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龐松:《一九四九——一九五二:工商業政策的收放與工商界的境況》,《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期。在上述研究中,雖然涉及私營工商業本身,但這些多是佐證主題的材料,而非論述的主體。當然,一系列關于土地改革的專著大都提及私營工商業問題,但其著眼點仍主要在政策和效果的討論上。。土改中私營工商業者的心態是中共在革命與建設中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回顧歷史可以看到,從蘇區土地革命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各時期私營工商業者的命運驚人相似。盡管中共在理論上一直強調保護工商業,但在具體操作層面卻往往出現侵犯工商業者利益,之后再進行糾偏的現象[注]關于土改中工商業受侵犯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李良玉認為對基層黨內不純過分估計、基層掌握政策的模糊性和滯后性以及戰爭環境的影響是土改中工商業受侵犯的主要原因。參見李良玉:《1948年前后土改中的工商業問題》,《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羅平漢認為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導致城里的工商業者受到侵犯。參見羅平漢:《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解放區土改運動中的“左”傾錯誤及其糾正》,《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2期。劉詩古、曹樹基通過研究南昌土改中“工商業兼地主”的身份及清算問題,指出土改中不斷出現的侵犯工商業問題是中共出于“革命實用主義”需要的有意的制度安排。參見劉詩古、曹樹基:《新中國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工商業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認定——主要以南昌縣為例》,《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2期;劉詩古:《國家、農民與“工商業兼地主”:南昌縣土改中的“清算”斗爭》,《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廉如鑒認為,土改時期出現的“左”傾現象不是個別干部造成的個別錯誤,而是革命政權為實施戰爭動員所必須采取的措施。參見廉如鑒:《土改時期的“左”傾現象何以發生》,《開放時代》2015年第5期。據筆者理解,李良玉和羅平漢的觀點傾向于認為土改中工商業受侵的原因主要出在下層民眾或基層執行者身上,而劉詩古、曹樹基、廉如鑒的觀點則意味著土改中對工商業的侵犯是必然的,且在中共高層的意料之中。。在此過程中,私營工商業者的心態也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激蕩。因此,與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將注重分析解放戰爭時期晉綏邊區土改中私營工商業者的心態變遷[注]關于土改時各階層的心態,已有學者做過一些研究。如李金錚、吳毅、吳帆、莫宏偉均對土地改革時農民各階層的復雜心態進行過探討。參見李金錚:《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以1937—1949年的華北鄉村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吳毅、吳帆:《傳統的翻轉與再翻轉——新區土改中農民土地心態的構建與歷史邏輯》,《開放時代》2010年第3期;莫宏偉:《新區土地改革時期農村各階層思想動態述析——以湖南、蘇南為例》,《廣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不過,就已有研究看,學者較多關注地主、富農、中農及貧雇農等階層,對土改中的工商業者則有所忽視。晉綏解放區是土改較為激進、“左”傾現象比較嚴重的地區之一,故本文選取該解放區為研究區域。,把私營工商業者的命運置于中國革命的長時段內,并試圖從心態史視角探討土改中私營工商業者利益在政府保護政策下卻被侵犯的深層原因,以克服以往研究中只見制度不見人的缺憾,揭示土改歷史的復雜面相。
一、解放戰爭時期中共私營工商業政策的演變
眾所周知,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對私營工商業的政策是明確的,就是保護工商業。這種保護的思想明確體現在1946年到1948年中共頒布的相關文件中。然而,在開展土改運動的實際過程中,私營工商業者卻往往未能受到有效保護。而且,不同時期中共對工商業者保護的提法也有一些變動。這期間,保護工商業的政策經歷了從保全、保護到禁止侵犯,再到鼓勵其發展的演變過程。看似微小的變動,也體現了中共對私營工商業政策的重大調整。
(一)保全私營工商業
私營工商業一直是中共革命關注的重要問題。從蘇區土地革命到抗戰時期,中共逐漸形成了一整套關于保護私營工商業的政策。[注]參見楊青:《抗戰時期黨的私營工商業政策與抗日根據地的私營工商業》,《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1期;楊青:《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的私營工商業政策與革命根據地的私營工商業》,《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5期。正因為此,解放戰爭時期土改伊始,中共就進一步確立了保全私營工商業的政策,其目的就是盡可能地保全私營工商業者的利益。這一政策體現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中。該文件提出:“除罪大惡極的漢奸分子的礦山、工廠、商店應當沒收外,凡富農及地主開設的商店、作坊、工廠、礦山,不要侵犯,應予以保全,以免影響工商業的發展。”[注]中央檔案館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3頁。同時指出,封建地主階級與工商業資產階級是不同的,待遇也不同:“我們對待封建地主階級與對待工商業資產階級是有原則區別的。有些地方將農村中清算封建地主的辦法,錯誤地運用到城市中來清算工廠商店,應立即停止,否則,即將引起重大惡果。”5月8日,毛澤東和劉少奇進一步強調:“對工商業政策和工人運動必須與土地政策農民運動有原則區別……使解放區工商業的發展立于不敗之地。”[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3、8頁。顯然,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對私營工商業的認識有了很大的提升,即土改反對的是封建地主階級,而不是工商業資產階級。進一步來看,對于封建地主階級而言,土改要沒收的是其封建剝削部分,而資本主義部分則可保全。這樣的政策符合土地改革反封建的目的,表面上看似合理。
(二)保護私營工商業
然而,上述看似正確、合理的“保全”政策實際上并未做到保全工商業。在實際執行中,工商業者利益受到侵犯成為普遍現象。中共很快意識到此事的嚴重性,進一步重申對工商業的保護政策。1947年10月10日,中共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第12條明確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晉綏日報》1947年10月13日。1948年1月12日,任弼時在關于《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進一步專門解釋了工商業的政策。他說:“對工商業不要采取冒險政策……一般工商業是應當受到保護的,就是地主、富農所經營的工商業,也不應當沒收,同樣是應當受到民主政府的保護……在斗地主地財時,必須規定不許破壞已有的工商業,否則要受處罰。”他還反復強調:“我們對工商業,應采保護和領導的政策,絕對不能破壞,破壞是一種自殺政策。”[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晉綏日報》1948年3月27日。可以看到,從“保全”到“保護”的政策轉變體現了中共保護私營工商業決心的增強。然而,中共保護工商業的政策規定常采用綱領性和原則性的形式表示,特別是對一些關鍵性問題的表述不夠清晰明確。例如,保護工商業者“合法的”營業,而何為“合法”、哪些為“合法”并未作具體規定。隨后進一步的政策解釋中提到“一般工商業是應當受到保護的”,但“一般工商業”的提法亦較為籠統。1948年2月,晉綏邊區行署在總結中提到:在土改中“我們對封建剝削部分與工商業部分缺乏明確的規定,尤其缺乏領導上的掌握,因此不少地主因受牽連而被群眾清算沒收”[注]晉綏邊區行署:《關于糾正執行工商業政策中幾個錯誤問題的指示》(1948年2月1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220-13-452。。可見,這種綱領性的“保護”政策有一定的模糊性,在土改浪潮中很難被下層正確理解并有效執行。結果,這一次政策轉變仍然沒有為私營工商業提供有效保護。1948年3月19日,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指出:“各地所發生的左的錯誤,正如來電所說,確是華北、華東較晉綏、陜北更為嚴重……這主要是在全國土地會議(指1947年7月至9月的全國土地會議)以前及會議時所犯的。在土地會議后,則以晉綏錯誤似較為嚴重。”[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265頁。顯然,晉綏邊區已成為土地會議后侵犯私營工商業者利益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而其中緣由則很大程度歸結于相關政策規定不夠明確、細致。可見,當時中共在制定工商業政策時,對私營工商業者的實際情況還缺乏詳細的了解。盡管中共已經意識到私營工商業對于土地改革以及解放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但尚未對私營工商業者制定更為具體的政策。
(三)禁止侵犯并鼓勵私營工商業
面對日益嚴重的私營工商業者利益受侵犯的問題,中共緊急向各地發出指示,強調禁止侵犯并鼓勵私營工商業。同時,晉綏邊區行署亦相應公布了保護私營工商業的具體條例。1948年1月22日,李井泉給毛澤東關于糾正晉綏“左”傾錯誤的報告中指出:“工商業問題,已先告知各地檢查,并禁止各地土改侵犯工商業。”[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135頁。1月23日,晉綏分局再次向中央報告關于糾正“左”傾錯誤的方針及步驟,提到:“關于保護工商業的指示,關于三查運動中一些問題的指示,都已先后發各地,并報中央。”同時,中共進一步細化保護工商業的政策,對地主、富農經營工商業的問題作了專門指示。25日,中共中央就地主經營工商業的政策給鄧子恢發出指示:“保護一切于國民經濟有益的私人工商業。過去鼓勵地主、富農經營工商業的辦法是正確的,今后仍應鼓勵。地主、富農工商業一般應予保護,而不應一般沒收。華中一般清算沒收地主、富農工商業的政策是錯誤的。”2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下發關于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文件。該文件進一步明確規定:“小商販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中和新民主國家中,應受到堅決的保護。”“一切從事正當活動的商業資本家的合法財產和合法營業,都應當受到堅決的保護,而不允許加以侵犯和破壞。”[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138、134、205、208頁。3月10日,晉綏邊區召開生產會議,對工商業政策作了重要決定:“為了保護工商業并扶植其發展,決定由行署頒布保護工商業條例。堅決貫徹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并決定免征四七年度的營業稅。”[注]《邊區生產會議勝利閉幕》,《晉綏日報》1948年4月29日。3月28日,中央在對新區土改的指示中再次指出:“應明白規定,不準侵犯工商業,包括地主、富農的工商業在內。”[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312頁。5月25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區各級黨委發布修改過的《關于一九三三年兩個文件的決定》,并且指出:“地主兼工商業者,其土地及其與土地相連的房屋、財產沒收。其工商業及與工商業相連的店鋪、住房、財產等不沒收。富農兼工商業者,其土地及與土地相連的房屋、財產,照富農成分處理。其工商業及與工商業相連的店鋪、住房、財產,照工商業者處理。”[注]《中共中央關于一九三三年兩個文件的決定》,《晉綏日報》1948年6月10日。5月,晉綏邊區行署發布關于保護工商業問題的布告,鄭重宣布“凡遵守政府法令,進行營業的工廠、作坊、商店,不分階級、籍貫,政府均依法保護其財產所有權與經營自由權,任何個人或團體,均不得加以干涉或侵犯”,同時還公布了保護工商業的一些具體細節。6月,晉綏邊區行署正式頒布《保護工商業條例草案》,對于保護工商業的若干具體情形作了細致規定,共計11條。[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編印:《晉綏邊區工商行政管理史料選編》,內部印刷,1985年,第203—204頁。由上可見,中共此時的工商業政策已從“保護”進一步演化為“禁止侵犯”“不得干涉”“不沒收”“堅決保護”“鼓勵”等。這實際上是進一步釋放了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堅決保護工商業。對于工商業者而言,這樣的制度細化和完善無疑是一個福音,說明中共對工商業的政策進一步明確,對工商業的保護決心進一步堅定,對工商業的作用進一步肯定。
由上可以看到,解放戰爭時期,保護工商業是中共對私營工商業者的一貫政策,這是明確無疑的。事實上,自土地革命以來,中共就有了保護工商業的認識。然而,數次實踐表明,盡管中共一再強調對私營工商業者進行團結和保護,但結果是土改中私營工商業者往往成為被侵犯的對象,隨后再進行糾偏。顯然,政策和實踐存在反差。土改時期,基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共上層政策,盡管表述非常具有合理性和邏輯性,但顯而易見的是其理論闡述和具體實踐之間存在差別,現實的斗爭常常與理論闡述不能完全吻合。無疑,中共上層政策與下層實踐脫節是土改中工商業者利益被侵犯的重要原因。那么,這種上層政策和下層實踐之間經常出現的脫節與背離,是否是中共出于某種需要而進行的有意的制度安排?保護政策不明確,是否是因為含有動機上的不明確?侵犯工商業,是否是中共土改的題中應有之義,糾偏是否是權宜之計?[注]參見劉詩古:《國家、農民與“工商業兼地主”:南昌縣土改中的“清算”斗爭》,《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劉詩古、曹樹基:《新中國成立初期土地改革中“工商業兼地主”的政治身份認定——主要以南昌縣為例》,《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2期。為此,筆者將考察土改中私營工商業者的心態,通過心態變遷來探討中共政策與實踐出現反差和工商業者利益常常被侵犯的深層原因,并對上述幾種觀點進行討論,從而說明中共面對政策失誤敢于承認、堅決糾正的作風。
二、土改前期的不滿、焦慮和恐慌心態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民眾心態是社會環境影響的產物,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個體等多方面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言:“社會心理永遠順從它的經濟的目的,永遠適合于它,永遠為它所決定。”[注]《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1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第715頁。可以說,私營工商業者的社會心理主要由其經濟狀況決定,心態影響和引導著經濟行為。因此,考察私營工商業者的心態,首先需提及的是他們在土改中的遭遇。1946年,晉綏邊區開始土改。由于邊區土改較為激進,許多市鎮的工商業遭到沖擊,工商業者的經濟利益受到侵犯。據晉綏邊區較為發達的9個市鎮統計,至1947年底,商戶倒閉651戶,占全部商戶的25%;縮小規模的141戶,占5%[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金融貿易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01頁。。在土改運動前期,由于經濟利益受損,工商業者表現出不滿、無奈、害怕、失望、恐慌等多重心態。
(一)被課以重稅后的不滿、無奈心態
邊區工商業者多為地主、富農兼任或由其轉化而來。在土改過程中,有的基層領導人抱著對地主、富農、商人報復的思想,隨意提高營業稅率并連續征稅,以求打垮地主、富農、奸商在市鎮中的經濟地位。邊區行署曾電令各分區,將最高營業稅率由42%提高到60%,對于停業者亦要征收其財產的70%。[注]山西省財政廳稅務局等編:《晉綏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1938.2—1949.12)》,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頁。重稅之下,不少商家被征了老本,如崞縣合計磨坊把牲口賣了交稅[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金融貿易編》,第606頁。。不少商戶還被預征稅,如臨縣銀匠永和爐1946年繳稅57.2石,1947年上半年又預征51.64石,不得不把家具賣掉[注]中共呂梁地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編印:《晉綏根據地資料選編》第4集,內部資料,1984年,第299頁。。有些還被臨時提高稅率,致使停業,如臨縣商人薛樹國(中農)毛收入僅300萬元,按規定營業稅率應為22%,實際卻按90%征稅,導致停業[注]《晉綏根據地資料選編》第4集,第298頁。。甚至貧農商人都被超征稅,如臨縣磧口鎮貧農崔生龍靠賣棉花、油鹽為生,亦被征稅征垮臺[注]《晉綏行署對磧口市工商業政策的調查材料》(1948年4月1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90-4-129。。不少中貧農階層商人被征以重稅后聲明不想再干了,非常痛心地說:“你們征了又重征”,“我們想垮也不敢垮了,停了征收70%等于全部交公”,“稅局收了錢,公商掙了錢,私商倒了霉”。有的嘆氣說:“共產黨要農不要商”,“政策就是要把商人搞垮”,“八路軍不要商人了”,“這年頭真不成樣子了”,等等。[注]《晉綏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1938.2-1949.12)》,第60、62、65頁。臨縣白文鎮商人征稅后情緒低落說:“生意人干不成了,刨鬧(即努力)的結果一下就弄光了,活不成了,還干什么呢?”[注]《臨縣第五區白文鎮工商業材料》(1948年3月6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90-4-128-6。顯然,對于土改中的重稅,私營工商業者表現出強烈的不滿和無奈心態。
(二)懲治“奸商”過程中的焦慮、不安心態
懲治“奸商”活動與土改同時進行。在懲奸過程中,工商業者的焦慮、不安情緒逐漸擴散、振蕩、強化。土改期間,懲奸的最初目的是清理內部、清洗破壞分子,后來逐漸擴大到一般私商,“懲奸”變為“無商不奸”。由于土改與懲奸同步進行,因此凡從地主、富農轉化來的商人,甚至部分中貧農商人都被波及,導致懲奸運動擴大化。據不完全統計,到1947年底,邊區共懲治“奸商”370人,其中包括地主142人、商人136人、富農38人、中農39人、貧雇農15人。[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金融貿易編》,第610頁。最初扣捕的私商人數較少,商人們思想波動不大,認為“被扣的都是壞人”,沒被扣捕的感到十分慶幸。隨后,第二批扣捕了與貿易公司往來的私商,部分商人心理有了波動,開始不安、焦慮。到第三批時,因被扣的多是一般商人,商人們就想不通了,大多數開始擔心、害怕。這種擔憂和焦慮,使商人們開始懷疑土改,嚴重影響其經商的積極性。不少商人主動停業或縮小規模,如一個開皮房的馬上辭掉4個雇工、雜貨鋪商戶迅速縮小經營開始賣山藥蛋。有的商戶直接嚇跑了[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金融貿易編》,第611頁。。臨縣白文鎮在土改總結中也提到:“在懲治奸商過程中究竟有什么理由逮捕罰款,沒弄清楚。不經說明,隨意逮捕扣人,造成社會不安。”[注]《臨縣第五區白文鎮工商業材料》(1948年3月6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90-4-128-6。不難看出,在懲奸過程中,商人的不安、焦慮心態迅速升級,并摻雜著無奈和抱怨。
(三)直接被扣捕與清算過程中的失望和恐慌心態
在土改進程中,土改群眾甚至直接進城扣捕工商業者、封閉門面進行清算。在這個過程中,工商業者的情緒從焦慮升級到失望和恐慌,并越演越烈。被清算和扣押者主要包括以下幾種類型:地主、富農兼工商業者;前輩是地主、富農的工商業者;與地主、富農無關系者。可以說,整個清算過程是不分階層的。被清算的工商業者涉及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各階層,被清算原因亦各不相同。例如,聞喜縣有9家堿店,土改中全部被清算。其中,振興堿店被清算,原因為東家是地主,出租過土地。富農孫殿英、富裕中農孫晉海的堿店,以及義盛長(東家一家是中農、兩家是富裕中農)、信義昌(東家一家是富農、五家是中農)堿店被清算是因東家在土改中被斗爭,堿店亦被清算。而永義成堿店則因東家持有張英三、晉興源兩家股金,而這兩家被清算,永義成亦難逃被清算的命運。[注]《聞喜縣堿店簡料》(1948年11月9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293。另據資料記載:“該縣小學教員趙仲秀(全家11口),其父親是農民兼擺小攤,土改初期定為富裕中農,后改為富農被斗爭清算,家中完全被沒收,最后又改為地主,其本人都搞不清到底是什么成分,最后連小雜貨攤也被斗了。”[注]《聞喜薛店商聯會各小組人員情況》(1948年11月15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306。
事實上,土改中被清算的工商業者大都為小規模經營。例如,聞喜縣被清算的6家爐園(經營鑄造農具的作坊),人員均在4人至6人之間,且經營者成分多為中農[注]《全縣爐園情況:與小組會議經過》(1948年11月13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295。。據當地一位村民回憶,其父親當時在縣城經營一家爐園,經理、學徒、工人在內總共6人,家中成分為中農,但仍被斗爭清算。當時不僅爐園被迫停業,家中財產(包括衣服)都被沒收。[注]筆者對山西省聞喜縣桐城鎮吳家房村村民吳太合的采訪(2015年8月2日)。特別是一些地方的土改領導是大膽又不太正派的貧雇農,其出發點主要是報復,土改過程中常發揮“邪氣”[注]《平魯黨史縣志資料選》第8期,內部資料,第9頁。。這些地方的工商業者幾乎是被無理由清算。例如,“土改時朔縣農民進城大鬧三天,全市被沒收的500多家商戶,有240家是正當工商業。山陰縣地富、中農的鹽鍋幾乎全部沒收或獻出”[注]《晉綏根據地資料選編》第4集,第333頁。。又如,“興縣土改團一進城就開始扣捕商人,究竟扣的什么人,工作團不了解也不問”[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金融貿易編》,第613頁。。1948年1月22日,李井泉在給毛澤東關于糾正“左”傾錯誤的報告中說:“工商業,在這兩個地區(興縣蔡家崖與五寨縣)主要是土改牽連較大。而朔縣則更嚴重,鄉村農民數千人進城扣押敵偽人員及地主,沒收財物,領導上未加控制,異常混亂。”[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136頁。據時人回憶,當時的情況是“誰有錢就斗誰,誰有錢清算誰”[注]筆者對山西省聞喜縣桐城鎮吳家房村村民吳太合的采訪(2015年8月2日)。。從前恨自己不富、現在恨自己不窮的怪心理在商人心中蔓延。
可以說,私營工商業者的上述心態都是基于自身利益考慮的“理性人”反應。邊區私營工商業者多數為農戶兼營,從事以生存為目的的小規模商業活動,而土改已經觸碰了他們的生存底線。在土改進程中,現實向工商業者傳遞著一種負面情緒,他們周圍形成一種四面楚歌的氛圍。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這樣的謠言:“使用過白洋就是奸商。”[注]《晉綏革命根據地工商稅收史料選編(1938.2—1949.12)》,第66頁。在這種情況下,工商業者很難保持冷靜,甚至亂了方寸,最終導致整個工商業界出現恐慌。邊區商人恐慌心態的產生不僅來自暫時的情境,而且來自過去互動的歷史和對未來的展望。恐慌出現后,整個商業界變得盲目、焦急不安、秩序混亂,無法進行應有的各種商業活動。不僅被清算的工商業者普遍恐慌,而且許多未被扣捕清算的也惴惴不安。商人們人人自危、提心吊膽、疑神疑鬼,猶如“驚弓之鳥”。有些大的商戶連店員都不敢用了,如雜貨鋪掌柜王向年親自去擔水,不敢叫店員做。商人們想的是,每天只要有兩頓飯吃就可以。[注]《聞喜城內糾偏工作結論》(1948年8月30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304。經營爐園的工商業者都不敢搞生產,有的逃跑,有的怕斗不置家具。[注]《全縣爐園情況:與小組會議經過》(1948年11月13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295。由上可說明以下兩點:其一,私營工商業者無力直接對抗,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只能通過口頭抱怨、逃跑、偽裝起來等手段來表示不滿與反抗。其二,工商業者的心態具有傳染性,特別是負面的失望和恐慌情緒更容易在群體中傳染。正是這種傳染性,使得普遍的失望和恐慌在工商業者群體中產生。
綜上所述,土改運動前期,由于工商業者被清算斗爭的面較廣、程度較深,多數工商業者經歷了不滿、害怕、失望甚至恐慌。可以說,在土改慣性下,由于工商業者群體心態相互傳染,普通小私營工商業者的上述遭遇和心態是中共高層始料未及的,亦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扭轉工商業者的心態、使其恢復信心成為擺在土改面前的一道難題,是政府亟須盡快解決的問題。從根本上講,使貧弱的私營工商業者得到基本的制度保障是邊區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更重要的是,不能讓工商業者失去希望。因為,失望和恐慌情緒不消除,不滿心態不轉變,工商業者的生產積極性就無法調動,土改就達不到推動生產的預期目標。
三、土改后期從懷疑到信任的心態
如前所述,土改前期因大多數工商業者被清算、斗爭,不滿、焦慮、恐慌情緒不斷滋長,并成為大多數工商業者的心態。工商業者的心態是復雜的。社會心理學認為,在社會急劇變遷時,社會心態變化快、心態復雜,無論對個體還是對社會組織和制度的影響都很大。政府方面的正式信息必須介入。介入越晚,人們就覺得事情越嚴重,越需要釋放和消解恐慌。[注]參見楊宜音:《個體與宏觀社會的心理關系:社會心態概念的界定》,《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4期。因此,針對前述情況,中共迅速進行了糾正。毛澤東指出,晉綏“在土地改革中侵犯了屬于地主富農所有的工商業;在清查經濟反革命的斗爭中,超出了應當清查的范圍;以及在稅收政策中,打擊了工商業”[注]《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07頁。。1948年2月,中共對晉綏分局關于糾正土改中侵犯工商業者的“左”傾現象作了批示,目的是使現有工商業者安心經營自己的企業,使去年受過打擊但還有力量恢復營業的工商業者敢于重新復業,使其相信中共對工商業的政策確有改變。[注]《中央對晉綏分局關于糾正“左”的工商業政策的補救辦法的批示》,《人民日報》1948年2月4日。
(一)由害怕到懷疑
土改后期,隨著糾偏工作的展開,商人心態逐漸由不滿、焦慮、恐慌開始向懷疑、猶豫轉變。糾偏伊始,不少商人對政策持懷疑態度,認為公家補償只是口頭說說。例如,聞喜縣河底鎮1948年糾偏后,有些商人慢慢準備發展,但相當一部分人不相信政策,“在自己思想上總有些悲觀”,不敢發展。[注]《河底市場調查》(1948年9月23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307。不少商人心存謹慎和猶豫。堅決保護工商業的政策執行后,聞喜縣大小商戶共增加到190余戶,但屬于一個人經營的很多。[注]《聞喜城內糾偏工作結論》(1948年8月30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304。由此反映出商人的疑懼心理。
可以說,商人的主要心病是,因被斗爭而害怕發展,對中共的政策捉摸不定,從而產生懷疑心態。主要表現為:其一,因不相信政策而害怕被再次斗爭。例如,聞喜縣有的商人說:“人家說不斗爭了,咱可知道斗也不斗?由人家說哩,說斗就斗,說不斗就不斗,咱能管下嗎?”[注]《聞喜縣起火小店車馬大店小組會總結》(1948年11月8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302。像這樣的人大多處在觀望的疑慮狀態中。顯然,商人對糾偏政策是懷疑的。其二,因不了解政策而產生懼怕被共產的平均主義心態。不少商人懼怕發展大了被共產,認為共產黨就是要共產、平均一切物品。[注]《聞喜縣起火小店車馬大店小組會總結》(1948年11月8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302。例如,臨縣三交群眾說:“好壞不能鬧商了,盡量縮小,越窮越好。”[注]《臨縣三交工商業材料》(1948年3月6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90-4-128-4。上述均反映了商人的基本心境。由于這種心態的存在,即便是在政府明確宣布保護工商業者的政策后,商人依然懷疑自己的生意能否繼續,害怕政策再變。顯然,土改時期,由于私營工商業者處于高度緊張的壓力之下,雖然中共迅速實施糾偏,多數商人對被斗仍心有余悸,對政策持懷疑態度,故而對發展依舊顧慮重重。
(二)由懷疑到信任、高興
為徹底解除商人的一切顧慮,中共基層領導干部通過多次召開會議和個別宣傳讓商人了解各種政策與糾偏的意義,說明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是社會主義工商業的基本方針。經過反復的宣傳和實際糾偏行動,商人們的心態開始轉變。
例如,邊區商業重鎮磧口的工作團、稅務局、貿易局專門召開商民會議解釋黨對工商業的政策,并說明政府絕對保護工商業者的利益。會議上說:“保證過去征重稅的,無法恢復營業的,經研究后可分別輕征或免征;土改是斗地主,對工商利益決不侵犯,就是地主富農的工商業部分亦不動。會后大家安心了,都開始營業,并增加了兩家商鋪。”[注]晉綏行署檢查團:《關于磧口市廿三家工商業補正的材料》(1948年1月15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90-4-127-2。又如,聞喜縣行村在糾偏過程中,不僅召開村干部會議詳細解釋糾偏的意義以打通思想,而且逢集就與攤販、外貨商人進行交談,解除他們的顧慮。[注]參見《行村鎮糾偏經過》(1948年9月1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294。經過商談后,大部分商人的顧慮開始慢慢消除,但還有一絲猶豫。有的人問:“還斗不斗工商業啦,如不斗這可好啦,我們就能一心做買賣;但不知是真是假,心里總有些不放心。”[注]《聞喜城內糾偏工作結論》(1948年8月30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304。有的人則進行自我說服,心里想:“毛主席革命不能不要老百姓,如果不是老百姓那么他靠誰革命?老百姓只要能發財致富就能支援前線。”[注]《聞喜縣堿店簡料》(1948年11月9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293。
隨著被斗戶果實被退還、基層領導干部承認錯誤,商人對中共的政策逐漸有了深入的了解,并產生了一定信任感,其心態也從懷疑逐漸轉變為信任、高興,甚至興奮。例如,臨縣在1948年2月退款后,群眾情緒大為提高,大小商人都表示高興。商人說:“雖然退款不多,但只要現在少有幾個,大的鬧不起可以鬧小的。高興的是今后能鬧了。”[注]《臨縣三交工商業材料》(1948年3月6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90-4-128-4。再如,聞喜縣大部分商人“對共產黨存的懷疑態度已經煙消云散了,了解到我們共產黨究竟是干什么的,真正是為人民。”[注]《聞喜縣起火小店車馬大店小組會總結》(1948年11月8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302。不少商人不但自己解決了問題,而且還向其他人宣傳,解除別人困難。特別是,政府還對需要貸款的商人給予貸款,并充分發揮力量供給商人生產工具。由此可看出,糾偏以后,私營工商業者是相當高興的。特別是政府的大力扶助,使他們更加信任中共,認為中共能夠給予其生意更好的發展空間。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外出逃亡的商人陸續返回復業,心中也產生了對中共的信任。[注]《我保護工商業政策影響下,晉南四千商人返回復業》,《人民日報》1948年7月8日。可見,經過政府的大力糾偏,商人的心態經歷了由波動到平穩,由懷疑到信任,由沮喪到高興的復雜轉變過程。當然,商人信心的建立是需要經歷一個過程的。
四、從心態變遷看私營工商業者利益被侵犯的深層原因
中共的糾偏是及時且真誠的,因為侵犯私營工商業者利益并非中共事先所能預料。透過私營工商業者的內心激蕩歷程,筆者將對私營工商業者利益被侵犯的深層原因作一下探討。
(一)上層政策的模糊是私營工商業者利益被侵犯的根本原因
中共清醒地認識到,工商業的發展“對于繁榮中國的經濟是有利的,是需要的”[注]魏宏運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編》5,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1頁。。土改期間,中共在政策上對私營工商業者給予高度重視。就原則來看,保護工商業始終是中共堅持的基本立場。即便是在各地工商業者利益已普遍受到侵犯的情況下,這一原則依然不曾改變。如果說蘇區時期由于處于殘酷戰爭的非常時期,工農民主專政雖有保護中小工商業者的口號,但因種種因素難以落實,[注]參見溫銳:《蘇維埃時期中共工商業政策的再探討——兼論敵人、朋友、同盟者的轉換與勞動者、公民、主人的定位》,《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4期。那么到解放戰爭時期,工商業者的利益在新民主主義政權的保護政策下何以仍然被侵犯?顯而易見,把土改時期私營工商業者的命運放到中共革命的整個歷史進程中,結合私營工商業者的心態變遷及中共糾偏進行考察,可以發現工商業者屢次受侵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上層政策的模糊。土改時期保護工商業的政策規定本身是不夠清晰明確的,是模棱兩可的。這種政策模糊并非中共有意而為。中共深知保護工商業的重要性。然而,在瞬息萬變的戰爭環境下,中共雖有心保護工商業,但受戰爭影響,常常力不從心,不能把工作重點集中到工商業上,從而導致制定的工商業政策不夠明確。這種政策的不明確使得在土改進程中諸多工商業者的利益被侵犯。進一步來看,這種政策的不明確與模糊主要表現在以下關鍵的兩方面。
首先,土改政策對工商業者收入性質和數量的規定不夠明確。工商業者收入性質的確定是土改中工商業者利益是否被侵犯的關鍵。依照前述“凡富農及地主所設的商店、作坊、工廠、礦山,不要侵犯”的規定,言外之意是富農及地主除商店、作坊、工廠、礦山等之外的財產,如來源于土地等的收入是可以“動”的。這樣,工商業者收入性質的界定就成為土改的關鍵。當時的土改政策對工商業者收入的性質及待遇也作過規定:“如果是大商人,而且家里有不小數目土地出租伴種或招伙計的,那就是大商兼地主,他們的土地應和地主土地同樣處理。至于中小商人……他們的土地要斟酌具體的情形,但在負擔上必須計算其商業收入部分。如果他的收入主要是地租而商業收入較少,那么對于他的土地部分就要按照對地主土地的原則處理。”[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山西省檔案館:《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農業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2頁。顯然,這樣的規定是不夠明確的,在實踐層面操作彈性極大。然而,土改政策未能就如何區分商人的收入性質作出更為細致的規定[注]事實上,中共在頒布土改政策時亦意識到商人的土地問題是常常弄不清楚而容易劃錯的問題。參見《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農業編》,第340—342頁。,而是將這一任務留給基層去“斟酌”解決。在界定商人收入性質、數量時,大多基層干部是通過群眾調查和群眾估計進行的,這樣就大大提高了收入估算的不準確性,從而出現商人利益受侵犯的現象。例如,臨縣磧口土改中因征稅而垮臺的商人,其收入的界定依據均為群眾估計,“沒有按紅利的收入數目課征,而是根據估計的財富冒征的”[注]晉綏行署檢查團:《關于磧口市廿三家工商業補正的材料》(1948年1月15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90-4-127-2。。顯然,政策的模糊性增加了工商業者利益被侵犯的概率。關于這一點,中共當時亦是認識到的。如一份調查指出:“土改時期的前一段時期,對工業政策,尤其是對地富兼營工商業的政策仍不明確,清算了地主的工商業,因而封閉了商店。”[注]《臨縣城工商業調查》(1948年3月9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90-4-128-2。到新區土改時,中共中央正式在文件中就因工商業政策的模糊性導致私營工商業者利益受侵的事實指出:“對工商業,確定‘一般采取保護扶植政策。地主兼工商業的,在農村者,不與封建聯系的不動。其與封建剝削分不開的分配’。根據老區經驗證明,這樣提法毛病極大。地主、富農工商業,在農村中,與其封建剝削是很難分開的。尤其我們同志對什么是封建剝削,什么是資本主義剝削,十分模糊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個口號一定會大開斗爭工商業方便之門。”[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313頁。
其次,土改中階級劃分政策不夠具體、明確。依據當時土改政策,不僅私營工商業者收入性質、數量難以界定把握,而且因政策不明確,階級成分的劃分也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如此進一步加劇了私營工商業者利益受侵犯的程度,如崞縣土改“將一些有商業關系的中農訂成富農”[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280頁。。前述某工商業者被頻繁變更階級成分以致他最終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成分的事例亦充分驗證這一點。據資料顯示,晉綏邊區土改過程中,“將工商業從經濟上分為大中小三種。凡資本在一千白洋以上者均為大商,一千以下五百以上為中商,五百以下為小商。在政治待遇上,大商等于地主,中商等于富農,小商等于中農。因此,大中商均在清算之列。這樣的劃分,不按剝削關系而看鋪攤攤,必然產生的結果是對工商業的侵犯形成過左的政策”。[注]《臨縣城工商業調查》(1948年3月9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90-4-128-2。臨縣在總結土改經驗時提出:“商人的階級劃分是不合適的。”[注]《臨縣城工商業調查》(1948年3月9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90-4-128-2。中共中央工委亦曾就成分劃定問題指示晉綏分局:“你們《土改通訊》第二號關于后木欄干村成分問題的意見,是不妥的,偏于過左的。”[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94頁。1948年1月,任弼時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曾以興縣蔡家崖為例,談到因土改中成分錯劃而導致打擊面擴大的問題。[注]參見《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104—105頁。顯然,邊區土改中成分劃分是有問題的,這導致工商業者利益屢被侵犯。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又專門向各地印發共25章2萬余字的更為詳細的在土改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文件草案。中央認為:“單有土地法大綱及其他黨的若干指示而無這樣一個完備的文件,很難使我們的工作人員不犯或少犯錯誤。”[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228頁。隨后,邊區各地緊急改訂成分。從1948年2月開始,《晉綏日報》曾連續數月報道各地改訂階級成分的案例和經驗。8月15日,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正式對土改中的“左”傾錯誤作出檢討,承認“主要是我們(對政策)缺乏系統的分析和系統的說明”,并強調“應當把正確宣傳與執行黨的政策看作黨的生命”。[注]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宣傳部:《關于去年土改中我們在宣傳黨的政策上所犯的左的偏向與錯誤的檢討》,《晉綏日報》1948年8月15日。顯而易見,在模糊的政策之下,私營工商業者的利益很容易受到侵犯。
(二)基層干部素質偏低導致上層政策與下層實踐脫節是私營工商業者利益被侵犯的直接原因
基層干部是土改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各項工作的直接落實者,其素質既關系到本地區土改及糾偏的成效,又關系到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大局。筆者認為,基層干部素質偏低導致中共上層政策與下層實踐脫節,是私營工商業者利益被侵犯的重要原因之一。考察從下層視角分析工商業受侵的相關研究成果,一個傾向性結論是,把工商業受侵要么歸于農民的平均主義傾向,要么歸于基層干部的革命過激傾向。然而,如研讀當年土改基層檔案,審視當時中共高層的工商理念,分析私營工商業者心態的轉變,可發現,導致私營工商業者利益受侵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基層干部較低的素質,這導致其未能深入解讀中共的上層政策,從而使土改基層實踐與中共上層政策產生脫節。而工商業者心態的成功轉變亦是建立在基層干部多次反復地學習、研讀中共土改及工商業政策的基礎之上,得益于強有力的基層干部或基層干部素質的提高。
解放戰爭時期,晉綏邊區一些基層干部文化水平比較低,很多參與土改的干部素質并不高。據資料顯示,晉綏邊區經濟文化歷來落后,工農干部多數從小就失去受教育機會,文化水平很低。土改期間,晉綏邊區干部中又普遍滋長輕視文化、忽視教育的錯誤理念。[注]參見山西省地方志辦公室編:《晉綏革命根據地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33—436頁。邊區土改委員會主任趙林曾就臨縣土改中的問題給晉綏分局寫信,其中第一條提的就是干部素質:“三個行政村共19個干部(現在看來質量極差,有好些還不夠條件),每個行政村只有一個至二個較強干部來掌握。”[注]《趙林同志來信關于臨縣普遍群眾運動中幾個問題的檢討》,《晉綏日報》1947年11月3日。由于文化水平低,不少干部在對黨的土改政策和工商業政策還不了解的前提下就展開土改。例如,聞喜縣行村土改干部說:“雖然我們在城內住,在那時(指斗爭工商業戶時),我們對于政策也不甚明了。”[注]《行村鎮糾偏經過》(1948年9月1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294。又如,臨縣招賢鎮總結土改經驗時指出:“土改中在思想上對保護工商業不夠明確。”[注]《臨縣八區招賢鎮工商業調查》(1948年3月4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90-4-128-5。顯然,在土改進行時,有些基層干部甚至上一級干部對政策也不了解。例如,崞縣在討論村主席時,群眾代表們認為他們是“通天瞎棒”,辦不了事。[注]參見《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289頁。再如,右玉縣三區幾位區干部曾指出:區長和副區長識字不多。他們在接到縣上指示和信件時,常因文件字體潦草馬虎或一些“官話”(如“延期”、“先斬后奏”、“手續正規化”等)而看不懂、無法理解指示的意思,以致工作常常被拖延、出錯誤。因此必須找文化程度較高一些的區助理員幫忙解釋、講清,才能理解文件的意思。[注]參見重捷:《給區村工農干部寫信下通知不要寫草字文句要通俗》,《晉綏日報》1948年7月9日。顯然,文化素質低使得很多干部無力深入解讀保護工商業者的政策。例如,崞縣土改干部在檢討過激錯誤時說:“當時(指理解政策時)只記住一句話:‘不能包庇地主’……當時(指犯錯誤時),一來是‘鬧不機明(即搞不清楚)’,二來怕人說包庇地主、富農。”[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280頁。顯然,基層干部未能全面地、充分地、正確地理解土改相關政策是工商業者受侵的直接原因。
進一步來看,從基層干部本意及情感來講,他們也不愿意侵犯工商業者。例如,聞喜縣一名貧商團長說:“我就知道怕斗下錯,可果然就是這樣。”[注]《聞喜城內糾偏工作結論》(1948年8月30日),聞喜縣檔案館藏,檔案號2-304。臨縣土改中“由于追查歷史、劃分成分、過重的營業稅,甚至引起當地干部的不滿”[注]《臨縣八區招賢鎮工商業調查》(1948年3月4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90-4-128-5。。可以說,部分基層干部在土改過程中出現過激行為,一方面源自上層政策本身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則源于基層干部較低的素質。有了這些前提,農民的平均主義傾向、基層執行者的革命過激傾向和土改的運動慣性才有了滋生的土壤。李新在回憶錄中談道:“晉冀魯豫邊區永安縣農民運動中發生的簡單報復行為,是農民落后性的表現……土改復查時,群眾把工商店鋪里的東西全分了,連藥鋪里的藥都分了。我問當地干部:‘你們為什么要把藥鋪分了呢?’他說:‘上面說我們不徹底嘛。’我馬上召集各區區長及各村干部開會講:‘中央的精神嘛,很明白,也很簡單。工商業對發展生產有益,所以要保護。平分土地不是平均主義。誰叫你們把藥鋪都平分了?分藥鋪,破壞工商業,不是中央精神!怎么能見風就是雨呢?’”[注]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3、274、275頁。這一番對白觸及了私營工商業者利益被侵犯的重要原因,即部分基層干部未能正確理解并執行中央的政策精神,而這其中的緣由是“農民的落后性”。那么農民為什么具有落后性?這固然與其經濟地位有關,但與素質偏低亦有一定關系。有學者曾指出,私營工商業者利益受侵犯“反映出一些人對私營經濟在發展國民經濟、推動經濟現代化中的作用還缺乏必要的認識”[注]虞和平:《中國現代化歷程》第2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83頁。。認識的差異源自文化素質的差異。因此,正是基層干部的素質存在差異,才能解釋土改時同一邊區為什么有些地方侵犯工商業較重,而有些地方侵犯較輕。晉綏邊區行署在總結中指出:“(土改中)產生的錯誤,主要是由領導上負責,而各個地區所產生的影響不完全相同。”[注]晉綏邊區行署:《關于糾正執行工商業政策中幾個錯誤問題的指示》(1948年2月1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220-13-452。正如李井泉在給毛澤東關于糾正晉綏土改“左”傾錯誤情況的報告中提到的:“有較強骨干的地方,錯誤較少,改正較快,否則錯誤較大。”[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136頁。為此,在糾偏后,為進一步貫徹中共的工商業政策,晉綏邊區行署強調:“宣傳黨的政策時……必須事先很好地教育干部。”[注]晉綏邊區行署:《關于糾正執行工商業政策中幾個錯誤問題的指示》(1948年2月1日),山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A220-13-452。而土改、整黨、工商業、城市等政策有關文件亦被作為邊區在職干部學習計劃的重點講授內容。[注]參見《邊區一級在職干部學習計劃》,《晉綏日報》1948年9月30日。可見,基層干部的素質對于上層政策能否正確執行進而私營工商業者的心態能否成功轉變,是至關重要的。
當然,土改時期私營工商業者利益被侵犯的原因是復雜的,本文只是從一個視角進行分析。正如有的權威著作所指出的:“這些‘左’的偏向的發生,有黨的政策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更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這時許多干部缺乏進行大規模土改的經驗……放任或者附和農民自發的平均主義要求,因而造成‘左’的偏向。”[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757頁。進一步來看,盡管中共上層政策的模糊和基層干部的素質較低等導致工商業受沖擊,但私營工商業者的心態轉變不僅說明中共在土改期間的糾偏措施是及時的、成功的、贏得人心的,而且折射出中共在面對他們的利益被侵犯的既成事實時進行糾偏的決心和努力。否則,就不會出現眾多私營工商業者的興奮、信任以及大多數外逃商人返回的現象。1948年1月,晉綏分局給毛澤東的關于糾正“左”傾錯誤的報告強調:“分局對于糾正左的錯誤,是堅決的。”毛澤東對該報告的批示是:“你們所采取的方針及步驟是正確的。”[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文件選編(1945—1949年)》,第135—138頁。同年《群眾》周刊刊登的一篇關于保護工商業政策的文章亦說:“今天保護、提倡、幫助、發展工商業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不是一種手段,而是今天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之一。”[注]姜凡:《土改與保護工商業(解放區報導)》,《群眾》1948年第10期。可以說,侵犯私營工商業者利益絕非中共土改的題中應有之義,糾偏也并非權宜之計。糾偏反映了中共面對政策失誤敢于承認、堅決糾正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使中共最終贏得了民心。私營工商業者的心態變遷進一步說明,他們的利益受侵犯的根本原因雖源自中共上層政策的模糊,但這種模糊并非中共有意所為,現實中各種情況亦絕非中共能事先預料。換言之,“黨的政策不完善”[注]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下冊,第757頁。并非有意的不完善,更非動機上的不明確,因為一項成熟政策的形成是需要時間的。事實上,不僅邊區的私營工商業者,就連國統區的大多數工商界人士此時也相信中共將來不會為難自己。[注]參見高華:《歷史學的境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20頁。因此,把保護工商業者的政策視為中共臨時性策略的提法,以及侵犯工商業者是中共有意的制度安排的觀點都值得進一步商榷。[注]參見劉詩古:《國家、農民與“工商業兼地主”:南昌縣土改中的“清算”斗爭》,《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
五、結 語
解放戰爭時期是中共踐行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黨在解放區全面開展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實踐,而土改是重中之重。但就私營工商業者而言,其心態變遷表明解放戰爭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實踐確實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在土改過程中,私營工商業者的內心激蕩及平復反映出上層政策與下層實踐出現的巨大偏差絕不是中共事先能預料到的。其中緣由是復雜的,或由于疏于溝通導致上下級信息不對稱,或由于土改慣性與農民的平均主義傾向導致運動過激、土改中武斷現象頻發,等等。然而,縱觀上述緣由,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上層政策的模糊與基層干部素質較低導致其未能正確把握上層政策的尺度,可能是上述諸多緣由的重要前提。在明確政策、迅速糾偏后,中共亦注意到基層干部素質的問題。事實上,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因黨員干部素質低
下、上級尤其是分區委領導不力導致的上層政策與下層實踐的背離常在黨內文件提及。[注]參見李里峰:《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支部研究——以山東抗日根據地為例》,《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8期。毛澤東曾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6頁。顯然,中共上層政策的清晰、明確與基層干部的自身素質對于助推晉綏邊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至關重要。也許,正是部分基層干部素質低下的現實與中共推行新民主主義經濟實踐的人才需求之間的巨大矛盾促使中共不得不在土改的同時進行干部整改。但由此也不難發現,正是中共擁有面對政策失誤時敢于承認、堅決糾正的優良傳統,才使得土改時中共上層政策與下層執行雖有背離,但很快就能被發現并得以迅速糾正,從而贏得民心。這其中包含的經驗也值得總結和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