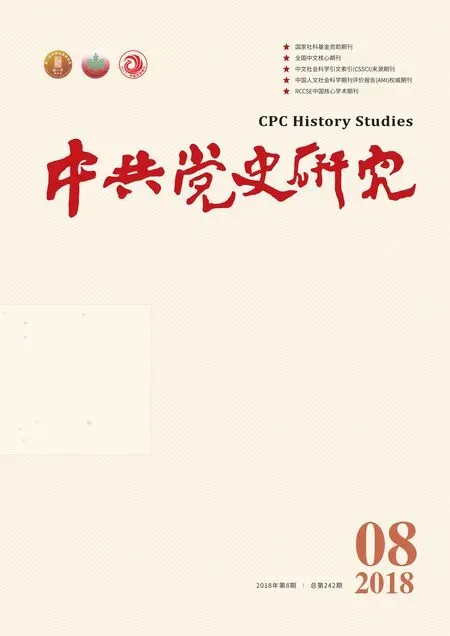中國農村改革是如何率先突破的
蕭 冬 連
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回憶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步階段有兩件事做得很成功,第一是最初幾年把改革的重點放在農業方面,這一改革打破了農業長期停滯的局面,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調整和體制改革起了重要推動作用;第二是加快集體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允許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三資企業的適當成長,很快形成了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格局[注]參見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51—352頁。。這兩件事的成功,使中國改革在國有部門受阻時,卻在非國有部門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突破,由此形成了被稱為“體制外先行”的基本路徑。然而,從歷史過程看,農業改革并不是預先選擇的突破口,它是在較為寬松的政治環境下,農民實踐對政策的突破與地方上開明的領導人相互推動,一步一步獲得共識形成全國性政策的過程,農業改革最能體現中國改革的漸進式特征。而20世紀80年代前期農業超常規增長,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隨后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對中國市場化改革具有全局性意義。
一、包產到戶在大爭論中興起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出臺的農村新政,基本屬于調整的范疇,并沒有把人民公社體制的改革提上日程。它把政策底線劃在維護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之上,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干,不許包產到戶”。然而,政治環境變了。農村新政使農民獲得了過去所沒有的自主權和選擇權,大幅度提高農產品價格又使農民獲得了利益刺激。隨著為地富摘帽,右派改正回城,農業學大寨運動銷聲匿跡,這些信號明白地告訴農民:階級斗爭的時代確實過去,政治上的“緊箍咒”松動了。雖然農民選擇包產到戶還心有余悸,但實際承受的壓力遠不如從前。正是在這種政治環境下,農民敢于不斷突破政策底線。
包產到組是對舊體制的第一波沖擊。1979年春耕之前,全國有多少社隊實行了包產到組,沒有準確的統計。有的省估計有50%,有的省估計有20%。還有一些地方搞了包干到組,如安徽鳳陽縣湖馬公社的10個生產隊搞了包干到組。包產到組保留了生產隊的統一分配,而包干到組取消了生產隊的統一分配,更帶有“分隊”色彩,“三級所有”實質上變成了“四級所有”,因而引起的爭議更大。縣委書記陳庭元得到地委書法王郁昭的支持和省委書記萬里的默許,在鳳陽縣全面推行包干到組。1979年最初的幾個月里,鳳陽就有2556個生產隊分成了9074個小組,實行包干到組,還有202個單干戶[注]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4、215頁。。這個縣的小崗村農民秘密搞起來了包干到戶。由于集體秘密按手印的傳奇色彩,小崗村后來成了農村改革的明星,不過當時并沒有暴露。
少數貧困縣開始搞了包產到戶。1978年夏天,安徽省遭受大旱,秋種無法進行。萬里作出決定: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可以借給社員種麥、種油菜,誰種誰收誰有,國家不征公糧,不派統購任務。[注]楊勛、劉家瑞:《中國農村改革的道路——總體述評與區域實證》,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00頁。肥西縣山南公社首先進行了這種試驗,大大加快了種麥進度,鄰近生產隊相繼仿效。1978年底,肥西縣有800多個生產隊實行了包產到戶。[注]蕭冬連:《崛起與徘徊——十年農村的回顧與前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5頁。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召開常委會討論如何處置山南區的問題,正式決定把山南公社作為包產到戶的試點[注]吳象:《農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歷程》,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23頁。。在中央明令“兩個不許”的情況下,以省委的名義把一個公社定為包產到戶的試點,是需要很大勇氣和膽識的。萬里所依據的思想武器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給出的理由有兩條:一是包產到戶是好是壞要經過試驗,二是小范圍內試驗風險不大。[注]《萬里文選》,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1—122頁。當然,他也在向上尋求支持。1979年6月18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開幕式,會議休息時,萬里到大會主席團對陳云說,安徽一些農村已經搞起了包產到戶,怎么辦?陳云答復:“我雙手贊成”。之后,萬里又找到鄧小平。鄧小平答復:“不要爭論,你就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實事求是干下去。”[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云年譜(1905—1995)》(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280頁。在這里,鄧小平是默許試點,陳云的態度則更加明確。1962年,陳云直接向毛澤東建言,主張在一些地方實行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單干以渡過難關,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因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云贊成包產到戶并不奇怪。
其實,除了安徽,貴州、四川、甘肅、內蒙古、河北、河南、廣東等省、自治區的一些貧困社隊的農民,也或明或暗地搞了包產到戶或類似的包干到戶,地方黨委也并非完全不知情。1978年6月,中共黔南州委給貴州省委的一個報告中就說:“5月底統計,發現分田單干和包產到戶、包產到組、按產計酬的生產隊共1886個,占生產隊總數10.3%。”[注]池必卿、高春生:《貴州全省實行“包干到戶”的前前后后》,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269頁。廣東省海康縣北和公社譚葛大隊南五生產隊1978年就進行了包產到戶的試點,取得豐產。受此鼓舞,1979年譚葛大隊全隊悄悄地搞起了包產到戶。“像北和公社這么早就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后來發現各地都有。”[注]林若:《回憶八十年代初期湛江地區的農村改革》,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310、311頁。1978年,廣東省還采取借冬閑地給社員耕種的辦法,鼓勵社員發展家庭副業,全省借地達80萬畝以上[注]杜瑞芝:《永遠和人民在一起——廣東農村改革歷史性突破的回憶》,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330頁。。1979年3月26日,四川省委辦公廳一份《情況反映》登載,豐都縣有10%左右的生產隊,有的公社有20%至30%的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注]趙文欣:《振興農業的良方——四川農村改革初期的回顧》,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379頁。。1979年上半年發現,甘肅省宕昌縣哈達鋪公社、武威縣的一些社隊,內蒙古托克托縣中灘公社等地,也在搞包產到戶,多數秘而不宣[注]秦其明:《包產到戶的緣起、爭論和發展》,《農業經濟叢刊》1981年第4期。。在河北省大名縣,萬北一隊則早在1977年夏收后就試行包產到戶[注]楊澤江:《談談河北農村的“大包干”》,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412頁。。 “上述事例都因為得到了地方干部的支持而得以記錄下來,實際上,全國各地都有實行分田單干、包任務、包上交的生產隊。”[注]盧邁:《中國農村改革的決策過程》,(香港)《二十一世紀》1998年12月號。
各地農村不同形式的責任制在干部中引起很大爭議。首先引起公開爭論的,還不是包產到戶,而是包產到組即所謂“分隊”問題,因為包產到戶多數還保守著秘密。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甘肅讀者張浩來信并加編者按語,反對包產到組,認為這是解散了集體經濟,指出要穩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能退回去。“張浩來信”在安徽、甘肅、河南等地農村引起波動,肥西縣山南區的試驗不敢搞了,在安徽省委領導人出面支持下才又穩定下來。報社收到500多封來信,大多是批評張浩來信和按語的,也有少數表示支持[注]劉堪:《回顧一九七九年七省農口干部座談會》,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89頁。。3月30日,《人民日報》不得不發表觀點相反的讀者來信和本報記者調查記,力陳包產制的好處,以平息紛爭。
3月12日至24日,國家農委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 參加座談會的有廣東、湖南、四川、江蘇、安徽、河北、吉林七省農村工作部門和安徽全椒、廣東博羅、四川廣漢三縣的負責人(稱為七省三縣座談會)。會議由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主持,專門討論建立健全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圍繞聯產計酬問題進行了熱烈爭論。爭論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實行包工包產到組應當堅持什么原則,二是對包產到戶應采取什么態度。對允許包產到組比較容易地達成了共識,爭論大的是包產到戶。來自地方的與會者贊成包產到戶的占多數,而國家農委主要領導強調集體經濟特別是統一調配勞動力的優越性。20日,華國鋒到會講話,以洞庭湖區農業生產的經驗,來證明分工協作的必要性和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出發點在于鞏固集體經濟制度[注]劉堪:《回顧一九七九年七省農口干部座談會》,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87、88頁。。但他的語氣是和緩的,論證也是經驗性的,并未強調意識形態。這就有了討論的余地,既然可以拿經驗證明集體化的優越性,也可以拿出更多的經驗事實證明包產到組之類責任制的優越性。與會者達成妥協,對于群眾搞了包產到戶“不要勉強去糾正,更不能搞批判斗爭”。最后,華國鋒同意“深山、偏僻地區的獨門獨戶,實行包產到戶,也應當許可”。[注]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6頁。4月3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農委黨組上報的會議紀要。一方面指出,包產到戶“本質上和分田單干沒有多少差別,所以是一種倒退。搞了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的地方,要積極引導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另一方面把“不勉強糾正”“獨門獨戶”的話寫進了會議紀要。會后,各地沒有硬性“糾偏”,沒有人受到批判,一些地方是“你說你的,我做我的”。這個文件并沒有阻止住包產到戶的擴展。1979年下半年,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發展很快,黨內黨外爭論不斷,許多地方出現農民與政府“頂牛”現象。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基本精神仍然是不要搞包產到戶,但把“不許包產到戶”改成了“不要包產到戶”,口氣溫和了。文件規定:“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992頁。這實際上對包產到戶開了一個小口子,一是特殊的副業生產可以搞,二是單家獨戶可以搞。
1980年初,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露出水面。于是從年初開始,全國上下爭論的焦點從包產到組轉到包產到戶。爭論遠遠越出了實行包產到戶的農村地區,從農村到城市,從地方到軍隊,從基層到領導機關,從理論界、新聞傳媒到社會輿論,都在爭論。反對者的理由有兩類。一類來自意識形態,指責包產到戶姓“資”不姓“社”,或擔心它會沖毀集體經濟、滑向資本主義。另一類基于現實的考慮,擔心單家獨戶無法使用大型機械、實現規模經營,將阻礙農業現代化。與以往不同,在各級黨委第一把手中都有包產到戶的支持者,省委書記中以安徽的萬里為代表,還有貴州的池必卿、內蒙古的周惠、甘肅的宋平等,地委書記中有王郁昭(安徽滁縣)、林若(廣東湛江)等,縣委書記中有陳庭元(安徽鳳陽縣)、陳光寶(廣東海康縣)等,公社書記中有湯茂林(安徽肥西山南公社)等,還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字。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王任重重申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杜潤生安排安徽周曰禮在會上作了兩個小時的發言,介紹安徽包產到戶的情況,引起激烈爭論。一部分人把主張包產到戶斥為刮單干風,另一部分人則熱情支持包產到戶,兩種意見爭持不下。1月31日,杜潤生向中央政治局匯報,華國鋒在聽取匯報后講話,重申了他在七省三縣座談會上的意見,強調集體經濟的優勢,要求對搞了包產到戶的“要認真總結經驗,提高群眾覺悟,逐步引導他們組織起來”。李先念也插話說:“總是要堅持集體方向嘛!不管怎樣,把樹砍了,把拖拉機賣了,這是什么方向道路?”最后鄧小平說,對于包產到戶這樣的大問題,事先沒有通氣,思想毫無準備,不好回答。[注]轉引自周曰禮:《家庭承包制是解放思想的產物——農村改革回眸》,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259—260頁;杜瑞芝:《永遠和人民在一起——廣東農村改革歷史性突破的回憶》,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327頁。可見,決策層的主導意見仍然是不贊成包產到戶,但并沒有壓制不同意見。由于兩種意見相距甚遠,中央沒有批轉這次會議的紀要,而是以國家農委名義于3月6日印發。紀要對包產到戶問題講了兩句話,一是從全局說“不要包產到戶”;二是搞了包產到戶的也“不要硬性扭轉”,“更不可搞批判斗爭”[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中國新時期農村的變革·中央卷》(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第86頁。。國家農委希望遏制住包產到戶的蔓延之勢。《農村工作通訊》3月號發表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的文章,提醒大家包產到戶有瓦解集體經濟滑向單干的危險。文章指出:“包產到戶不應作為方向提倡,只要領導稍微放松點,背后的經濟力量就會使它滑向單干的道路上去,最后非沖破集體經濟不可。”包產到戶當然也能增產,但這是多年來集體的積極性沒有發揮的緣故。文章規勸大家把希望放在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積極性上,如果包產到戶,“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體經濟沒有了,基本建設也不搞了,科學種田也搞不起來了,農村的社會主義陣地就被破壞了”。[注]《農村工作通訊》1980年第3期。這是杜潤生在會上講話的修改稿。《農村工作通訊》是國家農委主辦的內部刊物,有相當的官方色彩,而杜潤生又是公認的農業權威,因此被理解為主管部門很強的信號。不過,這并不反映杜潤生的真實態度[注]杜潤生在自述中說:王任重在修改講話稿時把李先念所講“幾千年來都是小農經濟,已經試驗過了還要試驗什么?”的話加到了他的講話中,把原稿中“準許地方試驗”的話刪去了,修改稿未經他校正就拿去發表了。參見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第108頁。。比較準確的判斷可能是,杜潤生不希望大面積蔓延,但主張允許地方試驗。對于包產到戶的看法,此時杜潤生還沒有定型。
面對難以遏制的包產到戶的趨勢,地方黨委的態度各不相同。有些率先支持包產到戶試點的省份出現了反復,如安徽省。1980年2月,萬里調離安徽赴京任職,新任省委書記堅決不主張搞包產到戶,提出“要堅決剎車”,“對越軌的,必要時要采取行政手段”,要以“破壞三個秩序論處”。由于“糾偏”的風是從省委刮下去的,結果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亂,許多地方形成農民與干部“頂牛”。1980年安徽糧食減產共31億斤,減產主要發生在包產到戶動蕩不定的地區。[注]周曰禮:《家庭承包制是解放思想的產物——農村改革回眸》,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261、263頁。
有些省份在與農民激烈地“頂牛”中由反對、猶豫轉向支持、領導,如貴州省。1980年元月,貴州省委通知各地、州、市、縣,再次強調“三不許”。隨后省委派工作組下基層去“糾偏”,各級也紛紛派出工作組。由于認識不一致,有的 “糾偏”認真,甚至采取壓制的辦法;有的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農民要求包產到戶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有的生產大隊農民“罷耕”、上訪,出現僵局。為了穩定農村,保證春耕,省委不得不讓步。3月17日省委決定:“立即停止糾偏”,不要再跟群眾“頂牛”。這一次“頂牛”對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震動很大。他到黔東南州調查了六個縣,感到農村生產關系需要調整。正在這時,得到消息: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長期規劃座談會期間,有四位副總理都提到一些地方可以包產到戶,其中包括了貴州。5月12日到21日,省委召開了9天的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農業政策。7月15日,省委正式發出《關于放寬農業政策的指示》(省委38號文件),其中有這樣的規定:居住分散、生產落后、生活貧困的生產隊可以實行包產到戶;少數連包產到戶也困難的生產隊可以包干到戶。省委作出明文指示,領導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在全國還是首家。
有的地區更帶有農民的自發性特點,如廣東省。在廣東省,農村包產到戶是在省、地、縣政府一次次“糾正單干風”中擴大的。當時的省委主要領導人堅持反對包產到戶,于1980年5月27日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教育引導農民回到社會主義的正軌上來,首先要把分田單干和變相單干的糾正過來。隨后,省委從省直機關調了230名干部,組成調查組分赴惠陽、湛江、梅縣、汕頭、海南5個地區的16個縣,幫助解決所謂分田單干和變相單干的問題。這些調查組發現,廣東一些地區實行所謂分田單干和變相單干的生產隊已經不少,甚至比反映到上面的數字還要大,“單干風”糾一次擴大一次。原因在于最先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普遍增產,產生了強大的示范效應。當然,也有少數地、縣領導干部違背省委的指示,支持和同情農民包產到戶,如湛江地委書記林若、海康縣委書記陳光寶等。其實,其他縣也有這種情況,但多數不敢聲張,怕受到上級批評。湛江地區包產到戶或分田單干的,1979年已有2萬多戶,1980年上半年增加到6萬多戶。按林若的說法,到1980年上半年,包產到戶在全區“即成燎原之勢,到處冒煙”。[注]林若:《回憶八十年代初期湛江地區的農村改革》,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312、314頁。
二、政策是怎么被突破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官員和公開媒體就包產到戶問題激烈爭論的時候,支持包產到戶的聲音開始在最高決策層增強了。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萬里進中央書記處并調任國務院副總理(4月)兼國家農委主任(8月)。這個人事變動加強了支持包產到戶的力量。
春夏之交,中央一些領導人分別到云南、青海、寧夏、陜西、內蒙古、黑龍江、吉林、遼寧等省區和北京市郊區農村作調查,聽取農村干部和農民的意見[注]蕭冬連:《崛起與徘徊——十年農村的回顧與前瞻》,第71頁。。地方的材料也不斷反映到中央。在夏種夏收的大忙季節,一些縣社在包產到戶問題上仍在變動,有的在繼續擴大,有的布置立即糾正,致使這些地方人心不穩。中央決策層不能不有一個明確的態度和統一的說法,以盡快穩定人心,穩定農村的混亂局面。[注]參見《中國新時期農村的變革·中央卷》(上),第93頁。
1980年4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萬里、姚依林、鄧力群談長期規劃問題。姚依林提出,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拿農業來說,有些省份,中央調給他們的糧食很多,如甘肅、內蒙古、貴州、云南,這是國家很大的負擔。可不可以考慮,對這些調進糧多的地區,在政策上搞得寬一點,讓他們自己想辦法多生產糧食,減少國家調入,逐步做到自給。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政策要更放寬一些,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讓他們多想辦法,減輕國家背得很重的包袱。姚依林是從甩掉國家財政包袱出發,提出索性讓貧困地區農民包產到戶自謀生計的想法的。鄧小平贊成姚依林的意見,表示:對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生活窮困的地區,政策要放寬,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給組,有的可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農業問題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資,還是多從政策上考慮問題。[注]參見池必卿、高春生:《貴州全省實行“包干到戶”的前前后后》,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281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615—616頁。這是鄧小平就包產到戶問題作的第一次表態。在鄧小平看來,農業問題的解決主要不能靠國家投資,而是靠放寬政策,包括可以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找門路”。
5月31日,鄧小平與胡喬木、鄧力群談話。他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5、316頁。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促使鄧小平對包產到戶明確表態,最主要的是這樣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包產到戶收到了普遍增產增收的效果。不過這時,他還是把包產到戶當作一種局部地區短期內的權宜之計,沒有想到包產到戶將是農村普遍的長期實行的政策體制。
鄧小平的表態,使本來就已有包產到戶的安徽、云南、貴州、甘肅、內蒙古等省區更加放開了膽子。到夏天,安徽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發展到30%,貴州發展到50%,甘肅和內蒙古至少有20%[注]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第232頁。。云南也占到1/3[注]池必卿、高春生:《貴州全省實行“包干到戶”的前前后后》,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295頁。。有些猶豫遲疑的省區如陜西、四川、江西、新疆、河南等也紛紛開了口子。
然而,鄧小平的談話并沒有“一錘定音”,有些省仍然堅持反對開口子,如吉林、黑龍江和江蘇等省。不過反對的理由不是意識形態方面的,而是現實的。吉林省人口2100萬,面積卻有18萬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達四五畝,有的縣高達七八畝(全國僅為1.8畝),人均有糧850斤,溫飽問題已經解決。因此,吉林省委領導人把發展農業的希望寄予發展集體經濟和實現農業機械化。黑龍江農業機械化有較大發展。114個大型國營農牧場已經實現了機械化。農村人民公社的田間作業50%實現了機械化。黑龍江省寄希望于機械化大生產,反對劃小耕地,包產到戶。江蘇省社隊企業較發達,1978年江蘇省社隊企業的收入已占人民公社三級經濟總收入的43%[注]袁養和、華惠毅:《江蘇調整社隊企業立足發展》,《人民日報》1979年10月11日。,擔心集體土地和生產資料的分配會導致社隊企業財產損失[注]盧邁:《中國農村改革的決策過程》,(香港)《二十一世紀》1998年12月號。。
6月19日,趙紫陽就農村政策問題給萬里和胡耀邦寫了一封信,隨即發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他談了自己的三點看法:第一,在那些困難、落后的地方,可以包產到戶;第二,在那些生產比較正常、集體經濟搞得比較好的地區,原則上不搞包產到戶;第三,現在有些集體經濟搞得比較好的地方也搞了包產到戶的,允許進行試驗,經過一段實踐看看結果如何。[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2頁。開的口子是可以在10%的貧困地區實行包產到戶。六七月間,國家農委組織調查組分赴西北、西南、中南和內蒙古等十幾個省區進行調查,調查的中心問題是包產到戶。大量調查來的材料使大家得到一個共識:在長期落后貧困的社隊,包產到戶經濟效果最顯著,可以迅速改變面貌。[注]吳象:《陽關道與獨木橋——試談包產到戶的由來、利弊、性質和前景》,《人民日報》1980年11月5日。胡耀邦在7月11日至12日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中央不反對搞包產到戶。”“我們不要把包產到戶同單干混為一談,即使是單干,也不能把它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不要一提到單干就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說單干就等于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我國目前條件下,單干戶,也就是個體所有制的農民,已不同于舊社會的小農經濟,它同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是密切聯系著的,他本身沒有剝削,在一般情況下,不會發展到資本主義。不要自己嚇自己。”[注]轉引自吳象:《胡耀邦與萬里在農村改革中》,《炎黃春秋》2001年第7期。9月14日至22日,胡耀邦主持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包產到戶問題。據吳象說,這個會是萬里建議胡耀邦開的。“中國的事情特別是農村的事情,省委一把手不贊成的話,不好辦,辦不了。”[注]蕭冬連對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象的訪談,2008年5月9日、5月21日、7月16日。
會議開始時,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受中央委托,作了一個專題報告,對國家農委起草的“代擬稿”作說明。胡耀邦、萬里、習仲勛等有一個一致的意見,就是不搞“一刀切”,不給政治壓力。在會上,爭論仍然很大。表態反對的占多數,明確支持的有貴州池必卿、廣東任仲夷、內蒙古周惠。最有名的故事是貴州的池必卿與黑龍江的楊易辰的“口頭協定”。楊易辰堅決不同意包產到戶。他在會上插話說,反正這個東西在黑龍江行不通,至于貴州等地怎么樣,那我們管不了。休會時,池必卿找楊易辰個別談話,說我們可否達成協議: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互不干預?楊易辰答道:好的,可以。池必卿在第二天會上的發言,談到了他同楊易辰達成的口頭協定,并上了會議簡報,因而“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傳為佳話。[注]參見池必卿、高春生:《貴州全省實行“包干到戶”的前前后后》,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295—296頁;吳象:《陽關道與獨木橋——試談包產到戶的由來、利弊、性質和前景》,《人民日報》1980年11月5日。會議通過了題為《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幾個問題》的會議紀要,9月27日印發全黨(中發〔1980年〕第75號。以下簡稱“75號文件”)。“75號文件”充滿了兩種對立意見折中的痕跡。但文件修改得各派都擁護,很不容易,因為對各派都沒有限制。[注]轉引自《國家農委負責人1980年10月17日講話記錄》,解放軍政治學院《形勢教育參考材料》1980年第9 期。
“75號文件”最重要的突破,是承認了少數地區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合法性。文件指出:“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這是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么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并不可怕”。“75號文件”提出“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的方針:在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地區,長期“三靠”的生產隊,群眾要求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并在一個較長時間內保持穩定;在一般地區,集體經濟比較穩定,生產有所發展,就不要包產到戶;已經實行包產到戶的,群眾不要求改變,應該允許繼續實行。文件特別強調要做好約占50%以上的“屬于中間狀態的社隊”的穩定工作。“75號文件”特別推薦一種聯產計酬責任制,就是專業承包。當時的指導思想就是既要充分發揮個人承包的積極性,又不至回到小而全的一家一戶的小農自然經濟。但這個想法并沒有實現,因為脫離了實際,多數農村并沒有明顯的分工分業。
三、覆蓋全國農村的大變革
“75號文件”雖然作了一些松動,但并不認為包產到戶或包干到戶是全國普遍適用的形式,希望把雙包到戶控制在占生產隊總數20%左右的范圍內,對于包產到戶的性質也沒有作明確的規定。此后,中央工作的著眼點放在如何穩住占50%至60%左右的中間社隊。對于這部分地區,中央特別推薦了“統一經營,聯產到勞”的生產責任制,認為這種形式“既保持了集體經濟統一經營的優勢,又吸收了包產到戶發揮個人積極性的好處”。而占生產隊25%左右的先進社隊,則適用“專業承包,聯產計酬”的責任制。[注]杜潤生:《關于農村經濟政策問題的一些意見》,《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冊,第1082頁。多數地方領導者都在做著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解釋少數地區包產到戶的合法性,以穩定人心;另一方面是努力將包產到戶限定在這20%左右的“貧困地區”,穩住占70%以上的一般地區。
1981年,各種形式的聯產承包制都有發展,但發展最快的是包產到戶。一是突破了原來只在邊遠山區和長期貧困落后地區實行的設想,幾乎不可阻擋地向更大范圍發展。二是包產到戶本身大部分又發展成為包干到戶,就是“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農民也沒有接受中央推薦的專業承包責任制,普遍采取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辦法。為了進一步解決不同地區農村的生產責任制問題,1981年1月1日至8日,趙紫陽到鄂、豫、皖三省的宜昌、荊州(重災區)、南陽、開封和菏澤五個專區考察農村情況,杜潤生等隨行。一路聽到的都是好消息,農村情況比城市好,原來困難落后的地區尤其好。農民普遍要求,允許再搞三年包產到戶,趙紫陽當即表示可以答應。趙紫陽雖然沒有改變把包產到戶作為權宜之計的看法,但內心感到對這個問題要重新加以認識。回到北京后,趙紫陽對國務院干部們說,群眾的呼聲要好好聽一聽。[注]轉引自《國家農委負責人朱榮在政治學院的報告》,《形勢教育參考材料》1981年第3期。趙紫陽把這次所見所聞告訴了鄧小平、胡耀邦等人,并以杜潤生的名義寫了一份《關于農村經濟政策問題的一些意見》的報告。農民為什么要求包產到戶?杜潤生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解釋說,除了能增產吃飽肚子外,包產到戶對農民的吸引力還有兩條:一是可以自己作主了,二是自由了。農民說:“過去愁著沒飯吃,現在愁著糧食沒處放,再不用出門要飯了。”“聯產聯住心,一年大翻身。紅薯換蒸饃,光棍娶老婆。”他們說:“二十多年了,可熬到自己能當家了”。現在是“既有自由,又能使上勁”。“戲沒少看,集沒少趕,親戚沒少串,活沒少干,糧沒少收。”198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將杜潤生的報告轉發全國。中央領導人的考慮是:既要對各地實踐有所指導和規范,又要保持政策有較多彈性。中央辦公廳的批語,也只是要求各地“作為處理當前出現的一些農村經濟政策問題的參考”。[注]《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冊,第1079、1078頁。
趙紫陽總結沿途所見所聞,提出了全國三類不同地區可以采取三種不同的形式:好的地區實行“專業承包、聯產計酬”;中間狀態地區實行“統一經營、聯產到勞”;困難落后地區搞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然而在實踐中,這種“切三刀”的辦法也沒有阻擋住包產到戶向中心地區發展。只要不是硬性“糾偏”,與農民“頂牛”,農民的選擇總是一步到位: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山西是一個起步較晚卻發展迅速的省份。1981年初,山西省委組織各級領導干部到農村作調查,了解民情民意。全省組織了1萬多名干部下鄉調查,寫出調查報告和典型材料3000多份,省委常委平均下鄉58天。在機關爭論不休的問題,下鄉調查后很快達成了共識。[注]王庭棟:《回憶農村改革的初期》,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385頁。7月7日,省委召開地、市、縣委書記會議,肯定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增產效果顯著。會后,山西境內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就像打開了閘門,一發而不可收。時任山西省副省長霍泛回憶說,當時的形勢“如水之就下,來勢之猛,如狂風驟雨,勢不可擋”。速度之快,完全沒有遵守省委“分批展開,穩步前進”的方針。到1981年底,包干到戶已占到全省12.6萬個核算單位的69%。“農民的積極性一觸即發,全省沸騰,成為一次真實的發自群眾內心的自覺的運動。”[注]霍泛:《從農業合作化到家庭承包責任制》,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71、75、72—73頁。
1981年下半年,全國各地包產到戶的隊已占 32%[注]黃道霞:《五個“中央一號文件”誕生的經過》,《農村研究》1999年第1期。,到1981年底已占50%左右[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中國農村經濟的系統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36頁。。面對迅猛發展的形勢,趙紫陽作了一個原則性指示:“讓群眾自愿選擇,領導上不要硬堵了。”[注]轉引自杜潤生:《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77頁。這基本上等于放手。5月,杜潤生受中央委托專程到河北省邯鄲、邢臺、石家莊、衡水、滄州、保定等地考察,態度更加明朗了。5月22日,他在省直機關講話,告誡大家“不要和群眾頂牛”,“有利有害都由他們自己承擔,我們無權強制,當然也不能放棄領導”[注]杜潤生:《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第43、44、413頁。。6月29日,杜潤生對中共中央黨校的學員說:“包產到戶的發展是一個信號,代表生產力而行動的農民,已經提出了經濟改革的愿望。這是不可違背的社會潮流。”[注]杜潤生:《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第66頁。當時,國家農委的領導層不支持包產到戶的占多數。為轉變觀念,萬里推動農口各部門領導到農村調查,這次下農村調查的有國家農委、農業部、農墾部等農口各部門領導140多人,組成了17個調查組,分赴15個省區,調查了不同類型的地區,各調查組共寫出上百篇調查報告,說他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與在北京想的不一樣。據說過去反對最堅決的也改變了看法。萬里授意把匯報會情況寫成內參發到縣級,并在8月4日的《人民日報》上以《實踐使他們提高了認識》為題公開發表,對全國是一次有力的推動。[注]參見張廣友:《改革風云中的萬里》,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9—287頁。
胡耀邦、萬里等都主張制定新的文件,進一步放寬政策限制。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新任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改革熱情極高,稱農村改革是“一馬當先,方興未艾”[注]轉引自萬里:《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開幕會上的講話》,《中國新時期農村的變革·中央卷》(上),第161頁。。7月31日,胡耀邦在批給萬里的一份《國內動態清樣》上提出:“今年九、十月要再產生個農業問題指示”。此前,萬里也提出:“1980年中央75號文件已被群眾實踐突破,要考慮制訂新的文件。”8月4日,胡耀邦找杜潤生談話,布置文件起草工作,提出文件要寫繼續放寬政策問題。9月上旬,國家農委召開座談會,討論文件的起草問題,安徽、浙江、黑龍江、貴州等省農口負責人和滁縣、嘉興等地區主要負責人參加。10月4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開農村工作會議,討論修改由國家農委主持起草的農村工作新文件。12月21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杜潤生向胡耀邦建議,將文件安排在新年元旦發出,成為新年第一號文件,以引起全黨、全國重視。胡耀邦當即表示贊成。[注]轉引自黃道霞:《五個“中央一號文件”誕生的經過》,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第133、135頁。從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連發五個“一號文件”,以指導農村改革的深入。這是第一個“一號文件”。
與“75號文件”相比,“一號文件”進一步放寬了政策。文件高度評價農村正在出現的大變動,說這是“反映了億萬農民要求按照中國農村的實際狀況來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強烈愿望”,“是一場牽動億萬群眾的深刻而復雜的變革”。“一號文件”肯定了雙包到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提出了兩個“長期不變”的方針:中國農業必須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產資料公有制長期不變;集體經濟要建立生產責任制也長期不變。雙包到戶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明確和兩個“長期不變”方針的提出,基本結束了持續兩年之久的雙包到戶姓“社”姓“資”的爭論。至此,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幾乎完全放開了,到1982年夏季,雙包到戶已在全國74%的生產隊推行。[注]趙華胄、邵永力:《“雙包”責任制是治窮致富的“陽關道”》,《人民日報》1982年8月22日。
雙包到戶的最后發展階段是向全國20%左右的富裕地區發展。從不能包產到戶到少數貧困地區可以包產到戶,再到承認廣大中間地區包產到戶的合法性,這是實踐推動觀念和政策變化的三個階段。最后的疑慮是,在那些機械化程度較高,農民生活較富裕的地區能不能實行雙包到戶?1983年中央一號文件取消了這最后限制,指出聯產承包制“具有廣泛的適應性”,要求林業、牧業、漁業、開發荒山荒水以及其他多種經營方面,都要抓緊建立聯產承包責任制。1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對大包干不要再堵》。在中央精神的鼓舞下,1983年包干到戶形式向更廣闊的領域發展。一是在分工分業較細和機械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普遍建立,他們的主要形式是聯產到勞或聯產到機組。最具有階段性標志意義的是,等待了四年之久的黑龍江省,終于在1983年春在全省全面推開,85%的生產隊落實了家庭聯產承包制。二是雙包到戶責任制從農田擴展到林牧副漁業,從農業擴展到工業、商業、服務業等領域。三是雙包制發展到國營農場,產生了大批家庭農場。1983年底,全國農村雙包到戶的比重已占到生產隊總數97%以上[注]詹武等:《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發展》,《中國農村經濟》1985年第1期。。一場覆蓋全國農村的大變動即告完成,包干到戶取代其他各種形式,成為中國農村主要的經營模式。當然也有例外。據調查,堅持不分田到戶,利用原有集體在土地、人力以及政治資源上的優勢興辦鄉鎮企業而富裕起來的,全國仍有幾千家,有名的如河南南街村、北京竇店村、江蘇華西村、天津大邱莊等,中央政策也不是強求一致。
包產到戶從根本上動搖了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政社分開的行政改革提上日程。早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就有人提出“政社合一”利少弊多,需要改變。此后黨內對“政社合一”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體制的否定意見日益強烈,指出人民公社既是經濟組織又是基層政權組織,容易發生用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產生強迫命令、瞎指揮和“一平二調”“共產風”,集體經濟所有權不可能得到很好的保護。1979年8月以后,在部分地區設了改革“政社合一”“三級所有”體制的試點。試點地區先后有:四川省廣漢、邛崍、新都等縣,吉林省榆樹、懷德、農安縣,甘肅省古浪縣、文縣石坊公社,河北省來城縣都馬公社,浙江省黃巖縣店頭公社,廣東省開平縣金雞公社,遼寧省鐵嶺縣熊官公社,安徽省鳳陽縣考城公社等。1982年11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規定,設立鄉、鎮一級人民政府。1983年1月,中央一號文件正式把實行政社分設作為一項重大改革步驟提出。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各地農村政社分設的工作,爭取在1984年底以前大體完成。到1983年底,全國已有1188個縣的14636個公社實行了政社分設,占原公社總數的27%。1985年6月,全國各地全部完成了政社分設的工作。建鄉前全國共有5.6萬多個人民公社,政社分開后,建立了9.2萬多個鄉、鎮人民政府。實行了26年的人民公社體制模式被終結了。
杜潤生說:“農村改革并沒有一幅事先描繪好的藍圖。它是在農民、基層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領導各個層次、各個方面的互動過程中完成的。”[注]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前言”第1頁。農村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氣候下農民的自我選擇。然而單有農民的選擇,沒有一批領導干部的同情、默許、支持和政策的跟進,農村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全國性的突破。從中央文件看,從“不許分田單干,不許包產到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到允許少數地區包產到戶(1980年9月中央75號文件),再到承認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1982年1月中央一號文件),改革政策步步深入。在農村改革中爭論不斷,反對的聲音很多,但支持者也不在少數,包括中央和地方許多干部。農村改革對增產的顯著效果為自己開辟著道路,既給農民帶來好處,又豐富了城市居民的餐桌,同時滿足了政府足額收購的要求。相對于城市工業,農業是計劃控制較為薄弱的部門。因此,從意識形態上提出的反對意見不足以阻止改革的進程。
四、農村經濟超常增長的諸因素
農村改革贏得廣泛認同,主要原因還在于農業和農村經濟出現了超出預期的增長。1979年至1984年,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8.98%,其中種植業每年平均遞增6.61%,超過新中國成立后30余年間任何一個時期。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間,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3.25%,其中種植業每年平均增長2.59%。60年代帶有恢復性質,農業的年增長率也只達到5.6%,種植業年增長率只有4.86%,遠低于這6年。[注]周其仁等:《發展的主題——中國國民經濟結構的變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頁。糧食產量持續快速增長尤其令人鼓舞,1978年全國糧食產量為30477萬噸,1984年增長到4073l萬噸,平均每年增長1709萬噸,單產提高 40%。人均占有糧食也打破了20多年的徘徊局面,從637斤增加到近800斤。這次糧食總產量的大幅度增加,并不是沿襲過去“以糧為綱”,擴展耕地和擠占其他農作物的播種面積的辦法實現的,相反,是在糧食種植面積大量減少的情況下獲得的。1979年至1984年,糧食種植面積由18億余畝減少到16.9億畝,減少了1.15億畝,平均每年減少近2000萬畝。糧食畝產由 337斤提高到481斤,平均每年增長24斤。這就支持了種植業結構的調整。棉花、油料及其他經濟作物都大幅度增長。棉花總產量從1978年的216.7萬噸增加到 625.8萬噸,6年間增長近2倍,每年增加1300萬擔。油料產量結束了11年徘徊,增長了1倍多。其他經濟作物增長幅度也在50%至300%之間。[注]蕭冬連:《崛起與徘徊——十年農村的回顧與前瞻》,第106—107頁。《周少華工作筆記》,未刊稿,第2043頁。
農村幾年內涌出那么大的活力,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多年來大家感到無法解決的問題,幾年時間就轉過來了,過去糧食那么緊張,到了 1984 年竟然發生了農民有糧賣不出去的問題,國家收購的糧食壓在倉庫里很多。農業的超常增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行無疑起了主要作用。
然而,把農業增長全部歸因于家庭承包制,也是認識上的誤區,其他因素同樣不能忽視。一是農副產品大幅度提價。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總水平1984年比1978年提高53.6%,同期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只上升4.4%,[注]《中國經濟年鑒(1985)》,經濟管理出版社,1985年,第2—15頁。這不僅使農民獲得了直接的經濟利益,更是一種刺激,調動了農民增加農業投入和提高農副產品商品率的積極性。二是減少了統購、派購的數量。過去多少年來農民吃不飽肚子,每年糧食一收下來就交公糧、余糧,這種狀況持續了20多年。三是國家下決心連續幾年進口1300億斤到1500億斤糧食,這意味著城市基本上不吃農村糧。這才有可能減少糧食征購,給農民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這三條一配套,加上家庭承包制改革,農村一下子就搞活了。四是科技和物質投入。70年代興建的17個大型化肥工廠,1979年以后陸續投產,每年生產化肥1000多萬噸;雜交水稻、玉米以及棉花良種的普遍推廣;過去長期的農田水利建設,到1979年,全國共修筑大中小型水庫8.4萬余座,灌溉面積由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約2000萬公傾增加到4500萬公頃,排灌動力機械7122萬馬力,化肥施用量1086萬噸,農村建小型水電站8.3萬余座,農村用電量282億度[注]《中國經濟年鑒(1981)》,經濟管理雜志社,1981年,第VI-12、13頁。《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關于一九七九年國民經濟執行結果的公報》,《人民日報》1980年5月1日。。這讓農民不用擔心單干會發生生產方面的困難。1984年世界銀行報告指出:“從長期擴展農業生產來看,給予農民適當的鼓勵(這是改革的實質),仍將是一個關鍵的環節。然而鼓勵是否有效,則取決于耕地、灌溉用水、肥料和良種等關鍵性的投入物的供應能達到何種程度。”[注]世界銀行1984年經濟考察團:《中國:長期發展的問題和方案(主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第63頁。這個分析是中肯的。改革的推動力是巨大的,但是改革不是點金術,經濟關系的變動不能代替物質投入。
五、農業改革釋放出市場能量
農村改革更具意義的,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釋放出巨大的市場能量。家庭聯產承包后釋放出大量剩余勞動力,據1981年初調查,全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約占農村總勞動力的30%至40%,約1.3億。隨著收入的增長也出現了剩余資金,1983年底農民儲蓄存款已達228億元。這為農民發展多種經營提供了需要和可能。國家統購派購的品種逐步減少,仍然統購派購的農產品實施定基數的方法,在品種和數量兩方面為農村市場的發育留下了空間。只要給農民以經濟自由,農民自然要搞商品經濟。從這個意義說,農民天然具有“自發傾向”。1983年至1984年,農村開始出現許多新的經濟現象,如承包大戶、雇工、長途販運、個人購置農機和農副產品加工機具,私人開辦工商業、農民外出打工等現象。專業戶除了從事農林牧漁業,還有專事工礦業、運輸業、建筑業、商業服務等非農產業。據一份調查材料顯示,后者占到61.9%。[注]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資料室:《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198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21頁。到1983年底,農村個體工商業發展到419.5萬戶,538萬人[注]《中國經濟年鑒(1984)》,經濟管理出版社,1984年,第IV-52頁。。在個體經濟中發展出雇工經營的大戶。據調查,1984年底,雇工經營的戶占專業戶的15.7%,平均每戶雇工4.1個[注]《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1985)》,第23頁。。一些專業大戶雇工人數大大超出平均數。這就觸碰到一個核心問題:社會主義是否允許“剝削”。中央的政策是:允許帶兩個徒弟請五個幫手,但現實很快突破了這個限制,引起很大爭論。
1981年4月,廣東有一個叫陳志雄的,承包了400多畝魚塘,雇用了5個固定工,1000多臨時工。這個承包大戶得到廣東省農委和省領導的支持,這件事在全國引發一場允不允許專業戶雇工及雇工多少、是否是“資本主義剝削”的激烈爭論。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場關于承包魚塘的爭論》,并開辟了專欄展開討論,討論歷時三個月,基調是肯定的。然而,這件事在廣東省內部也爭議很大。有人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登在1982年1月17日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上,引起中央領導人的重視。胡耀邦、萬里、杜潤生都作了批示,沒有明確表態,只是要求調查酌處。另有一位領導給任仲夷寫了一封信,態度很明確地說: “我個人認為,按這個材料所說,就離開了社會主義制度,需要作出明確規定予以制止和糾正并在全省通報。事關農村社會制度的大局,故提醒省委考慮。”萬里見到這封信加了一句話:“此事請調查研究,對農民發展商品經濟的積極性要珍惜和保護,不可輕易用老框框來套。”[注]蕭冬連對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象的訪談,2008年5月9日、5月21日、7月16日。可見,高層意見兩端。
包產到戶后出現的一些新經濟現象,再次引起激烈爭論。引起爭論的主要有兩個東西,一個是長途販運,一個是雇工。1982年4 月,根據國務院領導的意見,國務院農村政策研究室派出七個由杜潤生等農口主要負責人率領的調查組,分赴山東、安徽 、江蘇、四川 、廣東、廣西、河北 、山西、遼寧、吉林等地調查,隨后召開了五次農村經濟政策研討會,主要研究包產到戶后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起草新的農村文件。會上爭論熱烈,重點在于如何對待雇工和長途販運,實質是允許不允許農民私營經濟的發展。杜潤生先后向胡耀邦等同志匯報了調查和研討會的情況,提出進一步放寬政策,得到他們的支持。[注]參見黃道霞:《五個“中央一號文件”誕生的經過》,《農村研究》1999年第1期。
包產到戶以后,農副產品大幅增長,卻面臨賣不出去的問題,當時的統購統銷政策和國營渠道逐步批發的體制已經完全不能適應農村的發展,農民長途販運應運而生。按照過去的政策,這就是投機倒把。胡耀邦明確支持農民的行為。針對農民長途販運是“二道販子”的說法,他在1982年8 月10日的批示中說:“不對,是二郎神” ( 解決農村流通困難的“神”)[注]轉引自黃道霞:《五個“中央一號文件”誕生的經過》,《農村研究》1999年第1期。。爭議更大的問題是是否允許雇工。1981年12月,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成員寫了一篇《到處出現雇工剝削引起的思考》,反對以雇工為特征的私人企業。研究室內部對這份報告產生分歧,林子力、吳象將報告送萬里,萬里批調查材料是“左”;胡耀邦說,這是從概念出發;陳云說,黨內有不同意見,是黨興旺發達的標志。鄧力群想召開一次省市委研究室主任會議討論雇工問題,被胡耀邦制止。胡耀邦認為,這樣做會使下面的人感到中央的政策變了。[注]鄧力群:《十二個春秋》,未刊稿,第498—501頁。蕭冬連對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象的訪談,2008年5月9日、5月21日、7月16日。12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討論1983年一號文件時,陳云針對農村雇工限額問題的爭論說:“過去國務院規定最多不超過七個,現在實際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幾個合適,還要看一看。但對這類問題,報紙上不要大張旗鼓地宣傳。”[注]《陳云年譜(1905—1995)》(修訂本)下卷,第364頁。1983 年 1 月12日,鄧小平在找胡耀邦、萬里、姚依林、胡啟立、張勁夫、宋平、杜潤生、朱榮等人談農業問題時指出:農村個別戶雇工,不怕,沖擊不了我們;有什么問題,我們來得及解決,十年、八年解決也來得及;農業搞承包大戶我贊成,現在是放得還不夠;農業文章很多,我們還沒有破題[注]轉引自黃道霞:《五個“中央一號文件”誕生的經過》,《農村研究》1999年第1期。。陳云、鄧小平對待雇工的態度都是不急于取締,看兩三年再說。安徽蕪湖有個年廣久,在街邊以炒賣瓜子謀生,1980年注冊了“傻子瓜子”商標。瓜子生意很火,小作坊很快發展成“大工廠”,雇工100多人。按照傳統的觀點,這就是剝削。1983年底,有人把年廣久雇工的問題反映到上面,安徽省委派專人到蕪湖調查,并寫了一個報告上報中央。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說:“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頁。“看幾年再說”,反映了鄧小平和陳云都抱著試驗的心態。也許是一個策略,以便繞過意識形態障礙。不管哪種情況,都在事實上默認了私人經濟的存在,開啟了私人經濟發展的窗口。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盡管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上爭論不休,農村政策文件的制定者卻高聲呼喚農村商品化時代的到來。究其緣由,在于中央政策必須回應農民的要求,跟進農村的現實。198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農村經濟必須實現兩個轉化,即從自給半自給經濟向較大規模的商品生產轉化,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不過,回避了商品經濟的“經濟”兩個
字,代之以“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說法。為促進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還進一步放寬了政策,其中包括:承認、支持專業戶 (承包專業戶和自營專業戶);允許資金、技術、勞動力一定程度的流動和多種方式的結合;允許農村個體工商戶和種養業的能手,請幫手、帶徒弟和雇用一定數量的雇工;允許農民個人購置大型和中小型拖拉機、汽車、農副產品加工機具和小型機動船;允許農民個人從事商業和運輸業;允許農民個人或合伙進行長途販運;允許農民個人或合股集資興辦農村倉庫、公路、小水電等基礎設施;允許林區適當擴大自留山,扶持育苗造林的專業戶,林木誰種誰有,農民個人所造林木有繼承權。[注]參見《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16—230頁。1984年至1986年的三個中央“一號文件”[注]分別為:《中共中央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一九八六年農村工作的部署》(1986年1月1日)。,政策進一步放寬:允許土地轉包;允許農村社會資金自由流動,鼓勵加入股份制合作,入股分紅;允許農民購買大型生產資料;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城鎮做工、經商、辦企業;鼓勵農戶個體和聯合辦企業,對雇工經營不急于限制。所有這些,目標就是放活商品和要素流通,推動農村經濟向大規模商品化生產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