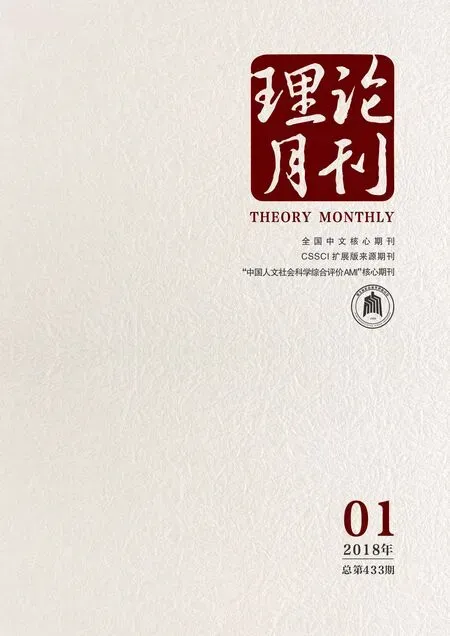從數字式脫貧到發展式脫貧:一個省級貧困鄉的貧困治理邏輯分析
□盧艷齊
(武漢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一、引言
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而貧困則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阻礙。2014年初中央制定了精準扶貧戰略,具體是指“通過對貧困戶和貧困村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引導各類扶貧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扶貧到村到戶”[1]152,這為當下中國的扶貧開發指明了新的道路。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明確提出“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2]的脫貧戰略目標,將精準扶貧戰略轉變為精準脫貧戰略。
精準扶貧實施以來我國的扶貧工作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仍存在不少問題。挪用扶貧資金,截留扶貧資源,或者“扶農”不“扶貧”等問題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一些偏遠的地區,“越扶越貧”的亂象也時有發生。針對不同的扶貧亂象,學界開展了相關研究。葛志軍(2015)等人關注了地方扶貧實踐中出現的貧困戶參與不足,幫扶政策缺乏差異性和靈活性等問題[3](p157),唐麗霞(2015)指出扶貧政策本身存在制度缺陷[4](p151),邢成舉(2016)指出精準扶貧中財政扶貧目標偏離的情況以及農村貧困轉型對精準扶貧的挑戰等問題[5](p109),劉司可(2016)則研究了精準扶貧工作中貧困退出機制不健全的問題[6](p45),李群峰(2016)分析了村干部權力尋租等瞄準偏離的現象[7](p73),李博(2016)則進一步探討了項目制在扶貧開發中出現的功能式微問題[8](p106)。2017年,學界關于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的文章呈現爆發式增長,據中國知網(CNKI)的數據分析,2017年相關文章數量400余篇,涵蓋的問題更加廣泛且細致。如雷望紅(2017)指出,精準扶貧政策在執行中存在著明顯的不精準執行現象,表現為識別不精準、幫扶不精準、管理不精準和考核不精準等問題[9](p1);朱天義等(2017)認為精準扶貧中鄉鎮政權采取了選擇性的治理行動[10](p212)。不僅如此,由于對精準扶貧的研究呈現多學科交叉分布的特點,不同學科對精準扶貧中出現的問題關注也有不同,例如經濟學關注產業扶貧、金融扶貧(劉建生,2017;謝玉梅,2016)[11](p127)[12](p79),政治學關注貧困戶的政治權益(李洪波,2017)[13](p145),社會學關注精準扶貧中的社會組織力量(黃建,2017)[14](p179)。這些研究對進一步深化學界對精準扶貧戰略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提供了多元化的認知角度,取得豐碩了成果。但是在精準扶貧主體的探討層面,這些研究大多將精準扶貧中出現的問題對準中央國家、縣市一級或者是村莊,卻忽視了鄉鎮一級政府作為精準扶貧主體的重要地位,缺乏對貧困地區鄉鎮政府的扶貧和脫貧能力及其政策執行行為的研究。此外,也很少有學者關注到鄉鎮政府當中的“數字式脫貧”現象。事實上,在壓力型體制下,鄉鎮一級政府處于國家權力末梢,是國家精準扶貧戰略實施的落實者,是多元主體協同治理貧困中的實質性主體和主導,也是整個精準扶貧體系的“最后一公里”。筆者對A鄉的精準扶貧工作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田野調查,認為貧困地區鄉鎮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隱瞞和虛報的“數字式脫貧”現象,但同時為了切實減少和消除貧困,鄉鎮政府又在大力實施“發展式脫貧”政策。此類“貌合神離”的行為所帶來的問題即是為什么鄉鎮政府會在精準扶貧工作中出現隱瞞和虛報的情況?鄉鎮政府又是如何采取改進措施的?其效果如何?本文試圖通過透視當下我國鄉鎮政府精準扶貧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和困境,探索具體治理情境下優化我國精準扶貧戰略實施的改進思路。
二、田野呈現:湖北省A鄉的精準扶貧對策
A鄉位于湖北省C市西南,距市區54公里,屬省級貧困鄉。全鄉總面積56.3平方公里,主要地勢以丘陵為主。A鄉下轄13個村(居)委,92個自然村,123個村民小組,總戶數4822戶,總人口2.13萬人,是一個典型的小鄉鎮。A鄉地理位置偏僻,屬傳統粗放型純農業生產鄉鎮,工業基礎薄弱,外出務工人員高達61.5%,空心化現象十分嚴重。
2015年,全鄉進行了對建檔立卡的戶數和人數進行了摸底排查,最終按照農戶申請、組級評議、組級公示、村級審核、村級公示、鄉鎮復核、村級公告精準識別“七步法”流程和精準扶貧對象識別“十不評”有關要求,確定全鄉精準識別的對象,共有347戶737人被列為精準扶貧對象。根據上級政府精準扶貧工作的總體部署,全鄉計劃5年內每年幫助229人實現脫貧,并力爭到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在對貧困戶進行精準識別的基礎上,A鄉制定了周密的精準幫扶實施方案。為了督促幫扶單位和幫扶干部,A鄉執行了嚴格的考核制度,將扶貧工作的目標任務完成、投入、駐村幫扶情況列入考核目標,實行一季度一督查,一季度一評比,考核結果列入年度科學發展綜合考評,獎優罰劣,并將其作為評優評先、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據。
從A鄉的精準扶貧工作部署來看,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考核等都有明確的文件規定,唯獨缺少精準管理這一項。事實上,精準管理機制的不健全和信息的不透明恰恰給鄉鎮政府數字脫貧留下了可供操作的空間。在A鄉,針對“脫貧任務能否完成?”這個問題,扶貧干部的普遍回答是“肯定能,這個東西就是你說脫貧他就脫貧了”①正文中楷體字部分均為筆者2017年7月至8月底在A鄉進行調研時獲得資料,撰寫的觀察筆記以及訪談記錄,所有人名和地名均做了相關技術處理。。扶貧干部的回答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鄉鎮政府掌握了脫貧的主動權和控制權;第二,精準扶貧對象并不清楚自己的脫貧狀態。精準扶貧主體和對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造成了鄉鎮政府在精準管理上的自由裁量權出現了擴張,使得鄉鎮政府可以在精準扶貧對象不知情的情況下將一些扶貧對象列為已脫貧狀態,自動消除這些扶貧對象的貧困檔案和信息資料,按照這樣一種方式,不論是提早兩年還是三年,都能夠順利實現上級政府的目標和任務。如此一來,便出現了一種欺瞞上級和下級,運用精準管理上的漏洞和缺陷完成脫貧指標任務的“數字式脫貧”現象。
數字式脫貧是貧困地區鄉鎮政府在目標管理責任體制下回應上級政府的一種策略選擇。但是,鄉鎮政府并不能完全依靠數字式脫貧來治理貧困,解決當地的貧困問題,也很難完成最后的驗收工作。因此,鄉鎮政府仍然需要通過實際行動來治理貧困,幫助貧困對象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脫貧。A鄉目前的扶貧方式主要是產業扶貧,主要有東塘村的平菇種植基地、800畝高產油茶種植基地、富民花生油生產合作社;河平村1200畝中藥枳殼子種植園;石竹村的薯粉加工項目和黑美人西瓜苗項目。各村委主動將扶貧對象吸納到產業扶貧項目當中,通過年終分紅的方式幫助部分村民實現脫貧。不僅如此,在2016年6月,換屆選舉之后新任領導干部通過多方渠道又為A鄉拉來了高達3千萬的扶貧項目,分別是3600畝的坡耕地改造項目、扶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以及立體生態旅游項目,與現行的短、平、快扶貧項目相比,這些新項目很難在短期內實現創收,需要通過較長時間的成本投入才能順利回本增收。時間長、創收慢,A鄉的扶貧方式不能幫助當地政府實現2020年全面脫貧的目標,因而并非針對上級政府下達的政治任務,A鄉的扶貧選擇是通過振興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來帶動全鄉農民增收,實現整體性的脫貧,也即是一種發展式脫貧。
三、數字式脫貧:鄉鎮政府精準扶貧工作中的主要問題
從粗放扶貧到精準扶貧,由“大水漫灌”轉為“滴灌”,“輸血”轉為“造血”,國家的扶貧戰略不斷優化和改善,這一政策過程的價值取向是促使改革成果在更廣范圍共享,而其目標則是實現社會主義國家的全面脫貧。放眼全國,一場場脫貧攻堅戰正在打響,舉國上下為了實現脫貧目標而奮力作為。在此形勢下,中央與貧困情況嚴重的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簽訂了扶貧攻堅“軍令狀”,試圖以“軍令狀”的方式來推動扶貧攻堅工作。周黎安(2014)在將行政發包制與“政治錦標賽”結合進行分析時指出,“行政發包和晉升競爭在多層級同時進行意味著縱向層級間會產生一些有趣的博弈互動”[15](p39),其導致的結果便是經濟指標從中央、省、市至縣的“層層加碼”現象,而在脫貧任務的具體情境中,這一結果則表現為脫貧時間的不斷提前。湖北省設定的全省脫貧時間是2020年,大部分縣市的脫貧時間和省里保持一致,也有少部分縣市在此基礎上將脫貧的時間又提早了2年,定為2018年。“層層加碼”之下的橫向競爭無疑加重了地方政府的扶貧任務,在壓力型體制下,這個扶貧重擔又通過權力加壓和任務傳導的方式交給了鄉鎮一級政府,而實際上,鄉鎮一級政府卻處于貧困治理的重重困境之中。
(一)鄉鎮政府的精準扶貧之困
1.目標之困:艱巨的脫貧任務
2016年3月A鄉出臺了精準幫扶的實施方案,文件指出,“緊緊圍繞2020年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按照市委、市政府精準扶貧工作的總體部署,動員和組織全鄉力量與貧困戶結對幫扶,力爭通過2—3年的努力,全鄉基本消除絕對貧困現象,以村組為單元的區域性貧困現象徹底消除。”根據部署,全鄉確定了幫扶時間安排,2016年3月15日至2016年3月20日為宣傳動員階段,2016年3月21日至2016年3月31日為聯系結對階段,2016年4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為開展幫扶工作階段。同時,全鄉制定了詳細的結對幫扶安排表,通過“幫扶單位—幫扶企業—幫扶工作隊長—幫扶鄉干部—幫扶村干部”五級聯動的方式,將任務落實到每一個工作崗位上,細化到每一個鄉干部身上。2014年4月A鄉又相繼下發了精準扶貧結對幫扶工作職責的通知,以及幫扶工作考核指標體系的相關規定,進一步明確了鄉干部與所掛點村(居)委年終考核結果實行同獎同罰的考核獎懲機制。
韋伯(1997)在闡述科層制的特征時指出,為了實現組織目標,組織常常“把為實現組織的目標所必須的日常工作,作為正式的職責分配到每個工作崗位”[16](p213),而科層制的發展與再發展恰恰是當下中國政府所實行的目標管理責任制。作為政治組織形式的各級政府,為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預定目標與任務,各級政府之間、各政府組織內部及其單位與個人之間,制定了相應的目標及達到目標的計劃、獎勵乃至處罰措施,在貧困治理的工作中,實際上采用的管理方式仍是目標管理責任制。關于目標管理責任制,王漢生(2009)等人肯定地認為,“作為一種實踐性的制度體系,目標責任制在上下級政府權威關系的基礎上,引入了一種更具平等意涵的‘責任—利益連帶’關系,從而在實際上創造出一種少見的政府間全面競爭的機制,推動地方經濟發展與維持社會秩序兩個基本目標以及推動地方政府改革與創新模式先行”[17](p89),海外學者高杰(2015)等人則認為“目標責任制的獨特設計,即自上而下分解下達的結果導向型的指標與高激勵機制的結合,為惡性博弈的產生提供了溫床”[18](p635)。事實上,目標管理責任制運行中有兩個核心要素,一是指標體系,二是考核方式,而兩個核心要素最終都落實為“數字化管理”,以便于進行簡單管理和高效監控。在貧困治理中,當數字化的管理方式遇到以結果導向型的指標體系,二者的結合催生的便是數字式脫貧的亂象。
A鄉5年扶貧工作中都是一個量化的任務指標,那就是每年幫助229人實現脫貧。但是實際上,就目前A鄉扶貧項目的數量和質量來看,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以A鄉最大的扶貧項目高產油茶種植基地為例,800畝的高產油茶,以1000元每畝的價格計算,每年盈利80萬,能夠幫助東塘村委9戶精準扶貧對象脫貧,而東塘村委的貧困戶數是51戶,這就意味著需要6年時間才能實現全面脫貧。由此,在目標管理責任制下,面對時間緊、任務重的形勢,鄉鎮政府在貧困治理的明線上采取了“數字式脫貧”的方式,以應對上級政府的考核和任務審查。
2.能力之困:弱化的貧困治理能力
貧困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消除或減輕貧困的過程是國家實現經濟發展、減輕貧困雙重目標的過程,也是一個國家治理的過程。治理理論中的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過程中,并非只有政府一個主體,還包括非政府組織、私人機構、公民個人等多元決策中心[19](p47)。然而,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治理貧困的經驗則表明,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是以政府為主導的貧困治理體制。林閩鋼(2008)指出,“政府主導型”的貧困治理形成了以政府為主的自上而下的動員結構和機制,這一結構和機制在多年的扶貧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也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如扶貧效率問題、貧困人口的“等、靠、要”被動扶貧現象[20](p51)。同時,在壓力型體制的作用下,直接肩負脫貧重擔的實質性主體是以鄉鎮為中心的基層政府。由于級別和權力層次的限制,除非上級政府主動要求,基層政府特別是鄉鎮政府很難參與到上級政府的政策過程中去,由此一來,鄉鎮政府有執行決策的義務卻沒有參與政策制定的權利。同樣的,在貧困治理中鄉鎮政府必須毫無偏差的執行扶貧政策,完成脫貧任務。
近些年來,國家正在逐步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構建多元化的貧困治理主體,通過充分動員發達地區各級黨政機關、民主黨派、社會團體、民間組織、私營企業和志愿者個人共同參與來解決貧困問題。A鄉在精準幫扶方式中也提到要實行鄉村干部結對幫扶全覆蓋,鄉屬及駐鄉單位結對幫扶全覆蓋,企業員工、農村能人(大戶)、社會組織及社會愛心人士結對幫扶貧困戶全覆蓋的幫扶措施,充分利用社會力量來推動全鄉脫貧目標的實現。然而在實際中,這種多元貧困治理主體的構建卻出現了目標偏離的現象。在同一份文件中,A鄉又明確指出鄉黨委、政府,村黨支部、村委是精準扶貧攻堅的責任主體。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社會力量往往“出工不出力”。主管扶貧工作的鄉干部指出,“市委市政府給鄉里安排了相關幫扶單位,卻很少看到這些單位下來協助我們的扶貧工作;還給省級貧困村東塘村配置了扶貧第一書記,但他來了之后給了1萬元就沒再管這件事。”還有平菇種植基地的幫扶單位C市某職業技術學院,在將相關技術和資料轉交給鄉里之后也沒有再來過。顯然,A鄉的遭遇使得鄉政府只能通過自身力量來治理貧困,而A鄉又是一個省級貧困鄉,治理資源和能力方面都處于嚴重匱乏狀態。
周飛舟(2006)通過對稅費改革過程中政府間財政關系的考察,發現過去一直依靠從農村收取稅費維持運轉的基層政府正在變為依靠上級轉移支付,基層政權從過去的汲取型變為與農民關系更為松散的“懸浮型”[21](p1)。賀雪峰(2008)則進一步指出,稅費改革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也加劇了基層政權的財政困境,削弱了基層政權的治理能力,基層政權在無法做壞事的同時,也喪失了為農民提供公共服務的動力[22](p168)。學界的共識是,治理能力是反貧困過程中的關鍵因素,而一個懸浮型政權一方面來面對上級政府的脫貧任務,另一方面又要面對底層民眾的脫貧訴求,其自身貧困治理能力不足的現狀迫使鄉鎮政府做出一種基于“有限理性”的選擇,這便是通過脫貧數字上的變動暫時性的擺脫困境。
3.對象之困:“精英俘獲”下的鄉村
2006年國家稅費改革之后,國家的資金大部分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到達基層,向上要錢成為鄉鎮政府獲取運轉資金的主要來源。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分稅制改革的完成,國家的各項財政資金逐步通過“專項”和“項目”的方式向下分配,并慢慢成為一種主要的財政支出方式。作為一種國家治理的重要方式,項目制是指政府運作的一種特定形式,即在財政體制的常規分配渠道和規模之外,按照中央政府的意圖,自上而下以專項化資金方式進行資源配套的制度安排[23](p82)。項目制形成后,便在中國落地生根,并不斷下沉最終進入了鄉村社會,這便有了項目下鄉一說,而稅費改革與項目制下鄉的合成,使得當前基層政府的貧困治理需要通過依靠項目的爭取和運作實現脫貧。
在鄉鎮政府陷入財政困境的情況下,項目制下鄉為貧困治理提供了一條主要的“財路”。然而在實際中,項目制的運作導致國家的扶貧資源出現被村莊精英截留的現象,不僅被精英村莊俘獲也被精英人物俘獲。首先是被精英村莊俘獲。A鄉的12個村(居)委有兩個是省級貧困村,根據省里的財政安排,兩個省級貧困村每年各能獲得20萬元的資金扶持,但這筆資金用來發展產業扶貧卻遠遠不夠。為了向上爭取更多的資金扶持,東塘村和河平村主動通過各自的權力關系網絡,不斷到市里和省里爭取項目,在鄉政府的努力和配合下,東塘村和河平村分別爭取到了3個競爭性扶貧項目,共獲得扶貧資金300多萬。而在其他村委,由于缺少關系沒有門路,只能等著上面的一些非競爭性項目,陷入極為被動的境地。這種緣起于村莊整體能力而導致的項目配置不均衡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村莊之間的差距,導致一些邊緣化的村莊長期不具備脫貧能力。其次是被精英人物俘獲。項目爭取下來后,根據2015年1月實施的村財鄉代理制度的相關規定,村里的項目資金統一交由鄉財政所代管,但項目的運作權卻委托給了村委,具體則是由村支書等村莊能人來打理。這些擔任村干部的精英人物本身就有著銜接扶貧項目的明顯優勢,而且由于他們在跑項目的過程中立下了功勞贏得了鄉政府的信任和尊重,因而精英人物掌握了扶貧資源的配置權和實施權,這也為精英人物截留扶貧資源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市場化程度加深,農村社會階層出現分化,精英階層通過與鄉鎮政府的利益連接進入村委,實際掌控了村莊兩委,加之城鎮化從農村帶走了數量可觀的勞動力,留守農村的“386199”部隊難以對村莊能人形成有力的監督和約束,鄉村治理內卷化[24](p86)趨勢加強。不論是精英村莊俘獲還是精英人物俘獲,扶貧資源在“贏利型經紀人”的把持和操控之下,通過精準扶貧的第一道關卡——精準識別就有計劃的流入到了少數人手中,而一些真正的貧困對象則被排斥在外。因而,項目制下鄉過程中出現的精英俘獲現象這事實上加大了鄉鎮政府脫貧的難度和準確度,為鄉鎮政府實現全面脫貧目標埋下了隱患。
(二)數字式脫貧的生成條件和隱患
1.數字式脫貧的生成條件
鄉鎮政府一方面陷入貧困治理的重重困境之中,另一方面又要完成超越實際貧困治理能力的脫貧任務,2020年前幫助全鄉347戶737人實現脫貧所面臨的挑戰不可謂不艱巨。為了按期完成這項硬性的指標任務,A鄉采取了數字式脫貧的治理對策,即利用精準管理上的漏洞通過數字上的變更來實現脫貧目標。但是這項對策的實施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通過上級政府的檢查;二是消除扶貧對象的疑慮。第一個條件不難滿足,這可以通過基層政府間的“共謀現象”得到解釋,但貧困治理中“共謀現象”的發生,正如周雪光(2008)所說“不能簡單地歸咎于政府官員或執行人員的素質或能力。共謀行為的產生和重復再生是政府組織結構和制度環境的產物,是現行組織制度中決策過程與執行過程分離所導致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近年來政府制度設計、特別是集權決策過程和激勵機制強化所導致的非預期結果”[25](p1)。重要的是如何消除扶貧對象的疑慮。筆者曾隨扶貧干部到新樓村完成脫貧對象的圖像采集工作,貧困戶對自己低保資格被取消一事進行了利益訴求,鄉干部的解釋是“我們也沒辦法,這是上面的政策,實在困難的鄉里會想辦法幫你們申請其他補貼”。上面的政策是什么樣的,貧困戶并不知情,利用信息不對稱來化解扶貧對象的疑慮,可以說是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無奈之舉,但也暴露了鄉鎮政府刻意逃避責任的缺陷。
2.數字式脫貧的隱患
不論其初衷如何,以數字式脫貧來應對上級政府的目標和任務最終將會產生巨大的負面效果。從國家層面來看,數字式脫貧通過隱瞞和虛報的行徑將會對我國貧困治理的整體進程產生阻礙作用,由于中央政府難以把握地方精準扶貧的準確信息,在政策制定中必然出現偏差,導致全面性的不良影響。從基層政府層面來看,數字式脫貧雖然在一定時期內能夠幫助地方順利通過上級驗收,完成目標和任務,但是從長遠來看它無法實質性解決貧困問題,將對國家的合法性基礎產生消解作用。如果扶貧沒有扶到根上,貧困問題就將繼續困擾國家和地方政府。從精準扶貧對象層面來看,數字式脫貧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是貧困戶在脫貧之后迅速返貧,降低農民對政府的政治信任,從而進一步激化基層的矛盾糾紛,由此引發基層社會的動蕩和不穩定。2015年中央將精準扶貧戰略上升到精準脫貧戰略,再一次重申和明確了脫貧的目標和任務,雖然有學者認為“精準脫貧意在通過一系列的脫貧機制使貧困者具有自主脫貧的能力”[26](p7),但是在當前的治理情境下,不論是政府主導還是多元主體協同的治理格局,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仍是精準脫貧的實質性主體,提升貧困人口的脫貧能力首先還是要提升基層政府的脫貧能力。
四、發展式脫貧:精準扶貧工作改進思路初探
數字式脫貧展現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中國式情境下基層政府的策略思維,但是這種方式無法為基層官員贏得實質性的晉升籌碼,也無法解決貧困的本質問題。無論采取什么樣的應對策略,最終還是要回到精準扶貧的根本目標——精準脫貧上來。為了實質性解決貧困問題,A鄉緊鑼密鼓的探索了相關改進思路,確定了以精準扶貧之名行經濟發展之事的發展式脫貧道路,這既是一種貧困治理思維的轉變也是一種精準扶貧的差異化選擇。作為一種有別于標準化脫貧道路的差異化選擇,發展式脫貧在當前嚴峻和緊迫的脫貧形勢下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同時也不乏一些不足和缺陷。
(一)發展式脫貧的生成機制
1.精準扶貧與經濟發展的“互嵌”
在精準扶貧戰略實施以前,鄉鎮政府的主要任務一是發展二是維穩,自從精準扶貧這項民生工程正式下達到基層以后,鄉鎮政府的工作重點向扶貧轉移,地方經濟發展退居次要地位,A鄉同樣如此。然而,A鄉面臨的實際情況卻是:貧困治理能力不足、經濟發展上不去、地方維穩工作有條不紊。負責綜治工作的黨委委員總結當地的維穩工作時說,“近20年來,我鄉綜治情況保持良好,沒有出現進京上訪事件,沒有出現重特大刑事案件,沒有發生民轉刑事件,沒有出現宗族械斗事件,沒有發生需要專門力量參與的涉訪涉穩事件,沒有出現刑滿釋放人員重新犯罪的案件。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矛盾糾紛不上高(法院),涉穩問題不越級上訪。”在實際調查中筆者也發現,當地民風淳樸,無論多大的矛盾糾紛群眾首先想到的是鄉政府,政治威信的樹立消解了A鄉的維穩難題,因此維穩問題并不在鄉政府的重點工作當中。作為一個經濟排名墊底的邊遠鄉鎮,A鄉面臨的最大問題仍然是發展。2015年正式實施精準扶貧之后,A鄉在精準扶貧道路上做了一個調整,這便是將精準扶貧與經濟發展進行“互嵌”,通過發展經濟這第一要務實現全面脫貧目標。
2.“由點到面”的扶貧方式轉變
A鄉的扶貧措施較為單一,主要依靠產業扶貧。在扶貧的初期,A鄉的發展定位是:精準扶貧與產業發展相結合,突出發展現代農業。A鄉2015年的扶貧工作匯報這樣闡述自己的扶貧道路:我鄉將重點依托現有資源,圍繞現有產業,做到“一村一法”“一戶一策”。一是依靠致富能力帶領村民致富。采用“村黨支部+農民合作社+農戶”的運行模式,按照“三統一”原則(統一免費技術指導,統一生產資料,統一銷售渠道),帶領村民一起脫貧致富。二是按照“一村一品”特色產業的理念,依托我們現有的油茶、花生、蕎頭等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家庭農場,重點發展油茶、花生、蕎頭等當地特色產業,構建“產業基地+合作社+貧困戶”的產業扶貧模式,為貧困戶提供產銷一條龍服務,幫助貧困戶脫貧致富。但是,在實際的扶貧工作中A鄉走的是一條“以點代面”的發展道路,將大量的扶貧資源輸送給兩個省級貧困村,導致扶貧資源難以得到優化配置。不但如此,就產業扶貧發展的現狀來看,注重前期的投入而忽視后期對于技術、管理、資金等方面進行扶持的情況比比皆是,這也導致一些產業所投入的項目半途而廢,出現“年年扶貧年年貧”的現象。為了扭轉局面,A鄉決定回歸“由點到面”的扶貧方式,在不破壞既有成果的前提下,將著力點放在推進整村脫貧的“面”上。通過積極地爭取項目和資金,3600畝的坡耕地改造項目、扶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以及立體生態旅游項目等陸續上馬。投資大、見效慢是這些項目的共同點,這就意味著A鄉需要通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來解決貧困和發展問題。
3.政府的路徑依賴與貧困人口的可行能力
改革開放30多年的扶貧之路表明,政府主導型的扶貧方式仍是我國貧困治理的主要經驗,而政府最拿手的卻不是扶貧而是發展經濟。制度經濟學大師諾斯(1990)對制度變遷當中路徑依賴的研究表明,路徑依賴的形成不僅僅是歷史偶然事件或小事件引起的,而更多是由行動者的有限理性以及制度轉換的較高的交易成本所引起[27](p317)。當扶貧成為鄉鎮政府的主要任務而經濟發展退居次要位置時,政府的路徑依賴由此顯現,而從制度經濟學的層面來說,將扶貧與經濟發展相互嵌套則能夠為政府減輕交易成本,并且通過資源轉換,能夠幫助基層政府獲得更多發展經濟的資源。此外,在目前的形勢下,政府還需要考慮貧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從實際情況出發做出準確判斷。長期以來,我國貧困人口基數大,受輸血式扶貧方式的影響,基層民眾形成了等、靠、要的依賴思想。A鄉的扶貧干部反映:“給老鄉送飼料,他們不主動來領,反倒插著手等鄉干部給他們送上門。”這樣的情況并不在少數。貧困理論家阿瑪蒂亞·森(2013)提出能力貧困的概念,認為貧困是對人的基本可行能力的剝奪,要幫助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應當從提升可行能力的角度入手[28](p62)。但是在當下,貧困人口的依賴思想并沒有得到完全轉變,依靠自身脫貧的能力不容樂觀,提升其可行能力的路徑選擇與急切的脫貧任務之間存在一定張力。
(二)發展式脫貧的價值與效度
鑒于數字式脫貧這種完成目標任務的捷徑,無論其初衷是否符合相關法規制度以及道德倫理,都難以從事實上、根本上減少和消除貧困,為此就需要鄉鎮政府著實從政策執行上進行審慎考慮,切實將扶貧工作落到實處。在此情境之下,鄉鎮政府的選擇是發展式脫貧。發展式脫貧立足于較長的脫貧時間節點,意圖采取將扶貧與發展進行“互嵌”的方式,大力推進由點到面的扶貧政策,從而實現整體性脫貧。這一差異化選擇體現了鄉鎮政府的脫貧意愿和策略選擇,在由“管”到“治”的政府職能轉型過程中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我國的貧困地區,普遍面臨的發展難題是交通不便、區位優勢不明顯、生態環境惡劣以及資源匱乏等,當經濟發展尚沒有得到根本改善的前提下,將主要精力放在脫貧上對鄉鎮政府而言是個不小的轉變,需要克服重重困難。走發展式脫貧的道路,將發展與扶貧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可以實現資源在同一層級的互通和共享,能夠實現資源利用的最大化。
但同時也應當認識到,在“省市一盤棋”的目標體制下,受自身治理能力等因素的制約,發展式脫貧也存在一定的危機。例如,由于無法同時兼顧扶貧和發展,導致一損俱損的局面出現,反而阻礙了國家整體性脫貧目標的實現。此外,招商引資競爭激烈、農村能人缺乏、大量資源流向少數精英手中的情況客觀存在也加大了發展式脫貧實施的難度。民間流行的一句說法是“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一個地區生存和發展道路的選擇始終還是要以自身的實際為基礎,充分結合群眾的意愿和想法,才能為實現國家和社會的共同目標做出更加有利的貢獻。
五、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貧困治理是國家治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于以往的粗放式扶貧,2014年開始實施的精準扶貧戰略更加突出對貧困治理的精和準,將國家的扶貧資源進行精確的技術瞄準,做有針對性的扶貧。當下,我國的精準扶貧工作仍然是由政府主導,針對在其中所產生的各種問題,在扶貧主體的研究層面,大多數學者停留在具體村莊或者是市縣一級,忽視了鄉鎮一級政府。事實上,在壓力型體制下,處于國家政權末梢的鄉鎮政府是精準扶貧的實質性主體。基于此,本文從實證的角度出發探討了精準扶貧視閾下鄉鎮政府治理貧困的策略選擇。研究發現,鄉鎮政府在精準扶貧中為了實現脫貧任務,采取了隱瞞和虛報,利用精準管理中的漏洞做文章的“數字式脫貧”,為了改進這一行為的負面效果,又采取了發展式脫貧的解決措施。此類行為說明,鄉鎮政府在治理貧困過程中出現了目標與行為的偏離,實質上是貧困地區鄉鎮政府“策略主義”的體現。所謂“策略主義”,在歐陽靜(2011)看來,是指基層政權組織缺乏穩定的、抽象的、普遍主義的運作規則,以及基于長遠發展的戰略目標,而以各類具體的、權宜的和隨意的策略與方法作為原則,并只顧追求眼前的短暫目標[29](p116)。策略主義的實施凸顯了鄉鎮政府治理貧困的實踐困境,表明貧困治理能力較弱的鄉鎮政府,其在幫扶農民脫貧的過程中必然力不從心,由此出現有令不從、欺上瞞下的悖逆現象。
精準脫貧作為國家“十三五”時期的重要戰略目標,面對貧困地區鄉鎮政府采取策略性選擇的治理情境,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糾正:首先,建立健全貧困地區鄉鎮政府的扶貧信息反饋機制,及時掌握貧困地區的實際情況,摒棄脫貧目標“一刀切”的做法;其次,政策制定中要統籌兼顧,充分考慮鄉鎮政府的貧困治理能力,尊重不同地區的差異化選擇;再次,構建多元主體聯動的貧困治理體系,通過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參與貧困治理,監督和催促各級機關單位履行貧困治理責任的方式,優化貧困治理格局。最后,不僅要提升貧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更要注重提升鄉鎮政府的可行能力,強化基層政權的貧困治理能力。
[1]左停,楊雨鑫,鐘玲.精準扶貧:技術靶向、理論解析和現實挑戰[J].貴州社會科學,2015(8).
[2]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EB/OL].新華網,2015-10-29.
[3]葛志軍,邢成舉.精準扶貧:內涵、實踐困境及其原因闡釋——基于寧夏銀川兩個村莊的調查[J].貴州社會科學,2015(5).
[4]唐麗霞,羅江月,李小云.精準扶貧機制實施的政策和實踐困境[J].貴州社會科學,2015(5).
[5]邢成舉、李小云.精英俘獲與財政扶貧項目目標偏離的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13(9).
[6]劉司可.精準扶貧視角下農村貧困退出機制的實踐與思考:基于湖北省廣水市陳家河村152戶貧困戶的問卷調查[J].農村經濟,2016(4).
[7]李群峰.權力結構視域下村莊層面精準扶貧瞄準偏離機制研究[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2).
[8]李博.項目制扶貧的運作邏輯與地方性實踐:以精準扶貧視角看A縣競爭性扶貧項目[J].北京社會科學,2016(3).
[9]雷望紅.論精準扶貧政策的不精準執行[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
[10]朱天義,高莉娟.選擇性治理:精準扶貧中鄉鎮政權行動邏輯的組織分析[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7(1).
[11]劉建生,陳鑫,曹佳慧.產業精準扶貧作用機制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7(6).
[12]謝玉梅,徐瑋,程恩江,梁克盛.精準扶貧與目標群小額信貸:基于協同創新視角的個案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6(9).
[13]李洪波.精準扶貧視野下農村留守兒童的權益保障[J].學術交流,2017(4).
[14]黃建.論精準扶貧中的社會組織參與[J].學術界,2017(8).
[15]周黎安.行政發包制[J].社會,2014(6).
[16][德]馬克斯·韋伯.支配社會學[M].康樂,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17]王漢生,王一鴿.目標管理責任制:農村基層政權的實踐邏輯[J].社會學研究,2009(2).
[18]Gao Jie:Pernicious Manipulation of Performance Measuresin China’s Cadre Evaluation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2015(23).
[19]張文禮.多中心治理:我國城市治理的新模式[J].開發研究,2008(1).
[20]林閩鋼,陶鵬.中國貧困治理三十年回顧與前瞻[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08(6).
[21]周飛舟.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系之影響[J].社會學研究,2006(3).
[22]賀雪峰.稅費改革的政治邏輯與治理邏輯[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
[23]周雪光.項目制:一個“控制權”理論視角[J].開放時代,2015(2).
[24]賀雪峰.論鄉村治理內卷化——以河南省K鎮調查為例[J].開放時代,2011(2).
[25]周雪光.基層政府間的“共謀現象”:一個政府行為的制度邏輯[J].社會學研究,2008(6).
[26]虞崇勝,唐斌,余揚.能力、權利、制度:精準脫貧戰略的三維實現機制[J].理論探討,2016(2).
[27]North,D.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8][印]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M].任賾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29]歐陽靜.壓力型體制與鄉鎮的策略主義邏輯[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