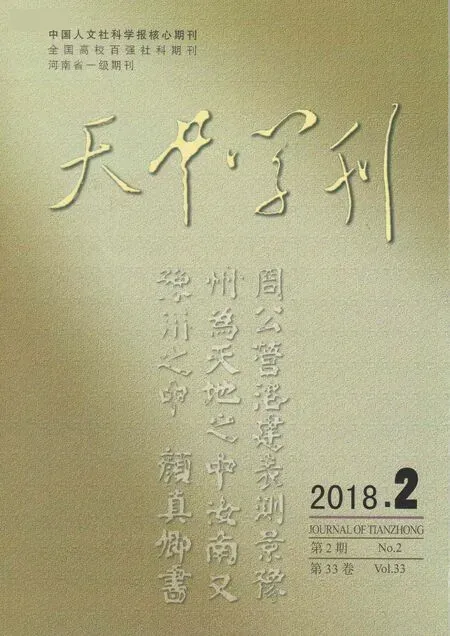論近代歷史小說中的大連敘事——以《孽海花》《中東大戰演義》為主
侯運華
?
論近代歷史小說中的大連敘事——以《孽海花》《中東大戰演義》為主
侯運華
(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中國近代歷史小說對大連的敘事有直接、間接之別。間接書寫者以甲午戰爭為描述對象,大連是潛在的背景;直接書寫者對近代大連的命運有具體展現。高層的失誤、將領的怯戰、日軍的懷柔、民族國家意識的缺失等,是民心轉向的主要原因。敘事空間的顯隱影響小說的敘事特征,隱去空間凸顯普泛性的集體記憶,張揚的是民族集體情緒;如此敘事,描述事件簡潔,但敘事風格飄忽,易使所敘事實產生虛浮感。描繪具體空間,則凸顯區域特征,產生樸素真實的敘事效應,描述人物命運則可建構血淚相融的質感。歷史小說創作不應忽視主體意識的介入。這樣,歷史小說才會具備獨特的氣質和靈動的風格。
歷史小說;大連敘事;原因剖析;敘事特征
當“中國近代”和“大連”這兩個詞聯系在一起時,人們馬上想到的是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可是,當我們從超過萬部近代小說中找尋大連的印記時,卻發現很少有相關描寫。即便是擴大視野,把描寫甲午戰爭的小說都算進去,也不超過10部。當然,這里不包括現代、當代時段創作的小說。本文把那些描寫甲午戰爭的小說視為間接書寫大連的小說,將《中東大戰演義》作為直接書寫大連的典型文本,討論近代歷史小說怎樣書寫大連的,闡釋其藝術特征和文化內蘊,進而剖析歷史小說創作中的虛實關系等學術問題。
一
小說文本描寫特定空間時,有直接描繪和間接描繪之別。近代以來,大連成為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發生地,理應有許多作家關注這里。遺憾的是,關于日俄戰爭,沒有找到中國作家創作的小說,僅有一部《旅順口》,還是蘇聯作家阿 · 斯捷潘諾夫1944年創作的。小說以俄國軍人的視角反映1904―1905年發生在中國東北的兩國之爭。中俄戰爭堪稱世界歷史上奇特的一幕,交戰雙方在第三國領土、領海上作戰,主權國竟然號稱中立。實際上,清政府的“中立”凸顯出中國政府的尷尬與大連地位的尷尬——政府方面,想作為而無力;大連則作為中國領土得不到國家的保護。雙重尷尬的現狀必然影響國人的認知和此后大連人的身份認同,出現諸多看似不合情理的現象。盡管遼寧是戰爭的主要受害地,但中國小說家不關注這次戰爭,僅有的小說是由參戰國俄羅斯人寫的,便是這種后果之一。
甲午戰爭是中日直接對陣終以中方失敗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對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的震撼巨大,正如梁啟超所言:“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1]因此,有不少小說直接描寫甲午戰爭,或以甲午戰爭為背景。1895年在《新聞報》發表的高太癡的《夢平倭虜記》,敘述某布衣精通兵法謀略,夢中被皇帝委派帶水師遠征日本并大勝,凸顯作家面對現實的無奈和幻想戰勝日本的心態。1900年,洪興全的《中東大戰演義》由香港中華印務總局出版,是全面描寫甲午戰爭的小說。平情客演的《中東和戰本末紀略》僅9回,1902年在《杭州白話報》連載,描寫甲午戰爭的經過,側重揭露清政府官員的議和行為,諷刺其貪生怕死。1903年《孽海花》前6回在《江蘇》第八期刊載,1905年東京翔鸞社印刷、上海小說林書社發行,該書描繪了甲午戰爭中高層決策和戰爭過程。1911年老談的《逐日演義》在《民立報》連載,小說以寓言的方式描寫夸父甲午年遭日君孫開暗算,此后臥薪嘗膽,260年后的甲午年,建立中華大國,戰勝日君,表現出渴望戰勝日本的愿望。因為這些小說中以《孽海花》和《中東大戰演義》最具代表性,故本文以其為典型文本展開論述。
綜觀描寫甲午戰爭的小說,或側重戰爭過程的描述,如《中東大戰演義》《中東和戰本末紀略》等;或聚焦決策過程,探究戰敗原因,譴責貪生怕死的官僚,如《孽海花》等;或對現實絕望,萌生“精神勝利法”,在幻想中戰勝日本,如《夢平倭虜記》《逐日演義》等。這三個層面的內蘊,基本包括了甲午戰爭后國人的情緒反應,亦凸顯讀者的心理期待。雖然大部分小說沒有提到旅順等具體空間,但是,只要讀者看到戰爭過程、戰爭場景的描述,都會聯想到旅順等具體地點。尤其是《孽海花》,在總體反映同治到光緒三十年社會重大事件的框架內,直接描寫甲午戰爭的就有5回。如第24回敘述日本介入朝鮮事務引發中日沖突、朝廷內部戰和爭論,并通過新科狀元章直蜚的視角得知:“……日本給我國已經開戰了,載兵去的英國高升輪船已經擊沉了,牙山大營也打了敗仗了。”[2]213第25回敘述清軍陸軍平壤戰敗,海軍在大東溝也被日軍打敗,擅長紙上談兵的何玨齋臨危請命,卻遲疑進軍,而在大廟內作秀,已經埋下后續敗仗的伏筆。第27回敘述威毅伯到日本談判被刺事件等。顯然,《孽海花》只是將中日甲午戰爭作為敘事背景,故缺乏對大連的直接描寫。這種間接描寫并非毫無意義,它不僅對小說刻畫威毅伯、何玨齋等形象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也勾勒出戰爭背景下大連城市的悲劇命運。
直接描寫甲午戰爭的歷史小說《中東大戰演義》,又名《說倭傳》,作者為洪仁玕之子洪興全。該書33回,主要敘述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東學黨起義導致時局動蕩,韓王請中國出兵以穩定局勢,日軍亦趁機占領漢城;此后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慘敗,日軍攻占旅順,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戰后,李鴻章出使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軍民奮起反抗,與黑旗軍一起堅持斗爭幾十年。該小說是唯一一部多角度描述大連在甲午戰爭中遭遇的小說,直接提到的地名就有鳳凰城、金州、摩天嶺、蓋平、旅順、大東溝等,均為甲午戰爭期間陸上、海上發生戰爭的地方。這些空間的積聚,勾勒出甲午戰爭發生的具體空間,即使作者因為側重過程描述而沒有具體展現戰爭場景,讀者依然能夠聯想到血肉橫飛、斷壁殘垣的畫面。第1回就寫到朝鮮東學黨起事、淮軍將領葉志超帶兵三千入朝平叛事;第2回敘述日軍也趕到,兩軍對峙。第4回敘述日軍擊沉高升輪。第6回敘述大東溝海戰失敗。尤其是第11回正面描寫日軍進攻旅順的場景。小說先總體概括旅順港口的地勢險要:“雖是一掌之地,實為北洋門戶,船塢、軍火、糧食、器械,多在其間。各處炮臺,俱系用巨石砌成,堅固異常,大有金湯之比。且海口狹窄,敵船輕易難入。險阻之處極多,雖三歲孩童守之,可保無虞。雖西國至強之兵,莫敢覬覦。”[3]475此處的極力渲染,蘊含著作者對旅順失陷的悲憤。城池如此堅固,西方列強不敢覬覦,但最終卻被日軍輕易攻占,恰恰說明守軍之懦弱!
總體上看,《中東大戰演義》對人物形象的描寫,聚焦在軍隊高級將領和普通大連人身上。第11回透過日軍策劃攻擊時的對話,點明“龔照玙等輩,俱系貪生怕死之流”,既說明日軍知己知彼,對中方將領了解很透,也凸顯出清軍將領之怯懦畏敵已成為眾人皆知的事實。果然,當日軍繞道金州,進攻旅順時,“龔照玙聞言,不禁心寒膽落,慌忙無主,遂暗中逃去。黃統領仕林,探知龔照玙已經聞風遠遁,遂亦逃走。俄而倭兵將到。各兵弁不見了統領,軍中無主,遂各散去”。難怪作者感慨:“可憐旅順船澳炮臺,費盡國家巨款,百余年之積聚,為中國最險固之區,今一旦(彈)未戰,而竟付與敵人之手,良可惜也。”[3]477棄守逃跑不是個別現象,第13回敘述敵軍進攻蓋平,統領高元鼎幾戰皆敗,也棄城而去;日軍繼續攻擊,“惟所到之處,皆衛汝成兄弟一流,望風而走”[3]483。日軍不到一個月即進到牛莊。第14回敘述自愿請纓如吳大澂,也多為紙上談兵、臨陣無用。小說寫其帶湘軍到山海關駐扎,先發布告虛張聲勢,戰斗爆發時“令其兄吳大良統領前軍,不想未戰之先,已為倭人之炮聲嚇破其膽,立即斃命。吳清帥得聞其兄兇報,益加嚇煞,未至陣前,一聞炮聲,便棄寨而走”,乃至“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3]486。
前線守軍不戰而逃,嚴重影響高層對戰局的判斷和普通百姓對國家的信任。第12回敘述李鴻章看到清軍兵敗如山倒,便謀劃借俄國力量收復旅順,故朝廷派王之春赴俄簽署中俄密約,希望借助西方列強之力制止日軍侵略。顯然,這樣做是與虎謀皮,然由此可見當政者的無奈。而普通百姓對軍隊的絕望則可能使其倒向敵方而充當內奸。第13回敘述中日金州、蓋平戰事。聶功亭帶兵薄衣御敵,大獲全勝,不料有華人甘做日軍奸細:“倭帥設計,用厚資賄賂愚民,使作奸細。遂從小路將士兵大半混入了金州,以作內應……華軍雖奮于死戰,奈奸細極多,窩藏敵人在金州城內,出沒無常,不分晝夜,亂來攻擊。一連十日,倭人照樣施計。”[3]482聶功亭無奈,只好舍棄金州,直奔鳳凰城。大好局面被毀,并非完全是敵人強大所致,而是由于我方出現了奸細。
二
為什么出現如此多的內奸?難道是大連人都不愛國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閱讀這類小說,我們仍然會心情沉重。內奸的產生以及抗擊侵略戰爭的失敗,究竟有哪些深層次的原因,值得探究。
從小說的描寫看,首先是政府決策失誤與清軍的荒唐表現使然。《孽海花》第25回敘述戰爭爆發后,作為朝廷重臣的龔尚書和高中堂根本不關心軍務,反而為丟失的鶴撰寫《失鶴零丁》,見面后龔尚書談夢占,高中堂談災變,難怪章直蜚正色斥責他們:“兩位老師誤了!兩位老師是朝廷柱石,蒼生霖雨,現在一個談災變,一個談夢占,這些頹唐憤慨的議論,該是不得志的文士在草廬吟嘯中發的,身為臺輔,手執斧柯,像兩位老師一樣,怎么好說這樣咨嗟嘆息的風涼話呢!”[2]217不理戰事的重臣如此,精通戰務的意見能否被采納呢?《中東大戰演義》第3回討論戰、和問題時,李鴻章面圣陳述不宜戰的五個原因:士兵缺乏操練、不懂陣法,道途遠隔、后勤保障難繼,邊防線長、戰艦太少,商務易受影響、易引發列強干涉和內部叛亂,國庫空虛、軍餉難籌等。李鴻章的觀點,可謂知己知彼的洞見,如此務實的主張竟被主戰的喧囂湮沒,導致戰爭爆發。而清軍將領的懦弱、荒唐表現,則是失敗的內因。天險要塞被輕易放棄,遠望敵軍即拼命逃跑,已經令目睹者絕望,臨戰時的戲園休閑更是令人不齒。第11回寫道:“據言倭軍攻至旅順之時,中國海軍中人,尚多有在戲場觀劇者。丁統領汝昌亦在其間。后聞告警,方始遁回兵艦……有伶人名朵朵紅,與云仙花旦,竟然媚敵,手執戲單,跪請倭人點戲。倭將不禁失笑曰:‘喪師失地,汝等尚在此演戲也。無恥之徒,直類禽獸耳!’”[3]477耳聞目睹怎不使當時的大連民眾對國家和軍隊絕望呢?民心所向一旦轉向,即便是軍事實力強大,也難以戰勝敵方,因此,甲午戰敗、大連失陷,乃高層失誤、將領怯戰、民心喪失的合力所致。
絕望中的大連百姓遇到日軍的懷柔政策,更容易使情感的天平傾斜。《中東大戰演義》第13回寫日軍占領金州后,“將寨下好,出榜安民”;得到蓋平,“遂用財利以結愚民之心”。戰火剛滅,日軍就貼出安民告示,并以財產收買人心,會改變普通人對他們的認知。戰亂時代的百姓,對生命安全、財產得失的現實關切遠大于民族立場,尤其是身處中日對峙前線的近代大連人,更看重這些。日本人蓄謀侵占中國東北已久,對民心取向是深知的,故從軍事行動方面強化百姓的安全需求。如第15回所敘:“且說倭軍自據了旅順,便將旅順所有貴重器皿,遷掠一空。又將鐵艦排除旅順口外,四處游弋。”[3]487一方面防止戰爭再起,鞏固既有戰果,使百姓認為清軍不可能打回來了,內心徹底絕望;另一方面,穩定局面也能給大連人帶來安全感,強化其認同意識。
危難之際,身處自保無力國家也不能保護自己的處境,很容易使普通百姓產生被遺棄的心理。受此影響,民眾則生成現世觀,關注安全需求與利益得失,而不在乎民族大義和愛國與否。不到10年,日俄戰爭爆發時清政府的所謂“中立”,使大連人再次遭遇到戰火蹂躪,卻沒有引起中國作家的關注,不能不說在此時已經埋下了伏筆。眾所周知的魯迅“棄醫從文”事件中,那幅引發魯迅憤慨的幻燈片所描述的場景——中國百姓替俄國人做奸細,被日本人抓住后處死,周圍眾多圍觀者表情麻木,激發魯迅喚醒大眾的愿望,使其注重促使大眾靈魂的覺悟,而非肉體的保全。仔細想想,甲午戰爭,大連人做日本人的奸細;日俄戰爭,東北人做俄國人的奸細,恰恰說明當地人并無鮮明的民族意識或國家概念,他們需要的就是利益與生存。那些圍觀者的麻木,是否也說明這類現象太多,他們已經見怪不怪了呢?
國人的民族意識、國家立場是近代以來經嚴復、梁啟超等先覺者倡導而逐步傳播開來的,在現代中國建構之前,大多數國人所積淀的依然是傳統的君臣、主奴關系。不然,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何抗日戰爭時期,還會有那么多漢奸存在?為何軍隊成建制投敵成為偽軍?民族集體無意識的更新是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因此,無須過分譴責甲午戰爭或日俄戰爭時期部分大連人的行為,應該思考的是什么使其做出那樣的選擇以及選擇之后其人生中蘊含的悲哀。
三
絕大部分描寫甲午戰爭的小說都沒有明確提到旅順、金州等大連地名,是否意味著小說家有意忽略?《中東大戰演義》的描寫具體到戰役地點,有清晰的大連空間勾勒,是否就具有更高的藝術性?從敘事特征考察這種現象,能對近代歷史小說的闡釋提供怎樣的借鑒呢?
筆者認為歷史小說創作中,有沒有具體空間顯示均可以。那些沒有標明具體空間的小說,并不會誤導讀者將事件發生地移至他方,因為歷史小說是以歷史事件為描寫對象的,而歷史事件的發生地是固定的。但是,就表達效應看,寫不寫具體空間還是有很大區別的。無論小說家有意無意,小說不聚焦地理空間,文本凸顯的是具有普泛性的集體記憶,張揚的是民族集體情緒,如此敘事,既有簡潔描述事件過程的方便,更有渲染激憤情緒的動機,包括對決策者猶豫不定的譴責、對清軍將領臨陣脫逃的揭露和對日軍入侵國土的憤慨;也有敘事風格飄忽的弊端,事件缺乏明確的空間依托,易使所敘事實產生虛浮感。如《中東大戰演義》那樣具體點明戰役發生地旅順、大東溝、金州、蓋平等,則能夠凸顯出敘事空間的區域特征,便于將所敘事件落到實處,產生樸素真實的敘事效應。以此為背景描述人物命運,則建構起血淚相融的質感。
敘事空間的顯、隱,關聯歷史小說創作中虛實關系的處理。小說本質上是虛構藝術,不應該過于拘泥于史實。但是,中國小說具有強烈的史傳傳統,漫長的文學發展史中人們對小說的定位都是“史補”,故創作小說總要尋找一個可感的歷史背景。到近代,接受西方小說理念影響,部分小說家開始重視虛構,眾多深受中國小說傳統影響的小說家依然堅守力爭使文本成為正史之補充的理念,才出現近代小說過于拘泥史實的現象。若從藝術成就方面考察,則以《孽海花》為代表的虛構類小說更符合小說創作的內在規律。以史實為基礎,曾樸充分利用自己的法國文學修養,展開想象的翅膀進行適當的虛構,使其文本充盈著藝術的清逸和適度的浪漫。尤其是在描述甲午戰爭爆發前后決策層戰和之爭的同時,穿插進朝廷高官的個人生活、情感經歷等,使文本具有多重內蘊。即便是李鴻章、葉志超等歷史人物,小說也化名為“威毅伯”“言紫朝”等。凡此種種,說明曾樸創作《孽海花》時,其主體意識清楚藝術創造與歷史紀實的界限,因此,《孽海花》成為近代小說代表性文本,就不足為奇了。
《中東大戰演義》則長于寫實,弱于虛構。作者在《自序》中對小說創作的虛實關系有辯證的認識:“從來創說者,事貴出乎實,不宜盡出于虛,然實之中虛亦不可無者也。茍事事皆實,則必出于平庸,無以動詼諧者一時之聽;茍事事皆虛,則必過于誕妄,無以服稽古者之心。是以余之創說也,虛實而兼用焉。”這是很難得的小說理論闡釋,遺憾的是創作中作家并沒有做到“虛實兼用”。小說對甲午戰爭前后的中外時局變化、戰爭中的敵我雙方對陣情況、戰后議和進程等詳細展開,的確達到了記錄時代大事的目的。但也有敘事過于煩瑣之弊。如議和一事,竟然鋪展21回,占全書篇幅的64%。其目的在于探索失敗的原因。因此,文本既有對外因的描繪,如日本的貪婪、中國的積弱等,更注重對內因的剖析:如清軍將領中的葉志超、蔡廷干等人也與漢奸無異;葉志超不戰而棄牙山,反而發電報報捷;蔡廷干見倭人軍威雄壯,膽戰心驚,恐防有失,遂修書降倭。倭人以其技藝頗精,使其照常統帶水雷。“技藝頗精”,竟然不思報國,反而為敵所用,清軍如何不敗?陣前將軍如此,朝中大臣如何呢?第18回寫面對危局,翁同龢主張遷都,李鴻章主張允許俄國在黑龍江修建鐵路,換取俄軍出兵東北,“俄皇若允出師,倭人自然收兵回國,那時乘勢攻之,旅順可復也”。顯然,皆非應對良策。而上下無計應對,恰是作者對晚清現實的概括。
《中東大戰演義》不僅按照戰爭進程描寫甲午戰爭,詳細描寫戰役發生空間,而且對歷史人物采用原名,中方從李鴻章、袁世凱、葉志超到吳大澂、左寶貴、衛汝成等各級將領,日方從伊藤博文到各路統領,均大致與史實相符。如此描述,其正效應是能夠使讀者了解戰爭的過程,知曉交戰雙方的對陣將領;其負效應是缺乏戰場細節和人物心理的刻畫,使其文本涉及人物雖多,卻多為扁平人物形象。從敘事效果觀察,敘事的敘事進程遲滯,缺乏波瀾,除了激發讀者的情緒性反應外,很少引發讀者對戰爭性質的思考和對人性內涵的觀照。而創作主體退隱,使其小說文本更像是歷史事件的紀實,缺失了小說家應該凸顯的情節設計、結構調整和心理描寫才具。
近代歷史小說對大連的書寫與大連在近代歷史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由于戰敗的屈辱和近代傳媒傳播速度較慢,使讀者對事件過程保有好奇心,加上傳統小說觀的影響,近代小說家把描述甲午戰爭的過程作為創作的主題,而忽視了自我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思考。實際上,歷史小說創作的成功,離不開小說家主體意識的干預。無論是《孽海花》等近代小說的成功,還是革命歷史小說中官方意識形態的投射,抑或是新歷史小說中作家主觀意識的強化,均說明歷史小說的創作不應忽視主體意識的介入。而具體空間的描述,不僅可以成為所敘事件存在的物理依據,更可以拓展活躍其間的人類的生活,進而展現其人性內蘊、精神內涵。這樣,歷史小說才會具備獨特的氣質和靈動的風格。
[1] 梁啟超.甲午政變記[M]//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7.
[2] 曾樸.孽海花[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3] 洪興全.中東大戰演義[M]//中國近代珍稀本小說.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
〔責任編輯 劉小兵〕
On Dalian Narrations in Modern Historical Novels
HOU Yunhua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s havea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s on the narration of Dalian. The indirect writer takes the war of 1894 as the description with Dalian a potential background, and the direct writer has a concrete display of the fate of modern Dalian.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turn of the people are the failure of the high level, the timid war of the generals, the Japanese army's invasion and national state's lack of consciousness.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narrative space affects narrative features. The hidden space can highlight the universal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national mood. Such narrative has concise narrative style, but it is easy to make the real sense of narrative in vain. Specific space description can highligh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duce real effect of simple narrative. The describing of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can construct the texture of blood and flesh. 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novels should not ignore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this way, the historical novel will have the unique temperament and the style of spirit.
historical novels; Dalian narration; cause analysis; narrative features
2017-09-02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11&ZD110)
侯運華(1965―),男,河南上蔡人,教授,博士。
I206
A
1006–5261(2018)02–01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