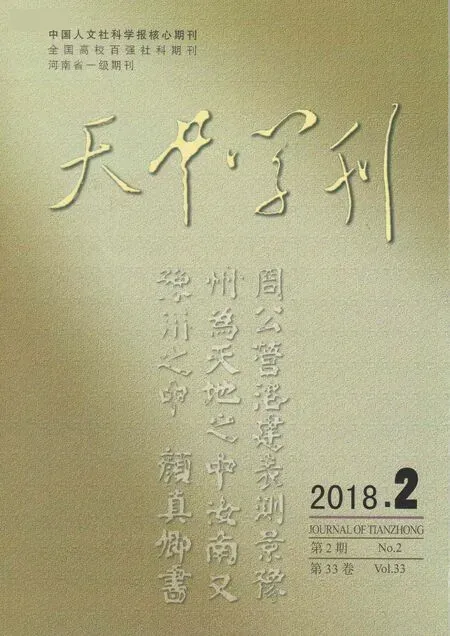翁方綱與姚鼐的詩學觀及題跋詩創作之比較
傅元瓊
?
翁方綱與姚鼐的詩學觀及題跋詩創作之比較
傅元瓊
(泰州學院 人文學院,江蘇 泰州 225300)
姚鼐居京時常與翁方綱談詩論文,二人思想有契合處,亦有分歧。他們都主張中和漢宋學,持義理、考據、詞章結合的文章學觀點。但翁方綱力倡學人之詩,以補明詩之失;姚鼐崇尚文人之詩,對何景明、李夢陽等人多有推崇。然二人題跋詩創作,皆具質實風格。翁詩屢為人詬病的“少性情”,雖與其詩學觀有關,但亦與其題跋文體的大量創作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翁方綱;姚鼐;詩文觀;題跋
翁方綱、姚鼐同處乾嘉時期,都反對將漢宋之學截然對立;姚鼐為文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并重,翁方綱也把此當作詩文創作所應達到的最高境界。然姚鼐以文章學為后人所推重,翁方綱則以詩學、金石學著稱。二人術業之別,使其義理、考訂、詞章并重的主張呈現不同的表現形式。姚鼐的文章成為古文創作的典范作品,而翁方綱的詩文則因考據、金石書畫之學的融入而為人所詬病。這種由于詩文觀的不同而呈現的差異早在姚鼐與翁方綱的論學、商討中已有明顯表現。
一、姚鼐與翁方綱的“藥言”之交
姚鼐長翁方綱兩歲,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進士。據《姚惜抱先生年譜》,“(乾隆)乙亥(1755年),先生年二十五歲居京師”[1],在中進士前近10年的時間里,姚鼐移居京師立館任教,結交名士。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春姚鼐辭官返鄉,居京約20年。此間翁方綱與姚鼐多有交往,這種交往在同編四庫全書時尤為密切。據《翁氏家事略記》《三十八年癸巳(1773年)》:“自癸巳春入院修書……每日清晨入院,院設大廚,供給桌飯,午后歸寓,以是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處,在寶善亭與同修程魚門晉芳、姚姬川鼐、任幼植大椿諸人對案,詳舉所知,各開應考證之書目”[2]72–73;“自壬辰(1772年)、癸巳以后,每月與錢萚石、程魚門、姚姬川、嚴冬友諸人作詩課”[2]74,詩文甚至是金石書畫都成為他們之間談論的話題。姚鼐雖年長,但由于翁方綱本為京都人士,友朋如云,且弱冠中舉,至姚鼐中進士,翁方綱已為官十多年。加上其治學勤謹,多為友朋推敬,這些皆決定了在姚、翁二人的交往中,翁方綱所處的政治、學術地位要比姚鼐高得多。考察姚、翁交往,不難發現翁方綱在二人交游圈中的核心地位。
翁方綱時常邀請友朋集會,姚鼐曾多次為其中的一員。現姚鼐集中存《為翁正三學士題東坡天際烏云帖》《花朝雪集覃溪學士家歸作此詩》《七夕集覃溪學士家觀祈巧圖或以為唐張萱筆也》《今歲重九翁覃溪學士登法源寺閣,作“斫”字韻七言詩,亦以屬鼐而未暇為也。學士屢用其韻為詩,益奇。臘月飲學士家,出示所得宋雕本施注蘇詩,舊藏宋中丞家者,欣賞無已,乃次重九詩韻》《冬至大風雪,次日同錢萚石詹事、程魚門吏部、翁覃溪、錢辛楣兩學士、曹習庵中允、陸耳山刑部集吳白華侍讀寓,同賦得三字三十韻》等作品,可略窺姚鼐與翁方綱及其他友朋之間的交往情況。4次集會中有3次以翁方綱的家院為集會地,翁方綱在集會中的主導作用由此可略知一二。姚鼐對翁方綱的蘇米齋曾賦詩曰:“宋賢遺故跡,乃在嶺南山。海上流云氣,冥蒙石壁間。披榛逢節使,摹石載舟還。遠興高齋對,猶令客動顏。”[3]544此詩從翁方綱祖籍福建莆田寫起,緊扣其金石書畫愛好及收藏,并刻畫出覃溪當時聚客蘇米齋共賞金石的情景。另姚鼐有《十一月十五日,雪,翁正三學士偕錢萚石詹事、辛楣學士登陶然亭,回至鼐寓舍,與程魚門吏部、曹來殷贊善、吳白華侍讀、陸耳山刑部同飲至夜,翁用東坡〈清虛堂〉韻作詩垂示,輒依奉和并呈諸公》等詩,也可證明翁方綱當時在翁、姚等人交往中的核心地位。
在翁方綱的集子中,提及與姚鼐交往的作品也不少見。《晨起同姬川陶然亭作》創作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仲子自江南寄近作學古詩相質,因賦詩5首以代面談,兼寄呈述庵、辛楣、姬川、端林》創作于嘉慶八年(1803年),《感舊》創作于嘉慶十七年(1812年)。這些作品皆是翁方綱與姚鼐幾十年友誼的見證。
然而,在翁方綱與姚鼐的交往中,二人由于見解主張的差異所產生的摩擦與辯爭也時有發生。翁方綱《感舊》曰:
昔從擇友初,辛苦求良藥。孰以漢學師,心弗宋儒怍。中間盧與姚,往復盟言酌……尚想桂宧燈,訂我瀛池諾。(姬川南歸時,于魚門桂宧餞筵,屢及校讎時相箴切語。)竟爾雄辨騁,漸即偭規錯。不以虛懷貯,安得深根托……苦言辣可憎,正未深咀嚼。(昔送姬川詩有“苦言近辣有人憎”之句,姬川作色曰:“鼐非敢憎也!”)俱成八十翁,豈比偶語謔。未得置書郵,暇且舊句削。[4]282
此詩作于耄耋之年。翁方綱回憶他與姚鼐之間的交往,頗有諍友如良藥之嘆。詩中提及“苦言近辣有人憎”句,見于翁方綱《送姚姬川郎中假歸桐城五首》其五,詩曰:“新蔬軟脆帶春冰,風味端宜筍蕨勝。淡意回甘無物喻,苦言近辣有人憎……”[5]456–457此詩創作于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年)春姚鼐離京南歸之際,當時姚鼐、翁方綱僅40余歲。翁方綱自言“苦言近辣”,而姚鼐因此而“作色”,不難猜測二人當初論學時相互之間的些許不快。其他4首詩記述同朝為官、同纂《四庫》之情誼,論詩談文,亦及學術及姚鼐辭官養親之事。在姚鼐南下友朋寫下的眾多贈別詩作中,翁方綱所作算是其中篇幅較長者。除此之外,翁方綱還曾作贈序一則:
姬川郎中與方綱昔同館,今同修四庫書;一旦以養親去,方綱將受言之恐后,而敢于有言者:竊見姬川之歸不難在讀書而難在取友,不難在善述而難在往復辨證,不難在江海英異之士造門請益而難在得失毫厘悉如姬川意中所欲言。姬川自此將日聞甘言,不復聞藥言,更將漸習之久,而其于人也,亦自不發藥言矣。此勢所必至者也。夫所謂藥者必有其方,如方綱者,待藥于君者也,安能為君作藥言乎?吾友有錢子者,其人仁義人也。其于學行文章深得人意中所欲言,愿姬川之聞其藥言也。君之門有孔生者,其人英異人也。其于學行文章樂受人之言,愿姬川之發其藥言也。[6]494–496
此序頗耐人尋味,其中“藥言”一詞反復被提及。“藥言”最早見于賈誼《新書》卷九“藥食嘗于卑,然后至于貴;藥言獻于貴,然后聞于卑”[7],蓋指有助于國治民安的言論。而翁方綱文中所指,則是逆耳忠言。上文《感舊》中“昔從擇友初,辛苦求良藥”與此序中的“藥言”相呼應,是翁方綱對40年前與姚鼐相處之事的回憶。逆耳之言,多不同于自己的見解,從“藥言”中亦不難體味二人在學術或詩文方面的相互辯難。同時,此序寫得情真意切,可見翁方綱的一片真誠。
二、“讀常見書”與翁、姚詩文觀的分歧
姚鼐主張讀常見之書,影響極為廣泛。此語首見于《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三,由姚鼐南歸,翁方綱送行引發:
當是時,學者多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詆為空疏,掊擊不遺余力,先生獨反復辨論。嘗言“讀書者求有益于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為玩物喪志,若今之為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罕見者為功,其玩物不尤甚耶?”瀕行,翁覃溪學士來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間未見書,某則愿讀人所常見書耳。”[8]
姚鼐不主張漢宋之學兩立的思想由此可見一二。“乞言”事后被《經學通論》[9]《東溟文集》[10]等多書引載。此事翁方綱、姚鼐著作皆不存,且頗具傳奇色彩,“乞言”二字不切合二人當時身份及在文壇中的地位,也不符合送別場景,略有抬高姚鼐的意味。而翁方綱在《漁洋載書圖》的題跋中也有關于讀常見之書的闡述:“況所謂真讀書者,元止在童而習之之諸經、正史,穿穴玩索,且終身不能竟矣。彼撥棄目前常見之書而高談耳目之所未及者,本非讀書,直以邀名耳。”[6]1348–1351此語較姚鼐之論又入木三分。讀“常見之書”,不論是翁、姚二人平日論學時的話題還是確為姚鼐的臨行之言,由此可見翁方綱與姚鼐的學術觀點的挈合并不局限于中和漢宋之學,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不可偏廢,他們二人作為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代表,有著更多相同見解與更多相互理解或交流的可能性。
翁方綱與姚鼐的交往在姚鼐南下之前較為密切,他們二人的見解既有契合處又有分歧。對二人的沖突我們從翁方綱贈序與贈別詩可知其大略,而真正能反映他們之間的分歧的,則在二人的討論中。這些討論,或面議或書面交流,而書信,無疑是我們今天探究二人此類交流的最佳媒介。姚鼐有一篇頗能代表其文章學主張的作品《與翁學士書》,是其與翁方綱在文學主張方面見解不同而激發創作的一篇作品,文如下:
鼐再拜,謹上覃溪先生幾下。昨相見承教,勉以為文之法,早起又得手書,勸掖益至,非相愛深,欲增進所不逮,曷為若此?鼐誠感荷不敢忘。雖然,鼐聞今天下之善射者,其法曰:平肩臂,正脰,腰以上直,腰以下反句(勾)磬折,支左詘右;其釋矢也,身如槁木。茍非是,不可以射。師弟子相授受,皆若此而已。及至索倫蒙古人之射,傾首,欹肩,僂背,發則口目皆動,見者莫不笑之。然而索倫蒙古之射遠貫深而命中,世之射者,常不逮也。然則射非有定法亦明矣。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是安得有定法哉?
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為詩者殆數千人,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制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人情執其學所從入者為是,而以人之學皆非也;及易人而觀之,則亦然……鼐誠不工于詩,然為之數十年矣。至京師,見諸才賢之作不同,夫亦各有所善也。就其常相見者五六人,皆鼐所欲取其善以為師者。雖然,使鼐舍其平生而惟一人之法,則鼐尚未知所適從也。[3]84–85
此文詩文兼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其一,針對詩文有無定法發表見解。姚鼐以射箭無定法比附詩文無定法可循,生動形象,卻不無戲謔之意,尤其是對善射者及其弟子與蒙古人相比時的窘態,實是對翁方綱所論之法的一種側面敲擊。針對翁方綱所言的“為文之法”,姚鼐提出詩文創作“非有定法”。很明顯,姚鼐是以“非有定法”駁斥與拒絕“為文之法”。言辭之中看似恭敬,但其中的不屑也表露無遺。其二,強調“意”與“氣”與詩文之美的重要性。姚鼐把立意看作詩文是否優美的要素,認為“詩文美者,命意必善”;又把“氣”看作詩文作品的靈魂:“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與言于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3]84并在此基礎上剖析意、氣、辭、聲音、節奏等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意與氣相御而為辭,然后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彩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3]84–85這些論述實際是在表達自己的詩文創作之法。姚鼐在論其法完畢后做出“是安得有定法哉”的反問,其實是在以一種迂回的方式拋出自我之法,并否定翁方綱關于“法”的理論。其三,陳述自己“法乎眾”的觀點,以“法乎眾”來拒絕翁方綱的一己之法。翁方綱論詩反對擬古,主張“師法古人,以質厚為本”“學古而不泥古”。翁方綱的這些主張在姚鼐看來是遵從翁方綱一人之法,同時又是對眾家之法的忽略。因而,姚鼐對翁方綱建議有所抗拒。
在《與翁學士書》整則書信中,姚鼐言語看似謙恭有禮,實則對翁方綱建議的反對與抗拒異常決絕,其中不僅無半點思索接受的誠意且多有不屑、調謔之言,甚至在反駁過程中,故意出現偏激、矛盾之論,一面言無定法,一面以己之法作為駁斥翁方綱的武器。同時,以自己所認為的法乎善,影射翁方綱論之不善,以一己所論的“法乎眾”,來拒絕翁方綱主張的“師法古人”。整篇文章,姚鼐毫不領情的意氣充斥其中,可算得上是一篇體現其詩文重“意”“氣”的典范之作。
《清史稿》列傳二百七十二曰:“鼐清約寡欲,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歡,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學品兼備推鼐,無異詞。”[11]然從姚鼐此書及翁方綱耄耋之年回憶的因贈別句而“作色”看,卻頗見其“接人極和藹”的另一面。從書信及翁方綱的回憶來看,若非緣于姚鼐當時的年輕氣盛,則可知翁方綱、姚鼐二人歧見之深。
與姚鼐的回復相比,翁方綱寫給姚鼐的書信則顯示出較為明顯的質厚平和風格。姚鼐《與翁學士書》的創作精確時間已難考定,據《桐城派三祖年譜》,此文作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年),“或稍前后,作《答翁學士(覃溪)書》”[12]。在此文創作較為接近的一段時期,翁方鋼曾寫給姚鼐兩封論詩書信,分別為《與姬川郎中論何李書》《再與姬川論何李書》。這兩封信存于《復初齋文稿》第一冊。前一封記于《同館送姚姬川郎中序》文之前,與一些題跋文相混錄入,大約占紙五頁,前兩頁所記位置在題跋文的頁眉處,第三、四頁頁眉、正文位置皆為此文,第五頁頁面部分記乙未年正月事,是一則關于孟法師碑的題跋。而書信文字與此跋穿插錄入,穿插處信文小于頁眉處無穿插者。《再與姬川論何李書》是與序文混雜而錄,書信的部分篇幅記于其他文章文字的頁眉空隙處,同時前后又各有整頁紙張書寫者。如此混雜的錄入方式,或是由于書信過長,翁方綱并非一氣呵成,而是在寫作過程中插入其他作品的創作;或是此文早已經完成,翁方綱為保存文獻,重新把與姚鼐交往的資料記入贈序前后,而從文字嵌入的方式來看,書信屈就其他文字的跡象更為明顯,據此我們可以推斷,此兩封信的創作日期極有可能要早于與其混雜而錄的頁面文字的創作日期。在第一封信之前及第二封信之后所記錄的兩篇題跋作品的日期分別為乾隆四十年(1775年)二月與四月;《同館送姚姬川郎中序》文云:“乾隆三十九年冬,姬川郎中以養母告歸,明年春將出都,以詩別館中僚友……館中人慕其孝養之誠,咸和詩以美之,而屬方綱為之序。”[13]100–102據《惜抱軒詩文集》詩集,卷八有《乙未春出都留別同館諸君》,乙未為乾隆四十年,而在此前并無此類詩作,翁方綱所做的五首贈別詩后有小注曰“以下乙未”,也是創作于乾隆四十年。以此與序參讀可知,此序的創作時間為乾隆四十年春,且極有可能在二月至四月間。同時,我們也可得出結論,翁方綱寫給姚鼐的兩封書信,創作時間應不晚于這段時間,或與姚鼐所作《與翁學士書》的時間較為相近。然從內容上看,這兩封書信似并非姚鼐回復中所提及的“手書”。此二書卻在反映二人“藥言”之交上,較為突出地代表了翁方綱的態度,并集中體現了翁方綱的詩學觀點。
翁方綱的詩學理論“肌理說”的提出是為消除明代詩歌諸家泥古、虛空的弊端。李夢陽、何景明是前七子的領軍人物,前七子為反對臺閣體的詩風,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為當時的詩壇帶來一些生機,然由于過分強調復古,又有其弊端。反對前七子的過分擬古,是翁方綱詩歌主張的重要組成部分。翁方綱的《與姬川郎中論何李書》《再與姬川郎中論何李書》二文篇幅極長,在翁方綱詩文中比較少見。第一書開篇曰:
君子不以鄙言為妄,容而納之,且或動見顏色。方綱于今世未見有受言若此者,非執事性肫摯而契進于善不能及此。以方綱之愚,復何敢有所論辨以瀆左右?而今有不得不明白剖說者。昨見?約道執事所以成就惓惓之意,于詩則曰宜法何、李,此方綱所以不能嘿息者也。[13]89
?約姓孔名廣森,受知于姚鼐。翁方綱曾作《孔?約集序》,其中稱自己與?約“相與對榻論析非一日矣”[6]138–139,可見二人交往亦較頻繁。此信由翁方綱聽孔廣森言姚鼐建議其學詩宜法何景明、李夢陽引發,然由開頭幾句極易品得翁、姚二人曾經交往的不愉快。但翁方綱此番有關何、李詩的論述卻不厭其煩,他陳述自己的觀點,指摘何、李之詩的弊端,認為何、李之詩對于盛唐詩歌來說,是“襲其貌,演其腔,吞剝其句與言,在明人已有剪彩為花、木魚為饌、尸舍珠貝為珥之喻矣。此即語言氣象,尚且不得謂之肖”[13]91。何、李詩只得盛唐詩之貌而不得其神,早在明代已有人批駁。在翁方綱看來,何、李詩之長在語言氣象,不足在缺乏根柢融貫。因此,他以根柢之虛空而否定前七子,而重視意、氣、辭的姚鼐對以語言氣象見長的何、李詩持認可態度,則難免使二人的詩學觀點呈現對立狀態。接下來是翁方綱對其重視“根柢”的解釋:“若以根柢言之,則唐人各有唐人之學識,凡一家之氣、體、聲、律,皆有其自出之本焉。自出之本奈何?曰性情而已矣,時勢而已矣,境遇、學術而已矣。”[13]91以唐及唐前各家詩作各有自家特色來反證前七子模擬之非,主張在義理上與古人合,而不僅僅是貌襲。最后從學術角度論述前七子詩歌之不可學的原因,進一步批駁李、何詩“意氣凌人,虛驕而已”的弊端,并稱:“使昔之獻吉、仲默生于今日,將亦必帖然平心,去其矜驕之氣,而為質實之言。舉所謂空同、大復集者,厭而自焚之矣,而豈有吾輩尚學之理哉?”[13]92–93以何、李若生清代當自焚其詩反對姚鼐學習何、李之詩的主張,極有力度。如果姚鼐之《與翁學士書》是對此類書信的回復,其中的意氣蓬勃、當仁不讓或并不難理解。同時,翁方綱以“矜驕之氣”與“質實之言”相對,提出自己反對氣盛之詩的觀點。從姚鼐書對意、氣、辭等的強調,也可看出二人詩學觀點分歧的針鋒相對。
但翁方綱此信與姚鼐書不同的是,不僅其論證有力,且語氣較為誠懇。信末云:“何、李在詩家為前輩,方綱豈敢僭論?顧學者用力之途,則不可誤涉足焉,不僅為?約也。抑猶望于執事之盡棄其夙聞,于何、李之為詩者而易轍焉。則作詩與解經誠為一事矣,不然則學自學,而詩自詩,誠其人而偽其言也,竊為執事惜。”[13]93–94翁方綱反復強調以學為詩,學詩結合,真誠勸說姚鼐放棄對何、李詩歌的推崇,確如姚鼐書中所言,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吐胸臆相教”。在此書后,翁方綱又作《再與姬川論何李書》,此書乃抱疾而作,但更加不厭其詳,尤見翁方綱待人赤誠。書信開篇多為套語。然覃溪與姚鼐論何、李詩的第二書,則以肺腑之言始。其曰:“君子之學,未有以口舌爭者也,以心融而已;未有以意氣勝者也,以心平而已……而謂方綱不喜何、李,不深求之,其可乎?夫何、李則奚性情學術之有哉?此言一出,似乎過當。而方綱敢于為此言者,試觀其集而知之矣。”[13]97“心融”是翁方綱的待人之道,“心平”,則見翁方綱之秉性。不以口舌爭,不以意氣盛,或是針對姚鼐之回信有感而發。姚鼐此書今不見于其文集,書信內容、態度我們只能從翁方綱的回信中略知一二。翁方綱的回復中多提及姚鼐書信所涉言語。對姚鼐“謂方綱不喜何、李,不深求之”“謂方綱論明詩太過”“謂學杜者昌黎、子瞻、山谷、空同(李夢陽)俱在宋二陳(陳與義、陳師道)、海叟(袁凱)之上”等問題[13]98,翁方綱分別給予詳細答復并結合具體實例,說明何、李詩歌復古模擬之弊,甚至其對后七子的影響也剖論甚詳;并借姜夔語,以韓愈、蘇軾、黃庭堅等人為例,表達自己“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求與古人異,不若(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的觀點?①[13]98,同時以證何景明、李夢陽等人詩歌創作中存在的問題。他認為“若使何、李早悟,有何、李之筆力氣魄,而充以自己實學實境,則明之詩可以云詩矣”[13]102,從而闡明其“以學為詩”的詩學主張,并再次把此主張推薦給姚鼐,認為“執事之學之識,則可以為詩者也,則可以為經學,詩學合一之詩者也。既可以為第一等之詩,而甘為等而下之之詩,曰何、李固當如此也。明人固皆嘗如此也,執事請反而思之,恐當啞然自笑者也”[13]103–104。翁方綱推行自己的詩學主張,勸告友人的不懈與不厭其煩,頗見其為學之執著與為人之摯誠。同時,翁方綱質厚平和的文風在此二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質厚平和,是翁方綱詩文的總體風格,也是其性情在詩文中的反映。
綜觀姚鼐、翁方綱的論詩書,不難發現二者在詩學觀點與文章創作風格方面存在的差異。二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姚鼐論詩主張意、氣、辭三者并重,提倡文人之詩的創作,而翁方綱則將為文之法融入詩歌創作,提倡筆力氣魄與實學熔為一爐的質厚平和的“學人之詩”。翁方綱與姚鼐之間的論爭,歸根到底是由學人之詩與文人之詩的不同而引發;而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主張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又和此二人作為金石學家與文章學家各自不同的專長有著莫大關系。翁、姚二人各自堅持自己的觀點,在詩歌創作中也各自呈現不同的書寫視角。
三、翁方綱與姚鼐題跋的比較
翁方綱詩歌較為質實,而姚鼐的詩歌創作則相對更重意境氣勢。現以二人對同一幅《祈巧圖》的題跋為例略作分析。張宣《祈巧圖》,據《式古堂書畫匯考》卷三十八,又稱《漢宮祈巧圖》:“絹本,掛幅長四尺七寸,闊三尺二寸,唐張萱真跡,流傳者絕少,此圖乃其尤最者。向蔵宣和御府,所作朱欄碧瓦,曲折工麗,極盡六宮之勝,幾筵盤盂,種種臻妙。宮嬪三十一人,晚妝妍靚,端雅豐厚,各具意態。至于庭柯掩靄,儼然夜色,洵非神手不辦也。”[14]姚鼐、翁方綱題跋張宣《祈巧圖》是在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年)的七夕。此圖當時為陸費墀收藏,七夕日,由陸氏攜至翁方綱蘇米齋。當時共同欣賞者還有錢載、錢大昕、程晉芳、曹仁虎、陸錫熊諸人。關于此圖,翁方綱作《七夕萚石、辛楣、魚門、習庵、姬川、耳山、丹叔小集蘇米齋,丹叔攜所藏唐張萱〈祈巧圖〉同賦》,詩曰:
去秋秋暑非積霖,椒花舫子書不蟫(魚門、寓齋)。斜街斜月上我襟,此幀在壁靜愔愔。瓜花匜粉圍鼎琛,一人顧步梧影森,二人昂首同穿針。戲盆者亦繡帨紟,一掩紈扇旁沈吟,一于樹側三花陰。花復繞出于髻簪,葵黃桂凈露涔涔。我時送友涼不禁,更訂斯夕指斯今。聚散陰雨毎難任,八人如期果招尋。我齋雖淺坐轉深,絹端如有風露音。蘭堂玉殿鏘鳴金,神光離合燈不侵。九衢人海幾同岑,斯夕觴為斯畫斟。寸絲零落如球琳,生氣炯炯欄砌林。照見世間隙駒骎,多少匠巧棖觸心。三伏已過云不霒,空窗卷待白河沈,曙光耿耿聞驚禽。[5]450
姚鼐作《七夕集覃溪學士家觀〈祈巧圖〉,或以為唐張萱筆也》,曰:
驪山秋樹圍宮殿,列屋同居異歡宴。人人七夕望牽牛,歲歲秋風落團扇。渭南渭北明河光,張生腕底風露涼。定知紈袖停針后,金井殞梧聽漏長。玉貌綺羅天寶末,霜霰未深炎已奪。宮中兒女為情死,墻外書生籌國活。燒燭披圖又一時,夜深題作女郎詩。青天纖月長如此,巧拙人閑那得知。[3]457
翁、姚二詩一立足畫作原貌及與之相關的事實的再現,一立足于自我情懷及人生命運、興廢之感的抒發。前者注重的是學術,出于一金石學家的責任。后者注重的是抒情,有濃郁的抒情言志的傳統特色。兩首詩作,一為客觀題記,一為主觀寫情,分別代表學人之詩與文人之詩的特色。如果以文人之詩的標準衡量,翁方綱的作品無疑難與姚作比肩;但若從學人之詩的角度考量,則翁方綱詩作的學術價值及其為我們了解《祈巧圖》所發揮的題跋功能同樣為姚鼐詩所無法比擬。
翁方綱與姚鼐關于《祈巧圖》的題跋大體代表了二人詩歌的基本特色。然翁方綱其他題材的詩作及部分題跋詩尤其是題畫詩中,也不乏文人之詩的作品。而對于姚鼐來說,文人之詩是其詩歌的主要創作類型,但從題跋類作品來看,其詩作也有一些受題跋文體學術性相對較強的影響,更具學人之詩的特征。如《今歲重九翁覃溪學士登法源寺閣,作“斫”字韻七言詩,亦以屬鼐而未暇為也。學士屢用其韻為詩,益奇。臘月飲學士家,出示所得宋雕本施注蘇詩,舊藏宋中丞家者,欣賞無已,乃次重九詩韻》:
學士金石搜南朔,攬異為詩工刻斫。閉門高興逸如云,舒紙揮毫疾逾颮。今秋九月金垂砌,西嶺無云玉出璞。霜寒勇上寺樓看,風舞懸幡翩不卓。成詩淵海得驪珠,欲和空倉饑雀啄。茲晨招客為看書,來似鴻儔飛撲撲。雕鐫遠有嘉泰字,收藏近與商邱較。蘇詩傳世幾千首,高語去天真一握。當年獄案可悲傷,他日注家還舛駁。此編晚出施顧手,黨禁正解東南角。后來補闕更何如,虎賁雖在中郎邈。耽詩愛古皆結習,計短衡長非大覺。曾薄富貴書何厚,甘典衣裘襟可捉。子瞻自是千載人,學士豈比無心學。佳本與公吾亦欣,叩門會辦來觀數。[3]457–458
另如《為翁正三學士題東坡天際烏云帖》:
東坡自謂字無法,天巧繩墨何從施。青霄碧海縱游戲,自中律度精毫厘。嘗托西湖佳麗地,仍記閑情書小詩。前人不見蔡君謨,后人不識柯九思。人生翰墨細事耳,古今相接良賴之。學士新作蘇米齋,欲飽看字輖饑。此冊神妙尤所秘,云煙閱世憐公癡。今朝我更作公病,斂冊向篋重手持。日午來看到昏黑,兀兀不樂歸車馳。學士平生妙臨本,試作嘗眩真鑒知。請煩冰雪襟懷手,再寫佳人絕妙辭。[3]452
此詩的重客觀與翁方綱《祈巧詩》并無太大區別,筆法平實,呈現出與《七夕集覃溪學士家觀〈祈巧圖〉,或以為唐張萱筆也》截然不同的風格。然而,姚鼐的題跋詩作以題畫詩為主,畫作題跋多以畫面景、物、事觸動作者思緒與情感,從而與畫作產生共鳴,并在此基礎上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翁方綱主張以學為詩,但其題畫詩中,主觀情感表達相對碑刻、書法題跋較常見。姚鼐的題畫之作更加如此,但以上所舉幾例也在一個側面表明實學盛行的時代即使是不主張以學為詩的文人,其題跋也不可避免地會沾染一些重實色彩。而翁方綱作為當時金石之學的擎天柱,在學術責任感與實學之風的影響下,作品重學重實風格的出現,有其合理性。翁方綱以金石書畫之學入詩,也是在“肌理說”的約束與指導下,嘗試在詩歌創作中將義理、考據、詞章三者結合,使詩歌在承載學術的同時,盡可能保持其審美價值。
翁方綱與姚鼐多次論爭,表現了二人在詩歌創作中的分歧,而金石書畫題跋風格的相似,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金石書畫題跋的文體傳統所決定。文章學家與金石學家的不同身份,決定了二人在散文創作中金石書畫題跋文體所占比例的差距。翁方綱大量金石書畫題跋的創作,影響著其詩文整體風格,從而使質實、多考訂等題跋文體通常具備的因素,成為以審美為評判標準而忽略題跋文體特征的批評家詬病翁方綱詩文的理由。質實、重考訂是乾嘉時期學術的重要特征,同時也是金石書畫題跋的文體特點。而翁方綱對金石書畫之學的嗜愛,以學入詩,義理、考據、詞章結合的觀點,則在主觀上推動著金石書畫題跋文體創作的輝煌,并在此基礎上促進了金石之學在清代的獨立與繁興。因此,翁方綱屢遭詬病的詩文,其實對金石書畫題跋及金石學的發展有著他人無法替代的意義。
注釋:
①孫守真疑翁方綱原稿“求”前脫一“不”字,為“不若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參見“任真的網路書房”《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http://13165621.blog.hexun.com/69855915_d.html)第545頁。
[1] 鄭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譜[M].清同治七年刻本.
[2] 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M].乾嘉名儒年譜本:冊8.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3] 姚鼐.惜抱軒詩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二)[M]//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一)[M]//續修四庫全書:第14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M].影印李以烜光緒補刻本.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7] 賈誼.新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69–70.
[8]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M].長沙:岳麓書社,1991:1134.
[9] 皮錫瑞.經學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1954:76.
[10] 姚瑩.東溟文集[M].清中復堂全集本.
[11] 趙爾巽.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7:13396.
[12] 孟醒任.桐城派三祖年譜[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163.
[13] 翁方綱.復初齋文稿:冊1[M].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14]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1523.
〔責任編輯 劉小兵〕
2017-08-19
江蘇高校品牌專業建設工程一期項目“漢語言文學”(PPZY2015C207)
傅元瓊(1971―),女,山東蘭陵人,講師,博士。
I206
A
1006–5261(2018)02–01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