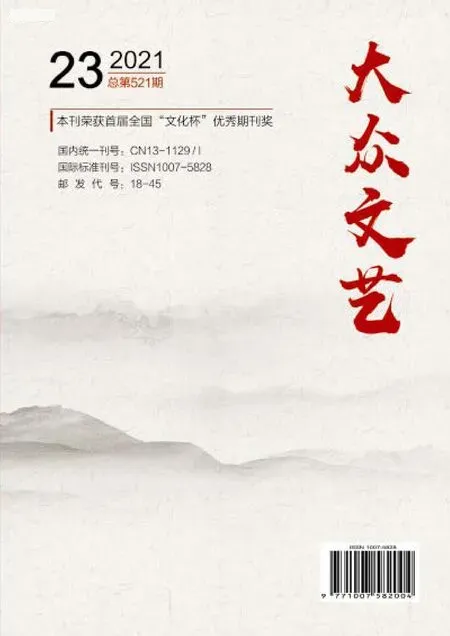80年代小說成長主題的私語性
(畢節職業技術學院 551700)
一、與西方“成長引路人”的切合
在成長小說中,成長引路人是重要的一個構成單元,“從社會學角度看,每一個人的成長都會受到一些人的影響,這些人從正、反兩方面豐富著主人公的生活經歷和對社會的認識,在觀察這些人扮演的社會角色過程中,青少年逐漸確立起自己的角色和生活方向。”1
《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中威廉完成從年少幼稚到成熟沉穩的成長過程中,不能不說受到領路人的引導,外鄉人,牧師等陌生人都在他迷惘或滯留的關節點給予了他指引。另外還有《遠大前程》中具有父親形象的鐵匠喬·葛吉瑞和罪犯馬格韋契,喬的樂于助人和富有同情心,馬格韋契的慈愛和無私都給了主人公匹普很大的影響。而《哈克貝利·芬歷險記》中正直善良的黑人吉姆也扮演著哈克精神導師的角色,這位黑人奴隸的友愛善良促成了哈克道德上的進步,并引導他從少年到成年,無知到有知的轉化。在領路人的誘導下,主人公憑借一系列歷練中的觀察、實踐、體悟,最終真正實現對成長的超越。
《饑餓的女兒》設置了一個非常廣闊的歷史存在領域,從1949年到大躍進時期,從大饑荒到文革,從文革到八十年代解凍時期,歷史跨度雖大,作者卻有意淡化那游離于個人記憶之外的抽象的時代背景,整部小說濃縮在六六狹小的生活空間中進行,以“尋找父親”為一條暗線架構在了“身世之謎”的枝干上。她生命中出現了三個父親,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而牽引著她在成長道路上跋涉。
六六生父的角色是缺位的,十八年都以一個模糊的跟蹤者形象出現在文本中,直到最后的現身卻揭開了這個家庭隱秘的一道傷疤,這個給予六六生命而無力保護和照顧他的父親,實際是喪失了男性家長的權威人格、陽剛的父權特征的,因此,他的角色是一個觀望著,在六六成年后才作為一個情感慰藉與情感回歸的角色出現。養父沉默寡言,忍下家庭的恥辱而將六六撫養長大,然而他卻從未與六六有過心靈上的溝通,他“不動怒不指責,卻終日憂心忡忡地看著她。”這種隔離的情感狀態只能喚起六六對愛的渴望,以至向外尋找愛的填補。歷史老師可以說是一個“父親的替代者”,不能說她與歷史老師的戀情是她叛逆脾性張揚過程的一個偶然事件,是她靈與肉的爭斗中一次不經意的偏失,更確切地說,是她在特殊時代夾縫中破繭而出所經歷的一次必然的陣痛。
劉再復在小說的末尾曾經說過,六六的饑餓是雙重饑餓,“食饑餓”和“性饑餓”,生理上的饑餓使她尋找養父,心理上的饑餓使她尋找生父,身體上的饑餓使她尋找歷史老師這樣一個朋友、情人、父親。然而,他們其中任何一個人都沒有帶領她擺脫現實和精神的困境。三個父親角色的人充當了六六生活的闖入者,他們作為一個觀望者促成了六六成長的催化劑。也就是說,六六并不是借助父親的力量完成了成長,而是通過尋父的過程,實現對個體存在意義和價值的探尋。
二、社會場域的書寫缺位——饑餓“成長”的個體自我關懷
將西方成長小說作一個梳理分析,其實在《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之前,德國作家閔里美豪森的《癡兒流浪記》就已經第一次涉及到人的成長問題。2當時,西歐的長篇小說,特別是西班牙的流浪漢小說在17世紀翻譯介紹到了德國,在這種環境下,德國小說的“成長”主題初露了端倪。任何文學的表現必然帶著時代的投影,18世紀的德國正處于封建體制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因此,德國新生資產階級關注個體的發展首先是關注在信仰心理層面上的,于是,對個體內在心理成長的描寫在此時就奠定了根基。維蘭德的自傳體小說《阿伽通的故事》,就是一部揣摩主人公情感性格的作品,主人公在參與社會過程中不斷豐富自己的閱歷而達到成長。到了歌德1795年開始創作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而真正開啟了歐洲成長小說的先河時,德國成長小說慢慢開始從“內在塑造”轉向了“外在的經驗”,強調了人的社會化過程。像英、法這樣具有浪漫風格的成長小說里,作者傾向于按照主觀的感情邏輯去想象和創造主人公的成長世界,因此,以自己的感情投射來設置故事,并將主人公投入社會場域中進行塑造。
新時期小說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知青文學”等,成長主題都或隱或顯地貫穿于其中,然而那時候并沒有成長小說生存的文化土壤和時代背景,最多是一種帶著歷史傷疤的青春緬懷。就算《青春之歌》這樣比較切合德國傳統成長小說特質的文本,主人公自身的成長經驗教訓也被提升到社會原則的層面加以總結,這種引領社會風向標的成長因對某種意識形態認同而導致了個性生命特質的喪失。 而到了80年代,徐星,劉索拉、王朔等作家也將筆墨觸及到了“成長”的領域,他們的作品描寫成長,戲謔成長,嘲弄神圣和反叛舊秩序的巨大聲音遮蔽下的“成長”書寫,更多讓人看到的是青春的傷痕累累,彷徨后無路可走的迷惑,以及對整個社會秩序強烈的不恭和反叛。盡管如此,作家在關注于個體自我主體成長的同時,與社會歷史時代是緊密相連的。
買琳燕曾在《從歌德到索爾·貝婁的成長小說研究》中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總結了成長小說需要具備的要求:“主角而非視角、時空轉換和心智變化”,3即是以一個主人公為主,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中,努力適應社會,以達到世界觀、人生觀諸多方面的發展。《饑餓的女兒》描寫六六以及和她有親緣關系的幾位女性如母親,大姐、二姐、四姐五個女性,這仿佛與成長小說“一個中心主人公”的特征相沖突,不過作者筆墨輕重的當,因此,也可以看出六六占主體地位的痕跡,以她為主線貫串起一系列女性的命運沉浮;在時空轉換方面,作者集中在六六家鄉而輕描淡寫了社會場景;心智變化也著重在對親情的體認和對苦難的冷靜接受之上。這就是說,《饑餓的女兒》更多關注在成長個體的自我關懷上,而對社會場域的書寫,有一種無意識的遮蔽處理,主體通過自身的認識追尋,完成了自我的身份認證。
“成長小說”曾經被叫作“教育小說”,這就表示成長的過程必定會有教育的施予過程,社會這個大場域必定是不能缺乏的一個施予單位,“德意志發展史小說多半只把它們的主人公帶到他該從事活動和干預世界的地方。”4這就是說,主人公性格的完成,主體地位的確立,必然是在社會化過程中完成的,因此,離開社會,成長小說就失去了成長的土壤。而《饑餓的女兒》在主人公與社會這一維度的展示,顯得有些捉襟見肘。小說中作者沉迷于六六的內在感情流動,而對六六與社會的摩擦接觸,卻用了非常少的筆墨。六六十八歲之前的行蹤幾乎局限在家鄉一片狹小的區域,與家人、鄰居和歷史老師的接觸就覆蓋了她全部的生活軌跡,在此時她被禁錮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并隔離在社會圈層之外,因此很多矛盾都被遮掩甚至忽略。作者對社會的描述集中在她離家出走之后,這及其粗線條的勾勒顯得小說的重心不穩,她成年之后才被拋入社會舞臺,以一種極端化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失落和對青春的反叛,然而這段描寫是少之又少的,作者用一種粗糲化的手筆將六六在社會中的歷練一帶而過,與社會的碰撞過程因此就顯出太輕的分量。其實,成長小說的優勢正是對人社會化的描摹,主人公在面對自己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與社會的多維交涉中逐步成長,而《饑餓的女兒》在這個鏈條上的缺乏,使得小說深度廣度的力度減弱,更多帶上了私人化獨語的性質。
三、結語
本文通過對西方成長小說與《饑餓的女兒》的對照,從敘事人物方面入手進行了研究,分析《饑餓的女兒》與西方成長小說的諸多聯系。但是,在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底盤不斷發生置換的情況下,個人無疑是時代與文化的強導體,因此,拋開時代背景而泛泛討論一個文本,是沒有根基和力度的,這種研究只能作為一種參照系存在,而且中國關于成長的小說帶上了歷史、時代、文化的印記,不但與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緊密相關,還與作家的文化情結和創作理念等因素割裂不開聯系。因此,本文不僅僅以西方成長小說作對比來分析中國小說《饑餓的女兒》,還將它放在時代歷史的大底盤中,尋找出它不同的本土性特色和不足之處,力圖以一種客觀的姿態還原小說的本真狀態和真實內涵。
注釋:
1.芮渝萍.《美國成長小說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25頁.
2.李學武.《蝶與蛹——中國當代小說成長主題的文化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7頁.
3.買琳燕.《從歌德到索爾·貝婁的成長小說研究》,2008年第183頁.
4.余匡復.《德國文學史》,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