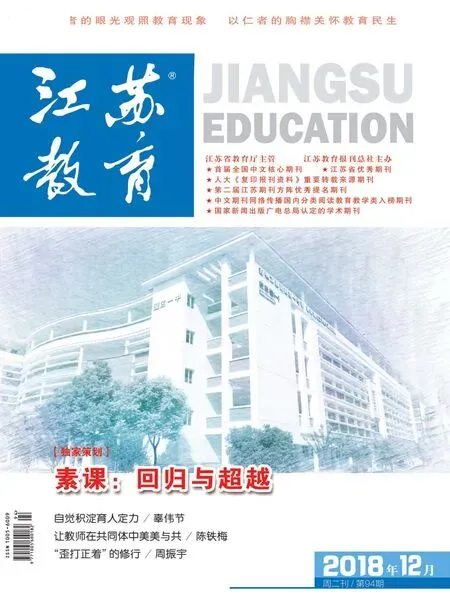“歪打正著”的修行
在絕大多數成功者的成功秘籍里,“心無旁騖”都是核心關鍵詞。但是,我的成長之路卻是迂回曲折的,頗有些“歪打正著”的意味。
一、“歪歪扭扭”的專業發展之路
從進師范學校讀書開始,我的專業發展之路似乎就走“歪”了。很有幸,我當時的語文老師是鼎鼎大名的文學評論家汪政先生,這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事情。先生常常呼吁大家營造一個安靜的教室,教導我們潛下心來閱讀,為人生奠基。可我那時剛從初三一年的題海中穿越出來,正是“樂不思蜀”的年紀,哪里在意老師這些情真意切的教導?參加合唱隊、器樂團、舞蹈隊,癡迷練書法、畫速寫,還報名參加了某高校的國畫函授班,樣樣都想學,樣樣有興趣,最終落了個“雜而不精”的下場。那時家里不寬裕,有限的生活費十之八九用到了這些地方。汪老師每每走進教室,看著滿屋子的二胡、琵琶,聽著到處回蕩的南腔北調的“樂”聲,便會眉頭緊皺,甚而“拂袖而去”,我們卻一臉茫然,甚是費解。畢業以后,漸漸知道老師當時那些“要多讀些書”的話的分量,但是,時光卻再也回不到從前了。
畢業后去家鄉的小學報到,剛跟校長說上兩句話,門外有人大喊,家住學校里面的音樂教師臨產了,正疼得滿頭大汗。校長拉住我一起飛奔,我們用臨時自制的擔架抬著那位音樂教師送到醫院。拖著疲憊的身體重新回到學校,校長盯著我看了良久,憋出一句:“這學期就由你來教音樂吧!”于是,我干了一年專職音樂教師,接著教了兩年數學,繼續兼教音樂,還負責訓練學校的民樂隊。
畢業3年后,我調到海安縣實驗小學,適逢當時學校唯一的自然課教師停薪留職在外創業。報到之日,校長找我談話,主旨是學校希望我能擔任專職的自然教師,并且幫我畫了一個天大的餅,希望我有朝一日能成為一個自然學科的特級教師。那時“特級教師”還是個極稀罕的頭銜兒,我聽得腦袋一陣轟鳴,一臉懵懂。當然,若干年后,等我真的成了特級教師的時候,我把這稱之為發生在我身上的“皮格馬利翁效應”。
我的自然教師身份并沒有一成不變,第二年就變成了數學教師,然后是數學教師兼自然教師,后來又兼教過體育、思品、勞技等等。直到差不多10年前,我才自己痛下決心,放棄了我的數學教師身份,真正成了一個純粹的科學教師。
從2007年開始,我擔任學校的教科室主任,在其位,得謀其政,我不得不花出大量的時間進行學校的“共生教育”課題研究,閱讀重心都放在教育生態學、“共生教育”等方面的教育理論書籍上,寫作的重心也都在“共生教育”研究方面,很少有時間顧及我自己的專業:科學課堂教學研究。這一度讓我非常沮喪,覺得自己的專業發展之路極為不順暢,總是充滿曲折與艱難。我特別羨慕那些可以不管不顧、心無旁騖地走自己的專業發展之路的人,尤其是海安實小在我之前走出過10位特級教師,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有明確的專業發展目標,并且圍繞這樣的目標堅定不移地前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教學思想。華應龍的“化錯”教育、許衛兵的簡約數學、仲廣群的“助學”課堂、賁友林的“學為中心”、徐金貴的“共生語文”、儲冬生的“問題驅動”,都是我內心深處想要效仿和學習的成功之路。可是,我卻總是一路朝三暮四,難以專心沉潛。
從2012年往后,我的發展道路好像一下子順了。2012年我被評為南通市學科帶頭人,2014年被評為江蘇省特級教師,2016年又被評為據說是當時南通市的小學里最年輕的正高級教師。這些稱號當然不代表專業水平本身,但是兩年一個臺階的跨越在圈內也算難得。如今回過頭去看自己走過來的路,依然覺得都是“歪門邪道”,難登大雅之堂。但是,存在的總是合理的,憑我一個資質一般的人,歷經磕磕碰碰,居然也能登堂入室,這種“歪打正著”的背后也會有些深層的原因。
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驚喜
中國傳統文化里講究“舍得”,有“舍”方有“得”。我既不聰明,亦算不上勤奮,老天能夠如此眷顧于我,我究竟“舍”了什么,又“得”了什么呢?回首思量,無非幾點:
其一,失了深度鉆研卻多了廣度涉獵。
雖然最終走上了科學教學研究的道路,但我卻是野路子出身,沒有經過正規的科學類學歷教育。中師時讀的是普師專業,大專、本科都靠自考,專業分別是小學教育和教育管理,讀在職教育碩士時的專業方向仍然是“萬金油”式的小學教育,畢業論文的選題方向是以課堂觀察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可見學歷教育與科學以及科學教學都沒有太大的關系。細細回憶,即使專門從事科學教學之后,也沒有接受過多少科學類的專業培訓。在很多人眼里,科學教師應該是個“博士”,上知天文、下曉地理,問到哪里懂到哪里。我也覺得是這樣,可我自己卻做不到,常常汗顏。
但是,從中師開始,我一直興趣廣泛,文學、音樂、美術、舞蹈、歷史、書法、播音,我樣樣都有涉獵,也樣樣都還玩得不賴。參加工作之后,無論多忙,我總還抽出時間關注我的這些興趣愛好,甚至門類更多,見識也隨著時間的積累越來越廣。說句玩笑話,在教師圈子當中,我是懂點音樂的人當中文學水平比較高的,懂點歷史的人當中書法水平比較高的;與厲害的科學教師比,我對科學知識體系的把握可能不如他們,但是我在科學以外很多方面的造詣卻超過了他們。
這種狀況為我當小學科學教師提供了很好的基礎。首先,我對一切都好奇,對一切都感興趣,這種對于未知的向往深深感染了學生,他們都喜歡跟我在一起,因為跟我在一起非常好玩,人人都成了“好奇寶寶”。其次,小學科學強調不單純傳授知識,而是幫助學生體驗獲得知識、建構知識的過程,這種理念正適合我揚長避短,我了解很多門學科的學習方法與技巧,輕易可以找到幫助學生化解難題、思維發展的方向。第三,廣泛的興趣和知識面讓我具備了扎實的教學基本功:清晰而幽默的表達、好聽的嗓音、漂亮的粉筆字、隨手畫就的簡筆畫、跳脫的思維……這一切,讓我的課輕松超越了很多同行。
2000年,我參加江蘇省小學科學青年教師獨立備課、上課比賽,抽到的課題是《月球探秘》,在全封閉的備課環境下,大家都“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限的教學資源上不出生動的課堂,我卻靠著良好的師生互動引發了學生對月球這一“暗箱”無窮的科學猜想,大家忘情地爭論,最終靠思辨與推理概括出月球的基本情況,我的課毫無爭議地獲得一等獎。2006年,我參加江蘇省的教學基本功大賽,實驗操作、演講、粉筆字、課件制作、理論筆試、說課六大環節,雖然我的實驗操作水平在所有選手中較為一般,但是我卻沒有其他明顯弱項,并靠著演講、寫字和說課的強項一舉制勝。
其二,舍了學科鉆研卻得了理論視野。
海安實小是學者型教師的搖籃,一大波名師在我身邊拔節而起,聲名遠播。他們無一例外地對自己的學科深耕苦研,修為登峰造極。我心向往之而不得,非常焦急。但是,我從事學校的教科研工作,使命在身,不得不耐著性子讀尾關周二、佐藤學,讀范國睿和吳鼎福兩種不同版本的《教育生態學》,讀金生鈜的《理解與教育》,讀柳夕浪的《為了共生的理想》,等等。這些純理論書籍大多艱澀、不好讀,更不好懂。可是,我們要做的不僅是讀懂這些理論,而且是要在這些理論的支撐下建構海安實小屬己的“共生教育”實踐路徑,這是一個開創性的工作,對我們這些毫無理論功底的“土包子”而言,何其艱難!
好多次想放棄,但是領導總在艱難時刻送來寬容與鼓勵,加上年輕的自己不服輸的勁頭,我不但啃了很多本這樣的書,有的一遍讀不懂還反復讀了好幾遍。終于,慢慢讀出些體會,慢慢有了些自己的想法,基于海安實小的“共生教育”路徑也慢慢成形,不斷完善,成果開始不斷顯現出影響力。想起這些,我心中也有小確幸,畢竟自己在其中也有不小的貢獻。但是,稍有閑暇,心中又不可遏制地升起一個念頭:學校的課題研究蒸蒸日上,可我自己的學科專業發展卻停滯不前,慢慢荒廢!
帶著這樣的焦慮,我總是千方百計抽空關注我的學科專業,每年上個三兩節科學公開課,寫上一兩篇學科論文,不讓自己與專業追求漸行漸遠。慢慢下來,也有了些積累,但是一比較心理陰影的面積就大了:很多科學名師每年可以上七八十節公開課,每年發表二三十篇學科論文,我卻只有十分之一都不到;科學名師們對科學教材如數家珍,教材分析如庖丁解牛,教學設計如周瑜一般“一步三計”,不假思索。而我對于教材體系的熟悉程度遠不及此,備一節課常常需要幾天甚至幾個星期在腦子里反復琢磨、反復煎熬,比起諸葛亮的“三步一計”也差之甚遠。唯一欣慰的是,他們的文章更聚焦于學科本身,而我寫出來的文章則更多教學行為背后的理性思考和理論闡釋;他們的文章大多發表在學科期刊上,我的論文則更多發表在綜合性理論刊物上。很多人為在核心期刊發一篇論文而發愁的時候,我卻已經發了十來篇“核心”了。雖然缺了學科鉆研,但卻厚了理論功底,這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
其三,與其顧此失彼不如共生發展。
時至今日,我仍然在學校辦學主張建構和課題研究方面承擔著重要的任務,但是,我又一刻也舍不得放下我所喜歡的小學科學教學。與其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總是面臨顧此失彼的尷尬,倒不如讓學校的教科研與我的個人研究融為一體、共生發展,我開始嘗試尋找“共生教育”與小學科學教學之間的橋梁。
“共生課堂”理念把課堂視為一個生態系統,以學習為課堂的核心目標,強調學生、教師、課程、環境與技術四個課堂生態因子關系和諧、相互促進、共生發展。而科學教學中強調探究,探究式教學的前提條件是教師要放棄課堂的主導地位,退到學生身后,給他們留出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只有當他們陷入困境的時候才現身助推。這兩者之間有太多的共通之處,只是需要一個可以操作的路徑把兩者連通起來,“共生課堂”就能落地,我的科學教學也就有了理論之根。
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我在《中小學教師培訓》發表文章,提出了我的“問題驅動、板塊推進、嘗試交流”的“共生”科學教學主張。所謂問題驅動,指在學習活動開始時,教師要通過巧妙提煉生產生活中的實際難題,引導學生認真討論,分解成若干個可供研究的問題,這些問題之間既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學生在完成學習的過程中需要逐一解決這些問題,還要嘗試在這些問題之間進行思維鏈接,互相驗證、互相協調、互相妥協,直至完成任務。同時,我們認為學習過程不應該是教師與少數學生的蘇格拉底式逼問,而是學生團隊圍繞某一主題持續開展的學習活動。課堂學習的結構不應該是師生一成不變的問答式線性推進,而是圍繞主題展開的學習活動模塊的串聯。當課堂的結構簡化成三兩個關鍵的學習板塊時,自主學習才擁有了時間與空間上的可能性。在每一個學習板塊內部,圍繞核心問題或本原問題,應該讓學生先獨立思考或利用教師提供的材料進行自主探究,嘗試形成解決問題的屬己辦法。在充分嘗試之后,或者嘗試陷入困境時,再開展交流活動,嘗試提煉學習過程中的思考,發現、反思、改良嘗試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逐步建構概念。2016年6月,我在江蘇省“教學新時空”欄目向全省科學教師網上直播了用“共生”科學教育理念執教的《平衡》一課,獲得了點評專家們的高度評價以及觀課教師們的廣泛關注,課堂實錄在《教育研究與評論》雜志發表。
針對國內的分科學習體系當中學科壁壘森嚴、學習過程割裂、學習狀態被動、學習進程劃一等明顯的弊端,海安實小從2012年起與北京中關村三小、深圳南郵小學等七八所國內名校一起成立了小學教育國際聯盟,共同學習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小組倡導的項目學習(PBL)方式。成立大會回來后,我們迅速組建了團隊,培訓教師,創編并實施項目學習案例。從無到有,從模仿到建構,幾年的時間下來,我們形成了符合中國學校實際情況的項目學習實踐經驗與理論思考,形成了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的一套項目學習課程。學生進校后每學期經歷一次歷時一周到一個月不等的項目學習過程,12個學期的12次學習經歷共同組成了一個系列化的項目學習周期。如今,海安實小的項目學習課程基本成熟,我撰寫的課程實施綱要在《教育》雜志發表,我的實踐經驗與理性思考也在《人民教育》“眾創”欄目發表,關于項目學習的整體研究水平走在了全國前列。2017年,學校將項目學習研究申報江蘇省基礎教育前瞻性項目,成功獲得立項。整個申報過程我都積極投身其中,從項目申報書的起草到現場答辯,從理論的思考到案例的開發,我都親力親為。這一兩年來,我們又嘗試在語文、英語等學科領域開始了學科教學項目化實施的探索,也取得很好的效果。
與項目學習的研究相伴相生的是,在科學教學領域,從西方刮來一股STEM教育的改革之風,我國也將科學、數學、工程、技術的融合列入了最新版的《小學科學課程標準》,使之成為科學教育領域最熱門的研究方向。STEM教育理念和項目學習理念都強調以項目或問題驅動,立足于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都強調跨學科的融合學習,都強調學生團隊的合作學習、深度學習,兩者之間存在太多的共通之處,甚至嚴格說來,STEM教育就是項目學習的一種具化的表現形式。因為有著長期研究項目學習的基礎,我們將項目學習的理念融入科學教學中,STEM教育自然水到渠成,鑒于這樣的理解,我們所展示的STEM課堂顯出了與眾不同的深度,海安實小也得以成功獲得了江蘇省“STEM教育實驗學校”、全國“STEM教育領航學校”的稱號。
外國人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中國人說“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都旨在告訴人們,通向成功的道路千千萬萬,不拘一格。現在回過頭來看,自己看似走了“歪”路,其實只是發展道路的“巧妙不同”而已。無論走怎樣的路,只要是適合自己的,那就都是好路,只要永遠向前,終能修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