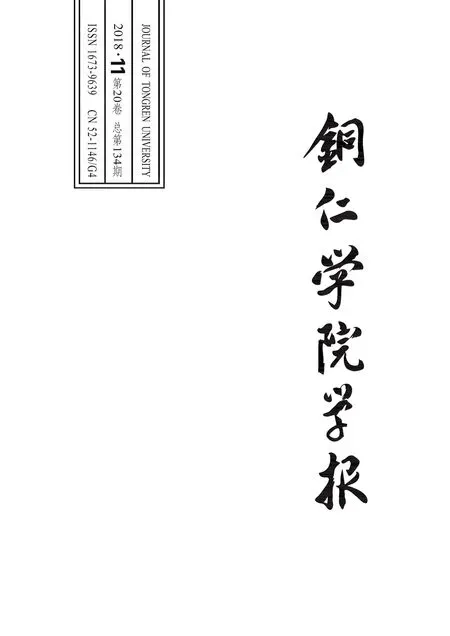追本溯源與學術創新
范子燁
?
追本溯源與學術創新
范子燁
(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范子燁(1964-),1964年5月生于內蒙古莫力達瓦旗尼爾基鎮,次年5月遷居黑龍江省嫩江縣城郊人民公社團結大隊第五生產小隊。黑龍江大學中文系學士(1985)。哈爾濱師范大學中文系碩士(1988)。陜西師范大學文學研究所博士(1994)。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集部文獻與文學研究”項目首席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教授、中國古典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內蒙古藝術學院音樂系兼職教授,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兼任中國《文選》學會理事、中國孟浩然研究會理事、中華文學史料學會理事、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理事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古文學與文化,兼涉中古史、中國古代音樂文化史和游牧民族音樂史等等。主要著作有《魏晉風度的傳神寫照——〈世說新語〉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悠然望南山——文化視域中的陶淵明》(東方出版中心,2010),《中古文學的文化闡釋》(臺灣成文書局,2011),《春蠶與止酒——互文性視域下的陶淵明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和《竹林軒學術隨筆》(鳳凰出版社,2012),發表學術論文二百余篇。
進入本期“梵凈古典學”欄目,可以發現這里是一個中年學者與青年學者交相輝映的學術天地。學術的激揚與靈感的躍動,發生在不同年齡段的學者身上。他們的學術書寫是各具特色的。而以個人的學術理性,試圖恢復古人的本真,邀接古人的心靈,成為古人的異代之音,則是這四位學者的共同追求。
陳桐生教授的《殷商甲骨卜辭的散文成就》一文,追溯我國散文的源起,為我們還原了先民散文的草創時代。他指出,殷商甲骨卜辭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散文文獻,在我國散文史上有篳路藍縷之功,構成了我國散文史最早的一環。文章認為,殷商甲骨卜辭散文的藝術成就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作為中國記敘散文之祖,甲骨卜辭已經具備了記敘散文的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這些基本要素,甲骨卜辭記敘事件首尾的寫法,對此后記事散文產生深遠影響,這是從中國文學發展史宏觀上著眼的;二是甲骨卜辭用字特別精煉,講究措辭精確,驗辭之中有少量描寫文字不乏精彩之筆,這是從書寫工具的角度考察的;三是甲骨卜辭開始運用一些簡單的比喻修辭手法,這是從文章學的角度來進行觀察的。在論述的過程中,作者援引了大量的殷商甲骨卜辭,并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充分表現了作者在先秦文獻方面的深厚功底。作者的態度是冷靜的,論斷是科學的,“由于甲骨卜辭處于中國記事散文的發軔階段,因此在討論殷商甲骨卜辭散文成就時,我們要特別注意把握分寸,既不要低估殷商甲骨卜辭所取得的敘事實際成就,又不能無限地拔高。”基于此種認識,作者指出:“與中國后世規范成熟的記敘散文相比,殷商甲骨卜辭在敘事藝術上還處于非常原始的簡陋狀態。殷商巫卜祝史并沒有散文寫作的意識,他們只是在忠實地履行王命,如實地記下占卜情形。由于受到書寫工具以及文體的限制,殷商甲骨卜辭這一文體在基本定型之后,其敘事結構基本上沒有多少發展演變的空間,它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這種論斷足以表明作者是多么富有學術經驗!更足以彰顯作者在自己專攻的學術領域游刃有余的大家風范。我從來佩服老陳,原因就在于此。
王小巖博士《知音的詩學——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知音”話語分析》一文,發現并闡釋了古代文藝批評常用的一個術語——“知音”。他認為,“知音是中國古代調節作者與讀者關系的重要術語。知音本來是指鑒賞音樂的能力,進而指能鑒賞音樂的人,在音樂鑒賞屬公共話語范疇的時代,知音指能夠洞察政治治亂之人。”就音樂鑒賞而言,這是第一個層面。其次,伯牙、子期的故事意味著“知音開始用于解讀私人之志的人”,這是音樂鑒賞的第二個層面。由此“知音”開始用于文學批評,特指那些符合作者預期的理想的讀者。以清晰的理論辨析和理論意識為基礎,作者進一步指出,“與音樂‘知音’必須依靠現場不同,文學‘知音’可以遠離作者的時代,延遲到‘千年之下’,作者借此摒棄讀者的平庸之見,樹立寫作的信心。”讀文至此,我確實怦然心動。很多文學史上的杰出作家,常常寄情于來世,在孤寂的一生中,常常對自己的作品的知音有一種身后的預期,如杜甫稱李白“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即是此意。從揚雄到陶淵明,也無不如此:揚雄到六朝始被尊奉為漢代以來的新圣,而陶淵明到蘇軾時代才其道大光。西方作家如卡夫卡、紀伯倫之類的人物,也都有一個被重新發現的過程。即使在音樂、繪畫藝術的領域,這種情況也比比皆是。更為可貴的是,小巖在最后一部分特別捻出戲曲“知音”的問題,指出:“元代以后出現的戲曲‘知音’,需要重回表演現場,需要有對戲曲作品、戲曲表演作綜合批評的能力。經由一些戲曲批評家的論述,戲曲‘知音’轉向指代專業戲曲批評家,這與明清文學批評轉向專業化契合。”小巖本來師從李玫教授,專攻戲曲之學,故其所言所論,皆有依據,由此其所闡釋的“知音”意涵不斷擴大,而全文一脈貫注,層層遞進,文思縝密。對于《文心雕龍》關于知音的理論,小巖石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尤其是對劉勰提出的“六觀”法,他給予了深入的闡發,由此摒棄了關于作家作品的不可知論,足以堅定我們追求艱深閱讀的文學信心。小巖的文章寫得好啊!
雖然討論的話題不同,李光先博士的《劉勰夸飾觀辨析》一文卻與小巖之文具有關聯性,這種關聯之點就在于《文心雕龍》這部體大思精的理論著作。光先從大處著眼,從小處入手,對夸飾的本義詳加辨析。他認為,“夸飾的本義是夸張和矯飾”。具體來說,“夸張指直接對事物進行夸大、縮小之辭,矯飾指借助具體事物進行矯飾,從而夸大、突出抽象事物的奇特之辭。夸張用在具體物和人,矯飾適于抽象事物。”在論證過程中,他旁征博引,或取人之長,或正人之謬,揮灑自如。在此基礎上,他指出:“夸飾的原則有四:一是依據事實,二是符合義理,三是抓住要點,四是要有節制。”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光先是從《文心雕龍》的整體格局來審視夸飾問題的,這就是劉勰的宗經思想、征圣思想、奇正思想和中和思想,這些思想都反映在《夸飾》篇中。這篇文章顯示了作者扎實的理論基礎和清晰的邏輯思維,對于《雕龍》之學的研究在局部上確實有明顯的推進。
談到《文心雕龍》,自然離不開《文選》。如徐中原博士所言:“關于‘選學’,學界多從版本、校勘、音韻、訓詁、編撰,以及《文選》與《文心雕龍》之關系及其與時代之關系進行了較為深入、透徹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的《讀<文選>李善注札記二則》是一篇短小精悍的考證文字。“書名的背后反映書名擬定者或著錄者的學術思想。”由此種認識出發,他詳細考察了從《水經》到《水經注》,從《文選》到《文選注》的書名的嬗變過程。文章指出,《文選》李善注引酈道元注《水經》之“注文”專稱之為《水經注》而非《水經》,反映了李善重酈道元“注文”的價值取向。由此,《文選》李善注創生了《水經注》專書名。李善所注《文選》,從唐至清,清之前各種目錄著錄其題名為“文選”,反映了對“選文”的文學范本意義的高度看重,這是與封建科舉考試重辭科的需要相適應的;而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卻著錄其題名為“文選注”,反映了對“注文”考據意義的重視,這是與清代盛行的乾嘉樸學思潮相適應的。這些解說都是富有新意的,值得我們重視。中原的這篇文章喚起了我早年的學術記憶。多年以前,我曾經從李善(約630-689)《文選注》出發考察《世說新語》之原名。《新唐書》卷220《李邕傳》:
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為《文選注》,敷析淵洽,……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這是《文選注》得名的早期記載之一。李善在其《文選注》中征引《世說新語》,皆以《世說》為稱。如卷13晉潘岳《秋興賦》李善注引《世說?言語》第107條,卷20潘岳《金谷集作詩》李善注引《世說?仇隙》第1條,卷21南朝宋顏延年《五君詠?向常侍》李善注引《世說?文學》第19條,卷38南朝梁任昉《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李善注引《世說?言語》第83條,任昉《為蕭楊州作薦士表》及卷39任昉《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啟》和卷40任昉《奏彈劉整》李善注,皆引《世說?德行》第23條,卷42魏曹丕《與梁朝歌令吳質書》李善注引《世說?巧藝》第1條,卷50南朝宋范曄《逸民傳論》李善注引《世說?言語》第61條,卷59南朝梁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李善注引《世說?賞譽》第32條,卷60任昉《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李善注引《世說?文學》第66條。據此,我得出如下結論:“由上述兩方面,并參以《南史》卷十三《劉義慶傳》、《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世說新語》原名為《世說》,已是鐵案無疑。”(《<世說新語>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頁)此種研究路徑與中原不謀而合,而他能夠從學術和文化的時代取向考慮同一部經典名稱的變化問題,則是匡我不逮。
本期的四篇論文都具有很強的探源求真的意識,所取得的學術創獲也是顯而易見的,在學術研究的范式上也多有可資借鑒之處。
梵凈山人
2018年7月15日
(此文為本期“梵凈古典學”欄目主持人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