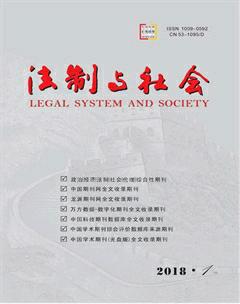拉米斯與激進民主
摘 要 20世紀70年代一些小規模的社會運動此起彼伏,拉米斯的激進民主思想由此產生。本文在拉米斯呼吁將民主變成一種常識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他對西方民主體系的批判,并由此提出如何回歸民主美德。
關鍵詞 激進民主 民主狀態 民主美德
作者簡介:李玲,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5級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中圖分類號:D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1.177
在西方許多民眾甚至是社會科學家都把民主看作是一套有利于人們贏得和擁有這種權力的制度時,拉米斯卻要求為民主正名,認為民主應該是一種常識,呼吁將民主回歸。
一、拉米斯與激進民主
(一)理論產生的背景
由于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取得較好的發展,社會相對穩定,社會結構發生了較為顯著的變化。在冷戰后期雖然大規模的工人運動鮮有成功,但是一些小規模的以訴求新社會變革的環保運動、女權主義的運動、反對種族歧視的運動等依然非常有活力的存在著,這就激起了左翼對反資本主義道路的全新探索,激進民主應運而生,拉米斯就是一個代表人物。
拉米斯在總結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新社會運動的經驗,提出要促進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多樣化發展,形成面對面的小團體,爭取用普遍的價值思想在社區等公共工作場直接行使民主和自治,壯大公民的民主,建立自由的空間,逐步消除資本主義代議制民主的制度安排,也可以替代傳統左翼的權威主義的組織方式使得左翼重新獲得目標和號召力,這樣一來民主將再次和人民站在一起。
(二)激進民主的界定
拉米斯經過對民主的梳理指出了“民主”被統治者盜用來為他們治理國家提供合法性,民主的范圍逐漸縮小,為此他提出要為民主正名,還原民主原本面目。面對眾多思想流派對民主的定義,拉米斯提出“民主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被選擇的生活方式,除此以外還有別的選擇。” 這就可以理解為權力被有原則的使用,民主達成一個共識從未逐漸轉變成一種常識。
“所謂民主就是人民擁有權力,而激進的民主就意味著本質、要素形式的民主,根本民主,確切地說就是民主本身。” “激進”更清楚的說明了民主的本質和構成要素,是民主在政治上的一種激進模式。換而言之,激進民主就是將民主直接放置在政體的中心,它不會向某一邊移動,并且它的中心源泉就是人民民主。激進民主主張權力來自于人民且使用于人民,而不是由少數統治者去支配。
二、對西方民主體系的批判
(一)民主狀態的局限
孟德斯鳩認為民主狀態應該先于制度,民主狀態是立法者的位置由人民自己占領,它的美德應該是肯定的、有創造性的,且能夠建立比較公正的法律。而拉米斯對孟德斯鳩的這種民主狀態卻不是很贊同,他指出“所謂的政治美德背后的政治制度不過有三種形式,一個人的、少數人的、或者是大多數人的統治,而在這些統治的背后其實還有兩個具體的狀態:即腐敗的統治與不腐敗的統治。” 拉米斯所指的民主狀態是大多數人的不腐敗的統治。再結合孟德斯鳩的觀點后會發現:如果將美德和腐敗看成約束民主“規范性”的要素,那有沒有美德或者有沒有腐敗都不會影響制度的存在形式,人民根據自己的意志或自己認為的政治美德去組成不同的政治團體,代表自己利益去行使民主權力。
由此拉米斯提出由民主狀態所產生的權力難以被解釋或者甚至難以形成對這種權力的認知。在總結一系列社會運動的經驗后,拉米斯指出激進民主并不是簡單的意味著人民要有一致的行動,而是人們能夠憑借對彼此的信任結合在一起自發的去做一些事情,這就是一種無形的力量,而這種人民的力量在一起發揮作用時就變成了自由的行動。當罷工成功了,人們的要求得到滿足之后,一切又恢復到原本的模樣,權力很快又回到了統治者手中,人民的自由的行動又再一次變成了制度化行動。看似民主的力量能夠帶來一系列的變革,卻不知在這種情形下民主的狀態反而顯得脆弱。激進民主在這種狀態下就很難運作,人們不知道該如何利用好民主的力量去保持一種平衡感,政治美德的不可描述性導致即使是身處民主狀態之中,人們也不知該如何描述他們的狀況,只能一次又一次的不斷回到被管理的狀態中去,這就是民主狀態的一種局限性。
(二)反對民主的帝國
從雅典的傳統民主中我們可以看見在由公民構成的少數族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其實是與民主狀態相近的某個東西。但是關于古希臘和羅馬,我們則該反思為何最后它們反而成為了一個殘忍的帝國,而不是民主的帝國。在伯利克利統治時期的雅典還是十分繁盛的,等到了聽從亞西比德時就逐漸敗落。同樣,羅馬在最開始的共和國時期是值得其他國家效仿的,可是在后期的內部腐敗之后,就變成了一個殘忍的帝國。或許有些學者認為這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可是作為激進民主主義者,拉米斯提出:“這些制度或者體制之所以會出現破壞,其實在它們的本質里就有問題。” 在雅典人的集體行動中,他們的主要內容是征服,他們在打敗波斯人之后忙著把自己建立成一個帝國,他們覺得這樣做是出于他們自己集體的意志,而不是在有權柄的統治者的制約下做出的,這就使得他們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這種力量卻又沒有能力去容納自身的一個民主現狀,就不得不去繼續擴張,雅典在這種情況下卻沒有辦法尋找一個確切的點去停止這樣一種不民主的行徑,雅典最后終結于使它強大的軍事力量。而羅馬帝國也是相似的情形。
從雅典和羅馬兩個國家我們或許會產生疑問,假定軍事可以維護這樣的帝國長久發展,那在這種軍事包圍下的帝國去建立一個民主政體又會是怎樣的一個結果?如果假定成真,那么公民就必須同時生活在兩個政治身體中,“民主”的身體和帝國的身體,顯然帝國的身體又會侵害“民主”的身體。拉米斯認為:“這樣一來,激進民主在“民主”國家之中其實具有顛覆性的。” 當一個國家試圖通過軍事力量去擴充自己的領域來給本國的人民更多的權力,其實質上它也在破壞別人的民主,在一個共同的生存環境下,擴張后的國家所實現的民主其實是一種自我毀滅模式,因為在此狀況下并沒有能力去真正的尋找有效的方法來達到民主的狀態,這種自我毀滅直接地同激進民主的實質相抵觸。endprint
拉米斯認為就激進民主而論,帝國的民主不是一種真正的民主,那些謊稱為了國家的民主而斗爭的想法應該受到摒棄,一個國家的民主可能只是短時間的存在,那如果所有的國家為了一個更大的民主的世界去斗爭,那么這才是真正為民主斗爭的最大意義。
(三)跨國境的民主
在西方國家,帝國的權力不斷具體化,形成了三個實體:在國內假冒的民主、廣大的軍事組織以及尋求將全人類和全自然置于管理控制之下的跨國公司。這樣一來那些影響廣大人民的重大決定將不再由人民在自己國家作出決定,而是由一些大政府、跨國公司等機構作出決定,而此時的參與性民主則指有著能夠作出影響一個人的生活決定的權利。倘若作出決定的權力能夠跨越國界則對抗這種權力的權利也就可以跨越國界了。在跨國界的民主中,大家提到的最多的不是利益而是正義,只有通過呼吁正義才能在其他國家尋找到支持者,因此他們的立場也是普遍的。
這就導致一個“跨國境的民族”的產生,作為一個抽象的存在它是沒有力量也沒有權威,可是一旦將周邊國家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等方面的差異融在一起形成一個有意識的公共體,那它的力量就是無窮的,勢必會引起很多國家反對。因為有很多民族比較喜歡通過種族戰爭和屠殺性質的部族戰爭來保持它對人民的至上性。在此情況下跨國境的公民社會就很難長久立足,人民就會把希望寄托在跨國境的政治運動中,借助信息交流、人員聯系、相互理解和聯合行動來擴大它的影響。
可是在跨國界的運動中,會下意識的將利益塑成正義,從而將正義與權利又聯系在一起,雖然在跨國界的政治運動中沒有強制執行者,但是如果利益、權利和正義的關系權衡不好,就會導致這種運動無法被不同民族的人們接受,一旦過多的將利益渲染成正義就會滋生腐敗,如此一來人們反思是否真的是公平民主。
三、民主美德的回歸
(一)公共信任
在民主環境中建立的社會秩序是相對穩定有序的,而這種社會秩序的建立更是來自于人們彼此的信任,所以那些通過暴力手段、戰爭掠奪、官僚統治等方式建立起來民主社會只會增強人與人之間充滿恐懼感和距離感,沒有信任自然就不能更好地追求民主自由。對于信任感所創造出來的秩序,通過可以結合盧梭的社會契約來理解。因此可以把契約看作是一種諾言,而諾言在未侵犯自由的情況下就建立了秩序。信任關系是通過無數的承諾和契約建立起來的,有些信任關系是明確的,但是大多數的信任關系則是不明確的,這些承諾和契約使人們在無數的年代和無數的世代的日常生活中所慢慢建立起來的。
信任不是道德,卻能產生美好行為和美好的人格。當一個國家的人民彼此信任,依照信任產生的社會契約去生活,那么這樣狀況下的人民的民主狀況就會產生很好的效果,這將會是一個很好的民主狀態,人們不會因為自己的個人要求沒有達到或者因為對方沒有遵守約定而去進行斗爭,相反,每個人心中都遵守承諾,相信美好的人和物,這就減少了社會爭斗,促進社會向一個更美好的民主狀態發展。
(二)民主信仰
民主信仰是建立在對人民所可能出現的軟弱和害怕恐懼的理解的基礎上,民主信仰是決定去相信人們能夠在一定狀態的基礎上去建立自己的信任。費爾巴哈曾主張人類是從自己最優良的品質中創造出上帝,但是這位上帝有著道德上的確定性,而這種確定性恰好是人類所不能達到的。其實在道德上沒有絕對的確定性,因此對于信仰的選擇要慎重,一旦選擇錯誤的對象,就會使我們走向錯誤的道路。唯一能夠使我們“更好、更勇敢和更積極”且不會讓我們變得愚蠢的信仰,這是一種對現實人類的信仰,也是對民主的信仰。
因此在人的信仰中,不可能產生出一個明確的結果,人民不是呼喚上帝來給予民主,民主其實是人們的一個信念或者一種信仰。在此拉米斯指出“重新以現實的人作為信仰的原初和唯一恰當的對象是民主思考的開端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激進民主不要求引進一些英雄主義的新倫理,它要求我們更好地使用已經擁有的一些常識性的美德。
(三)公共幸福
阿倫特在《論革命》中提到“當整治行動成功地產生了真正的權力時,參加者們將經驗一種幸福感,不同于一個人在私人生活中找到的幸福感”。公共幸福其實也是民主美德的一個方面,一些民主運動或者一些公共運動的產生都是因為某些方面或者某些要求未能達到期待值,這便會產生一定的遺憾,可是當一場運動一旦開始產生真正的公共希望時,人們的這種遺憾就會消失。
公共幸福是自由的人們在公共信仰被贖回并且被歸還的人民手中的,自由的人民是見到公共希望成為公共權力、成為現實的人民。可見公共幸福其實追求的是一種分享的感覺。這種幸福使得人民不再遭受某種異化的力量的壓榨,而是他們此時正在做的某種東西。
公共幸福的經驗在我們時代的政治中是一個少有的經驗,在所有的地方都曾經歷過公共幸福,有的時候可能會很短暫。因此,要想考量一個國家的民主狀態如何,就要看看公共幸福是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有存在的可能性。
注釋:
][美]道格拉斯·拉米斯著. 劉元琪譯.激進民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1,15,100,120,122.
參考文獻:
[1][英]恩斯特·拉克勞查特爾·墨菲.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2][美]查特爾·墨菲.政治的回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