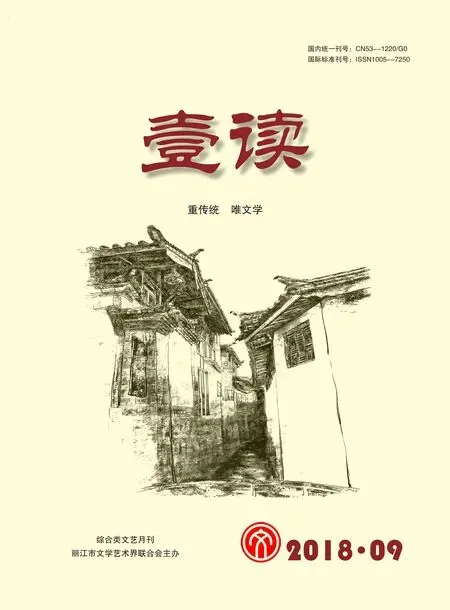沙瑪大哥
芭納木
在二零零三年的那個暑假,曾經有過一段難忘的經歷,里面有一個我一生都難以忘懷的彝族大哥。
那時我還在寧蒗縣城當老師,有幸參與縣里的一個調研項目去牦牛坪,是平生第一次去到一個人口多又純粹的彝族聚居區。同行的四位男同事也都是彝族,他們做彝族畢摩文化方面的調研工作,我負責拍攝圖片資料。現在他們個個都成了彝文化專家,我則成為了一個老文藝青年。這并不妨礙我們變成了一生的摯友,因為我們都是追求純凈靈魂的人,和深愛著自己民族文化的人。
牦牛坪是寧蒗縣城東邊高山上的一個平壩,海拔高,氣候冷,土地多產量少,那時只有洋芋、蕎麥、燕麥和蔓菁。那里的洋芋是我吃過的最好吃的洋芋,沙沙的,甜甜的,是老天賜給那塊美麗卻曾經貧瘠的土地最好的禮物。初到那里,放眼望去,視野開闊遼遠,廣袤的土地上,蕎麥花和洋芋花美得無法形容。山坡上綠草茵茵,點綴著星星點點的牛和綿羊,牦牛們在這個季節則進入了更高的山里。迎面而來的風帶來了周邊森林的香氣,花的香氣,還有泥土和青草的香氣,令我興奮不已。我從小都是這樣的一個人,只要有美景,就會立馬愛上這個地方,不管吃住的條件怎樣。我很慶幸,現在依然如此。
第一個晚上,村委會殺了頭一百多斤的豬做成坨坨肉招待我們,這是彝族比較高的接待禮儀了。記憶中吃飯的人很多,大家都很熱情,風景又好,村委會的房子也不錯,在那里睡得很好。第二天一早,我是在幾個男同事亢奮夸張的洗漱聲和高聲談笑中醒來的。起床去洗漱時,一位四十多歲身形魁梧,長相憨厚的彝族大哥慌忙過來幫我打水。我笑著對他說我會打井水不用幫忙,但他還是幫我打了水,并解釋這不是井是地窖。我那時還想著井和地窖不都一樣,把水桶放下去打水提上來不就可以了。后來喝過了水才知道,井水和地窖水區別可大了。早餐時,見到這位大哥在廚房里給我們做苦蕎粑粑和煮茶,我才知道他是村委會請來的炊事員。因為成年人不可以讓比自己還大的人伺候你,我馬上就過去幫他準備早餐。他很客氣,覺得你是縣里來的專家,不能讓你幫忙,我卻執意要幫。這樣,我知道了他的彝族姓是沙瑪,我就叫他沙瑪大哥了。他的漢語還可以,他和我的男同事之間用彝語交流時,簡單的我也能聽懂,同為彝語支的摩梭語和彝語很多單詞是一樣的,半聽半猜就好了。
苦蕎粑粑我從小就很愛吃,那地窖水煮出來的茶就難以下咽了。顏色渾濁不說,還苦,澀。“從沒喝過這么難喝的水。”我在那里叫嚷。沙瑪大哥笑著不語,那幾個男同事就數落我了。說牦牛坪自古缺水,現在還是政府幫忙修了水窖,下雨時把雨水存起來,一年才有水喝。“哦。但是周圍都是森林,植被那么好,應該有山泉水,怎么不把山泉水引到村里呢?”我又問。他們告訴我,離這里最近的一眼山泉來回要走七八公里,而且方圓幾十公里只有那一眼泉水。我心想完了,這一周我就只能喝這苦澀的地窖水了。想到這里,我的記憶突然就被打開了。在我很小的時候,曾經當過解放軍的爸爸,經常會講他以前參加剿匪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就發生在牦牛坪。一九五九年,當時編號為三六七八部隊的解放軍在牦牛坪剿匪,土匪一直占據了那里唯一的一眼泉水。有一次他的兩個戰友趁天黑去取水,結果被躲在林子里的土匪開槍打死了一個,另一個跑了回來才得以幸存。后來經過長期爭戰,才奪得這一眼泉水。如果這地方真的只有一個泉眼的話,那就應該是這一眼泉水啊!我開始興奮起來。另外,我的小姨也曾繪聲繪色的跟我講過,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縣文工團會去牦牛坪慰問演出,她當時是團里的舞蹈演員。每次去,那里的彝族姑娘們會提前一天,來回走十幾公里路,把文工團喝的、洗漱的水背好等著。那時我就會想,該是多淳樸多善良的人們,才會用這樣的方式來歡迎給他們送去精神食糧的人?在那樣一個缺吃少穿的年代里,還能有如此美好的心靈。那這些可愛的人們應該是我周圍的這些人了!我立馬激動地給男同事們講了這兩段故事。他們跟我開玩笑說我現在是他們的敵人了,因為我是解放軍的女兒,他們是土匪的后代。我就跟他們嬉皮笑臉:“好吧,敵人就敵人咯,反正還不是從此要一鍋吃飯,有本事就不要跟我一起吃!”一整個早上,我們就在那里貧嘴,憨憨的沙瑪大哥就在那里看著我們笑。從那時,我就隱隱感覺到他身上有一絲孤獨和苦楚,我甚至于在想他是不是孤身一人,所以才會這么享受地看著我們說笑打趣,所以一個大男人才會來村委會做飯。當然關于這個猜想,后來的答案是否定的。
那天傍晚,當我們回到村委會時,沙瑪大哥已經煮好一大鍋雞肉和一大鍋米飯等著我們了。那是高山的彝家養了兩年以上的大肥母雞,又香又油,那漂在雞湯上的金燦燦的油,至今還清晰地浮現在我眼前,現在已經很少能吃到那樣的雞肉了。雖然我現在回老家也能吃到正宗的土雞肉,但我們壩區和高寒山區的雞肉真是沒法比的。沙瑪大哥給我們擺好碗筷就到門外抽煙,無論我怎么叫他他都不進來和我們吃飯。那幾個男同事跟我說不用喊了,他可能是客氣,也有可能村委會主任要求他不要和我們同吃。我一下子覺得不舒服了,都什么年代了還講階級,人又不多,才六個人,一起吃不就好了,但在人家的地盤上我也不好安排。于是我拿了個大碗,夾出最軟和的幾塊留給他。因為不能讓比你大的人吃你的剩飯剩菜,還因為我早上見到他笑時,一整口牙沒剩幾顆了。雞腿也留了一個給他,因為在摩梭家里,雞腿是給家里的男長者吃的,他比我們幾個都大,又是給我們做飯的辛苦的人,理應由他來吃。我就像個摩梭主婦一樣在彝族家里安排著飲食,現在想想真是可愛啊!這回男同事們不再玩笑我了,而是贊賞地看著我,隨我安排。
之后的那天,令我至今還在過意不去、還會濕了眼眶的事情發生了。早飯時,我突然發現茶水的味道變了,變得好喝了,苦和澀的味道蕩然無存,我高興得又在那里嚷嚷開了。沙瑪大哥見我喜形于色,也開心地看著笑。一個男同事說,因為昨天早上我說地窖的水苦,不好喝,沙瑪大哥就一大早背著個二十斤的塑料壺去背山泉水了。我頓時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接下來就為自己的不當言辭勞累了別人而羞愧難當,在那里連連致歉,沙瑪大哥自然也是憨憨地笑,那就是沒關系的意思。男同事們見我實在是抱歉的樣子,便安慰我,說因為昨晚給沙瑪大哥單獨留了雞肉,還一天幫他干活他才感動了去背泉水給我喝的,叫我放心喝吧,還說托我的福,他們也喝上了好喝的泉水。我這才安下心來,也暗自竊喜:我對別人的關心竟然馬上就得到了回報!
后來的幾天,雖然我一直要求沙瑪大哥不要再去背水,我可以喝地窖的水的,但他嘴上從不做回應。每天早上,那個發黃的二十斤裝塑料壺,依然會如期地,安靜地擺在廚房的墻角,裝滿甜甜的山泉水,裝滿一個魁梧木訥的彝族漢子對一個善良活潑的摩梭妹子的喜愛之情。我們倆一個出生在寧蒗縣城的東面高山上,一個出生在離縣城好遠的北面的永寧壩子,中間相隔近二百里,因為這壺飽含愛意的泉水,讓我們有了兄妹一樣深的感情。整個寧蒗縣恐怕有數都數不過來的山泉水,數都數不過來的家庭,為何這一眼泉水,獨獨使得我們這一家中有三個人,和這眼泉水,和泉水周圍的人有這樣的緣?莫非冥冥之中有神靈的安排?我常常會思考這個問題。
那一周,我和沙瑪大哥相互合作,默契地安排著一日三餐。牦牛坪氣候冷涼,很少有蔬菜,偶爾會有人家的屋后種著幾棵青菜,幾叢小蔥,路過時我就會去跟人家買。但那些善良的人從不會要錢。后來蔬菜我就不再提錢了,直接討要。雞蛋、雞就買,我們有生活補貼,而且還是歸我管,每次我都想多給點,但結果是從來都沒買貴過,山里的人真是淳樸啊。有時我還會直接鉆到人家的里屋去翻老洋芋和老蔓菁,要回來做菜。直到那次才發現,這山區的彝家真是困難啊,七月沒過,新洋芋沒出來,家家都只有不多的一堆老洋芋堆在屋角了,再有個半袋蕎麥,半袋燕麥,有點買來的白米,就是條件比較好的了,每次我看到這一切時心里都不是滋味。
沙瑪大哥教我揪去老洋芋長長的芽,削了皮做菜吃,因為洋芋芽有毒不能吃。吃老蔓菁就只有芽可以吃,整個塊莖基本上是中空的,邊上是干癟的,沒什么可吃的了。也是在那一次,沙瑪大哥教我用蕎麥的嫩葉做菜,炒菜煮湯都可以,十分好吃。每次用蔓菁芽做菜時,我就跟沙馬大哥說這是彝族老爺爺的胡子,從地里摘回來的蕎麥葉子,我就說是彝族老奶奶的羅鍋帽。后來蔓菁芽就被男同事們戲稱為“彝族老倌兒的胡子”,蕎麥葉被他們戲稱為“彝族老媽媽的羅鍋帽”,感覺我們天天都在吃人的胡須和服飾一樣。生活雖然清苦,卻過得充滿了趣味。
那時,幾個男同事豪情萬丈,激情滿懷,常常被各種美好的愿景和宏大的規劃亢奮得不會餓也不會累。我那時并不懂畢摩文化為何,以及它對于彝族的意義,但也深受他們感染。當然現在我知道了,畢摩文化對于彝族,是精神的源頭,是思想的出路。一個民族的思維結構和行為模式,只有它的原始宗教可以去梳理和指引。這在其他民族也是一樣的。我前面這個幾千年來能夠固執地死守自己信仰的民族是值得尊敬的!無論這種信仰的實用功能在今天究竟還有多大。
我就這樣跟著他們翻山越嶺,走訪周邊的村寨,午飯常常晚點。但只要看到美景,看到古樸純粹的民族服飾,舉起相機就忘了饑餓和勞累。我有幸看到了成片成片的紅豆杉樹是多么的美麗,風吹過時,沙沙作響的她們是那么的高貴和優雅。有幸看到了長坡上洋芋和苦蕎和燕麥如何把綠色漸變。有幸看到了成百上千林立的木條,造就的柵欄充滿了力量和節奏的美感。有幸看到了彝族大媽一根一根搓出的羊毛線織成的只有三個顏色的羊毛裙,是那么的樸素而莊重。有幸看到了彝族女孩將自己的情感和對色彩的認知,一針一線詮釋在刺繡里,悄無聲息。有幸看到了平時略顯卑微的彝族婦女們,打跳時是那么的熱情奔放,完全壓倒了男權的樣子……啊,太多的幸運。我將這所有一切,拍成了圖片,保存下來,也記在心里。當我老了走不動的時候,我才會把這一切畫成畫,讓人們看到,那個時候的美!
一周的調研結束了,由于我有另一個項目要參加,較男同事們提前一天返回縣城。臨走,我交接了財務,把組里用剩的筆記本、碳素筆等文具全部送給沙瑪大哥,因為他家里有讀書的孩子,我真的有些掛念。有多少次想找去他家里看看,但總是想著他會不會不好意思,最終沒去成。當我收拾好行李,坐著村里唯一的一輛跑縣城的吉普車,離開村委會的那個清晨,這五個男人顯出了不舍的情緒。也是,我不在了他們多無趣啊,只剩下了酒。沙瑪大哥依然是笑笑的,沒說什么,但那種笑和之前有點不一樣了。我倒沒有更多的不舍,那時我滿以為這個地方離縣城又不遠,我還會回去的。想著可以約人去攝影,或是可以去畫畫。但是離開了十五年,卻再已沒回去過了。
回到縣城的當晚,我打了個電話給村里小賣部,想了解下他們的情況。那時牦牛坪還沒手機信號,我們都去小賣部用座機和外界聯系。正好村委會主任在那里,他告訴我,從我走后,沙瑪大哥就開始喝酒,喝得爛醉如泥,中午晚上都沒做飯,那幾個男同事自己做的飯。那一刻,我的心揪著疼。我是何德何能,一周,讓一個荒山僻野里的中年大哥,和我有了這樣的情感。可以為我早起一個多個小時去背泉水,無論我講什么,可以靜靜的傾聽,然后報以兄長般慈愛的笑容。是的,我知道,他把我看成了一個給他枯燥貧窮的生活帶來歡樂的人,一個仿佛生在和他不同的地方,等他過了半生才來相見的,處處關心和愛護著他的妹妹。結果這種相聚如曇花一現,馬上就過去了。所以他才不顧自己的職責,連最后一天的飯都不做了。
是的,此生不止一次看到過,一個個剛性過火的彝族男人,當他脆弱到不堪一擊時,會如何用酒精為自己剩下的路壯行。我都懂。我仿佛看到了《巴黎圣母院》里埃斯梅拉達對于卡西莫多的意義,仿佛看到了《人猿泰山》里珍妮對于的泰山的意義。雖然這兩個故事里是愛情,我們是親情,但那種兄長般的喜愛,和妹妹般的依賴之情,多數時候這兩種情況是相通的。因為這兩個故事最后都是悲劇,讓我尤其傷感。
大概一周后,我把所有照片沖洗出來,把村里人的照片挑好,準備請那位吉普車司機帶回去給村民時,才發現竟然沒能給沙瑪大哥拍一張,也許是在一起時光忙著做飯了。那時真的好后悔啊,想著下次回去找他補拍,結果再已沒回去了,一晃就是十五年。
去年,牦牛坪終于接上了自來水。知道消息后的那天,我無比的興奮,真心為牦牛坪人民高興,在網上到處留言,評論。因為我知道常年喝地窖水是什么滋味,常年沒有充足的水洗頭洗澡洗衣服是什么概念。我們離開牦牛坪后不久,國家低保政策開始在村村寨寨鋪開。后來,牦牛坪大量引進了中草藥種植產業,加上交通便利后,勞務輸出和農產品輸出,讓那里的經濟收入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些我們走訪過的農戶,應該早就大變樣了。
現在,我已移居麗江多年,每次回老家,看到牦牛坪山梁上那些充滿詩意的白色風車時,我都會想,我的沙瑪大哥應該也過上好日子了吧?子女應該都成人了吧?但同時也會有一絲擔憂,一個動不動就喝酒的中年男人,會不會健康欠佳,已經去世了呢?那我就真見不到他了。
人生就是這樣,你會有一兩個雖然已經不再聯系,但一直會像掛念自己的親人一樣掛念著的人。你明明知道相隔不遠,可以馬上就去尋找,但似乎又沒有更為充足的理由去找他們。既然這樣,那么,就讓他們繼續長駐在你的心里吧!等有一天緣分到了,自然就會再相見。此刻,只想真摯的禱告,我那個彝族的哥哥,還在離我不太遠的地方活著,活得平安和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