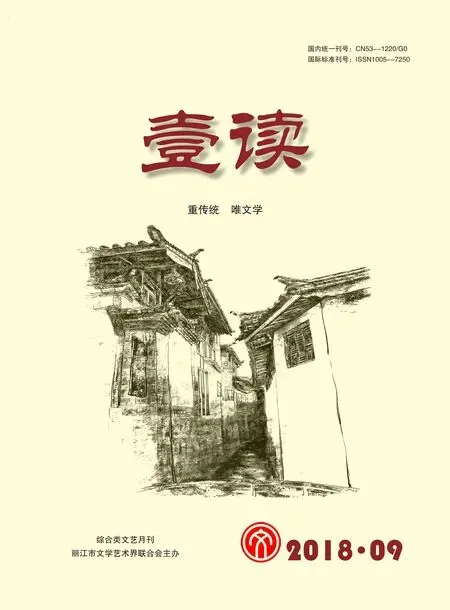一個人的時間簡史
華秀明
1
公元一九八八年,王三泰死后三個月,他建造的那座碉樓被拆除了。這碉樓堅固無比,王家興請了七八個幫工足足用了半個月才把它拆除完畢。未拆除前的碉樓,土木結構,樓高七丈,跟村中那些低矮的泥墻瓦房相比,儼然是拔地而起的人工建筑了。
因為這座碉樓,王家興和父親王三泰在“文革”中被批斗,說是建造碉樓是保護私有財產的,是漏劃的地主,被整得死去活來。大冬天的,以朱朝芬為首的紅衛(wèi)兵沖進碉樓揪出王三泰和王家興父子,讓他們站在村中的曬場上接受批斗。一個村子的人,在那時全成了王家的仇人。他們往王家興父子身上潑冷水,在他們的褲襠里塞蕁麻,還強迫他們喝糞水。
后來朱朝芬和王家興這一對冤家竟然還成了兒女親家,王家興的大女兒夢蘭嫁給了朱朝芬的長子順發(fā)。王家興說到當年被批斗的情形,朱朝芬臉紅得就像打了雞血,場面十分尷尬,王家興說了幾次,就不再說了。
王三泰是在他的碉樓里去世的。
拆除碉樓是有原因的。王三泰臨終時,回光返照,他抬起一只枯枝一樣的手指著碉樓的西北角說,把它——把它——交給政府!王三泰說完這句話就咽氣了。
這就奇怪了,莫非有什么寶物藏在這座古舊的碉樓里?之前,大概是在一九八三年,那時王三泰早已不是什么“富農”了,包產到戶,形勢一片大好,階級斗爭漸行漸遠。王三泰的心開始活泛起來。有一天,王三泰率領兒子兒孫拿著鐵鍬、鋼釬之類的開掘的工具,背著手圍著自家在“文革”中早已被夷為平地的老屋基轉了幾圈,突然停下來,指著一個土堆下面說,就是這里,給我挖!
要挖啥,誰也不知道。畢竟上了年紀的人,誰也不好拂他的意,挖就挖唄,王家興和七八個子女有一鍬沒一鍬地掘起土來。挖了三天,連一根毛也沒挖出來,王家興急了,說,爹,你說挖,我們就挖,挖了三天,除了土啥鬼影都不見一個,您到底要挖個啥嘛?
剛說完這句話,厚厚的土層下面?zhèn)鞒觥扮I”地一聲,他的鎬頭碰到了一個硬物,聽聲音像是金屬之類的東西發(fā)出的。
“小心,小心,怕是挖到了!”王三泰一把從兒子手中奪過鎬頭,扔在地上。他蹲在地上,用一塊木片一點一點地刨去浮土,那物什很快就露出了它的面目,是個香爐。
王家挖出銀錠和宣德爐的消息不脛而走。
山村里很快就來了兩個收古董的,神秘兮兮的,裝作走親訪友的樣子。
按照王三泰的意思,香爐是絕對不能賣的,香火要一代代傳承,賣了它豈不斷了香火?這只香爐是朱家灣王氏一脈代代傳承下來的,就是在那些逃荒要飯的歲月,先祖?zhèn)冋l也沒打香爐的主意,更何況現(xiàn)在天下太平,吃穿不愁了。王三泰的意思,破“四舊”的時代過去了,把香爐從土里挖出來,重新續(xù)上香火,好讓祖先庇佑子孫后代,讓他們繁榮昌盛福祿綿長。
王氏家譜記載,這王氏一脈源起江蘇淮陰大槐樹,不知道這大槐樹是一棵樹,還是一個地名,總之家譜上說他們遠祖曾做過大宋仁宗皇帝的駙馬,后來歷朝歷代都有祖先在朝或地方為官。后來這一支衰落了,因天災人禍輾轉流離,大約在清朝光緒年間遷徙到了這個小山村。
王三泰拗不過獨子王家興,最后還是變賣了香爐。
那年冬下,王家掘地窯燒磚燒瓦,在朱家村首先建起一排七間青磚瓦房。
莫非這碉樓里還藏有古董?
王家興把耳朵貼近他爹王三泰的嘴,大聲叫起來,爹,你要說啥你就說嘛,我聽著哩,啥子東西要交給政府?王家興多么希望從這個將死之人的口中再聽出點什么來。
守孝僅三個月,王家興就迫不及待地要拆除他家這座在村中屹立了七十余年,經歷無數(shù)風雨的碉樓。動工那天,王家興從自家堂屋里搬來陶瓷香爐,在碉樓門口上了三柱香,磕了三個頭。他率領一家人和幾個請來的幫工開始拆碉樓。
2
青龍溪發(fā)源于背籮山,白虎溪發(fā)源于水頭山。青龍溪流出十余里后與白虎溪交匯,孕育出一大片平整的土地。兩溪交匯后,水量陡然大增成了河。當?shù)厝税阉麨榍逅樱逅铀澹荒晁募境讼奶焐胶楸┌l(fā),河水有點泛黃外,其余時間都是清粼粼的,遠山近嶺倒映水中,當然還有兩岸綠了又黃黃了又綠的肥田沃土。
河岸上是當?shù)馗粦糁爝h山開辦的水碾房,青磚青瓦,一盤水碾子長年在環(huán)形的碾槽內緩緩地轉動著,發(fā)出隆隆的悶雷滾過天邊似的響聲。
現(xiàn)在是春二月,幾架水車吱吱呀呀地工作著,沿河一帶的秧田里進了水,秧苗淺黃淺黃的。水車汲水灌溉不到的土地里,豌豆花開得蓬蓬勃勃。一塊豌豆花田里,白色的花多,藍色或嫣紅的花少,偶爾有那么幾朵零星地點綴在白色的世界里,看上去煞是搶眼。
今年王三泰家的豌豆花田里,有幾朵花開得很特別,這幾朵花比普通的豌豆花要大出許多。起初人們誰也沒注意這種花,直到它們從花田里探出頭來,艷麗奪魁時人們才察覺它們的與眾不同。
王三泰家的豌豆花田里開出了一種奇怪的花。
這事一傳十,十傳百,一下子在朱家灣傳播開去。人們爭相前來觀看這種花,嘖嘖稱奇,誰也不知道這是一種什么花。
但王三泰知道這是什么花。
去年秋天,田地里的莊稼收割脫粒揚場進倉后,跟往年一樣,王三泰肩頭搭個褡褳又去永北城攬活了。
說起永北城,這已經是鄰縣的轄境了。這永北城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間,是滇西北的一個重鎮(zhèn)。城內街道縱橫店鋪林立人煙阜盛。
走了三天,這天王三泰進入城來,已是午牌時分。他先在“蘭子掛面店”吃了一碗掛面,墊了個底,出了面店朝縣衙這邊走來。仿佛到了永北城,不去縣衙看一眼,就跟沒來過似的,心頭空落得很。縣衙大門兩邊,各有一個挎槍的兵士守衛(wèi)著。王三泰往里瞅了一眼,右首那個當兵的橫了他一眼,他不敢往里多看,趕緊走開了。他摸了摸肩上的褡褳,里面還有一個銀元,硬硬的硌手。這永北城許多人家都給女孩取名叫蘭子,誰也不知道這永北城里到底有多少個蘭子。他要去紅云巷,紅云巷有個他往年相好的,也叫蘭子。頭天進城,攬活的事不忙。
翠云軒其實不是軒,只是幾間青磚瓦房而已,不知道哪個文人雅士給它取了這么個名號。進入翠云軒,老鴇過來打招呼,一眼就認出了王三泰。打扮得花枝招展,卻又難掩厚厚的胭脂俗氣的老鴇從腋旁斜襟那兒抽出一塊絲巾,撩了一下三泰的臉頰,操一口流利的永北話說,客家今兒個要點哪個妹子?
三泰扭捏了一下,說,蘭子嘛,你曉得的,我只跟蘭子!
老鴇掀開簾子朝第三間瓦房里喊,蘭子,你表哥來了!
唉,就來!瓦房里應答著。不一會兒進來一個青衣女子,一雙小腳,不施脂粉,看上去臉色臘黃臘黃的。
三泰說,我說的不是這個蘭子,是去年冬天在你這兒的那個蘭子!
老鴇說,你是說去年冬天——騾子屁股水蛇腰,眉間有顆胭脂痣的那個蘭子——她早嫁人啦!
嫁人啦?三泰一下子失望起來。
嫁誰?
靈源的龍五老爺,三十個大洋贖她出去的!反正是蘭子,要不這個蘭子您就將就一下?老鴇說。
去年此時他在這里偎紅依翠,今年此時卻是人去樓空了。世間事再也沒有比這物是人非更讓人傷感的了。三泰搖了搖頭,走出了翠云軒。
靈源在城郊。這里依山傍水,建寺廟一座,叫靈源寺。方圓十里每逢集日,總有善男信女來廟里上香,所以香火非常旺盛。寺廟依山而建,廟中的觀音圣像相傳是唐代著名畫家吳道子的手筆。圣像是作在廟中石壁上的,金漆描畫,果然是吳帶當風端莊典雅。在城中吃過早飯,一大早三泰就來廟里上香了。
到了廟里,三泰在功德箱里投了幾個銅子,從廟祝手里接過三柱清香恭恭敬地插在香爐里,俯身磕了三個頭,許了一個愿。在廟里逛了一圈,王三泰就出來了,也不曉得他許了個什么愿。
經過一個莊戶人家當路的一面院墻,七八個人圍在那面院墻下看墻上的告示。三泰也湊了上去,原來那墻上貼的是一張招工的告示。三泰不識字,問旁人墻上寫的是什么?那伙人中,有一個識文斷字的,他打量了三泰一眼,見他肩上搭個褡褳,像個攬活的短工,就說,你這老鄉(xiāng),莫非想謀這份差使?
三泰點點頭說,我想攬活!
那人指著告示說,那我告訴你,天下不太平了,土匪猖獗,這不,昨天晚上土匪又洗劫了上方村,糧食牲畜搶劫一空。龍五老爺家要募工筑碉樓!你要攬活就去他家,他家正需要你這樣的短工哩!
王三泰眼前一亮,趕緊問,那龍五老爺家在哪里?
那個夫子模樣的人就指著不遠處的一座青磚院落說,那不是?趁早去吧,去晚了恐怕您謀不這份差使啦!
原來龍五老爺家就在靈源寺出門左手面的一塊坡臺上,門前有一對威武的石獅子,遠遠看去倒像一個辦事的衙門。這龍五老爺在永北城里開了幾處米店,店里自有掌柜和伙計打理,每日里他手里捧個黃銅煙壺踱步去店里打個照面,人卻住在郊外。
三泰在龍五老爺?shù)拈T首躞蹀了半天,出來一個管家模樣的人說,你這人在這里探頭探腦了半天,你要干啥?王三泰說他是看了墻上的告示才來的,聽說龍五老爺要筑碉樓,想來攬這個活兒。
那人說,你是木工土工還是泥水匠?
三泰說,我會筑墻。
管家朱天佑從頭到腳地把三泰打量了一遍,見他身板結實,倒也像個筑墻的把式,就說,你跟我來!
這是個七進七出的院落,兩旁有數(shù)十間廂房,院中用花磚隔斷開來。這院子其實是個分隔開來的大花園,院中栽種了幾十株臘梅。眼下已是秋末冬初,梅花未開,卻也看得出來那青灰色的枝條上隱隱冒出打了蠟似的芽苞。
偌大的院子,四角上有些房屋已經拆除了,地上散亂地堆放著磚石和木枓。院子南面是個很大的糧倉,原來龍五老爺城里的米店出售的大米,都是從這里發(fā)出去的。天下不太平,看來龍五老爺確實打算筑碉樓了。
管家朱天佑帶著三泰進入院子,在東面的賬房里作了簡單的詢問,做了登記,領了鋪蓋出了賬房左拐,進入一個角門,眼前是一排十來間瓦房。原來,這里才是干體力活的下人居住的地方。從這里看出去,正北面是后門,七八個短工正在那里進進出出地往里送材料。朱天佑打開第三間瓦房,屋里共有七八個床鋪,他指著其中一個空位安頓了三泰。離吃晌午還有些時候,朱天佑說,一日三餐都在這院子里,你先歇歇,下午開工,休閑時不要在院子里胡亂走動!說完,就出去了。
十天后的一個上午,王三泰接到了一個臨時的差遣,管家要他牽馬隨龍五老爺去一趟后山。三泰從馬廄里牽出龍五老爺?shù)哪瞧ド砀唧w健的大白馬,在院里集束整齊,這才把馬牽到大門口候著。過了一盞茶的工夫,龍五老爺出來了,他身后跟著二人抬的一頂小轎,轎簾下垂,不知道轎里坐的是什么人。
三泰牽著馬,龍五老爺騎在馬背上,后面緊跟著一頂小轎。一行人走了半個時辰,來到后山。這后山上有一塊幾十畝大的坡地,荒著。坡地上,這里一堆那里一堆,堆放著無數(shù)小墳包一樣的草皮灰。接近山腰的地方,隱隱露出四五間黃泥小土屋。龍五爺一行朝山腰的那些小土屋走去。
方伯帶領七八個短工從土屋里走出來,迎接龍五老爺。
五爺來啦?方伯問候龍五爺。
嗯,來了,來了,龍五爺說,你這里準備得怎樣了?
方伯說,草皮灰已焐好,只要散開這些草皮灰,今天就可以開種。
嗯,好,很好,你辦事就是周全!龍五爺轉身朝轎里喊,你下來吧!
轎夫放下轎子,掀起軟簾,出來一個懷孕的女子。天哪,這不是蘭子嗎?想不到轎子里坐的竟是蘭子,還懷了孕,挺著個大肚子。三泰擦了擦眼晴,看到的一切跟做夢似的。
龍五老爺說,你把那東西拿出來吧!
蘭子解開斜襟開的襖兒,從貼身的肚兜下面掏出一小袋東西遞過龍五老爺。原來那一小袋東西撐大了她的小腹,她不是懷孕,三泰又是一驚。
方伯說,嗯嗯,這東西就是要沾女人家的氣息,尤其是那種地方的女人——相信來年,五爺?shù)墓麅壕拖衲切┠腥说墓麅阂粯哟蓪崳∪畟€大洋,值!
蘭子臉頰緋紅,站在一旁低頭不語。龍五爺爽朗地笑起來,方伯也笑起來。一陣山風吹過來,他們笑聲便在風中散布開來了,就像開在春天的一種無比燦爛的花。
四個月后,龍五老爺?shù)乃淖飿强⒐ち恕}埣掖笤赫嫉貎砂儆喈€,四座碉樓分別修筑在龍家大院東西南北四個角落。每座樓有五層,每層均設有機槍射口。雖然天下不太平,鄰近許多村鎮(zhèn)都遭了土匪的搶劫,但有了機槍又有如此固若金湯的防御工事,龍五老爺總算可以長長地舒一口氣了。
三月間龍五老爺帶領了一個小衛(wèi)隊,依然讓三泰牽馬,他們又去了一趟后山。喲嗬,前次來這里還是一大片荒山幾間黃泥小屋,這回卻變成了花的世界。你看那花一朵挨一朵,每一朵都是那么艷麗,就像永北城醉春樓中那些穿了粉色、紅色、紫色或天藍色旗袍的娘們兒,甚至比那些穿旗袍的娘們兒還要妖艷。
看著一朵白色的罌粟花,三泰想起了在翠云軒初次相遇的蘭子。
那天蘭子剛從鄉(xiāng)下來。蘭子她爹是離永北城三十里地銀官村的一個小地主,他在田原深處有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幾匹騾馬,二十余畝水田;家里雇有長工和忙月,日子倒也過得殷實。可惜好景不長,蘭子她爹染上了煙癮,先是典當家當,漸漸地又開始抵押房屋田契,祖宗留下的家產被他典當一空,最后打起妻兒的主意。就這樣,蘭子被她爹以十個銀元的價格賣給了翠云軒的老鴇柳翠兒。
當天夜里,老鴇柳翠兒就把蘭子的初夜以三個銀元的價格賣給了王三泰。王三泰不是那種朝三暮四的人,每年秋后,來永北城攬活兒,他只去蘭子那里。跟其他煙花柳巷的女子不一樣,蘭子從不沾染鴉片,蘭子恨死了鴉片。
幾十畝罌粟花離結果還有十來天。龍五老爺帶領他的衛(wèi)隊巡視了一遍罌粟花就回來了。
碉樓竣工,結算完工錢,龍五老爺遣散了其他短工,唯獨留下三泰。結算完工錢的第二天,龍五老爺又率領他的衛(wèi)隊,連同三泰朝后山走來。這回,那幾十畝山地里,罌粟花全凋謝了,一根根直立的植株頂端結滿了雞蛋大的果子。收割生煙的季節(jié)到了。這時警戒就顯得尤為重要,龍五老爺把自己的衛(wèi)隊分成兩班倒,在罌粟地邊日夜巡視。
三泰參與了收割生煙的任務,接下來還要把當天收割下來的生煙熬制成煙膏。
割煙是個技術活兒,煙刀從罌粟果的表皮劃過,一般是三至四道口子,那口子不能深也不能淺,力道要均勻,深了淺了罌粟果都不能流出乳白色的汁液。三泰心靈手巧,看過割煙的老把式方伯操作一遍就會了。從每一個罌粟果上收集起來的生煙,在空氣里氧化后呈黃色,待到熬制成煙膏后就成黑色了。要不了多久,這些煙膏會被送進永北城大大小小幾十家煙館。
修筑碉樓的那段時間,龍五老爺每隔十五天就去城里翠云軒老鴇柳翠兒那里接過來七八個女子撫慰那些短工。作為翠云軒過來的女子,蘭子也被龍五老爺插進了慰安女子之列。
在這些慰安女子之中,三泰寧愿龍五老爺克扣他工錢的三分之一,他只要蘭子。這樣一來,就沒有其他短工跟他爭蘭子了。在過去的四個月內,沒人染指蘭子,蘭子是他一個人的蘭子。當然,這樣的日子不是很多,每隔半個月才有這樣的一個夜。
第一鍋新煙熬成,龍五老爺和方伯就躺在床上迫不及待地要品評今年地頭產出的新鮮貨。后山比不得家里,有三姨太伺候,龍五老爺便叫來三泰,替他捶腿。
吸了幾口,方佰說,今年這煙油性大,比其它煙要好,送進城五老爺可要賺大發(fā)了。
龍五老爺說,討你吉言,果真如此,明年再把東邊那塊荒地拾掇出來,一并種上這玩意兒。
三泰替龍五老爺捶著腿。
龍五老爺冷不丁說,三泰,你們那旮旯產豌豆么?
不曉得龍五老爺為啥突然問及這么個問題。三泰愣了一下說,產的,我們那旮旯豌豆好得很!說到豌豆,三泰有點兒自豪,他們那旮旯確實盛產豌豆。
龍五老爺說,要不,你也弄上兩口?
三泰說,我不弄,聽蘭子說,這東西害人哩!
龍五老爺和方伯就笑了,笑得很開心的樣子。
說到蘭子,方伯說看來這娃對你屋頭那女子感興趣了——三泰你弄三百大洋來,我讓五爺把他屋頭那女子轉讓給你,如何?
三泰說,我沒錢,我要是有三百大洋,我早把她弄走了。三泰低頭為龍五老爺按上一顆煙泡。龍五老爺“咕,咕”地吸了幾口,吐出一陣煙霧來。
你娃真想有錢?龍五老爺說。
三泰說,五爺說笑了,這世道誰不想錢,只是錢不想我!
龍五老爺和方伯又笑了,笑得開心。
這有何難,我給你幾個果子,有豌豆的地方就能種植,這東西頭一年必須要適應水土第二年才長得旺盛。給多了也無益,到時你拿兩個果子回去延個種,一兩煙土一兩銀,到時你還怕沒錢?龍五老爺說。
有了錢,你可以帶走那個女子,不過我有個條件,明年,不,后年你把所有的煙土送我府上來我按價收購,你看如何?龍五老爺又說。
3
第一年,王三泰在豌豆地里收獲了幾十個果。人們問,三泰,這是啥?三泰說,藥材,永北城的龍五爺托我種的藥材。
第二年,到了豌豆花開的季節(jié),王三泰家臨河的那塊田里開出的全是罌粟花。周圍大片大片豌豆花在這個季節(jié)全失去光澤。
站在罌粟花田旁,三泰又想起了山那邊的那邊的永北城。
那年臨走前,王三泰是給蘭子留下了一句話的。臨走前的那一夜,龍五爺安排蘭子侍奉三泰。三泰說,我走了,按照約定,龍五爺會待你如閨女,沒人再接近你的身體,你好生呆著,兩年后我來娶你!蘭子流著淚答應了。
那年老爹帶三泰去翠云軒是有原因的。
之前,三泰談過一門親事。女方是河那邊陳家莊陳三貴的閨女。洞房花燭夜,新人安歇,突然房梁上躥下一只貓。那只貓是在捉老鼠,它碰翻了五斗櫥上的一只瓷瓶。瓷瓶墜地,黑暗中傳出一聲瓷瓶碎裂的脆響,再加上貓捉住老鼠時喉嚨里發(fā)出的嗚嗚聲和老鼠吱吱的慘叫聲,三泰冷不防被這些聲音嚇著了,軟得就像一根煮熟的面條。那以后,三泰再怎么嘗試都沒能堅強起來。過了一年,三泰沒有任何起色,女方家退回了所有聘禮,把女兒帶回去了。
你說怪不怪,也許這就是緣分吧。
那年秋后,他跟老爹去永北城攬活,直到憂心忡忡的老爹把他帶進翠云軒,直到在那里遇到了剛從鄉(xiāng)下來的蘭子,這個問題才從根上得到了解決。
在一大片罌粟花里,王三泰覺得蘭子就是其中一朵白色的罌粟花。那一年,蘭子用自己的身體為龍五爺捂花種,眼前這些花都是沾上了她的芳澤的。
三泰把自己的嘴唇貼上了一朵開得正盛的白色罌粟花,他仿佛又嗅到了當年蘭子身上那些白色的芬芳。罌粟花無罪,罪惡的是人。三泰知道鴉片這東西害人,蘭子一家就是被它毀掉的。而眼下為了得到蘭子,他不得不種植這種花。三泰站在花田旁,一時陷入了矛盾之中。
朱遠山從他的水碾房里鉆出來,手搭涼棚朝這邊張望,一望就望見了王三泰站在那塊艷麗的花田旁。朱遠山就從他的水碾房那里走上來,跟三泰搭話。
大侄子,朱遠山說,你這花兒咋不見你澆過一次水啊?
三泰說,這花不大喜歡水,這里靠近河邊地皮潮,這點水汽兒就夠它消受了。
朱遠山說,這花好看得很,你給我兩個果兒,明年開春我也種點花看!
三泰說,這是永北城龍五爺托種的藥村,可不敢亂給!
朱遠山說,小氣了不是,鄉(xiāng)鄰鄉(xiāng)親的,你給我兩個果兒又咋啦,龍五爺如何曉得?
三泰說,您看,正開花哩,結出果兒還早,到時又說,到時又說!
朱遠山朝四周瞅了幾眼,四處沒人,這才放低了聲說,聽說永北城那邊有人在種一種東西,叫鴉片,一兩鴉片一兩銀,聽說那東西可值錢哪!
朱遠山又打量王三泰幾眼。
三泰說,嗯嗯,聽人說,是有這種東西,我還沒見過哩。三泰故意把語氣說得很輕松。
朱遠山說,這話倒是,那么金貴的東西,想必永北城那些大戶人家才種得起。
碾房那頭,有人喊碾米,朱遠山要回他碾房里去了。看著朱遠山青布長衫的背影,王三泰心想,不行,一粒種子都不能留在朱家灣,這東西害人!
這一年的煙膏,王三泰把它全部送到了龍五爺府上。龍五爺拿出一桿精致的桿秤將三泰送來的煙膏過秤,付了三泰三千個大洋。三十封大洋,隨便拆開一封都是白花花的銀元,三泰這輩子哪里見過這么多大洋,額頭上沁出了密密的汗珠,他不停地搓手,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不過,龍五爺說,你還得付我三百大洋!那女子從此就是你的人了!
龍五爺又從紅紙封就三十封大洋中拿回了三封。
三泰說,五爺說到做到,三封大洋是應該的!
過了一會兒,龍五爺又從三封大洋里取出兩封放進了三泰的那堆大洋中。
龍五爺說,這是給我干閨女的嫁妝!
這下三泰受寵若驚了。他給龍五爺磕了三個響頭。
酒過三巡,三泰漸漸放松下來。龍五爺說,姑爺明年還種這東西嗎?
三泰猶豫起來。
蘭子說過,鴉片這東西是世間的毒藥,多少人家被它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種鴉片是一件損陰德的事,死后得下十八層地域!
那么,干爹的意思呢?三泰說。
龍五爺說,種!明年再種!
那我再種一茬!三泰說。
次日清晨,龍五爺叫家丁抬出一頂花轎放在堂前。叫下人從東廂房里扶出蓋了蓋頭的蘭子,在正堂前向他行了叩拜之禮后,他親自把蘭子扶上花轎,又送出龍家大院,另派幾家丁領了幾條快槍一路護送蘭子的花轎,朝朱家灣而來。他確實把蘭子當作他出嫁的閨女了。
4
蘭子的小腳,與眾不同。這里的山里人家,女子不裹小腳。不過,聽老人說,很久以前,還是裹小腳的。說是長毛叛亂那一年,村里要來長毛子,于是村里的莊戶人家,紛紛往深山里逃。
剛好有這樣一家,男人外出謀生計去了,家里只剩下小腳媳婦帶著三個娃。聽說長毛子要來,這個小腳媳婦也帶著三個娃往山里逃,剛到村口就逢上打前站的哨探。那個探子說,你這個大嫂拖娃帶仔的,要去哪里?小腳媳婦就說,聽說村里要來長毛,帶三個娃子逃難去。那個探子又問,三個娃都是你家的?媳婦說,背上背的是小叔家的,小叔得了傷寒死了,娃兒他媽就改嫁了,這懷中抱的也是小叔家的,手里拉著的這個大的卻是自家的。
后來的結果是,長毛派來打前站的那個探子被她的這種義行感動了,就說,你一個小腳女子能逃到哪里,告訴村里人,以后女子再不可裹小腳,你也不用逃難了,你去告訴村里人,要他們家家戶戶在門上掛一把艾草,保你們一個村子的平安!就這樣一個村子得以保全下來。自那以后,村子里的女子就再也沒裹過小腳。
從蘭子下轎的那一刻起,她的一雙小腳就出現(xiàn)在眾人的視線里。
有一回蘭子端著個木盆,篤篤地踮著小腳去河邊洗衣衫,她后面跟著一群半大的小孩瞎起哄:
“討個永北婆,當?shù)抿呑玉W;討個永北婆,當?shù)抿呑玉W!”
“大腳江山穩(wěn),小腳遍地滾;裹小腳一雙,流眼淚一缸。”
……
蘭子并不生氣。這一來,那群小孩起哄得更歡實了。
三泰不允許村中的小孩取笑蘭子。這天傍晚蘭子又去河邊洗衣服,一群小孩又跟上她了。三泰沖上去,朝那群小孩吼道,你婆你媽才是騾子哩!再叫,再叫,老子騸了你幾公子!那群小孩一哄而散。
蘭子卻在一旁柔柔地說,你吼那么大聲干啥,莫嚇壞了人家的小子!
跟鄉(xiāng)下所有的暴發(fā)戶一樣,有了錢王三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房造屋筑碉樓。
清水河南下三十里是斯木鎮(zhèn)。
王三泰從鎮(zhèn)上請來了木匠、瓦匠、石匠和泥水匠。他要造房,他要把自己房子造得比朱家灣富戶朱遠山家的那幾間白墻青瓦的房子還要漂亮。
王三泰是去過永北城見過世面的。
王三泰請來的木匠是劍川木匠,木匠姓段,段木匠的絕活兒是在門窗上廊沿上雕刻蘭草牡丹松鹿仙鶴。講好了價的,段木匠的工錢等于他在上好的木材上雕刻下來的木屑的重量,一斤木屑等于一個銀元。石匠姓徐,叫徐景清,他打磨出來的柱墩叫八柱頂瓜,就是小小的八根龍柱八個龍頭向上共頂一個金瓜。
王三泰一下子鬧出了這么大的動靜,更加證實朱遠山先前的猜測。朱遠山沒見過罌粟,這下他更加堅信,去年春天王三泰在河邊種植的那一大片奇花就是罌粟花。
朱遠山是個心頭活泛的人,見人家發(fā)財,他也想沾點兒光。這樣一來,朱遠山就成了朱家灣第一個向王三泰討要罌粟種子的人。
那天傍晚,從水碾房里下了工后,朱遠山叫他女人燒了一大鍋熱水,洗過熱水澡,換上了他吉日或出行才穿的那一襲有團福字的綢衫,打躬作揖,求到三泰門上來了。
朱遠山說,三泰侄呀,你莫想瞞你老叔,眼下你發(fā)財了,也不想要帶攜帶攜你老叔!
三泰說,哪里發(fā)財了,只不過托了永北城龍五爺?shù)母#N了點藥材,賺了幾個小錢!
你種的是藥材?朱遠山說,你種的是鴉片,是大煙哩!
王三泰剛想搭話,蘭子就撐著一盞清油燈進了堂屋,她放下燈盞說,我知道了,叔也想種點兒藥材,三泰,你就給叔幾個種嘛!
蘭子向三泰使了個眼色。朱三泰欲言又止。
朱遠山剛要搭話,蘭子又說,叔,您看這樣行不?今天天晚了,也不曉得您要來,那東西我們不曾備得,明天吧,明天您再來,我挑選幾個大的,您老拿去作個種!
朱遠山站起來打躬作揖,說,你看,還是我這侄媳婦知書達理,三泰呀,你真是個有福之人哩,找了個好媳婦!朱遠山恭維了一番,說了一車好話,去了。
蘭子確實知書達理。
朱遠山前腳剛走,三泰就說,你真要把種子拿給姓朱的?
蘭子說,給,肯定要給;不給,他四處宣揚,說咱種的是罌粟呢!三泰,你這去拿幾個種子來!準備個罐子,咱把煮熟的種子送給他!
三泰說,你這不是害他么,分明是讓他長不出苗來?
蘭子說,不是害他,我就是要讓它長不出來!
頓了頓,蘭子又說,三泰,這東西可不敢再擴散了,這是害人哩!我看咱也別種了!
三泰說,可我答應了干爹的,咱再種一薦,種完這薦,咱再也不種了!
蘭子嘆了一口氣,不再說話了。
因為要筑碉樓要造房,三泰這一年忙壞了。一會兒要去瓦窯看燒窯,查看青磚和瓦片的成色,一會兒要分派人手去石灰窯運石灰,再一會兒又要去測量民工運來的材料合不合乎尺寸。蘭子裹著一雙小腳,不好拋頭露面,這些事三泰只好親歷親為了。再說蘭子最近有喜了,害口害得把膽汁都吐了出來,得歇著。這樣一來修房造屋所有的事項,他無不一一經手,著實忙得不可開交。
忙活了大半年,一座七丈高的碉樓和一座白墻青瓦的四合院在朱家灣落成了。
完工這天,三泰去斯木鎮(zhèn)請來了一個草臺班子,唱了一臺戲。小地方的戲種,上不了大臺面,不過是根據(jù)“二十四孝”的故事改編過來的《百里負米》《蘆衣奉母》《臥冰求鯉》《賣身葬父》等幾出小戲,另外也有一些插科打諢的段子。戲臺就搭在三泰新落成的那座院子里。
吹拉彈唱唱念做打,山里人家哪里聽過什么正經的戲文,都張著一張嘴睜大好奇的眼睛盯著臺上。臺上戲文淺顯直白,戲子唱到心軟處,臺下的婆子媳婦們都唏噓不已落下淚來。
兩盞瓦斯汽燈把戲臺照得如同白晝,臺上戲中人物你來我往,走馬燈似地轉,演到妙處臺下叫好聲不斷。
忽然大門外傳來聲音說,吳保長來了!吳保長來了!
三泰朝戲臺上揮了一下手,正在上演的戲暫時停了一下。三泰和蘭子走到大門外躬身相迎。吳保長是騎馬來的,身后跟著的兩個跟班,一人手里提著一盞風燈,肩上各挎著一條火銃。
吳保長一下馬就說,老弟這里燈火通明,熱鬧得很,熱鬧得很哪,老兄我坐不住了,來捧捧場子,來捧捧場子!
三泰躬身作揖,說,一個草臺班子,不敢驚動保長!
每年秋后,三泰都去永北城攬活,見過世面,場面上的話自然學了不少,平時派不上用場,沒想到這回用上了。
三泰叫個短工,把吳保長的馬牽到后院馬廄飲水上料,這才把吳保長和他的兩個跟班引到戲臺前首坐下。蘭子自去東廂房里忙活著茶水和點心。
怎么停下了?還叫鄉(xiāng)黨繼續(xù)看戲嘛!吳保長說。
三泰朝戲臺上一揮手,臺上立馬管弦齊鳴鑼鼓響起。兩盞瓦斯汽燈照得臺上人物纖毫畢見,這一出唱的是《賣身葬父》。不一會兒,茶水上來了,蘭子親自向吳保長奉茶。
吳保長接過蓋碗茶,用碗蓋拂了拂水面的茶葉,啜了一口,轉頭對三泰說,到底是大地方來的女子,兄弟好福氣,弟妹賢惠得很,堪比臺上的七仙女嘛!
三泰說,哪里,哪里,保長夸獎她了!吳保長跟三泰客套了一番,繼續(xù)看戲。
轉眼到了秋天。收獲完畢,要是往年這個時侯三泰又該肩上搭個褡褳,去永北城攬活了。自從種上罌粟以來,三泰不再去永北城攬活了,秋收后正是播種罌粟的季節(jié)。
誰也不曾想到,三泰沒去永北城,倒是龍五爺從永北城來朱家灣了。
龍五爺帶了他的那個小衛(wèi)隊,用四匹大青騾馱著八個木箱子,騎著他的那匹大白馬來了,領頭的正是去年護送蘭子出嫁到朱家灣的那兩個家丁。
龍五爺和他的小衛(wèi)隊一行十余人,還有四匹載重的牲口,在那兩個家丁引領下,徑自來到了三泰新造的那個白墻青瓦的四合院門首。
龍五爺?shù)倪@副派頭和陣式早驚動了三泰和蘭子。三泰和蘭子把龍五爺恭恭敬敬地迎進院子,進入堂屋,讓龍五爺坐在堂屋正中的太師椅上,磕頭行了大禮。
行過禮,三泰說,哪陣仙風把干爹吹來了?
龍五爺說,想我女兒了,過來看看,順便認認家門,以后走動起來方便些!
三泰說,是,是,不開親是兩家人,開了親就是一家人,踩不斷的鐵板橋,以后還望干爹常走動!
蘭子奉茶,龍五爺看了一眼蘭子的腰身,輕身對三泰說,蘭子有喜了?
三泰點頭說,嗯,嗯,托干爹的福,有喜啦,有喜啦!
哦,好得很,好得很哪,龍五爺說,生產時可得派人去永北城報喜。
三泰說,一定,一定,到時一定派人跟干爹報喜!
寒暄了一陣子,龍五爺說,你們去把東西抬進來吧。
出去了幾個家丁,不一會兒就把七八個木箱子抬進堂屋。龍五爺吩咐家丁打開箱子,只見前兩個木箱每個箱子里整齊地擺放著八條快槍,一共十六條快槍,全是清一色德國造的毛瑟步槍。其余六個箱子,每個箱子里裝了兩千發(fā)子彈。龍五爺把手一揮,一個家丁又呈上一個布包。那個家丁就打開布包,里面是二十封紅梅紅紙封就的銀元。
三泰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說,干爹這是?
龍五爺端起矮幾上的蓋碗茶,用碗蓋拂了拂水面的茶葉,啜了一小口,放下蓋碗,用眼光掃了一下三泰。三泰隱隱覺得龍五爺眼里有一股凌厲之氣,脊背仿佛被秋風吹了一下,涼颼颼的。
今年我要你擴大種植面積,那東西被稱作黑色的銀子,龍五爺說,既然是銀子,你就得看住它,這就像個小孩抱著個金娃娃過鬧市,難免有人起覬覦之心!怎么辦?你得用槍支彈藥來保衛(wèi)它。
你這里,煙膏子質量好得很,龍五爺又說,這些錢你用來買地;我是個生意人,當著我女兒蘭子的面,咱翁婿倆在商言商,這些錢和槍支彈藥,我不是白給,要從下一年的煙膏子中扣除。
這一來,龍五爺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確了。
三泰唯唯諾諾。蘭子微微地嘆了一口氣。
三天后,龍五爺帶著他的衛(wèi)隊離開朱家灣,回永北城了。
山里的土地不值錢,三泰找了幾家朱姓人家的土地賣主,一畝土地十個大洋就搞定下來。
在買賣土地這件事情上,蘭子留了個心眼,所有地契上買方的署名都是永北城的龍五老爺?shù)拿帧YI地的事辦得很順利。現(xiàn)在以朱遠山的水碾房為中心,一夜之間,清水河邊一百五十余畝土地變成了龍五老爺?shù)耐恋亍M跞┫朐谏厦娣N啥就種啥,當然對外宣稱的是,替永北城的龍五老爺種藥材。
這一年王三泰要做的事情還很多,但事分輕重緩急。
對于王三泰來說,他現(xiàn)在首要的任務就是要把來年的一百五十余畝罌粟的種子播撒下去。他開始在朱家灣雇傭短工。每年秋后,大多數(shù)佃戶閑了下來,王三泰很快就雇到三四十個短工。
罌粟這東西不擇土地,卻很需要肥力。為罌粟提供肥力最好的是草皮灰。這草皮灰就是把草燒成灰,然后把它均勻地散到土地上。朱家灣四周都是山嶺,王三泰帶領雇來的短工去山坡上鏟草皮,把鏟下的草皮運到地里,在秋后的某一天,王三泰在那些草皮堆上點了一把火。一時間,朱家灣上空風煙滾滾,遮天蔽日,雖然陽光最終還是穿透了濃煙落到地面上,但那層陽光慘淡而稀薄,幾乎失去了熱力。最奇怪的是夜間,遠處傳來幾聲夜貓子的叫聲,小山一樣的灰堆還冒著余煙,天空中就出現(xiàn)了一輪血色的月亮。
種植秋豌豆的時間,也正是種植罌粟的時間。
三泰播撒罌粟的種子需要河水。清水河邊,那幾架閑置了一段時間的竹水車又開始吱吱呀呀地工作了。它們從低處把河水一竹筒一竹筒地汲上來,倒進高架木槽,木槽再把河水引進岸邊的田地。
罌粟的種子,比秈米籽還小,細如金黃色的塵粒,誰會想這么一粒種子種進土地,它竟會開出那么艷麗的花,結出雞蛋大的果來。
罌粟無罪,它只是一種植物。人類劃傷它的果皮,流出來的那些白色汁液,也無罪。有罪的是那些把罌粟的汁液提煉成毒品的人。
種植罌粟,不需要鋤頭,人們只需要散開草皮灰,用筷子在草皮灰上戳一個洞,放上罌粟的種子,再把草皮灰覆蓋過來,在草皮灰上均勻地灑上水,讓它在地里萌芽就行。
剛種下去的種子,也需要保衛(wèi)。
接下來,王三泰開始招募鄉(xiāng)勇,保衛(wèi)自己的罌粟。第一個報名的,是朱家灣的朱大才。此人家里窮得實在揭不開鍋了,當他從王三泰手里接過三塊大洋時,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三叔朱遠山家糴米。在鄉(xiāng)下,一個銀元可以糴米兩石。這么豐厚的報酬,半天工夫,王三泰就在朱家灣招募了十五名鄉(xiāng)勇。可是這十五名鄉(xiāng)勇誰也不會放槍,就連拉開槍栓把子彈推上膛這樣簡單的事也不會。
不會放槍,還談什么武裝保衛(wèi)罌粟,正宗德國造的毛瑟步槍在這些泥腿子手里還不是一根打狗棍?
在這件事情上,王三泰一下子就想到了沿清水河南下三十里處斯木鎮(zhèn)的神槍手李應龍。王三泰決定聘請李應龍當教練。
李應龍是“白家米號”的一名伙計。“白家米號”是斯木鎮(zhèn)上唯一的一家米店,獨家經營從川滇道上運來的大米。
據(jù)說這一年,白家米號的掌柜白胡龍的馬幫經過川滇道的九道拐時,有一伙土匪潛伏在那里,準備攔路搶劫。由于要上天險九道拐,白胡龍先讓他的馬幫在崖下歇息。這時“啾”地一聲,左邊的斷崖上出現(xiàn)了一只蒼鷹,并在斷崖上空來回盤旋。
白胡龍指那只蒼鷹跟手下的伙計打了個賭說,誰要是把這只鷂子打下來,到太平鎮(zhèn)上時我請他逛窯子。
李應龍說,白掌柜此話當真?
白胡龍說,當真,只怕你打不下來!
本來是一句玩笑,誰知伙計李應龍“咔嚓”一聲拉開槍栓,把子彈推上膛,槍一上揚,那只老鷹發(fā)出一聲凄厲的長嘯,像一只斷線的風箏一樣,打著旋落到山腰的一堆亂石堆后去了。那堆亂石下面剛好潛伏著龍頭山的土匪賀老六和他手下的一干兄弟。無巧不巧,那只老鷹剛好落在匪首賀老六跟前。
最后的結果是賀老六硬是沒能發(fā)出那一聲號令,眼睜睜地看著白胡龍的馬幫馱著百十馱大米從自己的眼皮下過去了。
王三泰親自到鎮(zhèn)上來請李應龍。剛巧李應龍又去太平鎮(zhèn)押運馬幫了。白家米號接到飛鴿傳書,說三天后馬幫才能趕回。
王三泰在鎮(zhèn)上等了三天。第三天午后,白家米號的掌柜白胡龍和他手下的伙計才押著馬幫從太平鎮(zhèn)回來了。
這李應龍的職責是幫白家米號押運馬幫,一個月在斯木鎮(zhèn)和太平鎮(zhèn)之間往返一次,平時賦閑在家。三泰說明來意,并許以重金,李應龍痛快地答應了。不過,臨行前李應龍擔心東家有臨時的差遣,又去號上告了半個月的假,這才隨三泰來到了朱家灣。
5
朱遠山的毛驢兒腳程慢,緊走緊走硬是用了兩個時辰,他和他的毛驢兒才遠遠地望見了清水河邊的斯木鎮(zhèn)。
清水河到了斯木鎮(zhèn),河面變寬。河面上搭了一座鋼絲吊橋,騾馬和行人走在橋上,一晃一晃的,就像蕩秋千。朱遠山和他的毛驢兒晃過鋼絲橋,朝鎮(zhèn)上走來。
朱遠山是騎毛驢兒來的,到達斯木鎮(zhèn)上時已是晌午時分。他先把自家的毛驢兒牽進橋頭丁家馬店,囑托店主丁七兒給他的毛驢兒上水上料,說下午還得往回趕。
丁七兒說,大老遠來了,就不住一晚上?
朱遠山說,不住了,不住了,兩頭有事哩。
他來到街上,街邊這里一伙那里一伙圍著一些人。有人圍著個賣老鼠藥的,他操著一口川北話介紹老鼠藥的功效。有人圍成一圈觀看猴戲,場子中央有三只猴子,在耍猴人那面銅鑼和鞭子的驅使下,做著各種滑稽的動作。有兩頂驕子穿過街面,拐進街道東邊的一個胡同,看起來是有人娶了寡婦或小老婆,又不愿聲張的樣子。
朱遠山擠進那伙觀看猴戲的人群中,看了會兒猴戲。當耍猴人停止猴戲,把一面銅鑼伸到他面前討錢時,他側身鉆出了人群。
日近晌午,朱遠山肚子里空蕩蕩的,仿佛藏了一只咕咕鳴叫的鴿子,他在路旁隨便找一家茶棚,鉆進去點了一壺老茶,從褡褳中掏出一個飯團就著茶水,一口飯團一口茶水地吃起來。
朱遠山是來告狀的。
告誰?
告朱家灣富戶王三泰,告他在鄉(xiāng)下大面積地種植罌粟。
朱遠山在他的水碾房旁邊有一塊沃地。往年他在這塊地上種秋豌豆,今年他種下了罌粟。朱遠山沒種過罌粟,不過有活教材,王三泰怎樣種,他也跟著怎樣種。半個月后,王三泰的苗子長出來了,像極了春天萵苣,綠油油的,這里一大片那里一大片。而自家的那塊地里,一苗不出。朱遠山百思不得其解,為何同樣的種子同樣的土地同樣的種作同樣的管理,王三泰的苗一天天茁壯成長,而自家這塊地里卻光板板的,只有幾只蛐蛐子在土旮旯下面叫?
后來朱遠山想通了。問題肯定出在種子上,一定是王三泰在那些種子上做了手腳。
早年間朱遠山仿佛聽人說種植罌粟是犯罪的,要打進大牢要殺頭。
王三泰呀王三泰,你不仁就別怪我不義了!朱遠山咬了咬牙下了個決心,他要狀告王三泰。
之前,朱遠山找過吳保長。那天朱遠山從他的水碾房旁邊的那塊地里歸來,氣不打一處來,他順道去了村子東頭的吳保長家。
吳保長喜歡打獵,家里養(yǎng)著三只獵狗。
這平時吃肉的狗和土狗就是不一樣,吃肉的狗那叫聲仿佛是從胸腔里蹦出來的,甕聲甕氣,叫人不寒而栗。朱遠山剛到吳保長家院門外,院子里就傳出來一陣狂吠,拴狗的鐵鏈子似乎快要掙斷了。朱遠山小時被狗咬怕了,這會兒腿肚子直打顫。
誰在門外?吳保長朝著大門喊。
朱遠山說,三哥,是我,遠山,找你有事!
訓練有素的獵狗跟土狗就是不一樣,吳保長朝著籠子喝斥了一聲,那三只狗就爬在鐵籠子里悄聲寂氣了。
吳保長打開院門,朱遠山左右瞅了一眼,四周沒人,這才進了吳家大院。
朱遠山進屋,坐下。
找我啥事?吳保長說。他繼續(xù)用一塊青布擦拭著他那支嶄新的毛瑟步槍,連眼也沒抬一下。
也沒啥事,朱遠山說,就是河邊那些煙苗嘛,王三泰種的可是鴉片呢!
啥,鴉片?吳保長盯了朱遠山一眼,兄弟,你可不敢亂說,那是藥材,永北城龍五老爺托他種的藥材!
吳保長又說,永北城的龍五老爺,你知道吧,就是縣長的那個大舅子。說完用一塊青布繼續(xù)擦拭他那只正宗德國造的毛瑟步槍。
朱遠山愣了一下,隨即說道,哦,是藥材啊,我沒見過大煙,我還以為是煙苗哩,誤會,誤會!
之前,吳保長找過王三泰。
吳保長說,兄弟,你河邊上種的那玩意兒真是藥材?怎么我看上去那東西怪像鴉片的,今年的種植面積還不小呢,估計有一百五十余畝了吧?
王三泰說,藥材,真是藥材,是永北城的龍五老爺托我種的藥材!
這龍五爺好像是縣長的舅子,是吧?吳保長說。
是大舅子!王三泰說,你看我這記性,我這干爹呀,他聽說您愛打獵,平時就愛弄個槍支彈藥什么的,這不,前不久他托人捎來一支獵槍,叫我替他轉交給你呢!稍晚些,我親自把它送到府上!
吃了一盞茶,吳保長說,這幾日豌豆地里的斑鳩正肥著呢,他要去豌豆地里打斑鳩啦。
走出院門外,吳保長回過頭來對王三泰說,這藥材好,這藥材好著哩!
小小的斯木鎮(zhèn),鎮(zhèn)上的人家有三分之一是白姓人家。鎮(zhèn)長也姓白,叫白胡彪,是白家米號的掌柜白胡龍的大哥。這鎮(zhèn)長白胡彪行伍出身,聽說早年去過省城的陸軍講武學堂上過幾天學,后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退學了。
退學就退學吧,反正白家騾馬成群良田沃地多的是,不缺吃不缺穿,娶妻生子傳宗接代是正事。
白老太爺說歸說,但到底還是為他兒子白胡彪在縣里謀了個保安隊隊長的職務。白胡彪在干了三個月保安隊隊長,斯木鎮(zhèn)鎮(zhèn)長的職位空缺了出來,上頭一紙任命書下來,白胡彪就被提拔做了斯木鎮(zhèn)的鎮(zhèn)長。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其間雖然換了很多任縣長,但白胡彪的鎮(zhèn)長一職卻雷打不動,一直做了下來。
朱遠山走進鎮(zhèn)公所時,鎮(zhèn)長白胡彪正坐在他寬大的紫檀木辦公桌背后的太師椅上打盹。辦事人員不敢驚動他,就叫朱遠山在檐下候著。
朱遠山朝辦公的屋子里望了一眼,只見墻上左邊掛著一副先總理像,右邊掛著一面青天白日旗。過了半晌,白胡彪咳嗽了一聲,那個辦事人員趕緊進來替他沏了一壺龍井。白胡彪抿了一口茶,轉過頭來詢問辦事人員,有什么緊要事么?
辦事人員說,倒也沒什么緊要的事,來了個山民,說要告狀,現(xiàn)在正在檐下杵著。
白胡彪說,叫進來!
那個辦事人員就把朱遠山叫了進去。
鏟煙隊是第二天中午開進朱家村的。
那時,王三泰和聘來的幾個鄉(xiāng)勇正在院子里吃晌午。吳保長火燒了房子一樣跌跌撞撞地闖了進來。一進院子就說,三泰,快,快,鏟煙隊來了!
王三泰從來沒見過吳保長還么犯急過,他趕緊吐出嘴里還沒來得及咽下的那口米飯。院子里,幾只雞仔沖過來搶食王三泰吐出來的那口米飯。
鏟煙隊,啥叫鏟煙隊?王三泰說。
吳保長一跺腳說,嗨,就是鏟你煙苗的隊嘛!不曉得哪個狗日的去鎮(zhèn)上吃了報口,白鎮(zhèn)長親自率隊來了,一行三十多人,已到了我那保公所!
王三泰剛要沖出院子,卻被吳保長叫住了。你要去哪里?吳保長一把抓住王三泰。王三泰說他要去面見白鎮(zhèn)長,當面領罪。
吳保長說,三泰你急糊涂啦,罪是要領白鎮(zhèn)長也要見,可眼下正是晌午,你看人家白鎮(zhèn)長大老遠地來了,腳也沒歇一下水也沒喝一口!
哦,是,是,是,我這就安排晌午!三泰說。
這就對了嘛,啥事都要分個輕重緩急嘛,吳保長說。接著他湊近王三泰的耳朵,如此如此地安排了一番,回他的保障所去了。
這頭三泰忙活開了。
第一件事,三泰打開一個小小的樟木箱子,從箱子里掏出一盒去年留下一盒煙膏擺在堂屋左邊的那張矮幾上,在矮幾旁邊安了一張?zhí)梢巍?/p>
第二件事,三泰叫蘭子打開錢匣子拿出兩個銀元托鄉(xiāng)勇李五兒去村中買了一頭肥豬一只肥羊。
第三件事,三泰叫來本家侄兒王七斤,讓他拿著兩個銀元去獵戶趙打山家購買去年冬天趙打山腌制的那一對熊掌。
其實,這三件事都是吳保長安排下的,王三泰只是照做而已。
最后一件事是王三泰自己想出來。三泰進屋說,蘭子,把干爹捎來的給你坐月子補身子的燕窩挑兩個出來,用最好的冰糖熬上!
蘭子說,三泰,要不咱也別折騰了,白鎮(zhèn)長不就是要鏟煙苗子么,由他鏟了干凈,咱正好不種那害人的東西!
三泰說,你說不種就不種啦,永北城那頭咋交待,那些槍支彈藥,還有那兩千大洋,他會白給?現(xiàn)在咱就是人家手頭的棋子哩!
蘭子嘆了一口氣,不再說話了。
煙槍是白胡彪自帶的。過足了煙癮,白胡彪站起來伸了個懶腰,人也變得精神了起來。三泰向蘭子遞了個眼色,蘭子端上了那碗燕窩。
白胡彪說,這是啥?
王三泰說,燕窩!
你這里還搞得到燕窩?白胡彪說。
三泰說,是永北城的龍五老爺送來給他女兒補身子的。
哪個龍五老爺?白胡彪說。
就是縣長的大舅哥,永北城郊靈源的龍五老爺嘛!吳保長插話說。
這燕窩倒是個稀罕物哩!白胡彪說。
鎮(zhèn)長趁熱吃,這東西大補!王三泰說,聽說是從一個叫什么泊爾的國家?guī)н^來的。
吳保長說,尼泊爾。
王三泰說,對對對,就是從這個尼泊爾國帶過來的,你看我這記性,簡直讓狗吃了!
白胡彪說,我在鎮(zhèn)公所悶得慌,就想來這山里散散心,打打獵,倒讓你們費心啦!
王三泰說,說哪里話,鎮(zhèn)長是一個鎮(zhèn)的鎮(zhèn)長,能來咱這里一趟,是咱的福氣哩!
吳保長也說,就是,就是,白鎮(zhèn)長平時公務纏身,難得出來散散心,這趟出來了就在山里多呆幾天,咱這里窮山惡水啥都缺,就是不缺獐子麂子黃羊野兔這些野味!
第二天,王三泰和吳保長安排了一場盛大的狩獵活動。一大早,鎮(zhèn)長白胡彪帶著手下三十余名兵丁,吳保長牽了三頭獵狗,王三泰也帶了那十五名鄉(xiāng)勇,另外叫上了獵戶趙打山,一行四五十人去龍頭山打獵了。
也就是這一天,王三泰家每一塊地里的煙苗幾乎都遭到了盜竊。被盜竊的煙苗不多,一塊地里也就是那么三五株,如果不細心察看,還真發(fā)現(xiàn)不了一塊地
里有那么三五株煙苗遭到了盜竊。
6
最近王三泰很納悶,朱家村幾十戶人家,幾乎人人見了他都繞道而行。實在繞不過去時,那些人低著頭急急地就過去了。王三泰跟他們搭話,他們也只是嗯嗯啊啊,答非所問。這是咋了?一個村子里的人,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這會兒咋都變成了這副樣子!王三泰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還是是蘭子破解了這個難道。
蘭子說,記得那天你說煙苗地里有盜竊的痕跡,你說過這話么?
王三泰說,我說過這話。
蘭子說,那么你想到是誰盜竊了這些煙苗么?
王三泰如醍醐灌頂,一下子明白過來。
那么問題又來了,王三泰說,他們把這些煙苗種在哪里?
種在自家院子里,蘭子說,要不了兩年,這里沒人種莊稼啦!
四個月后,罌粟成熟了。王三泰忙著收煙熬膏,當他帶著鴉片膏子來到永北城郊龍五老爺府上時,龍府正在發(fā)殯。
他一打聽,說是龍五老爺殯天了。
事情來得太突然,王三泰徹底懵了。三泰本來想把煙膏子交出去的,可是龍府上下亂成一片,也沒個主事的,就沒交成。
這龍五老爺人強命不強,年過半百膝下只有一個傻子兒子,是第五房姨太太生的,七八歲了,癡癡呆呆的,成天在院子追著自己的影子跑。如果沒個專人看護,他會跟著自己的影子跑出府外,一直跑到廣闊的田野里去。倘若是春天,他喜歡在那里捉蜻蜓,用一根絲線拴住蜻蜓的腳,讓那只蜻蜒像一只小型的風箏一樣,在田野上空飛,這時他嘴里會發(fā)出嗚嗚的歡呼聲。
正是這個傻子兒子要了龍五爺?shù)拿D翘戽九涮m帶他在花園里玩耍,玩了一陣,翠蘭覺得累了,就坐在廊子下歇息。坐著坐著,倦意襲來,一不留神,翠蘭就扶住廊下的欄桿睡著了。龍五爺?shù)纳祪鹤泳透白幼撸灰粫壕统隽舜箝T。這一回,他的影子把他帶進了一個長滿水葫蘆的池塘。撈上來時,那個傻子鼻孔里嘴巴里塞滿了淤泥,身上纏滿了水葫蘆白色的根莖。
龍五爺活埋了婢女翠蘭。從此,龍五爺臥床不起,病了四個月,最后也一命嗚呼了。
剛把龍五爺葬進祖墳,他的七房姨太太就鬧著分家產。王三泰想把膏子交上去,結果還是沒交成。看來這龍府大勢已去,再沒個主事人了。王三泰決定把那些鴉片膏子賣到煙館去。
可是這回永北城也變了模樣,大大小小的煙館都遭到了查禁,門上一律貼著封條。街上行人很少,每個人都是那么行色匆匆。王三泰想去紅云巷翠云軒問問老鴇柳翠兒,這城里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沒想到翠云軒也遭到了查封,老鴇柳翠兒不知去向。
從紅云巷出來,王三泰去了“蘭子掛面店”。
“蘭子掛面店”沒被查封,只是食客稀少得很。三泰點了一碗掛面,過了半晌,跑堂的才端上了一碗掛面。三泰問那個跑堂的,這城里發(fā)生什么事了?
跑堂的說,這世道變天了,縣長挨了槍子兒了!就在這時有一隊軍紀嚴明的隊伍喊著口號從街道上走過去,一直走到衙門那邊去了。
王三泰打了個激靈,趕緊低頭吃掛面。吃完掛面,他扛著貨匆匆離開了縣城。
山里一如既往,還是那樣寧靜。三泰回到家里,把他在永北城的遭遇說了一遍。
蘭子說,這下好了,再也沒人脅迫咱啦!
蘭子又說, 這世道恐怕要變天啦,三泰,這兩年咱是跟著龍五爺做壞事哩,那東西不曉得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往后咱別種了,把那些土地都退回去,咱種不了那么多土地,只留河邊那三畝水田就夠了,財多傷身哩!
三泰說,你知書達理,我聽你的!
第二天,蘭子叫三泰在自家的院子里控了一個坑,把那些鴉片膏子全部投入坑里,鋪上一層生石灰,再往坑里倒水。生石灰遇到水,一下子就沸騰起來,坑里冒出一陣白色煙霧。煙霧散盡后,坑里只剩下了一層灰色的石灰漿。
接下來,蘭子開始著手處理河邊那一百五十余畝土地。
蘭子叫三泰挨家挨戶通知過去,叫他們來取回地契。三泰拿著一面銅盆當鑼,一路敲打下去,邊敲邊喊,退地啦,退地啦,龍五老爺退地啦!
不一會兒,所有出售了土地的人家都聚齊在小院里。
見蘭子捧著個木匣子出來,眾人七嘴八舌地嚷開了,我們沒有贖金啊,三泰媳婦,你叫我們拿啥退地?
蘭子說,各位叔伯,你們先聽我說,其實我不是龍五老爺?shù)母膳畠海抑皇莻€普通人家的女子。十六歲就被我那抽大煙的親爹賣到龍五老爺家做丫環(huán),我恨透了鴉片!
蘭子說,我們家三泰只是替龍五爺種鴉片,如今龍五爺歿了——
蘭子剛說到這里,眾人嚷開了,什么?龍五爺歿了?
蘭子說,是的,永北城的龍五爺歿了——幾房姨太太鬧著分家產,家里已沒了主事人。
蘭子說,今天把大家叫來,就是要大家把地契領回去,這地契大家要妥善保管,今后可以作為退地的憑證;這是龍五老爺?shù)牡兀敵趿⑾掳准埡谧郑@一點地契上寫得明明白白,至于贖金嘛,現(xiàn)在龍五老爺歿了,贖金也就沒了!
小院子里歡騰起來,原先變賣了土地的人家又拿回了土地,都念叨著蘭子的好,都說蘭子得人心,這件事處理得很妥當。
眾人散去后,蘭子說,現(xiàn)在咱家只剩下河邊三畝水田了,你不會怪我吧。
三泰說,你知書識理,我聽你的!
蘭子說,你看這龍五爺吧,那么大的家財,到頭一空,落得個家破人亡,可見平時不積陰德,財大傷身,再說眼看著孩子就要出世了,我們得為后人積點陰德!至于那些槍支彈藥,咱還得留著,世道亂了,這些東西說不定有一天還會派上用場。
三泰說,你知書識理,我聽你的!
這一年秋天,河邊那幾架大水車閑置了一段時間后,又開始吱吱呀呀地工作了。被水車汲上來的河水,經過高架木槽的導引,嘩嘩地流進河邊的田地。這個秋天王三泰拾掇好自家的三畝水田,撒上了秋豌豆。撒豌豆那天,朱遠山又鉆出他的水碾房,來到三泰的地邊看三泰撒豌豆。
兄弟今年不種那東西啦?朱遠山說。
三泰說,不種了,不種了,那東西害人哩!
朱遠山說,去年弟妹給的那幾個種子成活了,我延了種,今年我倒想種一薦呢。
顯然,朱遠山在撒謊。給他的那些種子,蘭子是煮過的。那樣的種子能育出苗來,這不等于說煮熟的雞蛋又孵出了小雞。不過,此地無銀三百兩,朱遠山欲蓋彌彰,這不正好說明他是去年盜竊煙苗中的一員么?三泰想,這真是不打自招啊。
三泰說,我勸你也別種啦,種了也白種,永北城大小幾十家煙館都貼上了封條,你往哪里賣?
朱遠山說,我往鄉(xiāng)下賣,這東西緊俏得很哩!
種植豌豆的季節(jié),也正是種植罌粟的季節(jié)。清水河邊,又有幾個人湊過來跟三泰閑聊,他們都說他們買到了種子,今年正準備種一薦罌粟呢。
聊了一陣,三泰卷起袖子又開始干活。
近來王三泰干活時渾身有使不完的勁,這干活的勁頭來源于半個月前,蘭子為他生了個白白胖胖的小子。蘭子裹著一雙小腳是干不了活的。不過這有啥要緊,三泰想,自己有的力氣,能養(yǎng)活娘兒倆,自己只要每日間想想孩子,想想蘭子眉間的那顆豌豆大的胭脂痣,這輩子干再苦再累的活都值了。
自從嫁到朱家灣,蘭子最遠只去過斯木鎮(zhèn),去了三次。蘭子腳小,每次去斯木鎮(zhèn)都是騎著廄里的那匹毛驢去的。
斯木鎮(zhèn)上有一家賣書的鋪子,蘭子每次到斯木鎮(zhèn)都要去那家書鋪里買幾本書。
三泰最喜歡看蘭子坐在院中的那棵石榴樹下看書的樣子,一看就是半天。有時,蘭子迎著他的目光微微一笑,他才曉得田地里還有許多事等著他去做,就趕緊走開了。當然,三泰忙外蘭子忙內,一到屋里蘭子就把他服侍得妥妥貼貼的,家里也收拾得干干凈凈。
這樣過下去,挺好,挺好!三泰想。
7
逢七是斯木鎮(zhèn)的集天,也就是說,農歷每月初七、十七、二十七這三天是斯木鎮(zhèn)的集日,上一場集和下一場集之間隔著十天。
每到集日,山民用馬匹馱著山貨往鎮(zhèn)上趕,活躍在川滇邊界的行商也往鎮(zhèn)上趕。白家的米號在這一天生意極其興隆,那些大大小小的商鋪生意也極其紅火。玩雜耍的,走親戚的大多也集中在這一天。
斯木鎮(zhèn)三面臨水,一面靠山,從外界進入斯木鎮(zhèn)必須要通過河上那座吊橋。
臘月初七這一天,從斯木鎮(zhèn)趕集回來的人說,斯木鎮(zhèn)河邊的那座吊橋斷了,死了十幾個人和幾匹騾馬。連接鎮(zhèn)子和外界的吊橋斷了,最著急的是鎮(zhèn)上的白家,于是由白家挑頭,貼出告示說,要重修河上的吊橋,叫山里人家有錢的出錢無錢的出力,修橋的時間定于下月十五。
蘭子說,孩兒他爹,要不咱也捐一點,修橋補路,為孩兒積點陰德!
三泰說,捐!捐多少?
蘭子說,兩百大洋,你看咋樣?
三泰說,就兩百大洋。
修橋那天,三泰早早地趕到了工地。這回主事的是白家米號的掌柜白胡龍。白胡龍?zhí)Я艘粡執(zhí)珟熞巫跇蝾^,旁邊設一張方案,案上擺著文房四寶,案下放了一個笸籮。募捐活動開始了,陸續(xù)有人往笸籮里扔錢,一個銅子兩個銅子。逢到有人往笸籮里扔一個銀元時,白掌拒站起來拱拱手,隨即叫號上的伙計記下那個人的名字。
大家都想早點把橋修好,捐款的人很多。
三泰走上前說,我捐兩百大洋!
他取下肩上的褡褳,往笸籮里一抖,那些散裝的銀元嘩啦啦地掉進了笸籮。
白掌柜趕緊從太師椅上站起來,向三泰深深地鞠了一躬。三泰也拱了拱手,回了禮。
請先生留下姓名!白掌柜大聲說。
不必了!說罷,三泰轉身離去。
看著三泰的背影,白掌柜說,這人是誰?
募捐的人群中,有人認得三泰。那人就說,他是此去三十里地朱家灣的王三泰。
所以至今斯木鎮(zhèn)外清水河邊,一塊被荒草掩沒了半截的石碑上還刻著王三泰的名字。
許多大事注定要在這一年發(fā)生。
先是南邊響起了槍聲,一股土匪攻破了斯木鎮(zhèn),鎮(zhèn)長白胡彪帶著幾個家丁,拖家?guī)Э冢皆綆X,逃到北邊的永北城去了。那股土匪搶劫了白家米號,白掌柜白胡龍被活埋在清水河邊的沙灘上。帶頭的土匪正是盤踞在龍頭山猖獗于滇西北一帶的賀老六及其手下的那股土匪。這股土匪在太平鎮(zhèn)搶劫時被人民解放軍滇西剿匪縱隊團團包圍,經過激烈的戰(zhàn)斗,匪首賀老六帶著他手下四十多人僥幸逃脫后,躲進了深山老林。人民解放軍滇西縱隊正要進山追剿這股殘匪時,突然接到了新的戰(zhàn)斗任務。就這樣這股土匪在深山老林里呆了一陣子,又出來四處搶劫了。
那天逢七,正是斯木鎮(zhèn)上的集日,許多趕集的人走到斯木鎮(zhèn)外清水河邊的吊橋頭時,聽到鎮(zhèn)上的槍身,折身回來了。最后一撥回來的人說,那股土匪搶了白家米號的大米,過了吊橋,正往山里趕來。
朱家灣是個小小的村子,只有五六十戶人家。
自古土匪占山為王,靠的就是險峻的地勢。顯然,這股土匪朝朱家灣方向撲來是有意的。朱家灣只有兩條小道可通外界,一條向北,翻山越嶺,可達永北城。一條沿河南下,穿越龍?zhí)兑痪€天,可達斯木鎮(zhèn)。東西則壁立千仞,連鳥兒都飛不過去。現(xiàn)在只要把南北方向的兩條小道一堵,這里完全就成了一小塊與世隔絕的地方。
土匪從南來,朱家灣已亂作一團。
三泰有槍支彈藥,這個時侯他再不站出來,朱家灣就要變成土匪窩啦。
三泰不允許朱家灣變成土匪窩,他把朱家灣所有人都召集到了自家的院門外的那塊場壩上說,去年練過槍的,快跟我去碉樓里取槍!咱得把土匪堵在龍?zhí)兑痪€天外,其他人進我院子,躲進碉樓!
當三泰率領十幾個鄉(xiāng)勇趕往一線天時,已經來不及了,那股土匪已越過了一線天,正向著朱家灣撲來。在開闊的平地上與土匪展開較量,吃虧的肯定是自己。三泰只好下令后撤,邊撒邊放槍,以此來延緩土匪前進的速度。
現(xiàn)在,三泰的院子里碉樓里擠滿了鄉(xiāng)民,哭聲喊聲響成一片。吳保長是最后才提著槍進入三泰的院子的,他從鐵籠子里放出了他那三頭獵狗。
快,上碉樓!三泰喊。
三泰的碉樓共四層,每層有四個射口,整座碉樓一共十六個射口。三泰在每個射口安排了一條快槍。
村子里槍聲一響,打頭陣的是吳保長的那三頭獵狗。它們率領著村里四五十頭土狗沖向敵陣。這伙土匪搶劫過許多村寨,他們還從來沒見過這么兇猛的狗。
賀老六罵了一聲,該死的畜生!他拔出手槍,叭地一聲,吳保長的那只領頭的獵狗應聲而倒,喉嚨里發(fā)出“嗚——”地一聲慘叫。
他娘的,敢打我的狗!吳保長朝土匪放了一槍,剎時碉樓上槍聲響成一片。那伙土匪的囂張氣焰被壓了下去。
他娘的,遇到硬骨頭了!賀老六罵了一聲,手一揮,那股土匪撤退了兩百多米,躲到場壩那頭的土坎下面去了。這頭吳保長剩下的兩頭獵狗率領村中那四五十頭土狗趁勝追擊,一直追到了場壩邊上。這回它們不敢過分靠近坎下的那股土匪,但也絲毫沒有退卻的意思。就這樣,土匪只要從土坎下一冒頭,坎上的狗就叫成一片,狗一叫碉樓里的立馬就開槍。賀老六帶領那股土匪沖鋒了三次,三次都被壓制下來,退回到土坎下面去了。
最后這一小股土匪在朱家灣沒占到絲毫好處,燒了幾間民房,沿著小道往北邊的永北城方向去了。
三個月后,這股土匪被人民解放軍滇西剿匪縱隊殲滅在離朱家灣三十里地的一個叫沙家壩的小山村。
8
1950年春,朱家灣駐進了兩個工作隊,一個是鏟煙工作隊,一個是土改工作隊。鏟煙工作隊武裝鏟煙,僅用了兩天時間就把朱家灣的煙苗鏟除干凈了。土改工作隊也很快就把朱家灣的階級成分調查清楚了。
朱家灣有兩個地主,一個是吳保長,一個是朱遠山。
吳保長占有土地九十畝,朱遠山占有土地四十五畝。吳保長還因為當過民國的保長,開過公審大會后被處以槍決。朱遠山在文革中成為重點批斗的對象,最后上吊自殺。
王三泰家雖然在清水河邊只有三畝水田,但他家在舊社會建了一座碉樓和一座青磚四合院,被劃為富農。
一九六四二月,蘭子死于干病,死時人瘦得就像一具骷髏。
最后還要說的是,王三泰的那座碉樓被他兒子王家興撤到一半時,出現(xiàn)了一個夾層。夾層里有兩只大木箱和五只小木箱。小木箱里裝的全是子彈。大木箱里裝的是步槍,一共十五支清一色德國造的毛瑟步槍。按照王三泰的臨終遺言,王家興把它們全部交給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