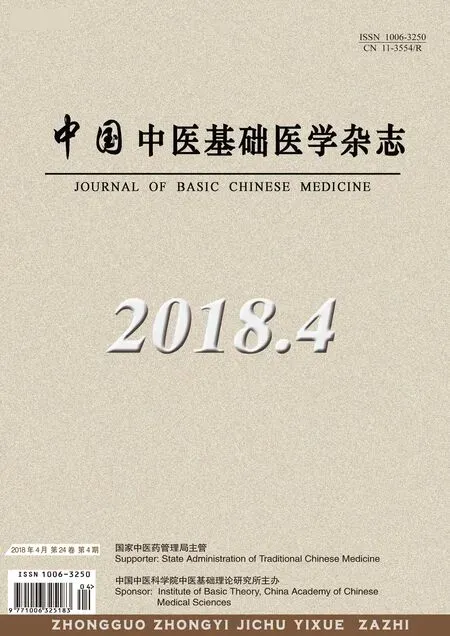薛雪治濕法度述要?
鄭 齊,于 崢,張宇鵬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基礎理論研究所,北京 100700)
薛雪是清代溫病學派著名醫家,其代表性醫著《濕熱論》對濕熱病的病因、發病、傳變、證候表現、辨證要點、治則治法、處方用藥等內容進行了詳細闡述,初步奠定了中醫濕熱類溫病診療理論的基礎。盡管其所論濕熱主要為外感,但辨治理論亦對內傷濕證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從其醫案著作《掃葉莊醫案》《三家醫案合刻·薛氏醫案》來看,在痞滿、泄瀉、淋證等諸多疾病涉及濕證的治療時,充分體現了他在《濕熱論》中所闡發的一般性原則,而又能緊密結合臨床實際,圓機活法。故筆者結合其具體醫案,對其診治內傷濕證的法度作簡要分析。
1 分消濕滯法
分消濕滯法主要針對濕滯脾胃證,脾虛生濕,而濕困脾氣,脾虛與濕滯是難以割裂的一對矛盾,關鍵是判明脾虛與濕滯孰為矛盾的主導,從而采用有針對性的治法。對于濕滯脾胃證而言,濕滯是矛盾的主導方面,所以分消濕滯是關鍵,所謂分消主要是分別從三焦給濕邪以出路。薛雪在《濕熱論》中明訓:“濕多熱少,則蒙上流下,當三焦分治。[1]”濕蒙上焦,多以藿香葉、薄荷葉、鮮稻葉、鮮荷葉等輕清之品宣陽除濕。濕伏中焦,輕者治用藿香、佩蘭、蔻仁、石菖蒲以芳化,郁金、厚樸、六一散等以疏利,使伏濕得解;若濕邪極盛于腸胃之證,重用辛開之厚樸、半夏、干菖蒲、草果等藥物,使氣機得行、濕邪得化;濕滯下焦,多用滑石、豬苓、茯苓、澤瀉、萆薢、通草等滲利清熱藥物。
案1:酒客濕勝熱郁,脹悶噯氣無寐,得茶愈脹,先與三焦分消。白蔻仁、杏仁、紫厚樸、茯苓皮、綿茵陳、金石斛、半夏[2]。
按:從案中可見,盡管在理論論述上薛雪是按三焦分治,而在實際中這3種治法是有機配合在一處,可謂一法之中三法備焉。以杏仁開達肺氣、通調水道,以厚樸、蔻仁等芳香行氣、苦溫燥濕,而以茵陳、茯苓皮利水滲濕、急開支流。從案方來看,杏仁、白蔻仁宣上暢中,輔以滲下之品,吳鞠通的三仁湯于此已見雛形。
2 苦溫燥濕法
苦溫燥濕一法主要是選用味辛、苦、性溫的一類藥物,由于辛苦之味多偏燥烈,而性溫之品又能溫燥,所以本法立意就是以燥勝濕,主要用于水濕困脾,以脘腹脹滿、口淡食少、腹瀉便溏、小便短少、舌苔白厚而膩為主要表現。本法最為代表性的方劑就是平胃散。薛雪在此方基礎上,多伍用行氣化濕的香附、砂仁,芳香化濕的草果、藿香梗、白蔻組合成方。
案2:脈沉遲,食入腹脹便溏,平昔飲酒中傷,留濕阻氣,小便不爽,用香砂平胃散。香附、砂仁、制茅術、厚樸、廣皮、炙草、水泛丸[2]67。
按:本案是非常典型的脾胃濕滯證。病因是平昔飲酒,病機是留濕阻氣,可謂描述得言簡意賅。從臨床表現看,食入腹脹是典型的脾虛中滿表現。大便溏泄、小便不爽則是因濕邪內停、脾失轉輸、濕趨大腸,脈沉遲則是陽氣不振的表現。治方是在平胃散的基礎上加用香附、砂仁。方中蒼術苦辛溫燥,最善燥濕運脾;厚樸苦溫芳香,行氣散滿;陳皮理氣化滯,合厚樸以復脾胃之升降,這3味是苦溫燥濕的主藥。香附、砂仁是常用藥對組合,香附乃氣中血藥,善于理氣開郁,而砂仁是芳香化濁、行氣化濕的佳品,二藥配伍恰好應對病機中“留濕阻氣”一語。
3 健脾化濕法
脾虛生濕,濕停亦會困厄脾氣加重脾虛造成惡性循環,所以健脾化濕應該是最為經典的治濕之法。但是在實踐中該法多不單純使用,多與其他諸法合并使用。因為濕邪內停,氣機阻滯,此時本虛標實,如果僅以健脾益氣固本,不僅脾濕不化反致氣壅不行。所以本法或是和芳香、行氣、滲利諸法合用,收標本同治之功,或是在化濕消導之后,濕邪衰其大半,正氣益虧,以該法善后收功。
案3:長齋數年,脾胃日弱,食進脘中少運,小溲入暮漸多,色萎黃,脈弦虛,皆中氣不足。香砂異功散,水泛為丸[2]79。
按:案1明言中氣不足,可見脾虛是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亦有濕阻氣機的情況,所以當在補中氣同時佐以行氣,選方是異功散。本方來源于《小兒藥證直訣》,在四君子湯的基礎上加陳皮,意在行氣化滯、醒脾助運,有補而不滯的優點,主治脾胃氣虛兼有氣滯的病證。薛雪又在此基礎上加用香附、砂仁,行氣化濕之功更強。
4 清熱利濕法
清熱利濕法是治療瀉利最為常用的治法。濕邪屬于陰邪,但蘊結體內日久化熱,此時濕處熱中,熱伏濕內,濕熱交織,羈久不愈。薛雪有謂:“熱得濕而愈熾,濕得熱而愈橫。[1]53”濕為陰邪,宜芳香溫化;熱為陽邪,宜苦寒清解。濕熱相合,溫化則恐助熱,清解則礙濕化。正如吳鞠通所言:“徒清熱則濕不退,徒祛濕則熱愈熾。[3]”治療易左右牽制,難于速解。對于本證,溫病學派醫家提出濕熱證治療的關鍵在于使濕熱兩分。葉天士在《溫熱論》中亦云:“或滲濕于熱下,不與熱搏,勢必孤矣。[1]15”薛雪亦云:“濕熱兩分,其病輕而緩;濕熱兩合,其病重而速。[1]53”濕祛則熱孤,而無狼狽為奸之虞。從薛雪醫案中也可以看出,其用苦寒清熱的同時,強調分利、淡滲。在使用芩、連、柏這些苦寒燥濕之品的同時,也配伍茯苓皮、滑石、淡竹葉、澤瀉等滲利水濕之品,甚至還佐用厚樸這類溫化之品,可見他對濕熱證的治療是頗有心得的。
案4:下痢腹痛,初因寒濕傷脾,久變濕熱,著于腸胃,痛利不減,腸中硬起不和,不得流通明甚。當以苦泄小腸,兼分利而治。方藥:川連、楂肉、木通、川柏、澤瀉、苦楝皮[2]62。
按:案中對濕熱下利證的病因病機演變敘述得比較詳細,治法也交代得比較清晰,一要苦泄,二要分利。處方也緊緊依據立法,黃連、黃柏、苦楝皮苦寒燥濕,木通、澤瀉淡滲水濕,佐用楂肉消食化滯,其理法方藥,絲絲入扣,中規中矩。需要指出的是,薛雪在治療濕熱證時常配伍使用厚樸等苦溫化濕之品,這似與濕熱的病機不符,但與大隊的寒涼藥配伍并無溫燥助熱之弊,而其化濕之能得以彰顯,又可行氣導滯,其與劉河間芍藥湯中的肉桂、當歸可謂異曲同工。由此可見,薛雪在濕熱證診治方面確實匠心獨具,在充分繼承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又結合自己的臨床體會自出機杼,顯示了較高的診治水平。
5 利水滲濕法
利水滲濕法主要是運用淡滲利水的藥物,治療水濕內停之水腫、淋證諸證,也常配合運用在分消濕滯法中,治療泄瀉、痞滿等證。
案5:今夏瘧疾,皆時令穢濕之邪,瘧后食物不慎,濕留生熱下注,遂患淋瀝莖痛便難。閱醫取苦勝濕,寒勝熱,甚是近理。但加地黃汁膩濁滋血,與通利未合。方藥:海金砂、茯苓皮、山茵陳、晚蠶沙、菖蒲、黃柏、萆薢[2]130。
按:從案中來看,發病的季節和病因病機都很清楚,濕熱下注,故組方亦是一派利水通淋、滲濕泄熱之品。文中特別提及去掉前醫之生地,慮其“與通利未和”,足見薛雪在處理利水與養陰的關系上十分靈活。一方面他很注意利濕傷陰的問題,對濕熱傷陰的證治頗有見地;另一方面又能急則治標、甚者獨行,單刀直入,速戰速決。
6 通陽化濕法
通陽源于葉天士“通陽不在溫,而在利小便”一語。通陽之法與治療陽氣損傷之溫陽法有所不同。溫陽法是根據“虛則補之”的原則溫補陽氣。如脾腎陽虛之證,用藥如附子、肉桂之類,良姜、干姜之屬。而通陽是用于濕阻氣機、陽郁不暢之證,通陽的目的在于“通”而不在于“補”。所以葉天士明訓“通陽不在溫”“不在溫”指的不是溫補之法,而是溫通之意,并非不用溫性之藥。溫藥才能助氣化以宣通陽氣,掃除濕阻。“利小便”是驅逐濕邪的一種重要方法,但是單純“利小便”并不能達到通陽的目的。小便通利則說明陽氣得通,升降有序,氣化有權,病情可愈。因此準確地說“利小便”應理解為“使小便利”,小便利是陽氣通暢的標志。本法早在《傷寒論》以五苓散治療泄瀉、消渴諸證中有所體現,薛雪在葉天士所論的基礎上,將通法與溫法并列為治療久瀉的二法,同時亦師張仲景五苓散之意治療陽郁濕滯之瀉利證。
案6:痢疾自止,頭痛至腰,二便得通少安。議通太陽以驅濕郁。方藥:木防己、生白術、紫厚樸、桂枝木、苓皮、廣皮[2]56。
按:案中言痢疾自止,但從頭至腰疼痛顯系陽氣郁滯、濕邪停留于足太陽膀胱經,經輸不利。且提到二便得通少安,說明通過二便排出濕邪,陽氣的郁滯就會得到改善。從選方來看,基本上可以視為五苓散或苓桂術甘湯的變方。薛雪處方保留了這類方劑中最重要的藥物茯苓、桂枝和白術,可見其對張仲景學術研究之精。茯苓在方中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甘淡利水以消陰,二是行肺之制節之令而通利三焦,三是補脾固堤以防水泛,故為方中主藥列于首位。桂枝在本方的作用主要是通陽以消陰。此方如有茯苓而無桂枝則不能化氣以行津液,如有桂枝而無茯苓則不能利水以伐陰,所以苓桂相須相成而缺一不可。至于白術則協茯苓補脾以利水。防己類于張仲景澤瀉、豬苓之用,厚樸、陳皮則有溫中燥濕的佐助之功。
7 溫陽化濕法
溫陽化濕法主要是通過溫補脾腎的藥物以補火暖土而化濕,針對瀉利日久、脾陽受損、日久及腎之脾腎陽虛證。薛雪在案中提到:“久痢治法,非通即溫。”前已述及通陽之法,本法即是溫陽之法。其選用的方劑主要有三,一是所謂的補腎柔劑,多是溫補腎陽而不剛燥,兼能澀腸止瀉之品,如補骨脂、菟絲子、肉豆蔻等,基本不出四神丸的法度;二是張仲景四逆湯。補腎柔劑不應時多投以此方補火助陽、回陽救逆;三是理中丸偏重于溫脾陽。通過溫補脾腎之陽使氣化濕化,同時亦增強陽氣的固攝之力,使瀉利得止。
案7:久痢久瀉肛墜,頻頻不爽。此乃腎傷,脈來數小,醫作脾胃病治,故不效。方藥:熟地黃炭、炒焦歸身、漂淡補骨脂、炒菟絲子、五味子。
接案:久痢治法,非通即溫。既曰腎病,則陽宜通,陰宜守矣。熟地炭、熟附、桂枝木、五味、炒川椒、炒歸身。接案:柔中佐剛,利未得減,下焦常冷過膝。張仲景四逆湯[2]60。
按:這是薛雪醫案中較為少見連續記載診治過程的病案。初診已是久利脫肛之候,且前醫治脾胃不應斷為腎傷,但處方中沒有1味溫補,將四神丸中偏于溫燥的吳萸、肉蔻換為平補的菟絲子,而且還用了2味養陰補血的熟地和當歸。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案中“脈來數小”一證,久利之體,陰陽兩傷,此處之脈來數小恐為陰血耗傷之象。所以此時未用較為剛燥的溫陽藥,恐重傷陰分,而且還加用了補陰養血之品,然又慮其陰柔礙陽,所以熟地用炭、當歸炒焦,這些細微的炮制之處不可不察。再診時應是效果不明顯,所以案中才有了非通即溫之語,已有求變之意。處方中在保留熟地、當歸的同時,將溫腎柔劑的菟絲子、補骨脂換為附子、川椒,使溫陽之力加強,同時加用溫通陽氣的桂枝,意在使陽氣周流、陰霾散卻。三診依然是“利未得減”,原因恐怕就在于“柔中佐剛”。由于加用了陰柔之品,使得補陽之力稍遜,薛雪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三診抓住“下焦常冷過膝”一證,果斷投以四逆湯,使得溫陽之力更加精純。
8 養陰燥濕法
養陰燥濕法主要應對濕熱久羈、耗傷陰血之證。此時濕熱和陰虛兩類具有矛盾性的病機共存一處,前文已述及濕熱并存就具有一定的矛盾性,此時又添陰虛與濕滯一對具有矛盾性的病機,處理起來更加棘手。這一證型在臨床實踐中是常見的,對這類證型的治療才最能體現中醫辨治過程中圓機活法的特點。處理這類證候關鍵在于清熱、燥濕、養陰3種治法的比例與各自切入時機的把握,另外對具有這三類功效的藥物也需要認真選擇。清熱多以甘寒養陰之品或苦寒配以甘寒,一般少用淡滲水濕,多以燥濕之品應對濕邪;養陰盡量使用味薄不膩之品,避免助濕。
案8:拙見論病先究體質,今素有血癥,且客游遠臨,從陰虛伏邪,是用藥須避溫燥劫陰矣。鼻躁齦血,舌絳干涸,陰液有欲盡之勢,奈何?邪熱內迫,有油干煙滅之危。醫見病治病,不審肌如甲錯,脈細尺不附骨,入夜煩躁不寐。議以護陰,急清陰中之邪熱。生雞子黃、黃柏、清阿膠、白頭翁、北秦皮、小川黃連、細生地[2]56。
按:本案從病史、癥狀等方面來看,陰傷較重,已有津枯液涸之勢,此時救陰護陰乃當務之急,而泄熱又是救陰不可避免的一環,這二者在應用的主次上要有所考慮。從用藥來看,這個方劑基本是由黃連阿膠湯、白頭翁湯兩方相合加減而成,以黃連、秦皮、黃柏、白頭翁清熱燥濕涼血,以雞子黃、阿膠、生地養陰護液。生地、細生地功用大體一樣,都是滋陰補腎、涼血清熱,但生黃味厚滋膩,大量或久服容易滯膩有礙胃口,細生地養陰而不膩,適合溫熱病后期陰津不足而食納不好的情況。
參考文獻:
[1] 葉桂.溫熱論[M].張志斌,整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53.
[2] 薛生白,也是山人.掃葉莊醫案,也是山人醫案[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10:52.
[3] 吳瑭.溫病條辨[M].南京中醫藥大學溫病教研室整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