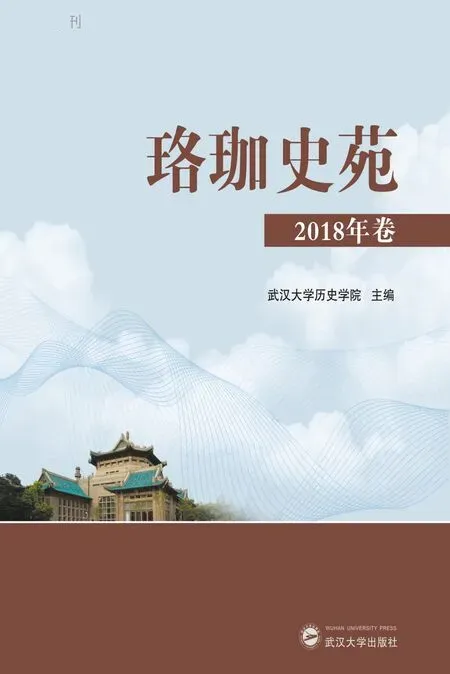試析查士丁尼時期上層婦女的婚姻地位
王冰瑩
家庭作為組成社會的基本單位,它的發展與人類社會從蒙昧、野蠻發展到文明階段并行。隨著家庭形式的不斷進化,婚姻這一制度也隨之產生并發展起來,二者的發展進程密不可分①韋斯特馬克在《人類婚姻史》第一卷中提到,不少早期民族中,男女之間的真正婚姻生活并不是從正式宣布結婚或訂婚的時候開始的,只有到孩子出生或者已明顯懷孕時,婚姻關系才算最終確定。在其他情況下,男女的性關系一旦導致懷孕或生育,其最后結果照例是結婚或強制結婚。作者由此認為是婚姻起源于家庭,而非家庭起源于婚姻,筆者也贊同這一說法。詳細的論述和例證可參照E.A.韋斯特馬克:《人類婚姻史》(第一卷),李彬、李毅夫、歐陽覺亞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72~75頁。。通過結婚,男性與女性得以并入到一個新的家庭中,進而生育并培養下一代,充分發揮家庭的社會功能。除了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外,婚姻和家庭對于男性與女性也有著重要影響,在具體的性別史研究中也是不能忽視的一隅。婦女們在不同時期的婚姻地位也能夠反映當時社會的進步狀況。
作為拜占庭帝國由早期向中期轉變的重要節點,查士丁尼(Justinian the Great,527—565)在政治活動外,其上層社會生活狀況的變化也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是同羅馬帝國時期相比,律法、宗教、婚姻與家庭,各方面都有新發展。以狄奧多拉(Theodora,查士丁尼的妻子)與安東尼娜[Antonina,將軍貝利撒留(Belisarius)的妻子]為代表的上層婦女的婚姻生活,在展示當時社會獨特風尚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查士丁尼時代相較于前代的進步狀況。
有關拜占庭女性的研究,既是拜占庭學研究的新領域,亦是西方婦女史研究不斷拓展所產生的新分支,早在19世紀末就已在國外興起,至今已有不少著作問世。①對拜占庭婦女史的學術史梳理可以參考劉洪英:《11—13世紀拜占庭皇室婦女地位探究》,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第1~2頁。由于文字史料與考古資料的局限所迫,致使以皇室女性為主的上層婦女成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就查士丁尼時代而言,最吸引學者目光的當屬皇后狄奧多拉,相關研究也不少見。②如林達·加蘭的《拜占庭皇后:公元527—1024年拜占庭的女性與權力》 (Lynda Garland, Byzantine Empresses: Women and Power in Byzantium, AD 527-1024.New York:Routledge,1999)、利茲·詹姆斯的《早期拜占庭的皇后與權力》(Liz James, Empresses and Power in Early Byzantium.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以及伊文思的《查士丁尼皇帝與拜占庭帝國》(J.A.S.Evans, The Emperor Justinian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Greenwood Press,2005)等書中都有專門針對皇后狄奧多拉的描寫。伊文思本人還在《狄奧多拉皇后——查士丁尼的伴侶》(J.A.S.Evans,The Empress Theodora-Partner of Justinia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2002)一書對狄奧多拉的生平經歷,尤其是身為皇后時的種種政治、宗教行為做了詳細的研究和考察。從研究角度來看,學者們更關注她們的政治生活,更確切地說,皇室女性如何憑借她們自身所處的特殊地位獲取并運用政治權力是主要研究內容,對婦女們婚姻生活狀況的討論則相對較少。
與國外學界相比,國內的西方女性史研究起步較晚。代表作品是裔昭印等人所著的《西方婦女史》,對西方社會由古至今女性地位的變化過程有一個基本梳理。①裔昭印等:《西方婦女史》,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而具體到對拜占庭女性的研究上,則主要以碩博士學位論文為主。②如:賈繼玉:《早期拜占庭(4—6世紀初)紫衣女性地位評析》,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趙瑞杰:《論狄奧多拉對查士丁尼時代政策的影響》,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邵兆穎:《貝利撒留研究》,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等。而同歷史學領域相比,作為民事法律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羅馬法中的婚姻、家庭和繼承制度在法學領域中也得到了比較多的研究。③如譚建華、張兆凱:《論〈羅馬民法大全〉對婦女權益的維護》,《政治與法律》2007年第2期;郭愛玲:《淺析古羅馬婦女法律地位的變革》,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楊曉兵:《從“嫁資”制度看羅馬法中的夫妻財產關系》,《經濟研究導刊》2011年第35期;戴夢楚:《論羅馬法離婚法規的嬗變及影響》,《邊疆經濟與文化》2012年第9期等。但其中針對拜占庭帝國早期的婚姻繼承等問題的法律研究比較少。因此筆者試圖結合歷史學與法學材料,對這一時期的婚姻關系做一梳理,并從婚姻關系的三階段來考察上層婦女的婚姻地位情況。
一、婚姻關系成立前的上層婦女
(一)上層婦女締結婚姻時的意圖
結婚這種社會行為,本身就有極強的目的性。而隨著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結婚意圖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羅馬-拜占庭社會的結婚意圖大體上可以總結為金錢、家族繼承和市民義務三種。就上層婦女而言,婚姻中的經濟與政治意圖更為明顯。
首先是經濟意圖。按照羅馬法的規定,女子出嫁時,父親具有為女兒設置嫁資的義務。①保羅語,載D.23,3,1(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頁)。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前期,羅馬法學因法學家活躍的活動而繁榮發展。這一時期,許多法學家都通過著書立說來解釋法律,其中不少還被皇帝賦予了法律解答權。其中最著名的五大法學家分別是:蓋尤斯、伯比尼安、保羅、烏爾比安以及莫迪斯蒂努斯。到查士丁尼時期,國家的立法有了進一步發展。在查士丁尼看來,“那些法律(即羅馬法)沒有給予這些服務自己丈夫,還冒著生命危險為家庭誕下新生命的婦女們以絲毫的憐憫之情”②Lynda Garland, Byzantine Empresses: Women and Power in Byzantium, AD 527-1024.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6.。對此,他不光通過《學說匯纂》繼承了羅馬時期強化婦女在父家地位的相關規定,③狄奧多西皇帝(Theodosios,379—395)和瓦倫丁安皇帝(即瓦倫提尼安,Valentinian,364—375)致羅馬城元老院,載 C.6,61,1(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頁)。而且,他還進一步限制了丈夫處置嫁資的權力,命令“丈夫不僅不能未經妻子的同意將嫁資田宅進行抵押,而且亦不能出售。因為要避免丈夫利用妻子的軟弱使她迅速地變得貧窮”④優士丁尼皇帝(即查士丁尼)致君士坦丁堡和所有行省的民眾,載C.5,13,1,15b(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頁)。。這些規定在保證父家與夫家對財產的傳承和使用有合法權利的同時,也為婦女們在父權制下的家族以及與丈夫構筑的婚姻中的地位提供了明確的經濟保障。
其次是政治意圖。上層女子往往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而成為名貴家族間政治聯姻的重要籌碼。比如在羅馬時期,愷撒(Caesar)就曾因政治利益的變化而解除女兒原先的婚約關系,轉而將她許給了當時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龐培(Pompeius)。⑤參見[古羅馬]蘇維托尼烏斯:《羅馬十二帝王傳》,張竹明、王乃新、蔣平等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14頁。
而在早期拜占庭時期,上層女性婚姻的締結過程仍包含濃重的政治色彩。從君士坦丁(Constantine,306—337)到查士丁尼,多位皇帝的婚配對象都是上層貴族之女,甚至還有不少與皇室有關。如君士坦提烏斯二世(Constantius,337—361)的堂弟朱利安皇帝(Julian,361—363),他的妻子海倫娜(Helena)就是前任皇帝的姊妹,亦是君士坦丁皇帝之女;雖然查士丁(Justin,518—527)與外甥查士丁尼的妻子并不是上層出身,但無論是尤菲米婭(Euphemia,即查士丁的妻子)還是狄奧多拉,在為王位繼承人挑選伴侶時,也受到這一傳統的影響,更多考慮到候選人的上層背景。①尤菲米婭看不上狄奧多拉的貧賤出身,她的去世使后者的婚姻阻力大為消減;狄奧多拉則選擇將自己的外甥女嫁給繼位的查士丁二世皇帝(Justin II,565—578)。從這一角度上講,婚姻已不單是男女雙方的個人事務,而是二者背后兩個家庭、家族結成利益共同體的象征,上層婦女在婚姻的結成過程中只能服從來自“家父”的命令,雖然與婚配對象門當戶對,但很難有說“不”的權力。
不過,與東方社會中重視繼位者血統純正性的現象不同,在羅馬社會,“家庭姓氏比起血緣關系要重要得多”②菲利浦·阿利埃斯、喬治·杜比主編:《私人生活史》(第一卷),李群等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頁。。對于上層家族來說,“有時領養和結婚一樣,是一種控制財產外流的方法”③菲利浦·阿利埃斯、喬治·杜比主編:《私人生活史》(第一卷),李群等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頁。,加上當時的“社會生育能力從450年至460年間開始明顯表現出衰退趨勢,到查士丁尼時期達到了頂峰”④羅伯特·福西耶主編:《劍橋插圖中世紀史(350—950年)》,陳志強等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頁。,人口的失衡狀態在客觀上也促使收養之風盛行。隨著收養制度的不斷發展成熟,也使得大家族對于婦女生養后代不再有強制性要求,這在客觀上對婦女權益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使她們不至于淪落為卑賤的生育工具。
在政治與經濟意圖外,還有一些特例也值得關注。其中以帝國統治者查士丁尼與狄奧多拉皇后的婚姻為主要代表。當查士丁尼將狄奧多拉立為自己的皇后時,他“將愛情、情欲視為被灌輸在年輕男女血管中的一股破壞性力量,以及一劑來自愛神丘比特之箭的毒藥。這導致他們……忘卻了羅馬的婚姻重在經濟地位的考量以及與有名望的家族的聯姻”①J.A.S.Evans, The Emperor Justinian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Greenwood Press, 2005, p.29.。根據著名史家普羅柯比(Procopius)的記載,狄奧多拉不過是一位馬戲團熊師傅之女,出身低下。還在母親的安排下,早早地就開始登臺演出。②普羅科皮烏斯:《普羅科皮烏斯戰爭史》(下卷),王以鑄、崔妙因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971~972頁。
當她與時任愷撒的查士丁尼相遇后,“他(即查士丁尼)很快便為她的天生麗質、聰穎和對時世的見解所傾倒。經過5年的接觸,年已43歲的查士丁尼一世完全被她征服”③陳志強:《拜占庭帝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頁。。甚至還“把她提升到貴族的地位。提奧多臘(即狄奧多拉)于是得以立刻取得了非同尋常的影響和相當大一筆的財產”④普羅科皮烏斯:《普羅科皮烏斯戰爭史》(下卷),王以鑄、崔妙因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974頁。。可以看出,查士丁尼是在愛情的指引下,選擇了地位低下的狄奧多拉,同后者的婚姻顯然難以為他帶來經濟或政治上的利益。與他類似的是,其部下貝利撒留也娶了一位駕車手之女為妻。這位女子不僅地位低下,而且在與貝利撒留結為連理之前已經生過好幾個孩子,⑤普羅科皮烏斯:《普羅科皮烏斯戰爭史》(下卷),王以鑄、崔妙因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931~932頁。不過這些都無法阻礙貝利撒留對她萌生摯愛之情并選擇與她共度余生。可見當時的上層社會中也有以愛情為目的的婚姻。
雖然有這樣的特例,但從總體上看,上層社會在考慮婚姻問題時,仍然以經濟、政治意圖為中心。眾多貴族女性失去了婚姻自主權,大多只能完全服從家族的安排。
(二)上層婦女締結婚姻時受到的限制
雖然有種種目的促使男女雙方選擇了結婚這一社會行為,但婚姻的結成仍受到社會道德與法律的種種約束。社會賦予婚姻的條件主要可以分為對“婚意”與“婚姻待遇”的規定、對合法婚姻的規定兩部分。
第一項是“婚意”與“婚姻待遇”。前者即羅馬法學家所說的“結婚意愿”,指的是“在男女之間建立起一種持久而親密的同居關系并且共同生育和撫養子女的合意”①黃風:《羅馬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頁。。而且,他們還強調“婚姻不是基于交媾而是基于婚意產生”②烏爾比安語,載D.35,1,15(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頁)。。比起辦理法律手續或立下書面證明等行為,男女雙方之間存在“婚意”的心理要素更為重要。而用于證明這一合意的外部行為則被稱為“婚姻待遇”,也就是“配偶雙方在各個方面以夫妻相互對待,并且達到使其婚姻關系在社會上得到承認的程度”③黃風:《羅馬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頁。。最重要的一種外部行為是丈夫在家中接納他的妻子。女方必須被男方接到其家中居住,而不是僅僅通過書信等形式表示自己對婚姻關系的認可。④參見黃風:《羅馬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頁。到了查士丁尼時代,“只要雙方有結婚意愿,則婚姻有效。盡管嫁資未給付(dave),或者就嫁資未寫任何文字依據,但是,在這種情形下如同文件寫成一樣,婚姻是有效的。因為婚姻不是通過嫁資而是通過雙方結婚的意愿所締結”⑤優士丁尼皇帝語,載C.5,17,11pr.(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頁)。。這些規定都將合意提升為締結婚姻的首要條件。上層女子在法律上被賦予了自主尋找合意對象的權利。
第二項是合法婚姻。相關規定中既有基礎性要求,也有不少禁止性規范。前者包括“婚意”、通婚權、適婚年齡以及尊親的同意;后者則分為出于血緣考慮的亂倫禁忌與出于政治考慮的跨等級結合的禁令。
首先是“婚意”,因前文已有涉及,此處不再贅述。其次是對通婚權的規定。羅馬時期就要求男女雙方必須是“羅馬市民或者享有與羅馬市民通婚的資格,并且是自由人”①黃風:《羅馬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頁。。到了查士丁尼時代,《法學階梯》中還有更明確的規定,“合法的婚姻在羅馬市民之間根據法律的規定締結”②I.1,10pr.(徐國棟:《優士丁尼〈法學階梯〉評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頁)。,這一條令進一步排除了外邦人、野蠻人以及奴隸能結成合法婚姻的可能性。再次是對于適婚年齡的要求。法律中將不完全適婚年齡(相當于最低婚齡)規定為男14歲與女12歲,而完全適婚年齡規定為男18歲與女14歲,這一點是以女性能承受男人且不受其傷害為標準。③參見徐國棟:《優士丁尼〈法學階梯〉評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9~80頁。最后,如果兩位年輕人中有一方仍是處于“家父”控制下的“家子”,那么二者的婚姻必須取得他這位“尊親”(通常就是“家父”)的同意。
在滿足這些基礎性要求之外,男女雙方在締結合法婚姻時還會遇到不少禁婚規定。根據法令,這些被強令禁止的婚姻主要是出于家庭倫常和社會秩序兩方面考慮。
從維護家庭倫常上講,查士丁尼在立法時堅持了自羅馬時期即有的一夫一妻制原則以及近親之間不能婚配的原則,并且禁止直系親屬以及第三親等④親等:用來衡量某一親屬關系遠近的標準。直系親屬之間按照代計算,旁系親屬之間則由己身向共同的祖先上溯,再從該共同祖先向另一親屬對象回溯,并計算其間代數。參見黃風:《羅馬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頁。內的旁系親屬之間的結合。即使兩人之間是因為收養行為才有了名義上的尊親屬與卑親屬之分,也不能因收養關系的解除而結婚,因為在他們之間仍存在擬制血親的障礙。⑤I.1,10,1(徐國棟:《優士丁尼〈法學階梯〉評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頁)。同時,出于對姻親關系的尊重以及對倫常的維護,法律禁止姻親間的結婚。例如“不許娶繼女或媳婦為妻”,“禁止娶岳母和繼母為妻”等。⑥I.1,10,7(徐國棟:《優士丁尼〈法學階梯〉評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3~85頁)。
而從維持既有的社會秩序上講,禁婚規定是對社會已有分層的再一次強化。尤其是對上層貴族而言,其可婚配對象受到嚴格限制。那些在帝國各處擔任要職的人不能娶具有當地籍貫或居住在當地的女子為妻,最多允許二人訂婚,直至男方離開這一地區去他處任職或是放棄公職后,才能締結合法婚姻。否則,將受到一定的懲罰。①參見保羅語,載D.23,3,38pr和D.23,2,65,1(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頁)。同時,“除元老院成員及其兒子之外,允許所有的生來自由人娶被解放的女奴為妻”②杰爾蘇語,載D.23,2,23(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除非這些上層人士愿意主動放棄他們的顯貴地位,否則嫁給他們的女子們將無法取得妻子的名分。③參見烏爾比安語,載D.23,2,27(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同樣,元老院成員的女兒也不能同解放自由人④解放自由人是指奴隸經主人解放后而取得自由權的人。在查士丁尼時期規定,奴隸一經解放,便可成為自由人,除受恩主權限制外,享受與生來自由人相同的權利。參見周枏:《羅馬法原論》(上冊),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247~249頁。結婚,否則婚姻將被判定為無效。⑤參見保羅語,載D.23,2,16pr(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
不過這些禁婚規定對于國家最高統治者的約束力有限,因為皇帝本人掌握著立法權。在查士丁尼的鼓動下,他的舅舅查士丁允許獲得貴族身份的前女演員們可以嫁給自己喜歡的任何人,他和狄奧多拉也得以順利締結合法婚姻。而且在541年的一條正式法令中,他幾乎將所有橫亙于不平等階級間通婚的障礙都移除了。⑥J.A.S.Evans, The Emperor Justinian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Greenwood Press, 2005, p.29.得益于他的努力,不同社會階層間的結婚阻力不斷縮小,但可惜這一努力并未撼動已有社會等級的根基。因為對上層人士而言,比起虛無縹緲和滿含沖動與激情的愛情而言,經濟與政治上的有利可圖明顯更為現實。
二、上層婦女在婚后生活中的地位
(一)“女主人”積極參與經濟和政治生活
當男女雙方正式締結婚姻關系后,女性的身份地位也發生了變化。從原本的“受到父親約束和制約的居家女子上升為具有一定地位和自主權的家庭主婦”①裔昭印等:《西方婦女史》,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83頁。。她們平日的主要工作就是協助丈夫處理家內事務和撫育子女,而當其夫外出工作時,她們就成為宅邸中一切事務的全權負責人。
與中下層婦女可能仍需自己親自操辦家中瑣事不同,上層婦女的“女主人”形象更為鮮明。得益于尊貴的身份地位,她們的身邊往往充斥著大量奴仆以供差遣,穿衣打扮等小事根本無需她們親自動手,而是理所當然地交由侍女與仆人操勞。②Judith Herrin, Review about Byzantine Women and Their World.Speculum,2005(80),p.598.她們自己則主要負責為每一件事務選派合適的人手,同時用心經營自己的上層社會圈。
“女主人”的身份和執掌不僅使這些貴婦們在婚姻、家庭中得到了應有的尊敬,也帶給她們種種特權。以狄奧多拉為例,原本君士坦丁堡的上層貴族因她曾經的演員經歷與妓女的身份而非常看不起她。但當狄奧多拉成為皇后后,她對宮廷禮節的強調達到了一個新高度,以還擊那些令人不適的目光。她命令那些想要謁見她的人必須在接待室中耐心等候,直至她做好準備去見他們為止。而在見面時,他們還必須拜倒在她面前,親吻她的腳面以顯示他們的敬意,彰顯出她身份的顯貴。③J.A.S.Evans, The Emperor Justinian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Greenwood Press, 2005, p.38.
除了禮節上獲得的尊重外,“女主人”的身份還為這些上層婦女拓展了可以自由活動的空間,在經濟、政治、宗教、社會公益活動等多方面都有她們積極參與的身影。
在經濟上,由于在羅馬社會早期時,婦女并不能享受到平等的繼承權及財產主導權,因此在夫家大多居于弱勢地位,受到丈夫的強力控制。直至羅馬共和國晚期,隨著“無夫權婚姻”①無夫權婚姻:與“有夫權婚姻”相對,指婦女不為丈夫“所有”(in manum)。無夫權婚姻履行程序簡單,只要男女雙方有結婚意愿,婚姻即告成立,而無需再進行諸如麥餅婚、買賣婚與習俗婚的法定形式。原本因結婚而脫離“父權”的婦女在婚后仍要接受“夫權”的控制,無夫權婚姻使得她們能夠在結婚后不落在夫家,而是仍接受父權在名義上的控制,并由此獲得了父親財產的繼承權利。參見奧托·基弗:《古羅馬風化史》,姜瑞璋譯,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宮秀華:《從共和走向帝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129頁。的越發普遍,女子在出嫁后雖仍處于“夫權”名義上的掌控下,但實際受到的控制與影響卻大為減弱,而且還因此獲得了父親家相關財產的繼承權。在轉入帝制時期后,女子對父親家財產的繼承情況更加好轉。直至查士丁尼時代,“在財產繼承問題上,女子取得了與男子基本上相等的權利”②裔昭印等:《西方婦女史》,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04頁。。遺產繼承權利的獲得使婦女的婚后生活在嫁妝之外又多了一份身份和地位的保障。獲得了足夠的經濟支持,她們在家中的話語分量也確實得到了提高,并在更多領域中發揮自己的作用。
在政治上,她們雖無法直接干預政治運作,也無法參與公開的政治活動與討論,但與公共空間受到男性掌控相對應的是,她們通常會在私人的家庭生活中對丈夫施加壓力,或通過為他出謀劃策從而間接地參與到政治決策中。如在532年爆發的尼卡暴亂③尼卡暴亂:也稱為“尼卡起義”,指公元532年在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爆發的暴亂(平民起義),因參加者高呼“尼卡”(希臘語,意為勝利)而得名。暴亂的起因是藍綠黨下層人員對官吏的橫暴與苛稅不滿,要求罷免卡帕多西亞(Cappadocia)人約翰(John)和潘菲利亞人(Pamphylian)特里波尼安(Tribunianus)兩名官員,并釋放兩黨被囚禁的成員。他們請求遭拒,隨即便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暴亂。最終在拜占庭軍隊的圍攻下被成功鎮壓。中,面對暴亂的局勢和想要逃跑的查士丁尼,皇后狄奧多拉果斷表達了自己要留下來捍衛皇室權威的想法,使得皇帝和在場朝臣也受到莫大的鼓舞,放棄了私下出逃的計劃。接著,她又建議查士丁尼從暴亂根源——藍綠兩黨身上著手,激化其內部矛盾并分裂他們的勢力,同時派遣將軍貝利撒留和蒙頓(Mundus)帶領軍隊實行武力鎮壓,最終使這場暴亂得以順利平息。①普羅科皮烏斯:《戰史》(上卷),崔艷紅譯,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49~53頁。她的勇氣與智謀在這一事件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此外,與男性之間所形成不同的政治集團類似,在上層婦女之間也有多個關系緊密的社交圈,她們會在圈中交流分享自己的見解、互相出謀劃策。狄奧多拉與閨中密友安東尼娜就是其中一例。安東尼娜曾在皇后陷害卡帕多西亞的約翰時協助她完成了這一陰謀,作為回報,皇后替安東尼娜尋回了她的情夫賽奧多西(Theodosius)并將他藏匿于宮中以便二人復燃舊情。安東尼娜還曾利用這層關系屢屢替對外作戰的丈夫在頻繁的政治斗爭中保全身份、地位和功名。而當貝利撒留在548年再次遇到危機之時,他的妻子匆忙趕回首都,并試圖尋求自己這位密友的幫助,只可惜狄奧多拉此時已經去世,再也無法替他們在皇帝面前周旋一二。②J.A.S.Evans, The Emperor Justinian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Greenwood Press, 2005, p.40.
由此可見,上層婦女在參與政治生活,多采取私人的、較隱秘的方式。其目的并不是為了與男性在政治舞臺上平等地二分天下,對她們而言,更為重要的是能夠支持丈夫的政治事業蓬勃發展,從而使自己也能夠享受到更高等級的特權服務。但可惜物極必反,貴族女性所擁有的政治影響力越大,出于維護既得利益的需要,她們濫用階級特權的可能性就越高,反而對所屬階層的政治威信產生了負面影響。被查士丁尼設為“共治皇帝”的狄奧多拉,專門豢養了一批間諜來收集人們在公開市集與自宅中的行為和話語,使那些膽敢冒犯她的人無法隱瞞。在懲罰這些觸犯她權威的人時,為了不使外界知曉,她會先召見此人,然后將其秘密交付給自己的親信臣子,由他暗地里送去拜占庭帝國最邊緣的地區并找人嚴加看管。類似的懲罰行為要直至皇后心情轉好時才可能停止,又或是因受懲罰之人于經年之后精力耗盡離開人世而宣告結束。①普羅科皮烏斯:《普羅科皮烏斯戰爭史》(下卷),王以鑄、崔妙因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007~1008頁。
(二)“女主人”熱心宗教和社會公益活動
在宗教活動方面,拜占庭的上層女性也有活躍表現。隨著羅馬眾神教與基督教勢力的此消彼長,基督教不僅順利登上國教之位,在公元4世紀時,與教會配套的修道院制度也開始興起,它們為早期拜占庭的社會風氣添加了新元素。②參見菲利浦·阿利埃斯、喬治·杜比主編:《私人生活史》(第一卷),李群等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頁。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女基督徒,她們樂于把自己的財產奉獻給教堂與修道院,還親身參與女性修道團體,整日學習《圣經》并向上帝誠心祈禱。因為比起之前羅馬眾神教時期在家祭中微不足道的存在,她們在基督教時期可以自主選擇傳教布道、禁欲苦修及以身殉道等方式向上帝展現自己的虔誠與忠心。而且同從前只針對女性強調保持童貞的重要性有別的是,基督教的禁欲主義也適于男子,男性悔罪者會被質問是否還保有童貞以及是因何而失,③菲利浦·阿利埃斯、喬治·杜比主編:《私人生活史》(第一卷),李群等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86~287頁。這種不可思議的質問體現的男女平等的觀念無疑會對在家庭中處于服從地位的女性產生吸引力。而上層婦女們對宗教活動的熱衷對整個社會風氣的轉變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除了宗教等方面的活動外,上層婦女還熱心于面向社會的公益活動。其中皇后狄奧多拉因為自己的身世經歷,對女性問題更加關注。她曾將五百多名在市集上做生意的妓女集中起來,送到對岸大陸的懺悔堂中,試圖強迫她們改變生活方式,雖然不太受妓女們的歡迎,但仍然不失為一次積極的嘗試。在她的影響下,查士丁尼在新的律令條文中提到在上帝面前不存在男女性別之分,人人都有平等的地位。④Nov.J.5.2(AD535),轉引自Lynda Garland,Byzantine Empresses:Women and Power in Byzantium, AD 527-1024.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6.對那些試圖扣留女性繼續表演的人將處以罰款,款項被用于幫助這名女性開始一段新生活;而如果一名需要被扣留的女性無法為自己提供保釋金,她也不會被送進監獄,而是被送往修道院,以防在獄中遭到男看守的侵犯。①參見Nov.J.134.9(AD559),轉引自Lynda Garland,Byzantine Empresses:Women and Power in Byzantium, AD 527-1024.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6;J.A.S.Evans, The Emperor Justinian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5, p.29.這些為提高女性權益所做的努力雖然無法扭轉男女地位的巨大差異,但也不容忽視,它為中世紀拜占庭帝國女子地位的進一步上升做了良好的鋪墊。
(三)“女主人”同丈夫和諧相處
這一時期的貴族婦女的婚后生活,除了主動依托手中權力參與各類活動,盡享婚姻帶來的自由外,這些“女主人”們還需面對常規家庭生活,因此如何處理與“男主人”之間的關系就顯得非常重要。通常基于經濟、政治等原因而結成的婚姻,在夫妻雙方之間會有默契地保持一種相敬如賓的狀態。對丈夫而言,取悅自己妻子的主要目的是她的嫁妝和地位崇高的父親。②菲利浦·阿利埃斯、喬治·杜比主編:《私人生活史》(第一卷),李群等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頁。對妻子而言,與丈夫的結合主要是為了完成“父家”的聯姻與“夫家”的傳承香火任務。如果出現兩人“恰好相處得很好,這是最好不過的,但互相理解并不重要”③菲利浦·阿利埃斯、喬治·杜比主編:《私人生活史》(第一卷),李群等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頁。。對更多家庭來說,丈夫需要努力適應妻子脾性上的缺陷,而妻子則要努力適應丈夫混亂的婚外生活。伴隨著女性地位的提高,她們參與的各類活動開始在各方面影響丈夫,因此兩人的關系也變得更為密切。再加上一些婚姻在結成時表現出的濃濃愛意,也為夫妻間的和諧相處提供了基礎,甚至還出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信賴關系。
貝利撒留的妻子安東尼娜與繼子賽奧多西私通。一次,貝利撒留在迦太基(Carthage)親眼目睹了他們的荒淫之事,但他對妻子濃烈的愛意和信賴使他相信了妻子冠冕堂皇的借口,寧愿認為是自己眼花。后來,在二人私通一事已經變成人盡皆知的丑聞之時,有一位女奴勇敢地向貝利撒留揭發了他妻子的奸情,卻沒想到在安東尼娜的努力下,貝利撒留不僅沒有相信這一指控,還在妻子的要求下將這位女奴交給她處置。①普羅科皮烏斯:《普羅科皮烏斯戰爭史》(下卷),王以鑄、崔妙因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933~934頁。貝利撒留的盲目信賴致使安東尼娜此后更加肆無忌憚地與情夫來往。這種信賴雖然稍顯極端,但可以看出在愛情的催化下,一些夫妻在婚姻生活中的相處已不再保持傳統的相敬如賓的模式,而轉為具有兩人特色的新形式。
三、上層婦女在婚姻結束階段中的婚姻地位
(一)夫妻間婚姻關系非自然解除的原因
并不是每一段婚姻都能一帆風順直至夫妻雙方自然死亡,在各種外力與內力的作用下,婚姻關系也有著被解除的可能。具體而言,一段合法的婚姻關系既會因為外部社會原因而解除,也會因為夫妻雙方的原因而破裂。
在由自然降下的“天災”和受國家強權影響下的“人禍”面前,單個家庭的力量總顯得不堪一擊。因此法律中規定,如果配偶中的任意一方死亡,或是在戰爭中被俘虜,②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9頁。那么他們之間的婚姻關系就會隨之解除。無論是542年幾乎蔓延整個東地中海世界的腺鼠疫,還是查士丁尼在位期間發動的以波斯、汪達爾和哥特戰爭為代表的眾多對外戰爭,都造成不少家庭的非自然破裂以及男女雙方婚姻關系的解除。
與難以預料的外力相比,夫妻二人之間結婚意愿的消除也會導致離婚。它與結婚時所要求的“婚意”正相反,雙方缺乏合意,想要永遠分開的想法是離婚的根本條件。“因此,在沒有堅定地表達離婚意愿之前,僅在偶然情形下或者在發火的氣頭上講離婚并沒有法律效力。”①保羅語,載D.24,2,3(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頁)。
(二)查士丁尼時代對上層婦女離婚權益的保護
實際上,離婚這一行為早已有之,至遲于羅馬帝國初期就已經出現夫妻離異的現象。②奧托·基弗:《古羅馬風化史》,姜瑞璋譯,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7頁。而隨著社會發展,不僅僅是離婚現象更加常見,人們對于結成與結束婚姻的態度也越發輕率,各種新的非法定離婚理由不斷出現。③奧托·基弗:《古羅馬風化史》,姜瑞璋譯,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3頁。
在羅馬法中對于離婚形式有著眾多規定,不同形式還具備有不同的法律效力。至查士丁尼時期,主要可歸為四種類型。第一種是合意離婚,顧名思義,是雙方因合意缺失而協商的離婚。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二人提出的原因與法定理由不符,婦女也無需等待五年,④“按公元449年東西兩帝的敕令規定……妻子沒有正當理由離婚的,嫁奩由丈夫沒收……妻子在5年內不得再婚”,參見周枏:《羅馬法原論》(上冊),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225頁。而是于一年后便可再婚。⑤C.5,17,9(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7頁)。第二種是善因離婚,指由于不可歸咎于夫妻任一方的原因而導致的離婚。比如前文提到過的戰爭、瘟疫等原因而致使婚姻關系解除的情況,以及丈夫身患不可治愈的陽痿、配偶中一方罹患精神性疾病、選擇修道院的修士或修女生活而放棄家庭生活等其他情形。⑥黃風:《羅馬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頁。而且在這種情況下的離婚,女性有權要求夫家返還嫁資。⑦參見C.5,17,10(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頁)。這無疑是對女性權益的合理維護。第三種是基于正當理由的片面離婚,是由夫妻其中一方根據合法的理由單方面決定的離婚。合法理由是指其中一方犯了難以容忍的過錯,包括:男方可因女方有通奸,故意流產,獨自去戲院、競技場等傷風敗俗的行為而選擇離婚;①黃風:《羅馬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頁。女方則可因發現男方有通敵叛國、謀逆篡位等行為而提出離婚②J.A.S.Evans, The Emperor Justinian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Greenwood Press, 2005, p.29.。第四種則是無原因的片面離婚。但在法律上它被判定為無效離婚,妻子在遭到事實上的拋棄后,在法律上卻仍是已婚者的身份,并受到婚姻關系的制約。但若有意愿娶她為妻的男子了解她不是被合法拋棄的,那么二人的結合就不構成通奸。③蓋尤斯語,載D.48,5,44(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頁)。同時,法律中還規定丈夫“禁止拋棄無嫁妝的已婚女性”④Nov.J.22.18, 轉引自 Lynda Garland, Byzantine Empresses: Women and Power in Byzantium, AD 527-1024.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6.,以防婦女在婚姻關系解除后難以為生。
這四種離婚形式基本涵蓋了婚姻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種種感情問題與生理問題,從中可以看出,法律在離婚問題上的規定有不少對婦女有利之處。而且對于沒有謀生手段的上層婦女來說,法律中還規定在婚姻解除后,丈夫“應當將嫁資返還給妻子”⑤烏爾比安語,載D.24,3,2pr(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婚姻、家庭和遺產繼承》,費安玲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頁)。,如果不歸還,婦女有權通過“嫁資之訴”要回屬于自己的財產,從而不至于妻子因為丈夫的惡意離婚而一無所有。對于妻子的嫁資外財產,丈夫不僅在婚姻生活中無權干涉,而且在受到妻子所托代為經管時,他也僅有這筆財產的經營管理權,財產所有權仍屬于其妻。并且當婚姻關系解除時,“丈夫有義務將嫁資外財產全部返還給妻子……以自己的全部財產作抵押保證上述義務的履行”⑥黃風:《羅馬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頁。。對于原本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來說,這些條文無疑是她們在婚姻解除后,能夠重新開始一段新生活的堅實保障。
除了法律之外,這一時期特殊的政治環境也為婦女的離婚、再婚提供了有利條件。由于受到皇后狄奧多拉保護婦女權益的影響,那些因犯通奸罪本應受到懲處的婦女,紛紛選擇“立即去皇后那里并且扭轉形勢而對丈夫提出反訴訟,還把他們強拖到法庭上來……而丈夫們從中得到的全部好處就是支付比妻子的奩資還要多一倍的罰金(盡管對他們并未提出任何指控),然后受到鞭笞并且通常被關進監牢,此后他只能看著奸婦們打扮自己并且更加肆無忌憚地接受她們的奸夫的擁抱”①普羅科皮烏斯:《普羅科皮烏斯戰爭史》(下卷),王以鑄、崔妙因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012頁。。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刑罰與罰款,這些丈夫只好忍氣吞聲,保持沉默。雖然有些極端情況反過來對男子權益造成了傷害,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恫嚇手段,直接針對那些懷有惡意、想單方面拋棄妻子的人。
總體上講,查士丁尼時代上層婦女的婚姻地位相比以往有不少提高之處。法律中對于她們在嫁資、嫁資外財產以及“父家”繼承權的確認是她們相關權益的最基本的保障。皇帝查士丁尼與皇后狄奧多拉對婦女權益問題的重視則為她們提供了特殊的時代背景。上層女性本身的特殊身份,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為她們萌發出自覺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打下了基礎。但同時,必須看到這種地位的提升始終居于一定限度之內。社會上各類活動的話事權依然牢牢掌握在男性手中。還有不少的婦女始終處于依附其夫生存的狀態之中。不應過于抬高這一時期上層婦女地位提高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