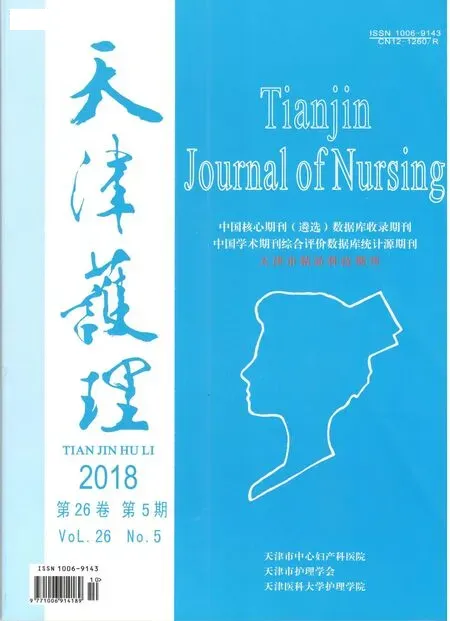對癌癥知情同意權的認知及病情告知模式探索的研究進展
岳 林 龐 微
(1.天津醫科大學腫瘤醫院 國家腫瘤臨床醫學研究中心 天津市“腫瘤防治”重點實驗室天津市惡性腫瘤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天津300060;2.天津中醫藥大學)
知情同意權包含了知情權和同意權,它是指在接受醫療服務時,醫務人員對臨床上具有獨立判斷能力的患者進行各種關于疾病相關醫療信息的告知,在患者充分、正確理解的情況下,自愿決定是否接受某種診療措施的權利[1,2]。1946年,二戰結束后的《紐倫堡法典》中知情同意權首次被定為法定權利[3];1957年在美國形成了系統的患者知情同意權的理論。西方國家,向癌癥患者本人如實告知病情已成為普遍現象[4]。相較于我國,向患者進行病情告知,落實其知情同意權的發展較為緩慢,最早是以手術簽字形式的出現[5]。隨著近年來癌癥發病率在我國逐年上升,癌癥患者的知情同意權在我國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因我國獨特的文化背景和國情,尤其在醫療改革不斷深入的新形勢下,如何保障癌癥患者的知情同意權和實現病情合理告知一直在被研究和探討,現就不同角度對癌癥知情同意權的認知和對癌癥病情告知模式的探索綜述如下。
1 不同群體對癌癥知情同意權的認知
1.1 醫生的認知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在醫療活動中,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應當將患者病情、醫療措施、醫療風險等如實告知患者,及時解答其咨詢,但是,應當避免對患者產生不利后果[6]。該條列明確規定了醫生的權利與義務,但在實際工作中,醫生通常選擇將癌癥患者的病情首先告知患者家屬。趙玉帥[7]的研究指出,由于知情同意而引發醫療糾紛的原因有以下幾點:告知缺失;告知不當;獲得同意權程序不當;知情同意難以履行。褚艷[8]關于婦科癌癥患者告知策略的研究中表明,有75.8%的患者認為應該在確診時將病情告知本人,此結論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證實[9,10]。但在臨床中卻難以做到直接將患者作為第一告知人,多數醫生未對患者的意愿進行有效評估的前提下,而是依據經驗認為癌癥患者不應該成為知道診斷的第一者。有研究報道指出[11],在知情同意權方面,65.41%的醫生認為自己已較好的履行了告知義務,但只有44.77%的患者對醫生的告知情況滿意。
1.2 護士的認知 護理人員同樣存在對患者知情同意權落實不到位的問題,集中體現在缺乏自我保護意識上。護士在患者的整個癌癥治療過程中都涉及到告知義務,而履行好告知義務是構建和諧護患關系的基石,同時也是實現自我保護的利器[12]。造成此種情況的原因包括:護士認知不足、法律意識薄弱、與醫生溝通較少、護士工作量大以及傳統文化的影響等[13]。
1.3 家屬的認知 由于受“家庭本位”思想的影響,癌癥患者家屬在知情同意權的認知上普遍處在偏差。在關于晚期癌癥患者病情告知的研究中發現:27.5%的家屬認為對患者的病情要絕對保密;53.5%的家屬認為要暫時保密;只有19%的家屬認為不需要保密[14]。可見癌癥患者家屬在面臨患者病情告知上多數家屬選擇保密。患者家屬在知情同意權的認知上存在誤區的主要表現為[15,16]:在權力的歸屬上,家屬普遍認為第一知情者應該是家屬而不是患者本人;在目的的理解上,家屬并沒有把告知病情同有利于患者治療相聯系,認為只是一種保護機制。分析原因主要為:傳統文化的影響、患者家屬的文化水平、家屬與醫務人員及患者溝通不足等[14]。另一方面,家屬在經歷了親人癌癥確診后,同樣也需承受很大打擊,此時,知情同意權已不是他們所關注的重點[17]。
1.4 患者的認知 癌癥患者是疾病的直接承受者,在知道自己病情后48 h內,會造成心率加快,收縮壓增高,SAS和SDS評分均增高等負面影響[5,18],其承受的首先不是病魔的折磨,而是精神的崩潰。如果在沒有充分評估患者的認知、情緒、性格和接受程度等情況下,而選擇冒然告知,通常會帶來不良的后果,甚至導致患者放棄生命。在此情況下,就迫使醫生,護士及家屬更愿意選擇保密機制,雖然在情理之中,但不能就此低估患者的接受程度。目前,國內眾多研究均表明,癌癥患者有強烈的知情愿望:曾鐵英等人[9]指出有91%的患者認為自己是最有權的知曉者;謝娟等人[10]的調查結果也在90%以上;丁紅琴等[19]得出的結論為只有19%的腫瘤患者不愿意知道自己的病情;而在其他的文獻中也得出了類似的數據[8]。所以,作為癌癥患者本人多數愿意在第一時間知曉自己的病情,這同時也說明,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們認知的提升,癌癥患者對于自身疾病的認識更加趨于理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告知患者病情,有利于增強患者自我認知提高從而提高積極治療的依從性[5]。因此需要探索一套合理的病情告知模式,使癌癥患者的知情同意不再是不可觸及的禁區。
2 國內外關于癌癥患者病情告知模式的研究現狀
2.1 國外關于病情告知模式的現狀 在伊朗,目前還處在對護士病情告知的認知調查和策略的構想階段。Imanipour M等[20]對德黑蘭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重癥監護室160名護士進行調查,研究顯示,91.2%護士對參與病情告知持肯定態度,78.8%的護士對如何進行病情告知的了解程度適中,但只有少數認知水平較好(16.2%)。2017年伊朗學者Ali等[21]的系統綜述中表明,首要的病情告知者是家屬,因為患者非常脆弱,直接的病情告知會損害其目前的狀況。在伊朗,雖然大多數的患者想要獲得病情的真實診斷,但在臨床醫護人員偏向于使用不直接告知的策略,并且強調了醫護人員掌握溝通交流技巧的重要性。
在西方國家和日本,對于癌癥患者病情告知模式的研究重點已開展到醫護人員告知時溝通技巧的選擇。Bumb M等[22]人2017年基于循證醫學的文章中表明,在告知壞消息時,現已有SPIKES模型和PEWTER模型。2000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即推薦使用SPIKES模型,且被運用在癌癥患者病情告知中[23,24]。此模型共分六個步驟:①設立溝通場景(SSetting);②評估患者認知(P-Patient's perception);③得到患者許可 (I-Invitation);④醫學專業信息告知(K-Knowledge);⑤移情穩定患者情緒(E-Exploring/Empathy);⑥策略與總結(S-Strategy/Summary)。 告知過程中主要強調四個方面:收集患者信息,傳遞醫療信息,提供對患者的幫助,贏得患者對治療的理解與支持。此模型可達到減輕患者心理負擔,融洽醫患關系的效果。PEWTER模型共分為五步,即準備、評估、講述、情緒反應、重新準備。被認為最重要的是“重新準備”這一步驟,其中涉及到患者和護士的合作來共同應對病情告知,確保患者在知曉病情后會對生命保持積極的態度。除了單獨使用兩種不同的溝通模型,護理人員還可以將兩種方式有機結合。日本學者[23]以及Rosenzweig MQ[24]同樣推薦使用SPIKES溝通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2 國內關于病情告知模式的探索 從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由立法開始規范關于患者的知情同意,發展至今歷時不長。由于受傳統文化、經濟和社會等多方面的因素影響,目前并沒有一套公認的告知模式可供參考。雷洪艷[25]嘗試將國外的知情同意制度引入國內進行本土化,探討適合我國國情的知情同意模式;近年來,SPIKES溝通模式被逐漸引入國內,目前該模型已在年輕乳腺癌患者中得以應用,有效的提高了該類患者的生存希望指數和積極應對能力,減輕了心理負性情緒[26],但由于研究的樣本量較小,病種較局限,能否適用于其他種類的腫瘤患者,還需要進一步驗證。Ling DL等[27]人認為,在國內大的醫療背景下,對臨終患者進行真實病情的告知是醫療實踐中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倫理問題。研究者提出在醫療實踐中,護士應根據不同情況對個人需要制定具體的方法,并建立起護士、醫生和患者家庭之間的聯系,以支持癌癥患者,并確保他們的自主權。
3 以患者為主體的病情告知建議及展望
3.1 遵循“以患者為中心”的原則 有學者建議建立院內評估系統[28],以問卷調查的形式評估患者的焦慮,抑郁狀態以及對危重病情告知所持態度。成立評估小組,由醫生、護士、家屬以及心理學專家組成,以評估得更加全面。在充分評估患者情況后制定一套個性化的告知方案。告知方案因人而異,但都必須遵循“以患者為中心”的大原則。
3.2 選擇合適的告知人員、環境、時機 有研究表明,53%的癌癥患者希望由醫生告知病情,29%患者希望由家屬告知[8]。因此在由誰告知的選擇上,多數被調查者認為應該由權威人士來進行。告知時,選擇一個安靜舒適的環境,即有利于患者平復心情,也有利于醫務人員進行準確的傳達,充分體現出尊重患者的態度。選擇一個恰當的時機將病情告知患者,如若判定患者無法立即接受,則暫不告知,可先告知其家屬或其他合適人選,然后以分次告知的形式,將全部信息告知。若患者能接受,則注意告知方式,不要過于激進,同時要隨時觀察患者的反應,并做好相應的應對措施。
3.3 選擇合適的內容 首先告知患者最為關注的信息,以達到高效,滿意的目的,對后續治療形成一個良好的鋪墊[13]。在后續告知中要將患者應該知道和醫生認為患者有必要知道的信息一一告知,做到告知內容齊全,讓患者及家屬對病情有充分的認知。在病情告知時,醫護人員要注意“度”的掌握以及語言的表達方法。
3.4 建立心理輔導中心 癌癥患者會經歷否認、憤怒、協商、抑郁和接受五個時期,建立心理輔導中心,成立輔導小組,定時對患者的心理狀態做測評,做好相關干預,幫助患者順利過渡到接受期。
4 小結
我國癌癥患者的知情同意現狀仍然以 “家庭本位”為主的保護性告知為原則,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患者認知的提高,患者的接受程度也在發生改變。如今研究的焦點從告知主體到對系統告知模式的探索,通過分析醫生、護士、患者及家屬各群體對知情同意的認知,總結國內外關于病情告知策略的探索,提示今后的臨床護理人員借鑒國際上成熟的告知模型,結合實際制定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告知模式,使病情告知更加合理和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