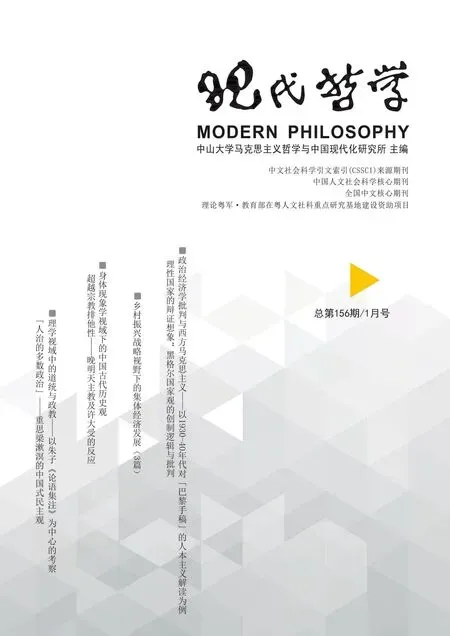儒學日常生活倫理的形上之維
丁成際
儒學的日常生活倫理不是通過概念進行抽象地演繹,也不是以建構形而上的體系來證實,其價值體現于“日用即道”中,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伴隨著形而上的終極關切,在日用生活倫理中蘊含著“知性、事天、立命”與“知天命”的終極追求。在儒家的日常生活倫理之中,貫徹著“天道”與“人道”相統一的原則,人的生命的內在超越與外在的倫理責任認同是相互關聯的,在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中追求著“中”與“和”、“誠”與“信”的人生價值理想,日常生活倫理的規定與道德的終極追問始終相伴隨,家庭生活倫理是儒家日常生活倫理建構之基礎。
一、儒家日常生活倫理中的人生意義問題
儒學日常生活倫理之形上方面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日常倫理生活的人生意義與人生價值。從形上方面來說,儒學日常生活倫理體現出某種宗教性的品格,牟宗三先生稱之為“圓教”。在他看來,儒家的“圓教”是一種人文宗教,在日常生活倫理中求得其價值之源,具有“提上去”以顯示其超越內在性的一面,又具有“落下來”建構生活世界的外在性一面,這與西方把人文世界與崇拜的對象相分離的“外在超越”之“離教”顯然有別。“宗教的責任有二:第一,它須盡日常生活軌道的責任……第二,宗教能啟發人的精神向上之機,指導精神生活的途徑。”*牟宗三:《生命的學問》,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63—65頁。“儒家教義即依據此兩面之圓滿諧和形態而得成為人文教。凡不具備此圓滿諧和形態者,吾皆認之為離教,或耶或佛。”*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1頁。杜維明先生也強調需要從儒家日常生活發揮儒學核心價值在當代的功用:儒家傳統具有宗教性與精神性的一面,在一些平凡人身上能看到他們的自我理解的深刻性。如果不理會這一點,將是一種很大的缺失;我們不能僅僅在習俗層面理解一種文化,而應對它的核心價值重新解讀、研究與闡發,否則會導致對它的誤解,以及這種思想對社會的影響力降低。儒學中的很多資源是基督教所無法把握的*[美]杜維明:《我最看重日常生活》,《大地》2004年第18期。,儒學最成功之處是“日用即道”,將其核心價值轉化為大眾的日常生活倫理,在日常生活倫理中顯現“安身立命之道”。
對于“立命”,朱子訓解說:“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94頁。《論語·述而》曰“志于道,據于德,游于藝”,朱子將這里的“道”解釋為“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立命”就是天命的實現。孟子曾對如何實現命做具體闡明:“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 知之于賢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孟子·盡心下》)對孟子而言,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要按照仁義禮智的要求來立命,來實現天命。對“天命”的覺解(即孔子所說的“知天命”),構成孔孟儒學精神生活的最高精神境界和人生自覺,凸顯出盡心、養性、修身的內容,表現為心性修養、倫理道德實踐的人生過程。在儒家的生活方式里,最高的精神境界體現于將天、命之超越融合于現世日常的倫理道德實踐過程中,形成一個人自覺地設定生命的意義、生活的目標,實現道德與自然、義務與現實之間的和解。儒家要求人對生活目的、生命意義的自覺,也是一個人實現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精神基礎。生命的意義、價值展現,綿延于日常生活相互對待的倫理實體中,父慈子孝的倫理實體與道德要求是生命得以開展與延續的最基礎的方面。在儒家這種孝與慈的道德責任踐行中,即在一種道德的理性自覺中,一個人無論是親代或子代都能感覺到生活的力量、生命的充實,并能從實踐努力的收獲中,在父母得到贍養與尊敬,子女獲得成長與成就中,感受到欣慰、幸福。這體現的是在現世的、平凡的生活中,儒家不企望超越生死,而是在家庭日用倫常生活的希望與責任中實現人生的意義。儒家所追求的人生價值的實現與人性的完善是一個不停息的過程,在“繪事后素”(《論語·八佾》)中不斷追求著人生的完美。因此在看似平常、平凡的儒家日常生活倫理中,卻有著豐富的結構與厚實的生活根基。這也是儒家文化有如此多姿多彩的歷史表現,以及在異質文化不斷侵襲的背景下仍能不斷保持其活力的精神特質。
二、儒家日常生活倫理中的形上之道:“中”、“和”
儒家日常生活倫理恪守著“中”與“和”的價值原則。就“中”的原則來說:孔子一方面要求在位者“守中”,行使“執中”之道;另一方面要求將“中”的原則化為百姓人倫日用之道,在生活實踐中能夠“守中”,“中”的現實化就是“禮”。“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禮記·中庸》),“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前揭書,第94頁。,都是主張人倫日用中的行為恰當、合宜與否需要用“道”這一抽象性的終極標準來衡量。但在現實生活中,“道”就要具體化為“禮”所要求遵守的規范,即在現實、具體的日常生活中,實行、踐履的具體規范是依“道”而立的“禮”*《禮記·仲尼燕居》明確記載了孔子與弟子們的對話:“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抽象的“中”與“和”的原則通過“禮”將天地秩序和諧之道運用到人類社會中,進而落實到現實的人倫日用中*《論語》中有不少記載“中”與“禮”關系的言論,如“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泰伯》)。
如上所述,在傳統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道”的不同層面和角度都與具體的做人規范即“禮”密切聯系在一起,表現為遵守具體的禮儀。對應“天道”有效祀之禮;對應“人道”尤其是“孝道”有侍奉父母兄長之禮。“夫妻之道”有婚姻六禮及居家之禮,“友道”有相見稱謂交接之禮,“職業之道”依職業不同有不同的禮儀。這些禮儀規范在傳統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是隨時隨事隨處而在的,在中國傳統家禮、家訓中表現得最明顯。如傳統中國人首推的“孝道”,所有家禮家訓基本都放在首條:“父母面前無違拗,在生不見子承歡,死后念經有何效?爾子在旁看爾樣,忤逆之人忤逆報,當知孝。”*羅文華、聶鑫森:《中華姓氏通書·陳姓》,海口:三環出版社,1991年,第136—137頁。如何孝?各種家禮家訓規定了詳細細節,包括對父母的晨省昏定、養身娛心及對已逝祖先的祭祀時享,在父母面前言語溫和、容色恭順、動作舒緩以免父母擔心驚嚇。繼承之后,家訓尤重夫婦之禮,對夫婦之義及相關規范有明確訓示:“和夫婦:陰陽交和,雨澤斯行。夫婦調和,家道乃成。夫為妻綱,正心修身。婦主中饋,內助殷勤。毋玷家聲。雍雍肅肅,如鼓琴瑟。君子偕老,詩詠睢麟。”*羅文華、聶鑫森:《中華姓氏通書·羅姓》,第119—122頁。這強調夫婦有禮有節是禮之始、家之成。雍雍肅肅,既是夫婦和諧之態,亦是家庭和睦親融而又整肅有禮的風范,可以說是所有的禮所要達到的功效。*王雅:《當代中國日常生活倫理的建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14—115頁。儒家的禮以“分”和“節”的形式,追求的最基本、最高的目標與境界是“和”。一方面,禮的制定本身要合道、合宜;另一方面,人在行禮之時必須依禮而行,無過無不及,恰如其分,復合中道。合情合禮、通情達理、謙和有禮,是傳統中國的齊家之道;禮讓為國,是對統治者為政之道的肯定與期許。在傳統中國社會,可謂“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堯曰》)。“禮”是人立身于社會、生存于社會的根本,日用常行不可一日不修。人一日“克已復禮”,一日身心平和,家和安樂,又能“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如果天下之人,人人日日“克已復禮”,就會實現大同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
三、儒家“誠”觀念的形上分析
儒學以“誠”“信”為日常生活倫理形而上方面提供途徑與擔保。就“誠”的意義來說,一是要處理好人禽之別。人們在日常生活人倫中關系相互信賴、相互期待,在真情實感中過著誠實不欺的生活,從而避免弱肉強食、急功近利之動物似的叢林法則*王雅:《當代中國日常生活倫理的建構》,第183—185頁。。二是要保證道德踐行。儒家的日常生活倫理為人們提供基本的原則與規范,為人們的日常倫理生活提供根本的路徑,也為人們的生命的安頓提供住所,為人之為人的內在超越之體認與確認提供形上本體。一旦通達了“誠”的境界,人自然會“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中庸》)。“誠者”是“天之道”,“誠之者”是人之道,使誠實現出來。普通人一般要經過“自明誠”與“自誠明”的雙重化過程。如果說“自誠明”是一個“尊德性”的過程,在日常生活倫理方面顯現的是形而上的“至圣”的追求,那么“自明誠”就是一個“道問學”的過程,踐行的是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倫理責任。“自明誠”與“自誠明”的形而上與形而下的互動與轉化,使在日常生活倫理的見習中達至“至誠”的形上境界成為可能。王陽明曾言:“《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后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圣之類,則又圣人之自能‘修道’者也。”*[明]王陽明:《傳習錄》,于自力、孔薇、楊驊驍注譯,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66頁。如此來說,“致曲”的過程就是由“人”至“圣”之“人之道”的過程。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明“誠之”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現實生活中實現“誠”的境界,因而為儒家所言的圣人與常人劃開一道界限。但是這個界限又不是絕對的,從“人人皆可為堯舜”的意義上言,“誠”可以在功夫論的方面得以實現,這是儒家將成圣之途落實到日常行為的重要表現。因此,“誠”的實現必須通過人的具體行為來完成。“誠”是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具體統一,說明儒學日常生活倫理既符合形而下的日常生活規范,也通達形而上的“人道”與“天道”的要求。
“誠”是世界的本來狀態,由“誠”到“明”是一個自覺反醒的過程。“自誠明,謂之性。”(《中庸》)這里的“明”是實踐理性,是認知與實踐的結合體達到反思之明,是一個明乎“善”的過程,可以說喚起心中的良性與良能。由“誠”到“明誠”,自“誠”到“明”理應為一個人“無可逃乎天地之間”的人生走向。所以,落實到日常行為的“誠”的實現就不僅是一種倫理意義上的規定,更是作為人性基礎的“天命”;“誠”的實現不僅是一個意愿問題,更是一個從日常行為“上達”天命的過程,這一過程就是儒家所強調的“自明誠”。誠的開啟首先需要人的“擇善”,需要的是“智”,即人的理智之知,使人保持“志于道”而不偏離人生的方向。經過擇善固執的操存涵養,終達至《大學》的“明明德”,照明內心之“誠”,使“誠”與人的自覺合一,“思誠”成為自覺的反思行為。孟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這里的工夫當然不僅是一種境界體認,更是對儒家日用倫常的落實。這種落實不只是按照外在的倫常要求去做,而且是從內心中生發出對“誠”的體認,并在此基礎上踐行對“誠”的體認,這就是功夫。“誠”上貫于天,下落于人,是純粹至善。周敦頤言:“誠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宋]周敦頤:《周敦頤集》,譚松林、尹紅整理,長沙:岳麓書社,2002年,第15—16頁。“誠”是宇宙的根本,也是人真實無妄本性的根源,是朱熹的天理的實然,無絲毫作偽的“誠”。具備“誠”、體證到“誠”的人就是圣人,是身心性命各得其正的人,或說是“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正蒙》)的人。成為這樣的人首先要擇善固執,也就是人事所當然,是盡人之道。
四、儒家“信”觀念的形上之辨
在儒學的日常生活倫理中,“誠”與“信”是互為表理的。“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于中者謂之孚,見于事者謂之信。”*[南宋]朱熹:《朱子語類》第21卷,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59頁。“誠”固然是本體心性,“忠”是盡這本體心性,“信”是本體心性的外在表現;“誠”是德性原則,“忠信”是德性與規范的合一,“誠”顯然是最為根本的。在現實中,誠與信通常是聯系在一起的,“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朱熹將守信、忠誠看成是安身立命之道,是做人的根本。“人道惟在忠信……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教人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忠信只是一事。但是發于心而自盡,則為忠;驗于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大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為本之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前揭書,第99頁;[南宋]朱熹:《朱子語類》第21卷,前揭書,第159頁。)陸九淵將忠信看作是人禽之別的標志,認為忠信是為人之本,不忠不信之人與禽獸無異,“人而不忠信,果何以為人乎哉?鸚鵡鴝鵒,能人之言;猩猩猿狙,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異于禽獸者乎?”*[宋] 陸九淵:《陸九淵集》第3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74—375頁。
“信”源于“誠”又超越“誠”。對形而上本體“誠”的確認在儒家基本是共識,正因為“誠”的存在,“信”“忠信”“誠信”等才具有根基和超越的意義。“誠”顯然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上,還要踐行于日常生活中,這就要由“誠”至“信”、“體信”,由道德主體走向道德主體間的確認與證實。“信”德作為諸多道德規范之一,自孔子提出并經后世儒家的不斷倡導、充實和完善,與“誠”“誠信”“忠信”等共同構筑起信德體系。其中,“信”的建構通常在兩個方向展開:一是在超越的形上本體中體認,即體“誠”、體“天道”;二是在形下的日常實踐中體認,即體認“人道”,具體要求就是在言行舉止上“體信”*王雅:《當代中國日常生活倫理的建構》,第167頁。。這種“體信”既包括言行者在自身言行中“體信”,也包括他人在言行中對他的體認和道德評價。換言之,一個人的舉止言行不僅是其自身“信”德的體現,也是他人對其進行道德評價的依據。將誠信融于日常言行中,必須持之以恒,即使面臨險境也不能失去誠信,即居險而不失信。《坎》卦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象傳》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信。”誠信出自內心,必定亨通。“習坎”即為多種險境,險阻重重。行險而不失信,才能達到內心亨通。將誠信融入日常生活中,絕非一時的工夫,必須持之以恒,常保美德。故孔子告誡弟子以“恭敬忠信”立身立人,強調“君子”要“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論語·衛靈公》),要具備“恭、寬、信、敏、惠”之美德。郭店楚簡的《忠信之道》也提到“君子”言行要秉持“忠,仁之師也;信,義之期也”*《郭店楚墓竹簡》,荊門市博物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63頁。的原則。至此,“信”作為君子人格和道德規范的意義已經牢固確立起來。
孔子給自己定立的人生三個最高目標中,“信”即是其中之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 公冶長》)在人的日常生活、言行舉止中,時時處處以“誠”德為標準和規范做事做人,是個人立身處世的根本、家庭和睦的基礎、人與人互信友愛的前提、國家安定的保障。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傳·文言》),就是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堅持誠信,真誠實在地生活。“誠”在現實生活中通常表現為“信”,“信”作為五倫之一,具有更強的實踐屬性和對實踐的規范。如果沒有“信”,“仁”“義”“禮”“智”可能只是虛懸之理。朱熹就是從“信”對“仁義禮智信”五種德性之確立的重要性的角度說明“信”何以成為“五德”:“信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南宋]朱熹:《朱子語類》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43頁。無法與真實的人的生命與生活相關聯,就失去了五倫的價值與意義。“信”就是真正、確實地擁有仁義禮智,而不是假的、虛的。“信”的實現要回到內心之“誠”中,回到“仁義禮智”的原發之地。“信”作為德性。成為人的行為之始的基礎與行為之中的依據,這就要求人要“擇善固執”、“操存涵養”。“擇善固執”是內在的修養與外在的踐履的統一,要求在個人的生命歷程中不斷地證實與“固執”應有的人倫關系。唯此,“信”德在日常倫理生活才得以完善與鞏固。因此,“信”的實現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由內心之“誠”自內而外地涵養,實現“誠”與“信”內在統一;自外而內地固執“信”德,使“信”在人們的日常行為中呈現出來。
五、余論
儒家日常生活倫理建立在家庭倫理道德基礎之上。在儒家的道德觀念中,家庭關系以夫妻關系作為組建基礎,夫妻之間和睦是家庭和諧的基礎,夫妻之間首先要誠信相待。夫婦關系的確立始于昏禮,昏禮的二性(姓)相合是效法天地而成人倫,即“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性,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禮記·郊特牲》)。此處雖強調“信,婦德也”,并因附有“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禮記·郊特牲》)之語,而被歷代反儒人士作為儒家“封建道德”壓迫女性的鐵證,但據此認為“信”只是對婦(女)單方面的要求是不確切的。這里的“幣必誠”“告之以直信”之語,都是指夫(男)的一方要真誠,把男方的情況直言相告,然后才能訂立婚姻信約。應該說,“信,事人也”是男女夫婦雙方當事人共同的信約,這一信約一旦確立就是一個家庭、一個家族千秋萬代之始,猶如天地合和萬物興旺一樣。夫婦以誠合一,以信相守,是夫婦長久和睦之道。早在《周易》中,對夫婦之道就多有闡發和規定。《小畜·象傳》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如果夫妻不和,家庭就不正常,就會有禍殃;如果夫妻誠信相待,志同道合,就會家道興旺。所以《咸》卦特別強調夫妻之間誠信的重要性:“咸:利貞。取女,吉。”《傳》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感應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孔穎達解釋說:“此卦明人倫之始,夫婦之義,必須男女共相感應,方成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荀子·大略》)那么,什么是夫婦之道?《家人》卦專門闡述了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夫婦關系及其原則對整個家庭關系的影響:“家人,利女貞。”《象傳》曰:“家人,女正乎內,男正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夫婦有分工、有合作,分工合作的基礎是“正”,所謂“正”就是效法天地之大義,真誠無妄,真實不欺,要“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象傳》)。言語真實,行為堅定,這樣的夫婦以誠信相待,以誠信治家,“有孚威如,終吉”(《周易·家人》),終令家道興旺吉祥,家人“交相愛”(《家人·象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