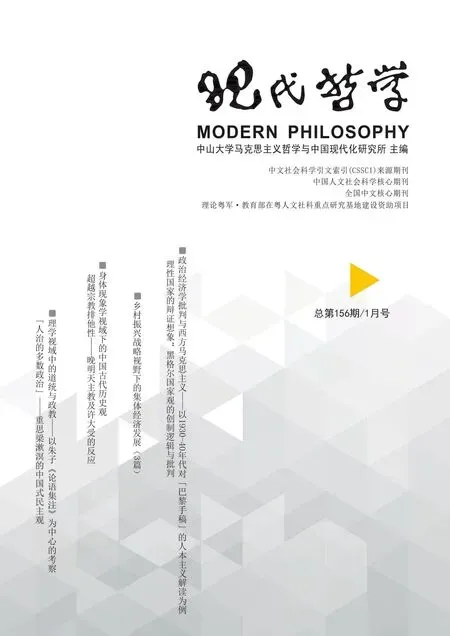等同鏈條、內(nèi)在分野與大眾認(rèn)同
——厄內(nèi)斯托·拉克勞論“民粹主義”的三個(gè)結(jié)構(gòu)性維度
張 炯
厄內(nèi)斯托·拉克勞(Ernesto Laclau)在《論民粹主義的理性》一書(shū)中詳細(xì)分析了“民粹主義”這個(gè)幾乎無(wú)法定義的術(shù)語(yǔ)。在他看來(lái),既有研究要么忽視民粹主義,要么只是作為一種現(xiàn)象來(lái)分析,除了訴諸道德譴責(zé),并沒(méi)有形成實(shí)質(zhì)性的推進(jìn),因?yàn)槲覀內(nèi)匀徊磺宄翊庵髁x為什么會(huì)發(fā)生。因而,要得出不同以往的新結(jié)論,就需要與先前的分析范式劃界。這一劃界首先需要確定:分析民粹主義的最小單位是什么?如果按照社會(huì)學(xué)的分析范式,把“團(tuán)體(group)”作為分析單位,那么民粹主義就被當(dāng)作一個(gè)既定團(tuán)體的動(dòng)員形式或意識(shí)形態(tài),抑或是組成團(tuán)體的方式。但組成團(tuán)體的方式不止民粹主義一種,總會(huì)有其它的社會(huì)邏輯使得不同于民粹主義的認(rèn)同類型存在。所以,對(duì)民粹主義接合實(shí)踐的標(biāo)準(zhǔn)的再定位,首要任務(wù)是找到一個(gè)比團(tuán)體更小的單位。拉克勞選擇了“社會(huì)要求(social demand)”,正是看中“demand”在英語(yǔ)中的含義是不確定的,既可表示一種“需求(request)”,也可表示一種“主張(claim)”。他認(rèn)為可以在“需求”到“主張”的變化中捕捉到“民粹主義”的三個(gè)結(jié)構(gòu)性維度的縮影:“多元要求統(tǒng)一于等同鏈條(equivalential chain);把社會(huì)一分為二的內(nèi)在分野(internal frontier)結(jié)構(gòu);等同鏈條通過(guò)建構(gòu)大眾認(rèn)同(popular identity)而得到鞏固。”*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77.
一、等同鏈條:從民主要求到大眾要求
拉克勞首先設(shè)想民粹主義的原初狀態(tài),分析這些相互分離的要求如何出現(xiàn),以及它們是怎樣接合起來(lái)的。在發(fā)展中國(guó)家的貧民區(qū)里有一大群農(nóng)村移民,他們希望地方政府解決他們的住房需求。此時(shí)的要求只是需求,一旦要求滿足了,這個(gè)事就結(jié)束了。但如果沒(méi)有滿足,那么他們可能會(huì)開(kāi)始逐漸意識(shí)到其它一些同樣沒(méi)有得到滿足的要求,如醫(yī)療、教育等。如果這種情況在一段時(shí)間內(nèi)僵持不下,那么這些要求將會(huì)聚集起來(lái),而既定的制度系統(tǒng)將愈發(fā)無(wú)力以不同的方式消化它們。之所以是不同的方式,是因?yàn)檫@些要求實(shí)際上互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解。一種等同在這些要求之間建立起來(lái)。我們能很自然地預(yù)想到結(jié)果:“如果沒(méi)有外來(lái)因素的干預(yù)解決,那么制度系統(tǒng)與人民的分歧將會(huì)越來(lái)越深。”*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74.
按照拉克勞的觀點(diǎn),這些原本相互分離的、未滿足的“民主要求(democratic demand)”*為什么拉克勞要用“民主的”來(lái)稱呼這些要求,而不是“特殊的(specific)”或“分離的(isolated)”?他在書(shū)中第四章的附錄專門(mén)作了解釋。這里的“democratic”不與某個(gè)特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有關(guān),它只是描述性的,表示要求之間的平等關(guān)系,而且這些要求的出現(xiàn)以某種排除或匱乏為前提。參見(jiàn)Ernesto Laclau, Why Call Some Demand “Democratic”? ;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p.125-128.,通過(guò)接合進(jìn)等同鏈條中,轉(zhuǎn)變?yōu)楦鼜V泛的“大眾要求(popular demand)”。正是這些大眾要求開(kāi)始建構(gòu)“人民(people)”這一潛在的歷史行動(dòng)者。拉克勞認(rèn)為這是最原初的民粹主義結(jié)構(gòu),從中不難發(fā)現(xiàn)民粹主義產(chǎn)生的三個(gè)前提,其中前兩個(gè)是顯而易見(jiàn)的:第一,內(nèi)在的對(duì)抗分野分離了人民與權(quán)力;第二,這些要求的等同地接合使“人民”得以出現(xiàn)。還有第三個(gè)前提,它只有在政治動(dòng)員達(dá)到較高層次時(shí)才會(huì)真正出現(xiàn),即這些要求被統(tǒng)一到一個(gè)穩(wěn)定的意指(signification)體系里,即形成統(tǒng)一符號(hào)。鏈接諸要求的等同鏈條要想得到鞏固,只有通過(guò)鏈條的不斷延展和尋求符號(hào)的統(tǒng)一。這可以用來(lái)解釋為什么法國(guó)大革命之前小范圍的地區(qū)暴動(dòng)沒(méi)有取得大革命時(shí)期暴動(dòng)那樣的成效。因?yàn)橐蟮牡韧湕l沒(méi)有延伸到其它社會(huì)成員的要求,沒(méi)有把其它要求接合到等同鏈條中。等同鏈條越延伸,進(jìn)入這個(gè)結(jié)構(gòu)中的鏈接(link)就越混雜。喬治·魯?shù)?George Rudé)在分析群體暴動(dòng)時(shí)寫(xiě)道:“群體之所以成為暴民是以下因素的混合:饑餓和恐懼、強(qiáng)烈的社會(huì)不滿、渴望立即改革、想要摧毀一個(gè)敵人或呼喚一個(gè)英雄,等等。不可能是其中哪一個(gè)在唱獨(dú)角戲。”*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History: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1730-1848) , New York-London-Sydney: John Wiley & Sons,1964, p.217.等同鏈條是形成大眾要求的前提,也是民粹主義出現(xiàn)的基本條件之一,它總是試圖不斷地接合那些未滿足的民主要求,以實(shí)現(xiàn)自身的充分延展。
二、構(gòu)建社會(huì):等同與差異的博弈
如果說(shuō)大眾要求的構(gòu)成以多元民主要求的等同為前提,那么相互分離的民主要求則面對(duì)著這一等同化的過(guò)程。但民主要求的分離并非絕對(duì),如果一個(gè)要求沒(méi)有進(jìn)入到與其它要求的等同關(guān)系中,那是因?yàn)檫@個(gè)要求已經(jīng)被滿足了。這個(gè)已滿足的要求不再是分離的,而是被印刻在一個(gè)制度性的或差異的總體(totality)中。所以,可能有兩種“社會(huì)(the social)”構(gòu)造:一是社會(huì)中相互鏈接的特殊性之間僅僅是差異的;二是社會(huì)部分地接受特殊性的差異,但重點(diǎn)在這些等同的差異之間的共同點(diǎn)。拉克勞稱前者為差異邏輯,后者為等同邏輯。自然地,我們會(huì)認(rèn)為民粹主義之所以出現(xiàn)是因?yàn)椴町愡壿嫷南撕偷韧壿嫷难由臁_@確實(shí)對(duì)很多情況是適用的,但未免太過(guò)簡(jiǎn)單化。拉克勞認(rèn)為,民粹主義不是等同與差異的“零和博弈”*零和博弈(zero-sum game)是博弈論的一個(gè)概念,指參與博弈的雙方在嚴(yán)格競(jìng)爭(zhēng)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博弈雙方的收益和損失相加總和永遠(yuǎn)為“零”,因此雙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實(shí)際情況要復(fù)雜得多,甚至差異和等同不得不相互照應(yīng)。但這如何可能呢?
對(duì)此,拉克勞如此解釋:例如,在以福利國(guó)家為最終視域的社會(huì)中,差異邏輯被認(rèn)為是建構(gòu)社會(huì)的唯一合法路徑。在這樣一個(gè)社會(huì)中,社會(huì)要求互不相同,社會(huì)始終無(wú)法實(shí)現(xiàn)總體化。事實(shí)上,在建立這個(gè)社會(huì)時(shí)遇到的那些阻礙(如個(gè)體無(wú)止境的貪婪、不斷擴(kuò)張的利益等)會(huì)強(qiáng)迫社會(huì)的擁躉去認(rèn)同敵人,同時(shí)再引入一種建立在等同邏輯之上的社會(huì)分離話語(yǔ)。如此,聚集在保衛(wèi)國(guó)家周圍的集體主體就出現(xiàn)了。等同邏輯的情況也與此相類似。首先,等同不試圖消除差異。在零和博弈的例子中,因?yàn)橐幌盗刑厥獾纳鐣?huì)要求消解了,等同隨之建立起來(lái)。實(shí)際上,差異會(huì)繼續(xù)存在于等同之中,作為后者的基礎(chǔ)并維持它們之間的張力。法國(guó)大革命的復(fù)雜歷史就體現(xiàn)了這一張力:“控制國(guó)家的人不屈服于工人的要求,但同時(shí)也不能忽視他們的要求;而工人任何時(shí)候都無(wú)法自治到可以拋棄革命陣營(yíng)的程度。”*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0.所以,“等同和差異雖然在根本上無(wú)法一致,但它們同時(shí)作為建構(gòu)社會(huì)的前提條件,依然彼此互相需要。社會(huì)不過(guò)處在它們之間無(wú)法化約的張力的中心”*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0.。
等同與差異的博弈對(duì)民粹主義而言意味著什么呢?拉克勞認(rèn)為,一方面所有社會(huì)認(rèn)同的建構(gòu)都建立在差異與等同的相遇點(diǎn)之上,另一方面因?yàn)樯鐣?huì)的“總體化(totalization)”需要以一個(gè)差異的要素表達(dá)一個(gè)不可能的整體,所以在社會(huì)中存在著根本的不平衡。一個(gè)特定的認(rèn)同將從整個(gè)差異的領(lǐng)域中被選中,成為它總體化功能的化身。正如在民粹主義的總體化語(yǔ)境里,“人民”不是作為共同體的總體,而是作為后者的組成部分,它希望被當(dāng)作唯一合法的總體。拉克勞認(rèn)為回到“人民”的古典術(shù)語(yǔ)能使這一區(qū)別變得明朗:“people”可以是“populus(人民)”,也可以是“plebs(庶民)”。*“人民”是政治學(xué)和哲學(xué)中最難理解且意思最含糊的術(shù)語(yǔ)之一,其內(nèi)涵與外延不斷演變,通常無(wú)法確定到底“人民”是指所有國(guó)民的全體,還是指國(guó)民中的普通百姓。如在羅馬共和國(guó)前期,populus(人民)與plebs(庶民)是有區(qū)別的,populus還包括貴族。雖然絕大多數(shù)公民都是plebs,但populus往往用來(lái)指稱貴族,而不是plebs。那時(shí)的共和國(guó)實(shí)際上只是貴族以“populus”的名義運(yùn)作的政治體制。在拉克勞對(duì)這兩個(gè)詞的使用上,我們姑且接受一個(gè)不嚴(yán)謹(jǐn)?shù)膮^(qū)分:populus指向作為整體的人民,是一種虛幻的、缺席的完滿;plebs指向作為部分的人民,是真實(shí)在場(chǎng)的部分。對(duì)“人民”概念的討論,可參見(jiàn)[意]阿甘本:《什么是人民?》,《無(wú)目的的手段:政治學(xué)筆記》,趙文譯,鄭州: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法]巴迪歐:《“人民”一詞用法的24個(gè)筆記》,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2ef2b20102vopw.html;藍(lán)江:《什么是人民?抑或我們需要什么樣的人民?——當(dāng)代西方激進(jìn)哲學(xué)的人民話語(yǔ)》,《理論探討》2016年第4期;吳冠軍:《“人民”的悖論:阿甘本問(wèn)題與“群眾路線”》,《學(xué)術(shù)月刊》2014年第10期。在制度主義的總體化話語(yǔ)中,這個(gè)區(qū)別只是同質(zhì)化空間中的一種差異,“populus”和“plebs”不是一種對(duì)抗關(guān)系。但民粹主義的“人民”意味著更多:“plebs”宣稱它是唯一合法的“populus”,是一個(gè)想要作為共同體的總體來(lái)發(fā)揮作用的部分。*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2.所以,在共同體的空間里將發(fā)生“plebs”與“populus”的激進(jìn)劃界。共同體中對(duì)權(quán)力的反抗非常活躍,它需要得到大眾要求的鏈條中所有鏈接的認(rèn)同,而這一認(rèn)同的原則就是圍繞一個(gè)共同的標(biāo)準(zhǔn),把所有那些相互差異的主張具體化為一個(gè)肯定的符號(hào)表達(dá)。至此,拉克勞認(rèn)為確定民粹主義的“等同鏈條”只是第一步,民粹主義還需要因社會(huì)的內(nèi)在分野而產(chǎn)生的對(duì)抗。
三、內(nèi)在分野:對(duì)抗而非差異
內(nèi)在的對(duì)抗分野把社會(huì)劃分為兩個(gè)陣營(yíng),但如果從一個(gè)陣營(yíng)走向另一個(gè)陣營(yíng),那么面對(duì)的是差異關(guān)系,這兩個(gè)陣營(yíng)的分歧并非是真正激進(jìn)的。拉克勞認(rèn)為,分歧的激進(jìn)性意味著它在概念上不可表達(dá)。如果完全以純粹概念化的意義來(lái)重組事件發(fā)生的序列,那么必然無(wú)法形成對(duì)抗性的分歧,而且沖突將表現(xiàn)為一個(gè)完全附庸于理性過(guò)程的現(xiàn)象。“在人民表現(xiàn)對(duì)抗關(guān)系的方式與對(duì)抗關(guān)系的真正意義之間有著無(wú)法逾越的鴻溝。”*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4.這就是為什么辯證法意義上的“矛盾(contradiction)”完全無(wú)法把握處于危機(jī)關(guān)頭的社會(huì)對(duì)抗。矛盾是辯證序列的一部分,它完全能被概念地把握。如果對(duì)抗是構(gòu)成性的,那么對(duì)抗的力量就表現(xiàn)為一種外在性,而不像矛盾那樣內(nèi)在于概念的、辯證的序列中。所以對(duì)抗可以被克服,但不能被辯證地回溯。這一構(gòu)成性的對(duì)抗,抑或說(shuō)這一激進(jìn)的分野,需要一個(gè)“斷裂的(broken)”空間。為什么?拉克勞對(duì)“斷裂”的三個(gè)維度進(jìn)行分析。
斷裂的第一個(gè)也是根本的維度是“缺乏(lack)”,即在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的社會(huì)中出現(xiàn)“缺口(gap)”。從缺口出發(fā)看不到共同體的“完滿(fulness)”,而“‘人民’的建構(gòu)將試圖賦予那個(gè)缺席的完滿以一個(gè)名稱(name)”*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5.。社會(huì)秩序如果沒(méi)有這種最原初的缺口,那么就不可能會(huì)有對(duì)抗、分野以至最后有“人民”。有“缺乏”才可能有“要求”,“要求”所要求的正是缺乏的東西。
第二個(gè)維度是“凝縮作用(condensation)”。拉克勞在此借用了弗洛伊德在釋夢(mèng)時(shí)使用的概念。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duì)“夢(mèng)”的解釋里,“凝縮”指的是以簡(jiǎn)單的圖像來(lái)表達(dá)大量復(fù)雜的意義,即夢(mèng)的隱意被濃縮到一個(gè)個(gè)簡(jiǎn)單的圖像中,這些圖像都是記憶中的夢(mèng)的顯意。“研究者在比較夢(mèng)的顯意與隱意時(shí),首先會(huì)注意到,夢(mèng)中進(jìn)行了大量的凝縮工作。夢(mèng)的顯意通常簡(jiǎn)潔、貧乏、緊湊,相比之下夢(mèng)的隱意卻冗長(zhǎng)而豐富。夢(mèng)的顯意假如可以寫(xiě)在半頁(yè)紙上,對(duì)于隱意的分析就會(huì)需要6倍、8倍甚至12倍的篇幅。”*[奧]弗洛伊德:《夢(mèng)的解析》,方厚升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261頁(yè)。將“凝縮”移置到政治語(yǔ)境將意味著,劃分社會(huì)陣營(yíng)的前提是出現(xiàn)一些凝縮了整個(gè)對(duì)抗性陣營(yíng)意義的“能指(signifiers)”*“能指(signifer)”與“所指(signified)”是索緒爾語(yǔ)言學(xué)創(chuàng)造的術(shù)語(yǔ)。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認(rèn)為語(yǔ)言的要素是符號(hào)(sign),符號(hào)又分為能指與所指兩部分,能指和所指結(jié)合一起才成為一個(gè)完整的符號(hào)。大致而言,能指是符號(hào)的音象(sound-image)在人們心中造成的心理印跡,并不是指物理的音象和有形可見(jiàn)的符號(hào);所指是符號(hào)的音象所代表的意義。。對(duì)敵對(duì)力量往往會(huì)形成諸如“政權(quán)”“寡頭”“統(tǒng)治階級(jí)”等能指,對(duì)被壓迫者則會(huì)形成諸如“人民”“民族”“沉默的大多數(shù)”等能指。拉克勞認(rèn)為在這個(gè)凝縮過(guò)程中不得不區(qū)分兩方面:“一面是話語(yǔ)地構(gòu)成社會(huì)分離的‘本體論的(ontological)’角色;另一面是在特定環(huán)境中扮演這一角色的‘本體的(ontic)’內(nèi)容。”*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7.這一區(qū)分很關(guān)鍵,因?yàn)椤氨倔w的”內(nèi)容可能在某一階段耗盡了自己扮演“本體論”角色的能力,但對(duì)這一角色的需要仍然存在。鑒于“本體的”內(nèi)容和“本體論的”功能之間不確定的關(guān)系,“本體論的”功能可能被一個(gè)完全相反的政治符號(hào)能指表現(xiàn)出來(lái)。
第三個(gè)維度是在那些業(yè)已成為“大眾的”復(fù)雜要求中等同與差異的張力。等同鏈條中任何一個(gè)民主要求的印記(inscription)都是一個(gè)混雜的“詛咒(blessing)”*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8.“blessing”是拉克勞使用的反語(yǔ)。。一方面,這個(gè)印記給予這一要求以有形的存在,使其不再是一個(gè)漂浮的、暫時(shí)的存在,話語(yǔ)的、制度的集合確保它能長(zhǎng)期幸存(survival)。另一方面,“人民”有其運(yùn)動(dòng)規(guī)律,無(wú)法保證這些規(guī)律一定會(huì)犧牲那些個(gè)體民主要求中的需求。拉克勞認(rèn)為“民主要求”像刺猬一樣,分開(kāi)會(huì)感覺(jué)寒冷,靠近取暖又會(huì)傷害彼此。這個(gè)冷暖拘束發(fā)生的區(qū)域并非風(fēng)平浪靜,它開(kāi)始有它自己的要求。往往在等同與差異的接合中會(huì)發(fā)生真實(shí)、極端的可能:在統(tǒng)治系統(tǒng)里,每個(gè)個(gè)體要求被當(dāng)作差異的要求被消化吸收了,隨之而來(lái)的是它與其它要求的等同鏈條也瓦解了。“民粹主義的命運(yùn)與政治分野的命運(yùn)密切相關(guān);如果這一分野不存在了,那么作為歷史行動(dòng)者的‘人民’也解體了。”*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89.以19世紀(jì)維多利亞時(shí)代的英國(guó)為例。19世紀(jì)30年代的英國(guó)改革激起民眾的暴力反抗,憲章派的反國(guó)家話語(yǔ)顯然是激勵(lì)和融合社會(huì)抗議的理想話語(yǔ)。隨著國(guó)家政策的改變,即國(guó)家以更人道的合法途徑解決人民的醫(yī)療、住房、教育等訴求,也愈發(fā)認(rèn)識(shí)到政治權(quán)力不應(yīng)干涉市場(chǎng)力量。等同的聯(lián)系松弛下來(lái),大眾要求逐漸分解為多元的民主要求。這一轉(zhuǎn)變意味著“政治不再是兩個(gè)對(duì)抗集團(tuán)之間的事,而是愈發(fā)成為一個(gè)在更大的社會(huì)層面協(xié)商解決差異要求的問(wèn)題”*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2.。所以當(dāng)工人階級(jí)再度出現(xiàn)時(shí),他們會(huì)發(fā)現(xiàn)與直接碰撞國(guó)家相比,與國(guó)家協(xié)商談判能更有效地解決他們的具體要求。
因而,“如果等同的關(guān)系沒(méi)有具體化(crystallize)為確定的話語(yǔ)認(rèn)同,那么這種等同仍然給人以不確定的結(jié)合感。”*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3.具體化之后的話語(yǔ)認(rèn)同不是把“民主要求”表達(dá)為“等同的(equivalent)”,而是表達(dá)為“等同鏈接(equivalential link)”。所以,在拉克勞看來(lái),“具體化”是建構(gòu)民粹主義之“人民”的關(guān)鍵,其實(shí)現(xiàn)離不開(kāi)大眾認(rèn)同的建構(gòu)。
四、大眾認(rèn)同:“空洞能指”的生產(chǎn)
回到“‘plebs’作為‘populus’這一總體來(lái)表現(xiàn)自身”*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3.這一觀點(diǎn)。拉克勞認(rèn)為這一說(shuō)法蘊(yùn)涵兩層意思:一是“populus”是一個(gè)集合社會(huì)關(guān)系的虛構(gòu)總體;二是“plebs”希望創(chuàng)構(gòu)一個(gè)真正普遍的“populus”,“plebs”作為一個(gè)確定的特殊性,以一個(gè)理想化的總體“populus”來(lái)認(rèn)同自身。在這個(gè)認(rèn)同作用里,多元的等同鏈接通過(guò)圍繞大眾認(rèn)同的凝縮而成為“奇異點(diǎn)(singularity)”*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4.。凝縮過(guò)程的原材料顯然只有特殊的個(gè)體要求,如果等同鏈接要在個(gè)體要求之間建立,就必須建構(gòu)一種大眾認(rèn)同。拉克勞指出把握大眾認(rèn)同建構(gòu)的關(guān)鍵在于:
第一,大眾認(rèn)同具體成為的那個(gè)要求是內(nèi)在分離的。一方面,它仍是一個(gè)特殊的要求;另一方面,其特殊性指向一些與它自身相當(dāng)不同的東西,即指向等同要求的整個(gè)鏈條。它既是特殊的要求,又成為更普遍的能指。這一更普遍的意義必然傳導(dǎo)到鏈條的其它鏈接上,因此整個(gè)鏈條可能分離成“要求的特殊性(particularism)”與“要求在鏈條中的印刻所賦予的大眾意義(popular signification)”。這兩部分的張力表現(xiàn)為:“一個(gè)要求越虛弱無(wú)力,它就越依賴于它結(jié)構(gòu)中的大眾印刻;反之亦然,這個(gè)要求在話語(yǔ)上和法理上越自主,它就越不依賴等同接合。”*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5.這個(gè)依賴關(guān)系的斷裂將導(dǎo)致大眾陣營(yíng)的解體,就像19世紀(jì)英國(guó)的情況。
第二,大眾認(rèn)同與“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s)”*拉克勞對(duì)“空洞能指”更為詳細(xì)的討論,參見(jiàn)Ernesto Laclau, Why do Empty Signifiers Matter to Politics? ;Ernesto Laclau,Emancipation(s), London: Verso,1997, pp.36-46.的生產(chǎn)。任何大眾認(rèn)同都需要圍繞一些能指(如文字、圖像)凝縮,這些能指指向整個(gè)等同鏈條。這一鏈條越長(zhǎng),這些能指離它們最初的特殊要求就越遠(yuǎn)。也就是說(shuō),鏈條表達(dá)相對(duì)普遍性的功能將戰(zhàn)勝它表達(dá)特殊主張的功能。大眾認(rèn)同從等同鏈條的一個(gè)外延點(diǎn)開(kāi)始愈發(fā)豐富,但是它自身的內(nèi)涵愈發(fā)貧乏,因?yàn)樗鼮榱四依切缀跬耆愘|(zhì)的社會(huì)要求,不得不把那些特殊的內(nèi)容從自身中驅(qū)逐出去,“大眾認(rèn)同作為一個(gè)部分的空洞能指在起作用”*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6.。“空洞能指”指的是在意義系統(tǒng)里有一塊不可表達(dá)的構(gòu)成性空間,這是作為主體的“我”可能意指的空洞,是在意義中的“空無(wú)(void)”*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105.。好比“0”意味著沒(méi)有數(shù)字,但為了給這個(gè)數(shù)字的缺席命名,我們稱之為“0”。“0”雖然是一個(gè)數(shù)字,但它指涉的不是“數(shù)字”,而是數(shù)字的“缺席(absent)”。所以“空洞能指”自身是空洞的,它放逐了它的本意,卻包含其它可能的各種意義。拉克勞強(qiáng)調(diào),不要將“空洞(emptiness)”與“抽象(abstraction)”混為一談,即不要把大眾符號(hào)表達(dá)的共同特征當(dāng)作最終的肯定特征。在等同的關(guān)系里,這些要求不分享肯定的東西,事實(shí)上它們?nèi)紱](méi)有得到滿足。以“正義”“平等”“自由”等術(shù)語(yǔ)為例,拉克勞認(rèn)為試圖給這些術(shù)語(yǔ)以肯定的定義、賦予其概念化的內(nèi)容是徒勞的,因?yàn)樗鼈兊恼Z(yǔ)義學(xué)角色不在于表達(dá)任何肯定的內(nèi)容,而在于作為一種完滿的名稱發(fā)揮作用;但這一完滿是持續(xù)缺席的,即必須有“不正義”“不平等”“不自由”存在,“正義”“平等”“自由”才有意義。這些術(shù)語(yǔ)只是賦予一種缺失的完滿以一個(gè)“名稱”,而沒(méi)有概念性的內(nèi)容,“它不是一個(gè)抽象的術(shù)語(yǔ),而是一個(gè)空洞的術(shù)語(yǔ)”*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7.。
通過(guò)上述討論,回到民粹主義的兩個(gè)基本問(wèn)題,將會(huì)得出與以往研究不同的答案:
第一,民粹主義術(shù)語(yǔ)(更確切地說(shuō),民粹主義的符號(hào))為何是“含糊不清(imprecision)”和“曖昧不明(vagueness)”的?往往因?yàn)檫@些特點(diǎn),很多研究者并不認(rèn)為這些符號(hào)是重要的,因?yàn)槊翊庵髁x包含許多不同的政治現(xiàn)象,這些政治現(xiàn)象可能基于不同的社會(huì)基礎(chǔ)、文化背景,不可避免是含糊與曖昧的。但拉克勞認(rèn)為,民粹主義的符號(hào)表達(dá)了民主要求,它無(wú)法還原為它所表達(dá)的東西。當(dāng)然,在地區(qū)斗爭(zhēng)中可能不會(huì)出現(xiàn)這樣的問(wèn)題,因?yàn)楸藭r(shí)我們很清楚自己的要求和我們要對(duì)抗的敵人。一旦試圖通過(guò)接合其它更多的要求,以建構(gòu)更大的大眾認(rèn)同和樹(shù)立更全面的敵人,會(huì)立馬發(fā)現(xiàn)諸如此類是難以確定的。隨著“空洞能指”的生產(chǎn),符號(hào)驅(qū)逐了它自身的特殊意義。“含糊不清”和“曖昧不明”不是由于民粹主義發(fā)生的境遇不同,而更應(yīng)看作是“空洞能指”的表達(dá),隱藏在其背后的是大眾認(rèn)同的建構(gòu)。如果忽視這些民粹主義的符號(hào),將無(wú)法理解大眾認(rèn)同,民粹主義的結(jié)構(gòu)也將是不完整的。
第二,領(lǐng)袖為什么占據(jù)中心位置?最常見(jiàn)的解釋是“暗示(suggestion)”、“操縱(manipulation)”或兩者的結(jié)合,這是群體理論家曾使用的范疇并一直沿用至今。不過(guò)就算接受這些解釋,能被解釋的也只是領(lǐng)袖的主觀意向,至于為什么“操縱”可以成功,則仍然不明確。拉克勞認(rèn)為,在大眾認(rèn)同的結(jié)構(gòu)中已經(jīng)暗示了領(lǐng)袖的關(guān)鍵作用,但這一暗示難以察覺(jué)。“大眾符號(hào)(或大眾認(rèn)同)作為印刻的表面(surface of inscription),它不是消極地表現(xiàn)印刻在其中的東西,而是通過(guò)這個(gè)表現(xiàn)的過(guò)程創(chuàng)構(gòu)它所表現(xiàn)的東西。”*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99.如果大眾符號(hào)只是表現(xiàn)那些印刻其中的東西,那么無(wú)論話語(yǔ)的或霸權(quán)的結(jié)構(gòu)怎樣統(tǒng)一,它總是處在為總體命名之前。如果大眾符號(hào)通過(guò)表現(xiàn)的過(guò)程來(lái)創(chuàng)構(gòu)它所表現(xiàn)的東西,那么這種統(tǒng)一就從概念化的秩序變?yōu)椤懊x上的(nominal)”即有名無(wú)實(shí)的秩序。在這個(gè)秩序中,那些通過(guò)名稱來(lái)保持異質(zhì)要素相互等同的諸集合,成為一系列的“奇異點(diǎn)”。一個(gè)社會(huì)越無(wú)法通過(guò)內(nèi)在的差異機(jī)制保持協(xié)調(diào)一致,它就越依賴于這個(gè)“點(diǎn)”。奇異點(diǎn)的極端形式是個(gè)體形式,所以會(huì)有這樣一層推進(jìn)關(guān)系:“等同邏輯導(dǎo)致奇異點(diǎn),奇異點(diǎn)使那個(gè)統(tǒng)一團(tuán)體與領(lǐng)袖之名的認(rèn)同作用發(fā)生。”*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100.在這一意義上,領(lǐng)袖的中心位置只是一種表象,甚至可能是一種假象。這可以看作是群體對(duì)領(lǐng)袖的認(rèn)同,但按照拉克勞的思路,這其實(shí)是群體對(duì)領(lǐng)袖名稱的認(rèn)同。有克里斯瑪型領(lǐng)袖個(gè)體存在的民粹主義其實(shí)是一種極端形式,真正決定民粹主義之所以然的中心不在于領(lǐng)袖,而在于那個(gè)作為奇異點(diǎn)發(fā)揮作用的“名稱”存在。
五、結(jié)語(yǔ):作為政治邏輯的民粹主義
拉克勞認(rèn)為,理解民粹主義時(shí),“不是在理解一類有著特殊社會(huì)基礎(chǔ)和特殊意識(shí)形態(tài)導(dǎo)向的運(yùn)動(dòng),而是在理解一種政治邏輯”*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117.。他把社會(huì)邏輯當(dāng)作一個(gè)滿是規(guī)則的體系,這個(gè)體系劃出一片視域,其中一些對(duì)象是可表達(dá)的,其它則被排除在外。但政治邏輯不同:“社會(huì)邏輯遵循規(guī)則,而政治邏輯則與社會(huì)制度有關(guān)。不過(guò)這一制度不是一個(gè)任意武斷的政法秩序,而是產(chǎn)生于社會(huì)要求之外、又內(nèi)在于所有社會(huì)改變之中。這一改變發(fā)生在等同與差異的各種接合中,其中等同環(huán)節(jié)意味著構(gòu)成全面的政治主體,隨之而來(lái)的是社會(huì)要求的多元化。這一過(guò)程轉(zhuǎn)而要求建構(gòu)內(nèi)在的分野,并認(rèn)同那些業(yè)已制度化的所謂‘其他人’。”*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Verso, 2005, p.117.拉克勞始終堅(jiān)持他在1977年的看法,即“所有為‘民粹主義’確定內(nèi)容的企圖終將失敗”*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Fascism-Populism, London: NLB,1977, p.143。所以他所建構(gòu)和分析的“民粹主義”不是概念性的,而是結(jié)構(gòu)性的。“等同鏈條”“內(nèi)在分野”與“大眾認(rèn)同”三個(gè)維度,正是在上引政治邏輯的運(yùn)演中統(tǒng)一起來(lái),共同構(gòu)成一個(gè)成熟完整的“民粹主義”。所以,現(xiàn)實(shí)中這些結(jié)構(gòu)無(wú)論在何時(shí)何地結(jié)合,無(wú)論政治運(yùn)動(dòng)的意識(shí)形態(tài)或社會(huì)內(nèi)容是什么,我們總會(huì)發(fā)現(xiàn)這樣或那樣的民粹主義存在。或許正如拉克勞所言,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邏輯,只要還有政治存在,就不可能為民粹主義的命運(yùn)畫(huà)上終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