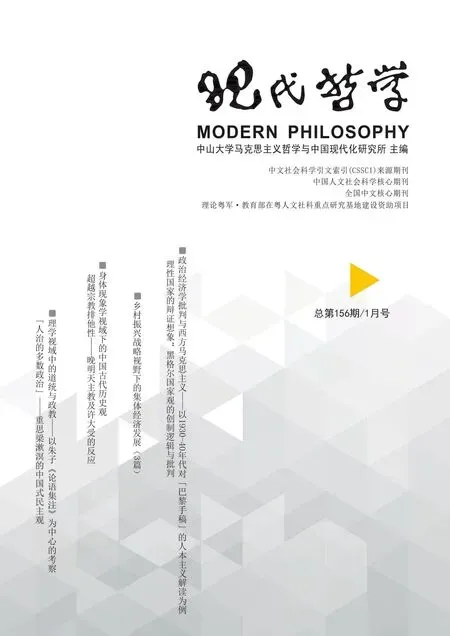理性國家的辯證想象:黑格爾國家觀的創制邏輯與批判
潘 斌
《法哲學原理》是黑格爾晚年最為重要的政治學著作,這部著作的出版及柏林大學的講學活動使得他成為普魯士王國的“官方哲學家”,書中也明確提出“哲學主要或是純粹是為國家服務”的觀點。正是在這部包含爭議而又極具思辨風格的作品中,黑格爾將思維辯證法發揮與運用到極致而精心構思與創制了獨具一格的現代國家學說。這一國家學說既奠定了黑格爾哲學作為普魯士“國家哲學”的地位,又對其否定辯證法的激進立場與革命取向劃定了邊界,更是構成了黑格爾思想體系的“頂層設計”。準確理解黑格爾國家學說的生成路徑與創制邏輯,對合理勘定現代政治中國家與社會、公民與市民、社會與個人的關系具有啟迪意義,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創新的積極嘗試。
一、絕對精神的先驗構造
對國家如何產生這個關鍵問題,黑格爾堅定地認為“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是作為顯示出來的、自知的實體性意志的倫理精神”*[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253頁。,作為倫理精神的政治國家是精神踏上外化之旅中的分裂環節,是自我意識通向絕對精神的必經階段,政治國家是絕對精神先驗構造的結果。如何理解國家?黑格爾認為國家只不過是倫理精神的世俗代表,“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這就是國家。國家的根據就是作為意志而實現自己的理性的力量”*[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59頁。。國家的政治權力顯然不是來自“君權神授”,黑格爾主張教會必須和國家分離,“教會與國家、崇拜與生活、虔誠與道德、精神活動與世俗活動決不能融合為一——這就是基督教的命運”*[德]黑格爾:《黑格爾早期神學著作》,賀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3頁。。國家作為一個公民國家不應該有任何宗教信仰,其管理者與治理者也不應該以任何宗教信徒的身份出現,宗教教育可能變成危害個人自由選擇的工具。但黑格爾也強調宗教文化對倫理生活會產生很大影響,各民族倫理精神的形成與宗教文化緊密相關,任何倫理問題的考察最終都要回歸到絕對性邏輯進路上,絕對精神與神圣意志具有相當的同一性,因此他自覺地借助神圣意志來為世俗國家進行正當性辯護。“國家是神的意志,也就是當前的、開展成為世界的現實形態和組織的地上的精神。”*[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71頁。國家是倫理精神的自我實現,但廓清倫理精神與絕對精神的關系才是問題的關鍵。
絕對精神先驗地生成了政治國家,邏輯前提在于絕對精神的“絕對性”,這一絕對性是無理由、無根據、無前提的,否則就不是真正的絕對性。相較政治國家的有限性,絕對精神的無限性使其先天地具有起源與根據的意義,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絕對精神為何構造的是政治國家,而不是構造了其他實體性對象?這與黑格爾所認知的現代社會的運行邏輯密切相關,他認為否定性辯證法不僅是自我意識發展的方法路徑,也是現代社會運行的根本邏輯。現代社會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分離與統一,即是各種力量之間如何既在對立中實現和解,又在統一中展現差別。只有這樣才既能憑借否定性力量推動社會的變化與新生,又能在和解與統一中達成共識而實現社會的凝聚與強大。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相互緊張是現代世界的主題與中心,兩者從原初統一到相互分離既是倫理精神外化的必經環節,也是各自從自在存在走向自為存在的過程。但彼此分離的結果是市民社會的利益雜多性與政治國家秉持的權力集中化構成矛盾與沖突,如不能實現和解則極易導致現代社會的崩潰與解體。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所建構的國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而是現代國家,是成熟的政治國家。必須澄清的是,黑格爾在1815年所開始辯護的制度已經不是他在1801年進行激烈批判的制度。在1805-1815年,整個德意志尤其是以黑格爾所居住與工作的巴伐利亞、普魯士、符騰堡地區受到拿破侖戰爭的劇烈震撼而不得不走向現代化改造,這些公國多少吸收了來自法蘭西的自由主義思想。*在政治立場上,黑格爾經歷了驚人的變化與往復。在普法戰爭拿破侖獲勝后,黑格爾毫不掩飾對拿破侖的美譽之詞,稱他是“巴黎偉大的憲法學家”,把“自由君主制的概念”的含義教給德國君主們。隨后不久出版的《精神現象學》也不乏對新時代的向往與溢美。但1815年滑鐵盧慘敗和拿破侖遜位給黑格爾帶來巨大震撼與政治沮喪,其政治立場隨后逐漸朝向保守主義,也不時為國王提出的憲章(“這是君王向其臣民曾經提出過的最自由的憲法”)進行辯護,但其理想的政治主張實際上是開明的君主立憲制。(參見[以]阿維納瑞:《黑格爾的現代國家理論》,朱學平、王興賽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第77—99頁。)與前現代國家相比,現代國家的人具有獨立人格與權利自由,個人利益與普遍利益并不必然發生沖突,“義務與權利是結合在同一的關系中,權利與義務相結合的那種概念是最重要規定之一,并且是國家內在力量之所在”*[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62頁。。在黑格爾看來,國家制度具有君主制、貴族制與民主制三種歷史形態,與三種形態相對應的是在國家治理中存在著“一個人、多數人或一切人”*[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88頁。。這三種形哪一種最可取?一方面,黑格爾認為品德是民主制的原則,貴族以節制為原則,榮譽是君主制的原則,“國家成長為君主立憲制乃是現代的成就,在現代世界,實體性的理念獲得了無限的形式”*[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87頁。;另一方面,他又說“我們不會提出這種無意義的問題:君主制與民主制相比,哪一種形式好些?我們只應該這樣說,一切國家制度的形式,如其不能在自身中容忍自由主觀性的原則,也不知道去適應成長著的理性,都是片面的”*[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91頁。。綜合而言,黑格爾傾向于君主立憲制,但在《法哲學原理》中又面臨著不得不為普魯士的君主專政制進行辯護的現實難題。
黑格爾對法國革命態度的變化深刻地反映了其政治立場與國家理念的變化。作為一個啟蒙主義者,他最初對法國大革命歡欣鼓舞甚至幻想也能在普魯士進行類似的運動。隨著雅各賓派上臺與羅伯斯庇爾的恐怖主義政策,黑格爾認為暴力革命的破壞性太大,其不易控制性將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因此對激進政治持謹慎態度而逐漸轉向政治保守主義,認為君主立憲制才是最成功的政治形態,可以避免流血沖突與暴力革命。正是在這種不斷變化的革命心態與立場的基礎上,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試圖構建和解的國家學來消解早年的激進政治思想:國家與市民社會、君王與市民之間的對立與沖突必須被先驗地調和,調和的理論基點就是絕對精神所據有的絕對性能緩和對立兩極之間的沖突,但調和不是簡單各自保存自己的特點而不受對方影響,而是對立兩極必須深刻地進入對方、占有對方、否定對方并最后實現自我與對象的辯證同一*在黑格爾哲學中常使用“同一性”概念而較少使用“統一性”概念,黑格爾反對抽象的“同一性”,即“A=A”模式的絕對同一,而主張“具體的同一性”,即有差別的同一,例如“a+b=c+d”。。
在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緊張關系中國家的先決性、前提性與至上性來自絕對精神,正因為絕對精神的無根據性、無前提性與普遍性才構造了市民社會是國家概念的運動結果。在客觀精神階段理念外化為倫理精神又通過國家形態得以顯現,也只有經歷這樣分裂與外化的國家才可能擺脫蒙蔽狀態而成為具有自我意識和追求主體自由的現代國家。國家就是普遍的自由精神:“自在自為的國家就是倫理精神的整體,是自由的現實化;而自由之成為現實乃是理性的絕對目的。國家是在地上的精神,這種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識地使自身成為實在,至于在自然界中,精神只是作為它的別物,作為蟄伏精神而獲得實現。只有當它現存于意識中而知道自身是實存的對象時,它才是國家。”*[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58頁。現代國家之所以優于傳統國家,是因為在現代社會里“國家是自由依據意志的概念”*[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61頁。,即國家是依據絕對精神的普遍性、絕對性與無限性行事,在國家治理的內政外交中都要依據理性精神與普遍法則行事,而依據個人的偏好、喜惡或特殊利益行事的傳統國家終要被否定與消解。君王專制的國家也不例外,王權雖然是“自我的任意的最后決斷”,但王權也必須在理性的規制與軌道中積極而妥當地運用理性,才能使得君王與市民社會之間實現有差別的內在同一。
二、理性國家的辯證想象
建構現代國家是黑格爾國家觀的核心要務,但普魯士君主制為何優越于民主制、現代國家如何與君主制相容是黑格爾要解決的理論難題,對此,黑格爾通過三重論證來為君主制進行理性辯護。
第一重是論證王權等于主權。“朕即國家”的王權思想是君主制國家的本質特征,“君主是國家中個人意志的、無根據的自我規定的環節,是任意的環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頁。,即“任意是王權”或“王權是任意”。王權自身包含三個有機構成部分: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制度,具有特定內容的特殊職能,自在自為的普遍物。這三個部分對應著普遍性、特殊性與個體性三個環節,三個環節彼此相連、各自顯現而最終落歸于個體性。黑格爾認為個體性表現為單一性,正是在單一性中才使得王權的“自我規定的最后決斷”得以呈現。王權不僅具有單一性,還能將多種差異性、雜多性融合為統一體,而國家的主權就是差異性與統一性結合而成的單一性,它既包含所有各種差別在內,又是各個環節的高度統一。主權是一切特殊權能的理想性,但它不是無法無天的任性,相反“主權正是在立憲的情況下,即在法制的統治下,構成特殊的領域和職能的理想性環節”*[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95頁。。
主權作為理想性環節是國家精神的理性顯現,“是國家的各主體的對象化的精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頁。,是作為最后決斷的自我規定而存在。但國家本身只有通過個人因素才能成為單一性的東西,“人格只是作為人才存在”,可見黑格爾想推論出有資格作為單一性人格的就是君王。他甚至直接說“在已經發展到實在合理性這個階段的國家制度中,概念的三個環節中的每一個都具有自為地現實的獨特的形式。因此,整體的這一絕對決定性的環節就不是一般的個體性,而是一個人,即君王”*[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95頁。。至此,黑格爾基本完成了王權就是主權的論證,而這一論證背后更為深厚的理論依據來自其著名的“實體即主體”觀點。實體與主體的同一性在《邏輯學》中經歷了“實體(意識)-自我意識-主體(絕對精神)”的邏輯建構,相應地在倫理精神階段,作為實體的主權與作為主體的王權也得到黑格爾的同一性辯護。
第二重是論證普遍性即是個體性。黑格爾認為國家是精神為自己所創造的世界,人們對國家的需求首先表現為國家應該是一種合理性的表現,國家權力的結構與分布體現為整個概念的構成環節。對通常所談論的包括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在內的現代國家的三種權力,黑格爾贊同立法權相當于普遍性,行政權相當于特殊性。但司法權不能代表概念的第三個環節即個體性或單一性,黑格爾認為司法權也屬于特殊性領域,應歸屬于行政權范圍之列,真正能代表單一性的是王權。
模型預測控制(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MPC)能夠有效處理非精確建模的多變量非線性動態系統,被看作是處理隨機多階優化問題的有效手段之一,從而在供應鏈管理領域中得以有效應用[1-8]。MPC可以通過一個優化函數有效跟蹤渠道的庫存水平以滿足客戶需求,該被優化目標函數可以是供應鏈績效的一個適當的測量值。在存在干擾和隨機需求下,模型預測控制可以實現供應鏈的穩定性和魯棒性。
根據“普遍性-特殊性-個體性”的邏輯理路,政治國家可以分為三種實體性的差別即三個環節中:“(一)立法權,即規定和確立普遍物的權力;(二)行政權,即使各個特殊領域和個別事件從屬于普遍物的權力;(三)王權,即作為意志最后決斷的主觀性的權力,它把被區分出來的各種權力集中于統一的個人,因而它就是整體即君主立憲制的頂峰和起點。”*[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86—287頁。立法權的普遍性與行政權的特殊性最后匯合與統一到王權的單一性中,而且王權的單一性還體現在包含著作為整體的國家所具有的三個環節,“國家制度和法律的普遍性,作為特殊對普遍的關系的咨議,作為自我規定的最后決斷的環節”*[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92頁。。國家的三個環節最后落歸于王權中,王權的三個環節落歸于“自我規定的最后決斷”,在其中“自我是最單一的東西,同時也是最普遍的東西”*[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92頁。。而既能做出自我決斷又具有普遍性的單一個體,無疑只有君王。主體性與客觀性、普遍性與特殊性、絕對性與相對性最終在君王中達到同一,君王的單一性就是絕對的普遍性。
第三重是論證義務與權利的同一。現代國家的焦點問題是在國家的普遍主義與個體的平等自由之間如何保持張力與平衡,前黑格爾哲學在這一問題上或強調二者之間沖突的絕對性而走向二元論,或強調二者的共同點與一致性而走向調和論。但黑格爾獨辟蹊徑地引入中介環節,即將各等級要素與官僚政治作為中介環節,形成一個“國家(君王)-社會(各等級要素+官僚政治)-個人(市民)”的否定之否定的結構。在這個結構中,通過中項的中介功能與橋梁作用實現了國家與個人、君王與市民的和解。“現代國家的本質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結合的,所以家庭和市民社會的利益必須集中于國家。”*[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61頁。正是在國家這里,個體權利與公共自由實現和解,市民的義務與君王的權利實現和解。
國家的目的是普遍利益,而市民社會是自私自利的戰場,無數持有特殊私利的市民彼此之間發生各種對立與沖突,那么市民與國家之間的沖突如何調節?黑格爾批判了17世紀以來古典自然法所秉承的權利本位說,即國家與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障個人所享有的各項自然權利。他從國家主義的立場出發試圖構建權利義務并重的學說:“國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終目的和個人的特殊利益的統一,即個人對國家盡多少義務,同時也就享有多少權利。”*[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61頁。與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相對,黑格爾認為個人對國家應盡的義務優先于國家給予個人的權利:“國家所要求于個人的義務,也直接就是個人的權利,因為國家無非就是自由的概念的組織。個人意志的規定通過國家達到了客觀定在,而且通過國家初次達到它的真理和現實化。國家是達到目的和福利的唯一條件。”*[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263頁。正是由國家的所代表的絕對精神客觀地賦予了個人義務,個人才在國家的背景里享受到自我的權利,因而國家是個人自由權利實現的前提與基底。然而,黑格爾嘗試提出的權利義務并重學說,顯然是試圖將個體主義的權利觀念扭轉為整體主義權利觀念,用國家的普遍性、前提性來約束與限制個體的特殊性、自主性,這里權利不過是用義務來解釋的權利,義務則充當了權利的根據與邊界。
上述三重論證中王權與君權的內在同一性是黑格爾國家觀的創制理念,普遍性經特殊性達到與個體性的同一是其國家觀的邏輯進路,義務與權利在國家框架內的辯證統一是制度保障,這三重論證構建了一個整體性、思辨性的國家學說體系。囿于歷史條件、時代境遇與社會環境的制約,黑格爾的國家觀總體而言只是對現代國家的辯證想象,但其政治理性主義的創制理念、縝密嚴謹的分析方法、否定生成的邏輯進路以及整體主義的視角可給予現代國家理論以重要啟示。
三、中介環節的邏輯演進
《法哲學原理》國家觀的創制關鍵是中項概念的運用,沒有它的中介功能,整個國家體系的總體架構將陷入嚴重的兩極對立與沖突之中直至崩潰與解體。*“中介”與“中項”這兩個概念在黑格爾著作中出現頻率最高在是《精神現象學》、《邏輯學》與《法哲學原理》,但它們基本被等同使用。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文也是同等使用這兩個概念。何謂“中項”?黑格爾做過一個磁體石的比喻:“磁體在中項里,在其無差別的點中,把自己的兩極結合起來,從而這兩極在其差別中直接就是一個東西。”*[德]黑格爾:《邏輯學》,梁志學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頁。作為中項的磁石承擔了連接南北兩極的中介功能,將原本截然對立的兩方統一為力的綜合作用。作為居間作用的中項,中介是肯定性環節之后所設定的否定性,而這一否定性又是達到否定之否定的必經之途,這是一個形式最為簡單的否定之否定過程。中介既是關系性范疇,又是實體性范疇;任何實體都可以作為中項,中項也是實體,或者說每一實體都曾經、正在或將要以中介的形式存在。在否定之否定的邏輯演進歷程中,實體即是主體而自我設定對象,對象以否定性的中介形式存在,但作為否定性環節的對象要被克服與揚棄,進而在否定之否定的環節即肯定性中達到同一性。這一兩極的對立與和解得以完成的關鍵環節正是中項,正是中項概念的建構與中介邏輯的演進才構造了黑格爾國家觀的體系與基石。
黑格爾的現代國家觀本質上是一個多重矛盾綜合的體系,其中君王與市民、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立法權與王權等諸多對立性范疇是矛盾概念的邏輯建構。任何能被公共語言表達出來的概念都具有普遍性,“君王”概念從邏輯上預設了其對立性概念的存在,即“市民”;同樣“政治國家”概念也預設了“市民社會”的存在。但對立的兩極之間如何實現同一?這就不得不借助中介環節。在君王與市民、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充當中介與橋梁作用的中項,正是“各等級要素”與“官僚政治”。
“各等級要素”是來自市民社會的代表,是從同業公會中遴選出來的代表。同業公會只是代表各個特殊行業、群體與社團的特殊利益,而各等級要素是從全體同業公會中遴選出來且代表市民社會利益的群體。“正如官僚是國家在市民社會中的代表一樣,各等級是市民社會在國家中的代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3—84頁。各等級本質上是一種中介機關,處于政府與特殊領域、特殊個人兩個方面之間,背負著復雜的政治任務,即既要忠實于所在團體與行業這一特殊群體、特殊個人的利益,又要聽從來自國家與政府的政策與方針。各等級處于極其獨特的中間地位,“由于這種中介作用,王權就不致成為孤立的極端,因而不致成為獨斷獨行的赤裸裸的暴政;另一方面,自治團體、同業公會和個人的特殊利益也不致孤立起來,個人也不致結合起來成為群眾和群氓”*[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第321頁。。無論是私人等級還是公共等級,其根本性的存在意義就是調和君王與市民、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立關系,因此市民社會選派的議員、選舉的自治團體與協會的首腦和其他相關公職人員,必須擁有獨立的財產而不受外界環境的限制,必須給予足夠的政治信任而能獨立行事。各等級的地位極其復雜,在政治上搖擺不定。對此,馬克思曾指出,從激進的立場來看“各等級是與政府相對立的人民,不過是縮小了的人民。這就是它們的對立派的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7頁。。從保守立場看,“各等級是與人民相對立的政府,不過是擴大了的政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7頁。。
“官僚政治”是黑格爾國家體系的又一重要中介,政府成員和國家官員屬于這一中間等級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一等級應該是大公無私、奉公守法、溫和敦厚,他們是國家在法制和才智方面的中流砥柱。國家的民族意志、文化教養、倫理精神首先表現在這一中間等級中。單一性的君主據有普遍性的權力,但這種原初的普遍性必須通過特殊性的環節才能外化與展開,即要通過選擇某些特定的個人擔負特定的國家職務,從不同的方面分有、踐行原本為君王所掌握的絕對國家權力。黑格爾把這些“不同的個人”稱為“公務員”,他們既不能來自貴族也不能來自貧民,而應來自有“教養的中間階層”,并且應由國家發放體面的薪俸。同樣作為中介環節,官僚政治與同業公會處于緊張的對立與協作關系中,官僚政治既要反對同業公會又離不開同業公會。對此,馬克思批判說:“同業公會是官僚政治的唯物主義,而官僚政治是同業公會的唯靈論。同業公會構成市民社會的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則是國家的同業公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8頁。官僚政治是完備的同業公會,同業公會是不完備的官僚政治。在國家整體主義取向下,同業公會面臨著不斷倒向官僚政治的危險,而官僚政治面臨著國家的普遍利益與特殊的私人目的同一化的傾向,國家利益正不斷成為一種特殊的私人目的。
為了避免君王與市民兩極之間的直接沖突與對立,市民社會派出它的委托人“各等級要素”,政治國家派出它的委托人“官僚政治”,兩個具有中介功能的被委托人進行談判協商,目的是解決各自委托人所提出的主張與訴求。一旦被委托人之間達成一致就意味著君王與市民之間取得政治和解,避免了沖突的擴大化。如果被委托人之間的協商最終失敗,則意味著對立兩極之間可能產生嚴重沖突甚至革命。可見,一個成熟、理性而強大的中間等級(“各等級要素+官僚政治”)是化解社會沖突、維護政治秩序與實現社會穩定的關鍵,積極建設與理性培育中間等級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有效手段。
四、對泛邏輯主義國家觀的現實批判
黑格爾國家觀本質上是邏輯主義的建構,或者說是《邏輯學》的方法論在政治哲學領域的現實展開與具體運用,馬克思有時稱之為泛邏輯主義、神秘主義。邏輯學是黑格爾哲學的靈魂,亦是其引以為傲的學術特色,他將邏輯學方法滲透與貫穿于整個哲學思想之內,將研究對象及其運動置于概念的邏輯發生史之中。黑格爾的邏輯學方法由三個環節構成:(1)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正題);(2)辯證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反題);(3)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合題)。不單是辯證法的運用,而是這三個環節的綜合有序的運用才構成黑格爾國家觀的創制邏輯。黑格爾用思辨的哲學語言表達了其理智但保守的政治主張,又用邏輯學的方法機智地傳達了其隱秘的激進政治意圖。理想主義的政治訴求與現實主義的政治困境間的二元對立,在黑格爾國家觀中被邏輯學的方法精巧而機智地結合在一起。在當時民主制與君王制交鋒中,黑格爾這一路徑無疑是極具創造性的理論嘗試。
國家治理與政治運行要符合基本的邏輯規范與要求,其本身也是處于特定境遇中的歷史事實,隨著環境與條件的變化國家制度與政治體制的內容與形式也將隨之變化。而這正是青年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進行清算與批判的理論任務,是馬克思在創立唯物史觀過程中所必須完成的理論飛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是馬克思專門針對黑格爾國家觀的深刻理解與批判,在這一文獻中馬克思正式與黑格爾哲學劃界和決裂,通過對黑格爾思維辯證法的顛覆,為唯物史觀的創立開啟了通道與大門。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在將哲學泛邏輯化的過程中有意地制造了三個“倒置”的錯誤,這是馬克思的黑格爾批判所要重點揭示的秘密所在。
第一個“倒置”是主詞與謂詞的倒置。命題形式的基本結構一般是“主詞+謂語動詞+謂詞”:“主詞”是主部的中心,通常由具有實體屬性的個別事物擔任,也有極少數由表示最小的類的詞充任;謂語動詞多是系動詞,充當主謂之間的連接與中介;謂詞則是對主詞的屬性、特質、功能或意義等表述,表示主詞“怎么樣”、“是如何”、“要怎樣”、“做什么”等。例如,通常說“政治信念是理想性中的必然性”,但黑格爾這里顛倒過來就變成“理想性中的必然性就是政治信念”。主謂倒置看起來只不過是一個語言游戲,但其背后是主體與主體性的有意混淆與替換。在邏輯意義上,主體是獨立存在的實體,主體性是對主體的屬性、特質與狀態的描述,因此一般意義上主體是主詞,主體性是謂詞。但在黑格爾那里,主體性被視為主詞,而主體被視為謂詞。*徐長福:《論馬克思早期哲學中的主謂詞關系問題》,《哲學研究》2016年第10期,第30頁。換言之,作為屬性與特質的觀念,本來應該作為謂詞來修飾與闡釋主詞或主體,但在黑格爾那里卻躍居為主體或主詞的地位,而主體或主詞被當作為謂詞使用。“主體性是主體的規定,人格是人的規定。黑格爾不把主體性和人格看作它們的主詞的謂詞,反而把這些謂詞變成某種獨立的東西,然后以神秘的方式把這些謂詞變成這些謂詞的主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頁。黑格爾之所以自覺地進行倒置,目的是通過邏輯學的方法來瓦解固有的本體論基礎,最終從絕對精神出發來構造包括自然、國家與社會在內的全部實體。
第二個“倒置”是邏輯與歷史的倒置。黑格爾構建國家觀之際面臨著兩難:從政治現實層面觀察,同時期法國的民主共和與英國的君主立憲明顯比普魯士的君主專制進步,但從哲學理念層面看,德意志“意識形態”又處于歐洲之巔。如何從哲學層面為落后的普魯士君主制進行理論辯護,顯然成為黑格爾國家觀不得不解決的理論難題。當歷史與邏輯發生沖突時,黑格爾站在邏輯優先的立場上,用邏輯學的方法構建政治國家。難得的是,黑格爾在論證過程中始終恪守政治理性主義原則與嚴密精巧的論證。在闡釋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時,本來市民社會產生政治國家,但因為政治國家從邏輯上就包含著作為其對立面的市民社會,二者又都是絕對精神外化的必然環節,因此國家作為“在地上行進的倫理精神”先驗地構造了市民社會。同樣,正像本來是立法權來規定與限制王權,但在邏輯上唯有王權的單一性能擔負起絕對精神的普遍性,故王權規定與制約了立法權,行政權只不過是王權的差異性環節。可以說,青年馬克思深刻地洞見到黑格爾哲學的秘密所在,即“真正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學,而是邏輯學。哲學的工作不是使思維體現在政治規定中,而是使現存的政治規定消散于抽象的空想。哲學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邏輯,而是邏輯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邏輯來論證國家,而是用國家來論證邏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頁。。換言之,青年馬克思重構了歷史與邏輯的辯證關系:既不能用邏輯來預設與構造歷史,也不能罔顧邏輯而歪曲歷史。歷史既是宏大的時間序列,是由無數歷史人物與事件編織而成,更是生產實踐的發展歷史。每一歷史都內蘊著自己獨特的發展脈絡與因果必然性,探尋其背后的歷史必然性是歷史自身的邏輯。歷史與邏輯的一致,必然回歸到既是歷史主體又是思維主體的人身上,人的自由與解放的程度才是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性所在。
第三個“倒置”是中介邏輯的倒置。黑格爾否定辯證法的激進意圖與其國家觀中保守的政治主張之間得以調和的關鍵是中介邏輯的介入。中介的本質是制造矛盾與解決矛盾。在黑格爾哲學中,令人驚訝地是幾乎沒有懸而未決的難題,解題的鑰匙正是中介的邏輯。中介是溝通對立兩極的通道,雖然本身不具有普遍性、絕對性,卻是促成對立兩端實現和解與統一的橋梁,包括“木質的鐵”、“圓的方”、“各等級要素”、“官僚政治”等都是中項實體。中項不再是橋梁或中介,而是實體對象、對立的兩極。中項不斷獲得獨立性、普遍性,從自在實體逐漸變為自為實體。中介邏輯促使黑格爾將中介實體化、主體化甚至本體化。
馬克思批判黑格爾將中項的功能過度詮釋與自覺放大,真正對立的兩極是不能互為中介的,也不需要任何中介,“它們彼此之間沒有共同之點,它們既不相互需要,也不相互補充。一個極端并不懷有對另一個極端的渴望、需要或預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0頁。。為此,馬克思用隱喻的修辭手法進行描繪:我們面前出現了一幫好斗之徒,可是他們又非常害怕彼此真打起來會打得鼻青眼腫,而準備打架的兩個對手也都想法使拳頭落在給他們勸架的第三者身上,但后來打架雙方中的一員又成了第三者,結果由于過分小心,他們始終沒有打起來。這一中介體系還采取這樣一種形式:一個人想打自己的對手,同時又不得不保護自己的對手不致挨打;由于身兼二職,他的打算全部落空了。*馬克思先后用“雅努斯的兩副面孔”、“夫妻吵架鄰居醫生調解”、“仲夏夜之夢的獅子”以及“打架者與勸架者”四個事例,形象地描繪了中介的中項功能,批評黑格爾將中介不斷實體化、主體化與本體化,認為這迫使黑格爾思辨哲學的理論前提必須不斷回撤到客觀的觀念論基礎上,辯證的方法論也淪為話語游戲。雖然黑格爾試圖克服近代哲學特別是康德哲學中存在的二元論、不可知論問題,而且用中介邏輯掩蓋同一性哲學背后的二元論問題的哲學嘗試不可謂不精致,甚至直到今天政治哲學還發生“黑格爾主義轉向”思潮。但黑格爾用泛邏輯主義的方法論不斷進行形而上學的顛倒與重置,其中介邏輯的調和式進路始終未能真正解決二元論問題。青年馬克思在“發現”黑格爾哲學的秘密之際也先后從勞動、感性活動、物質生產直至實踐活動的視角來解決主體與客體、自我與對象、存在與意識、現實與精神等的對立與統一,直到《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唯物史觀的建立才真正完成了對黑格爾哲學的清算與批判。二元論難題本身是一個開放性問題,包括黑格爾哲學在內對它的研究實際上反映著人類認識世界與自我的水平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