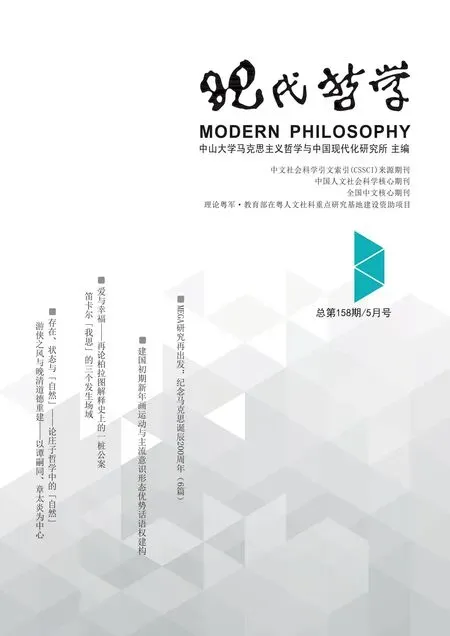論德里達對胡塞爾本質直觀問題的處理
余君芷
一
觀念之物(the ideal)在胡塞爾處有三種含義:一是指作為精神的構想和想法的觀念,如《觀念》著作群中作為標題的“觀念”;二是指“理想”,是近代自然科學理想化方法的產物;三是指“本質”、“一般對象”*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229—232頁。。作為本質的觀念之物是胡塞爾的主要研究對象,這種觀念之物具有先天的明見性以及超經驗的普遍有效性,這種普遍有效性的根基在于一般之物在經驗性的雜多中所保持的同一性。對胡塞爾來說,對作為本質的觀念之物的把握是認識的前提,所以認識如何可能、科學如何可能的問題,最終可歸結為本質如何被把握的問題。盡管胡塞爾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出進路、深度、清晰度、嚴格性等變化,但他的一個總觀點沒有改變,即作為本質的觀念之物是通過直觀來把握的*這點在《經驗與判斷》中呈現出較為復雜的情況,將在下文具體展開。。所以,德里達在《聲音與現象》中對胡塞爾的解讀是驚人的。對德里達來說,胡塞爾的文本顯示了,對于觀念對象的直接直觀把握恰恰是不可能的。觀念之物必須通過符號才能得到把握或者說構造。本文旨在說明,德里達通過對胡塞爾的文本的分析而達成這個結論,并對胡塞爾相關理論存在的根本困難有深刻理解,然而,德里達自己用以克服這個困難的方式卻是不令人滿意的。
本文第二部分展示德里達在《聲音與現象》中試圖表明,胡塞爾文本已把符號當作把握觀念之物的中介線索,但這與本質直觀理論顯然相悖。雖然《聲音與現象》并未直接討論本質直觀,但德里達對此有著深入思考。第三部分試圖表明德里達在《胡塞爾〈幾何學的起源〉引論》(以下簡稱《引論》)中對本質直觀的討論的確指出了胡塞爾的根本困難,并且認為這個困難的解決在于語言。第四部分通過把《聲音與現象》中的基本論點和胡塞爾處透露出這種傾向的文本進行比對,指出語言在觀念對象的構造或把握中的作用在德里達處被普遍化和根本化了,而胡塞爾在相關問題上闡述不充分為德里達的這種動作留下空間。德里達在《聲音與現象》和《引論》中的努力是一致的,即指出胡塞爾在把握觀念之物問題上的疑難,并試圖用自己的“延異”概念來提供一個解決方案。第五部分對延異概念作簡要闡述,指出德里達對于延異概念的論述并不足以使其成為解決問題的滿意方案。
二
在《聲音與現象》中,德里達把胡塞爾現象學論證為語音中心主義和在場形而上學,并從胡塞爾的文本中找出超越傳統形而上學范式的線索。德里達所說的在場形而上學(la métaphysique de la présence)中所包含的兩個方面,就是présent這個法語詞的兩個意思:呈現的和當下的。也就是說,在場形而上學就是一種把對象向主體當下呈現作為本原的形而上學。顯然,胡塞爾的基于意識意向性理論的含義理論,是在場形而上學的一個典型:含義的作用就是把含義所指的對象召喚到當下的意識中。那么,為什么這種在場形而上學支撐上的含義理論,乃至在場形而上學本身是成問題的呢?這是因為,符號的可能性恰恰植根于非當下的再現(représentation)中,而在場形而上學把非當下和不在場視作當下在場的變異(modification),直觀和在場的形而上學由此將會導致符號的“被抹去(effacement)”*Jacques 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 Paris : PUF, 1967, p.57.。而符號的被抹去是成問題的,是因為對符號的抹去將會掩蓋一種更為本源的關系,這種關系便是我與我的死亡之間的關系,也就是比在場本身更為本源的、在場與不在場之間的延異(différance)關系*Ibid, p.60.。這種關系本源性是如何被展示出來的呢?德里達認為,在胡塞爾文本內部所存在的一些張力恰恰表明了這點。所以,對于本源的延異的揭示,德里達并沒有另起爐灶,而是在胡塞爾的文本當中清理出諸多的重要線索。
德里達在《聲音與現象》中是如何達到這點的?具體地說,他對胡塞爾原先建立好的理論結構在三個層面(這三個層面分別是:實在話語與表象話語的區分、觀念性/含義理論、內時間意識)上進行翻轉,在翻轉的同時完成了一種重新構成(這種重新構成并不意味著建立起一個新的系統,而是用一種所謂“更本源”“更古老”的關系來超越胡塞爾乃至傳統形而上學的兩難困境),從而達成自己的解構。但是這種翻轉和構成并不是德里達憑空添加的,在胡塞爾的文本中實際上已經蘊含了翻轉的杠桿,這就是胡塞爾的一個術語:représentation(Repr?sentation)。德里達列出了語言當中所涉及的représentation的三種含義,即一般意義上的表象、作為體現(présentation/Pr?sentation)的重復與再造的再現(也就是作為體現的變異的當下化)、作為另一種表象的替代者的代表*Ibid, p.54.。我們要考察的,是觀念性/含義理論層面的翻轉。
在胡塞爾處,表達所區分于指號的地方在于表達具有含義,這種含義是在含義意向中被構造起來的,含義意向通過賦予表達以意義來激活表達。但是,“意指的本質并不在于那個賦予意義的體驗,而在于這種體驗的‘內容’,這個體驗內容是同一的、意向的統一”*[德]胡塞爾:《邏輯研究》第2卷第1部分,倪梁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406頁。。作為觀念之物的含義在無限雜多的個體表達體驗之中維持為同一的,這種同一性并非出于一種形式上的約定或規定,而是出于直觀的明見性*同上,第409頁。。并不是對個別雜多之物的直觀,而是對一般對象的直觀,因此含義的觀念同一性是種類的同一性*同上,第410頁。。“我明見到,我在重復的表象行為、判斷行為中所意指的或所能意指的是同一個東西。”*同上,第409頁。
德里達認為,這種觀念性完全依賴于重復行為的可能性,它是被重復行為構造起來的,絕對的觀念性相關于無限重復的可能性*Jacques 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 Paris : PUF, 1967, p.58.。對此,也許可以理解為:同一性總是兩個及以上的東西之間進行比較和認同才建立起來的,因此同一性總是被建構的,沒有一個事先的現成的同一性擺在那里*朱剛:《本原與延異:德里達對本原形而上學的解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7頁。。盡管胡塞爾的確把可重復性視為觀念之物的一個屬性,然而在胡塞爾處,觀念的同一性并非是無限重復的可能性的結果,而是其原因。如是,同一性的根源從胡塞爾的“一下子”觀念直觀把握偏離成了在無限個構造觀念的個別活動中的重復。
與這種偏離相應,德里達認為純粹的直觀不可能把握觀念之物。他通過對第一研究的解構試圖表明,符號不僅不可還原為對對象的直觀,而且是對對象的直觀的構成性條件,是一種把握觀念對象的必要中介。他把第一研究中的內心獨白稱為現象學的聲音,也就是不發出到實在世界、在內心中自聽自說的聲音,是一種不具有可外感知的外殼的符號。這種聲音由于還原了一切外在性而成為把握觀念對象的最佳媒介,“觀念化與聲音之間的共謀關系是永存的”,“一個觀念對象是一個其展示可以無限被重復的對象……恰恰是因為它擺脫了世界的空間性,它使我能夠不經過世界而表達的意向對象”*Jacques 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 Paris : PUF, 1967, p.84.。“現象不斷成為聲音的對象……對象的觀念性顯得取決于聲音并且在聲音之中成為絕對可支配的。”*Ibid, p.87.在德里達看來,符號和直觀是同樣本源的,它們之間的差異也是本源的,不能通過一方被還原成另一方而消解這種差異。這種差異的兩個方面之間是一種“延異”的關系,這種關系使得對觀念之物的單純直觀的把握是不可能的。
《聲音與現象》的整個解構策略的實施,在論證的嚴密性上不免遭到詬病。Claude Evans認為德里達的解讀擾亂了胡塞爾文本本身的一致性,并且歪曲了胡塞爾的理論意圖*J. Claude Evan, Strategies of Deconstruction: Derrida and the Myth of the Voice,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而錢捷看到的是德里達對黑格爾式的辯證法操之過急的運用*錢捷:《Vouloir-dire:創意還是誤讀?》,《哲學研究》1998年第2期。,并且“在胡塞爾的論證結構中占有極重要地位的有關范疇直觀的部分,在德里達的解讀中只字未提”*同上。。《聲音與現象》中德里達確實未與本質直觀理論正面交鋒,但實際上他并非對本質直觀問題毫無考慮。相反,德里達對這個問題有著非常深刻的思考,胡塞爾尤其在后期對于范疇的思考給德里達提供巨大靈感,下文對《引論》的考察將表明這點。
三
《引論》成書時間是1961年,早于《聲音與現象》。《引論》的目的與其說是把讀者引向胡塞爾的《幾何學的起源》,不如說是通過德里達自己對胡塞爾的激進解讀和思考把讀者引向現象學的邊界之處。之所以說是現象學的邊界之處,是因為在《引論》中,德里達把“超越論的歷史性”、“理念”、“目的(telos)”、“語言”等概念串聯起來,勾勒出一個使含義和本質以及超越論的現象學得以可能的源初領域。這個領域作為視域,作為背景和目的,作為一種康德式的理念,是一切意識構造的條件。然而這個領域自身的明見性是被胡塞爾簡單假定而沒有言明的*[法]德里達:《胡塞爾〈幾何學的起源〉引論》,方向紅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52頁。,而這種沒有言明不是偶然的,而是本質上不可能的,因為“理念不可能被親身給予,它不可能在明見性中得到確定,因為它只不過是明見性的可能性以及對‘看’本身的開啟而已”*同上,第153頁。。也就是說,這個領域不能作為直觀的對象,反而是直觀得以可能的條件。現象學不能以作為“原則的原則”的直觀來考察它自己的根源。
實際上,德里達在《引論》中直接討論本質直觀的文字并不多,只集中在第十章的其中一段。在這里,他比較了兩種觀念化(l’idéation),一種是構造幾何學對象的理想化(l’idéalisation),另一種是本質直觀(Wesensschau)。前者構造幾何學對象,而后者只是對于已構造好的對象的再次把握,所以前者反而比后者更為本源,它是本質直觀的條件*[法]德里達:《胡塞爾〈幾何學的起源〉引論》,前揭書,第149頁。。由于理想化也對應著康德的理念,所以這個論證就匯入到“理念是意識構造的條件,是直觀的條件”這個總論證。然而,理想化是本質直觀的源頭這點,在胡塞爾處僅對幾何學對象這種基于理想化的觀念對象是適用的,因為胡塞爾早就區分了精確的本質(數學和幾何學的對象)與不精確的本質(例如紅的本質),后者并沒有涉及精確性和理想化,但涉及描述上的嚴格性,所以對于這兩種本質的處理方法構成了數學等先天本質科學與作為本質科學的現象學的區別*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159—160頁。。只要聯系《引論》的整個理路去看待這段文本,就會發現德里達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非常深刻,因為他確實準確地指出了胡塞爾現象學中的一種根本張力,即存在論與目的論的張力。這種張力之所以會成為問題,是因為胡塞爾現象學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是徹底地存在論的,使得目的論的維度得不到支撐。
胡塞爾的現象學研究的目標在于“奠基”。無論是在學科上試圖建立一種其原則統攝其他科學的“元科學”,抑或是在意向分析中找尋一切現象的根源和基礎所在,“奠基”始終是向被奠基者的先天的可能性條件即其根源的回溯。在《邏輯研究》中,胡塞爾明確把奠基關系規定為存在上類似捆綁的關系:“如果一個α本身本質規律性地只能在一個與μ相聯結的廣泛統一之中存在,那么我們要說:‘一個α本身需要由一個μ來奠基’,或者也可以說,‘一個α本身需要由一個μ來補充’。”與此相應,用于揭示奠基關系的研究方法是還原,而還原的依據在于直觀。無論是本質還原、現象學還原還是超越論還原,在操作上實際都是存在論關系上的加減法(尤其是減法,這也是Reduktion一詞的固有意涵),操作的可行性和結果都是通過直觀來得到確定的。這是非常單純的存在論規定。
當然,胡塞爾的研究也是目的論的,這至少體現在三方面:1.用還原的方式來揭示出各存在領域在超越論主體性中的根源,最終是為了使這些領域的科學有一個穩固的根基;2.在意向分析的視野中,不僅是建立在含義意向和直觀意向上的認識論的意向活動,具有一種達到明見的充實的目的,而且整個意識生活一方面是時間意識中的前攝期待不斷被充實的過程,另一方面呈現出一種理性通過按照奠基順序從低級到高級的意識活動來實現自身的目的論運動;3.人類歷史的目的論在胡塞爾后期的研究中被主題化,并導向一種超越論的歷史學的,即歷史如何在超越論的主體性中得到構成的研究。這三個方面有根本聯系,而直觀作為首要的方法始終貫穿其中。然則直觀的局限體現在哪里?德里達指出,理念是不可直觀的。理念是沒有具體規定的一種“無定限”,卻對超越論的構成活動及構成內容提供出一種統一性,用康德的話說就是具有一種范導性的作用。這種統一性并不以可見的以及完全的方式給出,它始終是未完成的、被期待的,卻是始終以肯定的方式被預設的*同上,第152、153、156頁。。它作為目的干預著意識活動中的每一步的導向,但這個作用因子是不可直觀因此沒法給予明見的規定。這就導致直觀在動態生成的分析中的作用遠遠比不上在靜態結構分析中的作用,它能夠回答“怎么樣”的問題,卻不能回答“為什么”的問題,無論是動力上還是意義上的“為什么”。
直觀方法的這個局限也破壞著胡塞爾對把握觀念之物問題的闡述,因為他在論述本質直觀是如何發生的問題上表現出巨大的困難。早期胡塞爾把本質直觀視為一種與感性的直觀類比的“看”的體驗,普遍對象的非實在性并不妨礙它向意識的自身當下給予。到《經驗與判斷》時期,胡塞爾對于本質直觀的描述更加精微。在對象上,胡塞爾把知性對象性(“是”以及諸關系模態等范疇)和普遍對象性(諸本質,如紅的本質等)依據其不同的被構造方式作出區分;在操作上,知性對象性的構造分成被動階段和主動階段(在被動接受性的階段,對象預先被直觀給予;在主動性的階段,對象在謂詞自發性中被構造出來)*[德]胡塞爾:《經驗與判斷:邏輯譜系學研究》,鄧曉芒、張廷國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293—295頁。,而對普遍對象的本質直觀發展成基于想象的自由變更的“本質變換”。這些發展并沒有徹底解決問題,一方面被動階段和主動階段的區分被認為只是把對范疇的把握推向了意識結構的更難以闡明的深處,另一方面本質變換并不能成為本質直觀的構成性步驟,因為本質變換的可能性本身就預設了對本質的先行把握即預設了本質直觀*錢捷:《超絕發生學原理》第1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242、266頁。。錢捷把這些困難的原因歸結為胡塞爾的描述性方法與明見性原則之間的沖突*同上,第268頁。,這種沖突實際上還是由意識的目的論維度與存在論的直觀方法之間的張力所造成的。目的論維度被胡塞爾有所描述,卻是直觀的明見性所不能通達的。德里達從《胡塞爾哲學中的發生問題》開始,經過《幾何學的起源引論》到《聲音與現象》,所致力于指出和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既然純粹的直觀無法提供出對目的論和發生學的闡明,那么現象學的方法必須像本源地涉及直觀那樣本源地涉及非直觀的要素。德里達認為這個要素,就是語言。
四
前面提到,德里達認為觀念之物的把握需要一種不屬于直觀的中介也就是符號才能進行,從而反對胡塞爾所主張的直接的直觀把握。這在胡塞爾《經驗與判斷》以及《幾何學的起源》已有線索。在《經驗與判斷》中,與普遍對象不同,知性對象在接受性的直觀被給予性的基礎上還要有一個主動的把握,知性對象才能完整地被構造出來。“主動”這個術語除了指有作為我思的自我的參與之外,還指有謂詞活動即語言活動的參與:“在每一個判斷步驟中所發生的不僅是對先行的且已經接受性地被把握到的原始基底的規定和進一步規定;這個基底也不僅是以常新的方式被謂詞意指著并穿上了邏輯意義的衣裳;而且,同時還預先建構起來了一種新的對象性,即事態‘S是p’;該事態是產生于創造性的自發性中的。[…]在此成了一個新的判斷的主詞的那個對象,絕不是什么也可以在素樸的接受性中把握的到的東西,相反,這是一個全新類型的對象,一般說來,它只是在謂詞自發性的高級階段作為一種謂詞判斷作用的結果才出現。”*[德]胡塞爾:《經驗與判斷:邏輯譜系學研究》,前揭書,第279—280頁。
而在《幾何學的起源》中,語言的作用在另一個層面上表現出來。胡塞爾試圖探尋幾何學的非事實性的起源,一種基于超越論主體性的構造的先天的起源。這最終落實到一個問題:“幾何學的觀念性(正如所有科學的觀念性一樣)是如何從其最初的個人之中的涌現(在這種涌現中,它表現為在第一個發明者的心靈意識空間中的構成物)達到它的觀念客觀性的?”*[德]胡塞爾:《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433頁。隨即他回答:“這是借助于語言達到的,可以說,它是在語言中獲得其語言的軀體的。”*同上,第433頁。在幾何學對象的明見性的最初產生者的意識之中,最初被產生出來的自明之物可以以回憶的方式不斷被同一地喚起;而與他人的語言的溝通則使得這種明見性被同一地傳播到他人的意識之中。然而,“通過這樣的在一個人身上本原產生的東西向本原地再生產的另一個人的這種現實的傳遞,理念構成物的客觀性上沒有被完滿地構成”*同上,第436頁。。完滿的客觀性的構成意味著“即使在創造者及其同伴并不清醒地處于這樣的聯系中,或完全不再存活的時候,‘理念的對象’仍然持續存在”*同上,第436頁。。所以,流逝著的口頭語言并不能承擔起構成全時性的客觀性的任務,而文字使得幾何學的理念構成物被“沉淀”下來,使得對原初的明見性不斷激活成為可能,從而把理念構成物的客觀性實現出來。
要注意的是,我們很難簡單判斷胡塞爾在這兩個文本中的闡述是否與其觀念直觀理論相沖突。一方面,盡管在上述兩種情況中都有語言行為因素的參與,但是直觀行為因素在觀念對象的構造中始終是奠基性的出發點,這符合“原則的原則”對直觀首要性的規定。另一方面,在知性對象的構造中,對知性對象的相應事態的直觀并沒有把知性對象原初地給予出來*[德]胡塞爾:《經驗與判斷:邏輯譜系學研究》,前揭書,第293頁。,知性對象是在謂詞作用階段才原初地被對象化,這使得“原則的原則”在這里的適用性變成可質疑的,因為對于知性對象的相應事態的直觀并不是原初地給予著知性對象的直觀,“知性對象性[……]原始的預先被給予性方式就是它們在自我的謂詞表述舉動中的產生過程”*[德]胡塞爾:《經驗與判斷:邏輯譜系學研究》,前揭書,第293頁。。這就關系到胡塞爾未能言明的符號-含義的被給予性問題。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中明確地把符號-含義行為與直觀行為區分開來,但對于前者的明見性卻缺乏規定。《經驗與判斷》賦予謂詞行為在知性對象的構造中不同尋常的作用,然而這種作用是如何可能的,以及它與對于普遍對象的本質直觀如何真正區別開,這兩個問題仍然缺乏清晰的闡述。
《經驗與判斷》和《幾何學的起源》這兩個文本表明,德里達把符號視為把握觀念之物的必要中介的做法在胡塞爾處確有根據,但與胡塞爾原意并不完全相符。首先,在《經驗與判斷》中,謂詞僅在知性對象的構成中起必要作用,而普遍對象的構造無此需要。其次,在《幾何學的起源》中,語言文字使在個人之中產生的幾何對象的明見性超出個人之外而在人類共同體之中傳播從而實現一種客觀性,使得原來產生于個人之中的幾何學認識發展成為一門建立在交互主體性之上的、具有普遍性和全時性的科學,但是語言符號并沒有參與個人之中最初的幾何學明見性的產生。當幾何對象的明見性僅僅出現在個人之中、其客觀性還沒有實現出來時,它并不會因此成為不明見的;反之,當幾何對象的客觀性實現出來時,其明見性并不有所增長。幾何學的明見性仍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觀念明見性,這種明見性不是因為實現出客觀性而成為觀念的,而是因為是它本身就是觀念的,所以其客觀性的實現才是自明地可能的。所以在胡塞爾處,語言對觀念對象構成的作用實際上是有限制的;而在德里達的分析中,語言不僅成為構造觀念對象的必要中介,而且是意識及其活動即主體性得以可能的條件:意識主體的自身性并不是建立在自身意識也就是作為直觀的原意識上,而是建立在一種自聽自說的“自感觸”(auto-affection)的模式上*Jacques 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 Paris : PUF, 1967, pp.88-90.,即主體對自身的通達不是直接的直觀,而是需要符號(“現象學的聲音”)的中介作用。符號的作用被普遍化和根本化了。這固然與胡塞爾的原意不符,但是胡塞爾對于符號的被給予性的明見性以及符號在觀念對象的構造中的作用闡明不足,在某種程度上給這種普遍化和根本化留下空間。
五
從前面兩個部分可以看出,德里達并非對本質直觀問題避而不談,而是敏銳地觀察到胡塞爾的直觀主義在理念和符號兩個方面的局限性,并且試圖在超越直觀的范式上作出自己的努力。他試圖說明,直觀并不能獨自作為現象學乃至哲學的全部根基,作為本原的直觀需要一種非直觀的補充,才能不受他所指出的根本困難的威脅。《引論》和《聲音與現象》分別著重把理念和符號論證為直觀得以可能的條件,而理念和符號最終統一到對于“延異”(différance)的論述當中。
“延異”一詞為德里達所造,包含了“延遲”和“差異”兩重意思,是一種本源的生成運動。一方面,它以一種無法單純地還原為當下的時間性為特征。這種時間性以胡塞爾在《內時間意識現象學》中包含了滯留、原印象和前攝的當下時間意識視域模型為出發點。在胡塞爾處,原印象作為一種絕對的當下原本給予的意識,其相對于滯留和前攝的優先性是顯而易見的。德里達則強調后二者對當下的意識的構造作用。在《聲音與現象》中,滯留是一種使得當下得以顯現的蹤跡*Ibid, p.75.,而在《引論》中,滯留若沒有前攝則是不可能的*[法]德里達:《胡塞爾〈幾何學的起源〉引論》,前揭書,第151頁。,延異的時間性就蘊含在滯留、原印象和前攝之間辯證的動態關系中。另一方面,延異的運動產生差異,首先是時間性的差異(只有通過原印象與滯留之間的差別,原印象作為絕對當下,其同一性才能被建立起來*Jacques 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 Paris : PUF, 1967, pp.93-94.),然后是基于時間性差異的一系列差異,如感知與回憶的差異、直觀與符號的差異、觀念之物與實在之物的差異、超越論意識與未經超越論還原的心理意識的差異、言語與文字的差異、有限與無限的差異等。延異不僅是這些差異的共同根源,也使這些二元對立的其中一項不能以還原的方式排除另一項,所以直觀、觀念之物、超越論意識等無法是純粹的,因為其反面都對其起著辯證的生成作用*方向紅認為德里達“在《幾何學的起源》(此處應系筆誤,應該是《引論》)和《聲音與現象》都從世間性的角度對先驗性作了瓦解”,筆者不太認同這種理解。德里達試圖展示的是先驗性與世間性之間的辯證關系,即先驗性如果沒有世間性便不能建立起自身。不是先驗性被世間性所瓦解,而是為了通達延異這個根本環節,胡塞爾的那種基于當下直觀的超越論主體性雖然是必要的環節,但它必須前進到一種帶有理念和符號(未來與過去、非直觀)的“替補”的模式中。這可以從德里達在《引論》最后表達的對于現象學的態度之中看出來:“只要歷史位于現象學的可能性之后并接受現象學的合法的優先性,那么,對純粹事實性本身的重視就不再是向經驗主義和非哲學的回返。(……)惟有現象學才能通過下面這一點為存在的歷史打開含義的絕對主體性,即在經過最徹底的還原之后使超越論的絕對主體性顯現為純粹的主動-被動時間性以及活的當下的純粹的自身時間化,就是說,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顯現為交互主體性。”“超越論就是差異。超越論就是思想的純粹的、無休止的焦慮——思想通過超越事實無限性走向其意義和價值的無限性的方式不遺余力地對差異進行‘還原’,就是說,思想通過維持差異的方式對差異進行‘還原’。超越論就是思想的純粹確信——由于思想只能通過邁向無限地被保留起來的起源的方式而對業已宣示出來的目的進行期待,因此它永遠知道它總是要來的”。(參見方向紅:《生成與辯證法——德里達〈胡塞爾哲學中的生成問題〉主旨評析》,《南京社會科學》2003年第8期);[法]德里達:《胡塞爾〈幾何學的起源〉引論》,前揭書,第170—171、173頁。)。德里達把延異的運動與語言的作用等同起來,在這里語言仍是符號,卻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符號,而是一種形而上學的“非本原的本原”*朱剛:《本原與延異:德里達對本原形而上學的解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頁。,它的本質就是“原文字”(arche-écriture)。一切意識活動,包括觀念之物的構造,都脫離不了這種原文字,即語言和符號。所以,德里達并沒有試圖拆解或推翻胡塞爾的整個體系,而是作了一種“對本源的補充”(《聲音與現象》第七章標題),把延異概念嵌入到胡塞爾原本的體系的各個方面,試圖在根源處把胡塞爾所致力于作出的一切二元區分統一起來,并在生成問題上給出自己的解決方案。
這個解決方案并不能令人滿意。方向紅指出,德里達曾試圖發展出一種以有限性、必然性、本體性和先驗性為特征的辯證法,并在《胡塞爾哲學中的發生問題》一書中以一條注釋來把自己的辯證法與當時流行的思潮(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唐·迪克陶的辯證法、黑格爾的辯證法)區別開來,但是這條注釋后來也被他刪除,辯證法這個術語在隨后的著作中出現得越來越少*方向紅:《生成與辯證法——德里達〈胡塞爾哲學中的生成問題〉主旨評析》,《南京社會科學》2003年第8期。。但這并不必然如方向紅所推測的那樣導致了德里達對辯證法的放棄,只能證明德里達沒能解決把辯證法本身主題化所產生的困難,因為德里達在這以后的著作所主題化的對象都可以追溯到他對這種辯證法的思考所得。這種辯證法是他思想的根源所在,但是德里達并沒有很好地把這個根源本身確立起來。
德里達方案的另一個問題在于,他沒能運用這個辯證法在克服了胡塞爾現象學的直觀主義所引起的困難同時,為生成問題提供一個切實的回答。延異如何生成胡塞爾所指出的這些二元區分?延異的各個層面,即原文字、非當下的時間意識、交互主體性、符號和語言、空間等,是如何在生成中貫通起來的?我們僅在《聲音與現象》中,看到一種一氣呵成、過于簡潔的處理*Jacques Derrida,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 Paris : PUF, 1967, pp.95-96.。在德里達看來,延異的各個層面的統一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我們并不知道,時間意識視域中滯留、原印象、前攝的“暈圈”如何使得符號成為把握觀念之物的必要中介。也許德里達認為他只需要在根源處作出延異的補充,然后延異就會順著胡塞爾原先所分析的意識構成流入各個意識層面。然而,在通過超越論現象學這個環節通達了延異以后,對于延異的討論如何與之前的超越論現象學融貫起來,也就是說,延異回過頭來如何“重新獲得”意識構成的分析,這是需要討論卻又缺乏討論的。所以,盡管德里達的延異學說指出了解決胡塞爾生成問題的困難的可能方向,德里達卻沒有順著這個方向解決這些困難。胡塞爾在生成問題上的困難是德里達思考的出發點,并且解決這個困難是德里達最初的理論意圖,他卻沒能切實地回答這個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相當尷尬的境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