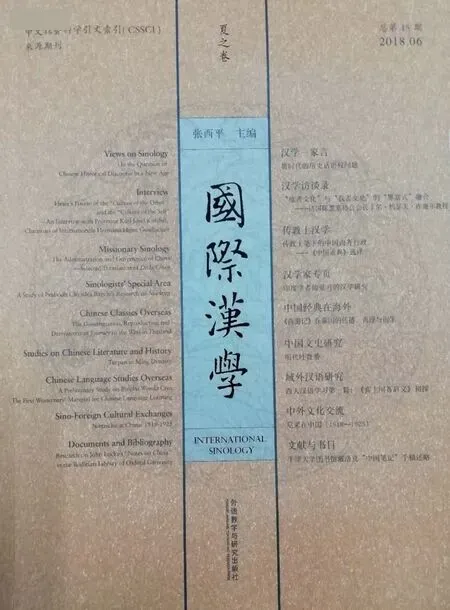尼采在中國(1918—1925)*
林振華 劉 燕 譯
譯者按:本文英文原文1971年發表于德國的《東亞自然和人類文化學協會簡報》(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lkerkunde Ostasiens, 110 [1971]: 5-47),是西方學者第一篇有關該課題的論文。本譯文是刪節版。文章以1918—1925年間中國文人、文學批評家、美學家、哲學家的著述為對象,考察了此間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及其作品在中國的翻譯、接受和傳播情況,著重分析了尼采從最初備受歡迎,到后來受到冷落的原因。認為尼采學說影響了魯迅、茅盾、李石岑等人的性格及其創作。指出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中國人就開始尋找適合行動的哲學,那些起初信仰尼采的人后來大多轉向了馬克思。作者高利克為斯洛伐克科學院研究員,著名漢學家和比較文學研究家,布拉格漢學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畢生致力于中西思想文化史、中西比較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基督教文學等領域的研究。
一
1889年罹患致命疾病不久,尼采仍然鮮為人知。當時,沒有人肯傾聽他的聲音,甚至他的著作也無人問津:由于找不到愿意編輯出版他著作的人,尼采不得不自費印行。就在他的思想行將泯滅之際,丹麥著名文學批評家、歷史學家勃蘭兌斯(Georg Brandes, 1842—1927)開始開設尼采哲學講座,并著書立說,把尼采重新介紹給德國。從那以后,尼采在文化界聲名鵲起。短短時間內,他的名聲就傳至遠東。毫無疑問,日本率先接受了尼采。岡崎義惠(1892—1982)甚至認為,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的日譯本“1882年便已于日本出版”①Okazaki Yoshie,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e Meiji Era.Tokyo: Toyo Bunko, 1955, p.6.(換言之,在尼采動筆撰寫這部名著之前)。
在中國,第一位提及尼采的名人可能是著名改革家、歐洲哲學與文學介紹者梁啟超(1873—1929)。在他看來,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與尼采代表了上世紀德國哲學的兩大主流。②M.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Marxism.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74.不過,第一位讓中國知識分子接觸尼采學說的是蜚聲內外的文學批評家、歷史學家王國維(1877—1927)。例如,他曾寫過《叔本華與尼采》,該文1905年收入《靜庵文集》。③O.Brière, 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London: Praeger, 1956, p.21.另見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北平人文書店,1936年,第364—367頁。此外,自1907年起,青年魯迅(1881—1936)的文章里也曾簡要提及尼采。④這些文章包括《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載《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179—234頁。第一位全面而科學研究尼采生平與作品的學者是哲學家、文學史家謝無量(1884—1964)。1915年,他發表了《德國大哲學者尼采之略傳及學說》。①《大中華》1915年第1卷第7—8期,第1—8、1—12頁。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已經開始對尼采感興趣,而在中國,這一情況至1919年最后幾個月及1930年最初幾個月才出現。這段時間興起的尼采熱奠定了當代中國尼采研究的基調。梁啟超是第一位試圖使中國哲學現代化的精神領袖,他把尼采與馬克思聯系起來;但比起馬克思,尼采在中國的境遇并不讓人滿意。1918年5月,《新青年》刊登了魯迅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狂人日記》。之所以在此提及該文,是因為它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現實社會對尼采產生興趣的氛圍。這一現實本身就受尼采的影響,是當時環境的產物。
尼采學說是如何推動中國進行政治、經濟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呢?它有助于道德領域的改革嗎?尼采哲學的實用影響能否以某種方式表現出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可以讓我們認清中國的未來。為什么中國人會對尼采產生興趣呢?因為中國革命者希望通過尼采達到思想與道德領域的目標。如果要我們簡要概括中國哲學家與文學家對尼采感興趣的原因,一句話便足矣,即尼采的至理名言——“重估一切價值”(Umwertung aller Werte)。“重估一切價值”是中國青年革命者雜志《新青年》的宗旨。1916年,當大總統袁世凱再也無法行使其絕對權力時,第一批反對孔子及其學說的文章開始出現。其中最杰出的反儒志士是后來的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1879—1942)和法律與政治學專家吳虞(1872—1949)。兩人的主要目的是摧毀儒家體系。他們認為,儒家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不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儒家價值需要重新評價、重新估算,儒家偶像必須破除。
總而言之,當時的中國哲學家、政治家、文學家紛紛援引各種方法或學說,其中一些人訴諸尼采也就不足為怪了。
二
第一個向“五四”運動時期中國讀者介紹尼采學說的人是沈雁冰(1896—1981),也就是后來人們熟知的茅盾。《學生時代》雜志曾連續四期刊登他的文章《尼采的學說》。他了解尼采是為了將其介紹給青年學生,同時介紹給其他讀者。
他先仔細閱讀霍夫丁(Harald H?ffding, 1843—1931)的《近代哲學家》(Modern Philosophers, 1920)和梯利(F.Thilly, 1865—1934)的《哲學史》(History of Philosophy, 1914)中有關尼采的章節。這些著作為他提供的信息重要但不夠詳細。茅盾希望寫一部更全面的著作。他很可能認為,尼采哲學應該可以適合新中國的需要。其文章(茅盾文章中最長的一篇)的主要參考資料是英國尼采哲學研究者盧多維奇(Anthony M.Ludovici, 1882—1971)1910年出版的著作《尼采生平與作品》(Nietzsche:His Life and Works, 1910)。
茅盾提到,自己翻譯尼采作品時,主要依據的是列維(Oscar Levy, 1867—1946)編譯的18卷本《尼采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1913)(他可能是第一個連續出版有關尼采著作的中國人)。在半月刊雜志《解放與改造》上,茅盾發表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第一部分第十二、十三章的譯文。②見《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6期(1919年11月15日),第61—64頁;第7期(1919年12月1日),第55—58頁。在評述尼采時,茅盾主要采納了盧多維奇原著中的觀點。盧氏的書共四章,分別為“非道德論者尼采”(Nietzsche the Amoralist)、“道德論者尼采”(Nietzsche the Moralist)、“進化論者尼采”(Nietzsche the Evolutionist)、“社會學者尼采”(Nietzsche the Sociologist)。茅盾的文章也如此劃分,只不過把原書第二、三章合而為一。
還有一件事值得我們注意:在茅盾撰寫這篇文章時(即1919年12月),《新青年》上刊登了一篇重要而有趣的文獻——《新青年雜志宣言》。《宣言》的作者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與李大釗(1888—1927);不過,文章大談實用主義,并沒有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容。當中國人開始對尼采感興趣之際,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及其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在中國正如日中天。
這份文獻獨具特色,且為中國接受西方文化營造了極其濃郁的氛圍,而這種氛圍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擺在哲學家與哲學普及者面前的是一個巨大的問題,即考察的方法。顯然,必須要考察運用歐洲與中國哲學廣闊視野,而考察的方法必須是杜威的工具法。身為最接近陳獨秀的年輕人,茅盾把《宣言》中的觀點視如己出。因此,在他眼里,尼采哲學很可能對中國人大有幫助。后文將指出,茅盾至少是本著實用主義的基本原則,從克魯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1842—1921)的無政府主義立場出發來評述尼采的。另外,筆者還認為,尼采的著作中,茅盾僅僅讀過《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茅盾選用盧多維奇的著作是出于這樣幾個原因:盧氏書中有許多內容涉及當時中國所關注的道德問題。此外,自嚴復以來進化問題就一直吸引著中國知識分子,而當時社會問題也是重中之重。
在向讀者介紹自己研究主題的《引言》中,茅盾寫道,從尼采著作那里獲得“最大的,也是最好的”見識,就是“重估一切價值”的假設。①茅盾:《尼采的學說》,《學生雜志》第7卷第1—4號,分別在1—12、13—24、25—34、35—48頁。此處引自第2頁。讀過梯利的《哲學史》后,他認為尼采是實用主義開路先鋒;在談到實用主義原則時,他指出研究尼采著作必須注意哪些是“極有用,極受益的”②同上。。茅盾希望能創造與基督教截然相反的新道德學說以及出色的超人思想。除了同意《宣言》作者的觀點外,他認為古人的話不必當作“天經地義”,人人都可以懷疑、批評這些思想。③同上,第3頁。因此,茅盾與盧多維奇不同,是以批判的眼光考察古人思想。
接下來探討尼采道德論的一章倒是有些意思。茅盾肯定地指出,尼采道德論是“極有革命性的”④同上,第13頁。。在這一章里,茅盾開篇就發表了自己對尼采道德論的見解,這不知不覺地反映出他如何理解尼采,尤其是如何誤解尼采的。由于這一部分展現了他的哲學方法(這種方法在他的文章中以各種形式不斷重復),我們有必要大段引用。
他(尼采)認為人生是競爭的,是向上的;他對于現社會的組織,道德,即至于“人”,都不滿足,他有他心目中的“超人”,為欲達到這個“超人”的目的,就犧牲了現代一切愚的弱的,都不要緊……我們要明白,人類固是求進步,但進步不一定從競爭——強吞弱——得來;愚的弱的,社會的齷齪面孔,固是進步的一個大障礙,固是消減“美”和“善”的,但不一定去了弱的愚的就可以達到“善”和“美”——超人。⑤同上。
這段引文至關重要,因為它提供了茅盾思考、理解尼采的線索。不難看出,在茅盾看來,錯誤并非在于沒有重估一切價值的道德理想,而只是達到這一理想的手段不正確。我們必須清楚,茅盾其實沒有理解尼采的“超人”。不過,當時也沒有哪個人能完全理解尼采。尼采的超人思想已經超出了當時普遍意識所理解和反映的內容。尼采的“超人”不能按照達爾文主義來解釋。考夫曼(Walter A.Kaufmann, 1821—1980)把德語“übermensch”創造性地翻譯為“overman”。如今所使用的“超人”術語其實容易產生歧義。⑥Walter Arnold Kaufmann,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Cleveland and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6, p.266.尼采著作的很多研究者及普及者都對尼采的哲學方法和象征主義感到震驚,并誤入歧途。這個現象在尼采生前便已出現,因而在《看哪!這人》(Ecco Homo, 1908)里,他提到了那些用社會達爾文主義附會其“超人”意思的“博學的公牛”⑦F.Nietzsche, Antichrist.Leipzig: Kr?ner, 1930, p.338.(scholarly oxen)。但這一解說在中國卻找到了得天獨厚的土壤:美國實用主義與歐洲馬克思主義到來以前,沒有哪種哲學像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樣對中國產生天翻地覆的影響。
上述引文中包含了“進步”一詞,但這個詞屬于茅盾,不屬于尼采。這段文字有理有據,義正辭嚴,讓讀者不禁以為尼采也相信茅盾所說的或者之前進化論所謂的“進步”。然而,尼采其實并不相信達爾文主義或社會達爾文主義定義的“進步”。同樣,茅盾也懷疑社會達爾文主義所謂的“進步”。⑧《尼采的學說》,第30頁。
在闡釋尼采學說的過程中,茅盾極為關注“主者道德”(master morality)與“奴者道德”(slave morality)的思想。①同上,第20—23頁。身為堅定不移的民主人士,他痛斥這一源自盧多維奇②A.M.Ludovici, Nietzsche: His Life and Works.London: Constable, 1910, pp.42-46.和(部分)霍夫丁的思想③H.H?ffding, Modern Philosophers.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15, pp.183-186.。“主者道德”在創造的、積極的、著名的、偉大的一切中展現自己,而“奴者道德”則指保守的、消極的、黑暗的一切,只能順應、應用環境。不過,相對而言,尼采的這兩個概念在他的著作中并不是很重要。④Kaufmann, op.cit., p.256.事實上,“主者道德”并不符合尼采自己的道德。盧多維奇十分在意“幻象”(illusion),他把尼采哲學的根基建立在某個微不足道的問題上。茅盾亦然。
茅盾察覺到尼采道德學說的最大價值,但他未能理解尼采道德論的主要內容,而且還誤以為這一學說注定適合被統治的大眾與統治階級。其實,尼采的道德論同他整個哲學一樣,只適用于極少數能懂得他的心思、能成為“超人”的人——這里的“超人”當然是尼采所理解的“超人”。
茅盾認為,尼采道德論的本意是創造“超人”。⑤《尼采的學說》,23頁。這個判斷顯然正確。不過,茅盾對“超人”的理解稍有偏差,這主要是因為他受英國達爾文主義的影響。這一影響在此清楚地表現出來,只是有些自相矛盾(從社會角度看,茅盾的思想并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當談到“超人”時,盧多維奇注意到達爾文主義思想與尼采主義的前提,因此希望強調尼采思想的優越之處。他批評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基本觀點,即“生命是活動”,或“內部關系不斷適應外部關系”;按照斯賓塞的觀點,“活動”意味著“為生存而斗爭”⑥Ludovici, op.cit., pp.64, 66-67.。盧氏說道:“生命的主旋律不是匱乏或節約的狀態;相反,生命的狀態是富饒、繁茂甚至是不可思議的浪費——哪里有斗爭,哪里就為權力而戰。”⑦Ibid., p.67.這里,尼采的影子清晰可見。當然,這與達爾文主義者的主張大相徑庭。不過,尼采走得更遠。在尼采看來,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意思根本就不是它通常暗含的那樣,也不是成長、生命和繁殖。尼采認為,生物已經準備好為生命與生存去冒險。⑧Kaufmann, op.cit., pp.213-214.然而,盧多維奇卻對此沉默不語,因為這不符合他對尼采的印象。
《看哪!這人》于尼采逝世八年后問世,尼采在書中提醒讀者盡量正確地理解他。⑨Ibid., p.215.在《權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 1901)中,他寫道自己只是希望發人深思。他強調“權力意志”是他確切表達本意的前提,可德國人只知道“權力”一詞的一種意思。⑩Ibid.盧多維奇完全沒有抓住“權力意志”的意義。茅盾顯然也沒有抓住。兩者的差別僅僅在于茅盾批評了尼采。他把“權力意志”理解為力量(force)、強權(authority)的代名詞(metamorphosis)。?《尼采的學說》,第29頁。在茅盾評述尼采的時代,“強權”一詞十分流行。
另外,茅盾認為,尼采的進化論思想讓人誤入歧途。他同樣批評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事實上,茅盾并不贊同生命只是遵循“為生存而斗爭”的原則,他相信人類文明還沒有臻于至善,無政府的社會還未到來(1919—1920年間,這正是他的理想)。茅盾堅信人類未來的出路在于相互幫助,而不是相互競爭,或者成為“超人”。這無疑使他不愿同情尼采。他無法認同超人思想,特別是因為它處處追求權力意志至上。達爾文主義害怕“超人”,相比盧多維奇,茅盾受此影響更大。
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尼采這樣問道(根據盧多維奇的譯文):“人如何被超越?”(How is man surpassed?)茅盾很可能沒有理解尼采的本意,而且他從未想到,自己的譯文與尼采的原文大相徑庭。①茅盾的譯文是:“人怎樣跨過前人?”——譯者注唯有在達爾文主義的潛移默化之下,才會產生這種歪曲尼采本意的譯文。②Ludovici, op.cit., p.71;《尼采的學說》,第32頁。
那么,茅盾是否屬于尼采鄙夷不屑的“博學的公牛”?很難這么說!既便如此,茅盾也毫不知情,不由自主。他以為超人比常人強,可從未提到常人之于超人,有如猴子之于人類。在茅盾看來,重估一切價值可以創造超人,③同上。這是多么引人入勝的想法——可他從未仔細說明。他跟盧多維奇一樣,也意識到“通過積累并提升自己的力量和安排(arrangements)”④Ludovici, op.cit., p.73.,人類可以做許多事情。然而,超人的概念仍然模糊不清,盧氏和茅盾都沒能準確說明他們如何理解尼采的這一術語。
盧多維奇把德語詞“überwinden”英譯為“to surpass”(超越),⑤Ibid., p.71.考夫曼與霍林戴爾(R.J.Hollingdale, 1930—2001)選擇了該詞的同義語“to overcome”(征服)。相比之下,后者更符合尼采的原意。正如我們所見,茅盾把這個英文詞正確翻譯為“超越”,但他牽強的解釋從根本上改變了原文。在尼采那里,“überwinden”具有道德意義,且經常如此。征服原則是尼采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牽涉到尼采哲學的主要前提,是其決定性條件。因此,權力意志的本意是征服,而不是超越自身。自我征服是道德律令的精髓所在。
在“重估一切價值”中,茅盾清楚看到尼采主義的真正要義,可他沒能進一步探索這一思想。⑥《尼采的學說》,32頁。他在其中找到了可能獲得真理的方法。⑦同上。這一次同樣點到為止,未加論述。
在《尼采的學說》最后一章,茅盾把尼采視為社會學者。比起進化論,尼采哲學的社會學方面更令茅盾感興趣。這里,他比盧多維奇走得遠,對尼采的反對態度也更明顯。
盧多維奇并不清楚如何呈現社會學角度的尼采。他認為,“社會學者”這個詞不適合表達尼采觀點的獨特之處。盡管盧氏沒有具體論述,但他知道,尼采不太關注社會學問題。茅盾從一開始就遵循盧多維奇的說法。對他而言,把尼采同“社會學者”聯系起來并無不妥。茅盾認為,尼采的道德論和進化觀點與其社會學說截然相反。在前兩個學科上,他至少還多少同情尼采,可在社會學上,他就當仁不讓了。之前,茅盾大加贊賞尼采破壞偶像的努力;但最后,他批評尼采思想保守,稱其為“人類中的惡魔”⑧同上,第35頁。。
茅盾反對尼采的社會學說出于四個原因:“(一)誤認于思想法則上可通的,也可應用于物質;(二)誤以為歷史上的因果,就是將來的因果;(三)崇拜向上太甚,誤認人性是惡;(四)誤認一切惡都是天生成,不是社會造成。”⑨同上,第36頁。
從后兩個批評意見看,我們能發現無政府主義對茅盾的影響有多大。茅盾認為,尼采社會學始于向上的擴張。⑩同上。這就是為何尼采反對平等原則。茅盾強調,尼采深感社會上大凡舉足輕重的人物都是品行兼優的個體,他們在進化之路上成功引導人類的前進。這些天才可以獲得各種機會達到沒有打擾、沒有阻攔的進化。不該為大多數人的緣故而壓抑他們。這些想法其實是他讀到盧多維奇類似觀點時形成的。?同上。另見Ludovici, op.cit., p.78.
茅盾只是從字面上理解尼采的哲學。尼采也好,其他哲學家也好,他都一視同仁;可他沒有意識到,尼采經常顧左右而言他。
在茅盾更深入研究尼采之前,他對尼采有何看法,我們不得而知。可如果茅盾從尼采那里看到“行動的工具”(這很有可能),那么他就大錯特錯了。一般來說,尼采哲學并不適用于大眾。這絕不是因為尼采哲學提倡貴族統治,不講民主或反社會,而是因為尼采本意是要教育那些能征服自己、精益求精的人。尼采把自己置于反對民主、反對社會主義的立場上,是由于他深深體會到,宣揚平等的思想會阻礙杰出人士的崛起與成長,而這些人乃人類的唯一希望。尼采關心的不是政治影響,而是道德影響。
茅盾指出,尼采的社會學觀點根本不該出現在民主當中。①《尼采的學說》,第40頁。對于尼采的著作,茅盾和其他中國民眾印象最深的是“重估一切價值”。盧多維奇在其書中的最后一章末尾引用了尼采《反基督》(The Antichrist,1888)的段落。不過,他未加評論,只是說它們再現了“他(尼采)重估我們當今價值所依據的道德法則”②Ludovici, op.cit., p.86.。
在文章的結尾部分,茅盾仍然認為尼采是偉大的哲學家。然而他也指出,尼采身上有危險的東西。尼采跟其他思想家一樣,在自己的哲學中探索有助于達到兩個目標的手段:改變社會生命、探尋真理。當茅盾認為這并非最佳手段時,他就不再關注尼采了。
三
1920年8月,《民鐸雜志》第二卷第一期出版了,這是尼采生平與作品專號。雜志主編、哲學家李石岑(1892—1934)撰寫了最重要的一篇論文《尼采思想之批判》。這是所有研究尼采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同時也是當今尼采研究的基石。
茅盾與李石岑的主要區別在于,后者并不想單純地介紹尼采。李石岑是哲學家,他的目的不是讓讀者熟知尼采,而是要向他們解釋尼采。不過同茅盾一樣,他也不希望宣傳尼采。另外,李石岑不但深諳日本研究尼采的材料,而且熟悉歐洲的相關研究著作。
在《我的生命態度的自白》③《李石岑講演集》,上海:上海書店,1926年,第1—23頁。該文寫于1924年新年之際。中,李石岑寫道,自己(時年33歲)全身心投入到某些著作的研究當中。25歲時(約1917或1918年),他對尼采的學說產生了興趣,認為這一學說是“絕大的暗示”④同上,第19頁。,十分契合自己的性情。尼采深深影響了他,而尼采的學說也成為李石岑生命觀的一部分。在中國哲學家和作家當中,李石岑無疑是特立獨行的一位。他的生活方式很像尼采。
《尼采思想之批判》開篇就指出,中國人甚至在自己還不了解尼采哲學時,就憎恨他,謾罵他,這對他無疑是不公正的。尼采成功攪動了中國人遲鈍而冷漠的神經。
從我們的角度看,李石岑對“權力意志”的闡釋很是有趣。他把這一表述一分為二。第一部分是意志(will),表達了一種源自內部、具有理性與精神色彩的力量。第二部分是力量(strength),具有爭斗和征服的特點。
李石岑有關權力意志的論述確實有道理。可我們應該注意,他忽視了尼采哲學的超越主題。事實上,權力意志是一種根本力量,可以用最多樣的方式展現自己,從自身當中創造出一切存在物。然而,我們必須特別強調,權力意志是一種努力。這種意志不單單適用于人類,還適用于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所有現象。權力意志具有二元效果(dualistically effective),⑤同上,第206頁。它是征服的力量,也是被征服的力量(überwunden),很像黑格爾(G.W.F.Hegel, 1770-1831)的絕對觀念。
當李石岑談到尼采與達爾文的關系時,我們發現他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比盧多維奇和茅盾要深入。他指出,對自然與人的理解,達爾文同尼采有著巨大差別。在尼采看來,“為生存而斗爭”或“自然選擇”并不重要,他只關注存在物的要義——內在創造力。達爾文過于強調外在部分。正是在“適者生存”的條件下,獲勝者往往最缺乏內在創造力。李石岑認為,尼采對物種進化并不感興趣,他的興趣所在是自我(ego)、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⑥李石岑:《尼采思想之批判》,載《民鐸》1920年第2卷第1期,第8—9頁。但李石岑并未指明尼采所說的哪類人具有資格,因為并非每個人都有能力做到自我實現。
李石岑清楚地指出,不應該從生物的角度理解或解釋“超人”,而人也不是動物與超人之間的過渡。“超人”是一種象征,是人類進化的象征,是人類希望的象征。這些都是李石岑的見解。①同上,第11頁。不過,他很少向讀者描述超人的具體形象。超人概念的這種模糊性正是中國人未能理解尼采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難理解李石岑對重估宗教、道德、哲學與藝術領域的一切價值倍感興趣。重估這些價值是因為它們妨礙討論與交流。同尼采一樣,李石岑也把這一過程看作虛無主義原則的運用。尼采認為,出現虛無主義只是舊價值不斷衰敗的漫長過程。在此過程中,一切都會貶值。②同上,第16頁。另見F.Nietzsche, Der Wille zur Macht.Leipzig: Kr?ner, 1930, p.10.因此,成為虛無主義者并不是可恥之事。
李石岑是時代的弄潮兒,在這篇文章中,他花了很多精力研究與“本能”這個矛盾的術語有關的問題,從本能論角度研究現實和與之相關的價值論問題。他把價值闡釋的問題同群體本能(herd instinct)聯系起來。群體本能是民眾最高級的模式。如果個體受壓迫,那么對人類的尊重(the honour to the mankind)就會表現出來。
然而,李石岑不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群體本能有其缺點。人不一定依賴群體本能,但一定會依賴自己。我們必須肯定“自我”,肯定靠自己征服并創造一切的人。③《尼采思想之批判》,第18頁。問題在于,李石岑所謂的“征服”(domination)到底有何意義?他的本意很可能是“surpass”,而不是“overcome”。靠力量和創造(自我作為原動力)去降服,此乃最高價值。盡管李石岑并沒有明確說明,但該意思正源自他的整個思想。這一認識也成為如今中國人描述尼采個人主義的來源。
李石岑認為,尼采與哲學的關系問題也應該從這種個人主義出發。《尼采思想之批判》中與此有關的段落可能是最有趣的部分,當然也是受時代精神影響最深的部分。他寫道,尼采把藝術看得比知識或道德都重要。在尼采的(其實是李石岑的)眼中,一方面道德、知識與生命之間存在巨大差別,另一方面藝術與生命也存在巨大差別。知識與道德對生命的影響姍姍來遲,可藝術卻使生命變得更有活力。知識與道德會僵化生命,它們一旦越過清醒的界限就會發揮毒藥般的威力。藝術則不然,它只會帶來活力,發揮積極的作用。因此,藝術是救命的燈塔,保護人類免受科學與道德的毒害。④同上,第22頁。李石岑甚至沒有說明,這些觀點源自何處。
留日期間,李石岑熟讀了和辻哲郎(1889—1960)的著作。和辻哲郎是當時有名的文學團體“白樺派”的成員,曾寫過《尼采論》(On Nietzsche)。“白樺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著作常被譯成中文的武者小路實篤(Mushano Koji Saneatsu,1885—1976)。他堅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已知還是欲知的)都是完善自己性格的方式。此外,他還注意擴展自我的界限,也即李石岑所謂的“自我擴張”。
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首先提出“生命即表現”,然后把藝術解釋為自我表現(盡管他并未使用這一術語)。李石岑則使用了該術語,而且從一開始,他最大的興趣就是“自我表現是藝術創造本質”的問題,其次才是生命。不過,結果殊途同歸,兩個結論一致。實現生命或許是自我表現的基礎。我們必須培養對家庭的愛,理智而勤奮地創造,“在自身周圍創造呼應內在世界的外在世界”,這便是卡朋特和李石岑所謂的“生命的充實”⑤李石岑:《藝術論》,載《李石岑講演集》,第108—109頁。另見E.Carpenter, Angel’s Wings.Oxford: George Allen &Unwin, 1913, p.214.。
對兩者而言,生命即藝術。尼采也持這種觀點嗎?其實,李石岑認為,美感源自享受美食與性快感的時刻,這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尼采的觀點。生產(procreation)與創造歸根結底是一樣的。⑥考夫曼對尼采的觀點有另一種理解:“生產不一定是空洞故事的乏味繼續,增加沒有用的東西也可以成為創造。”(269頁)。引自《尼采思想之批判》,第25頁。沒有活動的自由,就沒有美感。李石岑強烈反對唯美主義和“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因為他不相信離開生命,藝術仍將存在。①《尼采思想之批判》,第27頁。
從我們上述分析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李石岑希望解釋尼采,而在演講《尼采思想與吾人之生活》②李石岑:《尼采思想與吾人之生活》,載《李石岑講演集》,第136—143頁。里,他同樣希望宣揚尼采。演講一開始寫道:“我們的生命非常凄慘,我們的幸福非常貧瘠。記住我們的生命中所經歷的一切足矣……今年如此,明年如此,后年亦如此。為何個體生命如此蒼白,國家生命如此單調?原因何在?因為我們缺乏創造精神,我們根本沒想過改變自己的生活。如果我們想改變這一局面,就必須找到一種符合這一改變的學說,并潛心研究。”③同上,第137頁。
在李石岑看來,這就是尼采的學說。他將其視為有助于改變中國命運的最有力的意識形態武器。④同上,第128頁。
我們不妨做一番有趣的比較,看看茅盾與李石岑是如何出于功利主義的態度運用尼采學說的。
茅盾系統研究尼采之前,僅僅將其學說視為行動的工具,而李石岑在1928年赴歐旅行之前一直信仰尼采。⑤Brière, op.cit., p.22.此后,他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早在1917年,李石岑就對尼采產生了興趣,這種熱情一直持續了十年。值得注意的是,一開始他并不是出于功利主義考慮而研究尼采的,這種情況只是1923年以后才出現。
在這個演講中,李石岑以相當實用的方式闡釋尼采學說。他把權力意志解釋為人類的“潛藏力量”,不斷更新的“生命力”,是依賴自身、無窮無盡的力量。⑥《尼采思想與吾人之生活》,第138頁。唯有獲得這種力量,人類的能力才會提高。如果說《尼采思想之批判》中,李石岑沒有徹底回答“征服”與“創造”的含義,那么在這篇演講中,他已相當明確地給出了答案。李石岑認為,權力意志的活動可以用于兩個方面:征服環境和創造環境。⑦同上,第138—139頁。人受環境的擺布,因此,生命凄慘而蒼白。如果要使情況改觀,我們就必須影響環境,調整環境。⑧同上,第139頁。但同茅盾一樣,李石岑沒有注意到尼采并非社會哲學家;當尼采談論創造時,想到的根本就不是環境,而是如何創造新的價值,尤其道德與審美價值。
李石岑是“溫柔的尼采主義者”: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把尼采理想化,視其為預言未來光明的先知和人類個人主義的倡導者。在他看來,尼采是美化的范式(a paradigm of perfection),尼采的一生是未來充實生命的典范,是“生命完滿”的真正代表。
同日本白樺派一樣,李石岑也很少關注社會。在其哲學著作中,他經常使用“個人”“人類”“宇宙”等字眼,卻鮮用“社會”一詞。在這篇演講中,他也談到了能體現社會的“氛圍”(milieu)、“環境”,他的“征服”或“創造”設想只是宣言式的,缺乏具體操作。他的哲學知識對研究者而言極為有趣,對20世紀早期的讀者甚至極富吸引力。然而,沒有具體的實施計劃,環境是不可能按照個人愿望改變的。事實證明,作為社會計劃,自我表現、自我擴張、自我實現與自我創造都不盡如人意。不首先改造個體就不可能改造社會,但僅僅改造個體還不足以保證或推行社會改造。
在這篇面向大學生的演講中,李石岑談的內容不多。其中大部分已經在他的第一篇文章里提及。他沒有進一步展開他的社會改造思想,也沒有具體說明“超人”的意義。他坦言,超人是“距離之殤”⑨同上。,這就好像20世紀的人回望15世紀的人,或者文明人回望野蠻人,只是超人內心的這種情感更加強烈。這個看法令人困惑。不過,如果我們簡要梳理李石岑最初賦予超人的特點,理解起來就容易得多。這里,他也提到了“距離之殤”。尼采認為,現代歐洲人的價值遠小于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人。①《尼采思想之批判》,第10—11頁。據此他希望表明,人類并不像達爾文主義者所說的那樣,“能代表更好、更高、更強的發展趨勢”。他的言外之意是,超人在任何時代都有可能出現。超人(superman or overman)將“不再是動物,而是真正的人”,是最杰出的個體:哲學家、藝術家、圣徒以及道德高尚且富有創造力的人。②Kaufmann, op.cit., p.270.
當我們再次面對超人時,有一點必須指出,尼采的超人理論與永恒輪回(die ewige Wiederkehr)思想息息相關,后者也代表了其哲學的頂峰。
在李石岑看來,永恒輪回“掏空了超人的意義”③《尼采思想之批判》,第26—27頁。。一旦超人只對當下世界和現實世界感興趣,那么他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就像戰爭一樣,摧枯拉朽,尋求進步,自始至終都懷著抵抗精神。如此一來,永恒輪回的觀念就變得多余了。如果超人的行動與此前并無二致,那么他將失去作用。一旦權力意志是為了征服和創造,而宇宙戰爭也受制于它,那么永恒輪回就不可能存在。
李石岑的思路很清晰,但前提錯了。尼采的超人并非李石岑所想象的那樣,而是已經克服動物本性、控制內心激情、創造自己性格的人:超人是審美與道德上完美無暇的人。在尼采看來,權力意志并非統治的力量,而是征服自身的力量;如果它征服了自己,也就被征服了(überwunden)。
對于李石岑以及相信不斷進步的進化論者而言,對尼采的永恒輪回的思想難以接受,因為尼采并不相信所謂的不斷進步。他認為,永恒輪回的觀念可以以“最科學的”方式解釋過去或現在存在的現象或事物將來是否會存在。④同上,第282頁。尼采的前提是,如果有限宇宙與有限能量存在于無限時間當中,那么這種能量的結構(configurations)數量只可能是有限的。
盡管中國歷史學界沒有把李石岑列為中國20世紀杰出哲學家,但事實不容置疑。布里埃爾(O.Brière)就把李石岑視為當時獨領風騷的思想家。⑤Brière, op.cit., p.21.
尼采的觀點是李石岑個體哲學準則(individual philosophical discipline)思想的核心。要想進一步考察,還需從更多角度出發。
四
除了李石岑外,《民鐸》雜志尼采專號中還有兩位作者的文章值得我們特別關注。一篇是筆名S.T.W.的《尼采學說之真價》,一篇是筆名白山的《尼采傳》。
我們很難考證S.T.W.到底是哪位中國哲學家的筆名,難道是李石岑的朋友吳致覺(1888—1956)?⑥《李石岑論文集·第一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第136頁。S.T.W.的尼采觀與李石岑的又有所不同。雖然兩人都信仰進化論,但S.T.W.更強調達爾文的學說,更接近本能論。
S.T.W.指出,尼采的超人與永恒輪回觀念受達爾文《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 1859)的影響。⑦S.T.W.:《尼采學說之真價》,載《民鐸》1920年第2卷第1期,第2頁。此外,他還認為尼采甚至承認達爾文的進化理論。S.T.W.對超人的理解純粹從生物學角度出發,認為權力意志會孕育“超越人類”的超人。然而,S.T.W.并未把尼采看作達爾文思想的簡單復述者。他指出,尼采不同意達爾文對“為生存而斗爭”的解釋。他批評進化論者(斯賓塞)把生命等同于“內在關系對外在關系的順應”。尼采認為(S.T.W.如此解釋),這種順應的表現方式截然相反,生命有機體中的權力意志攻擊外部環境,由此而發展和變化。
接著我們看到,S.T.W.把尼采視為積極的個人主義者,宗教、哲學、科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偶像破壞者。超人的道德是個人主義的。S.T.W.重復了李石岑就道德、知識與生命藝術各自作用的論述。他也認為,道德與知識會僵化生命,藝術使生命積極向上,到達頂峰,自我轉化。因此,創造者通過自身力量,可成為藝術品的一部分。
白山的《尼采傳》很有趣,主要是因為它的寫作主要依據和辻哲郎《尼采論》的序言。事實上,白山的上述分析也參考了盧多維奇的著作,但我們的研究表明,他只是采納了傳記方面的內容。白山的文章與盧多維奇關于尼采的著作還是有所不同。我們從文章的第一行就看得出來。盧多維奇把尼采看作非道德論者、道德論者、進化論者和社會學者,而白山(和辻哲郎可能也是)則視其為極端的個人主義者、進化論者、新道德與新藝術的宣揚者。
白山的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尼采的著作有一種藝術色彩。因此,他個人的思想以不同于其他哲學著作的方式表現出來。為了邏輯推演,尼采常常借助于象征的表現。其學說中的矛盾之處并非其思想弱點所致,而是出于一種熱情,一種針鋒相對的目的,也是其天性使然。白山還強調尼采性格與發展的統一。①白山:《尼采傳》,載《民鐸》1920年第2卷第2期,第1頁。
這里,我們只需注意和辻哲郎及其中國譯介者對尼采的兩方面關注,即個人主義者與藝術理論家。
《尼采傳》的作者花了大量篇幅分析尼采的《悲劇的誕生》(Die Geburt der Trag?die, 1872)以及歷史哲學論集《不合時宜的沉思》(Unzeitgem??e Betrachtungen, 1876),不過,他對后者似乎不太感興趣。我們可以推斷其原因。尼采寫作《悲劇的誕生》后就認為,主體(如果是藝術家)將從他的意志中獲得救贖。詩人經常使用“我”這個字眼,他的意象是他自身,可他賦予“我”的深層含義卻不是經驗上作為真實人的“我”。情感熾烈的天才詩人能通過現實而物質的“我”,洞察一切事物的核心。②F.Nietzsche, Die Geburt der Trag?die.Leipzig: Kr?ner, 1930, pp.68-69.這個“我”并非創造者,而只能是中介者、反思者。
1878年起,尼采開始懷疑繼而否定自己早先創立的學說。此外,他還否定了自己的藝術理論。白山在文章里談到尼采的《人性,太人性》(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1878),但并未提及尼采的藝術理論。他注意到,尼采關于時間的哲學概念中存在自我的問題。他指出,尼采認為一切所謂的道德、法律、生命的法則都應該破除,應該只在人自身當中去尋找它們,這才是真正的生命。不過,我們很難確定作者的這一說法源自何處。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尼采原汁原味的觀點。只是在此書第一部分序言里,我們發現尼采說人必須是事物的目標和手段,③F.Nietzsche,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Leipizig: Kr?ner, 1930, p.11.而第二部分序言說,人唯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能訴說(因此也能去書寫)。接下來,尼采應該探討人征服了什么(was man überwunden hat)。④Ibid., p.3.尼采深信,他自己(ego ipsissimus),甚至他最親密的自我(ego ipsissimum)⑤Ibid.,就在他的作品當中。同樣,他注意到,自己角色的這一部分試圖尋找通向自身的道路。
因此,白山非常清楚尼采的“自我”本意,可他對構成尼采哲學基礎的“征服”只字未提;須知沒有“征服”,就很難理解尼采的個人主義。只有涉及具體個體時,尼采的個人主義才有意義;這里的個體可以描述為“征服的我”(überwindendes Ich),亦即可以征服的自我,然而在其他事物征服它本身之前,它需要重估價值,創造新價值。
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同樣寫到了“自我”。此處的自我是“事物的手段與價值”,且擁有三種屬性——必須是“創造的、甘愿的、估價的”自我。⑥F.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Leipzig: Kr?ner, 1930, p.32.此外,我們還看到,“個體(der Einzelne)是當代文明最后的虛構之物”。⑦Ibid., p.63.尼采認為,一個人如果把一切都看得無關緊要,或者從不評估、重估、(因而)創造,那么他的自我就毫無意義。
在白山看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尼采是自由精神的自我,他把宇宙生命等同于己,他的這本書最好,其中論述了“生命本身”、超人、永恒輪回。白山并不像李石岑那樣,輕視永恒輪回的學說,但他肯定地指出,尼采從永恒輪回中看到了“生命最高的肯定(Bejahung)形式”①《尼采傳》,第14頁。。
白山對超人的解讀比起以上提及的學者更具體和準確。超人是靠自我(或宇宙生命)尋求向上的人,是靠自己努力產生新價值的人。因此,超人是生命的有機目標。在他看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價值在于,它表明生命乃世俗之事,并相當重視自我和創造。②同上,第14—15頁。當然,白山的超人形象還不夠具體,無法充分表達尼采的超人觀念。自我是白山關注的焦點,顯然對和辻哲郎也是如此(他們關注的是應該會成為超人的自我)。
文章末尾,白山談到了尼采的藝術風格。他沒有說明自己的說法源自何處,不過很可能是《看哪!這人》。在該書《為何我寫如此好書》(“Why I Write such Good Book”)一章中,尼采提出了通過字符(Zeichen)傳達悲愴的內在張力。只有當風格致力于向讀者傳達作家或藝術家內心狀態時,才稱其為好的風格。③F.Nietzsche, Ecco Homo.Leipzig: Kr?ner, 1930, p.342.
讀了李石岑的藝術觀,我們發現他不太清楚作為文學藝術理論家的尼采。李石岑對藝術問題感興趣時,受到了和辻哲郎而不是尼采的影響。僅就我們對李石岑和白山的認識看,和辻哲郎感興趣的只是尼采的部分藝術觀。他的關注很可能已經包括了這個問題,然而在他看來,《人性,太人性》中的尼采是個人主義者(他只關注此書以后的時代),《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的尼采是藝術家。
《民鐸》雜志尼采專號中最后一篇文章是《超人和偉人》。作者朱侶云比較了尼采的超人概念與馬洛克(W.H.Mallock, 1849—1923)的偉人概念。1898年,倫敦出版了馬洛克的《貴族主義和進化》(Aristocracy and Evolution, 1898)。書中,馬洛克清楚地表達了自己反達爾文主義的態度,并花了大量精力批判斯賓塞的哲學觀點。朱侶云深信,尼采受過達爾文的影響;這足以讓《超人與偉人》的作者不再同情這位德國思想家。他指出,按照尼采的說法,誰能讓自己始終處于“適者生存”的斗爭條件下,始終“為生存而斗爭”,誰就能成為超人。超人不在乎多余的事物,他的出現是為了獲得最強大的力量和偉大的勝利。超人是精神世界、思想世界的一種表述;其中他是自己的目標,他自己的成長與發展的趨勢是決定因素。
相比之下,朱侶云更喜歡馬洛克的“偉人”。他認為,馬洛克不把“偉人”的目的放在個人身上,而是人所生活的社會當中。若僅以自己為中心,那就不過是動物中最合適者了。“偉人”的力量表現在對他人的影響。
馬洛克反對斯賓塞,但對尼采他只字未提。朱侶云用馬洛克的理論反對斯賓塞和尼采。在馬洛克看來,進化過程中沒有“適者生存”,而有“最偉大者的影響力”。④Ibid., p.150.朱侶云既不同意馬洛克,也不同意尼采。他承認,動物世界與人類世界中存在為生存而斗爭和適者生存的現象,但他強調人與動物在行為、目的、方式等方面都有所差別。他認為,尼采的理論完全取自社會達爾文主義,尼采是錯的。“超人”不能靠單純地為存在而斗爭產生出來。據此,馬洛克的“偉人”更切合真理,因為馬氏無私,而且支持社會進步。然而,朱侶云也看出馬洛克的不足之處:他認為馬洛克“偉人”的貴族主義站不住腳。他極為推崇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的人道主義(humanism),因為該思想中沒有英雄崇拜,而是頌揚道德。朱侶云認為,社會與個人都不重要,理想狀態是創造出兩者的必然統一。⑤Ibid., p.152.
白山的《尼采傳》還有一篇附錄,是譯自穆格(A.M.Mügge, 1878—?)著作《尼采生平與作品》(Fr.Nietzsche, His Life and Work, 1909)的《尼采之一生及其思想》。
《民鐸》雜志尼采專號收錄了兩篇譯文,一篇是張叔丹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序言,一篇是劉文超編譯的《人性,太人性》警句一百則。
這期專刊對尼采的介紹和評價參差不齊。顯然,主編李石岑并不要求其他作者具有跟自己一樣的看法。李石岑和白山的思想明顯受日本學者的影響,而朱侶云受英國學者影響更大。至于S.T.W.,我們很難指出其明確的立場,但他的文章仍然反映出他了解相關主題的英日文獻的研究成果。因此,這本雜志并未向讀者呈現千篇一律的尼采,這反映出在中國與世界文化相遇的初期,中國學者研究這位德國偉大思想家時所采取的眼花繚亂的方式。
五
郭沫若(1892—1978)很可能是通過德國表現主義者與活動家接觸尼采的,不過當他1923年上半年決定翻譯并闡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原譯名為《查拉圖司屈拉》)時,也可能同樣受日本學者思想的影響。1923年3月13日的《創造周報》第一期刊登了尼采這部名作的第一章中譯文。郭沫若沒有翻譯此書序言,他給出的解釋是中國已經有兩個譯本。事實上,除了之前提到的張叔丹譯本外,魯迅在1920年《新潮》雜志第二卷第五期上也發表了他的譯文。
郭沫若翻譯完此書第一部分后,很多友人和讀者不理解其內容,紛紛來信要求解釋。他的同事及好友成仿吾(1894—1984)也是催促再三。于是,郭沫若寫了一篇《雅言與自力——告我愛讀〈查拉圖司屈拉〉的友人》。①郭沫若:《雅言與自立——告我愛讀〈查拉圖司屈拉〉的友人》,載《文藝論集》,上海:光華書局,1929年,第417—424頁。他深感闡釋這部用“濃血與箴言”②F.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Leipzig: Kr?ner, 1930, p.41.寫成的著作讓自己力不從心。郭沫若謙虛地指出,論能力論學識自己都難以充分把握和解釋尼采的學說。郭沫若并不理解尼采,因此他很快就遠離了尼采。此后,他馬上轉向馬克思主義。
魯迅在談到20世紀上半葉某些中國文學團體的著作時,關注了尼采和中國的尼采主義。在他看來,尼采引起了沉鐘社的興趣。③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第四卷》,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第5—6頁。然而,該團體成員及沉鐘社紀念文章的作者陳翔鶴對尼采卻只字未提。④陳翔鶴:《關于“沉鐘社”的過去現在及將來》,載《中國新文學大系·第十卷》,第193—201頁。
魯迅同樣也談到了狂飆社。⑤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第12—15頁。該團體創始人高長虹是他的弟子。魯迅大量引用狂飆社發表的一份文獻,其中寫道“軟弱是不行的”,“我們要作強者,打倒障礙或被障礙壓倒”。⑥同上,第13頁。這段話出現在1925年2月。魯迅認為,狂飆社沒有論及“超人”,但后來這些人“超越”了自己。他們的不幸在于,未能像尼采那樣引起讀者的興趣。因此,狂飆社及其雜志也就未能持久。⑦同上,第12—13頁。
在狂飆社的主要成員向培良的著述中,魯迅聽見了“尼采的聲音”。
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這個我也說不出很多的道理。總而言之:我已經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在這里面游離了四年之后,我已經刻骨地討厭了這古老的虛偽的大城。在這里面,我只看見請安,打拱,要皇帝,恭維執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這都是奴才們的絕技!厭惡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魚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嘔吐,于是提著我的棍走了。⑧同上,第15頁。
我們很難從這段話中聽出尼采,但魯迅卻聽到了“進軍的鼓角”。他評論道:“尼采教人們準備著‘超人’的出現,倘不出現,那準備便是空城。但尼采卻自有其下場之法的:發狂和死。否則,就不免安于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即使在孤獨中,毫無‘末人’的希求溫暖之心,也不過蔑視一切權威,收縮而為虛無主義者(Nihilist)。”⑨同上。
從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30年代的魯迅如何理解尼采。他認為,尼采并不是虛無主義者,可要不是疾病使其喪失理智,尼采本會成為這樣的人。他的中國追隨者們,如向培良,都是虛無主義者。
筆者認為,狂飆社的反抗不是尼采主義的反抗,(盡管按照一般看法)而是虛無主義的反抗。尼采對虛無主義的理解與魯迅的截然不同。
塔格爾(A.Tagore, 1871—1951)在其《現代中國的文學爭論》(Literary Debates in Modern China, 1967)中指出,高長虹與向培良于上海創立了《狂飆周刊》,目的是“把尼采哲學引入現代中國文學”。可惜,他的觀點缺乏相關證據的支持。如果高長虹的話可信,我們就能從他致魯迅兄弟周作人(1885—1966)的公開信中看出,這個問題更為復雜。周作人指責高長虹深受尼采荼毒,自詡為天才,還想讓世人對自己頂禮膜拜。高長虹則反唇相譏道,自己是從周作人那里沾染尼采之毒后,①張均編:《現代名人書信》,上海:合家書店,1937年,第315頁。才對尼采產生興趣的,而且自己完全把他的著述當作藝術作品來閱讀。信中,高長虹還提到,自己非常喜歡一位德國人(他沒有說是誰),但肯定不是尼采。不過,如果讓他選出自己最欣賞的十個人,尼采很可能位列其中。但他喜歡尼采只不過是因為欣賞尼采著作的藝術價值。
可以肯定地說,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影響過林語堂(1895—1976)這位1920年以后中國最重要的人物。在《語絲》雜志中,他解釋過查拉圖斯特拉的格言,②1925年12月12日第58期,第1—2頁。還在其他地方把此書作為十本必讀外文書之一推薦給青年讀者。③章衣萍:《青年應該讀什么書》,載俊生編《現代論文選》,上海:仿古書店,1936年,第174頁。
魯迅是中國作家中最用心研究尼采的。20世紀初他就開始對尼采感興趣,而且這種興趣一直持續了整整20年。這里,我們僅僅分析1918—1925年間魯迅的觀點及其著作與尼采的關系。
首先應該注意到,魯迅也是深受達爾文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他相信進化,并且在自己的文章和創作中清晰地表現出來。同大多數中國的尼采仰慕者一樣,他也是從達爾文主義角度理解超人的。甚至在15年后的1935年,他還談到無限的超人。
正如許多類似著作和文學研究所述,魯迅借助了寓言(allegory)。例如,他用夜的寓言描述當時的中國現實,即黑暗籠罩,只有幾點微光:“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④同上。這里的“我”可以翻譯成“ego”,它是能影響社會的杰出個體的“ego”。在魯迅眼里,杰出人士包括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達爾文(Charles R.Darwin, 1809—1882)、施蒂納(Max Stirner, 1806—1856)、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尼采和托爾斯泰(Lev Tolstoy, 1828—1910)。⑤同上,第407頁。他們都是偶像破壞者和創造者。
當談到“個體”時,魯迅想到的正是這些人。尼采稱他們為“孤獨者”(die Einzelnen)。魯迅很熟悉這個詞。⑥同上。這些“孤獨者”遠離塵囂,不與蠅營狗茍之輩(代表了孤獨的敵人,而不是偉大的偶像破壞者和創造者)為伍。
乍看之下,魯迅對個體(自我)與人類的觀點似乎與日本白樺派不謀而合。可事實并非如此,因為白樺派很少關注社會,而魯迅始終以社會為重。在1918—1925年間,(對魯迅而言)個體正處于顯耀位置,必須首先改造個體,然后再改造社會。⑦魯迅:《隨想錄》第四十一、四十六則,見《魯迅全集·第一卷》,第400—401、406—407頁。魯迅與尼采都關注個體,但尼采卻不關注社會。
研究者很容易發現,尼采影響了魯迅的世界觀。不過,要找出尼采對魯迅短篇小說寫作的影響就難了。我們將具體談談尼采對《狂人日記》創作的影響。熟悉尼采著作和魯迅《狂人日記》的讀者,很可能驚訝地發現,《快樂的科學》(Die fr?hliche Wissenschaft, 1882)里的狂人與魯迅筆下的狂人極其相似。
首先,我們來簡單描述尼采的寓言。清晨,一個狂人提著點亮的燈籠來到集市,高喊:“我找到上帝了,我找到上帝了!”四周的人誰都不相信,還紛紛嘲笑他。于是,狂人指責這些人,也責怪自己,一起把上帝害死了。顯而易見,寓言里的狂人指尼采本人,集市上的人指他的言語對象,上帝指一切道德與審美的化身,上帝之死意味著舊價值的衰退。尼采給自己賦予重估一切價值的任務,寓言中的狂人同樣如此,他宣稱,自己不做上帝,而要做衡量萬物尺度的人。①F.Nietzsche, Die fr?hliche Wissenschaft.Leipzig: Kr?ner, 1930, pp.140-141.
在《狂人日記》中,魯迅同樣談論了狂人,但他創作的不是寓言,而是諷喻故事。篇章結構也更為復雜。
魯迅的短篇小說由序言和10個長短不一的故事組成。前兩個故事交代了故事發生的環境,描寫了主人公狂人(以第一人稱視角)凄涼的心情。所謂的狂人罹患妄想癥,他的恐懼似乎情有可原。他害怕鄰家狗兒的目光,害怕鄰家人的目光,害怕小孩的目光。每當皓月當空,夜色朦朧之際,他都苦惱不已。他感覺人人都要出來打自己,甚至還想要自己的命。
第三部分是狂人思想的高潮,包含了經常被引用和分析的句子:“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②《魯迅全集·第一卷》,第12頁。
整篇小說沒有戲劇性的高潮。在后面幾個部分,魯迅談到了食人族及其手段,還勸他們放棄不合自然的食性,威脅他們,呼吁“真的人”,呼吁拯救還未淪為盤中餐的兒童。③同上,第19頁。
讀到這,可能有人會問:魯迅讀過《快樂的科學》中的狂人寓言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魯迅研究并且熟知《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除此之外的尼采著作他既沒有提到過,也沒有引用過。
魯迅也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尼采筆下的這個狂人。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更清楚地展現尼采的超人概念,更方便考察魯迅的狂人。
不過,魯迅知道另一個“狂人”(尼采沒有這樣稱他),此君便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主人公。
在尼采著作中,魯迅提到最多的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序言》的第三部分。他曾兩次將其譯成中文④第二次翻譯見上文。第一次翻譯發表于《文言》雜志。,兩次引用⑤《魯迅全集·第一卷》,第401頁;《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第1—2頁。;此外,整部《狂人日記》都是對尼采這部分思想的闡釋。在魯迅看來:“你從蟲變成了人,可你仍是不折不扣的蟲。從前你是猿,即便現在,人還是比猿勝似猿。”1935年,魯迅暗示了這個意思。
魯迅似乎認為序言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高潮部分,而對其他研究者而言,第三部分才是全書的高潮,也是書中最詩情畫意的:其中既寫到了超人,又寫到了永恒輪回,象征了人類希望的雙重景象,尼采的努力及其哲學的目標。然而,魯迅對永恒輪回并不感興趣,身為進化論支持者,他很難相信類似的觀點。
序言第三部分的查拉圖斯特拉幾近癲狂,很似《快樂的科學》中的狂人。他也面向集市的民眾宣稱上帝已死。然而,《快樂的科學》中的狂人沒有為人類設定任何具體而有限的理想,只是聲稱上帝不存在,聲稱貶值后,價值混亂中的生命毫無意義;序言中的“狂人”卻設定了尼采的主要理想之一——超人。如前所見,超人的形象對魯迅來說過于寬泛和模糊。結果,在《狂人日記》中,他試圖用上述方式刻畫狂人,讓讀者能比他更好地理解超人。魯迅認為,尼采的理想不只是狂人,還是“真的人”。兩者名異而實同。
魯迅的狂人形象遠比查拉圖斯特拉具體生動,但層次不夠豐富。它確實讓人印象深刻,可藝術形象不夠豐滿。魯迅的狂人只有一個想法:他那個社會的吃人現象。他擔憂自己,擔憂接近他的人,尤其擔憂無辜的兒童。尼采的狂人像噴涌熱水的泉眼,像技巧炫目的雜耍藝人:他有許多看法,意想不到的觀念(常常是模棱兩可),甚至深不可測的象征。
這兩個狂人進入中國時,正值社會破除偶像(尤其是道德領域的偶像),他們的確對讀者產生了強烈的沖擊。當時的中國崇尚實用主義、達爾文主義;換言之,當時中國哲學家身上有濃厚的達爾文主義色彩。結果,人們立刻接受了魯迅的狂人;而尼采的狂人,他們不但沒有理解,而且還曲解了,因為這個人物并不是達爾文主義理想的解釋對象。魯迅對尼采的狂人也做了類似解讀。他認為,自然界中不可能存在超人,超人是新物種,而理想的超人也無法實現。盡管魯迅從未直接從哲學角度分析他理想中的“真的人”(以補充“無限的”超人),但他的著作,特別是議論文,正是這一理想人物的注釋。
如果我們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序言或其第三部分與《狂人日記》比較一番,能清楚地看到兩個相似點。兩部作品都是寓言(allegory),多少都具有短篇小說的形式。此外,序言堪稱尼采哲學的精巧介紹,而《狂人日記》(按照中國學者朱彤的說法)可視為魯迅頭兩部短篇小說集的宣言。①朱彤:《魯迅作品的分析》,上海:東方書店,1954年,第82頁。筆者認為,《狂人日記》還可看作“五四”運動時期魯迅哲學觀點的首次引人矚目的展示。作為那個時代的哲學豐碑與文獻,魯迅的這部小說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魯迅的狂人沒有模仿尼采的狂人,而《狂人日記》也沒有模仿《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序言。在《狂人日記》中,魯迅對主體和材料都進行了創新性加工。尼采創造主要靠誘因和沖動,這可不是魯迅亦步亦趨模仿的典范。從一開始,魯迅的狂人就截然不同,他(大部分時候)更集中,更具體,更有限,也更全面。尼采的狂人屬于歐洲,甚至世界,而魯迅的狂人屬于中國。魯迅筆下另一個狂人形象是《阿Q正傳》里的阿Q,這可能是中國現代小說中最偉大,或者(至少)從哲學角度看最感人至深的人物。尼采的狂人是靈感噴涌而出的結果,是深層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存在主義者、后自然主義象征論(postnaturalistic symbolism)詩人的先驅。魯迅的狂人是中國古典文學與歷史鑒賞家、勤奮鉆研“新科學”的學生、進化論倡導者的作品。
另外,中國傳統對狂人的理解與魯迅的解讀大不相同。傳統中的狂人要么是愚人,要么是隱者或出淤泥而不染者。后兩種人主要或僅僅關注自己,而魯迅的狂人主要關注社會和人類。
無論如何,魯迅對狂人的理解(狂人非愚人)與尼采更相近。魯迅研究過嵇康(223—262)的“狂人”,這很可能將其引向《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狂人,不過要是沒有后者,魯迅也不可能創造出他的狂人。顯然,這其中幾個因素的影響不可小視:一是重估一切價值的口號,二是后尼采時代破壞偶像的趨勢,三是民眾對世界名人的仰慕。
魯迅接觸尼采的“對頭”馬克思以后,對尼采的看法逐漸發生改變,但這是1925年后的事。不久,李石岑發表了《超人哲學淺說》。②見Brière, op.cit., p.173.根據鄭壽麟的研究,此書出版于1931年(鄭壽麟:《中德研究參考書目》,載《中國文化》1963年第5卷第2期,第140頁)。1935年,徐梵澄(1909—2000)以《朝霞》為名翻譯出版了尼采的《黎明》(Die Morgenr?te, 1881)③見傅吾康(W.Franke)與張紹典編:《德籍漢譯存目》,北京:中德學會,1942年,第5頁。、《尼采自傳》(Ecce homo: wie man wird, was man ist,1888)。④同上。此外,1935年,他還翻譯過《蘇魯支語錄》(即《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⑤同上。1936年出版了蕭贛(楚圖南)由英譯本(托馬斯·卡門[Thomas Common, 1850—1919]的譯本)轉譯而來的《扎拉圖土特拉如是說》。⑥同上。1939年,徐梵澄又翻譯了《快樂的知識》(即《快樂的科學》)。⑦同上。
1925年后,中國的尼采熱明顯消退,但并未就此消失。例如,哲學家方東美(1899—1977)在1936年發表的《科學,哲學與人生》中,就經常引用尼采。⑧Brière, op.cit., p.128.如果進一步研究,我們還能發現更多例子。
20世紀40年代初,“戰國策派”的哲學家與批評家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戰國策》本來是一部歷史作品,作于戰國時期與西漢交接之際,以其出色的文學性而著稱。戰國策派成員陳銓(1903—1969)在其《德國民族的性格和思想》中談到了尼采。他把尼采視為現代最有影響、最成功的哲學家。知識界反法西斯人士,如歐陽凡海(1912—1970)①歐陽凡海:《文學論評》,重慶:當今出版社,1943年,第149—163頁。、洛蝕文②洛蝕文:《魯迅與尼采》,載景宋編《魯迅的創作方法及其他》,桂林:新中國文藝社,1942年,第40—71頁。景宋為魯迅夫人許廣平的筆名。(即王元化[1920—2008]——譯者按)也曾提到或探討尼采。不過,在他們(特別是洛蝕文)看來,尼采是法西斯哲學的始作俑者。
六
在中國,馬克思與尼采被視為德國現代思想的兩位主要代表。歷史已經表明,中國人對馬克思推崇備至,而對尼采則漠不關心。他們都是從實用主義角度理解這兩個人。馬克思的學說正適合他們對進化過程的看法,而對革命的理解,也只有細微之別。那些起初信仰尼采的人后來大多轉向馬克思,其中就包括本文提到的茅盾、李石岑、郭沫若和魯迅,當然還可能有我們不曾注意到的人。這種轉變在茅盾和郭沫若身上一閃而過,李石岑和魯迅則花了很長時間。其原因很可能是個人學識深度不同,當然也有其他因素的影響。
尼采哲學不適合近現代中國。我們已經看到,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中國人就開始尋找適合行動的哲學,然而尼采哲學卻與此格格不入,即便中國讀者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曲解尼采的思想,它也達不到這個目的,恐怕以后依然如此。從一開始,中國人已經給它披上“法西斯主義的外衣”,如今想再褪去談何容易。因此,我們最好的辦法是敬而遠之。尼采本來想走向全世界,可由于他學說的特點,只限于正確理解其超人思想和接觸過他的少數人,如心理分析家、存在主義者、施賓格勒(O.Spengler, 1880—1936)、托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蕭伯納(G.B.Shaw, 1856—1950)、黑塞(H.Hesse,1877—1962)等。
中國人對尼采的極度渴求有何“收獲”?首先,尼采學說影響了魯迅的性格及其創作,當然也包括李石岑接觸馬克思主義前的創作。尼采在中國的失敗對我們有何啟示?陳獨秀和魯迅之后,中國人逐漸遺忘了價值,尤其是“道德”與“審美”價值。憧憬美好未來,期待社會、政治進步,逐漸掩蓋了其他一切。物質存在的重要性讓內在生命的重要性黯然失色。在沒有改造個人之前,中國人就開始改造社會。另外,即便是宣傳尼采學說的中國學者,也未能理解尼采追求自我完善的理想及其“突出個性”(giving style)的觀點,③Kaufmann, op.cit., p.359.而這正是他——一個“征服”并教育自己,可也經常遭蔑視、詬病、誤解的人的最根本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