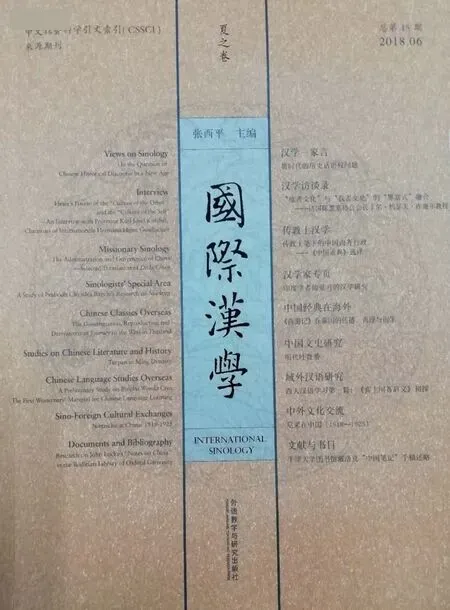西方早期漢學對宋代中國“重文輕武”形象的構建
——以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為中心*
提及宋代,人們往往會感慨它在文治和武功兩方面呈現出來的巨大反差,文治昌盛、武功不競,長期以來一直是貼在宋代歷史上的標簽。人們一方面稱許“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①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277頁。,另一方面痛心于宋朝軍隊對外屢戰屢敗,宋朝政府卑躬屈膝,甚至將之視為一個喪權辱國的時代。相比國內學者的怒其不爭,西方學者更多關注宋代中國在文明上達到的高度,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曾說:“綜觀11—13世紀的中國,便感到經濟和學識的驚人發展。……東亞與基督教西方之間的差距異常明顯,只需就每個領域(貿易額、技術水平、政治組織、科學知識、文學藝術)將華夏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略加比較,便可確信歐洲大大‘落后’了。毫無疑問,11—13世紀的兩大文明是中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②謝和耐著,黃建華、黃迅余譯:《中國社會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5、306頁。西方漢學家對中國宋代文明給出了極高的評價,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忽視了宋朝文、武發展的不平衡,黃仁宇(Ray Huang, 1918—2000)指出宋朝歷史上若干似是而非的現象,其中就包括它在文化上的輝煌成就和軍事上的無所作為。③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北京:三聯書店,1992年,第145、146頁。西方學界對于宋代歷史的這種印象始于何時何處,換句話說,西方學界對于宋朝的“文治武功”最初如何評價,這是學術史需要回答的問題。18世紀上半葉,法國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神父出版了巨著《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35, 簡寫為Description de la Chine,以下簡稱《全志》)①《全志》有兩個英文版本,一是由出版商瓦茨(J.Watts)于1736年12月在倫敦出版,書名為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Chinese-Tartary,Corea and Thibet,是一個節譯本。另一個是由出版商凱夫(Edward Cave)推出的全譯本,于1738—1741年陸續出版,書名是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 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Natural as well as Civil) of those Countries。本文以凱夫本為據。《全志》有關宋代歷史的記述分為兩種形式,一是有關宋代君主史綱,系參考袁黃的《歷史大方綱鑒補》(以下簡稱《綱鑒補》)編纂而成;二是大量宋人奏疏、文章譯文,系從明代唐順之的《荊川先生稗編》和清代徐乾學等編的《古文淵鑒》等書中選譯(參見藍莉[Isabelle Landry-Deron]著,許明龍譯:《請中國作證: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02、182、187—261頁)。因此,本文涉及史料的原始出處,一律從這些書目中摘引,而不選宋人第一手資料,特此說明。,其對宋代中國在文、武兩方面表現的描述和評價,影響了此后近兩個世紀西方學者對宋代歷史的認知和理解。本文嘗試就《全志》呈現的宋代中國“重文輕武”的形象展開討論。
一、宗教背景下宋朝君主“右文”的形象
宋承五代之弊,為扭轉長期失衡的文武關系,救治由此產生的社會動亂,宋太祖奠定“文治”的開國之基,此后的繼體之君奉為圭臬,終于確立起“崇文”的社會風尚。《全志》在宋代歷史概述部分的開頭就指出宋朝君主“重文輕武”的傾向:“歷史進入宋朝以后,國家從此前的混亂、戰爭和其他災禍中恢復,進入了長期的安定,如果宋朝君主能夠如同好文那樣尚武,和平帶來的幸福還會持續得更長久。”②J.B.Du Halde,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 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Natural as well as Civil) of those Countries. London: Printed by Edward Cave, at St John’ Gate, 1738-1741, vol.1, p.206.文化的繁榮離不開統治者的優容與扶植,宋朝君主對文學、文化的獎掖,終于促成了宋代文化的全面興盛:“在宋代以前,由于各種宗教和戰爭帶來的災患,國家喪失了對學術的熱愛,無知和墮落盛行,沒有任何學者能夠在普遍的萎靡中喚醒人們的意志,唯有宋朝統治者對古代經典的熱愛、對文人的尊重才使得文學逐漸復興。”③Ibid., pp.657-658.
杜赫德詳細列舉了宋朝皇帝“右文”的表現和舉措,比如宋太宗給予文人慷慨的支持,他自己也很博學,每天留出固定的時間讀書,他有一座圖書館,藏書達到八萬卷。④Ibid., p.207.這應該是指太平興國三年(978)設立的崇文院而言,參見袁黃:《歷史大方綱鑒補》卷二十八《宋紀·太宗皇帝》,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78a頁。宋真宗復刻古代經典在全國散布;⑤Ibid., p.208.宋徽宗愛好文學,并且造詣頗深;⑥Ibid., p.210.宋高宗性格平和,熱愛知識;⑦Ibid., p.211.時代的危機需要一位尚武的君主,但理宗卻完全沉浸于科學。⑧Ibid., p.213.在杜赫德筆下,宋朝君主是一個文化修養極高、愛好知識、尊重文士、好文勝過尚武的群體,他們或許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宋真宗崇信道教,宋徽宗耽于享樂,但在整體上卻充滿理性、遠離蒙昧。
在談及宋朝君主“右文”的表現時,杜赫德多次提到他們對孔子的敬奉,表面看來,這是為了突出他們對文治的重視,但稍加思考,便會發現其與當時歐洲“中國禮儀之爭”的背景密切相關。“中國禮儀之爭”是由耶穌會在華傳教策略和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而引發的不同修會之間的爭論,⑨有關“中國禮儀之爭”,參見David F.Mungello eds.,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Monumenta Serica, 1994; 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張國剛:《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鐘鳴旦:《禮儀之爭中的中國聲音》,《復旦學報》2016年第1期,第95—103頁,等等。“祭孔”是其核心問題之一,論爭的焦點在于祭孔是否帶有宗教性質,是否允許中國基督徒參加祭孔儀式。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認為,祭孔是一種政治性的、世俗性的人文活動,而不是宗教性的異端禮儀:
孔廟實際是儒教上層文人唯一的廟宇。法律規定在每座城市并且是該城中被認為是文化中心的地點都建造一座中國哲學家之王的廟宇。……每個新月和滿月到來時,大臣們以及學士一級的人們都到孔廟聚會,向他們的先師致敬。這種情況中的禮節包括焚香燒燭和鞠躬跪拜。每年孔子誕辰以及習慣規定的其他日期,都向孔子供獻精美的肴饌,表明他們對他著作中所包含的學說的感激。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正是靠著這些學說,他們才得到了學位,而國家也才得到了被授予大臣官職的人們的優異的公共行政權威。他們不向孔子禱告,也不請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幫助。他們崇敬他的那種方式,正如前述的他們尊敬祖先一樣。①利瑪竇、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著,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03、104頁。
利瑪竇把“祭孔”解釋為儒家教育和科舉制度的一種形式,而不是求神拜佛式的宗教性祈禱,在他之后的大多數耶穌會士也都承襲他的看法:“孔子與祖先之崇拜,是純粹一種非宗教性質,而并不與天主教義背反。”②魏特(Alfons W?th S.J.)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49年,第120—121頁。耶穌會的觀點招致了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等其他教派的非議,他們主張孔子不僅僅是受文人膜拜的先師,而且是被奉為神明的偶像,祭孔典禮是一種宗教異端行為,應予以嚴格禁止。
面對其他教派的聯合攻擊,耶穌會不得不派人到羅馬教廷解釋,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就辯解道:“至于人們對孔子的尊崇,并不是一種宗教崇拜,以其名命名的孔廟也不是真正的廟宇,那只是讀書人聚會的地方而已。”③李明著,郭強、龍云、李偉譯:《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72頁。耶穌會士同時發表大量著作,來爭取其他人的理解和支持,《全志》就承擔著這一使命。杜赫德與利瑪竇一樣,試圖從治國和教育的角度解釋祭孔行為,在記錄宋寧宗時期朱熹入祭孔廟時,他提到一項中國“傳統”:如果一個人品德出眾,或有杰出的治國才能,皇帝就會將他列入孔門弟子,可以在每年特定時候和孔子一起接受官吏和文士的禮敬。④Du Halde, op.cit., p.212.這一“傳統”從側面證明,人們對孔子的祭祀,是出于對道德和治國才能的尊敬,與迷信無關。
杜赫德述及,“韃靼”(tartar)君主金熙宗為了贏得臣民的愛戴,顯示對知識和士人的尊重,拜謁了孔廟,并效仿中國君主給予其皇家榮譽。大臣對出身卑微的孔子獲此殊榮頗為不滿,金熙宗答稱:“如果他的出身不足以獲得這些榮譽,他所創立的卓越學說足矣。”⑤Ibid., p.211.有關金熙宗敬孔,《綱鑒補》記載如下:
金主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一日,兀術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⑥《綱鑒補》卷三十四《宋紀·高宗皇帝》,第234b頁。
《全志》的敘述與史料原文所強調的重點顯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錯位。原文中金熙宗的種種舉措,最后都歸結為“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在他看來,和平時期應該注重培育文治的社會風氣,以達到完善的社會秩序,敬孔等舉措都是以此為旨歸的。相比之下,《全志》則希望說明,孔子之所以廣受尊敬,完全是由于他所創立的學說使然,從而消除祭孔禮儀中的宗教因素。
杜赫德對宋代君主尊孔的記述蘊含著明確的宗教目的,他并不僅僅是為了突出宋人“右文”的特質,更重要的是為耶穌會的傳教策略辯護。出于這種目的,他將一些歷史事件從原本的歷史語境中剝離出來,進行了有意的曲解和改寫,在此過程中,事件本身承載的歷史意義被淡化。有關金熙宗敬孔的記述已經顯露出這種趨向,對宋太祖尊孔的記載則更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杜赫德記載,宋太祖為鼓勵向學,拜訪孔子故里,撰寫贊詞,并對孔子后人予以封賞。①Du Halde, op.cit., p.207.這一記載當系建隆元年(960)三月“宋主視學”一事,《綱鑒補》載: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圣先賢像,自為贊書于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余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貴文學。②《綱鑒補》卷二十八《宋紀·太祖皇帝》,第62b頁。
原文在太祖“視學”后,尚有“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之語,這段話在宋初的政治語境中,有著明確的政治指向和突出的政治意義,它是在五代入宋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扭轉武人飛揚跋扈的態勢、平衡失序的文武關系、重建尊卑有別的君臣之道的一個重要舉措。③參見鄧小南:《談宋初之“欲武臣讀書”與“用讀書人”》,《史學月刊》2005年第7期,第45—55頁。太祖“視學”受到中國傳統史家的高度評價,《綱鑒補》中有明人周禮“發明”:“宋主視學乃見于得國之始,宋氏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盡在于此。自是而后,儒道稍稍振起,迨至關、閩、濂、洛之間,文運大亨。”④《綱鑒補》卷二十八《宋紀·太祖皇帝》,第62b—63a頁。史料并未提及宋太祖訪孔子故里之事,《御批續資治通鑒綱目》載周禮“發明”,其中提到“周太祖廣順二年,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參見商輅:《御批續資治通鑒綱目》卷一,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5年,第14頁),杜赫德或許有所誤解。在周禮看來,宋太祖的舉動奠定了有宋一代三百年基業,成就了宋朝“文質彬彬”的特質,因而影響深遠。杜赫德的敘述意在凸顯拜謁孔子與鼓勵向學之間的聯系,為世人尊孔提出解釋,但卻沒有抓住五代宋初時世鼎革之際偃武興文、重建秩序的深層歷史動向,因此也沒有真正觸及宋代歷史的脈動。
在杜赫德的闡述下,祭孔并不含有任何宗教因素,它一方面與尊重、追求知識的人文精神相關,另一方面與道德和治國相連,這就迎合了當時歐洲知識界對人文精神、對道德和治國之道的追尋,為耶穌會的寬容策略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不但宋朝皇帝對孔子禮敬有加,即便是入侵中國的“野蠻人”也不例外,金熙宗為獲得臣民愛戴而敬孔,元世祖忽必烈也精通科學,由于尊重士人和敬奉孔子而贏得臣民的善意。⑤Du Halde, op.cit., p.213.這些事例提醒羅馬教廷和那些對耶穌會抱有成見的人們,耶穌會士的做法有明確的歷史依據,要想使基督教被中國人接受,禮敬孔子是一條已經被證明行之有效的途徑,耶穌會的適應政策因此具有了合理性。
二、宋人對戰爭的慎重
杜赫德想要向西方讀者傳遞一個文明理性、清明開化的中華帝國形象,戰爭的殘酷是他想要隱諱的內容,但與此同時,兩宋時期大部分時間內,中原王朝都面臨著來自周邊民族政權的威脅,戰爭的壓力影響到內政的方方面面,這在客觀上使得在討論這段歷史時不可能對戰爭視若無睹。《全志》對宋代發生的幾次大規模戰爭都有所述及,但一般情況下只通報戰爭的結果和影響,盡量避免涉及戰爭的具體過程,比如對宋初的統一戰爭,僅以一句話概括:“太祖以其良好的性格紆尊降貴,重新臣服了諸國,再造和平。”⑥Ibid., p.206.歷史上,宋朝在對外戰爭中屢遭敗績,也因此被貼上“積弱”的標簽,但杜赫德并沒有突出宋朝的失敗,而是采用一些中性的詞句,對代表“中國”的宋朝多方回護。對宋太宗朝兩次大規模北伐失敗,杜赫德以雙方“各有勝負”來概括;⑦Ibid., p.208.宋金戰爭時宋高宗在金軍追擊下狼狽南遷,也被杜赫德美化為宋高宗“取得了幾次對韃靼戰爭的勝利,并鎮壓了叛亂”。⑧Ibid., p.211.
戰爭本身并不是杜赫德想要考察的主要對象,他的意圖不是揭示戰爭的起因、經過、影響等問題,而是通過戰爭來傳遞他理想中的“中國”形象。在談到宋太宗在位期間與遼朝的戰爭時,杜赫德寫道:
太宗迫切希望收回前任割讓給契丹的城池,但軍隊統帥張齊賢(Tchang si bien)總是勸他放棄這個想法,他說:“首先應該確保帝國的和平,達到這個目標后,我們將會輕易消滅這些野蠻人。”但太宗并沒有聽從這一勸告,雙方發生了幾次戰斗,各有勝負。張齊賢在解除一座城池的圍攻時采用了非凡的策略,他派出300名士兵,每人攜帶火把,列隊向敵營進發。敵軍被如此多的火把所震懾,以為是整個軍隊攻擊他們,驚慌失措,四散奔逃。張齊賢在道路上預先設下埋伏,只有極少數敵軍逃過了殺戮。①Ibid., p.208.
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率軍攻滅北漢,緊接著移師攻遼,企圖一舉收復幽云地區。結果宋軍在高梁河之役大敗,太宗股中兩箭,僅以身免。次年,有大臣建議再伐幽薊,張齊賢上書勸阻,認為首先應該嚴選邊將,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其次提出“先本而后末,安內以養外”,“廣推恩于天下之民”,“民既安和,則戎狄斂祍而致矣”。②《綱鑒補》卷二十八《宋紀·太宗皇帝》,第79b—80a頁。
至雍熙三年(986),經過幾年的休養生息,太宗又一次發兵北伐,卻再次以慘敗收場。由于大將楊業戰死,遂以張齊賢代楊業知代州,《全志》記載的張齊賢破敵便發生于此時,《綱鑒補》載:
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齊賢請行,乃命之。齊賢大敗契丹于土鐙堡,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于土鐙寨掩擊,大破之。③同上,第84b頁。
如上所述,《全志》對太宗時期宋遼戰爭的記述其實是綜合多處記載改編而成,張齊賢上書發生于太平興國五年,時任左拾遺,而非《全志》所謂“軍隊統帥”,其帶兵破遼則遲至雍熙三年。除去這些表述上的錯誤,更引人深思的是《全志》對這場戰爭的記述方式,太宗兩次北伐中,張齊賢并不居于顯著位置,但《全志》的記述卻恰恰是以這樣一個“邊緣人物”為中心的,這一選擇頗為耐人尋味。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張齊賢的事例恰好足以體現杜赫德想要表達的觀點:其一,中國的知識階層反對發動戰爭;其二,中國人在戰爭中表現出高超的智慧和美德。
杜赫德試圖說明,中國處在文人學者等知識階層的治理下,所發生的戰爭大多是不得已而為之,賢士大夫們反對戰爭,奉行和平的對外政策。杜赫德記載,宋神宗銳意開邊,但他母親留給他的大臣勸他應不計代價保持和平。④Du Halde, op.cit., p.209.作為證明,《全志》收錄了蘇軾的《代張方平諫用兵疏》,該文是熙寧十年(1077)蘇軾路過南都時代張方平寫就。蘇軾在文中寫道,“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也。”他指出,盲目用兵,不但失敗后會致使國家喪亂,即使勝利也會給國家帶來敗亡。他列舉秦始皇、漢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四位皇帝為例,證明“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的道理,勸神宗“遠覽前世興亡之跡,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⑤Ibid., p.563.康熙帝選,徐乾學等編注:《古文淵鑒》卷四十九《代張方平諫用兵疏》,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80—1083頁。這篇文章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勸誡用兵的代表作,南宋黃震稱該文“真可謂萬世人主好用兵、人臣好生事者之戒”,明代茅坤則盛贊該文為古代論用兵的頭等文章,“與天地并傳”⑥《古文淵鑒》卷四十九《代張方平諫用兵疏》,第1082—1083頁。。
與蘇軾文章類似,《全志》還收錄了南宋張栻的《入見孝宗奏》,⑦Du Halde, op.cit., p.577.同樣是勸阻皇帝謹慎對待戰爭。孝宗年間,虞允文以恢復北宋舊疆為念,數次遣人致意張栻,張栻因此寫下這篇奏章。他在文中說:“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后,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①《古文淵鑒》卷六十二《入見孝宗奏》,第1343頁。主張以明大義、正人心為本,考慮舉動的輕重緩急,反對盲目發動戰爭。這兩篇奏章共同向西方讀者表明,中國的賢士大夫們對用兵擴張是持否定態度的。
杜赫德嘗試通過對戰爭的描述,凸顯中國人的智慧和美德。兩宋之交的宋金戰爭中,徽、欽二帝被虜北上,繼位的宋高宗也在金軍追擊下一路南逃,甚至一度不得不浮舟海上。但《全志》對這場戰爭的記述卻絲毫看不到宋朝狼狽的跡象,其中凸顯的是宋人的三種形象。首先是忠臣。李若水(Li-so-shin)面對金人的勸降,堅稱“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咬舌自盡;②Du Halde, op.cit., p.211.《綱鑒補》卷三十二《宋紀·欽宗皇帝》,第194b頁。根據《綱鑒補》的記載,李若水并非咬舌自盡,而是為金兵所殺,杜赫德的敘述有誤。楊邦乂(Yangpang)被俘后寫下血書,“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③Ibid., p.211.其次是勇將。岳飛率軍長途跋涉解救南京(Nang King),殺傷金軍甚眾,使金軍此后再未渡過長江。④Ibid., p.212.最后是孝子。宋高宗雖與金朝簽訂了屈辱性條約,在條約中使用了“臣”(chin)和“貢”(kong)的字眼,但卻是為了迎回死去親人的骸骨。當這些親人的尸骨到達杭州時,人們以極大的喜悅迎接,朝廷也宣布大赦天下。高宗的行為得到史家的高度贊揚,被視為難得一見的孝道例證。⑤Ibid.
如上所述,戰爭并不是杜赫德的主要考察對象,在他筆下,也很少看到宋朝在對外戰爭中的失利和狼狽,他的目的是借助戰爭的背景,傳遞他理想中的宋代中國的形象:中國在“哲學家”即文人學者的治理下,所發生的戰爭多是迫不得已,士大夫熱愛和平,反對戰爭,同時具有高度的智慧和美德。杜赫德所確立的宋代中國的這一形象,其實是對歐洲尤其是法國國內形勢的反鑒。16至17世紀,歐洲不斷上演著血腥的戰爭,飽受戰爭摧殘的歐洲社會在17世紀末陷入巨大危機。在歐洲諸國中,法國是受戰爭破壞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由于連續不斷地卷入戰爭并一再失利,嚴重損耗了法國的國力,杜赫德舉出中國知識階層對戰爭的認識和態度,是對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統治階層的諷諫。他所提供的中國史實充實了歐洲知識界的思想,引起了極大反響,哥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1728—1774)在閱讀了《全志》后便把中國文人學者愛好和平和歐洲無休止的戰爭對比,指出不論從哪一個角度看,總有一條線索貫穿著整個歐洲歷史,就是罪惡、愚蠢和禍害,也就是政治沒有計劃、戰爭沒有結果。他借由中國哲學家之口,諷刺愛好和平的基督教君主陷于戰爭—媾和—戰爭的循環之中,戰爭不能解決問題,媾和也不能保證和平,窮兵黷武并不能帶來長治久安。⑥范存忠:《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75、176頁。
結語
長期以來,耶穌會士對中國形成了一脈相承的認識,在他們看來,中國是一個很少或沒有興趣擴張版圖的民族,這個國家由文人學者等知識階層來管理,人們對學者型官員極為尊敬,而軍人的地位相對較低。在中國,戰爭政策由文人學者規劃,軍事問題也由文人學者決定,他們的建議和意見比軍事領袖的更受皇帝重視。因此,凡是有教養的人都不贊成戰爭,他們寧愿做最低等的文人,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⑦《利瑪竇中國札記》,第59—60頁。中國忽視對武裝力量的建設,軍隊毫無英勇氣概,軍事訓練如同玩笑,科舉僅以文章取士,因而造成重文輕武的風氣。⑧曾德昭(Alvaro Semedo)著,何高濟譯:《大中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19—120頁。
杜赫德在《全志》中勾勒出一個文治昌盛、不尚武功的宋朝形象,它幾乎是傳教士此前建構的中國形象的縮影:這是一個具有高度文明的國家,不僅物質條件優裕,而且文化發達,同時沒有歐洲歷史上綿延不斷的戰爭。宋朝統治者崇尚文化、尊重知識、敬重知識階層,構成一個充滿人文精神和理性氣質的群體,在他們的扶植下,宋代文化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杜赫德記述了宋朝君主“敬孔”的種種舉措,一方面可以視為宋朝君主重教育、重文治的證據,另一方面也充斥著強烈的宗教色彩,他的目的是說明祭孔完全是一種世俗性的活動,與偶像崇拜有根本性的差異,從而為處在“中國禮儀之爭”中的耶穌會辯護。正因為這種目的,杜赫德對史料進行了有目的地剪裁和改寫,歪曲了史料的原意,泯滅了事件原本的歷史意義,使他的敘述未能揭示宋代歷史的特質,也未能真正觸及宋代歷史深層的脈動。
杜赫德對宋代歷史的敘述,服務于其樹立一個文明開化的帝國形象的總體目的,因此在涉及宋朝與周邊民族政權的戰爭時,他對宋朝多方回護。宋太宗兩次北伐、兩宋之交的宋金戰爭,宋朝都經歷了慘痛的失利,但在《全志》中卻很難看到此類痕跡,杜赫德顯然不愿意過多渲染“中國”在對外戰爭中的頹勢,以免引起西方讀者的輕視。戰爭本身不是杜赫德想要考察的主要對象,他對戰爭的描述不是要探究戰爭的起因、經過、影響,而是借助戰爭的背景來傳遞宋人的智慧和美德。這樣一種宋代中國的形象,并不完全來自于宋朝史料,同時也是對歐洲特別是法國國內連續不斷的戰爭的反鑒,是對歐洲統治階層的勸誡。杜赫德對宋代知識階層對待戰爭的態度和看法的描述,在歐洲知識界確立了一個“重文輕武”的宋朝形象,同時也充實了歐洲知識界的思想,使得宋代中國成為反襯歐洲社會的一面鏡子。
美國《近代中國》(雙月刊)2018年第3期重要文章介紹
《近代中國》(Modern China)是美國中國學研究重鎮之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編輯的一份以現當代中國為研究對象的重要學術期刊,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的歷史。在最近即2018年5月出版的今年第3期中,刊載了以下重要文章:《20世紀30年代陜北的英雄、烈士與土匪:劉志丹及其“草莽政策”》(作者:Xu Youwei, Philip Billingsley)、《后毛時代北京建筑垃圾傾倒的政治經濟學》(作者:Shih-yang Kao, George C.S.Lin)、《當代中國的儒家教育“精神”:嵩陽學院與鄭州大學》(作者:Linda Walton)。其中,《20世紀30年代陜北的英雄、烈士與土匪:劉志丹及其“草莽政策”》認為,由于無法招募到足夠多訓練有素的青年,劉志丹只得試圖籠絡盡可能多的土匪,而這些土匪均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本地區政治動蕩、環境惡劣的產物。然而,中國人對土匪普遍持有的惡感導致了其戰友對該政策的排斥心理。該文通過劉志丹與陜北三位土匪頭目的關系來審視其為了革命進行廣泛動員的策略。《后毛時代北京建筑垃圾傾倒的政治經濟學》通過在北京的田野工作,顯示了這個都市的管理層長期以來對垃圾處理的忽視是如何為社會基層的自我保護策略創造回旋余地的,以及市政府主管城市衛生的各個部門是如何通過公開著名攝影家所拍的建筑垃圾傾倒亂象的照片來明確其立場的。作者希望通過該個案來凸顯農村在城市環境轉變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及其與一個正在改革進程中的國家的互動關系。《當代中國的儒家教育“精神”:嵩陽書院與鄭州大學》聚焦北宋四大書院之一的嵩陽書院重張后與鄭州大學的關系,以及省政府與大學管理者合作開設依據儒家教學理念設計的國學課程,來審視當前中國熱議的現代大學教育與儒教、國學的關系以及主流意識形態下的文化管理與文化策略問題。(秋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