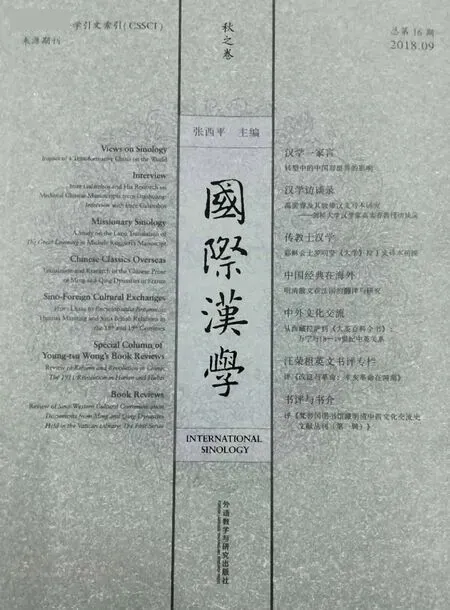評《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
□
要寫出一部關于辛亥革命的通史依然很困難。但是,最近以省級個案為重點的研究,為這一課題開展全面且令人滿意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如冉玫鑠(Mary Backus Rankin)對浙江的分析(1971)和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對廣東研究(1974)。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關于中部省份——湖南和湖北(歷史上著名的武昌起義于1911年10月在此爆發)——的專論,對最近這一學術研究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增補。
《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闡釋出色,資料來源豐富,可能是有關這一課題最成功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熟習一手與二手文獻,這些文獻來自中國、日本和歐洲幾乎所有可能的資源。正是基于此,作者有理由聲稱,他以全新的視角呈現了迄今為止對兩湖的辛亥革命最合理的思考。
令人印象更為深刻的是該書重要且全新的突破——那些引發爭論的觀點。如同最近其他一些研究辛亥革命的學者一樣,周錫瑞追溯了改良運動的發展進程,強調其與革命的重要聯系。改良派組織,例如省咨議局,“成了城市改良精英政治權力的制度表達。這種權力將引導精英們在辛亥革命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①Esherick, op.cit., p. 91.但是,周錫瑞還是以一種更為具體的方式論證了他的觀點:“改良與革命的關系多種多樣……1898年至1900年以挫敗為主題,改良者們遭受挫折與失敗,為實現他們的目的而轉向革命;1901年至1906年以催化為主題,旨在挽救民族危亡而制定的改良措施創建出了新的社會團體……這催化了政治穩定的衰落,促使其陷入更為嚴重的危機當中。”②Ibid., p. 142.
大體而論,該書最大的優勢在于對革命背后一股新社會力量的發現,即對民眾的發現。這樣一來,作者將以前被學者們忽視的改良運動的最大反對力量作為關注焦點。由于各種新政改革都產生開銷,并且比較貧困的階級常常要為這些只有利于上層階級的新政付費納捐,因此,在辛亥革命前夕,發生了“一系列反對新政的民眾暴動”。①Ibid., p. 7.周錫瑞也沒有忽略一個重要的因素——西方帝國主義。例如,在革命爆發之前,激烈的長沙搶米風潮,具有“反新政與反帝國主義相結合的鮮明特征”。②Ibid., p. 137.
源于反新政和反帝國主義的民眾暴亂促成了革命,從而削弱了舊政權。但是,當地城市精英,極力追求社會安定而選擇革命,卻成為辛亥革命真正的勝利者。他們不僅在革命中幸存了下來,而且還保持了其社會和政治影響力。這樣的評估很精準,也部分闡釋了革命失敗的原因。最后,周錫瑞給出了一個非常精辟的總結:
從這個意義上說,1911年辛亥革命的確確立了一種貫穿于大部分現代時間的趨向:一種由西方化的城市精英統治的趨向。然而,毛澤東并沒有延續這種趨向,他將其逆轉過來了。③Ibid., p. 259.
然而,像許多其他不錯的書一樣,這部優秀的研究著作并非無可挑剔。雖然作者使用中文史料的能力大體令人滿意,一些翻譯也確實巧妙,但是,在處理一些比較晦澀難懂的文章時,他顯然有些捉襟見肘。比如,有感于民眾暴力給地方紳士帶來的重大問題,他將紳士學者王闿運日記當中的一段話譯為:“隨著目前襲擊和盜竊的浪潮,無數人舉家搬遷。”由此,作者推論出“富人從農村的混亂中逃離,農村暴力進一步推動了紳士精英城市化的進程”。④Ibid., p. 119.事實上,與此相反,王闿運的這段話應解讀為:“目前的盜匪浪潮并不少見,因此,舉家遠走不明智。”這個例子顯示出對單一段落的誤讀有時會導致矛盾性闡釋。
另一處對王闿運日記的引用也值得商榷:
鄉人聽說應當借錢(來購買和囤積糧食),努力爭取獲得利息。投一可掙得上千銀兩。這樣,可見糧價上漲的利處。我告訴他(振湘,一個親戚)增加租金,且命令他動作要快。⑤Ibid., p. 126.
相反,這段話在原文中表明,由于糧食價格高漲,農村人有額外的資金放貸來獲取利潤。鑒于此,王闿運要求振湘增加租金,原因很簡單,就是佃戶有能力支付更多的費用。因此,如下表述顯然會更好:
聽說借錢有利可圖,農村人爭求著借錢放利;一呼可數千金。
周錫瑞其他一些論述或許可以以一種更加成熟的方式來呈現。
1. 沒有必要給出這樣生動的描述:“(在19世紀)湖南被視為中國保守主義和排外主義的中心,而在20世紀,它獲得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名聲。”⑥Ibid., pp. 2—3.要證明湖南一直就是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之間的戰場,找例證很容易。
2. 唐才常(1867—1900)的1900年起義是否可以被稱為一次革命非常值得懷疑。⑦Ibid., p. 11.將一次試圖讓皇帝重新掌權的起義貼上革命的標簽,似乎具有諷刺意味。
3. 第34頁關于改良派轉到革命立場的討論過于簡單,應該考慮到改良派從真正的轉變到不情愿地參與而采取的一系列“革命”主張。
4. 第54頁腳注中,作者評述:“革命聯盟這樣暗示性的解讀具有誤導性。1905年,同盟會成立,孫中山提出在名稱中包含‘革命’一詞的建議被明確否定。因此,譯者將其復原,似乎不可取。”事實并非如此。“革命”一詞被摒棄,不是因為其他革命者不喜歡,而是因為日本當局不認可。
5. “湖南熟,天下足。”⑧Ibid., p. 125.應解讀為“兩湖豐收,則天下糧足”。
6. “南京的收復即將到來”應解讀為“占領南京似乎指日可待”。因為革命派并沒有失去這座城市,因此不存在收復的問題。
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是,作者認為“歷來被輕視為‘東洋矮子’的日本”是“清廷之前的附屬國”。①Ibid., p. 11.對于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來說,這幾乎是常識——日本從來都不是清廷的附屬國。令人驚訝的是,這種顯而易見的錯誤竟然沒有引起作者論文導師的注意,在該書稿出版前所進行的嚴謹的修訂過程中也沒有注意到。
然而,盡管有些不足之處,周錫瑞的《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對目前的學術研究和理解是一個重要的補充。它是一部有價值的社會歷史著作,而且是現有最杰出的社會歷史著作之一。
《孔夫子:中國的道德》(Confucio, La morale della Cina,2016)出版
《孔夫子:中國的道德》(Confucio, La morale della Cina,2016)由羅馬智慧大學伊莎貝爾·圖魯利(Isabel Turull)教授從西班牙文手稿轉寫,并翻譯成意大利文,之后由意大利漢學家歐金尼奧·羅薩度 (Eugenio Lo Sardo) 先生對其進行簡要的注釋,并增加一篇長文進行說明。羅薩度先生此前曾在意大利羅馬國家檔案館(Archivio di Stato di Roma)工作,對早期入華的意大利籍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頗有研究。1993年,他編輯出版了該檔案館所藏的《羅明堅中國地圖集》(Atlante della Cina di Michele Ruggieri)。此次由他編輯出版的《孔夫子:中國的道德》亦是羅明堅于1590年在馬德里拜見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Feilipe II, 1527—1598)時翻譯而成。該手稿作為禮物敬獻給西班牙國王,并題書名為《論君子之學:在中國被普遍稱為四書中的第一部》(Disciplina de los Varones. Libro primero de los que comunemente se dizen en la China los quatro libros)。
《孔夫子:中國的道德》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導言”(Introduzione)、羅薩度的“孔夫子、王和傳教士”(Confucio, il re e il missionario)、伊莎貝爾·圖魯利的“有關譯自西班牙文的注釋”(Nota sulla traduzione dallo spagnolo)和正文“孔夫子”(Confucio)。羅薩度先生在其所寫的這篇文章中,主要是重構羅明堅翻譯中國《四書》的歷史原委,將其置于羅明堅在華傳教的歷史背景之中,包括其與在亞洲之巡視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神父、西班牙傳教士桑切斯(Alonso Sánchez, 1547—1593)和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關系。作者認為,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之所在,也是入華之歐洲人理解中國之核心。羅明堅翻譯《四書》,并獻給西班牙國王,其意便在于此。然而,中國和西方彼此之間仍有很多有待學習和理解之處。該書的正文部分“孔夫子”,并非譯自《四書》全文,僅僅是節選部分,包括《大學》《中庸》以及兩章《論語》。部分內容下面有羅薩度先生的簡單注釋。即便這是一部不完整的《四書》,缺少《孟子》,但仍舊是目前所知的早期耶穌會士向西方政治家介紹中國文化的《四書》手稿。(木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