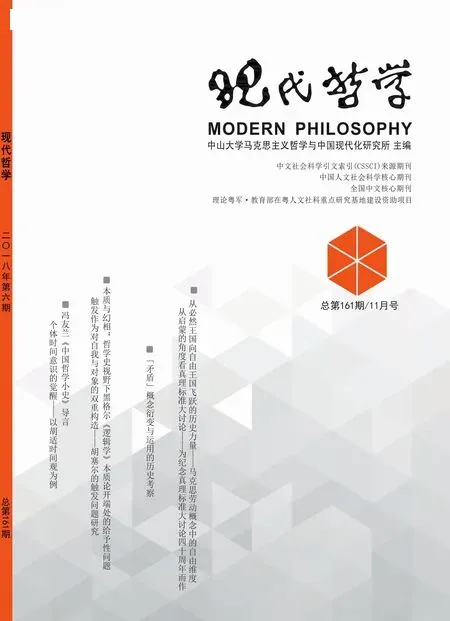個體時間意識的覺醒
——以胡適時間觀為例
方 用
一百年前,自美國留學歸來的胡適在《歸國雜感》中說:“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注]胡適:《歸國雜感》,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28頁。他認為“不值錢”的時間意識導致國人陷溺于不思進取、虛擲光陰的生活狀態,不僅踐踏了個體生命的尊嚴和價值,也將把風雨飄搖的國家帶入更危險的境地。個體和國家衰敝的現狀和期待“再生”的熱望,引起他對時間和生命的多重思考。在他看來,時間造就生命,一種新的時間觀將賦予個體生命以新的內涵和尊嚴,并引發文化的變革和社會的改造。
一、“進化的觀念”
晚清以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警醒了部分國人,亡國滅種的危機逼迫這些“先知先覺”者告別相對穩定的時間意識和生活狀態。風行一時的《天演論》正在重塑他們的世界觀,逐漸形成一種奠基于進化論的時間觀。龔自珍《己亥雜詩》之四四曰:“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但在胡適看來,中國傳統的“古時丹”已根本無法應對“今”之病:“今日吾國之急需……以吾所見言之,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歸納的理論,二曰歷史的眼光,三曰進化的觀念。”[注]胡適:《留學日記》卷3,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1頁。
胡適是進化論思潮的虔誠擁篤者:“進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的結果,便發生了一種‘歷史的態度’……研究事務如何發生,怎樣來的,怎樣變到現在的樣子:這就是‘歷史的態度’。”[注]胡適:《實驗主義》,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95頁。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過去、現在、未來構成時間的三維,三維的更迭即是歷史的進程。胡適以“進化”為原則來理解和評判過去、思考現在、探尋未來。“進化的觀念”是胡適時間觀的基礎,是其“歷史的眼光”的核心,是其救亡圖存最重的要藥方。
以“進化”為基礎的時間觀首先強調“時代性”,主張一切因時而變,古今異質。由此,“過去”之維被限定,“現在”之維得以凸顯。胡適早年以“文學進化之理”為據倡揚“文學改良”:“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注]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頁。文學改良之“八事”重在點醒古今之別,如“不摹仿古人”“不用典”等,都主張今人應直面生活的“現在”之維,以創新的形式、現代的語言,書寫這個時代真實的見聞思為,即“現在的中國人”應該創造“現在的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只有主動適應時代的更迭、積極書寫時代的精神,文學才能走出“古”的陳窠,獲得“今”的新生。他提出韻文有“六大革命”,其“革命”二字重在凸顯不同時代文學形式的差異性:“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跡。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自其循序漸進之跡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注]胡適:《嘗試集/自序》,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9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3頁。
文學改良只是當時風起云涌的“新思潮”運動的一個窗口。作為“今”的代表,“新思潮”被賦予復雜的內容和重要的時代意義。胡適指出,對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注]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03頁。,并明確將“評判的態度”視作“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和共同精神。“評判的態度含有幾種特別的要求:(1)對于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2)對于古代遺傳下來的圣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的嗎?’(3)對于社會上糊涂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應該這樣做嗎?……’”[注]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99頁。
整理國故,雖然首先是回到產生、盛行那個思想的具體時代,但更重要的是要評判是非、重估價值。眾所周知,進化論的風靡同時帶來一種“進步”的信念,表現在時間觀上,即主張古今有別,進而強調自古及今是一個推陳出新、日益增進和提升的過程,古不及今。這種不可逆的線性時間觀不僅嘲笑“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不變論,也有別于傳統的循環、輪回思想,更沖擊了各種以古為尊世風日下的歷史倒退論。
顯然,“評判的態度”的前兩個要求都主張站在“今”的立場,重新估定“古”的價值,以“現在”“今天”為標尺來審視歷史、文化的合理性并判定其命運。“時代性”意味著古代文化只在已逝的某個特殊時期有價值,但其價值不會伴隨歷史的洪流進入現在。“進步性”則闡明不管古代文化過去如何輝煌,終究遠遠落后或低于現在及未來的文化。
由于進化的觀念所強調的時代性和進步性,“國故”終究只是過去式,無法真正從“古”來到“今”。胡適說文言文是“死文字”,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現代文學。他主張“歷史的真理論”,認為真理的價值只是“擺過渡,做過媒”,可以隨時換掉、趕走。這樣的“國故”即使被“整理”出來龍去脈,其價值最終也極易被“評判”為陳設在博物館的、沒有生命的展品。時間之流終究被“評判”之利刀斬斷為古今的堅硬對峙,已“死”的過去走不進現在和將來的生命。所以,“評判的態度”不僅要求人們認清古今變易的大勢所趨,更要做“反對調和”的“革新家”,將目光聚焦于現在與未來。在胡適看來,生乎今之世而反古之道,是有違進化之跡的背時逆流。
五四運動喚醒了“我”,胡適堅信“唯有個人可以改良社會,社會的進化全靠個人”[注]胡適:《學生與社會》,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91頁。。“評判的態度”第三條把“社會”和“我”對立起來,“社會公認”不僅指人數多,也指通過權力、習俗等被固化的“過去”。胡適期待的“我”是“先知先覺”的少數人,“我”要有獨立精神,敢于質疑、敏于思考。“我”是能走出過去的枷鎖,尋找和創造未來的人。
進化論者一般認為,青少年是未來和希望的代表。例如,梁啟超歌頌“少年中國”,李大釗呼喚“青春”,陳獨秀情系“新青年”,都是這種時代精神的體現。胡適對年輕人也充滿熱情與期盼。他同情學生,自稱是“愛護青年的人”;呼吁“中國的少年”起來建造“少年的中國”,滿心歡喜地表彰“后生可畏”[注]“后生可畏”本是胡適對《大公報》的寄語。他把不滿二十八年的《大公報》稱作“小孩子”,把快六十年的《申報》和快五十歲的《新聞報》稱作“老朽前輩”,贊賞《大公報》為“后生可畏”。這也是胡適對年輕人的期待。(胡適:《后生可畏》,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78—179頁。)。
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青少年和老年往往構成不同時間維度的代表。但在胡適看來,“年齡”不是判定“老”的唯一尺度。暮氣沉沉的少年無法肩負將來[注]胡適對年輕人的“暮氣”非常憂心:“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觀,其取別號則曰‘寒灰’、‘無生’、‘死灰’;其作為詩文,則對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惟恐其速去,花發又惟懼其早謝;此亡國之哀音也。老年人為之猶不可,況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養成一種暮氣,不思奮發有為,服勞報國,但知發牢騷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將以促其壽年,讀者將亦短其志氣:此吾所謂無病之呻吟也。”(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8—9頁。),年歲漸增也可以老當益壯。他鼓勵年輕人要保有朝氣,勇立潮頭。他送給畢業生的臨別贈言是“不要拋棄學問”“趁現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努力去做一種專門學問”[注]胡適:《中國公學十八年級畢業贈言》,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77頁。。基于進化論以及“進步”的觀念,他相信一代總能勝過一代,提醒他們若沒有足夠的危機意識,必將被后進的少年無情地淘汰。在他看來,想在社會掙得一席之地,防止在不如意的現實中墮落,個體必須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
同時,胡適為不可阻擋的歲月中人開出一劑“精神不老丹”:“這個‘精神不老丹’是什么呢?我說是永遠可求得新知識新思想的門徑。這種門徑不外兩條,(一)養成一種歡迎新思想的習慣,使新知識新思潮可以源源地來;(二)極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養成一種自由的空氣,布下新思潮的種子,預備我們到了七八十歲時,也還有許多簇新的知識思想可以收獲來做我們的精神培養品。”[注]胡適:《不老》,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85頁。如果一個人能夠不為“舊”所錮,堅持求“新”,不拒新知的滋養,不失創造的精神,即使“白頭”,也是時代的“新人物”,不會在進化大潮中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可見,一個人“年輕”的時間長度,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物理時間。容顏易逝,而精神可以日新。
與同時代的魯迅相比較,胡適更為樂觀。本著堅定的進化觀念,胡適對年輕人,以及中國社會未來一直充滿信心。此外,基于進化的時間觀強調古今異質,一切皆變而無物常住。在進化洪流中,任何存在及其價值都是有限的,象征終結的“死”必將隨“時”而至。“死”也意味著隨時間不息地奔涌向前,歷史的人或事必定滯留于既往,而被進化之流無情拋棄。所以,胡適主張“死了的文言”當“廢”,作為工具的真理用過可“換”。所謂“過去”不僅是時間的流逝,而且意味著與那“時”有關的生命的消失。因時而變、與時俱進,似乎標志著一切過去都將被斬斷、被忘卻。往日不可追,故人舊事隨之沉寂。那么,還有什么可以傳承?還有什么值得留戀?
二、“不朽”
胡適論“不死”。“不死”即“不朽”,指某些不隨時間的流逝而消失、磨滅的持久因素或永恒存在。“進化”強調因時而變,“不朽”則揭示古今更迭的相對穩定性、連續性。胡適將“不朽”奉為“我的宗教”“我的信仰”,指出他所謂“不朽”既非“靈魂不滅”,也有別于以立德、立言、立功三事為“雖久不廢”的傳統不朽論。他要闡釋的是一種新的不朽論即“社會的不朽論”:“這種不朽論,總而言之,只是說個人的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言語行事,無論大小好壞,一一都留下一些影響在那個‘大我’之中,一一都與這永遠不朽的‘大我’一同永遠不朽。”[注]胡適:《不朽》,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80頁。它最鮮明的特點是強調“所有人”的“一切言行”都是“不朽”的,在歷史長河中,每個作為個體存在的“小我”都有其“時”。他認為這種觀點正能對治傳統“三不朽”的三大缺點:
第一,“不朽”的內容涵括了所有人的一切言行,這明確和推廣了過去含糊有限的僅以“功、德、言”為范圍的觀點。胡適認為“功、德、言”只是人類活動中非常有限的內容,而基于進化論,“功、德、言”的具體內涵在不同的國家或歷史時期也不盡相同。
第二,胡適認為傳統“三不朽”中,真能立功立德立言終究只是少數人,所以只是“寡頭之不朽”;而他主張“所有人”,包括“無量平常人”都能不朽。胡適提出“社會的不朽論”的直接契機是母親的離世。他的母親是一個極普通的女人,也是對其影響至深的人。平常人,尤其是女人,在過去的歷史觀中是被忽略或遺忘的。但現代是呼喚平等、呼喚“無量平常人”走上歷史舞臺的時代。每個作為個體存在的“小我”在其一生有限的時間中,都會留下自己獨特的歷史印記。胡適的“不朽”擯棄了貴賤有別的生命價值和帝王將相的英雄史觀,把普通人納入歷史主體的范疇,這無疑展現了平等的時代精神。對他個人而言,母親是他一生最難忘最溫暖的懷念。
第三,胡適認為傳統“三不朽”僅就功、德、言而立論,“沒有消極的裁制”。他強調一切言行,無論大小、成敗、善惡,都將在歷史中產生影響、留下印痕,雖然可能程度不同、性質有別。無數“小我”相互聯結、彼此承繼,構成歷史的“大我”,但這個為“小我”之“紀功碑”或“惡謚法”的“大我”很像唯識學中具有“藏”功能的阿賴耶識[注]“初阿賴耶識……是無覆無記……恒轉如瀑流……”([印]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唯識三十頌》)。作為輪回主體的“阿賴耶識”連接了“我”一期一期的生命,“無覆無記”即阿賴耶識作為種子將不辨善惡地記取“我”造作的所有業,“恒轉”即這些種子作為“因”將永恒存在,并在來世產生“等流”即同等性質的“果”。因果相牽,自作自受,世世流轉。當然,胡適不論輪回轉世的問題,其“大我”也并非作為某一個具體生命個體即“小我”的延續。。胡適強調“小我”的一切言行都將不朽。“善”將積極地推進歷史前行,是不朽的善因,將造福于后世的“小我”;而“惡”同樣有力量消極地阻礙歷史腳步,結下不朽的惡果。名垂千古或遺臭萬年都是“不朽”,因為“這一個現在里面便有無窮時間空間的影子”[注]胡適:《不朽》,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78頁。這是胡適經常引用的來勃尼慈(Leibnitz,現多譯作萊布尼茲)的話。。由此,胡適強調每個個體的歷史責任感:“我這個現在的‘小我’,對于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過去,須負重大的責任;對于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未來,也須負重大的責任。我須要時時想著,我應該如何努力利用現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負了那‘大我’的無窮過去,方才可以不遺害那‘大我’的無窮未來?”[注]胡適:《不朽》,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81頁。
胡適強調身處“現在”、作為獨立個體存在的“小我”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者:在空間上,其與社會或世界的全體互為影響;在時間上,其和社會世界的過去和未來都有因果關系。現在的“小我”是過去無數“小我”的各種“前因”而共同產生的“后果”,其間保留了過去“小我”的種種印記。現在的“小我”又是造就將來“小我”的“前因”,會把現在“小我”的種種印記傳遞到將來。無數的“小我”構成一脈相承永遠接續的“大我”。作為個體的“小我”生命有限,必死無疑,但由無窮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小我”代代相傳所形成的“大我”卻是連綿不絕,永遠不死的。
所謂“大我”之不朽,即通過因果關系的普遍性、必然性,以及前因后果的時間上的延續性,揭示“小我”在時間流逝中對個體和他人的種種廣泛持久的影響、作用。“進化”強調古今異質,側重過去、現在、未來三個維度的推陳出新、替代更迭。“不朽”凸顯了那些貫串于過去、現在、未來三個維度中并逐漸沉淀和持久留存的因子。任何的“小我”都只能在時間洪流的某一個特殊而有限的階段活著,但這個“小我”裹挾著某些不隨時間的前移而消逝的因素或力量,與已逝的過去、將至的未來因果相連。這些留存在歷史進程中的“紀念品”或“遺形物”[注]“文學進化的第三層意義是:一種文學的進化,每經過一個時代,往往帶著前一個時代留下的許多無用的紀念品;這種紀念品在早先的幼稚時代本來是很有用的,后來漸漸的可以用不著他們了,但是因為人類守舊的惰性,故仍舊保存這些過去時代的紀念品。在社會學上,這種紀念品叫做‘遺形物’(Vestiges or Rudiments)。”(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9頁),既是“小我”的“不朽”,又通過因果相續把無數已“死”或將“死”的“小我”串聯為“不朽”的“大我”。
為什么胡適特別強調“惡”也會不朽?這首先緣于直面和反省落后挨打的苦難現實。一方面,“我”現在遭受的一切苦難,正是過去懶惰不負責的“我”造成的,因而是現在的“我”無法逃避的“消極的裁制”,每個現實中具體的個體都只能背負著歷史前行。另一方面,現在的“我”必須很努力很謹慎,不能荒廢過去累積的善果,更不要種下未來必報的惡因。更重要的是,在進化論者看來,一切價值也因時而變,過去曾經的“善”在新的時代可能無用甚至成為阻礙時代遞嬗的“惡”的力量。現在的“我”如果不能從因循守舊的惰性中掙脫出來,努力創造新的“善”,未來的“我”將更積重難返寸步難行。可見胡適所謂“消極的裁制”,既指歷史進程中,現在的“我”無法推卸的、過去所遺留和累積的“惡果”,也指由現在的“我”的不思進取或為非作歹所引導的、必將成為未來的“我”不能逃脫的厄運或宿命。他確信“我們對于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系”[注]胡適:《易卜生主義》,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32頁。,強調“惡”亦不朽,意在喚醒每一個現在的“我”的歷史主體性和責任感。
誠然,胡適“社會的不朽論”籠統而粗疏,甚至帶有濃厚的佛教因果觀的色彩。但他納一切有限的“小我”于無窮的“大我”,由“大我”的“長生不死”,將“所有人”及其行為都平等地納入歷史進程;并通過對“消極的裁制”的凸顯,旨在呼喚當下每個個體即“小我”的歷史責任感,主動承擔過去的背負,也于現在積極努力地造善因集善緣,以避免未來更嚴酷的消極裁制。我們可以認為“功德蓋世”與“吐一口痰”都是“不朽”只是虛說,重要的是,每個個體都應該從“我”開始,從現在的點滴開始,勇于擔責,善于創造,即納須臾于永恒。這樣的個體才是真正推動歷史、積極對歷史負責的“小我”,由這樣的“小我”所構建的歷史才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大我”。
值得注意的是,標志時間和生命永恒的“不朽”,其背后挺立的仍是堅定的“進化”意識,被強化的仍是“現在”之維:不僅要勇于承受由無量“過去”之“因”積累而成的“現在”之“果”,更要努力從“現在”開始,改造舊社會,創造新氣象,能否推陳出新、推動社會進步仍是判斷“現在”之“小我”一切言行善與惡的唯一標志。“不朽”之“消極的裁制”強化了進化過程中歷史主體的參與意識。
胡適在晚年的一篇演講中指出:“我今天提議,不要把中國傳統當作一個一成不變的東西看,要把這個傳統當成一長串重大的歷史變動進化的最高結果看。”[注]胡適:《中國傳統與將來》,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71頁。“傳統”是“變”中之“常”,“把前代的創獲給我們保存下來,并傳給我們”[注][德]黑格爾著,賀麟、王太慶譯:《哲學史講演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8頁。。“傳統”凝結了歷史演進中相對穩定、世代傳承的文化或精神,即那些“不朽”的因素。如同強調“不朽”有“消極的裁制”,“傳統”在他看來也未必都是“神圣”的,中國傳統也有“種種長處和短處”。與“進化”結盟的“傳統”,不僅要指出某一具體傳統是如何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逐漸形成的,也要關注歷史的進化是如何造成傳統的進化。文化史就是從舊傳統中引出新傳統,新傳統又取代舊傳統的過程。
所以,“不朽”并不意味著單純的紀念或懷舊,而是意味著以“進化”為原則,主動地打破、革除舊文化的枷鎖,自覺地推進、創造新文化的進程。“傳統”之“常”并非凝固不變的,堅守傳統也并非固執舊制。所謂進化的“傳統”,是在積累和淘汰、吐故與納新、復興和創造中不斷生成的。
在胡適看來,當下的中國文化新傳統正在形成。但此傳統不可能拒絕西方文化的深刻影響。他特別指出:“這個再生的結晶品看起來似乎使人覺得是帶著西方的色彩。但是試把表面剝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這個結晶品的材料在本質上正是那個飽經風雨侵蝕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徹的中國根底,——正是那個因為接觸新世界的科學民主文明而復活起來的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我深信那個‘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的傳統沒有毀滅,而且無論如何沒有人能毀滅。”[注]胡適:《中國傳統與將來》,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81—183頁。在胡適心中,“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是中國文化之根,是中國文化真正的“不朽”,是延續千載、雖隱不絕的真“傳統”。
三、“經濟”
動蕩的時局,救亡的迫切,容易使時人產生歲不我與的焦慮,基于“進化”的時間觀更強化了時不我待的緊張。歸國的胡適對“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無奈而痛心。與現代西方大機器生產的高效率形成強烈反差的是,他所目睹的中國工人依舊非常落后低效的生產方式和工作狀態:“上海那些揀茶葉的女工,一天揀到黑,至多不過得二百個錢,少的不過得五六十錢。茶葉店的伙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鐘的工,一個月平均只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還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注]胡適:《歸國雜感》,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28頁。工作時間長、強度大,付出的時間成本很高,結果不僅勞動者個人的收入極為卑微,所創造的社會價值也非常有限。這樣的生產又如何能使民眾走出貧困,使國家走向富強?進而,胡適指出,低報酬的時間意識背后是對生命本身的漠視:“美國有一位大賢名弗蘭克令(Benjamin Franklin)的,曾說道:‘時間乃是造成生命的東西。’時間不值錢,生命自然也不值錢了。”[注]胡適:《歸國雜感》,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28頁。生命的“不值錢”不僅指付出與收入的巨大差距,更指維持和護養生命的存在,以及尊重生命價值之觀念的嚴重缺失。大多數人沒有花時間保健康的意識,甚至連死亡也無關輕重。但沒有對死亡的自覺和敏感,人對時間尤其是個體時間的感受也是空洞淡漠和無所敬畏的,不懼死,亦不知生[注]“通過時間之流經驗,有死的人類實現了對自身有終性的自覺。對死的自覺,同時就是對生的自覺。弗雷澤說:人……是有死亡意識從而有時間意識的生物。”(吳國盛:《時間的觀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4頁)。
胡適還目睹那些不明白時間應該“值錢”的人們隨意地虛擲自己的光陰,無端地空耗別人的時間,卻從未意識到在無所事事的呆坐、漫無邊際的閑聊中,不僅自己的生命正在變得空虛荒蕪,同時也“謀財害命”[注]美國總統富蘭克林(胡適寫作“弗蘭克令”)的這句話在當時影響深遠。魯迅亦云:“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于謀財害命的。”(魯迅:《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99頁),剝奪了他人生命的存在和價值。胡適慨嘆國人依舊沉浸于這種遲緩凝固的生活狀態。有感于此,他從文學入手求變,力圖倡導一種“經濟”的時間意識。他認為短詩、獨幕戲和短篇小說是“世界文學的趨勢”,首要原因就是力求“文學的經濟”:“世界的生活競爭一天忙似一天,時間越寶貴了,文學也不能不講究‘經濟’;若不經濟,只配給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老爺太太們看,不配給那些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看了。”[注]胡適:《論短篇小說》,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3—104頁。隨著“無量平常人”登上歷史舞臺,文學已不再是有閑階層的專利。走向忙碌的普通大眾的文學必須在“最簡短的時間”之內,講述或演出完整的故事,給觀眾帶來疾風暴雨似的心靈震撼。這就是“時間的經濟”。
力求“經濟”的時間意識是進化思想的必然要求。“過去慢”,相對穩定的時代容易產生近乎停滯的甚至循環的時間體驗。但進化揭示的是古今嬗變新舊更迭,個體已被綁上急速變化不斷前行的歷史大輪,只有緊跟時代的步伐才能應付。胡適區分歷史進化的兩種狀態:“一種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種是順著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進,后者可叫做革命。演進是無意識的,很遲緩的,很不經濟的,難保不退化的。有時候,自然的演進到了一個時期,有少數人出來,認清了這個自然的趨勢,再加上一種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進,使這個自然進化的趨勢趕快實現;時間可以縮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為時間忽然縮短了,因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個革命。其實革命不過是人力在那自然演進的緩步徐行的歷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注]胡適:《白話文學史》,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8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39頁。
雖然進化是大勢所趨,但若一味聽其自然無疑只能“緩步徐行”,而“革命”是以“人力的促進”撤除進化的障礙,加速進化的過程,所以是很“經濟”的手段。“經濟”的時間觀意味著時間并非外在于人而均質流動的,在某些特殊的歷史時期,“人力”可能極大地影響時間的方向和效用:既可能人為地使自己的時間減緩停滯甚至從現在拉回過去,也可能奮起直追,奔向未來,在較短的時間趕上甚至超越經過較長時間發展的他者。
可見,所謂“時間差”并不具有絕對意義。欲實現時間的“經濟”,“人力”的自由選擇和主動參與非常重要。胡適有一種不怕“晚”的信心和樂觀,呼吁“先知先覺”的少數人行動起來,引領大眾學會甄別和順應進化的方向,學會以“經濟”的方式加快前行步伐。他堅信只要持之以恒,“我們在十年二十年里,也可以迎頭趕上世界各先進國家”[注]胡適:《迎頭趕上世界先進國家》,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98頁。這是胡適在抗戰勝利后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集會上的演講。。
當然,片面強調效率、以“經濟”作為時間的唯一價值,必將導致人心的躁動虛浮和功利主義的傾向。單純強調文學是“經濟的”,必然會疏忽心靈同樣需要淺吟低唱的舒緩與曠日經久的熏染“文學革命”有其獨特的歷史意義,但以之為文學發展的唯一方向,不免失之偏頗。盡管胡適強調“革命”及“經濟”的時間在進化中功不可沒,但也痛感人心急不可耐的危險。他曾多次提到“勤謹和緩”四字秘訣。“勤”和“懶”是兩種不同的處理時間的方式,“勤”在一定意義上是指充分、合理地利用時間,一點一滴,堅持不輟。他強調要堅持利用和積累零碎時間:“至于時間,更不成問題。達爾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點鐘的工作。你們看他的成績!每天花一點鐘看十頁有用的書,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頁書,三十年可讀十一萬頁書。”[注]胡適:《中國公學十八年級畢業贈言》,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77頁。個體要確立自己的生活目標,努力化零為整,積少成多,終至不斷豐富和提升自我。在他看來,個體生命的價值并非等同于生命的客觀長度,通過“勤”,有效時間增加了,生命的價值也提升了[注]胡適曾引用兩首詩:“中國的懶人,有兩首打油詩,一首是懶人恭維自己的:無事只靜坐,一日當兩日。人活六十年,我活百二十。還有一首是嘲笑懶人的:無事昏昏睡,睡起日過午。人活七十年,我活三十五。”與此相對的是他尊稱為“科學圣人”的愛迪生:“睡四點鐘覺,做二十點鐘科學實驗,活了八十四歲,抵的別人一百七十歲。”(胡適:《終生做科學實驗的愛迪生》,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631頁)。“緩”并非松散、懈怠,而是能不為外在的時間所逼迫,確保自己內心沉穩的節奏,不忙不亂,不急功近利,不心浮氣躁,放慢速度,耐住寂寞,平心靜氣、從容處事。他特別指出:“緩,這個字很重要,緩的意思不要忙,不輕易下一個結論。如果沒有緩的習慣,前面三個字都不容易做到。”[注]胡適:《中學生的修養與擇業》,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74頁。“忙”者易“盲”,“緩”才能無征不信,杜絕武斷,慢工出細活。在胡適看來,“勤謹和緩”不僅是治學之方,也是為人行事之道。
可見,“經濟”的時間觀所指向的并非絕對客觀時間的長短,更多的是強調個體能合理而有效地支配自己的時間以期獲得最大的收益。“經濟”的時間觀給予他迎頭趕上的信心和樂觀,“勤”“緩”的處事態度又使其避免盲動及失敗帶來的徘徊和絕望。胡適再三強調“歷史的眼光”的重要性,主張既要通過客觀的比較,評判國家和個人在有限的時間中所取得的進步;也要了解事之艱辛、路之坎坷,破除“奇跡”降臨的妄想[注]胡適多次著文討論信心與樂觀的問題。例如,“今日最悲觀的人,實在都是當初太樂觀了的人……悲觀的人的病根在于缺乏歷史的眼光。因為缺乏歷史的眼光,所以第一不明白我們的問題是多么艱難,第二不了解我們應付艱難的憑借是多么薄弱,第三不懂得我們開始工作的時間是多么遲晚,第四不想想二十三年是多么短的一個時期,第五不認得我們在這樣短的時期里居然也做到了一點很可觀的成績。如果大家能有一點歷史的眼光,大家就可以明白這二十多年來,‘奇跡’雖然沒有光臨,至少也有了一點很可以引起我們的自信心的進步。”(胡適:《悲觀聲浪里的樂觀》,《胡適文集》第5冊,第365—366頁)。
相較而言,胡適更愿意用“改良”替代“革命”,重視“建設”勝過“破壞”。他相信進化是一個“很緩慢的過程”,主張“一點一滴的改造”。堅持“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注]胡適曾在1916年1月25日的日記中表明心跡:“適以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后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于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明知樹人乃最迂遠之因,然近來洞見國事與天下事均非捷徑所能為功。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為迂遠而不為,則終亦必亡而已矣。”(胡適:《留學日記》卷12,胡適著、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2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6頁。),以“勤”“緩”為美德。他一直比較警惕“革命”的破壞功能,反對走捷徑,反對“早熟之革命”。他主張“以學術救國”,認為“要科學幫助革命,革命才能成功”[注]胡適:《學術救國》,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03頁。。這既有其實驗主義的哲學背景,更與他以科學理性為基來理解時間、生命的密切相關。
四、“閑暇”
如前所述,“我”的覺醒也包括“我的時間”的覺醒,即“我”應該有自由支配“我的時間”的權利和能力。時間造就生命,而“我的時間”造就了與眾不同的“我”。
胡適重視每個作為個體存在的“小我”,反對在歷史進程或社會活動中無視“小我”的作用,或以任何名義淡漠甚至犧牲“小我”的論點。在他看來,每個“小我”時間都是無窮時間中“大我”必不可缺的一環,前有古人,后有來者;每個“小我”的生命歷程在進化之流中都會留下各種“不朽”,參與影響或構建創造歷史的活動。“小我”的一生并非只是來世間空耗了一段與己無關的“時間”。
因為確信現在的“小我”與無窮時間的“大我”的緊密聯系,胡適反對各種將“小我”游離于他人或現實之外的觀點[注]胡適認為個人主義有三種:一是“假的個人主義”,這是一種“自私自利,只顧自己利益,不顧群眾利益的為我主義(Egoism)”;二是“獨善的個人主義”,其性質是“不滿于現社會,卻無可奈何,只想跳出這個社會尋一種超出現社會的理想生活”;三是“健全的個人主義”。胡適認為只有最后一種才是“真的個人主義”。(胡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胡適文集》第2冊,第509-510頁)。他推崇以易卜生主義為代表的“健全的個人主義”,認為現代個體應該“須要充分發達自己的天才性;須要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注]胡適:《易卜生主義》,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40頁。。換言之,每個“我”都應該是因材造就且特立獨行的,甚至這就是基本人權之一[注]胡適曾說人權是“中國今日人人應該討論的一個問題”。“平社”時期,胡適、羅隆基等人合著《人權論集》,列出做人必要的條件即人權的三個要點,其中就包括“發展個性,培養人格”。(羅隆基:《論人權》,《胡適文集》第5冊,第492頁)。
另一方面,胡適反復強調“小我”若要真正有益于“大我”,必須先塑造自己,“你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注]胡適:《易卜生主義》,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41頁。。個體若不能堅定而充分地發展自我,就不可能積聚足夠的力量與社會或其他阻礙自我發展的勢力抗爭,既無法“救出自己”,也不能“霸占住這個社會來改造這個社會的新生活”,甚至會如《雁》中的少年,不僅無力走向將來,反而被歸化馴服,回到了過去。
顯而易見,一個為生計所困、每天必須長時間艱辛勞作的個體,幾乎不可能有自由支配的時間,更遑論發展有個性的自我。所以,時間的“經濟”是非常必要的。胡適重視科學的力量,贊嘆機器生產解放人力,期待通過改善生產方式提高效率,以便個體能在謀生的“工作時間”之外,騰出“閑暇”來發展“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與活動”。
胡適把“非職業的玩藝兒”稱為“業余活動”,把應付職業之外的時間稱為“閑暇”。他勸誡年輕人必須以“職業”謀生,但可不以“吃飯”為唯一目標,特別強調畢業后要“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即以自己的才性和興趣為研究學問的尺度,利用“閑暇”來發展“非職業的興趣”。他甚至認為一個人的“業余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古來成大學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善用他的閑暇時間的。特別在這個組織不健全的中國社會,職業不容易適合我們的性情,我們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墮落,只有多方發展業余的興趣,使我們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們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注]胡適:《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5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86頁。在有限的社會條件下,個體所從事的工作或環境很可能與個體的性情相違,因而工作時間的感受可能是不適的、厭倦的。但由“非職業的興趣”所充盈的“閑暇”卻是身處煩勞工作的個體的精神慰藉和生命期待。在“閑暇”中,個體從謀生的困苦中解放出來,充滿趣味和熱情地從事自己向往的活動,從中感受個性舒張的愉悅,享受稱心如意的快樂。在一種無壓迫無功利的自由狀態中,成功也常常不期而至。
當然,一個認為時間“不值錢”的個體也不會有珍惜時間的意識,不懂得如何創造和利用閑暇時間從事“正當”的活動。中國人從來不缺“閑”,關鍵在于如何“消閑”。這可能是魯迅所謂的“談閑天”,可能是王國維筆端的各種醫治“空虛之消極的苦痛”之方,也可能是胡適耿耿于懷的打麻將[注]胡適曾很悲憤地給打麻將算時間帳:“麻將平均每四圈費時間約兩點鐘。少說一點,全國每日只有一百萬桌麻將,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費四百萬點鐘,就是損失十六萬七千日的光陰,金錢的輸贏,精力的消磨,都還在外……只有咱們這種不長進的民族以‘閑’為幸福,以‘消閑’為急務,男人以打麻將為消閑,女人以打麻將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將為下半生的大事業……麻將,還是日興月盛,沒有一點衰歇的樣子,沒有人說它是可以亡國的大害。”(胡適:《漫游的感想》,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6—37頁)。面對“閑暇”,個體的自我選擇和堅持非常重要。“因為一個人成就怎樣,往往靠他怎樣利用他的閑暇時間。他用他的閑暇來打麻將,他就成了個賭徒;你用你的閑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閑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閑暇往往定你的終身。”[注]胡適:《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5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86頁。打麻將也是一種“消閑”方式,但沉湎于此,荒時廢業,甚或誤國。然若能潛心學問,或致力革新,假以時日,與己總有長進,與國亦有推動。
誠然,“職業”與“業余”、“經濟”與“閑暇”未必總是非此即彼地對立著。但“閑暇”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閑暇”與個體的自由相關。胡適強調個體的時間和生命不應為職業所限,個體應該爭取和創造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閑暇”。同時“閑暇”的利用取決于個體的自我選擇,個體應該充分利用閑暇以豐富自己的生活、發展自己的個性、提升自己的能力。“閑暇”時光正當的“業余”活動無疑是實現“健全的個人主義”的重要時間保證。胡適甚至視其為個體“保持求知的興趣和生活的理想主義”,防止在不如意的現實中墮落的“最好的救濟方法”。他特別喜歡“功不唐捐”一詞,在閑暇時間的付出終將在未來得以回報。種豆得豆,因果等流,個體如何支配閑暇,往往成就了個體獨特的生命內涵。無數“小我”匯合成“大我”,因而如何面對“閑暇”也成為國家文明的標志之一[注]“我的一個朋友對我說過一句很深刻的話:‘你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們怎樣待小孩子;第二,看他們怎樣待女人;第三,看他們怎樣利用閑暇的時間。’”(胡適:《慈幼的問題》,《胡適文集》第4冊,第587頁)。
五、結 語
胡適的時間觀以“進化”“不朽”“經濟”“閑暇”等為關鍵詞,顯然時間的客觀結構、特征不是其思考重點。“進化”強調古今異質以及革故鼎新的進步趨勢,這種不可逆轉的、線性的時間觀賦予個體追趕潮流、力求“經濟”的時間意識。“不朽”揭示古今相續,強調“小我”在無窮時空的延展中不可磨滅的影響,這既有對過往的尊重,或對守舊的抗爭,也有對未來的警示和擔當。“經濟”的時間強調高效,也使“閑暇”有了可能。
胡適認為生命的意義“在于自己怎樣生活”,若能堅定地“用此生作點有意義的事”,“活一日便有一日的意義,作一事便添一事的意義,生命無窮,生命的意義也無窮了”[注]胡適:《人生有何意義》,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71頁。。時間造就生命。他呼吁“無量平常人”要積極參與歷史進程,倡導“健全的個人主義”,即作為生命個體存在的“我”不僅要做“進化”洪流中圖存的“適者”,更要負責任地創造無窮時空中的“不朽”;不僅要有時間急迫感,追求“經濟”的時間,更要自主地駕馭“閑暇”時間,充分發展自我,實現個性。胡適對“個人”的大力弘揚,也標志著個體時間意識的覺醒。
與大多數進化論的信奉者一樣,胡適對年輕人和未來總是保有樂觀的。在古今中西的沖刷激蕩中,他反對過于迷戀過去、沉浸在中國古代所謂的“祖宗的光榮”,終其一生都在期待和致力于“中國再生”。“再生”是對時間和生命的一種特殊理解。少壯、衰老、死亡是生命規律,但“人類集團的生活和國家民族的文化之演進,雖也是由少壯而衰老而死亡;但是在衰老時期如果注射了‘返老還童’針,使獲得了新的血脈,那么一朝煥發新的精神,從老態龍鐘轉變而振作有為,于是,國族的各方面都表現了新的活動,這個時期,歷史家稱為‘再生時期’”[注]胡適:《中國再生時期》,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2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99頁。。在他看來,中國文化已充滿“老性”,暮氣攻心。雖然疲敝不堪、奄奄一息,但終究還有一條生路,那就是盡快輸入新鮮的“少年血性”。中國“再生”必須從“現在”開始,而現在的“少年”是睜眼看世界的一代,他們為中國創造新文化,是中國“再生”的新血脈。
20世紀中國思想界,既有以意欲為根基的時間觀(梁漱溟),也有以情感為時間奠基的唯情主義時間觀(朱謙之),更有以“道”為根基的絕對時間觀(金岳霖)和以心-本體為根基的時間觀(熊十力、牟宗三)。凡此種種,充滿意趣,給人以無窮的遐想與安慰,但終究可愛而不可信。圍繞現代中國與現代中國文化的重建,胡適以科學理性為根基理解時間,不僅可信,而且賦予過去、現在、未來以情感態度與價值,使冷冰冰的物理時間有了溫度、多了可愛。這是胡適時間觀的最大特點,也是他留給現代中國哲學的重要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