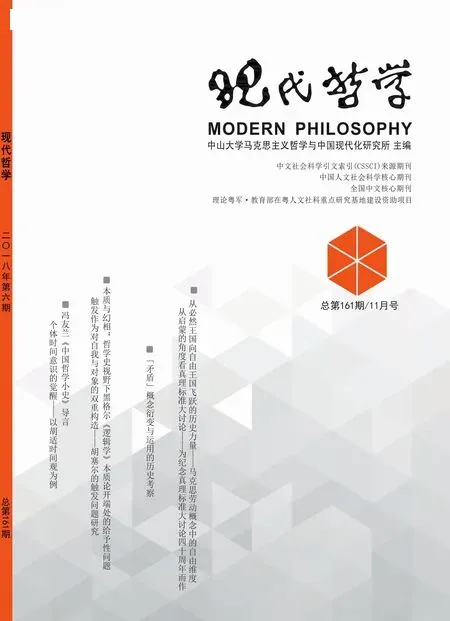人性的啟蒙
——何謂康德的純粹理性的建筑術?
張 廣
雖無法“高達蒼穹”,但仍須能使人“家居”[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35.本文標注頁碼并非引用書籍所標頁碼,而是按照研究習慣標注原著A、B兩版中的相應頁碼。。除去知識上似是而非的“幻象” (Schein),也還是“人得以為‘人’的規定” (Bestimmung des Menschen)。甚至,不論是賴以棲身的“房舍”,還是不可企及的“高塔”,只要是“建筑” 就已經表明:存在著一個主體營造自身的構想。因為,不管是否可能,作為人的“規劃” (Plan),“建筑”都是人造之物,都傳達了某種人對自身存在的處置。并且,在批判之中,也的確如此:理性的綜合不僅借助“直觀” 和“概念”的區分[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29、74、863.被發現為讓我們知識得以統一的“統覺” ,也借由對形而上學問題的解析被追溯為建構主體自身的“理想”。因此,作為說明理性如何建構的“方法論”,批判也就不僅是說明何謂“科學” 的“導引”(Prop?deutik)[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868.,也是一個闡明人之為“人”[注]Kant, Logik-Vorlesung, Hamburg: Meiner, 1997, IX,S. 25. 涉及康德其它著作,也按照研究習慣標注普魯士科學院版相應篇目縮寫與頁碼。的智慧的“啟蒙” (Aufkl?rung)[注]Kant, Beantwortung die Frage: Was ist Aufkl?rung, Hamburg: Meiner, 1999, VIII,S. 35.。
并且,指出存在著有衍變成“幻象”的可能,不僅沒有意味著就否定了理性的建構,反而因此排除了它的自我否定,為“家居”的自我建構提供了可能。因為,“幻象”只關涉“辯證”,只是一種混淆,它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了理性建構自身。并且,也正因為指出了“辯證”,才提醒了人們要謹守理性的“界限”,不要因為外在的干擾而招致自我否定的“背反”。何況,籍此,批判不僅排除了基于“幻象”所提出來的“家居”家長式的“獨斷” (dogmatisch),還提出了確保理性建構得以實現的“自由公民的認同”(Einstimmung freier Bürger)[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66.。可見,批判不僅闡明了理性的建構所以招致非議的原因,也呈現了確保自我建構的“規范”(Kanon)。如此一來,批判也就不僅是涉及一個建構人性的啟蒙,還是一個建構人性的奠基。
當然,要理解這一人性的奠基,也并不容易。并且,理解的困難就在于批判道出了奠基的不可能。因為,之所以難以理解不僅在于批判對體系的介紹不僅繁難,也有失語,也在于批判從一個“體系”中分離出了“直觀”和“概念”這兩個性質完全相反的要素。如此一來,不僅道出了理性的建構總是受到我們感性的限制;并且,批判也指出了,與“直觀”辯證還會導致對“概念”因而對理性的否定。更不要說,批判也的確缺少一個“概念”建構系統的詳盡演繹,盡管它提供了進行這一說明的所有環節。因此,相對于一個說明了自我建構何以可能的方法論,批判也難免給人一種印象:它并非一個什么說明了“人的本質”的啟蒙,而只是一個頂多說明了如何系統化我們知識的一個知識論。甚至,它都不被看作是說明了如何體系化我們知識的知識論,因而只被當作是一個我們知識要素的羅列[注]這種困難體現在有關批判的研究上的突出的表現就是人們局限知識論中對理性的限制,以及批判并沒有提供一個概念的系統以及說明概念如何演化為一個系統,而否定批判已經導出了建構知識的體系的可能(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1923, p.579; Paul Guyer, Kant and die Clai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5; Dieter Henrich, “Systemform und Abschluβgedanke—Methode und Metaphysik als Problem in Kants Denken”, In Kant und die Berliner Aufkl?rung: Akten des IX. Internationalen Kant-Kongresses, Bd.I, Berlin: Gruyter, 2001, S.90-104)。當然,盡管人們也會運用實踐的目的論來糾正這種偏差,但還是忽略了其在知識論中研討的必要(H?ffe, “Architektonik und Geschichte der reinen Vernunft”, in Immanuel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 v. Morl und Willaschek, 1998, Akademie Verlag, S.621)。可見,作為“科學”的“導引”,批判還沒有被充分地揭示為展示建構理性體系的可能的方法論。不過,這為本文的寫作留下了空間。。
一、科學:合目的的體系
作為一個對理性建構的專門稱謂,對于康德而言,顯然“建筑術”(Architektonik)[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860.這一術語并非如其字面所表明的那樣是一門關于如何建造屋舍、修葺庭園等等諸如此類機巧的“技藝” (Kunst)[注]H?ffe, “Architektonik und Geschichte der reinen Vernunft”, in Immanuel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S.619; Paula Manchester, “Kant’s Conception of Architectonic in its Historical Context”,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ume 41, 2003, p. 195. 在此,H?ffe的特別貢獻就是凸顯了批判的實踐旨趣,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引入世界公民的意圖;Manchester則回溯了建筑術的學術史,為我們理解這一概念的發展提供了相關背景。。不同于此,他所謂的“建筑術”與我們的認識能力相關,是對我們系統化我們的知識使之進階為“科學”這一理智能力的描述和提點。就此看來,似乎康德只是在比擬的意義上使用了這一術語:就像人們將四處分散的、不同性質的材料搜集起來,繼而建造出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場所那樣,我們也會運用我們的理性,將我們雜多的感知按照一定的規則整合起來,從而建立起它們之間的關聯,使之成為具有特定對象或者一般規定的系統性知識。不過,這樣一來,對于批判而言,使用“建筑術”這一術語簡直就是因為修辭而進行的一個冒險:將雖然有相似之處然而卻完全不同的兩個領域相提并論,盡管可以借助一個具象的領域來將一個抽象的領域描述得淺白易懂,但是這也會因為前者的具體而遮蔽后者的抽象。
與此同時,“建筑術”這一術語也并非只是指涉建造這一活動外在的形式和可能。它也涉及建造這一活動的基礎和意義。并且,在這個意義上它呈現出人之于他存在的基礎性意涵。因為,建造立足于對自我生存空間的一個整體性“規劃”之上。因此,“建筑術”不僅意味著將分散的、不同性質的材料搜集起來,也意味著構造出人存在的基礎和整體。在這一個意義上,它就是人本質的投射。因為,“建筑”(Geb?ude)意味著“定居”(Anbau)。不同于沒有固定居所的“游牧”(Nomaden),“定居”意味著人建立了固定的、一般的、整體性的生活。因此,作為“建筑”的科學,“建筑術”也就可以與外在的建造活動相剝離,進而有別于偶然的、變動的、沒有根基的生活被看作是對人的本質的研究和建構,因而也就是一個說明存在的“智慧” (Weisheit)的啟蒙。所以,使用建“筑術”這一術語,也可能不僅僅是一個修辭,因而只是用來說明“科學”所具備的一個形式。與之相反,它可能是一種洞見,即發覺知識包含著人本質的建構。這樣,“建筑術”這一術語不是形容了“科學”的形式結構,而是深化了對知識的本質認識。
誠然,就像批判區分“直觀”和“概念”所告訴我們的那樣,對于感性地認識對象的我們而言,也只有串聯起我們雜多的感知,建立起它們之間的關聯,我們才能領會對象。因為,存在于時空之中的對象,它所以如此,或者不能如此,都有賴于人們去發現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而建立起這一原因和結果的關聯,無疑需要一個主體意識的綜合[注]這里對應批判中的“形而上學演繹”,即區別于對象的給予,作為表象指出知識與概念之中的綜合有關。。不然,對我們而言,對象就只是雜多的觀感,而非一個因果的關聯。并且,這樣的一個認識只有追溯到一個主體之上才能得以完成。因為,要想達到對對象本質的認識,就要求對對象有一個原則性的把握。而處在感知之下的事物,它所以如此,總是取決一個先行的原因。但是,在時空之中對這一原因的追溯總可以上溯到更上的原因。因此,它永無窮盡,所以由此也不會得到任何對“事物自身”(Ding an sich)的認識。與之相對,原則不是別的什么,就是主體自身的規定。只有與一個主體關聯起來,人們才能為一個事物找到一個絕對的原因。可見,知識不僅與主體相關,并且也只有與主體關聯起來,它才能真正獲得自己的本質[注]這里對應概念的“先驗演繹”,即將概念上升到原則,因而超出一切經驗指出概念為主體的規定,知識奠基在主體的綜合之上。。
并且,同樣應當注意的是:康德首先是一個哲學家,而不是一位文學家。語詞的使用,對他而言,首先是傳達實質,而不是形象地說明。何況,沒有本質的澄清,也很難有說明的形象[注]“家居”這一話題也延續在荷爾德林的詩情與海德格爾對其的闡釋中。不過,盡管荷爾德林提出了面向神的存在之問(H?lderlin, “in lieblicher bl?ue”, in S?mtliche Werke, Bd. 2, Hrsg. von Friedrich Beiβer, Stuttgart: Cotta, 1953, 1808),并且海德格爾對此也有展開這一疑問的闡釋(Heidegger, “Bauen Wohnen Denken”, “... dichterisch wohnet der Mensch ...”, in Vortr?ge und Aufs?tze, GA VII,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 2000, 1951),但因為缺乏像批判這樣一個明確區分直觀和概念的方法論的自覺,人們從中所能看到的不過是諸多可能的變幻,甚至只是一個問題,而不是決斷的尺度、疑問的實質。因而,批判之于文學或許確有修辭上的抽象,因而較之相應的闡釋有脫離具體情境的缺憾,但仍不失為直指根本的覺察。。所以,“建筑術”這一術語不應只是一個知識形式的描述,因而只是一個沒有道出知識本質的修辭。將其只看作“科學”形式的形象說明,正如已經闡明的那樣,不僅低估了批判的深刻,也會因為膚淺與知識的本質失之交臂。與之相反,“建筑術”不僅提供了我們認識的一個整體框架,也說明了這一框架植根在主體的規定之上,是我們自身本質的展開。因此,運用”建筑術“這一術語,不僅道出了”科學”的形式框架,也形象地傳達出了康德對于“科學”和理性自身的準確把握。就此而言,無疑,即使康德可以因為運用一個具體的領域來說明一個抽象的意涵而占有修辭的形象,但是這一功效也要屈身于康德作為哲學家所具備的對事物本質的洞見。
事實上,對康德而言,理性的綜合不僅表現為發動理性對我們的感知進行整合,使之成為“系統”的“科學”知識,也建立在實現我們“理性自身的諸目的”(teleologia rationis humanae)[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867.之上,是一個我們本質的建構。因為,在批判之中,借由“直觀”和“概念”的區分,康德不僅像在范疇演繹中那樣將其展示為整合我們感知的“統覺”,也像在辨證論中所做那樣將其追溯到整合主體為一體的理性的“理想”。就此而言,理性的綜合無疑不僅被發掘為我們認識的主觀的原則,也是構筑我們主體性,并且是使之獲得普遍性的建構。因此,作為一個建構“體系”的方法論,批判不僅是一個說明了知識如何系統化的“科學”的“導引”,也是說明理性的綜合為一個我們本質的建構的“啟蒙”。對此,“建筑術“不僅相對于要素論,道出了批判說經何以建構的“體系”的方法,因而提出了批判的建構,也將批判從一個說明何為“科學”的“導引”轉變為了一個說明如何實現我們本質的一個“啟蒙”。
二、理性:不可能的直觀
批判立足于一個主體自身的建構之上,這一“建筑術”所傳達出來的見解似乎并不見容于批判。因為,在一個說明科學之為“科學”的“導引”中,無論如何理性都會被要求與對象相符合。并且,借由“概念”和“直觀”的區分,批判不僅首先表明理性會運用于“表象”對象之上,進而也將理性的運用限制在“可能經驗”的范圍,甚至最后還將理性超驗的運用都斷定為“幻象”。如此一來,批判無疑包含限制甚至是否定一個“體系”的因素,因而它的工作似乎只是消極的:將思辨的理性運用拉回到經驗的運用上來。不過,這不僅與“建筑術”所呈現的最終格局相左,也與批判所植根的形而上學的訴求相悖,甚至不能涵蓋批判分析的方法所呈現出來的內容。因為,致力于導出“先驗綜合判斷” 可能性的批判,其目的是提供科學體系的可能性,而不是限制理性的架構。因為,形而上學尋求的就是超驗的原則。因為,區分“直觀”和“概念”不僅表明了理性關切對象,也表明了它乃是出于主體自身的主張,可以為主體自身的規定。
實際上,批判一開始就表明了:理性不滿于經驗,必超出經驗。它所面對的問題,即“靈魂”“自由”和“上帝”[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391、828.,雖與經驗相關,并構成經驗的基礎,但它們顯然超出了經驗,不能混同為經驗。首先,“靈魂”盡管是現象的“本體”(Substanz)[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401.。但是,它超出了直接的“直觀”。繼而,“自由”雖然提供現象以一個原因,并構成現象的“總體”(Totalit?t)。不過,因為是一個絕對的原因,它不能等同于有限的經驗。最后,“上帝”,作為“總體”的“總體”而存在一個“理想”,更是遠離“直觀”。因此,可以說,這些問題的提出恰恰說明:人們不會滿足于在經驗中來認識,而是要超出經驗來認識經驗的基礎、架構和系統。因此,不管是解答這些問題,還是滿足我們不可以滿足的認知,都要求我們將理性與經驗剝離開來,從超驗的規定上來把握我們的理性。如此,康德才是承繼了而不是放棄了形而上學。
并且,形而上學的三個問題也的確給我們劃定了一個主體的領域。首先,“靈魂”這一觀念本身就意味著主體,因而它甚至并不會如康德所擔憂的那樣被錯認為一個超驗的客觀“本體”。再者,“自由”這一觀念因為是自身的原因,它也預設了一個主體。并且,因為它與客觀的“總體”相關,因而還是主體在這世界的展開。最后,“上帝”這一“理想”,也不是別的什么,而是一個絕對的主體性。并且,因為它綜合了理性所有的原則,在批判之中它更是一個主體的全體。因此,形而上學不僅意味著為現象提供一個主體上的根據,也意味著建立一個主體的本質。易言之,也就是依照“上帝”這一理念建構起一個理想性的人格。這樣,批判也就先定了自己要在主體性上找到客體性,并且還應是人類的規定的一個建構。
與之相應,劃分自身為一個分析要素的要素論和一個說明如何建構體系的方法論,以此批判也明確地表明了它尋求的是一個主體自身的建構,而不僅僅是一個對客體的綜合。首先,通過“直觀”和“概念”的區分,批判就已經清晰地說明了:不同于表象客體的“直觀”,作為“概念”理性是主體自身的綜合。進而,在這個基礎上,利用一個消極的辯證論,即一個關于“幻象”的邏輯論,批判還進一步說明了這種綜合絕不可能是對象的規定,反而是出于主體自身的一個建構。最后,在方法論的說明中,批判更是向我們闡釋了區分“直觀”和“概念”不只是為了說明“知識的體系”(System der Erkenntnisse)[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867.,而是為了給“人的本質規定”確立一個“立法”(Gesetzgebung)[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868.。可見,批判也是一個確立人之為人的“智慧”的“啟蒙”。
當然,無論是在形而上學之中,還是在批判之中,作為“科學”的基礎,理性的建構都無法脫離”直觀”,都需要與“直觀”結合起來。正如一開始就提及那樣,“科學”無論如何都是關于對象的知識,盡管同樣它也是主體的知識,甚至如我們所揭示的那樣在本質上為一個主體自身的建構。因此,也如批判所表明的那樣,理性的運用都應該限定自身在“可能經驗”的范圍內,并且不能將自己與“直觀”相混淆,因而只能將自己看作是純粹主觀的“概念”。但是,這個限定仍只是一個外在的限定,而不是一個根本的否定。它只是限定了理性運用的領域與方式,而沒有否定理性運用本身。與之相反,也如我們已經展示的那樣,批判不僅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對理性運用的限制,也提供了一個說明理性的建構是一個主體自身的建構的說明。并且,也如已經提到的那樣,后者的可能,恰是因為有了前者的限定,才解除了自我否定的問題。
三、辯證:仍未澄清的概念
為化解形而上學問題,進而說明一個“體系”的可能,正如《純粹理性批判》要素論所展示的那個樣子,批判拆解了“體系”。應該說,這樣的一個做法,說明了“體系”的可能,也給認識“體系”和批判帶來了困難。首先,綜合的“體系”湮沒在了拆分的“要素”中。當然,相對于此,批判不僅在要素論中最終分離出了“體系”,也運用了方法論說明了這種分離的成功。不過,這種分割的做法,還是可能帶來一種誤解:批判并非一個提供了建構一個體系的方法論,而只是一個分析了不同要素的要素論。在一個“體系”中分出“直觀”和“概念”這兩個要素,這一做法不僅將理性展示為“出于概念” (Aus Begriffen)[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41.這里對應的是康德所謂的“哲學知識”(philosophische Erkenntnis),即源自于概念自身規定的知識。的一個主體的綜合,也展示為一個在直觀中的“構造”(Konstruktion)[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41.這里對應的是康德所謂的“數學知識”(mathematische Erkenntnis),即運用在直觀上的概念的表象。。并且,后一種意涵被先行地展示了出來。這樣,人們很難避免不將批判理解為一個關于“直觀”何以可能的探究,而不是將其理解為“概念”建造了一個“體系”的說明。換言之,批判似乎更是一個“直觀”的解析,而不是一個“概念”的發掘。
其次,作為點明批判分離兩個要素是為了分離出一個體系的可能的方法論,相較于要素論的面面俱到,過于抽象和支離。這無疑也增加了人們理解批判為一個說明建構一個“體系”的難度。與之相反,方法論作為最后的總結,本應有點睛的功效。但是,它還是分出四個章節。并且,在每個章節中,還有進一步的劃分。不得不說,這樣的做法在力圖充分說明批判的意圖和功能的同時,也削弱了它自我總結的能力。并且,盡管不可不謂是面面俱到,但是在一些關鍵的地方,方法論還是有些含混。然而,事實上,相對于要素論,作為說明一個“體系”何以可能的總結,正如已經提到的那樣,方法論不僅提出了知識的系統化架構,完成了批判的建構,也因為引入了一個實踐的目的論,從根本上改變了批判的意涵。較之這些基本的意義,一個支離且抽象的方法論不可不謂捉襟見肘。
再者,康德在辯證論中分別處理了三個特殊的形而上學問題,卻沒有充分說明它們相互間的關聯,也削弱了它說明形而上學問題作為發源于同一個理性而具有的普遍意義的能力。與之相反,他應該將這些問題串聯起來,進而將它們演繹為理性走向一個體系的不同環節。否則,可以說,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個個特殊的形而上學問題,而不是一個普遍的形而上學。然而,形而上學作為理性的訴求,正如康德所揭示的那樣,它不僅是三個問題,不僅來源于三個不同的推理形式,也是源自于一個理性的一個“體系”。無疑,康德在一個需要發聲的地方保持了沉默。更不要說,這些問題的化解在一個分出兩個要素的要素論中,不僅被放置在最后的邏輯論中,還相對于肯定性的分析論被放入了否定性的辯證論。這樣的做法無疑也隱藏了批判試圖解決形而上學問題的抱負,因而遮蔽了它作為闡明一個體系何以可能的本意。
還有,對康德而言,區分“直觀”和“概念”的做法,不僅是一個分離出體系可能的方法,也是對理性運用的一個限制,甚至因此取消了理性的運用。利用一個要素論,批判不僅將”概念“與”直觀“分離了開來,進而在”概念“之中發掘出了一個體系,也就是理性的“理想”。與此同時,批判也表明了,理性的建構不僅與“概念”相關,也與“直觀”相關。并且,為此也明確地將理性的建構限制在了“可能經驗”的范圍之內。可見,批判在說明一個體系何以可能的同時,也帶出了對一個體系的限制。這就是說,理性的建構總受“直觀”的限制。又因為相對于“概念“,“直觀”總是有限的感性形式。如此一來,可以說,批判不僅將理性的建構限制在了“可能經驗”的范圍內,也取消了它得以完全實現的可能。因此,的確在發現了體系在“概念”有其可能的同時,批判也揭示出了理性建構的限制,并且在這一限制上取消了它現成地建成一個體系的可能。
并且,批判不僅道出了對一個“體系”的否定,還將這一否定追溯到了理性建構的自我否定。正如已經表明的那樣,批判是為了化解形而上學問題,才批判理性。但是,對于形而上學問題分析,批判并沒有只停留在“直觀”和“概念”的區分中指出:相對于客觀的“直觀“,作為”概念“的理性是純粹主觀的“觀念”,因而不僅它缺少建構一個現實的“體系”的客觀性,也不可能由有限的”直觀“那兒借取充分的客觀性。在這之上,批判還將形而上學問題揭示為理性自我否定的“二律背反”,并且是取消了理性”理想“的“辯證”。如此一來,批判也就不僅向我們展示了建構一個體系的限制,也展示了一個從根本上取消了建構一個體系的可能。可以說,正是因為要化解形而上學問題,尋求理性建構自我的可能,批判也帶出了理性自我否定的可能,因而它事實上不僅是一個說明了理性建構何以可能的重建,也是一個取消這一建構可能的毀棄。并且,正是通過與“直觀”的分離,批判道出了毀棄。
四、批判:啟蒙人性的導引
羅列認識“科學” 進而明了“智慧” 的諸多困難,并不表明在批判之中洞察這些進展就毫無可能,因而意味著從根本上就否定了批判帶來了這樣的轉變。當然,困難是確實存在的,而且也確如已經表明的那樣,它不僅體現為批判表述的繁難,也體現為這種轉變自身就帶有問題。但是,問題的存在并不意味著就可以為我們的一知半解或者拒絕認識這一轉變提供托詞。因為,困難的存在也意味著進行轉變的必要。因為,問題不僅意味著進入一個領域的障礙,也意味著我們的需要還沒有得到滿足。對一邊收到感性擠壓、一邊又會被理性引導的我們而言,一個超驗的“理想”我們不僅不會放棄,還會必然地主張(參見Antagonismus)[注]Kant, “Idee zu einem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in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Politik und P?dagogik,Berlin: Suhrkamp, 1977, VIII, S.20。。何況,作為“科學”的“導引”,批判不僅在一個要素論中分離出了一個“體系”的可能,也在一個方法論中運用“建筑術”這一方法論的說明說明了上述方法開啟了這種可能。可見,它既不乏進入“科學”的動力,也已經帶出了“科學”[注]H?ffe, “Architektonik und Geschichte der reinen Vernunft”, in Immanuel Kant-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S. 625.德國觀念論將批判貶義為還不足夠科學的導引,而將自身稱之為科學的展開,無疑忽略了導引對康德而言具有使科學成為科學的本意,批判也發現和展開了科學的根據,即我們理性的建構。盡管無論是費希特的主觀觀念論展開了觀念自身的活動,還是黑格爾客觀的觀念論呈現了觀念歷史的演進,這些確實展開了科學不同的向度。。
無疑,植根在“理性自身目的”之上的理性的綜合,不僅是一個建構”科學”的“技藝[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860.,也包含著實現我們自身的“智慧”。并且,借由要素論中“直觀”和“概念”的區分,批判已經向我們明確地展示了:我們的理性不僅在“直觀”中朝向客體,作為“概念”它也植根于主體,并且建構著主體。因為,它不僅被追溯為架構“直觀”的“統覺”,也是被揭示為建構了“概念”普遍規定的“理想”。與此同時,在方法論中通過”建筑術“這一章節,它也說明了上述方法所具有的相對于力圖揭示事物自身發展的“實現” (參見Werden)[注]Hegel, 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amburg: Meiner, 1988, 1807, S.13.而具有說明一個主體自我成就的能力。可以說,在“科學繁榮”(Wachstum der Wissenschaft)[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V.的時代,批判不僅立足于科學追求實效這一現代潮流,也揭示出了這種訴求所植根因而引為基礎的一個主體的自我建構。因此,它不僅揭示了“科學”的實質,闡明了“科學”的意味,也開啟了“智慧”,不可不謂是一個對人之為“人”的“啟蒙”。
并且,批判的上述功能,不僅體現出了一個以“科學”為特征的現代立場,也帶出了追求自我普遍實現這一一般的訴求。正如我們已經闡明的那樣,“先驗綜合判斷”之所以不僅是一個“科學”的架構,也是一個“人本質”的普遍“立法”,不僅是一個區分了“直觀”和“概念”之后的一個結果,也是一個本來就存在于形而上學之中因而存在于理性之中我們的一個普遍訴求。當然,批判并沒有像基于“概念”和“直觀”的辯證而賦予這一訴求以絕對的客觀性。但是,將其還原為一個主觀的“理想”,不僅修正了過去的錯誤,避免了現代的虛無,也超越時空道出了理性的本質和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批判對于理性進而對于人的說明具有一般意義。由此不僅批判可以提煉出自身的基礎,理性也為人展開其普遍的規定。
當然,作為純粹主觀的規定,理性不僅顯示為一個可能與他人達成一致因而超越了純粹主觀性的立法,也顯示為個體可以拒絕與他人達成一致,甚至因此引發與他人形成沖突的“任性”(Willkür)。并且,只要理性是一個主觀的規定,這種沖突的可能就不會消除。當然,理性總是主體的規定,這種沖突的可能也不會消除。因此,面對這一形而上學問題,盡管批判呈現了化解的可能性,但是聲稱可以使我們理性獲得“完全的滿足”,批判還是有因為對自身成果的樂觀而遮蔽我們理性自身復雜性的嫌疑。因為,達成一致,只是一種可能,一個“理想”,而不是客觀的現實,不是全部的可能。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將批判當作一個揭示了理性“立法”的“導引”。并且,是一個對理性“立法”的修正的修正:區別于因為辯證而主張的“獨斷的運用”(dogmatischer Gebrauch)[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41.和現代懷疑主義的放任自流,批判提出了理性“爭論的運用”(polemischer Gebrauch)[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98, B 767.,帶入了一個“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視角[注]Kant, “Idee zu einem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in Schriften zur Anthropolog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Politik und P?dagogik,Berlin: Suhrkamp, 1977, VIII, S.17.。
不同于被動表象對象的“直觀”,作為主動運思的“概念”,理性意味著主體自身的發動。即使這一主動因為有對對象的關切,因而被要求與對象相對應,以至于在這一對應中我們不再區別“概念”與“直觀”的差別,將“概念”就認作為“直觀”,從而讓純粹主觀的理性陷入自我否定的困境,進而失去了它自我實現的可能。但是,作為一個普遍的“概念”,理性既不能由有限的“直觀”所賦予,也必然會超出“直觀”,表現為一個主體自身的規定。因此,即使沒有批判,人們也還是會察覺,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并不局限于有限的“直觀”,對對象的把握除了這種被動之外,還有我們自身的主動,并且是能賦予我們感知基礎和整體性的主動。不過,對于曾迷失于和將來還會迷失于與“直觀”的辯證的我們而言,作為一個指出我們的本質植根于我們自身的“概念“的說明,批判永遠都不失為一個必要的、能揭示我們本質的一個啟蒙,而且是一個揭示了我們本質普遍實現的啟蒙。
五、結 論
指出我們在世“家居”,就不僅道出了在世所具有的整體狀態,也道出了人的操持是建構這一整體的基礎。可以說,“建筑術”不僅呈遞了“體系”這一我們感知的基礎形式,也呈遞了構筑這一基礎形式的主體性。因此,理性的建構在批判中不僅可以理解為整合我們外部世界的一個建構,也應該理解為發端于人自身對存在的一個全面“規劃”,因而是人自身本質的一個展開。并且,就實質而言,它只能被理解為后者。因為,正如批判區分“直觀”和“概念”所表明的那樣,能夠賦予存在以整體性的只能是提出了普遍原則的內在的自我意識,而不能是隨時空轉變的外在的周遭世界。另外,相較于“巴比倫塔”式的主張,“家居”還是一個修正,并且是修正的修正:它不僅排除了引發爭議的理性“獨斷”的運用,也排除了對理性運用的否定,而以“爭論”的運用方式展示了理性普遍運用的可能性。
對批判而言,“建筑術“不僅綜合了它之前所區分出來的“直觀”和“概念”這個不同的要素,提出了“體系”這個理性可以賦予知識同時也可以賦予批判以整體性的“科學”架構,也因為聯系到一個實踐的目的論在基礎上改變了“體系”因而也改變了批判的意涵,讓批判由一個說明了科學何為科學的“導引”進階為闡明人何以為人的智慧的“啟蒙”。無疑,“建筑術”是批判達臻成熟和深化的標志。并且,借由上述兩個要素的區分,批判不僅排除了引發爭議的理性與“直觀”的辯證,也補足了近代立足于經驗而無法洞察經驗植根于我們自身的普遍規劃之上的不足。這樣,它既賦予了理性運用立足于“科學”的現代形式,也補足了現代對于道德考量的不足,提出了理性普遍運用的可能。當然,作為一個形而上學問題的化解,批判不僅提供了建構“體系”的可能,也帶出了否定“體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