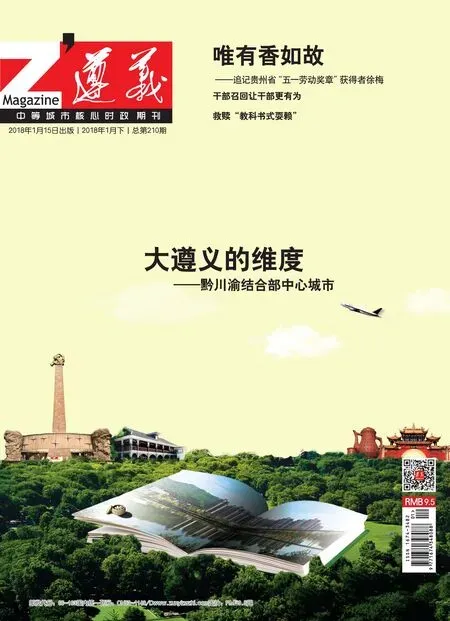他在湄潭建起了“東方劍橋”
文丨 李 想
71年前為躲避戰火,浙江大學入遷貴州湄潭,它的到來為大山深處的小城,激起文明進步的浪花;而質樸的山區,在烽火連天災難深重的歷史關頭,也豐滿了一所名校的精神,為其帶來金子般的7年珍貴時光。

1936年的4月7日,竺可楨被任命為浙江大學校長。他這一天的日記寫著:晨雷雨。上午有霧。午有雷。下午四點見陽光。晚又雨。玉蘭盛開,杏花落,寓中白櫻花開。
浙大有幸,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擁有了這么一位領路人。一所只有3個學院16個學系的大學,在顛沛流離中,發展壯大成7個學院27個學系的當時全國最完整的兩所綜合性大學之一,被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稱譽為“東方劍橋”。
而遵義湄潭,何其幸運,71年前為躲避戰火,浙江大學入遷貴州湄潭,它的到來為大山深處的小城,激起文明進步的浪花;而質樸的山區,在烽火連天災難深重的歷史關頭,也豐滿了一所名校的精神,為其帶來金子般的7年珍貴時光。
小城情緣
1937年11月5日,日軍在全公亭登陸,距杭城僅百公里。為了保全浙江大學,1938年1月11日至13日,竺可楨率全校師生分三批離開杭州,一遷浙西建德,二遷江西泰和,三遷廣西宜山,歷時兩年半,橫穿浙江、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6省,行程2600余公里。最終將校址遷到貴州省湄潭縣,并在當地辦學7年。這一壯舉,被彭真稱贊為“一支文軍”的長征。
隨后的7年是一段金子般的珍貴時光,在烽火連天災難深重的歷史關頭,湄潭成為避風港,浙江大學再次得以喘息、停留、發展,免于戰爭的紛擾。
浙江大學教師、學生及家屬一千多人、幾千箱圖書儀器,在輾轉贛、湘、粵、桂4個省份,跋涉2600余公里后,終于在1940年初先后遷抵貴陽花溪青巖、湄潭永興。
貴州向來給人的印象都是“蠻荒之地”,“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的評價也由來已久。因此,隨著浙大第五次無奈搬遷,陸續到達遵義的浙大師生,一開始對遵義這個地方的第一印象并不是很好。再加之當時,隨著日軍不斷入侵,北方和東南沿海的大批高校紛紛內遷、難民一并涌入,遵義人口由原來的7萬多,激增到10萬人,上漲的房價令浙大師生難以負荷。
這個時候,距離遵義75公里的湄潭縣向浙大師生張開了雙臂。湄潭縣位于遵義東面的一個小盆地中,四周峰巒迭起,碧波清澈的湄江從城西蜿蜒而過,城內隨處可見堰壩、水車和依山而筑的吊腳木樓。這里環境優美,物產豐饒,素有“小江南”之稱。雖是偏遠的小山城,但在抗戰時期,卻是一處難得的清幽之所。
貴州湄潭浙江大學西遷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黃正義介紹,時任湄潭縣長的嚴溥泉,曾經在國外留過學,是一個很開明的縣長。在得知浙江大學的竺可楨校長從宜山來到貴州選址以后,他就主動寫信邀請竺校長來到湄潭考察。
時年4月5日,湄遵公路通車,國立浙江大學理學院、農學院以及師范學院理科系的近千名師生,乘校車搬遷到湄潭。湄潭縣長嚴溥泉成立了浙大遷移協助會,提供房舍250多間,讓出文廟、民教館、救濟院等辦公房屋,不僅如此,湄潭當地的部分居民還讓出自己的房子,給師生們居住。當時的湄潭縣,人口只有1000多人,國立浙江大學遷入后,讓這座封閉的小縣城一下子熱鬧起來。
浙大在湄潭期間,國民政府派農學院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劉淦芝出任當時中央農林部湄潭茶葉試驗場場長。在浙大農學院專家的指導下,劉淦芝博士借湄潭山水之靈氣,把湄潭的茶文化與現代科學技術結合起來,改進了湄潭茶固有的品質,引進了異地的優質茶種和杭州“龍井茶”的生產技術,培育出龍井茶、綠茶和紅茶,使湄潭茶葉頓時名揚四方,受到浙大教授、專家的好評。
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整,國立浙江大學終于在貴州安頓下來。學校本部辦公機構、文學院、工學院和師范學院文科系留在遵義;理學院、農學院和師范學院理科系,落戶湄潭;一年級新生從青巖搬到了湄潭縣城外15公里的永興鎮。
弦歌不輟打造“東方劍橋”
其實,到浙大當校長,竺可楨一開始并未接受。
當時,浙大學生因反對校長郭任遠,爆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學潮。蔣介石急著物色一位有聲望、有學術成就的人去接任,以平息家鄉的學潮。
竺可楨希望這不是真的。一則他放不下氣象研究所的工作;二則大學校長事務繁雜,又要同官場打交道,他自知不善亦不屑于官場應酬。
竺可楨當時是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這是他1928年創辦的,也是我國第一個氣象研究所。此前,1918年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后,他在東南大學創建了中國大學中的第一個地學系。
但此后的13年間,他最主要的工作,不再是氣象研究。竺可楨從一個科學家,成為了一個教育家。
雖烽火連天,顛沛流離,卻弦歌不輟。每到一處,稍作安頓,師生們就打開教案,拿出課本復課,科學研究也沒有停頓過。
戰時,科研儀器缺乏,實驗條件簡陋,師生們自己動手造。遵義沒有電,改造的設備用桐油代替柴油發電為工學院的學生開出了實驗課。王淦昌教授在指導研究生葉篤正做“湄潭近地層大氣電位的觀測研究”課題時,沒有觀測儀器,找了個損壞的電位計修復后進行觀測。訂閱外文期刊和專業刊物很難,竺可楨撥了近萬元費用專門托在上海的教授選購外文書刊。
“大學無疑的應具有學術自由的精神”,因為“大學的最大目標是在蘄求真理”,沒有獨立研究的氛圍,自由討論的刺激,真理何由得明?在竺可楨的倡導下,浙大的學術討論之風盛行,教授與教授之間常常為學術問題爭得面紅耳赤。
據不完全統計,在湄潭的7年中,浙大在國內外發表的論文超過當時所有的中國大學。英國《自然》周刊、美國《物理評論》經常收到來自“中國湄潭”的論文。
在當年浙大任教和求學的師生中,后來有50人當選兩院院士,走出了不少如李政道、程開甲、谷超豪、施雅風、葉篤正等科學界的精英。
當原本布局于東海之濱的浙江大學,化整為零地藏身于西部群山中的遵義、湄潭和永興三地時,曾到湄潭參加1944年中國科學社30周年年會的李約瑟,在英國《自然》周刊上這樣寫道:“遵義之東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學科學活動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動的一片繁忙緊張的情景。”
后來,他充滿敬意地寫道:在那里,不僅有世界第一流的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竺可楨教授,世界第一流的數學家陳建功、蘇步青教授,還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學家盧鶴紱、王淦昌教授,他們是中國科學事業的希望。
李約瑟甚至斷言:這就是東方的劍橋。
竺可楨之子竺安回憶起當年浙大的湄潭時期,物質條件極差,但學術民主氣氛很好,教授們心情舒暢,專心教學與研究,不論是誰,只要有了好的成果,竺可楨都極力鼓勵,即使教授間有了矛盾,他也是盡力調解,從不打一派拉一派。
他的愛心和提倡的求是精神,融化到教師和每一個人身上,形成了優良的學風,并影響到后來的學生,他們沒有見過竺校長,但他們對于竺校長十分崇敬,對母校十分熱愛。
1945年,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遵義和湄潭,浙大師生欣喜若狂。他們明白,流亡的日子即將結束,他們很快就會回到久違的西湖之濱。
從1937年跨出西遷第一步,到1946年返回杭州,浙大的流亡辦學幾近十年。這是山河破碎的十年,物力維艱的十年,也是向死而生的十年,鳳凰涅槃的十年。在時局動蕩、校址偏僻、經費拮據、疾病侵襲的條件下,浙大出人意料地從一所地方大學,成長為與中央大學、西南聯大和武漢大學齊名的民國四大名校之一。
而被竺可楨選擇這座小小的湄潭城,打下了隆重的浙大烙印,諸如街巷和學校的命名:可楨路,浙大北路,浙大南路,求是路,浙大小學,求是中學。這座深藏于千山萬壑中的小城,浙大在此的6年,是它最值得驕傲的往事。對浙大來說,湄潭的接納,使它在艱難歲月里逆風飛揚,終成名校;對湄潭來說,浙大的到來,為這座閉塞落后的小城吹來了現代文明的新風,這座小城容納的,不僅是一座大學,更是一代人抗戰的回憶,一所大學、一個國家、一種“求是”精神的薪火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