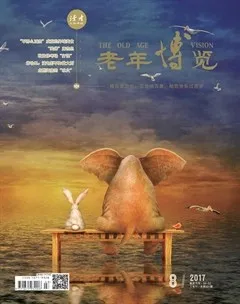蘇東坡破悶
黃庭堅填詞,偶爾運用拆字法,如“女邊著子,門里安心”,前者為“好”字,后者為“悶”字,合成“好悶”。清人彭孫遹在《金粟詞話》中對此不以為然,直批黃庭堅的詞句“鄙俚不堪入誦”。但文人雅士老是端著、繃著、藏著、掖著,好受嗎?難道他們就不能在作品里鄙俚幾回?倘若黃庭堅泉下有知,必定踢爛棺材板,大呼三聲:“好悶!好悶!好悶!”
在謫居地,黃庭堅心情不佳,填詞時就沒打算認真,只把小令當作文字游戲來玩,何曾想過效仿柳永,指望勾欄瓦肆中的如花女子將他的詞作一一度曲,唱得凡有井水處人人皆知?他喜歡將俗諺俚語信手拈來:“口不能言,心不快活”,“蟲兒真個惡靈利,惱亂得道人眠起”。
蘇東坡可算是古往今來數得著的樂天派,填起詞來,竟然也會犯嘀咕:“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瞧見沒有?好端端的身子被各方用力拉拽,喪失了把控權,你說他苦不苦,悶不悶?苦悶這東西,非得一刀剖開它,你才能見瓤見子。
蘇東坡怎么破悶?謫居黃州時,他耕荒田,治病牛,做紅燒肉,泛舟飲酒,月夜出游。他的《赤壁賦》,沒有一字寫到精神苦悶,卻字字顯鋒,句句露刃,都只為剖開那個“苦悶”的大瓜。
解決苦悶的良方首先在說服自己。可要說服自己談何容易?“蘇子曰”那段話很關鍵:“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遠離塵囂,自得逍遙,月亮底下不妨說說夢話,太陽底下處處見真章。你不爭權,奸人偏要傾軋你;你不爭利,小人偏要擠對你;你不爭名,惡人偏要陷害你。就算蘇東坡徹底說服了自己,他還是無法說服那些敵人。
醉了肯定會醒,傷了肯定會痛,大好的覺悟竟然只能腌制在詩詞歌賦的字里行間。“烏臺詩案”夠冤屈了,黃州安置夠倒霉了,令蘇東坡更覺苦悶的事情還在晚年,謫居嶺表,播遷海南。“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苦悶的人不妨享有幾許愜意,正如囚徒亦不妨夢到自由,但這絕對不是他的敵人喜聞樂見的事情。蘇轍多次規勸兄長盡可能不寫詩或少寫詩,蘇東坡也知道自己的死穴在何處,但苦悶狠掐脖子,寫詩是難得的深呼吸,否則恐怕真的會被活活憋死。蘇東坡賦詩《儋耳山》,“君看路旁石,盡是補天余”,他的感喟有多沉,苦悶就有多深。
和陶詩,釀桂酒,搜尋藥草,給朋友寫信,陪兒子蘇過讀書作文,去黎族農家吃瓜聊天,當然還有望海觀潮,蘇學士破悶的法子不多不少。靜觀,達觀,樂觀,以“滄海一粟”視己,以“眾生未免有情”視人,將一切輕輕放下,慢慢拋開。就算被流放到天涯海角,蘇東坡的智慧長堤仍未崩潰,精神廟宇也未垮塌。你說,在歷史的暗夜里,他究竟是流星,還是航燈?最黑最冷的時分彰顯最亮最暖的光明。奸人、小人、惡人全體失算,他們想用苦悶的鉛球砸死蘇東坡,誰知在這位魔法大師的手中,鉛球變成了香瓜,他一刀剖開它,吃得津津有味。
無論生存的壓力多大,夾縫多小,蘇東坡始終有歡笑,有堅忍,有寬容。憑此“破悶三刀”,那些敵人挖空心思、絞盡腦汁想害死他,卻始終無法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