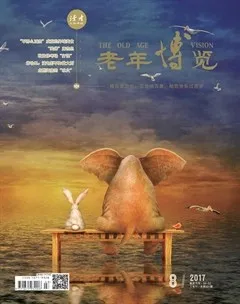美得讓人發(fā)愁的花
我喜歡那些美得扎實(shí)厚重的花,像百合、荷花、木棉;但我也喜歡那些美得讓人發(fā)愁的花,特別是開在春天里的,花瓣兒稀薄稀薄,眼看著便要薄得沒有了的花,像桃花、杏花、李花、三色堇和波斯菊。
花的顏色和線條總還比較“實(shí)”,花的香味卻是一種介乎“虛”“實(shí)”之間的存在。有種花,像夜來(lái)香,香得又野又蠻,的確是“花香薰人欲破禪”的那種香法。含笑和白蘭的香是葷的,茉莉的香是素的,素得可以入茶。而木本株蘭的香總是在日暖風(fēng)和的時(shí)候才聞得出來(lái),所以特別讓人著急,因?yàn)椴恢朗裁磿r(shí)候就沒有了。
樹上的花是小說(shuō),有枝有干,攀在交叉的結(jié)構(gòu)上,俯下它漫天的華美。“江邊一樹垂垂發(fā)”“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wàn)朵壓枝低”,那里面有多層次、多角度的說(shuō)不盡的故事。
草花是詩(shī)。由于矮,像是剛從土里蹦出來(lái)的,有一種鮮艷的、凝聚的美。
爬藤花是散文,像九重蘿、荼靡、紫藤、蔦蘿,乃至牽牛花和絲瓜花、扁豆花,都有一種走到哪里就開到哪里的瀟灑。爬藤花看起來(lái)漫不經(jīng)心,等開過(guò)了整個(gè)季節(jié)后回頭一看,倒也沒有一篇是沒有章法的—無(wú)論是開在疏籬間的,潑灑在花架上的,嘩嘩地流下瓜棚的,還是不自惜地淌在坡地上的,乃至于調(diào)皮刁鉆地爬上老樹,把枯木開得復(fù)活了似的……都各有其風(fēng)格。真的,絲瓜花有它的文法,牽牛花有自己的修辭。

如果有什么花可以稱為舞臺(tái)劇,那大概就是曇花了吧。它是一種徹底的時(shí)間藝術(shù),在帷幕的開闔間即生而即死。它的每一秒鐘都在“動(dòng)”,簡(jiǎn)直嚴(yán)格地遵守著古典戲劇的“三一律”—“一時(shí)”“一地”“一事”。使我感動(dòng)的不是那一夕之間偶然白起來(lái)的花瓣,也不是那偶然香起來(lái)的細(xì)蕊,而是那幾乎聽得見的砰然有聲的舒展的過(guò)程。
文學(xué)批評(píng)如果用花來(lái)比喻,大概像仙人掌花,高大嚇人,刺多花少,大剌剌地像一聲轟雷似的拔地而起—當(dāng)然,好的仙人掌花還是漂亮得要命的。
水生花的顏色天生的好,像極鮮潤(rùn)的潑墨畫。水生花總是使人驚訝,仿佛好得有點(diǎn)不合常理。大地上有花已經(jīng)夠好了,山谷里有花已經(jīng)夠好了,居然水里也冒出花來(lái),簡(jiǎn)直讓人難以置信,可它偏中了邪似的開在那里。水生花,荷也好,睡蓮也好,水仙也好,白得令人手足無(wú)措的馬蹄蓮也好,還有那種紫色的漲成滿滿一串子的似乎叫布袋蓮的也好,都有一種奇怪的特色:不管開它幾里地,看起來(lái)每朵卻都是清寂落寞的,帶著那種伶伶然的仿佛獨(dú)立于時(shí)間、空間之外的悠遠(yuǎn)。水生花大概是一闋婉約派的小詞吧,是在管弦觸水之際,偶然化生而成的花。
不但水生花,連水草,像菖蒲,像蘆葦,都美得令人發(fā)愁。一部《詩(shī)經(jīng)》,是從一處荇菜參差、水鳥合唱的水湄開始的—不能想了,那樣干干凈凈的河,那樣干干凈凈的草,那樣干干凈凈的古典的愛情……想了會(huì)讓人有一種舊王族被放逐后的悲慟。
有些花,是只在中國(guó)語(yǔ)文里出現(xiàn)的,像雪花、浪花。

所有的花都仰面而開,唯獨(dú)雪花俯首而開;所有的花都在泥土深處結(jié)胎,雪花卻在天空的高處成孕。雪花以云為泥,以風(fēng)為枝丫,只開一次,飄過(guò)萬(wàn)里寒冷,單單要落在一個(gè)趕路人溫暖的衣領(lǐng)上,或是一個(gè)眺望者朦朧的窗紙上,只在六瓣的秩序里美那么一剎,然后化為半滴水,回歸大地。
我所夢(mèng)想的花,是那種可以猛悍得在春天的早晨把你大聲喊醒的梔子,或是走過(guò)郊野時(shí)鬧得讓人招架不住的油菜花,或是清明時(shí)節(jié)逼得雨中行人連魂夢(mèng)都走投無(wú)路的杏花,那些各式各樣的日本花道納不進(jìn)去、市價(jià)標(biāo)不出來(lái)、不肯屈身就范于園藝雜志的未經(jīng)世故的花。
讓大地成為眾水浩渺中浮出來(lái)的一種意外,讓百花成為莽莽大地上揚(yáng)起來(lái)的一聲歡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