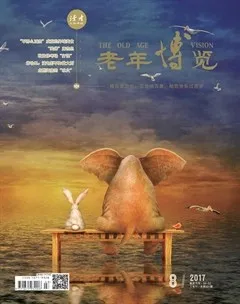為愛傾盡一生
1943年春末的一天,陽光格外好。重慶國立藝專的學(xué)生鄒佩珠正在離學(xué)校不遠(yuǎn)的路邊寫生,一位又高又瘦、“看起來病懨懨”的男子搖搖晃晃地走過來向她打聽:“請問國立藝專怎么走?你認(rèn)識李畹嗎?”
碰巧,鄒佩珠與李畹同住一個(gè)宿舍,就在她的下鋪。就這樣,在李畹的介紹下,鄒佩珠認(rèn)識了受邀到國立藝專教美術(shù)的李可染。
雖然是第一次見面,鄒佩珠卻像已經(jīng)認(rèn)識了他很久。她曾多次聽李畹用崇拜的口吻描述她的二哥李可染,從李畹口中,她知道他從小愛畫畫,因?yàn)榧邑殻陀闷仆肫诘厣袭嫅騽∪宋铮3H堑绵徣藝^;知道他曾是西湖國立藝術(shù)院的學(xué)生,校長林風(fēng)眠特別喜歡他;知道他在郭沬若主持的文化三廳工作,畫了很多抗日的宣傳畫。對這個(gè)“李老師”,鄒佩珠感到既熟悉又親切,看著他瘦弱的身體,得知他在戰(zhàn)爭中失去了妻子、長期被失眠癥折磨時(shí),憐惜之余,她想到了自己的經(jīng)歷。
鄒佩珠是杭州人,本來家境不錯(cuò),可是戰(zhàn)爭改變了一切。日本人打杭州的前一天,她和父母一路逃難,從上海到江西,再到長沙,炮彈就在她身邊爆炸,路上不斷有人倒下。離開長沙不久,母親就因在漂滿死尸的河里洗衣服而染上了病毒,第二天就去世了。守孝49天后,她輾轉(zhuǎn)到了重慶的姐姐家,進(jìn)入國立藝專學(xué)習(xí)雕塑。
戰(zhàn)爭拉近了彼此,失去親人的痛苦也讓他們同病相憐。在學(xué)校,李畹常邀鄒佩珠去李可染的小茅屋談?wù)撍囆g(shù)、請教繪畫。有一天,李可染在拉胡琴,聽得陶醉的鄒佩珠脫口而出:“你拉的是京戲曲牌《柳青娘》!”
她居然懂京劇!李可染既吃驚又激動。從這個(gè)清秀而又才情出眾的江南姑娘身上,他看到了發(fā)妻蘇娥的影子。令他驚喜的是,鄒佩珠不僅喜愛京劇,還能唱整折的老生戲,作為學(xué)生會主席,她常常登臺演出。在李可染給學(xué)生們排演的《奇冤報(bào)》里,鄒佩珠飾演劉世昌一角,她的表演贏得了師生們熱烈的掌聲。
共同的志趣讓他們越走越近,“他拉胡琴時(shí),我就在旁邊唱戲”,美妙的樂聲、清亮的嗓音就這樣回蕩在簡陋的小茅屋里。兩個(gè)人自然而然地相戀了。小茅屋的地上冒出青翠的竹子時(shí),李可染心有所感,想起晉人“不可一日無此君”的詩句,于是稱小屋為“有君堂”,又取“佩珠”的諧音,將這叢綠竹取名“陪竹”,愛戀之情不言而喻。

1944年,在林風(fēng)眠先生的主持下,他們結(jié)婚了。就這樣,鄒佩珠這個(gè)生于農(nóng)歷七夕的“織女”迎來了她生命中的“畫牛郎”。那年,他37歲,是4個(gè)孩子的父親;而她僅僅24歲,風(fēng)華正茂。
新婚之夜,望著“瘦得只有一層皮,肋骨看得清清楚楚”的他,她心痛難忍。“你放心,我一定要把你的身體調(diào)理好。”善良能干的鄒佩珠開始養(yǎng)羊養(yǎng)雞,一心撲在李可染身上。
愛是引領(lǐng),不是縱容。有一次,李可染出去辦事,遇到了好聽的戲,居然連聽三天,全然忘記了家中焦急等待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孩子。回家后,從不發(fā)脾氣的鄒佩珠責(zé)問他:“李可染,你要是這樣只迷戲,你的畫還能成嗎?”當(dāng)頭一棒打醒了李可染,從此他心無旁騖,一心鉆研畫畫。這也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對他發(fā)火。
“我把終身托付給他,不只是看中了他的忠厚善良、人品好,更重要的是他有才、畫得好,能成為民族、國家需要的人。如果他一天到晚泡在戲園子里,丟了自己的畫,那我的人生還有什么意義?”在鄒佩珠的支持和鼓勵(lì)下,李可染的畫作受到徐悲鴻青睞,并幸運(yùn)地成為齊白石晚年最得意的弟子之一。齊白石欣賞他的才華,曾如此稱贊:“昔司馬相如文章橫行天下,今可染弟之書畫可橫行矣。”
新中國成立后,李可染當(dāng)選為中國美術(shù)家協(xié)會理事。當(dāng)時(shí)有人認(rèn)為國畫是封建文人畫,于是他產(chǎn)生了革新山水畫的想法。
要想“精讀大自然”,出去寫生是必須的,而這也是鄒佩珠最為擔(dān)心和害怕的。李可染的腳天生畸形,腳底突出一塊,一走路就痛。他的鞋子都是她特殊加工過的,每一雙鞋,她都得在鞋底挖一個(gè)洞,使鞋子剛好合他的腳形,然后再加上一層鞋底。這樣一雙腳要去跋山涉水,她怎么能夠放心呢?
然而他決心已定,她唯有支持。“這輩子我做了多少雙這樣的鞋真記不清了。鞋壞了之后的路程對可染來說異常痛苦,但他還是會堅(jiān)持走完。”幾年時(shí)間里,李可染走遍大江南北,風(fēng)餐露宿,為了寫生,付出了艱苦的代價(jià)。回報(bào)同樣是可喜的:他為中國畫的發(fā)展開辟出一條充滿生機(jī)的新路,兩次“寫生畫展”的舉辦,確立了他在山水畫壇的地位。
軍功章也有她的一半。每次他出去寫生,少則兩個(gè)月,多則半年以上,最久的一次長達(dá)八個(gè)月,行程兩萬多里。盡管家中還有老老小小一大家人,但交給她,他是放心的。
為了讓他全身心地投入創(chuàng)作,曾參加過人民英雄紀(jì)念碑浮雕創(chuàng)作的鄒佩珠放棄了自己鐘愛的雕塑,承擔(dān)起家庭的重?fù)?dān)。幾個(gè)孩子要撫養(yǎng),老母親要贍養(yǎng),李可染的哥哥妹妹有困難也需要幫助,為了支撐一家人的吃穿,她一刻都不能停:白天,她要去好幾個(gè)學(xué)校兼課;晚上,她常常批改作業(yè)直到深夜,一天只能睡四個(gè)小時(shí)。

因?yàn)閻矍椋щy她也甘之如飴。“我很慶幸自己能咬牙熬過來,更慶幸可染在這個(gè)過程中取得了突破。”為了他心中的藝術(shù)理想,她無怨無悔。
“文革”開始后,李可染被剝奪了畫畫的權(quán)利,在連番屈辱之下,他一度罹患失語癥。鄒佩珠日日夜夜守在他身邊,給他講開心的事,聽說要抄家,她整夜不眠,把家里所有的書都拿出來一頁一頁檢查,生怕有什么對他不利的東西。
終于,雨過天睛。“文革”結(jié)束后,李可染重新煥發(fā)出藝術(shù)生命,他的山水畫以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清新的筆墨意境獨(dú)樹一幟,聲譽(yù)遠(yuǎn)達(dá)海內(nèi)外。
好的愛情,是互相成就。他們一起定下目標(biāo),共同努力。她創(chuàng)作的雕塑作品《彭雪楓烈士紀(jì)念碑雕像》《抗日戰(zhàn)爭群雕》成為他們共同的藝術(shù)結(jié)晶。在他的影響下,她的書法和繪畫也有了很深的造詣,書法作品充滿古韻而又不失現(xiàn)代氣息,畫作《雨后的蘇州洞庭東山農(nóng)舍小景》受到美術(shù)界人士的好評。她創(chuàng)作的《蝦》,他由衷地稱贊說比他畫得還好。
看遍山水,晚年的李可染藝術(shù)創(chuàng)作進(jìn)入了更理想的境界。“胸中丘壑,筆底煙霞”,每一幅畫都不只是簡單的風(fēng)景,而是凝聚著他對祖國的深情。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又上高峰之后,他對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上蒼沒有給他更多的時(shí)間—1989年冬天,因心臟病突發(fā),一代大師猝然離世。

初相識時(shí),他只是一個(gè)一無所有、渾身是病的窮教書匠,是她幾十年的悉心陪伴,才讓他有了如此輝煌的藝術(shù)生命。他走了,愛還在繼續(xù):她把“李可染書畫展”帶到臺灣的歷史博物館,以八九十歲高齡不知疲倦地主持出版了幾十種李可染畫集和書刊,還舉辦大型展覽,籌建藝術(shù)基金會,并把屬于自己的200多件李可染作品捐贈給了國家—那些作品的價(jià)值不可估量。
他去世后的26年間,她依然住在他們的舊屋里,嘴里仍舊“可染、可染”地喊著,仿佛一切都沒有改變。2015年5月4日,鄒佩珠去世。傾盡一生,她執(zhí)子之手,讓愛開出了人世間最美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