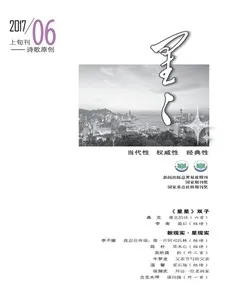生活賦予生活的,比想象更多(組詩)
吊 床
母親從舊衣服摘下紐扣
一顆顆曾經明亮的小鎖,如脫落的牙齒
松開了雙唇
刺啦,刺啦……
離開紐扣的衣服開始破碎,疼痛
院落里,我們停止聊天
質疑著不足以承載遠方的舊時光
母親笑著
把它們團在手心
那天傍晚,再次回到這里
一個布繩吊床——
母親,你懸在兩棵樹之間,一雙手柔軟,又溫暖
雨 上
陽光打進書房的上午
你向我敞開了一個小小的窗口。
最為明亮的部分。我一次次
途經:奶瓶。積木。打翻的水果盤。
我拾起其中的一個——
不同的事物,都有相同的蟲孔?
雨上,想象也許是誤會。
比如陽光,照不進一個人的內心。
比如,你在翻看小人書時
誤以為鮮橙,都有一個甜蜜的父親。
麻 雀
沒有蝙蝠的黑西服,也沒有喜鵲的好心情
自然的族譜里,它們個頭矮小
皮膚土灰,五臟俱全。但它們一再被賦予生活。
比如喜歡在人群中跳躍、張望、偷嘴兒
比如迷戀天空
樹枝,和人們保持飛行的距離
到了秋季,它們會成群結隊
從一個地方風暴般,突然升空,在稻谷和玉米的頭頂
盤旋。墜落。順手牽羊。
為了生存,它們不得不在飛行中覓食,做愛
拎著尖爪,完成遍布世界的霸業
這些好像并不是它們本意
它們中大多數和我一樣生活在鄉下,喜歡在自然的記事本
書寫自己的弱小,土氣,膽兒大
活在屋檐下
觸 角
生活賦予生活的,要比想象
饋贈的更多。想到的時候,已是中年的深夜
窗外的黑,是零下的冷風
打掃著城市的街道
沒有人。只有孤獨的路燈
在微微地等待
布羅茨基,獨自一人在紐約大街上穿行。
心里,裝著俄羅斯的冬天
那里有幾個牽掛的人,圍著一堆木柴寫著書信
異鄉的故鄉,并不缺少伙伴
但這里并不適合久居
他要穿過這條路,來到威尼斯的圣米凱萊
把自己和俄羅斯,種在石碑上
命運是命運的試圖
這樣的談話,顯然是一個人在說,一個人
取出詞語的剪刀
修剪著枯枝,和生活的毛邊
假設,這是一盞小燈的夜晚
那一定是生活賦予生活的,比想象更多。比如一些文字
黑螞蟻般排著隊伍
你們相互碰撞著觸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