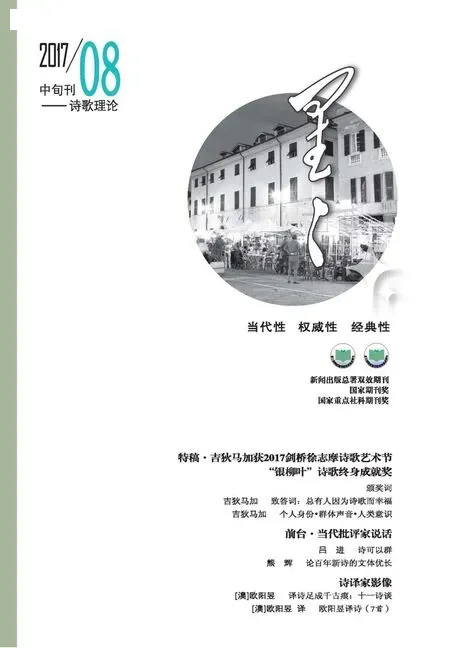有“度”的詠嘆調
盧貝貝
代 薇
有“度”的詠嘆調
盧貝貝
羅蘭·巴特高呼“作者之死”,讓我們對話前人作品時更理直氣壯,而當我們加入現代詩歌的宴席,巴特的這碗“壯膽酒”似乎降了度數。對于開放動態的詩歌文本,一定程度上的“誤讀”提供了闡釋的可能,闡釋屬于大眾,而詩歌的形成卻更私人化。詩人通過自我觀照,“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詩歌是詩人的詠嘆,他們或燭照內心,或直視身體,或洞察世界,本期的《停頓》《身體里漸漸有木質的東西》和《動搖》這三首詩,正體現了詩人們自我觀照的不同維度。
一輪圓滿可以在回憶里待續,半生遺憾何嘗不是在記憶里添油加醋?《停頓》一詩“我記得夜晚的唱片”,它的旋律還飄渺著那晚的蜃景。“我記得無能的力量”,揮拳無力的空虛,忍痛與世界妥協,卻偏不握手言和。“我記得你的眼睛”,它們有淚有痛有傷……代薇的詠嘆戛然而止,記憶卻彌散開來。結構主義詩學大家尤里·洛特曼認為,詩篇中看似完全重復的單位,其信息含量隨著位置的改變而改變。三個“我記得”在語法層是對等的,其結構在聚合軸上形成平行對照關系,遺憾的是語音層過于自由,未能錦上添花,在語義層上情感則層層深入。“唱片”“金屬”“火車”和“眼睛”蒙太奇式的跳躍,無意完整地講述什么,反而營造了回憶的模糊惆悵。整首詩的基調,看似是“失溫”的冷,“無力”的痛,而三次娓娓道來的“我記得”,卻升騰起脈脈含情的暖,正因為對記憶有情有義有溫度,才這般念念不忘。或許,這列移動的火車是命運樂譜上一個轟隆隆的休止符,停歇了一場本應繼續的故事。亦或是隨君直到夜郎西的明月心與火車同速同步,移動的火車反而像是自欺的靜止。我有富足的回憶,你的眼睛是否也記得我?
詩人窗戶也“只剩回憶了”,在《身體里漸漸有木質的東西》一詩中,年少時蕩漾的波心從圈圈漣漪變成同心圓的年輪,木質化的身體,有著陰陽割昏曉的紋路。詩人烹煮煎熬的粒粒文字——“木質”“水面”“愛情”,都淘洗于日常生活的米袋,為何詩歌并未因此而變得清淡寡味?現代語義詩學學者C.T.佐梁給出答案:詞被選入詩歌之前,本身就是多義的,潛在的意義相互指涉,詩歌就變得飽滿。“木質”指涉的是堅硬、成長、大地。生命經歷風沙的砥礪,逐漸纖維化,有的人干涸腐朽了,有的人獲得雨露的滋潤,茂盛于天地之間。木質化的我們如何獲得這份生命之水?詩人并未告知。他只是翻開記憶的口袋,蕩漾著青春的花葉與少女的裙擺,它們或許曾帶來一場暴雨,摧枯拉朽,又使人愈發堅韌成長。待盛夏明媚,木質的心,也會不期然地吐翠。
當人與木同構,心意便漸漸共振,目之所及皆生機勃勃。針對《動搖》一詩,在詩人眼中,路的拐彎也是野性的,詩人繼而把視野交給大雁,用雙翼丈量大地,俯視生動的草原,把握生命的脈搏。在這里,生命的誕生與捕獵的死亡同為一瞬,神圣與殘忍共為一體。詩人沒有沿著大雁的視線繼續展開,而是含蓄地吐露心事,他將“由于”獨立于詩歌一行,行末的停頓使完整句法一分為二,產生邏輯重音,于無聲處的停頓卻是另一種方式的呼喚,是詩人情感波動的表征。詩人也曾是“我們”中的一員,他似乎發現了什么而內心動搖,委婉地責怪風沒有吹來生之旋律,卻對“我們”不置一詞,這般謙虛有禮,實然已與“我們”保持了距離,這便是詩人敬畏生命的態度。
“停頓”的代薇燭照內心宇宙,呢喃過往,有溫度地自我慰藉;審視“身體正木質化”的窗戶,云淡風輕,有濕度地進行“光合作用”;正發生某種“動搖”的余真,俯瞰大地,有態度地指出人類過失。溫度、濕度、態度是三代詩人發聲抒情的不同音色,構成人生樂章的復調詠嘆。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
本期推薦詩歌
停頓
代 薇
我記得夜晚的唱片,金屬彎曲
漸失的體溫
我記得無能的力量
世界不可改變的方向
——痛心,執迷
移動的火車像漫長的停頓
我記得你的眼睛
像一個傷口挨著另一個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