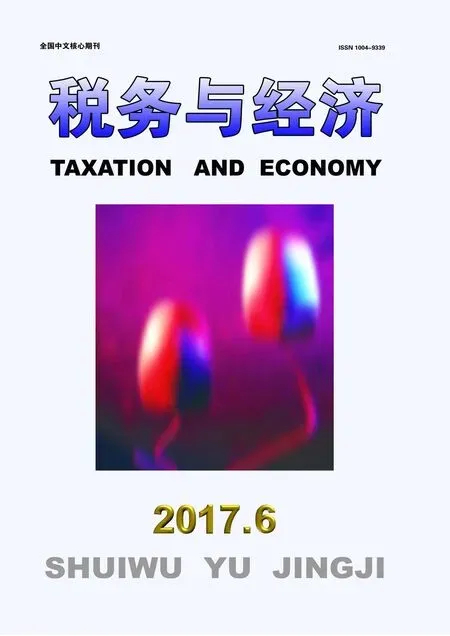中國沿海地區先行崛起的理論基礎與轉型路徑
姬 超
(1.許昌學院 中原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河南 許昌 461000; 2.山西大學 中國城鄉發展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在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現有的許多研究習慣于將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看待,但事實上我國不同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十分巨大。而在討論區域分化和引致差距的原因時,許多文獻又先驗地認為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起點是沿海地區,正是先行一步的優勢,導致了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那么,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率先崛起的條件和理論基礎是什么?這是本文在解讀中國經濟增長時所要重點回答的問題,也是本文的邊際貢獻所在。筆者認為,就中國不同區域的發展差異展開剖析,有助于克服單純地將中國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分析時所不可避免的合成謬誤問題,也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國經濟成功的真實經驗,同時更加客觀地理清中國經濟未來轉型的方向。
一、世界先行地區的崛起過程回溯
(一)先行地區如何實現最初的經濟起飛
這里的先行地區主要指的是發展初期就采用了英美憲政體制的歐美發達國家,也即“盎格魯—撒克遜”傳統文化映照下的發達地區。在一定程度上,當前主流經濟增長理論刻畫的正是先行地區的增長故事。自18世紀率先開啟工業革命的英國開始,人類近代史上首次出現了持續的經濟增長。隨后,現代經濟增長迅速向歐洲大陸其它國家擴展,進一步又擴展到了美國、加拿大等新大陸國家。新大陸的發現使得歐洲面臨的傳統資源約束得到改善,資源稟賦狀況發生了極大變化。新大陸的發現令英國等國家獲得了意外的資源暴利,包括殖民地廣袤的土地資源、糧食、棉麻、燃料等生產資料,同時將本國的紡織品大量輸出。在這個過程中,農業勞動力得以從土地束縛中釋放出來,為英國工業革命在全社會的全面展開創造了條件,以蒸汽機為代表的技術進步不斷發生,經濟開始持續增長。與此相反,資源稟賦特征決定了亞洲在當時只能沿著節約土地和吸納勞動的農業發展道路繼續緩慢前行。歷史大分流就此形成,西歐國家開始將中國等東亞國家遠遠地拋在了身后[1,2]。
(二)先行地區增長速度緩慢而持久的原因
總體而言,歐美先行地區的增長過程是極其緩慢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只有1%~2%,但這種增長卻持續了驚人的一至兩個世紀。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導致先行地區增長如此緩慢卻又如此持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先行地區增長速度普遍較為緩慢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一套完善并且可信的產權體系和市場交易規則對于歐美先行國家的持續增長必不可少。但是這一制度體系的形成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而是一個逐漸生成和完善的過程。特定的資源稟賦和經濟條件決定了什么樣的制度體系最具適應性,但是先行地區并無現成的制度規則可供直接模仿,只能在長期的探索過程中不斷試錯,通過經濟主體之間的互動博弈,最終才有可能形成一套全社會都認可的制度體系。[3]
在先行地區內部,不同國家的制度演化路徑也存在差異性。對于后發地區而言,它們既可以選擇全盤復制先行者的制度模式,也可以選擇不模仿。例如德國和美國就沒有選擇完全復制英國的個人資本主義模式,而是在其基礎上逐漸摸索出了管理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最終實現了對英國的全面超越。可見,即使沒有先行優勢,如果能夠充分發揮自身資源稟賦,并在此基礎上實現相應的制度創新,就有可能完成對先行地區的超越。如果只是一味地進行制度模仿,不僅可能遭遇水土不服的適應性困境,還可能長期陷入追趕陷阱。
二、我國沿海地區的崛起路徑和發展特征
(一)沿海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的形成路徑
作為我國最早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區域,沿海地區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與歐美先行國家的增長模式不同,這體現在沿海地區30多年經濟增長主要并不是由農業部門驅動(盡管我國經濟改革的起點始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主要在于工業推動的新興工業化戰略。工業化,特別是制造業擴張貢獻了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
與歐美發達國家不同,我國沿海地區在經濟起步時面臨更多的路徑選擇。歐美發達的市場為我國沿海地區率先實施工業驅動戰略創造了條件,它們不必再由農業部門緩慢地積累原始資本,這是沿海地區經濟迅速起飛和高速增長的重要前提,也是沿海地區高投入經濟增長方式的現實背景和前提條件。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體制的引入為沿海地區利用當時的國際產業轉移創造了條件,對外開放政策迅速吸引了大量內地的剩余勞動力,也吸引了大量的外來資本。[4]
(二)沿海地區經濟增長的外延式特征
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我國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差距越拉越大,發展水平明顯高于內地。但是以資本和廉價勞動力投入為主的“外延式增長”方式仍然非常明顯,大多數沿海地區始終沒有形成技術進步的內生機制,技術效率始終不高。一旦失去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的空間,要素使用效率就會迅速下降。
二戰后,現代民族國家紛紛獨立,毗鄰我國的東南亞國家率先發力,在“領頭雁”日本的帶領下,逐漸形成了兩翼齊飛的雁陣式發展模式。該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強烈的出口導向性,不同國家漸次起飛,不斷加大對歐美國家產業轉移的承接力度。在這個過程中,國家之間也面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最為典型的,亞洲四小龍地區需要同時面對其它“三條龍”的挑戰,而這些國家和地區在戰后對發展的需求都極為迫切。可見這些國家在世界分工體系中不僅面臨垂直層面的壓力,還面臨水平層面的直接競爭(美國、德國、法國等歐美“后發”國家在經濟起飛時的背景與此類似),迫使這些地區在經濟增長初期就不得不注重經濟內部的運行效率。[5]
反觀我國,20世紀80年代,沿海地區率先通過改革開放融入世界分工體系時,承接的則是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此時在水平層面與特區形成直接競爭的國家或地區幾乎沒有,國內其它地區的發展程度和對外開放程度普遍較低,這就導致沿海地區缺乏對經濟運行效率的重視。但是,忽略經濟基礎運行效率的弊端很快就湮沒在了巨大的經濟進步浪潮中,通過承接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移,沿海地區也可以輕易地獲得外生性的技術進步,因而投資效率在當時還不成為一個問題。然而隨著承接國外產業轉移的結束,沿海地區產業已經發展到相當高度,外延式增長方式就會立刻面臨動力衰竭問題。
三、我國沿海地區當前面臨的發展困境
(一)沿海地區經濟不可持續增長的直接原因
當前,沿海地區經濟超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經濟下行的趨勢非常明顯,并且成為難以改變的事實。筆者認為,以資本為代表的要素投入減少并非沿海地區經濟不可持續增長的根本原因,關鍵在于投資效率。一旦投資效率開始下降,可持續的增長就會遭遇挑戰,特別是在資源約束趨緊的情況下。理論上導致投資效率下降的原因有二:一是資本密度的上升,過度投入和減少勞動力數量都將導致資本密度上升;二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不斷下降,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又包括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等。這就意味著,決定投資效率的是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而不僅僅是要素投入數量。[6]現實中,導致沿海地區投資效率下降的原因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差異的一面。
(二)沿海地區投資效率下降的共性因素
1.通過承接國外產業轉移提高技術水平的方式接近尾聲。由于沿海地區經濟已經發展到相當高度,通過承接發達國家和地區產業轉移的空間已經非常有限,直接引進或模仿先進技術的方法已經行不通,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逐漸下降,其中技術進步的增長率下降得尤其明顯,這是我國沿海地區整體上都面臨的問題。
2.一味追求高新技術行業的政策傾向無法從根本上提高技術水平。為了提高技術水平和產品附加值,許多地區對高新技術行業表現出更強的偏好。或者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生產線,或者鼓勵自主研發提高產業層次,但卻忽略了產業之間的互補性,導致技術溢出效應不明顯,某一領域突破性的技術進步并不能持續地提高整個經濟的技術水平,于是表現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的大起大落,技術在整個經濟體系的深化不足。
3.外來勞動人口數量減少導致資本密度增加。隨著國內其它地區的發展,以及生活成本的提高,沿海地區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逐漸下降,勞動力增長率迅速下降,繼續增加投入很容易造成資本密度增加,即使在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不變的情況下,投資效率也會下降,導致粗放式增長。同時由于全國整體層面的人口紅利正在消失,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
4.較低的技術效率制約技術的應用。從全要素生產率的構成來看,大多數沿海地區的技術效率增長率落后于技術進步,在部分地區和階段,技術效率甚至呈現下降趨勢,這種局面持續至今并且有加劇趨勢。隨著發展程度的提高和國際市場的飽和,這種增長方式就將面臨可持續難題。
(三)沿海地區投資效率下降的個性因素
隨著經濟發展程度的提高,特別是國外發達地區的產業發展也已趨近技術前沿,我國沿海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逐漸失去了依靠外生技術引進獲得增長的條件,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持續下降,近年來這種趨勢更加明顯。除了技術效率增長率始終較低之外,制約不同地區繼續增加投入的原因還有所不同:一部分沿海地區的問題在于勞動力增長率的迅速下降,繼續增加投入必將引起資本密度上升和資本邊際生產率的下降;另一部分地區由于過早地追求產業高級化,忽視了產業之間的合理化,產業之間缺乏互補性,導致外生的技術進步產生不適應性,要素配置極不合理[7],繼續增加投入只能進一步加劇資源浪費現象;還有部分地區則是兼具產業合理化和產業高級化兩方面的問題,農業和服務業比重過高,工業基礎過分薄弱,投資機會過少,投資效率始終較低。
(四)進一步釋放沿海地區經濟增長潛力的方法
由于我國沿海地區的產業層次已經達到相當高度,技術接近前沿,因而繼續通過產業轉型升級大幅提高技術水平的余地不大。為了進一步釋放增長潛力,沿海地區一方面要強調技術深化,增加技術革新的強度。通過產業之間的合理化實現更寬廣領域對當前技術的采納,增強技術溢出效應,實現技術邊界的循序漸進的外移,而不是盲目追求重要的技術突破。當前,大多數地區的發展并沒有達到現有技術與生產能力所允許的最大產出邊界,因此,現代技術并不構成經濟進一步增長的瓶頸,真正的瓶頸在于廣大低附加值行業對技術應用的限制。
另一方面要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實現要素的跨部門再配置,進而提高技術效率。然而要素的自由流動在沿海地區也面臨嚴重的障礙,特別是競爭性行業和壟斷性行業之間的要素流動更加困難,也就制約了要素向高生產率行業的流動。[8]最終,要素只能在生產過剩的行業領域集聚,要素生產率進一步下降。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減緩,為了維持一定水平的經濟增長率,各地政府只能不斷尋找新的增長點。在扭曲的經濟環境和產業結構下,許多產業政策對經濟主體的激勵也必將扭曲甚至無效,要素的使用效率也是不可能得到提高的。
四、新常態下我國沿海地區的轉型路徑
我國沿海地區經濟起飛時面臨的是國內其它地區極其落后、國外先行地區高度發達的環境,如今的轉型則是面臨國內其它地區高速增長、國外先行地區經濟持續低迷的環境,繼續依靠特殊政策獲得增長優勢的方式不再可行。已經發展到一定高度的沿海地區不得不在面臨國內外雙向競爭的背景下,爭取進一步深化分工格局,在更高價值環節獲取競爭優勢。具體的,我國沿海地區的轉型發展至少包括以下幾個相互關聯的有機部分:
(一)從“總量導向”向“質量導向”轉型
在新的國內外形勢下,繼續追求高速經濟增長已經很難實現,區域競爭主題將由經濟總量的競爭轉換為經濟增長質量的競爭。目前,沿海地區經濟已經發展到相當高度,超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但是考慮世界其他趕超型國家和地區的增長情況,盡管沿海地區當前增長速度有所降低,只要能夠維持足夠長時間的增長,沿海地區也必定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沿海地區經濟的未來就不再是繼續通過要素驅動維持超高速的經濟增長,而是在日益緊張的資源約束條件下,通過創新驅動實現盡可能長時間的增長,哪怕增長速度在一定時期內有所下降。
(二)從“以開放促改革”向“以改革促開放”轉型
從轉型的方向來看,歐美發達地區并不能先驗地成為我國沿海地區未來轉型的模板,沿海地區經濟存在于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更為現實可行的轉型方向在于“由外到內”向“由內到外”的轉變,即從“以開放促改革”向“以改革促開放”的思路轉變。輕率地否定外向型經濟方式在當前并不可行,無論是沿海地區還是中國整體,在短時期內迅速轉型為內向型增長方式并不現實。在當前外貿形勢不斷惡化的背景下,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很難持續下去,沿海地區必須以全新的姿態加入到世界分工體系中,改變傳統的生產、加工、制造等低端位置,在更高附加值的設計、研發等環節與發達國家展開競爭,而不是簡單地否定外向型增長方式。
(三)從技術革新的“速度”和“高度”向技術革新的“強度”轉型
對于沿海地區未來經濟的持續增長而言,制約瓶頸并不是可以應用的技術的缺乏,而是對技術應用本身的限制。為了實現‘斯密式內生增長’,沿海地區必須在實踐中強調對原有技術的更好采納,強調技術邊界循序漸進的外移。當經濟和技術層次發展到一定高度時,繼續依靠重要的技術突破維持長期的增長并不現實,更為可行的方法在于通過激勵廣大部門的組織方式更新,將經濟體系的專業化推向新的高度,從而增強整個經濟體系的技術強度。在此基礎上形成技術進步的內生機制,保證新的技術突破的適應性,而不是盲目地追求技術的高度。
(四)從“為市場而生產”向“為市場而競爭”轉型
對于我國大部分地區而言,供不應求和短缺現象都是經濟增長初期面臨的主要問題,在這一階段,競爭性市場的缺乏使人們很少有進行深層次的技術自主革新的積極性。但是隨著經濟發展程度的提高,大部分領域逐漸面臨生產過剩和投資效率下降局面,就有必要強化人們為市場而競爭的積極性,打破行業和地區之間的壟斷格局,在更加廣闊的領域鼓勵人們加強市場競爭,實現對生產的投資向對競爭的投資的深刻轉變,從根本上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9]
五、我國沿海地區崛起過程帶給后發地區的經驗借鑒
前文從整體上概括了沿海地區經濟轉型路徑的主要內容,但是沿海地區內部的增長差異也必須得到重視。同樣是沿海地區,面臨大致相似的政策和國內外發展環境,但是不同的地區在利用發展機遇方面存在很大不同,經濟增長方式也有所不同,增長的結果因而存在很大差異。例如,有的地區的初始資源稟賦雖然不夠好,但是通過積極融入世界分工體系,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完成了對其他沿海地區的全面趕超。與此同時,也有部分地區并沒有充分挖掘最有效的經濟增長方式,經過30多年的差異化增長,沿海地區之間的差序格局逐漸形成。新的發展階段和發展環境中,沿海的不同地區也都面臨著相應的問題和困境,轉型的重點因而有所不同,能夠率先創新突破制度瓶頸、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地區也將獲得新一輪的增長優勢,甚至改變當前的差序格局。
1.第一層次:上海、深圳、廣州等一線城市。這類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經接近甚至超越高收入國家,相對其它沿海地區,這些地區的技術高度和技術效率都顯著占優,產業層次業已達到相當高度,通過承接發達國家和地區產業轉移的空間已經很小,也就意味著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并不大,進一步的增長必須依靠技術邊界的外移,實現新的技術突破,與世界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展開直接的競爭。
2.第二層次:廈門、珠海、蘇州、天津等二線城市。這類地區的主要問題在于較低的技術效率水平,也就是外生性的技術進步,這種差異意味著這類地區基本上已經不具備繼續承接發達國家和地區產業轉移的空間。由于產業轉型升級是通過要素再配置提高要素生產率(包括單要素和全要素)水平傳導至經濟增長的,增長的本質要求人們重點關注要素質量的提升而不是要素數量的增減。然而在扭曲和僵化的市場結構體系下,單純強調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或許能夠在短期促進經濟增長,但卻導致了市場參與者的短視行為,無助于經濟結構的長期優化。由于過分追求產業高級化而忽略了產業合理化,導致產業之間的互補性不足,無法發揮協同效應。因此,對于這些地區的經濟轉型而言,繼續追求產業高級化并不可行,通過產業合理化實現產業之間的協調互補才是關鍵,例如,重點推動資源要素的跨部門流動,通過技術外溢效應增加各個行業的技術強度,最終提高整個經濟體系的技術水平,這也是這類地區繼續追求高新技術產業和技術邊界外移的基礎和前提。
3.相對落后的沿海地區,例如海南和汕頭。這類城市的主要問題在于較低的技術進步水平,表示這些地區仍然可以有選擇地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盡快提高技術水平,通過工業深化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例如,海南的困境在于過分龐大的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導致海南同時面臨產業合理化和高級化的困境,薄弱的工業導致海南無論是農業還是服務業都無法走得更遠,區域一體化和對外開放顯然還沒達到足以彌補這種產業體系失調的程度。[10]汕頭的困境類似于我國整體的情況,過分龐大的國有經濟比重仍然是制約汕頭經濟活力的重要因素。
因此,對于沿海地區的轉型,結構調整應做為主要內容,盡管調整的重點有所不同。可以推斷,全國其它相應區域類型,也都相應面臨著各自的轉型困境。總體而言,沿海地區最為關鍵的問題都在于繼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但是全要素生產率是由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構成的,不同地區在這兩個方面存在很大差異。由此可見,較低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不一定是因為技術水平低,也有可能是經濟運行效率低和外生性的技術進步造成的。
六、結 論
綜上所述,我國沿海地區經濟起步時面臨的國際環境完全不同于歐美發達國家,與東亞發達地區也有所不同。改革開放以來,沿海地區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水平也有了很大程度提高,這主要是由經濟結構的迅速變化和簡單復制先行地區技術帶來的快速技術進步造成的,而通過要素跨部門流動和再配置實現的技術效率增長始終較慢。這是我國沿海地區經濟不能形成內生性技術進步機制和“內源式增長”的主要原因。長遠來看,我國沿海地區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勢在必行,轉型的關鍵在于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一方面要強調技術深化,增加技術革新的強度。通過產業之間的合理化實現更寬廣領域對當前技術的采納,增強技術溢出效應,實現技術邊界循序漸進的外移,而不是盲目追求重要的技術突破。另一方面要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實現要素的跨部門再配置,特別是打破壟斷性行業的進入障礙,進而提高技術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1]文貫中.中國的疆域變化與走出農本社會的沖動——李約瑟之迷的經濟地理學解析[J].經濟學:季刊,2005,(2):519-540.
[2]郭金興.技術進步、制度變遷與資源暴利:中西方歷史大分流的解釋與啟示[J].經濟評論,2009,(2):122-126.
[3]姬超,等.可持續和過程視閾下的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一個基于供給創造需求范式的分析[J].稅務與經濟,2013,(5):10-15.
[4]姬超,袁易明.中國經濟特區差距的變動趨勢及其影響機制[J].亞太經濟,2013,(5):119-126.
[5]姬超.韓國經濟增長與轉型過程及其啟示:1961~2011——基于隨機前沿模型的要素貢獻分解分析[J].國際經貿探索,2013,(12):45-60.
[6]姬超.投資效率與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趨勢考察——基于中國經濟特區的差異比較分析[J].財貿經濟,2014,(3):91-99.
[7]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77-102.
[8]袁易明.中國所有制改革對效率改進的貢獻[J].中國經濟特區研究,2008,(1):27-45.
[9]張軍.改革、轉型與增長:觀察與解釋[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10]姬超,袁易明.中國經濟特區發展和轉型的制度本源效應追溯——基于特區經濟發展30年的經驗證據[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6):6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