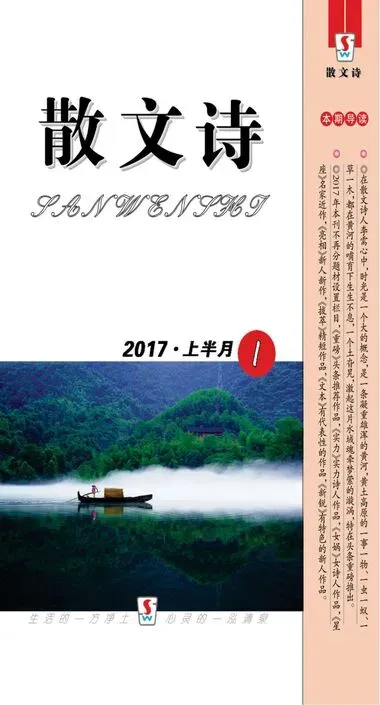柳堡風
江蘇◎王壟
柳堡風
江蘇◎王壟
柳堡風
當我一次次在柳堡風中蘇醒,仿佛對生命有了全新的體驗。
比向往要近的村莊,好像是肉身206塊骨頭的集中。
沒有人拒絕這自由的飛翔。
農舍保持著尊嚴。大地的寬容,在日月的更迭中顯現。
我喜歡,在這古樸而新穎的內省里靜坐。柳堡,如行走民間的華佗,用遼闊、茂盛的莊稼、草木,以及上等的流水和鳥鳴,給我煎熬靈魂向上的偏方。
每一棵樹,都鐫刻著地理性標志。誰要嘗試去除那獨特的胎記,誰就會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找不到江山,找不到萬物,找不到祖先,找不到自己。
青銅從風俗里起身,矗立著鄉土文明的頭顱。綠色的風,吹過情感的湖泊,緩慢地駛向夢境。
仁義似金,道德如銀。第四種宗教,被柳堡認可。留住千年不腐的根,這是柳堡風教會我的唯一選擇。
泥土的氣息,燈火的味道,老家的心跳。
方言俚語,還在繁衍。
朝霞夕光,依然延續。
柳堡的信仰,在風里傳承,就像開闊的道路,帶給我們更多的忠貞和陌生。
草木
做一株草木,隨了柳堡的姓,叫做柳堡的名,多好!
精神從根部上升,靈氣在身上集中。
不求多么高大、偉岸,在綠色的底層,與大地保持最近的距離。風,是最干凈的一縷。葉子因陽光和雨水的豢養,有著青春的膚色。
生長于野外,自由在荒地。植物中的隱士,與四季同步,讓節氣做了生態的奴隸。
花開,或者葉落,總順著柳堡的脾氣賣萌。星星,鳥語,在林陰間斑駁。一張張和藹可親的面孔,安靜地忽略了生死、枯榮。
依稻麥為鄰,傍瓜果成友。
柳堡的草木,以纏繞的藤蔓、執著的根須,熱戀著鄉土。是什么讓它們表現得如此神圣,我看見它們,就看見了柳堡的親人。
善良的羞恥,可以借一雙綠眼審視。我旁觀著柳堡的草木,柳堡的草木卻思辨著整個人間。
簡單,平淡。世界歸于一,命運類似草木。
俯下身體,仔細聆聽柳堡草木的心跳。繁華如煙,名利虛空,唯有草木教會我們健康、愛情和歡樂的真諦。
線裝的柳堡
新潮的柳堡,過于喧囂。血壓升高的夜晚,夢,都難得做圓。
那陳舊泛黃的歲月,像是一本線裝的古書。我在木刻年畫的志趣中,遇上了小村吉祥女巫。這怪怪的癖好,不會比喜歡一個名字,還要執著。
沉湎于老式的愛情、老套的傳說,不能自拔的我,任天空被白云拐跑,河流讓魚兒搶先注冊。
我甘愿在風車下打盹。野兔、野鴨,還有不可一世的田鼠,在鄉村的大舞臺上,或自由穿梭,或翩翩起舞。
往事的蹤影,無法分配給死亡。
記憶保存的那些種子,在拓荒者胸懷,生命力蓬勃。
我只是對黑白的影像沉醉著迷,我催促彩色的鏡頭快快切換到過去。
早期的雨水,下在干涸的心田。那條叫母親的河流,馱著我寓言般的乞求,在紙醉金迷的城市,向童年的鄉村回溯。
耕牛,已走出田壟的畫框。
越來越稀罕的野草,提醒我趕緊把柳堡的故事收購、存貯。
還有一百米的距離,我們就能走進那一首經典的老歌。但是,小學課本上的那些音符,也許下輩子才能再次觸摸。
瓢
我用瓢舀起柳堡的凈水,或白花花的米。
幸福,允許小容量地放縱。
這分娩于瓠子或者葫蘆的家什,在母親的手上,成為柳堡最后值得信奉的事物。
時光和夢想在瓢里積淀。一只反扣的空心的木魚,發出銅鈸的聲音。一種孤寂,柳堡的缸和壇子聽得最清。
與莊稼一樣來自于土地以及根與藤的民歌,保持鄉下孩童一般的膚色。父親制瓢的日子,是一種過程,也像一種儀式。
游弋在回憶里的瓢,仿佛盛滿了柳堡前世的月光。
我觸摸過一種土老帽的氣息,也領略了近似寶盒的神秘。
柳堡的瓢,以完美的曲線和外形,搖曳成和詩一樣深邃的思念。
把內心的貧困舀干,瓢把它純粹的名字,安置在我們精神的家園。
在金黃色的深處,瓢,如同詭異的符號,攜帶柳堡的吉祥與祝福的隱喻。我的胸懷被瓢的目光打磨得精細而寬廣,那些與瓢有關的段落,貫穿于我中年的血脈——
“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