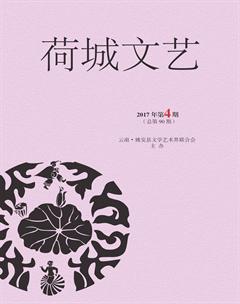偷渡者
段海珍
有新聞報道疑似某失聯航班的飛機殘骸在南印度洋被發現,新聞最后并沒有說出是不是真的。莫小貝看見這條新聞的時候,心里有些莫名的難受,她說不清楚什么感覺。總之,她心里覺得很不是滋味。
最近,飛機失事的新聞接連不斷,弄得每次乘飛機都有想要寫好遺書的沖動。莫小貝想,世事無常,那樣的事最好不要發生在自己和親人的身上。說起親人,其實對于從小就是孤兒的莫小貝來說,除了未婚夫梁良是她在這個世界唯一的依靠,她已經沒有任何親人。莫小貝索性關上電腦走出房間。她想出去透透氣。她最近以來莫名其妙的煩躁和郁悶。莫小貝的郁悶是從被公安機關傳訊后開始的。
莫小貝卷入了一起非法集資案,被公安機關列為偵查對象。由于案件涉及資金數額巨大,人員范圍廣,莫小貝被指定只能在允許的范圍內活動。也就說,一段時間里,她堂堂一個高學歷的女子,就只能在超市與菜市場活動,而不能走出小城半步。在這段時間,只要她一走出所規定的活動范圍,手環就會發出滴滴的報警聲,她的行蹤就隨時會被公安機關電話跟蹤問詢。
傳喚順序是按照資金的大小數額來排序進行。莫小貝涉及的資金數額是五萬元。她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才會輪到自己,就只能在焦躁中等待著配合公安機關調查。
二
在一個百無聊賴的早晨,莫小貝去了一趟菜市場。她的未婚夫梁良已經好久沒和她見面了。梁良在參與一個試驗項目,已經兩天兩夜沒有休息過。當然,這些信息都是她從電話里知道的。
莫小貝到菜市場買了二兩菠菜、一兩豆芽,一朵西蘭花和四兩牛肉。莫小貝準備給梁良做一頓豐盛的午餐,叫他中午一定要回來吃飯。
莫小貝走出菜市場后,又折回去買了一只烏雞和四兩蟲草花。他要給梁良煲一鍋蟲草花雞湯。在買蟲草花的時候,莫小貝聽見有人議論說,一會兒將有一批新鮮的荔枝要運往鎮南超市。她想直接去鎮南超市等待新鮮荔枝,卻又覺得那樣的等待沒有底。她只好先回家一趟,然后又再來超市。
莫小貝是剛從外地趕回來準備與梁良完婚的。可是,梁良一直都未曾謀面,他被一個科研項目組抽調去工作了。莫小貝在一中教書兩年后,由梁良自費供她去讀環境保護專業的研究生。一個月前,她研究生剛畢業正在待業。莫小貝決定完婚之后,又再另找工作。作為孤兒的莫小貝來說,她一直有個想法就是要做一番大事業來報效社會。當然,這其中的辛苦她可以忍受。
正在籌備婚禮的這段日子,一個多年不見的同學突然找上門來,說急需一筆資金周轉,希望莫小貝能夠出手相助。那同學是做家居市場的,是莫小貝高中時的舍友。高中時,那女同學整天一副假小子打扮,隨時充當莫小貝的保鏢。這次見面的時候,假小子完全改頭換面打扮成一幅精品女人形象。女同學這次上門,說她有一個上千萬的新店開張急需資金周轉一下。莫小貝覺得還有三個月才到婚期,也不急等著錢用,就在電話里和梁良商量把準備婚禮的錢暫時借女同學用一下。
梁良很爽快就答應了。他說,只要你覺得可行就行,我沒任何意見。
女同學借到錢后,便沒有了音訊。莫小貝反復打她的電話都是無法接通。后來,有同學告訴莫小貝說,那女同學不僅僅只借了莫小貝同學的錢,她同時還借了其他同學的錢。這個過程,她是在不斷地換著電話和各種借口找同學借錢的。
莫小貝從別的同學那里問到女同學的新號碼后,給她電話說,下個月十九號是我們的婚期,希望你能盡快把錢還回來。
女同學輕描淡寫地說,前些日子是我到廣州選貨去了,換了個手機號,你不要緊張。她這樣一說,反而讓莫小貝有些不好意思了。
末了,她對莫小貝說,你把卡號給我,我馬上就把錢連同利息一起打過來。
莫小貝把卡號告訴她后,就耐心地等著她把錢打過來。一周又過去了,依然什么動靜也沒有。不斷有同學傳來消息說,女同學還在換著電話借錢。
還有兩個月就到婚期了,莫小貝無可奈何又給她打了電話說,做人要講信用,借錢應該好借好還。
女同學不悅地說,你別緊張嘛,再等幾天,我就把錢打過來,我現在是正忙著新店開張的事情脫不了身。
莫小貝沒有了等的耐心,她對女同學說,如果你再不還錢,那就法庭上見。
莫小貝很干脆地掛了電話。
她以為這種激將法會起到促進女同學還錢的作用。結果莫小貝還沒有來得及與她對簿公堂,就被公安機關傳喚問詢了。原因是莫小貝借給女同學的錢,被一個小貸公司卷走了,莫小貝是第三方,需要在規定的時間地點配合公安機關偵查。
莫小貝莫名其妙被卷入了一起金融案件,還被列入了偵查對象。
案情一出,莫小貝感到郁悶至極。她一邊是被案件牽扯,一邊是自從她回來后,梁良還沒有露過一次面。整個婚禮的事宜都是她一個人在籌劃張羅。梁良只是在電話里和她作一些簡單的溝通。
莫小貝的錢被騙之后,梁良并沒有一絲責怪她的意思,只是在電話里安慰她說,事情總會有個水落石出的。他說,這件事,一開始就決定了會是怎樣的結果,只是我不忍心阻止你。現在只能把婚禮擺一下吧。
莫小貝讀不懂梁良的意思。她能感覺到梁良好像并不急于婚禮的籌辦。
莫小貝陷入了一種無比郁悶的狀態。更多的是梁良如此寬容和冷漠的態度讓她郁悶。要是梁良能夠埋怨她幾句或者當時就阻止她,她心里可能會好受一些。
一個月以來,莫小貝都是在懊惱和郁悶中度過。雖說梁良很早就說過,等你一畢業,我們就籌備婚禮。莫小貝回城都快一個月了,他卻沒露過一次面。
在莫小貝讀研的這幾年里,除了每天在長長的電話粥里感受他對她的關懷和溫暖,莫小貝幾乎沒見過梁良的面。每次假期回來,梁良都是那么巧合地被抽調到課題組去了。梁良只是每個月準時把錢寄過來,而且他每次都會多匯一些錢給莫小貝。天熱了,梁良會叫莫小貝給自己買條裙子。天冷了,梁良會叫莫小貝給自己買件棉衣。熱戀中的人幾年互相不見面,這邏輯在常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可是,對于莫小貝和梁良這樣有著遠大理想和抱負的年輕人來說,他們互相完全可以理解。
莫小貝非常理解梁良的工作,他參與國家重大環保科研項目,有時被某個課題組抽調,就是半年八月被安排在基地難以脫身。在莫小貝讀研的這些日子,梁良每天三次電話問候雷打不動。莫小貝每天都是在梁良溫暖的叫早聲中醒來,又在梁良溫暖的問候聲中幸福地睡去。不見面的這些年,莫小貝已經迷戀上了梁良清朗甜潤的聲音。
和梁良相愛的日子,莫小貝覺得她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莫小貝最大愿望就是學成歸來后,她就可以長久地和梁良呆在一起了,他們可以一起共同來完成對人類最有意義的事業。
莫小貝精心地給梁良煲了一鍋蟲草花雞湯,打電話告訴他中午一定要回來吃飯,她好想見他一面。
梁良說,他也很想她,可是,他從基地回到家里,乘飛機最快也要天黑時才能到達,他叫莫小貝自己先吃,不必等他。
莫小貝關了煲湯的火,就出了小區往碼頭的方向走去。她要在梁良回來之前,給他一個驚喜,她要買到他最愛吃的新鮮荔枝和榴蓮。
她希望她買了這兩樣水果回來的時候,是他在等她,而不是她在等他。
莫小貝不喜歡榴蓮的氣味,可是,她很愛梁良,她知道榴蓮是梁良的最愛,她決定不管怎樣艱難都要想辦法把那個麻煩的刺球帶回家。每次看著梁良對那個刺球如癡如醉的樣子,莫小貝覺得自己在梁良心中還真不如一只榴蓮。卻因為自己那么愛他,她也就接受了榴蓮的味道。
梁良在每次吃完榴蓮后,他會把榴蓮的皮切成小塊,燉在雞湯里一起喝了。梁良喜歡榴蓮似乎到了癡迷的地步。他說他迷戀榴蓮感覺就像迷戀莫小貝一樣。
后來,莫小貝不知道自己怎么也會迷戀上了榴蓮。
莫小貝后來在電話里跟梁良說,我明白了,你為什么會喜歡榴蓮,因為榴蓮的味道就是被愛著的味道,那是一種來自熱帶雨林的溫暖與清新。在榴蓮的余味里,有一種情懷,就像剛剛沐浴之后,等待愛人擁抱入懷的感覺,那種氣味充滿了情欲的誘惑與溫馨。
莫小貝說,每次聞到榴蓮的氣味,她就覺得,梁良一直就陪伴在她身邊,就算再寒冷再孤獨的夜,她也會覺得溫暖和甜蜜。
三
莫小貝聽見路上有行人在議論說,阿措耶島上的荔枝已經熟了,能想辦法拿到第一批荔枝,就能夠成為今年水果市場的龍頭老大。
莫小貝本來想直接去鎮南超市等待第一批上市的荔枝,卻身不由己跟隨那群婦人去了碼頭。那些談論荔枝的人是水果市場的一群小商販。從他們的對話里,莫小貝知道他們要把本地市場上的西瓜和榴蓮拉到島上去交換荔枝。
莫小貝居住的地方是一個很少能見到荔枝的城市。她對荔枝的印象最早來自己于唐詩中的妃子笑。
莫小貝本以為梁良晚上要回來吃飯,就特意到早市上給他買一些小商販們還來不及浸泡福爾馬林溶液的荔枝。大家都知道,荔枝是頭天變色,第二天變香。莫小貝是在用心準備一次和梁良的溫馨相聚。她要讓他感受到,多年以來,她對他的愛情一直如當季的荔枝一樣新鮮甜美。
十七歲那年,她愛上了她的物理老師梁良。他是那么俊美而博學多才。十七,十八,十九歲這三年,她天天可以見到梁良來給他們上課。為了實現她的理想,她使出渾身解數來學習理科。之后,她如愿上了大學。學成歸來,他們成了同事。他們的愛情也由地下轉為公開。后來,在梁良的資助下,她考取了環保和工程研究生。幾年過去了,她對他的愛還在與日俱增。她只有不斷的學習才能趕上梁良的腳步。如今,她又一次學成歸來,她離夢想的距離又近了一步。
在給梁良煲湯的時候,莫小貝特別用心。她特意把蟲草花挑撿了幾遍。她生怕有一點點過期變質的花芽留在里面而壞了湯的本質。
走在街上,她突然聽見前面有幾個中老年婦女在談論荔枝的行情,就好奇地跟了過去。
那群中年婦女每個人手里都拉著一部小拖車。那小東西身板雖小,卻能發出極大的噪音。她們不斷地往前走,拖車的隊伍就越來越大,以至于拖車發出的噪音把整條街道的聲音都淹沒了。
她們說,阿措耶島上的荔枝已經成熟,那種荔枝是當年楊貴妃吃了就不能忘記的那一種。
有人就好奇地大聲說笑,真的嗎?賣荔枝幾十年了,還真沒有見過傳說中的妃子笑。
是呀!有人用尖細的聲音附和著說,每次去水果市場批貨都說是妃子笑,其實全是假的,只不過是批發商在打一個招牌而已。
大家就嘰嘰喳喳地笑開了。仿佛這一次,她們確實已經找到了真正的妃子笑。可是,對于這一批期貨,大家都還蒙在鼓里,她們也不知道真正的妃子笑究竟是什么樣子。
四
為了聽清她們談論的話題,莫小貝悄悄混進了拖車隊伍。
當年,唐軍逼迫李隆基賜死楊貴妃在馬嵬坡,李隆基舍不得楊貴妃死,就故意安排了個微胖一點的婢女扮演成貴妃的樣子被賜死了。拖車隊伍中一個聲音尖細的老男人說,當年,李隆基悄悄派人把楊貴妃送到了一個島上,貴妃走時,不忘記帶上自己吃過了就不能忘記的那種荔枝核到島上去。荔枝成熟的時候,李隆基又悄悄劃著小船從水路來到島上看望白發的貴妃,兩人一起賞月品嘗荔枝,忘情于人間仙境。
那個正在滔滔不絕敘述的男人顯得有些振振有詞,仿佛他就是當年的親歷者。
那時,大唐正值盛年。后來,隆基駕崩,貴妃亦死。他接著說,那座島上全部長滿了荔枝,卻再沒有人去發現那座島。再后來,那座島上的荔枝核又被海風吹落飄到了阿措耶島上。多少個朝代更迭,人們再沒有發現那座島。千年以后,一個漁夫遭遇海難,被風吹到了阿措耶島上,發現了當年貴妃吃過的那種荔枝。千年之后的荔枝林也早已子子孫孫繁衍出島上一千年后的果實。據說那種荔枝的果核就像一根針尖那么細。人們都說那些荔枝是無心果,人們的肉眼根本辨識不出荔枝的果核。其實妃子笑還是有心的。那種彌漫著愛情味道的果核,總是讓人想起就針刺一般的疼痛,那是一種想念的痛啊,那是幾千年生生不息的想念的痛。
那個寬背矮胖卻聲音尖細的男人敘述得像是在發表演說一般。他在抒情地敘說著,一副完全沉醉于妃子笑的故事情節而不能自拔。
他振振有詞地說,多少世間事,只為一個情字難了,多少世間事,只因為用了心。人若有心就不怕磨折,人若有情就不怕萬水千山的阻隔。聽到動情處,大家也殷勤地附和著說,是呀,是呀,妃子笑肯定是用心的啦,那么愛她的男人都不用心,誰會用心呢?
莫小貝搞不懂她們說的是果核還是人心。她也跟著隨便附和了幾句。總之,她還是有些感動。她感動于他們述說的這種愛情和思念。至少,她知道梁良和她彼此都是用心的。她首先想到的是針一樣細的果核和針刺一樣疼痛的想念,以及那種被愛情彌漫著的溫潤的果香。
老男人扯著尖細的聲音說,如果不是海難漂到阿措耶島上的那個漁夫告訴大家消息,外面的人又怎么會知道島上真有妃子笑呢?他看了看四周壓低聲音說,其實那座島啊,早就被一片葦草和荷花隱蔽起來了,住在那座島上的人還不知道貨幣買賣,他們只知道物物交換。他們最喜歡島外的人用西瓜和榴蓮去交換他們的荔枝,這一次,大家帶的貨物就是西瓜和榴蓮。
大家說,是啊是啊,這是小道消息啊,其實真正的妃子笑只在阿措耶島上才有,其他在市面上賣的妃子笑全都是假的。
隊伍中,一個戴著頭巾的老婦人接過話說,據說只要吃到楊貴妃以前吃過的那種荔枝,就會長生不老,貌美如花,所以,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弄到那種荔枝。
就是嘛!多好的妃子笑啊。在充滿羨慕的嘈雜聲中,人們的嘴巴咂得嘖嘖直響,大家一窩蜂地附和著說,那么好的東西,我們又怎能放棄呢?其實,人在很多時候,對美好事物的向往,只是流于一種理想的概念而已,他們根本不懂得事物的本身。
莫小貝仔細觀察那個正在說話的婦人的樣子,她體格微胖,背有點拱,說話的聲音低沉而沙啞。她的整個臉部和胸部完全被一塊紫色的頭巾罩住著,只露出稍微圓潤的下巴和一雙美麗的眼睛。她說話時的語氣稍稍有些發嗲的矯情。那婦人的腰間系著一個鼓鼓囊囊的錢包,仿佛她錢包里的錢隨時都會把錢包撐破了跳出來一樣。
莫小貝想,這個老婦人年輕時,一定也是一個和楊貴妃一樣豐腴的女人吧。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行走了一段路,莫小貝發現拖車的隊伍越來越壯大,大得擠滿了整條街道。整條街道上的人向著碼頭的方向移動。快要靠近碼頭的時候,拖車的隊伍又漸漸縮小了。
莫小貝隨著拖車隊伍往碼頭的方向走去。她已經好久沒有走出小城的郊區了,她一越雷池半步,那刺耳的報警聲就會提醒她不再是一個自由的人。她就像一頭禁錮在草場的奶牛,只要走出草場半步,就會被監控報警系統叫回去擠奶。莫小貝覺得自己已經徹底變成了一頭任人操控的奶牛,她已經不再是一個自由的人。
隨著拖車隊伍一直往前,莫小貝的手環始終沒有發出一聲滴滴的報警聲。這讓她的心境異常安靜,她不必每時每刻再為城市四周的監控而小心翼翼。她不必再為她頭頂那張無形的網絡而焦躁不安。她感到從未有過的自在和快樂。她覺得她整個人輕松極了,就像長時間缺氧的人,突然走進森林里大口吸著雨后新鮮的空氣。她只想隨著人群永遠的走下去,她不知道究竟會走到哪里,可她畢竟是在走向一個自由的遠方。她完全忘記了梁良,忘記了即將到來的婚禮,忘記了她所有的功業和理想,她只想永遠那樣遙遙無期地走下去,那種獲得自由的愜意無以倫比。但是,每走出去一段路程,拖車隊伍中就有一個頭戴斗笠的人站出來在路邊清點人數。她分不清那個清點人數的人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只見那人形銷骨立,穿著一身皺巴巴的青衣。每次清點人數,那個戴斗笠的人都是指著那些人一直數到十九,然后就閃進了人群中不見了。
她們的團隊好像一共有十九個人或者更多。這一點莫小貝一直沒有搞懂。
莫小貝很想知道她們所談論的妃子笑究竟是什么樣子。處于一種強大的好奇心驅使,莫小貝還想知道她們究竟要去一個什么地方。和她們在一起,至少,她不必擔心她的手環隨時會發出報警聲。或許,她已經走進了一個監控的盲區。她想一直就這樣走下去。要是還有梁良的陪伴,那將是天下最美好的事情。
為了不暴露她和他們不是一伙的,莫小貝迅速地閃到路邊準備了一身與她們一模一樣的行頭。她把袖套、圍腰和頭帕裝點在身上,扮成和拖車隊伍里的人一個模樣。
大家很快就來到了一條小河邊。這時,河面上飄來了一艘寫著荷花號字樣的小船。那字跡深得古碑精髓,書風直追秦漢。船上鼓著兩頁白帆和插著一排灰白色的小旗子。大家們忙著把拖車里的西瓜和榴蓮搬上小船,就各自坐到夾板上去了。莫小貝也低著頭跟他們一起上了小船。
五
小船是中午時分在島礁靠岸的。
小船沿著河流一直往下。兩岸是一片茂密的蘆葦蕩,四面煙波微茫。小船前進了好長時間,兩岸的蘆葦蕩漸漸消失,身后出現了一片寬闊的海域。小船揚起白礬在海上行駛。天上有烏云翻滾起來,而且烏云翻滾的速度也越來越快,仿佛有什么情況要發生一般。小船繼續在海面上行駛,而且速度越來越快,似乎是在海面上飛了起來。這時的海面上,狂風大作,惡浪滔天。接著,厚厚的烏云間突然撕開了一道口子,光線從裂口里照下來,人們似乎看見遠處的天邊出現了一片碧綠的荔枝林。惡浪突然停止翻滾 ,灰色的海面瞬間變成了暗啞的深藍色。接著整個海面變得深藍到發紫。
此時,整個海島是安靜的。
船上有人低聲說,到了,到了,阿措耶島到了。
大家好像是剛從睡夢里醒來,還沒有弄清楚周圍的環境,就跟著一窩蜂地站起來,睡眼朦朧地整理衣冠。看見明亮的光線從云隙間斜照下來,她們急忙低下頭來,把頭上的帕子壓得低低的,剛好罩住了自己的半張臉。遠處射過來的光線被帕子擋住了,她們又悄悄坐回夾板上繼續她們的美夢。
莫小貝坐在夾板上往遠處望去,前方全是一片水霧籠罩的灰色,視野里零星分布著幾個星星點點的島嶼,如果不是細看,那些島嶼如水鳥的翅膀和灰色的波浪一樣,在視野里忽閃了幾下就消失了。
海面復歸于平靜。小船繼續往前航行。走了大約一個時辰,海面上又漸漸起風了,小船在風浪里搖晃得厲害。大家走出船艙,緊緊抓住從桅桿上懸掛下來的繩子,像一串螞蚱在夾板上隨著小船一起顛簸。
有人開始抱怨說,那片荔枝林不是老早就出現了嗎?怎么還沒有到啊?
有人說,海上的距離目測不太精準,再說海上風浪很大,小船行駛不了,飄蕩半天還在原地打轉。
那就再把船帆撐起來吧!船艙里冒出一個聲音說。人們不知道船帆是什么時候被收起的。
不能撐,現在海上刮亂風,撐起船帆會更加危險。有人在甲板上急促地吼道。
人們又在咕噥著抱怨起來,這樣任其漂浮,不知要飄到什么時候才能到達呀。
有人漫無邊際地說,不就是秋天嗎?秋天到來的時候我們就到了。
大家私下里嘀咕了一陣。小船在風浪中緩緩靠近一座灰色的島嶼,在一大堆礁石旁邊泊了下來。莫小貝看見眼前的那片海面,完全可以用荒無人煙來描述。島嶼周圍除了這一只荷花號的小船來過,看不到有其他的船只出現。
小船剛靠岸,一個頭戴斗笠,身穿灰衣的船工就把錨拋出去,將繩子拴在一塊巨大的礁石上。小船漸漸停止了擺動。大家佝僂著身子陸續從船上走下來,一窩蜂地站在那塊巨大的礁石旁。
狂風卷集著海浪噼噼啪啪向人們臉上身上砸來。大家縮著脖子聚在風中等待一個人的到來。
這時,一個瘦高個子的小伙子出現了。他身穿迷彩服,手里舉著一把小旗子,示意大家向他靠攏。風浪很大,大家聽不清他的聲音,就只顧捂住自己頭上的帕子跟隨著他往前走。
迎著大道一路往前, 路面越來越寬,大道兩旁長著許多高大的楸樹。
島上好像已經是秋天了,地上飄滿了楸樹的落葉。
這時,從礁石頂上走下來一個人,那人穿著一身棕紅色喇嘛服,頭發冗長而微卷。他踏著密密麻麻的落葉向莫小貝走來。莫小貝一眼就看出了他那雙熟悉的眼睛。
梁良,是你嗎?
小貝,是我。
喇嘛服轉身一閃,躲到了楸樹后面。
看樣子,梁良已經在島上好長時間了,他白凈的皮膚被島上的陽光曬得棕紅。他身上挎著一口方形的行李箱,正好與莫小貝的隊伍擦肩而過。莫小貝正要從隊伍中走出來和他相認,他卻急忙躲開了。
他示意莫小貝不要和他說話。
你什么時候到島上來了?莫小貝走過他身邊時,故意稍停下來悄悄問了他一句。
我在島上已經好多年了。我和他們在做一個重要策劃的文案工作,他們要我每天給你打幾次電話,不能讓你產生懷疑,其實,我已經被他們控制了。梁良無奈地說。
梁良正在說著,那個小伙導游就舉著小旗子吼道,掉隊的旅客趕快跟上來,不要走岔了。
莫小貝看見那條主干大道的旁邊有好幾條小路。每一條都是通往不同的方向。
梁良說,你不要出聲,你先和他們到上面去,你去到礁石頂上后,再折回來,從這條小道上往左走,我就在水邊等你。
梁良說完就忙著要走,他說,你快去吧,不能讓他們發現我們在談戀愛,否則,他們會把你推入海里的。
那個小伙導游又舉著小旗子大聲喊道,荷花號上的旅客快點往這邊走,不要走岔了啊。
莫小貝還想問些什么,梁良裝作不認識她的樣子從大道往水邊的方向走了。莫小貝只好追上那群戴著帕子的老嫗隊伍向著礁石的方向走。
六
小船靠港時,船上的人們只能依次排隊擠上小島。小島的四周被一些鐵欄桿圍著,上島的人必須一個個排著隊從欄桿的入口處往上走。在那場隊員中,又有人不時從隊伍中站出來在欄桿旁清點人數。她依然是點著人頭個數一直數到十九,就閃回到隊伍中去了。莫小貝用手里的竹籃遮住臉低頭混在人群中上了島。她奇怪那個人為什么每次總是數到十九就不再往下數了呢,莫小貝悄悄地數了一下他們的隊伍,總人數比十九人還多。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十九,對了,十九號是他們的婚期。
迷彩服的小伙子帶領隊伍上島之后,一群黑衣保安從船上陸續把西瓜和榴蓮搬下來,放在水邊的礁石旁。接著,又來了一群穿著五顏六色的人把西瓜和榴蓮運走了。
來到這條鋪滿落葉的大道上時,莫小貝看到島上到處布滿了大大小小的礁石和自然形成的洞穴。其實,這個島上可能還藏著其他一些神秘的人類,他們好像都披著動物的皮毛,一旦發現有其他人群出現,他們就閃進礁石的洞穴不見了。
莫小貝覺得島上其他人,他們可能也是偷渡過來的。
經過一段平坦的大道之后,島上的路就分成了幾條狹窄的小路。那些小路都是用石板鋪成,石板上已經長滿了青苔。斑斑駁駁的石板路一直拾級而上。在礁石頂端的小路盡頭,出現了一座白色的石頭房子。那個打著黃色旗子的小伙子指著石頭房子向大家介紹說,每一個新來的人都必須到那所白房子里去報到,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經過各種關卡到那座白房子里去,去那里報到之后,大家就可以在島上扎根了。
順著小伙所指的方向,大家很快就見到了那座建在石坎上的白色房子。莫小貝不知道那座白房子里面究竟藏著什么,可是,她感覺到那座白房子對整個島嶼都非常重要。白房子被一道道鐵欄桿反復包圍著。只有通過欄桿的缺口處那道鐵樓梯,才能到達礁石的頂部。
小伙子帶著大家經過那堵高高的石坎,往白色房子的方向走去。經過石坎的時候,有幾個穿著白大褂的人在石坎拐角處支起一張桌子,給每一個經過的人檢查身體。據說,他們是在篩查癌癥信息攜帶者。
白大褂舉著高音喇叭大聲叫道,荷花號客船上的人都集中往這邊過來接受檢查。
隊伍中有人說,我們又沒有病,為什么要給我們檢查身體呢?
白大褂中的一個矮個子說,我們主要是篩查乳腺癌的信息攜帶者,我們是怕島外的人把乳腺癌帶到島上來了,這島上的人是從來不會生病不會老死的,這島上的人都是在忙著搞研究,不能生病,特別是癌癥更不能有,這種病一旦蔓延開來,就會給整個島上帶來滅頂之災。
白大褂們把荷花號上的人全部堵住,要她們自己把衣服脫了配合檢查。
荷花號上多半是上了年紀的老婦,乳腺癌的發病率很高,大家都擔心自己得了乳腺癌,就忙著向白大褂們擠了過去。她們紛紛從自己腰包里掏出錢來,排隊去繳納昂貴的檢查費。大家都生怕出手遲了,就會失去寶貴的生命一樣。莫小貝夾在她們中間,推推搡搡地被擠著往前走。白大褂的隊伍由幾個中青年男子組成,他們給每個接受檢查的人發了一個水晶做的小瓶子說,在體檢的時候,把你們的奶水擠出來放在水晶瓶子里,做成項鏈送給自己最心愛的人,你的愛人就永遠不會離開你了。
老婦人們都忙著擠過去讓白大褂幫她們做檢查。
莫小貝也領到了一個精致的小瓶子,那個小瓶子外面鑲嵌著一顆璀璨的小寶石,她想,如果能擠一滴乳白色的奶水放在里面,那肯定能做成一根很漂亮的項鏈。
莫小貝突然想起,自己還沒有結婚,也沒有生過孩子,怎么會擠得出奶水來呢?
莫小貝看到同行的那些老婦人們,正敞開衣服讓那幾個白大褂在她們的乳房上摸來摸去的擠奶水。
人群中有人舉著小瓶子里的液體說,我擠出來的不是乳白色的奶水,是橘黃色的液體呀。
有人說,別傻了,那是初乳,是最好的奶水,小孩子吃了會增加免疫力的。
那人就沾沾自喜地拿著瓶子從白大褂身邊擠過去化驗去了。
有人又舉著瓶子說,我擠出來的是透明的液體呀,也不是橘黃色的初乳。
有人說,大傻瓜,那不是奶水,那是少女的體液,只有少女的身體才能擠出那種晶瑩剔透的液體來。
有人附和道,當然,只有少女的身體才是純潔無暇的。
咿,那不是乳腺癌的信息吧?少女的乳房是擠不出液體來的。有人煞有介事地插了一句。
七
大家還在擠擠攮攮地往前挪行,很快就輪到白大褂要來幫助莫小貝擠奶水了。只要他們幫莫小貝從乳房里擠出體液來,莫小貝就要繳納一筆昂貴的費用給他們,然后莫小貝才可以順利通過關卡到島上的白房子里去。
莫小貝不愿意任何陌生男人在她的身體上隨便摸來摸去。除了梁良,還沒有任何男人接觸過她的身體。她知道自己的少女之身是擠不出乳白色或者橘黃色的奶水來的。但是,如果不接受白大褂的檢查,她就過不了關口。莫小貝知道自己一旦被他們發現她是混進隊伍的偷渡者,她的后果將無法想象。他們一定會認為她是奸細,他們就會將她推入海里。
這時,莫小貝看見白大褂中為首的那個男人戴了個假發套,他正拿著一個擴音器在高聲宣傳著要給婦女同胞們做檢查。莫小貝看出那人是小鎮上理發店的老板。一個月前,莫小貝還去他的理發店里剪過頭發。那個理發店的老板似乎也同時看出了莫小貝。他害怕莫小貝會揭穿他的秘密,他立即舉起手里的高音喇叭喊道,閃開,閃開,荷花號上的一概不準上這里檢查了。
人群中頓時炸開了鍋。大家嚷嚷著說,為什么不給我們檢查呢?是怕我們不交錢嗎?我們不會賴賬的,我們馬上就把錢交了吧。
大家紛紛從錢包里拿出鈔票舉過頭頂,蜂擁向白大褂擠了過去。
白大褂中那個為首的男子一邊喊話一邊退到了一塊巨大的礁石后面。
這時,白大褂中一個個子矮小的男子走過來指著莫小貝說,快把你的衣服解開,你身上帶有乳腺癌的信息。
莫小貝緊緊捂住胸部說,我沒有!我真的沒有。
小個子男人不依不饒地說,怎么會沒有呢?你剛走過來,我們的儀器就開始報警了,你還想抵賴?
莫小貝說,真的沒有,是我的手環發出的報警聲。
矮個男子根本不聽她的解釋,走過來,一把扯開她的衣服。莫小貝的白襯衣被扯破了,露出了黑色的文胸。
那人接著一把扯掉她的文胸說,你看看,你的乳房都變形了,乳暈旁的皮膚還凸凹不平的,一看就是乳腺癌的跡象,你還說沒有乳腺癌的信息。
莫小貝覺得奇怪,自己光滑圓潤的乳房怎么會突然變得粗糙不平了呢?莫非是文胸勒得太緊的緣故。莫小貝局促地按住自己的乳房輕輕一擠壓,果然擠出了幾滴黑水。莫小貝看著水晶瓶子里的黑水,恐懼極了,她想,難道這就是癌癥的信息嗎?
莫小貝突然想到了梁良。他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見面了。她不知道她為什么在那時突然想到了梁良。莫小貝覺得她怕是要死了。她從沒有見到梁良的時候,她就郁悶得要死了。她想,如果她真的死了,她就再也不能見到梁良了。
莫小貝突然悲傷起來。
莫小貝想起剛才在島上還見到梁良的,他穿著一身棕紅色的喇嘛服,臉上的皮膚被曬得通紅,他好像比現實中的梁良大了幾十歲,而且頭發冗長而微卷,他整個人都變了模樣。只是他那雙含情脈脈的眼睛,讓她不能忘記。他知道那不僅是一雙喇嘛的眼睛,那還是一雙情人的眼睛。莫小貝徹底被那雙眼睛迷住了,所以在陌生的島上,她才敢主動走過去和他相認。
莫小貝想,也許是她認錯人了。是啊,就算他認錯人了,那人已經不是梁良的模樣,可是她覺得他的身上還帶著梁良的信息。他的身上有一種吸引著她想去親近他的力。
自從來到阿措耶島上,島上的天氣幾乎從來沒有晴朗過,天空灰蒙蒙一片混沌,從來沒有白天和黑夜之分。莫小貝的頭腦懵懂而混沌。莫小貝十分擔心自己的健康情況,她害怕自己得了乳腺癌,她很快就會死去。她非常的悲傷,她想不起自己究竟有多長時間沒有見到梁良了。很多事情的堆積,讓她沒有了時間的概念。
那時,她無比的想念梁良,那種想念是隔了幾生幾世的想念。她太想找個身心可以依靠的人。莫小貝是個游走在世間的孤兒,自從見到梁良以后,她覺得梁良就是她全部的依靠。
她后悔自己誤打誤撞闖入了一場小商販的隊伍,她們很可能是一群偷渡者,可是,她后悔已經來不及了,她已經和他們成了一個隊伍。她只能長此以往的堅持下去,只有堅持下去,她才能伺機找到脫身的機會。
莫小貝想起那場人每次數人都是數到十九就不再往下數了,莫小貝注意到他們一場人總共有二十四人,他們為什么數倒十九就不數了呢?莫非這真有什么特殊的意義嗎?莫小貝想起有一次,梁良給她排列過二十四香譜,她突然想到了二十四天尊。
莫小貝喜歡把什么事情都往梁良的身上靠。十七歲的時候,她愛上了老師梁良。十八歲公開戀情。十九歲上大學之后,她和梁良就幾乎不再見面。大學畢業后,他們又短暫的相處了一段時間,那時,梁良就經常被抽到到各種科研課題小組,一去就是半年八月。然后,她又由梁良自費供她讀研。他們又再一次分開了。每個月,梁良都會準時給他寄來足夠的生活費。她與梁良見面的機會幾乎為零,她每天只能聽見梁良在電話里對她問寒問暖。從梁良的聲音里她能感覺到,在世界的另一端有一個人一直在那么愛著她。
遺世獨立。莫小貝突然想到一個詞語。她覺得梁良一定是從上輩子遺留下來與她相見的。
那一伙白大褂還在煞有介事地給大家做檢查。莫小貝猜想,肯定是這伙白大褂在使用什么障眼法,讓大家心甘情愿把自己兜里的錢拿了出來。
莫小貝身上帶的錢不多,她出來買菜的時候,只帶了少量的現金。幸好,她兜里有卡,她卡上的錢是梁良的助手郝金匯寄給她的。
出門前的一天,梁良的助手郝金叫她去了一趟學校。郝金是一個精干的小伙子,他告訴莫小貝說,梁良在去課題組之前,就已經交待他要匯兌一筆錢給莫小貝,說是估計莫小貝畢業的時候,需要一大筆錢。結果錢匯過去,莫小貝為了盡快見到梁良,還沒來得及去取錢,就回到小城里來了。那筆錢又被退回了學校。郝金希望莫小貝過去把那筆錢轉到她的賬上。
那天,郝金在梁良的辦公室接待了她。他用梁良的水杯給她倒了水,那水杯是莫小貝送他的。水杯一共有兩只,一只送給梁良,一只莫小貝自己留下。莫小貝的那只水杯印著一個掉了牙的老頭圖案。梁良的水杯上印著一個掉了牙的老奶圖案。水杯里分別一倒上水,老頭老奶就笑了。
她離開梁良去大學的那天,她把那只水杯遞給梁良。她對他說,此時此刻,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
梁良接過水杯,閉上眼睛輕輕吻了一下說,我知道,杯子就是一輩子的意思,我會一輩子陪你,生生世世陪你。
梁良的辦公室被郝金打理得一塵不染,看樣子,他已經半年八月不在這間辦公室了。
郝金出去了好久都沒有進來,莫小貝就走出辦公室去,她想到熟悉的校園里四處轉轉。
莫小貝走出辦公室,就立即給梁良打了個電話告訴他,說她來到他的辦公室了。
梁良說,我正在開會,稍后再給你電話,就掛了。
莫小貝問,你鼻音怎么那么重?
梁良局促地說,我感冒了。
莫小貝還想再問點什么,就只聽見那邊傳來嘩嘩的水流聲。她想著梁良是在基地開會也就不足為怪了。
莫小貝走出辦公室,發現郝金正從衛生間里出來,她的手上沾滿了水漬。莫小貝和他打了個招呼就告辭了。
郝金說,好的好的。他說話時鼻音是有些重。莫小貝當時也有些納悶,但是走出學校之后,她也就沒再想什么。
一會兒,梁良以一種清朗的聲音回了電話。他說會議剛剛結束,馬上要去基地看一個實驗結果,沒時間再講電話。他叫莫小貝多喝水,注意休息,就掐了電話。
八
莫小貝氣憤地指著為首的那個白大褂說,有種你把你的假發套扯下來!莫小貝穿過喧鬧的人群向白大褂擠了過去。可是,她前面的隊伍已經把路堵得水泄不通。她無法接近為首的那個白大褂。
莫小貝在喧鬧的人群中吼道,你們這伙騙子,有種你們就把頭套扯了,露出你們的真實面目。
她知道,為首的那個白大褂根本不敢暴露他的身份。他看見莫小貝犀利的目光一直在盯著他,他心里也有些發虛。他拿著高音喇叭一邊叫喊一邊往后退,退到人群后的一塊礁石旁就突然不見了。莫小貝懷疑在那塊礁石后面一定還藏著什么機關。她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她必須想辦法盡快離開那里。
莫小貝與白大褂之間的人群聚集得越來越多,人們的情緒越發高漲起來,莫小貝的聲音很快就被喧鬧聲壓住了,她根本控制不了眼前的局面。莫小貝被喧鬧膨脹的人群不斷推著往后擠,她被擠到了一塊巨大的礁石旁。礁石后面出現了一條小路,小路一直通向遠方的水邊。
莫小貝發現這個島嶼其實和另外幾個隱形的島嶼是相連的。莫小貝猜想島嶼下面一定有什么重要的公事機關相連著。她覺得島嶼下面一定藏著什么巨大的秘密。
島礁后面是一條泱泱大河。他記得梁良說過,他就在水邊等她。梁良叫她順著大道左邊的小路下去就能找到他了。
莫小貝看了看礁石的方位,小路剛好向左。莫小貝順著小路一直往左邊走去。從島礁頂上建蓋著白房子的方位來看,莫小貝所在的地方應該是另一個島嶼了。
山頂上石頭房子里傳來一陣叮叮咣咣的打擊樂聲。莫小貝從一條十分隱蔽的小路順著聲音爬到了石頭房子的周圍。石頭房子被一些灌木叢緊緊包圍著。莫小貝扒開灌木來到石頭房子的后窗往里瞟了一眼。她看見一些女人正在石頭房子里換衣服。那一看,她完全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那里面全是一些驚艷的美女和英俊的男子。那些女人有的穿著獸皮,有的穿著麻布,有的系著圍腰,她們一脫去破爛陳舊的衣服就搖身變成了艷光四射的美女。那些女人中,就有當初有與莫小貝一同上島的那幾個老婦。她們取下頭巾圍腰和脫去破舊的衣服,一個個都是豐腴靚麗的女人。她們很快換上五彩斑斕的紗衣就到樓上跳舞去了。莫小貝注意到她們每個人都露出了深深的乳溝。
莫小貝明白了那些白大褂為什么要攔在石崖下檢查她們的乳房。原來她們是從島上散布到市井的宮女和樂師。她們只是暫時離開島嶼,到市井里轉悠一圈,又必須按照指令回到島上來。是的,她們正被一種指令控制著。她們回到島上的時候,得接受白大褂們的嚴格檢查。她看見那個戴斗笠的男人肩上扛著一架古琴。估計他是隊伍里的琴師。莫小貝倒吸了一口涼氣,悄悄退回灌木叢。這個立體的世界斷層把她的腿都嚇軟了。她趕緊從小路一口氣逃到了水邊。
水邊的這個島嶼很安靜,礁石間稀稀朗朗散落著一些樹木。林子里偶爾傳來幾聲輕快的鳥鳴和潺潺的流水聲,這里完全沒有了先前的喧鬧和煩囂,整個島嶼被一種巨大的安靜和美好覆蓋著。莫小貝從小路的石階上往下看,一條浩浩蕩蕩的河流正好把兩堆巨大的島礁隔開了。
莫小貝遠遠的就看見河邊走著一個身著青衣的男子。男子似乎一路迎風在思考著什么。
嗨!你好。莫小貝對著他使勁揮揮手。
是梁良。他抬起頭,正一臉陽光地對著她微笑。
看見梁良笑容滿面地向她走來。莫小貝對這次意外的相逢喜極而泣。
你怎么一個人在河邊啊?
我已經在這里等你好幾年了。梁涼胸有成竹地說,我正在研究這條河,我要把這條河里的水引到對面的島上去,那邊需要很多的淡水。他看上去非常的興奮。
是嗎?這樣到底行不行啊?莫小貝一臉疑惑地問。
行啊!我已經考察好久了,并且花了大量時間寫了一篇關于用蒸餾法調度和置換水質的論文,引起了上面的重視。梁良說,如果用攉水瓢把海水一級一級攉到礁石頂上,讓太陽能蒸餾之后,經過細沙和木炭過濾一遍,再用陶管把山頂的淡水引到對面去,就可以解決那邊淡水稀缺的難題了。梁良指著遠處的河流說,你看這些淡水白白地流淌了多可惜啊。
莫小貝順著梁良所指的方向望去,一片遠山近水朦朧。河水泱泱流淌而去的遠方,被一片濃厚的灰色覆蓋著。她不知道,那河流遠去的遠方究竟是哪里。
梁良說,再過七天,我就要到那邊報到去了,他們讓我去那里當縣令,就是專門負責治水和治理群眾糾紛問題的。
你要去當縣令?莫小貝覺得好生奇怪,縣令這個詞語她只在古裝劇里看過,梁良現在怎么也說縣令這個詞語呢?他還說,他已經在這里等她好多年了。莫非他是生活在古代?要么是她從現代穿越到古代來了。
他們為什么要你去當縣令呢?莫小貝好奇地追問道。
就是那篇論文吧。梁良輕描淡寫地說著,他帶莫小貝來到一座小院里。
這就是我辦公的地方,梁良指著一座青瓦白墻的小院說,我在這里搞研究已經好多年了。
九
院落十分狹小。小院正門對著一間低矮的平房。平房進門左邊的墻壁下,靜立著一張窄小的書桌和一把古舊的椅子。莫小貝走過去,在木椅子上落座下來,那把椅子不大不小,剛好容得下她嬌小的身軀。莫小貝才想起看看梁良的身體,也是那么消瘦而單薄。
莫小貝輕輕撫摸了一下擺在桌子上的黃楊木鎮紙,那木質如嬰兒的皮膚一般光滑細嫩。
梁良從桌子上拿起一疊薄薄的書箋遞給莫小貝說,這就是我寫的關于妃子笑的論文。
莫小貝接過書箋仔細看了起來。她聽見書房右邊小樓上的房間里好像有人在活動。莫小貝還在仔細聽,一個藍色身影從樓梯上走下來就閃出了大門。
梁良說,他是專門負責監護我的看守。
莫小貝一驚,幸好看守沒有發現他們在房間里,不然她肯定會被驅逐出去的。
中年男子并沒有發現梁良帶了莫小貝進來,他像往常一樣走到小院周圍巡邏去了。
小院實在太小,小得容不下一輛木輪車轉身。小院的大門后面種著一棵剛謝了花的荔枝樹。
梁良說,這棵荔枝是我在島上多年的研究成果,今年剛剛開始掛果了。莫小貝瞟了一眼門后面那棵一人來高的荔枝樹,樹上剛結了幾顆青澀的小荔枝。
莫小貝說,那你真要去那邊任職嗎?
是的,我也不想去啊,可是調令已經下來了。梁良從抽屜里拿出一疊材料遞給莫小貝說,你看,這就是調令,還有七天就去報到,后面附著的這個材料是引水上島的論文。
莫小貝接過論文,里面寫著怎樣引水上島,怎樣治理縣內水域的思路和對策。
莫小貝默默地看著眼前的梁良,他那么年輕那么俊美,他清俊中略有幾分道骨仙風的淡然,他的鼻翼和額頭都在閃著智慧的光。她沒有理由阻止他去赴任啊。
莫小貝有些失落。
她說,那個地方有你這樣一個有思想的父母官應該是他們的福氣呵。
聽說那地方黑幫暴政盛行,加上連年鬧水患饑荒,老百姓生活永無寧日,要是我去主政,我一定會努力治理好的。梁良志氣昂揚地說。
莫小貝翻開梁良遞過來的調令和論文,看見調令上清清楚楚寫著的是李良的名字。
莫小貝說,噢,這調令上明明寫的是李良,不是你呀?
是的,就是我啦!
可你是梁良,你不叫李良啊?
梁良說,我去那邊當縣令就叫李良,這是上面規定的,現在是李氏王朝的江山。
那邊是什么地方?
吳縣。
吳縣?那你怎么會叫李良呢?莫小貝急了,可你是梁良啊!
我去當縣令就叫李良啊。梁良蠻有把握地又重復了一遍,我不僅是個縣令,我還是個將軍呢。
莫小貝看著眼前的梁良,他既不是那個穿喇嘛服的長老,也不是搞環保研究的那個梁良。總之,他很年輕,很俊美。
你不是那個卷發穿著喇嘛服的長老嗎?怎么現在又是綰著頭發的樣子?
穿喇嘛服卷發的那個人也是我啊,那是以后的事了,梁良心不在焉地說,過幾天我就要去吳縣當縣令了,我就叫李良。
莫小貝眼前的這個人還很年輕,他意氣風發的臉上洋溢著自信的光芒。他的頭發高高綰在頭頂,身穿一件藍色的粗染裋褐,舉手投足干練利索,談吐間顯得博學多才。
莫小貝覺得很奇怪,眼前的這個梁良并不是她所認識的那個梁良,可是他們之間卻從來沒有陌生感。她又問了一遍,穿喇嘛服的那個人也是你嗎?
是的,那是以后的事了,在那個島上,大家都稱呼我為達摩蘇木長老,梁良輕描淡寫地回答了一句。
梁良一路和她并肩走著,臉上充滿了對未來的向往。他一路滔滔不絕地跟莫小貝說他去到那邊以后,將要怎樣治水怎樣治暴的計劃,全然不顧莫小貝的情緒變化。
莫小貝徹底的懵了,在她的生命里,究竟有多少個梁良呢?他一會兒叫梁良,一會兒叫達摩蘇木長老,一會兒又叫李良。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莫小貝的心里非常混亂和失落。莫小貝搞不明白,眼前的這個李良,他既不是自己的未婚夫梁良,也不是穿喇嘛服的那個長老,可是,在莫小貝的心里,她對他卻是那么熟悉,她覺得他們就是一對相愛了幾個世紀的戀人。
十
眼前的梁良已經徹底忘記了莫小貝的存在。忘記了他曾經答應過,半年后要和莫小貝完婚的事。莫小貝慢慢退到了梁良的后面獨自黯然神傷。
梁良還在繼續滔滔不絕講述著他到那邊要怎樣治水治暴的計劃。莫小貝已經忍受不住了,她輕輕打斷梁良的話說,你可以陪我到路上去走走嗎?
可以啊。梁良一臉輕松地回答,反正,過幾天,我就要到那邊去報到了。如果我的思路能夠實現,可以把淡水引到對面的島上去,那邊就可以種植大量的荔枝了。這是我在島上研制了多年的成果,現在終于成功了,也算是我將來送給你的最好的禮物吧。
莫小貝知道,他說的依然是妃子笑。他認為他付出這些年,所做的努力全是為了她,可她卻一點也快樂不起來。
她知道,梁良就要離開她了。梁良越是努力,離她想要的目標就越來越遠。
這些年,莫小貝不斷地離開梁良去學習,也是為了和他的距離不至于拉得太遠。結果,他們付出的越多,他們彼此間的距離就走得越遠,直到遙遠得他們彼此都不認識了。以至于他們彼此都只活在互相生生不息的想念里。
莫小貝想,梁良已經把要娶她的事情都給忘了。
梁良陪著莫小貝往小路上走去。這時,路邊不斷有許多人經過,大家可能與梁良很熟悉,那些人都向他們投來友好的目光。梁良一路點頭和路人打招呼,一邊在滔滔不絕講述著他的計劃。莫小貝默默地走著,什么也沒有說。她的心事很重。她覺得她在和梁良相處時,她已經沒有了時間和空間的存在。她不知道她究竟在哪兒,她也不知道他會去哪兒。
梁良說,我在島上是專門有人看護的,我走到哪里都被人監視著,這島上的人都知道我在研制一種產品,只是他們不知道,我是專門為你研制的,這樣也好啊,我研制出來了,對大家都有好處。
莫小貝勉強笑了一下,她覺得梁良說他來島上是專門為她在研制一種產品,她根本不快樂。她一點也快樂不起來,是因為她已經好幾年沒有見過梁良了。他們每天只在電話里互道相思之苦,他們每晚睡前道晚安,起床互相問好。可是,她已經記不清楚他的模樣了。她只知道,她很愛梁良,梁良也很愛她。看著身邊的這個年輕人,莫小貝的心里充滿了無限悲傷。他一身粗染藍布短褐,一直是她似曾相識的樣子。梁良還在津津樂道地說著他在島上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將要去那邊的種種理想和抱負。他卻不知道,莫小貝退在他的身后早已淚流滿面。
梁良說,前幾天,我叫人去島外運了一些西瓜和榴蓮過來,我要提取里面的元素制造一種香水。不論男人女人,只要聞到那種香水就會快樂無憂。
莫小貝知道,梁良說的島外運西瓜和榴蓮來的人就是他們那支一起偷渡過來的神秘隊伍。
她知道,他說的那種香水的味道,就是一種熱帶雨林中清新甜美的味道,那是一種被愛著的味道。
多少年以來,莫小貝一直被梁良這樣愛著,她的記憶里永遠彌漫著熱帶雨林里那種清新甜美的味道,而如今,面對眼前的這個俊美少年,那種味道卻離她越來越遠,遠得幾乎只剩下一絲記憶,遠到讓她有種抓不住的感覺。
十一
看到梁良去任縣令的決心已定,莫小貝不好再阻止他。梁良是個有思想的人,她不想耽誤了他去實現他的理想和抱負。莫小貝看看梁良身上的短褐,她在想,如果他去了吳縣,至少他這一身發舊的藍色短褐可以換為華麗的官袍。至少可以這樣。
這樣想的時候,莫小貝的心里就釋然多了,同時她也感到無限的失落。她覺得,眼前的這個人已經不再完全屬于她了,他只是屬于她遙遠的記憶。
梁良陪莫小貝來到水邊,看著泱泱流淌的河水,莫小貝忍不住對著河水淚流滿面。
梁良轉回身來,一臉疑惑地問,小貝,你怎么哭了?是哪里不好嗎?
沒有。我很好。我只想去一個地方。莫小貝強忍著淚水說。
很好啊,你要從哪里去呢?梁良像一只呆雞,一臉茫然地問她。
我想從這里去!莫小貝指著泱泱流淌的河水說。
不行不行,這里沒有橋,從這里下去會淹死的。梁良還是一臉的木訥。
我不從這里去,我能從哪兒去呢?莫小貝淚流滿面地說道。
從那邊,那邊有路啊。木訥的梁良依然不知道莫小貝心里的痛,他指著島嶼的方向認真地說。
莫小貝知道,此一去,她與梁良此生再難相見。
莫小貝揚起頭,讓自己單薄的身體迎風疾行。她知道,梁良在她的身后從此望眼欲穿。
十二
穿過那灣淺淺的海水,莫小貝來到一幢白色房子前,她看見,白房子的四周都有鐵絲網嚴嚴實實地圍著。在白色房子的南邊開了一道低低的大門。大門是那種鐵制的柵欄,一眼就能看見大院里的布局是幾排低矮的平房,平房的門上刷著乳白色的油漆。每一道門的上半部分都是用玻璃做成的,玻璃后面扯著淺黃色的紗布。院子里布滿了高低大小的礁石。莫小貝想,這里肯定是一個重要的基地,一定有人在這里做什么重要的科研項目。
莫小貝對著門往院子里看了一眼,見院子里一個穿白色上衣,頭戴白色帽子的人在巡邏。她對著那個人認真地看了一眼,那個人就向她走過來了。
梁良!莫小貝失聲喊了出來。你怎么會在這里呢?
我在這里值班啊,里面正在審理一件用陽光蒸餾海水與環境保護的案子。梁良說,我知道你會從這里經過,所以我就在這里等你呢。
我們快離開這里吧?你看,這兒四周都沒有公路,我們得盡快找到一個出口才是。
梁良走過來示意莫小貝不要出聲,梁良拉著莫小貝的手偷偷繞到一個正在燒水的鍋爐后面藏了起來。這時,一列火車從鍋爐上方的懸崖上呼嘯而來。莫小貝知道,那懸崖上有一條獨一無二的火車路一直通往山外。
莫小貝躲在鍋爐后面看著火車呼嘯而去,她示意梁良和她一起攀上懸崖逃走。
我們還是等第二列火車到來吧,現在,山上有一群長老正在給山洞里的人做祈福法會,那些人得了失憶癥。梁良小聲說,小貝,你別擔心,等我和他們一起做完法會,我一定會帶你出去的。
她聽見梁良在叫她小貝。她心中有了些許溫暖和感動。
梁良,我們是不是在一座孤島上啊?
不是,梁良悄聲說,我們是在一個天坑里,我們不能迎著來時的河流返回,我們只能從這片懸崖上爬上去坐上火車,我們才能回到原來的地方。
又一列火車疾馳而來,又呼嘯而去。
十三
梁良到山上和長老們一起做法事去了。莫小貝一個人悄悄爬上了懸崖。這時,她的手機突然震動起來,她打開一看,有無數條未接來電和一個郵件。郵件是梁良的助手郝金發過來的:莫小貝,對不起,我是梁老師的助手郝金。聽說你已經失蹤三個月了,公安機關正在四處尋找你的蹤跡。如果你收到信息,請你盡快回話。我不知道你現在是否還活著,可是有一件事,我必須要告訴你。因為,我知道宇宙中的能量是守恒的,有一天你終歸可以接收到我發出的信息。梁老師在你去讀研之后一段時間就失聯了,他是在被抽去基地的途中,飛機與地面失去了聯系。人們都不知道那班飛機去了哪兒。也許,你已經在新聞里看過報道了,只是你不知道你深愛著的梁老師就在那一班飛機上。或許,你已經知道了,只是你一直不敢承認事實吧。
莫小貝,我要告訴你這些,是因為我知道做人的信用也是宇宙間的能量。因為梁老師的最后一個電話是打給我的,他說,他們的飛機可能出了故障,如果他回不來了,叫我每個月就從他的科研獎金中拿出一定資金寄給你。他叫我每天以他的名義給你三次電話。叫早,晚安和中途的問候一個不能少。后來我用聲音模擬程序學著梁老師的聲音每天給你電話。開始的時候,你一直在問我,為什么我的聲音那么清朗那么甜潤,我說是給你電話的時候,心情特別好,聲音自然就甜潤了。你不知道,那是經過程序美化過的聲音。后來你似乎也習慣了那種程序化的聲音。在和你的通話中,我感覺到了你是那么的愛梁老師,你對他的愛是那種超越了生死和順從與充滿敬佩的愛。后來,連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我是我自己還是梁老師的替身。后來,漸漸的我才明白,我已經愛上了你,以梁老師的名義。
直到你和我說到婚禮的時候,我都不敢告訴你真相,我只好說,讓你按照自己的愛好布置我們的婚房,等到我回來的時候就可以完婚了。我知道,這對于一個待字閨中的女孩子來說,是多么殘酷的事。可是,你并沒有怨我。不,確切地說,是你沒有怨恨梁老師。我不敢告訴你呵,因為我不忍心傷害你。我知道你是那么的愛梁老師。從我與你這幾年以來的交流中,我知道如果你知道梁老師已經不在這個世界的時候,你一定會活不下去的。我只想一直在拖,希望梁老師能夠在你們的婚期如時歸來。
直到那天,你說你燉了梁老師愛吃的蟲草花雞湯,叫他中午一定要回來吃飯時,我才覺得,我徹底的懵了,梁老師的角色我再也扮演不下去。你說你還要去買他愛吃的榴蓮和荔枝時,我知道你愛梁老師已經愛到了骨子里。我知道你已經把對他的愛和依戀的能量已經轉換到一種特殊的食物和氣味上去了。我真不敢告訴你真實的情況,我只好說,叫你先吃,不要等我。其實,是我不知道要怎樣來面對你。我想,要么我要等到天黑的時候,我會帶上聲音模擬系統,化裝成梁老師的樣子來見你,可是,我不知道我們后面還會發生什么。我一直懼怕你發現事實的真相后,將是怎樣天崩地裂。可是,那天你掛了電話之后就杳無音訊。這三個月以來,我在到處找你,我利用公安的監控系統知道你去了菜市場。你和一群不認識的人去了河邊,因為他們的拖車噪音太大和他們的穿著一樣,以至于監控系統無法辨識出你來。
郝金說,莫小貝,不僅是梁老師愛著你,我發覺這三年多來,我也深深地愛上了你。我想我是不是承載了梁老師從宇宙傳來的能量?聽不到你聲音的時候,我一刻也活不好。我得告訴你,我是你高中時,隔壁班上的一位小男生,我愛上你已經好多年了,只是你的眼里只有梁老師,而沒有注意到我罷了。
電子郵件的內容還有很多,莫小貝還想繼續往下看,但她的手機一滑掉到懸崖下去了。莫小貝往上看,那懸崖是孤立的,與上面的火車路沒有連在一起,她根本上不去。她迎著來時的懸崖返回了天坑。
十四
冬天,懸崖上飄雪了。梁良在懸崖上鑿坎子。
莫小貝從身后給他端來一杯水,她迎著懸崖峭壁往上攀爬。快要來到梁良身后時,她已經累得臉色蒼白,她的眼前出現了一道道金色的光圈,她看見所有的時間和空間變成一堵無比巨大的巖石橫亙在眼前。她氣息奄奄地扒在巖石上,無法再往前半步,她看見自己瘦小的身軀擠進了一片巨大的巖石斷層。堅硬的巖石向她擠壓過來,她拼命地推開巖石,她看見梁良遠遠地在她前面鑿石坎。
她看著身后的懸崖峭壁說,梁良,懸崖那么陡,我們上不去的。
不怕,我會帶你出去的,梁良擦凈手上的石渣,把她攬在懷里說,我會每天為你鑿一道坎子,我一定要帶你出去。
梁良,我不想出去了,莫小貝靠在梁良的懷里說,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我們可以在天坑里種一棵荔枝樹。
我每天為你鑿開一道坎子,梁良認真地說,不管多少年,我一定會帶你出去的。
不用了,有你,我已經足夠,我不想你再離開我,我要永遠和你在一起。莫小貝一臉幸福地說,我愛你,因為你是我的梁良。
莫小貝笑了。梁良從未看見過莫小貝如此幸福的笑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