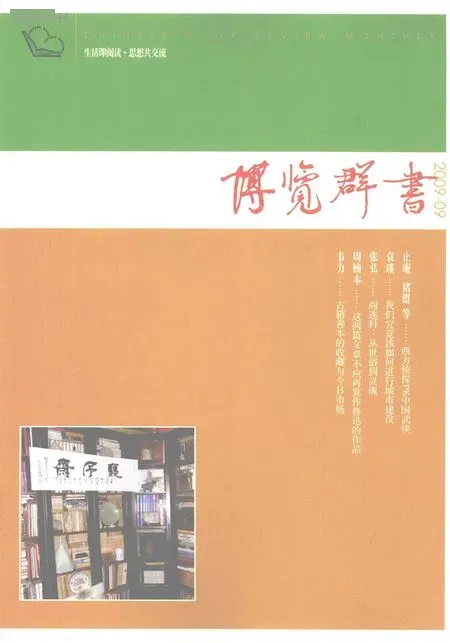六位恩師
談陳守實教授
20世紀50年代初期,復旦大學流傳著復旦教授有“八怪”的說法。十年前,我有一次在上海前復旦大學負責人王零先生家中聊天時,王老還對我說:“你知道嗎?陳守實先生也是八怪之一。”我雖然是1955年才進復旦讀書的,跟陳守實先生當研究生,又是1960年秋,但在入學以后,經過各種渠道,便聽到守實先生的一些怪事。例如:1950年“土改”時,組織老教授參加安徽的“土改”工作隊,陳先生在出發前夕,人已到了上海北火車站,但突然又掉頭返校,表示不去;“思想改造”時,要老教授們人人表態,挖“思想霉素”,陳先生從不發言,黨委的一位負責人,親自找他談話,他竟說:“你就是掏出手槍來對住我,我也不談!”又有一次,他在復旦大禮堂——登輝堂上馬列主義基礎課(陳先生是解放后第一個在復旦大學開馬列主義課程的),講到工人階級在舊社會、新社會的不同政治地位時,曾說:“現在的工人可不同了,阿貓、阿狗也當上人民代表了!”當即有學生遞字條給他,說他污蔑工人階級,是立場問題。陳先生很氣憤,從此拒絕再開這門課。現在看來,在人類社會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行為方式,陳守實先生也不例外。他的行為方式,也許不無可議之處,但要說怪,其實也不怪。透過種種怪事,倒是可以看出陳先生是個不停地閃爍著思想火花的人,具有剛正不阿的品格。就以上述幾件事而難忘風雨故人來論,組織“土改”工作隊,難道有必要非把老教授也趕到鄉下去參加運動不可嗎?這里,我不想全面評價20世紀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同“胡風分子”張中曉所說,為“追求思想的平均分數”,要每個人都表態、作檢查,顯然是不對的。陳守實先生在歷史上一貫進步,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即在《資本論》翻譯者之一郭大力等人的影響下,開始學習《資本論》等馬列著作,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堅定不移。在抗日戰爭中,他不僅自己曾投筆從戎,參加過新四軍;且其愛女陳次青,毅然參加東江游擊縱隊,后犧牲。對于這樣一位不斷追求進步、光明的老教授,不分青紅皂白地要他作思想檢查,他能不拍案而起嗎?至于說“阿貓、阿狗也當上人民代表”,他不過是偶舉一例罷了。對這件區區小事,有人竟給陳先生無限上綱,扣上那么大的政治帽子,難怪他拂袖而去了。
憶周予同先生
周予同(1898—1981)教授是教我們歷史文選、經學史的老師。當年“五四運動”時,他是愛國學生的骨干,參加了火燒趙家樓賣國賊曹汝霖的住宅。他待人寬厚,簡直是位好好先生。
予同先生的隨和,充分顯示在課堂教學中。他幽默風趣,談笑風生。一次,說起他當年拜錢玄同先生為師,真的跪在地上,向錢先生磕了頭。接著說:“現在多好,我教你們,是你們的老師,但都不要你們向我磕頭了!”他本人、我們全班同學,都忍俊不禁地笑起來。他曾幾次在課堂上笑著說:“中華民族的特點是什么?我看是吃飯、養兒子。”大家聞之大笑。周先生說:“我不是隨便說的。中國儒家最講究‘民以食為天‘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兩點對中國歷史影響太大了,確實成了中華民族的特點。”1961年冬,在上海史學會的年會上,予同先生發言時重申他的這一觀點后,還開玩笑說:“所以我勸在座的青年同志,凡是有了朋友還沒有結婚的,趕快結婚。”周先生的這一觀點,“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猛烈批判,被扣上“歪曲歷史”“污蔑中華民族”的大帽子。其實,今天我們冷靜地思考一下周先生的話,就不難發現,他說的絕非戲言。看來,研究中國歷史的人,如果不懂得中國人自古以來最重視“民以食為天”“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精神傳統,是很難透徹理解中國歷史的。
予同先生從不傷害別人。1958年的一天在復旦工會小禮堂批判蔡尚思教授。予同先生迫不得已,只好上臺講幾句,卻一如既往幽默地說:“蔡先生的大著《蔡元培先生學術思想大傳》,第一頁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照片,上面還有蔡元培先生的題字‘尚思吾兄,如何如何,大概蔡先生是要讀者知道,他跟蔡元培先生是本家吧?”引起哄堂大笑。我想,這樣的評判,絕不屬于“革命大批判”,傷害不了蔡先生的一根毫毛的。當時,除了予同先生,誰又能作這樣的發言呢?
憶蔡尚思先生
蔡尚思先生以104歲的高齡辭世,創造了中國歷代史學家的長壽紀錄。我作為這位人瑞的眾多弟子之一,悲哀之余,又深感自豪。
蔡先生所以能享高壽,固然與他長期堅持體育鍛煉、75歲時還在操場跳高、一直洗冷水澡有關。但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他始終童心未泯,個性率真,胸懷坦蕩,遇事每特立獨行,老而彌堅。
我是1955年考入復旦歷史系的。蔡先生是系主任。開見面會時,老師們當然都強調學習歷史的重要性,有幾位至今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譚其驤教授當時顯得很年輕,手里拿著一把很精致的折扇,一邊搖一邊說:“我本來喜歡文學,但最后還是研究歷史,歷史很迷人。”靳文瀚教授說:“我研究過政治學、法學、軍事學——在美國留學時,對各種武器的性能,非常感興趣,但轉來轉去,還是覺得研究歷史好,便研究世界現代史了。”針對有些同學被錄取到歷史系并非第一志愿,因而悶悶不樂,陳仁炳教授說:“舊社會男女結婚,很多并非是雙方自愿的,但進了洞房后,就慢慢兩情相悅了。我相信這部分同學與歷史專業也能建立起感情。”他說得很形象,不少同學都笑了。但是,蔡先生的講話,卻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說:“我出生在農民家庭,小時愚鈍,又不努力,讀小學時所有功課全不及格!我哥哥也一樣,真是難兄難弟啊!”同學們聽了,不禁大笑。蔡先生嗓門洪亮,而且富有表情,我立即感到,這是個與眾不同的老師。他又說:“不過,我后來發憤苦讀,北上京華問學,在南京國學圖書館,每天讀書十七八個小時,除詩集外,該館的經、史、子、集,我全部讀了一遍,抄錄的資料,裝了幾個麻袋,終于成了歷史學家。你們比我聰明,只要認真讀書,將來也一定會有成就!”環顧當代歷史學家,管窺所及,說自己兒時笨、成績差的,除了蔡先生外,只有謝國楨先生了。
事實上,蔡先生有時真像個老頑童。我清楚地記得,他在給我們講授《中國現代思想史》時,認為吳稚暉是個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者。他說:“吳稚暉居然說茅廁里的石頭也是有生命的!唔唔唔,這個吳老狗,這個吳老狗……”一邊說,一邊連連搖頭,滿臉不屑,一只腳還不斷踢著。我們都哈哈大笑。1996年5月18日,我到上海后,即去復旦第一宿舍探望蔡先生。這一年,蔡先生已91歲。他與我聊天時,依然談笑風生,甚至是手舞足蹈。他說20世紀30年代初,他曾去蘇州拜望章太炎,看到老先生為人寫字,潤格甚豐,好大一堆鈔票啊,看得他都傻眼了,邊說邊離開座位,蹲在地上,眼睛斜視,似乎正看著太炎先生數錢,并伸出舌頭。我一邊笑,一邊趕緊把他老人家扶起,他連連說,我不要緊的。我當時就想,中國不可能找出第二個這樣可愛的老學者。在另一次交談時,他說好多年前,他有一只牙壞了,感到其他的牙也不是好東西,要醫生全部拔光。陳圭如教授(胡曲園先生夫人)聞訊,說:“世界上哪有你這樣的拔牙法!”我覺得這很可笑,但他卻表情嚴肅。他批評時下有些人寫文章瞎編亂造,有個記者寫他“畢業于德化中學”,他說:“其實,當時德化只有小學,根本沒有中學,我就是小學生嘛!”這一天,我的日記里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時在1999年9月27日。我拿出一把紙扇,堪稱不同凡響,上面有我認識的文壇、學苑師友親筆簽名。如于光遠、丁聰、方成、王元化、王蒙、馮其庸、喬羽、朱正、李銳、李普、李慎之、杜導正、吳江、何滿子、牧惠、柳萌、張思之、流沙河、賈植芳、梅志、曾彥修、黃宗江等數十人。這年蔡先生已94歲。前一年,因胃癌開刀,不久前又因氣管炎住院,剛回家不久。人比過去消瘦,但思維、精神、嗓門依舊。我請他在扇面上簽名,并開玩笑說:“您老簽了名,這把扇子就是革命文物。”他說“不夠格”。我將扇面攤平,蔡先生放在大腿上,簽上名。他本來手有些抖。簽名時,卻一點未抖,字跡遒勁,宛如刀刻,真奇跡也。我請他寫上94歲。好讓我們也沾點福氣,他提高嗓門說:“我從來是忘我,不記得自己年齡的。”拒絕。endprint
蔡先生是中共黨員,帶頭在復旦工會小禮堂召開全系師生大會,批判自己。二位老師的發言最為特別。陳守實先生說:“你的書與文章,光是罵人,有什么用?你要是想罵我陳守實。我躺在地上讓你隨便罵好了!”此話很尖刻。(據劉伯涵學長生前1980年告訴我,陳守實師是當年陳望道先生主編的雜文、小品雜志《太白》的發起人之一,說話常帶雜文味。20世紀60年代初,有一次市委宣傳部請他做宗教問題的演講,結果聽眾寥寥。他在教研組里說:“下次請我做報告,干脆就到樓梯洞里算了!”)陳先生的發言,使蔡先生很尷尬。周予同先生素來宅心仁厚,他本來不愿批判蔡先生,但系領導要他發言,他只好很幽默地說:“蔡先生的大著《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第一頁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相片,上面還有他的題字‘尚思吾兄如何如何,大概蔡先生是要讀者知道,蔡元培是本家吧?”周先生是笑著說的,分明是開玩笑,會場上也是笑聲一片。但這樣一來,似乎讓人會誤解成蔡先生有攀附之嫌,這同樣使蔡先生尷尬,我記得當時蔡先生臉都紅了。會議結束,蔡先生發言,對陳、周二先生的發言,不但沒有怨言,還感謝幫助,稱這二位都是他的前輩。1992年6月28日、29日,香港《大公報》刊出我回憶陳守實、周予同、王造時三位老師的文章,文中曾述及這次小禮堂的大批判。次年冬,我在團結出版社出版了《阿Q的祖先——老牛堂隨筆》一書,內收此文。1994年初夏,我給蔡先生寄去一本,目的是供老先生消遣。但讓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7月26日,他給我寄來一封信,說了些夸獎的話后,寫道:“關于195頁所述周予同先生說我編的《蔡元培學術思想傳記》要讓讀者知道我與蔡元培是本家一事,我已經記不起來了。幾年前有來訪問的一個日本代表對我說:東京有人傳說您是蔡元培的侄子。還有一個安徽的讀者來信稱我是蔡元培的兒子。我都立即聲明:他只是我的老師而沒有任何關系。他是‘浙江蔡,我是‘福建蔡……我一向反對攀龍附鳳,妄認親戚。假使周先生有此笑話,我一點也不怪他。”“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蔡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胸懷坦蕩。
蔡先生治學,從不迷信權威,從事實出發,不斷挑戰權威。他對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花了很大力氣批判,解放初就出版了《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補編》,還著文批評梁啟超對袁枚的不公,著《王船山思想體系》一書,糾正章太炎、梁啟超、熊十力、錢穆、侯外廬等人對王船山的片面夸大之詞。1963年秋,我在復旦歷史系完成了研究生畢業論文《論l657年后的顧炎武》(正式發表時定名《顧炎武北上抗清說考辨》),通過大量事實考證,推翻了梁啟超、章太炎以及當代某些史家的顧炎武北上抗清說。從系里把論文提綱打印出來,征求各大學歷史系以及學部、歷史所意見,到1964年4月我的論文答辯會上(我的導師是陳守實先生,畢業論文由他指導,當時中國古代史教研組的負責人朱永嘉也參與了指導。),都存在著明顯的分歧。黃云眉先生、吳澤先生、李旭先生等是支持我的觀點的,但也有一些先生持反對意見,李學勤、張豈之二位聯名的意見,對我的論文完全否定。在答辯委員會主席周予同先生主持下,經過答辯、投票,我的畢業論文通過了。但這場爭論引起了蔡先生的注意。他向系里要了一份我的論文打印稿,看后,約我到他家長談。他熱情地鼓勵我說:“你的論文引起爭議,這是好事,就怕文章寫得不痛不癢。我讀完文章了,你敢于糾正前賢及時賢的論點,很有說服力!我支持你,文章由《復旦學報》發表。”我聽了很感動。這時《復旦學報》的主編正是蔡先生。雖然此后不久,“四清”來了,“文革”來了,“左”風猖獗,文章未能在《復旦學報》刊出,直到1979年冬,才在《中國史研究》刊出。但蔡先生當年對我挑戰學界權威的支持、鼓勵,我是一直銘記在心的。
20世紀90年代,國學大師“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我與蔡先生聊起這些人。他正色道:“他們一個也不合格!中國的國學大師只有三個: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一定要說有四個,只能勉強加上胡適。現在陳寅恪被大大圣化,其實他也不是國學大師;雖然懂不少門外語,看了不少外國書,但中國史書、文獻,仍讀得不算很多。他在一篇文章中說:世界文明無出佛教其右者,這是什么話?”他后來不但向記者發表談話,還寫了文章,公開闡明他的這些看法。我舉雙手贊同蔡先生的觀點。時下的國學大師,不過是學界某些老人,甚至是老朽的紙糊高帽,不值幾文錢。
顧炎武有詩謂:“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蔡尚思就是這樣的“蒼龍”“老樹”。他的雨露滋潤著學生、讀者的心田,他的大量學術文章,是開不敗的花朵。
憶王造時先生
20世紀50年代,復旦大學課堂秩序極好,上課前,班長要按花名冊一一點名。但盡管如此,仍有同學悄悄流動到別的年級,甚至別的系去聽課。我就曾經溜到高年級去聽抗日救國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教授的課。他教的是世界近代史。時正夏日,酷熱難當,不少同學神情倦怠,有的竟已打起瞌睡。王造時(1902—1971)先生見狀,立刻說:“諸位,現在我開始講拿破侖與約瑟芬的戀愛故事!”全體同學立刻眼睛一亮,豎起耳朵。王先生非常生動,但很扼要地講完了這段舉世聞名、扣人心弦的故事后,馬上就轉入正題,繼續講課。情緒既然已經被鼓動起來,當然再沒有人打哈欠、睜不開眼皮了。從這種小事可以看出,王先生不愧是位著名政治家,他是深知如何在關鍵時刻,去鼓動人們的情緒的。他曾積極參加“五四運動”,后來留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回國后,他教授政治學,后來投入抗日救亡運動,成了政治活動家。王先生的口才很好,嗓音洪亮。1955年,他在復旦大禮堂做紀念抗日戰爭的報告,說到他曾去鼓動張學良抗日,語重情長地問少帥:“張先生,別說報國了,難道你連令尊大人的仇都不想報了嗎?”少帥默然無語。他的報告,不時激起一陣陣掌聲。
王先生對學生、對年輕人,是很關心愛護的。他的助教結婚時,王先生買了一只大衣柜作賀禮。這在幾十年前,是相當可觀的禮品了。1957年后,他不幸被打入另冊,貶到資料室工作。我當研究生時,隨中國古代史教研組活動,特別是政治學習。王先生也參加這個組學習,這樣接觸就多起來。有時向他請教一些問題,他總是一邊吸著煙斗,一邊耐心解答。“文革”開始不久,王先生即被誣陷,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逮捕,關在提籃橋監獄,后含冤病死獄中。幾年前,我的一位老同學請我去她家吃飯,她的丈夫是“文革”中上海人幾乎家喻戶曉的楊仲池。在1967年夏天的上海柴油機廠事件中,他被“四人幫”逮捕,橫遭迫害,直到“四人幫”粉碎后,才被平反,調來北京工作。與老楊交談才得知,他在提籃橋監獄,竟有幸與王造時先生關在一個房間。雖然王先生已經年邁,并患黃疸病,身上浮腫,仍然偷偷地教老楊英語,傳授給他很多知識。這樣的誨人不倦,真可謂“春蠶到死絲不斷,留贈他人御風寒”。endprint
憶周谷城先生
周谷城先生被稱為周谷老,并非始于他當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之后人們對他的敬稱。早在20世紀50年代,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師生,對時已年過半百的周谷城教授、周予同教授、陳守實教授,便稱之為谷老、予老、守老。這不僅是因為三老年高,更在于他們有很高的學術聲望。因此,無論是當面還是背后,叫周谷城先生為谷老,既是尊稱,也是愛稱。作為他的學生,我當然也不例外,見面寫信都一樣。
1955年,我在復旦歷史系讀一年級時,世界古代史這門課,便是由周谷老講授的。雖說歲月無聲逐逝波,41年過去了,但谷老給我們上第一堂課的情景,至今宛如昨日事,歷歷在目。教室里坐得滿滿的,也有外系學生慕名而來,想一睹谷老風采。他與毛主席的友誼,當時已廣為人知,據說“復旦大學”這四個遒勁瀟灑的字,就是根據毛主席給他寫信的信封上的字制版的。谷老走進教室,我們不禁眼睛一亮:一身筆挺的西裝,領帶生輝,皮鞋锃亮。他微笑著向我們點頭答禮后,彎下身來,側著頭,吹掉講臺上的灰塵,便放下講義,開始講課。他把章節寫在黑板上,然后看著講義, 一句一句地念下去。他的湖南口音很重,有的字,我并未聽懂。
幾堂課聽下來,我們都有些失望: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周谷老,講課竟是這種填鴨式般照本宣科,索然無味。但不久,我又覺得聽谷老的課是太有滋味了。原來,谷老作了一點教學改革:在第二節課快結束時,掏出懷表看一下,留下幾分鐘,給我們介紹國內外史學動態,有時也提到與一些史學家的友誼。有一次說到郭沫若,他豎起大拇指,贊道:“有多方面的學術成就,是個全才,我很佩服。”不過,關于中國的奴隸制,他批評郭老的觀點,認為郭老沒有深入研究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因此對中國奴隸制的解說就不夠妥當,并幽默地說,你們可不要把我的看法告訴郭老,否則郭老會說,周谷城這位老朋友怎么不夠朋友啊?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有時,有同學遞字條給他,請他講講會見毛主席的情景。他雖然不能多說,但也總是介紹一些可以介紹的情況。他的渾厚的聲音,似乎仍在我的耳畔回響:“主席生龍活虎般的姿態,于學無所不窺。”后來他曾笑談毛主席請他在游泳池游泳,他不大會游,只敢待在淺水處,毛主席招呼他往深水區游,他只好說:“主席,您是由深入淺,我是由淺入深。”
說列國內外一些著名史學家,包括系內教授,他都很敬重,從來沒有鄙薄過誰。一次說到周予同先生,他豎起大拇指,笑道:“他是經學史專家,國寶。他要是死了,經學史就沒人懂了!”聯想予同先生去世已十幾年了,經學史雖然還有人懂,但何能望予老項背?甚至“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之輩,竟也侈談經學史,令人嘆息。他也盛贊譚其驤教授是歷史地理學的權威,國寶級專家。譚先生謝世后,他在晚年培養的得意門生葛劍雄教授有一次對我說:“我們在某一點上,可以超過譚先生,但在歷史地理學的總體上,不可能超過他。再產生一個譚先生這樣的專家,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我以為劍雄的話洵為至論,絕非諛師之詞。由此我們也不難看出,谷老四十年前對周予老、譚先生的評價,可謂知人。
谷老很重視師生情誼。即以我而論,不過是復旦歷史系一個普通的畢業生,而且從大學到研究生的八年多時間里,與他并無私下往來。但1978年,我為了工作調動事,去求教對我非常關心的譚其驤先生。譚師考慮再三,說:“谷老的面子最大。最好請他給胡喬木同志寫一封信。”我說,我與谷老并不熟,而且1964年批判他時,我也寫了文章。譚師說,那是市委、黨委布置的,你敢拒絕嗎?谷老才不會計較這種事呢。譚師還特地給谷老寫了一封信,夸獎我一番,請他務必幫忙。
我持此信去泰安路谷老的家登門拜訪,受到他的熱情接待。說起陳守實先生,他嘆息道:“守老很可憐,是被氣死的,沒有‘文化大革命,他不會生食道癌。最后被活活餓死。”對于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就與他結下深誼的、被上海學術界與他共稱“東西周”的周予同先生,他更是不勝唏噓,說:“予老可憐啊!眼睛失明,把他拉到曲阜批斗,嚇壞了。他頭發很長,指甲也很長,原先都不肯剪,怕有人害他,還是我與太太一起去,哄著替他剪了。他一聽到我的聲音,眼淚就掉下來了。”我說起他在報刊上發表的古詩。他笑著說:“那是打油詩。年輕時,我喜歡跳舞,現在老了,跳不動了,就寫詩。工作時要緊張,工作完了要放松。”谷老是多么坦誠。
雖然,谷老認為沒有必要專門給喬木寫信,并說進京開會見到喬木時,一定幫我說話。而事實上,在尹達同志和北京、上海市委的領導劉導生、王一平同志的關心下,不久我就辦好了調進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手續。但是,谷老的談話,仍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谷老進京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后,暫住中組部招待所。我受《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編委會的委托,去請谷老題書名。他滿口答應:“要得,要得。”并深情地說:“吳晗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61年我進京開會,他特地請我吃飯。那個時候困難啊,要不是他請我吃飯,哪里能吃到那樣好的飯菜?”說著,當場就用毛筆寫了書名。后來,我受人之托,幾次寫信給他,為書籍、縣志題簽,他都寫來寄我。值得一提的是,谷老給朋友、學生寫信,從來都是親自動手,而不用秘書代筆,包括賀年卡。他身居高位,平等待人。有一次我代表《中國史研究》寫信向他約稿,他很快回信,寄來文章。他的信,外人看了,不會看出是老師寫給學生的,而會認為是寫給朋友的。為師不以師自居,這并不是每位老師都做得到的,何況是名重當世的谷老。他的信、賀卡,我一直保存著,如今成了珍貴的紀念品了。
1990年深秋,我應邀參加故宮的學術討論會,與谷老不期而遇。他是坐著輪椅來祝賀的。我去向他請安,交談中,他嘆息道:“我現在跟康大姐一樣,腦子還清楚,就是不能走路,沒辦法。”看著他消瘦蒼老的容顏,我不禁黯然神傷。但沒有想到,此次見面,竟成永別。
周谷老是史學家,也是哲學家。得知他逝世的消息,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哲人不再。是的,像一片葉落,像大海退潮,像星辰隱去,像鐘聲漸遠,周谷老走了,走得那樣平靜。他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永遠也不會從這個世界消失。
憶譚其驤先生
亡友馬雍教授生前常跟我聊天。馬兄口才甚佳,嗓音洪亮。有一次我恭維他的口才,他連忙說:“我的口才算什么!我看當今史學家中,沒人能趕上譚其驤(1911—1992)先生。我聽過他的課,也聽過他的學術演講。條理分明,生動活潑。”1955年秋至1964年春,我在復旦大學歷史系攻讀,多次聽過譚先生的講話、報告、歷史地理課。“四人幫”粉碎后,更過往從密,我可以證實馬雍兄盛贊譚先生的口才極佳,絕非虛譽。1958年“大躍進”時,譚先生是歷史系系主任。當時很時髦的一件事是學生給老師、系領導提意見。我所在年級的兩位未免過于天真的學姐,給譚先生提了一條意見:“我們畢業后,有可能去當中學教師。但系里從不開歷史教學法這門課程,將來我們上不了講臺怎么辦?”譚先生當眾答道:“你們放心好了。我雖然沒學過歷史教學法,但教了幾十年書,從來就沒有被學生轟下臺過!”我們聽了都哈哈大笑,包括那兩位學姐。
1959年春,史學界因為郭沫若先生寫了《替曹操翻案》而掀起了討論曹操的高潮。譚先生基本上對郭老的論點持異議,在復旦工會禮堂為全系師生作《論曹操》的學術演講。談到史料上記載曹操先后兩次攻打徐州,殺人太多時,譚先生說:“固然‘多所殘戮‘雞犬亦盡之類的記載是形容詞,難免夸大。就拿‘雞犬亦盡來說,總不會在一場大戰后,打掃戰場時,有人突然驚叫一聲:‘喲,這里還有一只雞呢。”一全場立刻哄堂大笑。譚先生說:“盡管如此,《吳書》《魏志》等史料記載曹操大量殺人還是可信的,郭老予以否定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用亡友謝天佑教授的話說,歷史地理學“是在典籍字縫里做文章的大學問”,頗費考證功夫,相當枯燥。但譚先生講這門課時,從來不帶講稿,至多帶幾張卡片,各種地名的沿革了如指掌,娓娓道來,談笑風生。哪怕是炎夏,學生也沒有一個打瞌睡的。
譚師謝世12年了。望斷南天無覓處……唉!
(作者簡介:王春瑜,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