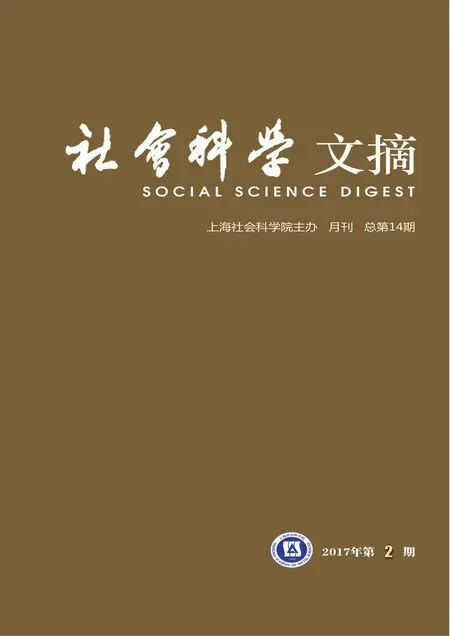論文化詩學與審美詩學的差異與關聯
文/李春青
論文化詩學與審美詩學的差異與關聯
文/李春青
文化詩學與審美詩學這兩個概念的含義可能是非常復雜的,也可以是很簡單的。就其復雜來說,我們專門用兩部書的篇幅來分別探討,也未必能夠盡其義;就其簡單言之,則我們可以說:文化詩學就是以文化為核心或主要研究視角的詩學,審美詩學就是以審美為核心或主要研究視角的詩學。無論哪種詩學,其研究對象都是文學現象,包括作家、文本和作品、讀者、文學團體、流派以及文學思想、理論與批評實踐,等等,否則便不能稱之為詩學。因此這里所謂“核心”,不是指研究對象,而是指研究的視角與目的——文化詩學是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考察文學現象,目的在于揭示文學現象與各種社會文化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審美詩學則是從審美的角度來考察文學現象,目的在于揭示這些文學現象所包含的審美經驗及其呈現方式。正因為如此,這兩種詩學也就必然地有著各自不同的言說方式與話語形態,承擔著各自不同的研究任務,是不可能相互包容或融合的。問題還不止于此,如果從更深層的邏輯來看,則文化詩學與審美詩學實際上是基于不同的社會狀況與文化語境而產生的兩種理論形態,在思想基礎、社會功能以及言說者身份等方面都存在根本性差異,因此試圖把二者“結合”起來無疑是異想天開,而不是實事求是的學術探討。簡言之,如果以審美為核心,那就不可能是文化詩學;如果以文化為核心,也就不可能是審美詩學。
鑒于學界不少人對這個問題并沒有清醒的認識,誤以為把不同種類的好東西湊在一起就會成為更好的東西,故而我們有必要對這兩種詩學理論的差異與聯系展開討論。在下面的闡述中,我們也將對這兩種詩學在中西方各自不同的形成原因與演變軌跡予以梳理。
從哲學美學到審美詩學
審美詩學的產生是以“美學”和“文學”這兩個概念獲得現代意義為標志的。德國哲學家鮑姆加登第一次命名了這個學科,使美學成為一門與邏輯學、倫理學相并立的哲學分支。美學成為一個學科或一門學問的意義在于:它使人的感性,主要是感情與感覺,作為把握美的東西的能力而受到空前關注,這是自笛卡爾以來的整個西方認識論哲學中未曾有過的。在鮑姆加登的基礎上,康德在理論上使美感或審美能力(判斷力)獲得普遍性并且成為一個與快感、道德感以及知性都清晰區別開來的概念,更進而揭示了其獨特性及其在人的精神結構中的位置。作為康德美學的繼承者,謝林美學在人類審美經驗上寄托了把握或顯現作為世界本體和根本動力的“絕對同一”這一神秘存在的重大企望,席勒則第一次賦予了審美以彌合人性分裂、進而改造社會的偉大價值。于是,一個令人心馳神往的審美烏托邦被建立起來了。至于歌德、施萊格爾和諾瓦利斯等人,則是通過創作充滿激情的戲劇、詩歌、小說和散文作品而對美學這個學科的獨立性作出貢獻的。鮑姆加登、康德和席勒等人建立起來的這門新學問是他們各自哲學體系的一部分,因此可稱之為哲學美學。它致力于探討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問題,試圖從根本上揭示人的審美經驗的一切奧秘。在這種哲學美學之后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審美詩學”——我們用這個概念來概括那些基于康德等人的哲學美學原理而進行的關于文學藝術的理論言說——諸如費歇爾父子和里普斯的移情論、谷魯斯的內模仿說、布洛的距離說以及現象學美學、表現主義美學直至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和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等文學批評理論,可以說都是對康德所代表的哲學美學的繼承與發展。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努力,一代一代的精英知識分子們終于把美學和與之緊密相關的審美詩學打造成一個純美的精神世界、一座象牙之塔。在這里一切都那么美好,那么絕假純真,審美于是成為人類的精神家園和自由的象征,成了現實世界的無邊苦海里的諾亞方舟和這個異化的世界里人性的最后避難所。然而到了20世紀后半期,隨著后現代主義的興起,隨著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人們開始以懷疑的目光審視這個美的世界。那些敏銳的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從不同角度對這個世界進行了顛覆性闡釋。
審美詩學與審美現代性
從馬克思到哈貝馬斯,再到齊格蒙特·鮑曼和吉登斯,100多年來,許多社會學家與文化理論家都指出過這樣一種現象:與資產階級的產生和壯大相伴隨的現代性可以分為兩大層次,一是表現在經濟、政治生活中的“務實的”或者“功利的”的現代性,一是表現在思想文化領域的“超越的”或者“精神的”現代性。在這兩種現代性之間是存在著矛盾的。第一個層面的現代性,本質上是借助于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工具理性”而使經濟生產和社會管理達到效率的最大化,這表現為一個“合理化”或者“理性化”的過程。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現代性理論依賴‘理性化’這一基本概念來解釋現代社會的獨特性質。理性化指的是作為一種文化模式的技術理性的普遍化,具體說,是把計算和控制引入到一個社會的過程,并使這個社會相應地增加效率。”正是這個層面的現代性導致了早期資本主義社會種種矛盾的激化,也使得文化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的產生成為必要。第二個層面的現代性,原本主要是為著在思想觀念層面的“祛魅”,即清除專制主義、蒙昧主義的思想傳統而產生的,故而被稱為“啟蒙現代性”。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隨著中世紀的夢魘漸漸被人們忘卻,這種啟蒙現代性的主要任務就轉變為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進行批判與反思了。如果說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可以算是代表了啟蒙現代性原初功能的完成,那么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說是啟蒙現代性后一種功能的典型體現者。應該說,批判和規范其賴以產生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方面面,恰恰就是文化現代性或啟蒙現代性的主要任務。
至于審美現代性則承擔著更為艱巨的歷史任務。一方面,作為整個文化現代性的一部分,審美現代性需要對封建主義價值觀進行否定與清算,這充分體現在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直至批判現實主義的歐洲文學藝術之中;另一方面,審美現代性還作為對“啟蒙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而存在。這主要體現在康德以來的美學理論以及現代主義或“先鋒派”的文學藝術之中。這就意味著,審美現代性肩負著雙重超越的任務:既要超越封建等級觀念與神學蒙昧主義的舊框框,又要超越工具理性、科層制度帶來的新限制。如果說康德美學旨在彌補以理性為核心的啟蒙現代性的不足,席勒美學的主旨在于調和感性與理性之間的緊張關系,他們還都沒有借助審美現代性來質疑和否定啟蒙現代性的意圖;那么到了費爾巴哈、叔本華、尼采乃至海德格爾和法蘭克福學派那里,那面從笛卡爾到斯賓若莎、萊布尼茨、黑格爾都一直高擎著的理性主義大旗就成了反思與批判的對象。
文化詩學與后現代性
正如“審美詩學”是現代性在文藝研究領域的話語表征一樣,文化詩學也是后現代性在這個領域中的現身。又正如“審美詩學”不是某種具體批評理論的專指,而是包含著所有以“審美”或“文本”“修辭”本身為中心的批評理論與方法一樣;我們這里說的“文化詩學”也是廣義的,不是特指一種理論或方法,而是指一種研究路向。它包含著但不限于格林布拉特和海登·懷特所代表的“新歷史主義”,而是可以涵蓋所有基于對審美詩學的批判性反思而從外部,即社會文化、歷史狀況角度,審視文學藝術與審美現象的研究路向。說文化詩學與后現代性具有內在關聯性,正是因為它是作為對審美詩學的反思而出現的,因此它是整個現代性反思思潮的組成部分,當然也就是屬于后現代性范疇的話語形態。各種各樣的文化理論,當它們面對文學發言時,它們是文化詩學;詹姆遜與伊格爾頓的意識形態的或政治批評,當然還有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也都是作為一種研究路向的文化詩學的代表性理論與方法。
文化詩學與審美詩學的根本性差異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看出:
首先,審美詩學追問“是什么”“怎么樣”,而文化詩學追問“為什么”。文化詩學不滿足于審美詩學把視野封閉在文本內部的做法,而是要通過文學文本介入到對社會歷史、社會文化的闡釋之中,所以文化詩學也可以稱之為“文學文化學”。
其次,審美詩學旨在發現或建構意義,文化詩學旨在揭示對象背后所隱含的復雜關聯。正如文化現代性的主導傾向是建立種種“宏大敘事”或云“元理論”一樣,審美詩學也旨在建構一個個“審美烏托邦”。審美詩學常常把文學藝術或審美與“自由”“人的解放”“人類精神家園”“人的自我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超越”“詩意的棲居”等現代性的元理論范疇相聯系,賦予其一種偉大的意義與價值。文化詩學則不參與對這些元理論范疇的尋覓與建構,而是把它們當作可以追問、反思和質疑問題來看待。
再次,審美詩學是“照著說”,文化詩學是“接著說”。審美詩學是關于文學藝術作品所表現的東西及其表現方式的鑒賞判斷,文化詩學則是關于文學藝術作品所表現出的東西及其表現方式的反思性批判。
在文化詩學與審美詩學之間
如果說審美詩學是把文學觀念、文本形式和審美趣味作為“所指”來加以把握,那么文化詩學就是把它們當作“能指”來展開分析。審美詩學所止步之處,恰恰是文化詩學開始之處。這就意味著,對于審美詩學,文化詩學可以采取反思、顛覆與吸收、借用兩種看上去迥然不同的策略。
就反思與顛覆的一面來說,自康德、席勒以降,審美詩學建構起來的種種神話需要文化詩學重新檢視。在文化詩學的視域中,那種超越歷史和語境的、純而又純的審美是從來不曾存在過的。
就吸收和借用的一面來說,則可以說,來自審美詩學的文本分析方法為文化詩學提供了寶貴的資源。例如結構主義方法就是文化詩學比較容易借用的一種文本分析方法。我們知道,結構主義并不關心一個文本傳達了怎樣的意義,而是關心它是用怎樣的方式、依照怎樣的規則來傳達意義的。而且結構主義所關心的還不僅僅是個別的文本特性,而是試圖揭示某類文本所共有的傳達意義的方式與規則。普洛普的“敘事功能”、托多羅夫的“敘事句法”、熱奈特的“元語言”以及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都是關于這種方式與規則的概括。文化詩學完全可以通過對文本構成的結構主義分析為進一步的歷史化、語境化研究提供便利。換言之,借助于審美詩學文本分析的方法與技巧,文化詩學可以采取一種“循環閱讀”的批評方法:首先分析文本結構等形式特征,概括出某些具有標志性的文本因素,然后將這些文本因素置于復雜的社會文化網絡之中,考察其生成的原因、過程以及其所表征的文化意蘊或意識形態性,而后回到文本世界,對其具有文化符號意義的諸文本因素及其相互關系進行定位與命名,并進而揭示整個文本的文化的或者政治的意義。
中國語境中的審美詩學與文化詩學問題
在中國,作為現代學術的審美詩學出現于清末民初,是中國文化現代性的主要標志。因此,相對于延續了上千年的“文以載道”傳統,審美詩學是具有某種啟蒙意義與批判精神的,無論是王國維對德國古典美學的借鑒,還是劉師培的中國式的“純文學”主張,莫不如此。稍后,諸如周作人的“為藝術而藝術”說、宗白華的“藝術意境”說、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歌批評、以朱光潛和李健吾為代表的“京派批評”,等等,都是中國語境中的審美詩學,屬于審美現代性范疇。20世紀80年代初期,“審美”成為一代長期飽受思想禁錮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烏托邦。讓文學回歸自身,不再充當政治的或階級斗爭的工具成為此時“審美詩學”的基本訴求。從今日文化詩學反思的立場上來看,80年代初的審美詩學正體現著知識分子尋求獨立性、主體性的強烈愿望,其表面上追求純而又純的審美,是對康德美學的繼承,但在骨子里卻充滿了政治性,表征著一代知識分子對話語權的爭取與捍衛。此期的審美詩學代表了當時的時代精神,具有強烈的革命和激進色彩。
中國的文化詩學作為一種研究路徑,可以說正是產生于對80年代建立起來的審美詩學的不滿,這一點與西方文化詩學的產生原因相近。在“方法熱”“主體性”“向內轉”“文藝心理學”這些80年代審美詩學關鍵詞相繼喧囂一時之后,文化熱、尋根熱出現了。產生于80年代后期的文化熱或文化轉向乃是中國當下文化詩學產生的現實基礎。海外新儒學的大量引進與現代以來學術史的重新發掘以及相伴隨的對古代經典的重視成為這一“文化熱”的主要表現。90年代以后,后現代主義在中國學界開始形成普遍的實質性影響,中國的文化詩學從中汲取了反思、質疑與批判的精神,并且把這種精神與“文化熱”中形成的文化整體性關聯的視野相結合,于是就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詩學研究路徑。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所固有的文史哲不分的存在樣態為中國文化詩學提供了施展的空間,因此中國文化詩學研究的主要成果是表現在對中國古代文學思想、文論觀念的研究之中。
我們的審美詩學和文化詩學與西方學界相比呈現出一種錯位:80年代的中國學界是審美詩學的天下,甚至當人們提到“美學”“審美”“文學”這類詞語時都帶有某種神圣感。而在這一時期的西方,以“新批評”和結構主義為代表的審美詩學早已式微,各種文化理論對審美詩學的“解構”已大體完成。而90年代中期以來,正當我們援引各種各樣的文化理論來建構中國式的文化詩學的時候,在西方卻已經開始了“理論之后”與“美學回歸”的討論。對于這種“錯位”現象不能僅僅從學術影響的“時間差”角度的來解釋。后現代主義學說在80年代中期已經為國內學界所熟知,但在當時卻沒有形成普遍性影響,這主要并非譯介與傳播的問題,根本上乃是社會現實的需要使然。
總之,在經歷了20多年的發展演變之后,在汲取了后現代主義的反思與批判精神的基礎上,今日中國的文化詩學正在成為一種更為有效的文學闡釋路徑。這種闡釋路徑以窮盡性地占有第一手研究資料為基礎,以反思、質疑和重新檢視一切舊有成說為手段,以梳理并呈現研究對象生成過程的復雜關聯及其所表征的文化意蘊為目的。中國的文化詩學既不刻意追求邊緣性的、非主流的、零零碎碎的材料,也不刻意回避對主體——無論是個體主體還是集體主體——的研究,更不刻意凸顯“斷裂”與“片段”,甚至不諱言“本質”與“規律”這些為后現代主義所忌諱的概念。它不預設立場與原則,不標榜解構與建構,而是在學術史的流變中提出問題,根據所能掌握的材料與重建起來的文化語境,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使人們對所闡釋的對象產生新的理解,獲得新的意義。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摘自《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