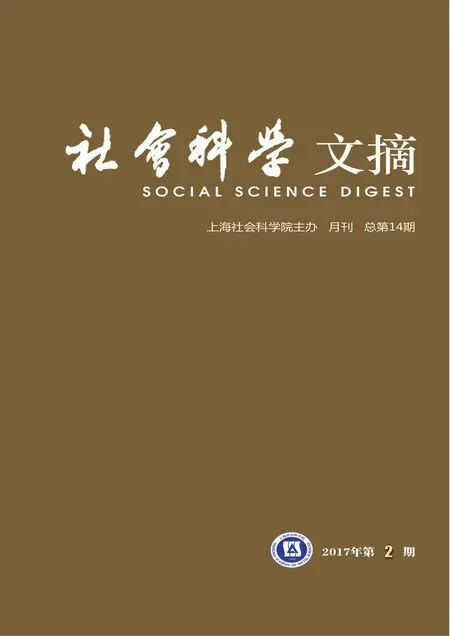西南聯大與抗戰時期學術發展
文/楊紹軍
西南聯大與抗戰時期學術發展
文/楊紹軍
抗戰時期是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重要時刻。國民政府為保存文化教育免遭毀滅,決定組建長沙臨時大學,但隨著南京、上海相繼淪陷,武漢告急,長沙臨大再次西遷,到達昆明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西南聯大)。在日寇入侵、風雨如晦的環境中,西南聯大學人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堅持剛毅堅卓的校訓,為國家和民族培養造就一大批人才。他們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出于對國家和民族的使命感,沉潛于學術研究或理論創造,以不朽的精神和辛勤的勞作產生一大批卓有成效、極具深遠意義的理論著述,有力地推動和影響戰時中國學術乃至20世紀中國學術的發展。
西南聯大學術成就及其貢獻
(一)西南聯大學術發展譜系和建樹
抗戰爆發,促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眾多學者匯聚昆明。他們不僅使西南聯大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的重要基地,而且形成特定的學術共同體。盡管這個共同體的教育背景、研究領域、學術方法等不盡相同,但作為共同體,他們在昆明建構新的公共空間和關系網絡,堅持學術文化創造,使昆明成為戰時中國學術界、思想界和教育界最為活躍的學術文化中心。
抗戰使眾多學者顛沛流離,對他們的學術創造影響深重,但中國現代學術研究卻在物質條件極為惡劣的西南聯大獲得空前的發展,創造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奇跡。我以為最重要的是,他們立足于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自覺承擔學術創造和文化傳承的使命,用他們思想和智慧的結晶譜寫濃墨重彩的華章,奠定他們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一,西南聯大學者先后建構自己的學術思想體系,推動中國現代學術極大發展。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哲學得到迅速發展并逐漸形成建構哲學體系的新高潮。馮友蘭被公認為現代中國的哲學大師,應歸功于他的“貞元六書”和獨具匠心的新理學體系。新理學體系的核心就是“兩個世界”(真際世界和實際世界)和“四個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他的“貞元六書”構成完整的新理學哲學體系,它從本體論到方法論,從東方傳統哲學到西方現代哲學,構筑起融匯中西、貫通古今的宏大思想體系。
同樣,作為現代中國分析哲學最為杰出的學者,金岳霖1940年出版《論道》。《論道》作為他的哲學體系的本體論,精心構造了一個先驗的邏輯世界,即用能與式、共相與殊相、理與勢等范疇,用邏輯方法演繹出一個“道”的本體世界。如果說《論道》是從本體論角度解決歸納問題的話,那么《知識論》則是從認識論入手,正面解答歸納問題的著作。在《知識論》中,他立足于經驗論的立場,堅持知識來源于感覺經驗,同時又看到感性認識的不足,承認抽象的理性在認識獲得過程中的作用,明顯地認識到經驗與理性的并重。他把西方哲學的根本精神和中國哲學的傳統相結合,用嚴密的邏輯分析和邏輯論證方法闡述對本體論和認識論的深邃思考,創造性地建構起一個體大精深、具有民族特色的哲學新體系——新道論思想體系。正是他們的共同努力,才使得中國哲學在抗戰時期得到較快發展,呈現“現代新儒學的興起與中國哲學新體系的構建”的嶄新面貌,為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奠定基礎。
第二,西南聯大學者相繼完成自己的代表性論著,奠定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史學素有鑒往知來的傳統,司馬遷的“述往事,思來者”,司馬光的“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無不體現傳統史家以史為鑒的旨趣。1939年6月,錢穆的《國史大綱》成書,次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隨被國民政府教育部指定為全國大學通史用書,成為風行全國、名動一時的名著。該著最鮮明之處在于首次將文化、民族與歷史綜合起來進行討論。他認為中國歷史的真相就是中國文化精神的演進,中國的文化主要表現在中國以往的全部歷史中,也就是說,民族的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文化的復興,而復興文化應該認識歷史。作為抗戰時期發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國史著作,《國史大綱》對20世紀中國史學界產生重要影響。
第三,西南聯大學者不斷開辟新的研究領域,作出創造性的卓越貢獻。他們根據戰時需要和地處邊陲的實際,走出書齋,走進田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以“匹夫有責”的救亡精神和卓越的行動,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建立,就是他們為促進中國邊疆民族地區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1942年6月,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聘請陶云逵主持研究室。根據計劃,陶云逵帶領邢公畹、高華年、黎國彬、賴才澄等赴紅河流域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調查,他們克服種種困難,寫出有價值的研究報告。可以說,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集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地理學和宗教學等多學科優勢,對西南少數民族的居住環境、社會歷史等進行大規模、長時間的調查,具有開路先鋒的重要意義。
羅常培到西南聯大任教,給他提供了從漢語方言研究轉向非漢族語言研究的重要契機。他將語言學與人類學研究結合,開辟語言人類學研究。他在云南的非漢族語言研究,一方面從人類學的理論出發,研究非漢族語言問題;另一方面由實地調查材料入手,探究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因此,以羅常培為代表的語言學家在云南開展的語言調查和民族文化研究,不僅豐富了語言學界得不到第一手資料而顯得較為單薄的少數民族語言研究,而且筑就中國語言學和相關學科新的路徑,取得突出的成就。
第四,西南聯大學者通過研究和教學的帶動,培養和造就了大批的杰出人才。在戰爭年代,西南聯大不僅是中國現代學術研究重鎮,而且是戰時和戰后中國學術發展搖籃。王浩在西南聯大畢業后到清華文科研究所攻讀哲學,1945年到哈佛大學留學。他對哥德爾思想的研究,屬世界性權威,著有3本與哥德爾有關的書(《從數學到哲學》《哥德爾》《邏輯之旅:從哥德爾到哲學》)。正是在昆明,他跟隨金岳霖學習數理邏輯,進而接觸到王憲鈞的符號邏輯,與哥德爾在課堂邂逅,最終走向國際學術舞臺的中心。
作為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恢復招收的首屆研究生,閻文儒師從向達學習西域史。1944年,由北大、中央博物院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由向達任組長,閻文儒隨導師前往。他隨向達進行考古發掘、石窟調查、藝術史分析,結合考古、歷史、藝術、文獻等多學科進行綜合研究,為他以后從事隋唐考古和石窟寺藝術研究打下基礎。其后,閻文儒出版《中國石窟藝術總論》《麥積山石窟》《龍門石窟研究》《中國考古學史》等多部著作,成為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石窟寺藝術研究的開拓者之一。
(二)西南聯大與抗戰時期學術發展之關系
西南聯大作為戰時匯聚眾多優秀人才的高等學府,是特殊時期出現的學術共同體,眾多學者懷著抗戰建國的堅定信念,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在中國現代學術領域做出杰出貢獻。因此,西南聯大學者的學術研究不僅是戰時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組成,而且由于特殊的戰時背景,使得他們的研究凸顯強烈的拯危救亡意識,激發起他們空前的愛國熱情。
抗戰時期,中國學術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強烈刺激下產生振興學術文化的強烈愿望,反而成為現代學術發展的收獲時節。在哲學領域,各種主要的中國現代哲學體系在抗戰時期逐漸成熟定型,產生廣泛影響,如馮友蘭的新理學體系、賀麟的新心學體系、金岳霖的新道論體系、熊十力的新唯識論體系,等等。在歷史學領域,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雷海宗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張蔭麟的《中國史綱》(第一冊),傅斯年的《東北史綱》第一卷、《中國民族革命史稿》,等等。在政治學領域,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陳之邁的《中國政府》,浦薛鳳的《現代西洋政治思潮》,等等。這些都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具有經典意義的論著,均完成于抗戰時期,經歷戰爭期間血與火的考驗,體現出戰時中國學術的巨大收獲。不難發現,昆明作為與重慶齊名的戰時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基地,西南聯大學者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留下許多傳世之作或開山之作,成為中國現代思想文化領域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
西南聯大學術繁榮之機理再認識
在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與傳承最為艱難的歷程中,西南聯大學者精誠合作,共濟時艱,結茅立舍,弦歌不綴,在若干研究領域取得突破,實現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就其動因來說,主要有:一是相對外在的動力,即抗戰時期知識分子承擔民族文化復興的使命意識;二是學術自身的演進與創新的結果。西南聯大學者在相對外在動力的推動下,主要依靠自身學術的演進和創新實現戰時中國學術的繁榮發展。
(一)中華學術傳承途徑之創新
中國現代學術的轉型,是在傳統學術在西方思潮的沖擊下因應時變的結果。晚清以降,作為傳統學術研究的重要方法,歷經兩千多年的考據之學飽受質疑,嚴復斥之為“錮禁智慧”“蠹壞心術”。其后,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將西方現代治學方法與傳統考據手段結合,為現代學術發展樹立新范式。胡適、陳寅恪、顧頡剛、傅斯年等,都對治學方法作過努力,倡導建立學術社會,構建學術共同體。抗戰時期,密切關注民族興衰,懷著家國情懷的知識分子,在中西文化交匯中,對中國學術傳承進行創造性的探索,西南聯大學者就是這種具體實踐的代表性人物。
湯用彤“幼承庭訓”,系統接受傳統文化教育,1917年赴美留學,接受白壁德(Irving Babbitt)“同情加選擇”的人文主義思想,逐步確立其文化轉化觀念和止血方法,用以“昌明國故,融化新知”。具體而言,就是他的研究深受人文主義思潮影響,采用傳統的考據和系統比較方法,深刻闡明傳統文化實現現代轉化的過程。綜觀他在昆明寫作的《魏晉玄學論稿》,其中既有翔實的考證、細致的比較,也蘊含“同情加選擇”的了解,更有對西方哲學方法、范疇的嫻熟運用。《魏晉玄學論稿》作為抗戰時期的創新之作,他將傳統考據之學與西方哲學范式結合,對中國傳統學術傳承方法進行適應性的創新,自然能體現出重要的價值。
(二)中西文化融通綜合之集成
自19世紀晚期中西文化發生碰撞以來,中國文化建設就無可避免地擔負起雙重歷史使命:一方面梳理和探究西方文化的根源與發展脈絡,用以理解并提升自身要義的借鏡;一方面整理和傳承中國文化傳統,用以實現并弘揚傳統學術價值。因此,中西文化的融通綜合乃是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的必由之路,西南聯大學者在研究中都有中西融通的思想和卓識。
1940年代,賀麟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成為中國現代新儒家的重鎮。他的《近代唯心論簡釋》將西方的新黑格爾主義和中國傳統的陸王心學融合起來,構建起一套涵蓋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新心學思想體系。在本體論上,他把新黑格爾主義的自我意識論和陸王心學的“吾心即理”觀念融合,提出知行合一、知體行用、知主行從、知難行易的知行論——“自然的知行合一論”,對直覺的思想方法進行研究。1942年6月,《近代唯心論簡釋》在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中央大學徐梵澄對他吸取、改造、融貫、發揮中西哲學的結晶和呈現出的個性追求與時代精神,對他開創中國哲學新格局的嘗試給予較高評價。
(三)理論創造與田野實證之聚合
1920年代以后,大批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陸續回國,他們受聘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積極從事教學和研究,為中國學術事業的發展和文化傳承作出努力。在此過程中,他們將在海外系統學習的社會科學理論傳入中國,與中國的現實社會相結合,在自己進行田野調查的同時,積極指導學生從事實踐,實現理論創造與田野實證的聚合,在不同研究領域結出一大批嚴謹務實的碩果。
1939年8月,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在昆明成立,該所設立的目的是為國民政府戰時及戰后制定“適合國情,通盤周密的統治計劃與整個國策”提供社會情狀、理論依據和技術經驗,為政府實行“全國總動員”和制定“建國的具體辦法”服務。1941年2月,所長陳達提出以云貴川三省作為全國人口普查實驗區的議案,得到國民政府批準。他對昆明市、昆明縣、晉寧縣等地進行調查,稱為“云南環湖戶籍示范區普查”。通過對滇池地區的人口普查,同時結合中國近百年人口發展規律的研究,他寫出中國實驗人口學的第一本專著——《現代中國人口》。該書于1946年在《美國社會學雜志》以當期全部篇幅發表,這在該刊歷史上是首次。陳達等學者經過實地調查得來的研究成果,促進戰時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創新,造就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研究的戰時高峰。
西南聯大與抗戰時期學術發展之啟示
西南聯大學者在嚴酷的戰爭期間,懷報學術報國的情懷,對民族文化復興和抗戰學術發展做出不朽的貢獻。在西南聯大的8年間,他們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理論著述,都產出一大批代表20世紀最高水準的論著,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給當代中國學術發展以重要啟示。
第一,精誠團結,開拓進取的時代精神。作為戰時惟一幸存的“聯合大學”,三校管理層聯系緊密,相互團結不足為奇。但是眾多學者價值觀念、政治傾向等各不相同,相互之間的思想交鋒有時十分激烈,而這些思想迥異、個性突出的學者團結成堅強的整體。由此不難看出,在家國情懷的感召下,他們匯聚于西南聯大,辛勤耕耘,共赴國難。當今時代,中國學者需要弘揚他們精誠團結,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積極探索,勇于創新,以強烈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覺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不竭的智慧和源泉。
第二,篤定心志,敢于擔當的使命意識。西南聯大學者是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學術報國的楷模,也是中國知識分子主動參與現實、推動社會前進的成功范例。由于全民抗戰,他們不可能離開校園親赴前線,但是他們致力于思想文化的創造,把學術研究作為文化抗戰的利器,認為思想文化的創造是文化和精神的抗戰。他們恪守旨趣,擔負起時代賦予的使命,或撰寫國史,或提出文化抗戰,或靜心著述,在嚴酷的環境中他們的愛國熱情空前迸發,成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學術報國的典范。
第三,至誠至真,兼容并包的治學態度。西南聯大學者自覺地將自己的命運和國家、民族的興衰緊密聯系,在艱難時世中創造出如此眾多的學術成就。他們在昆明低矮的房屋下精誠合作,相互包容,自覺維護良好的學術風氣,抵制社會的不公,使研究成果不斷推陳出新、日益精進。
第四,潛心治學,精于求精的敬業精神。西南聯大學者將學術研究看作是報效祖國的重要途徑,正是在這一思想的熏陶下,一批又一批出身西南聯大,后又到國外深造的學子,在學成之后義無反顧地放棄國外的優裕生活和良好的工作條件,如朱光亞、鄧稼先、王佐良等,回到祖國為中華民族的崛起作出貢獻。
(作者系云南大學社會科學處副處長、文學院教授;摘自《學術探索》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