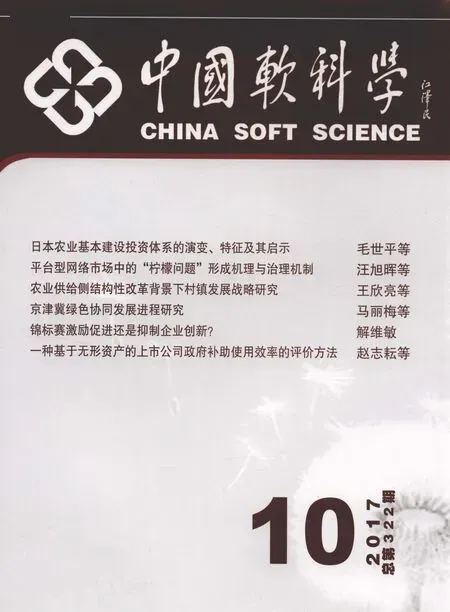超越問責:中美應急管理結構比較研究
——基于天津港與德州大爆炸分析
周利敏,李夏茵
(廣州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州 51006)
超越問責:中美應急管理結構比較研究
——基于天津港與德州大爆炸分析
周利敏,李夏茵
(廣州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州 51006)
在許多國家,重大化工爆炸事故往往暴露了許多問題,從而成為倒逼政府進行應急管理改革的契機。從“災害—沖擊”維度,中美兩國在結構固化、認識結構和輿論制度有趨同之處;從“回應—救援”維度,兩國在行動響應、救援失誤、流程結構和應急方式具有趨同現象。為了從“表面問責”向“結構反思”、從“應急危機”向“變革契機”轉變,需要在問責機制、信息發布制度、危化品應急預案制度、跨部門整體治理、應急行政框架、危化品動態數據庫和危化品應急技能培訓等方面進行結構性變革,從而克服制度結構、行動結構、認知結構和信息結構等應急“結構固化”局限,最終從“系統思維”層面上促進我國從第一代分災害應急管理體系、第二代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向第三代應急風險治理體系的轉變。
危化品爆炸;應急管理;應急法制;應急預案;災害
一、緣起:“問責”亦或反思“血的教訓”?
2015年“8·12”天津特別重大爆炸事故日漸遠去,人們關注熱情逐漸冷卻,如不及時進行深刻反思,未來相同悲劇極有可能重新上演。人們往往關注災害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造成的,停留在將相關責任人員繩之以法就算給“社會一個負責任交代”,僅持有這種觀點是片面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指出這次“血的教訓極其深刻”,2016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去年發生天津港大爆炸事故特別令人痛心,我們必須認真汲取教訓,將這一事件化為應急管理變革“觸發事件”,避免類似慘案再次發生。
這幾年來,國內危化品爆炸事故不斷出現,如2013年山東章丘爆炸事故、蘇州市燃氣公司爆炸事故、山東省濱州市博興縣重大爆炸事故和青島中石化輸油管道泄漏爆炸等,2014年昆山粉塵爆炸和佛山市爆炸事故及2015年安徽蕪湖爆炸等,給社會敲響了嚴重警鐘。無獨有偶,國外也發生了多起化學品爆炸事故,僅美國德州韋斯特鎮,2013年4月化肥廠爆炸前還發生了3次爆炸,2015年又發生了一次爆炸。這些特別重大的爆炸事故屬于典型的“人造災難”,雖具有“極低發生率”,但會產生“極嚴重的損害結果”,這對應急管理提出了嚴重挑戰。就應急管理研究而言,西方起步較早,已擴展到自然災害、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各個層面,同時建立了以計算機科學為基礎的應急管理模型和仿真模擬系統研究,最近又出現了跨學科研究及大數據研究趨勢。國內研究則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萌芽期,2003年以前主要聚焦于分災害管理研究。第二階段是迅速發展期,“非典”推動了應急管理理論與實踐發展。第三階段是繁榮時期,2008年以來重特大災害頻頻發生,應急管理研究也獲得了長足發展。本文主要集中幾個問題:為什么要選擇結構功能主義視角,為什么要進行案例比較,中美兩國應急管理結構有何異同,如何從已有經驗吸取教訓以避免危化品災害這一“定時炸彈”出現,現有應急管理結構存在什么漏洞及如何完善?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框架
(一)美國應急管理總體性研究
美國應急管理的總體性研究視角主要有:第一,發展歷程觀。從1950年代洪水與民防事務處置開始,20世紀70年代,FEMA成為全國緊急事件管理領導機構。第二,三重組織觀,地方政府是第一反應者,聯邦政府給予支持,社會組織參與[1]。第三,“全風險”、“全過程”與“全參與”應急管理模式,呈現出“三位一體”特征[2]。第四,“法律制度授權觀”,這是美國應急管理的基本特點。第五,“多方主體應急協調觀”,強調整合政府資源、社會資源及協調各方行動[3]。第六,“全社會參與”觀,美國吸取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經驗,確定了“全國準備”的基本戰略[4]。第七,“跨州區域應急管理協作”觀,制訂了《州際應急管理互助協議》。第八,“應急管理核心能力導向觀”,這一目標已經基本完成[4]。
(二)中國應急管理總體性研究
中國應急管理的總體性研究代表性視角主要有:第一,“一案三制”核心觀。它是指應急預案,、應急管理體制、應急機制和應急法制,以2003年“非典”為起點,還存在許多不足[5]。第二,“復合危機”趨勢觀。已出現“單一危機”向“復合危機”管理趨勢,目前以“條”為主的“單一災種”管理框架缺乏全災種規劃[8]。第三,“縱向與模向管理局限觀”。應急管理框架呈現出縱向“府際關系”行政化,橫向政府部門分工及整合不足[6]。第四,“多中心治理需求觀”。2009年南方冰雪災害中暴露出“強政府—弱社會”應急管理格局不足,需要以“多中心治理觀”重構政府—社會關系[7]。第五,“彗星”結構與“彗尾”效應觀,目前應急管理出現結構固化與結構演進并存局面[8]。
(三)理論框架
通過文獻研究發現,從2003年以來,我國應急管理研究從少到多、從慢到快、從邊緣到主流迅速發展起來了。基礎研究日益深入,開創性研究成果時有出現,延伸性研究不斷增多,但也存在理論研究薄弱、重宏觀輕微觀和比較研究缺乏等局限。災害社會科學主要有四大流派,即經典的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社會脆弱性學派、社會建構主義學派和社會韌性學派。結構功能主義一直是災害社會科學的研究主流,以DRC組織類型學為代表,但在應急管理領域中還比較缺乏。
結構功能主義視角首先強調“系統思維”和“整體視角”,比較適合宏觀與中觀研究。其次,我國應急管理存在許多發展困境,重要原因就是應急管理單一,發展脫離整體系統的“單兵突進”,脫困的根本途徑就是回歸結構[8]。結構功能主義將應急管理看成一個有機整體,各個組成部分是其中的重要結構,這些結構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它著重對災害組織績效進行探討[9]。結構是指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在類型上分為外在與內在、物質與非物質、顯形與隱形結構等,它不僅指組織結構、制度結構和行動結構等外在顯形結構等,還包括認知、思想和文化等內在隱形結構,是一種客觀存在事實。它不僅探討如何使結構“恢復正常”的核心議題[10],以夸蘭泰利(Quarantelli) 為首的DRC學派還進一步探討災難情境的“變”與“常”,關注結構在災難發生之后會產生何種變化[11]。本文從應急結構趨同、趨異及變革維度出發,對行動、管理、認知和應急方式等結構進行趨同比較,對應急組織、制度、預警與社會參與等結構進行趨異比較,從制度、行政和危化品管理等結構提出我國應急管理結構變革策略(如圖1)。

圖1 應急管理結構比較分析框架
三、兩個案例:德州大爆炸與天津港大爆炸
庫姆斯(Coombs)通過研究西方制藥公司爆炸事件,發現在不同危機階段需要采用不同的應對策略[12],才能有效應對應急管理提出的挑戰,因此首先需要對兩次大爆炸過程進行描述。
(一)案例選擇
選擇案例法主要基于三點考慮:第一,由于災害具有不可預測性、不可重復性和日益復雜性等特征,往往難以進行全面、規范和大規模問卷調查。其次,災害具有非線性特點,災害后果不僅具有客觀屬性,還具有社會建構的屬性,難以通過量化途徑獲得相關認知[8]。最后,研究倫理考慮。由于災害給民眾帶來重大精神和心理創傷問題,問卷調查可能會對其心理形成“二次創傷”。選擇比較法也基于三方面考慮,首先因為它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夸蘭泰利認為這是災害情境或災害組織的基本研究法[13]。其次在災害社會科學領域,已出現案例比較研究。最后通過對“焦點事件”比較,避免“先入為見”的價值陷阱。
進一步的問題是,為什么選擇這兩個案例?案例比較需要具備一些共性,第一,兩個案例都是危化品爆炸,具有可比較起點。第二,兩個案例都屬于重大的安全生產責任事故,對兩國而言都具有非常好的代表性。同時,案例比較也需要明顯差異。第一,案例發生背景不同,可以讓本研究獲得應急管理的比較認識。第二,案例產生后果不一樣,2015年美國德州又生了大爆炸,但這次并沒有像2013年那樣出現人員傷亡,這有利于對二者進行深層次結構性反思。第三,兩個案例關鍵要素有許多不同,例如應急制度、應急組織、災害預警和社會參與等。
(二)案例介紹
1.美國德州大爆炸
2013年4月17號,得克薩斯州韋斯特鎮一家化肥廠發生火災,在救火過程中,化肥廠受火勢影響再次爆炸,威力相當于一顆原子彈或2.1級地震,直徑30多米寬火球騰空而起形成高聳入云的蘑菇云,幾乎將廠區附近四個街區瞬間夷為平地,造成70人遇難,近兩百人受傷,70棟民宅被毀。
緊急救援:大爆炸發生后,6架直升機和所有救護車立即被調派參與救援,地方警察、消防員與志愿消防員等加入救援,數十個鎮縣派出專業救援人員協助。由于化工廠形成“次生災難”,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救援的近10名消防員遇難。美國煙酒槍炮及爆炸物管理局派出國家級突發事件應急小組奔赴現場勘查,專業有毒物質處理部門到現場處理,駐德克薩斯州軍事部隊對爆炸區進行實時空氣監測及生化物危害評估。
政府響應:4月17日當晚,州長佩里發表聲明稱正在密切監控事態發展及調動州內資源提供盡可能援助等。4月18日,白宮網站發布總統聲明,聯邦政府部署緊急救援工作并安撫人心,警方立即挨家挨戶緊急疏散危險區域住戶。五所學校全部關閉,周邊數公里被嚴密封鎖以防有毒煙霧擴散及引發新爆炸。
善后恢復:2013年4月25日,大爆炸一星期后,奧巴馬在為遇難者舉行的追悼會上向死難者致哀并安慰受災民眾,強調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密切聯系,確保搜救和重建需求得到滿足。在解除警報后,原本被疏散的當地居民有序回到韋斯特,配合政府開展重建家園工作。
問責反思:爆炸發生五天后,美國化學安全和危險調查委員會發布官方聲明,稱這一爆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化肥廠違背了聯邦及州法規高危化學品存放要求。事后一個月內,聯邦政府和德州政府共同派出專業人員組成調查隊。直到2016年,即使事故成因已有結論,聯邦、州政府及民間組織仍然拷問化學品管理制度。
2.天津港大爆炸
2015年8月12日,天津濱海新區瑞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危險品倉庫發生爆炸,能量相當于24噸TNT,造成165人遇難,包括公安消防人員110人,8人失蹤,造成798人受傷。
緊急救援:第一次爆炸后,天津消防總隊公安消防員和港務局碼頭專職消防員趕赴現場,遭遇了第二次爆炸,幾乎全軍覆沒。此后,消防官兵及公安民警到達分批次現場搶救。13日7點半,國家衛生計生委從北京等地組織血液藥品等醫藥物資及醫療專家趕赴天津協助救援。13日中午,天津武警總隊1500人和8360部隊防化中隊趕到現場,環保部應急中心迅速趕赴爆炸區域附近,對有毒有害氣體進行監測。
政府響應:8月13日凌晨4點,天津市領導第一時間趕到現場,隨后黨和國家領導人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國務院事故調查組迅速確定新工作思路:由于危化品數量及儲存方式不明,暫緩撲滅。同時,密切關注環境監測,調取海關、瑞海公司及其他企業數據,了解堆放危化品及所在位置,派專業人士確認火災及爆炸物質會不會引起其他災難。13日下午4點30分,舉行了首場新聞發布會。
善后恢復:李克強總理趕赴爆炸現場,看望慰問消防隊員、救援官兵、傷員及受災群眾,指示一視同仁犧牲的現役和非現役消防員。天津市濱海新區政府在官方網站公布受損房屋處置細則,同時抓緊進行烈士評定及骨灰安葬等事宜,已出院傷員按照無縫對接和就近理療原則開通綠色通道,對于不能出門傷員則提供家庭醫生,同時加強心理危機干預及建立專業干預隊伍等。
事后問責:2015年8月18日,經國務院批準,公安部、安全監管總局、監察部、交通運輸部及環境保護部等有關方面組成國務院調查組。2016年2月5日公布了調查結論,認定是一起特別重大生產安全責任事故,瑞海公司是主體責任單位,天津市交通、港口、海關、安監、規劃和國土、市場和質檢、海事、公安等部門及濱海新區環保、行政審批等單位未認真貫徹落實有關法律法規,違法違規進行行政許可和項目審查,日常監管嚴重缺失,有關中介和技術服務機構弄虛作假等。
四、結構趨同:大爆炸與中美應急管理比較
博林(Boin)與哈特(Hart)認為,應急管理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組織結構、媒體監督、人員壓力及不精確信息等都會影響管理者及其行為[14],大爆炸是由多種復雜因素造成的,結構趨同層面主要體現為應急行動、認知、應急方式和管理等四個結構層面(如圖2)。

圖2 中美應急管理結構趨同
第一,應急行動響應相似。2003年非典后,中國初步建立全面應急救災體系,雖不如美國那樣全面成熟,但已初步形成統一的行動規范,應急行動日趨規范與專業。例如,兩國政府領導人都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或下達緊急救援命令,救援隊在第一時間內也進行緊急救援,醫院、衛生和安檢等部門參與了救災工作。賴利(Reilly)認為危機發生后需要立即成立處理小組并將危機隔絕[15],兩國在危機爆發后都迅速成立了專門小組。面對重大的事故災難,國家相關部門需要在24小時內參與救災行動,以便國家迅速調集大量資源和專業力量應對災難及提供專業性指導意見。努納美克(Nunamaker)等指出在應急處置階段還需對專門小組提供資源幫助[16],兩國在大爆炸后都調動了各種資源協助專門小組進行應急處理。
第二,應急救援失誤相似。杜福特(Dufort)認為在突發事件中,由于管理者急著在最短時間內控制風險及降低不確定性[17],意味著采取相應行動失誤風險的增加。由于危化品具有易燃易爆的性質,但天津港和德州大爆炸都反映了相關的危化品應對經驗及管理制度缺乏,消防員在第一時間內進行了緊急救援,都沒有料到會發生“次生災害”,都出現了消防員傷亡的重大失誤。雖然消防員第一時間奔赴現場勇氣可嘉,但由于缺乏危化品應急預案及日常的應急演練而釀成慘案。當災害初次發生時,政府官員和現場指揮人員也都誤以為這是一起普通火災,按照一般的應急方案進行應對,其緊急救援決策存在明顯失誤。
第三,結構固化及碎片化管理相似。在天津大爆炸中,安檢部門、危化品管理機構及海港管理局等在安全生產、安全管理和應急處理中職責模糊,縱向是一套體系,橫向是另一套體系,橫向政府不同部門之間形成了條條框框的碎片化關系,容易導致“應急失靈”和“組織失效”。德州大爆炸事故也反映出了類似問題,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美國災害應急響應和救助指揮就掌握在不同部門中,指揮分散情況非常嚴重,美國試圖建立以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為中心的整體性救災機制,但在德州大爆炸中碎片化管理問題依然突出,明顯缺乏對化學品運輸、儲藏及應對的整體性管理或跨域管理機制,兩國在“管理—碎片化”方面具有相似性。
第四,應急管理流程結構相似。布賴恩(Brien)認為美國綜合應急管理主要包含三大制度:“全危險方法”是對所有災害進行統一管理,“應急管理信息系統”將各種災害管理機構信息進行共享,“應急管理循環流程”包括減緩、準備、響應和恢復的全程管理流程[18]。2003年非典之后,中國建立了“一案三制”體系,2007年又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建立了應急管理循環即PPRR管理模型,分為預防、準備、響應和恢復四個階段,形成了以時間為主軸的鏈式管理流程模型,在這一點上兩國具有相似性。
第五,危化品認識結構不足相似。危化品大爆炸是死亡人數最多的災難事故類型之一,需要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重視,但兩次大爆炸均反映了危化品認識結構性缺乏。在德州爆炸事故中,涉事化工企業不知道如何安全存放危化品,消防員沒有接受過危化品應對培訓,對硝酸銨和危化品缺乏正確的認知。雖然相關部門要求消防員撤離現場,但消防隊長沒有下達命令,在“二次災害”中,再也沒能走出來。天津大爆炸反映相關部門對危化品風險缺乏正確認識,消防員沒有撤離火災中心,沒有針對危化品進行專業滅火。化學品火災不同于其他火災,化學物相互反應會造成難以預料變化,會迅速引發其他危化品連環爆炸。而且,某些化學品用水無法撲滅,兩國消防員缺乏危化品風險認識是極為相似的。
第六,前期常規應急方式相似。應急方式結構包括常規與特殊應急兩種類型,德州大爆炸是一起由一般危化品引發的災難事故,消防員采取常規方法進行滅火。雖然有害物質小組趕到現場進行特殊處理,但前期基本上以常規方法為主。天津大爆炸由特殊而非一般危化品引起的,在首次長達半個小時救災過程中,消防員一直使用水與泡沫滅火降溫。危化品燃燒時,貿然用水或泡沫進行搶救可能會導致化學反應加劇,從而造成“二次爆炸”。換句話說,特殊危化品引發的火災一般不能采用常規應急方法,需要專門的危化品應急方案(如使用沙土蓋滅)加以應對。這兩次大爆炸前期都采用了常規方法應對,都造成了重大的救災失誤。
總之,從“災害—沖擊”維度,兩國應急管理在結構固化、認識結構和輿論制度有許多相似之處,而在“回應—救援”維度,兩國在行動響應、救援失誤和流程結構也具有趨同現象。
五、結構趨異:大爆炸與中美應急管理比較
大爆炸也呈現出兩國應急管理結構趨異現象,結構趨異分為應急組織、制度結構、預警結構、社會參與和應急反思等五個層面(如圖3)。
第一,應急法制不同。德州大爆炸雖然存在救援失誤,但整個應急過程體現了應急法制相對完善的特點。早在1950年,美國制訂了《災害救助及緊急援助法》。1988年,出臺了《斯塔福德減災和緊急援助法》,賦予聯邦應急管理署在災害應對、準備和減災等領域更多權限。1992年出臺《聯邦應急計劃》,2004年的《國家響應計劃》建構了綜合應急管理框架。2005年,提出了《國家應急反應框架》。相對而言,我國法制還比較單一,2007年頒布了應急管理領域的基本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公共事件應對法》,標志著我國應急立法進入了新高度,但系列性和專門性的應急法制仍然缺乏。雖然后來也制定了《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和《生產安全事故報告和調查處理條例》等,但在安全評估和環境評估等方面專門法制還非常薄弱。天津大爆炸不僅反映法制建設明顯不足,還出現漠視既有法制及“立而不行”等問題,二國屬于“法制驅動模式”及“體制驅動模式”的不同。

圖3 應急管理結構趨異
第二,應急管理體制結構不同。在“府際關系”層面,美國應急救災體制分為聯邦和州兩級,呈現出合作與制約的特點。德州大爆炸發生后,州政府首先啟動應急預案進行救援,同時第一時間上報聯邦政府,聯邦下派應急小組與州政府一同救援。緊急救援過后聯邦應急小組撤離,地方政府負責災后重建工作。這一體制優點是地方政府能快速、準確開展應急行動,缺點是面對重大災害時州政府向聯邦政府求助程序繁瑣。在天津大爆炸中,應急救災流程是當地政府或相關單位先行處理,同時上報國務院應急辦,應急辦派出專家小組與地方政府共同進行應急救援,緊急救援后專家小組撤離,地方政府負責善后工作,國務院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擔災后重建工作。雖然我國出臺了《泛珠三角區域內地九省(區)應急管理合作協議》,但針對的是不同省份的橫向合作關系,與美國《州際應急管理互助協議》相比,部門合作缺乏明確的協調機構及機制,沒有統一應急指揮權及跨區域應急預案體系[19]。
第三,消防員職業制度不同。美國消防員分為職業制和義務制兩種,消防員有著非常嚴格的篩選制度,學歷最低標準是高中,很多部門要求至少具有兩年制火災專科學歷,甚至需要大學本科學歷。職業消防員是一個英雄般職業,平均薪資遠超地方平均工資。業余消防員雖沒有工資,但享受健康保險、生命險、殘疾保險、養老撫恤和稅收減免等政策。中國消防員主要有公安消防部隊、企業與政府專職消防隊及志愿者三種類型,公安消防隊實行現役軍人制,占全國60%以上,約有23萬人。近年來,現役消防編制緊縮,地方開始大量招收合同制消防員,數量基本與現役消防員等同。公安消防員和專職消防員一般依法享受保險和福利待遇,但專職消防員福利水平與美國相比差距較大,造成專職消防員流動性較大,我國的消防體制需要進行反思與變革。
第四,應急管理組織不同。1979年,美國將各救災單位合并成立“聯邦緊急事故管理署”,2003年并入“國土安全部”,作為應爭管理的最高領導機構,直接受總統領導。同時,在全國各地建有直屬的應急辦事處,4000人隨時待命。同時還制訂了“國家應變架構”,統一各政府機關的應急管理行動,并建立全國性 “國家突發事件管理系統”。2003年“非典”后,我國應急救災體系從原來的單一災種向綜合性災種發展,將自然災害、生產事故、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等統稱為“突發事件”,并建立了應急管理辦公室,直接隸屬于國務院。同時,實行“分類管理”原則。天津大爆炸體現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統一指揮下充分調動各方力量和資源及時行動優勢,但中央層面沒有專業應急管理機構,國務院應急辦只具有協調功能,沒有直屬專業應急救援隊伍,也不是各地應急辦直接領導機構。
第五,應急預警不同。德州大爆炸并不能掩蓋美國“預防重于救急”或“預防導向型救災”的核心理念,非常注重預防和減緩作用,FEMA推崇理念是“預防上投資一美元,恢復上節約兩美元”。大爆炸后,美國進行了深刻反思,再次從制度和行動上強調應急預防的優先地位。中國雖然也強調災前預防工作,但在實踐中體現的是“結果導向型救災”特點[20],地方政府重視災后應急救援與處置,在預防、準備、預警和監測等方面投入不足。美國的預警設施遍布各地,較為發達,我國這些年雖然有了長足進步,但在許多偏遠地區仍然缺乏預警設施。在危化品預防設施方面,可以安裝火警報警器、有毒氣體監視器及溫度監視器等,能有效預防及處理危化品事故,將風險和損失降到最低。
第六,危機信息發布制度不同。大爆炸發生后政府首先要面對媒體無情審判,庫姆斯(Coombs)和霍拉戴(Holladay)指出危機最初響應會奠定日后人們對于組織及危機的感知[21],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即回應,保持沉默是最糟的策略選擇。政府有責任第一時間向媒體公布災害事件真相以避免謠言滋長,德州大爆炸后,政府立即通過媒體進行信息披露,這有利于政府進行形象管理。在天津大爆炸中,地方政府前后共舉行了十一場記者發布會,每次幾乎都導致4個以上“次生輿情”而受到眾多質疑:為何不及時公布相關信息、爆炸現場是否有700噸氰化物、為何5小時后才辟謠及為何信息源不統一等。李克強總理抵達爆炸現場后針對謠言四起現象表示“權威發布跟不上,謠言就會滿天飛”,反映地方政府無論在立即回應策略方面,還是運用其他策略方面都存在明顯缺陷,因此,需要通過問責或反思教訓倒逼地方政府進行危機信息發布制度改革,以加強政府應急管理的權威性。
第七,社會參與不同。克雷普斯(Kreps)認為在災害事件中,災民擁有社會支持越多,越有利于災民恢復[22]。在德州大爆炸中,FEMA聘請了大量具有專業知識及應急技巧的志愿者隊伍,強調“全社會參與”,注重調動民眾、應急管理人員、社會組織領導人及政府官員參與應急救援的積極性,稱為“跨部門協力”擴張架構。同時,非常重視對志愿者進行應急培訓,視為政府的“聯動伙伴”和緊急救援的“應對主力”。在天津大爆炸中,體現了政府主導的應急救災模式,出現了社會組織參與應急救援不足現象,雖然有安全和規范等方面的考慮,但民間組織參與不足也是事實。近年來,我國民間組織參與救災數量和頻率呈上升趨勢[23],但是構成復雜且分散,在實踐中容易形成無序局面,需要建構民間組織和政府之間“公私協力”、“多元參與”和“多元治理”機制[24],使其在應急救援中發揮更大作用。
第八,應急反思不同。夸蘭泰利(Quaranteli)認為災害事件之所以釀成為災難,主要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政府、社群及個人層次等原因導致[13]。德州爆炸案這一“積淀事件”在美國社會中產生了廣泛影響,美國政府進行了長達兩年的追蹤調查與反思,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和制度改革。例如,美國政府因此專門頒布《緊急情況及公共有權知道法》一系列制度,同時要求各州成立緊急響應中心和地方應急計劃委員會。2015年德州又發生了一起危化品爆炸事故,這次沒有出現傷亡報告。通過總結2013年大爆炸原因,美國政府修訂了相關法制,加強了對化工廠的安全檢查。天津大爆炸給人民留下了慘痛記憶,問責是必要的,但還需要對災難進行深層反思,推動政府進行應急管理制度改革。這些年,我國危化品事故呈增長趨勢,政府面臨的安全生產壓力也越來越大,這固然與工業高速發展有關,但也與各級政府只注意效率,不重視安全生產有關。我國雖制定了《安全生產法》、《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危險化學品經營管理辦法》、《港口危化品管理規定》等法制,但還缺乏專門的危化品應急管理法制,許多法制在執行過程中似乎變成了嚇唬“麻雀”的“稻草人”。2016年2月,天津出臺了《危險化學品企業安全建設實施方案》,但還沒有上升到國家層面。2016年11月29日,在吸取大爆炸教訓基礎上,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危險化品安全綜合治理方案》,開展為期3年的危化學品安全綜合治理,為進一步的反思、配套性制度改革及制度執行變革奠定了良好基礎。2017年5月31日,天津港再次發生大火災,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也反映了不能放松2015年天津港大爆炸悲劇有可能再次發生的警惕。
綜上所述,兩次大爆炸體現了中美在應急管理上的結構趨異,主要有專業性與非協調性、法制驅動與體制驅動、合作制約與上下隸屬、職業制與專職制、預防導向與結果導向、應對主力與有限參與、系列反思與反思欠缺的區別(如表1)。

表1 大爆炸中兩國應急管理結構比較
六、比較啟示及治理變革
在許多國家,重大危化品爆炸事故往往會暴露出許多問題,人們對于同一或其他地方是否會發生類似事故的關注會大大增加,從而成為倒逼政府進行應急管理變革的契機,即所謂的“焦點事件相關政策變革”(event-related policy change)。通過對兩次大爆炸進行比較,為我國應急管理提供重要的變革啟示(如圖4)。
第一,問責制度變革反思。羅伯特(Robert)與洛伊陶(Lajtha)認為應急管理的焦點是在面對危機時如何學習與反思,以避免或降低類似危機的發生,這樣才能真正使得管理者有能力處理類似的非預期危機[25]。天津大爆炸后政府進行了嚴肅問責,處罰了一批相關責任人,國務院反復強調在問責基礎上重視對事故真相的了解,促使政府和民眾真正從事故中學習與總結教訓。目前問責制形成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突發事件的推動,還存在許多不足,需要從“事后問責”向“事先預防”和“風險問責”轉變[26],因為對付災難最有效的方法是預防(preventive)。而且,現有問責制使得許多人關心災害后果承擔,不愿采用新的應急理論和方法,可能會使相關人員失去學習機會而導致創新不足。例如,復雜成分可燃性研究是一個國際學術界前沿問題,針對這一研究已出現了一些新成果,但目前并沒有將這一安全領域的最新成果運用到實踐中來。

圖4 應急管理結構變革框架
第二,危機信息發布制度變革。信息發布制度是應急管理最被人關注的環節之一,天津政府面對輿論關心的一些核心問題反應遲鈍,多次出現“不知道”、“不掌握”和“無法回答”等詞眼。李(Lee)在飛機因天候因素造成失事的應急管理研究中發現,否認策略會讓民眾感知組織應負更多的責任,從而對組織產生系列的負面印象[27]。因此,福爾圖納托(Fortunato)指出當危機爆發后,管理者首要任務就是立即采取形象修復策略[28],及時降低或扭轉民眾對政府的負面印象。而且,在不同危機發展階段,需要靈活使用相應的輿論應對策略,如合理化、同情、歉意及補充策略等[12],天津大爆炸反映了危機信息應對策略及發布制度需要進行結構性變革。
第三,應急預案制度有效性變革。卡斯蒂略(Castillo)認為危機預案管理模型由三個要素構成,即危機戰備、危機響應和危機善后制度[29]。在德州大爆炸中,消防部門沒有專門的危化品應急預案,也沒有針對硝酸銨引起的火災進行過演練。因此,聯邦應急管理局加強了與各州地方應急管理中心合作,幫助各州制定專門危化品爆炸應急預案。在天津大爆炸中,也沒有建立專門的應急預案,消防員沒有相關的危化品火災應急演練。而且,即便制定了相關預案,但大多流于形式,缺乏實操性與有效性。因此,我國需要實現常態性與非常態性危化品預案的有機結合,并制定相應的應急預防措施,如控制人員接觸、遠離人口居住或密集的區域、密封包裝、相隔足夠距離及禁止煙火等措施。在2017年5月31日天津港火災中,由于附近空曠,周邊無居民和企業,因而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同時,還需要加強危化品緊急救援與疏散演習,通過分類分層、情景模擬及演練并舉等途徑增強地方政府、消防員和公眾應對危化品災害的能力。
第四,跨部門整體治理策略。康福特(Comfort)等學者指出跨部門協調與合作能有效提高應急管理的績效[30],在德州大爆炸中,事故的直接誘因是硝酸銨,根本原因是由于硝酸銨監管分散在聯邦和州各個行政機構之間。針對這一現象,德州議會舉行了多次聽證會,討論將監管職權集中同一機構的可能性。奧巴馬也于2013年8月簽署行政法令,要求各級聯邦機構與州政府合作。在天津大爆炸中,也存在危化品管理部門眾多、職責重疊、垂直和橫向管理混亂及應急監管分散等問題。由于應急管理往往具有“跨域”或“跨界”治理特點,需要在互惠與協作基礎上,建構跨部門、開放性、全風險和協同治理的整體應急管理框架。
第五,應急行政框架及法律改革。德州大爆炸成為推動美國應急管理改革的“政策之窗”,倒逼美國進行行政和法律改革。奧巴馬在行政令中要求各級聯邦機構與州政府制定或更新相應的規章制度,從系統上提高整個化工行業的安全性。2014年5月,聯合工作小組詳細闡述了過去一年聯邦政府為了提高危化品行業安全性而做出的種種行政和立法改革。天津大爆炸的發生與不嚴格遵守安全規定有關,也與應急行政框架及安全法律漏洞百出有關,因此應急行政及法律需要進行相應改革。例如,大爆炸發生前天津市簽署了《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規定取得港口經營許可證企業在港區內從事危險化學品倉儲經營,不需要取得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這是具有明顯漏洞的制度安排。
第六,危化品動態數據庫建構。美國境內硝酸銨的儲藏地點和方式屬于政府秘密,普通居民沒有辦法查詢住所附近是否有危化品倉庫。而且,應急人員也沒有危化品動態數據,對事故現場的危化品狀況也不清楚。在天津大爆炸中,地方政府對于存放的危化品沒有盡告知義務,消防員也不了解危化品相關情況。康福特等學者認為運用信息科技技術,有利于提高應急管理對抗風險的能力[40]。因此,中美兩國都需要建立危化品公共動態數據庫,構建網絡化協調和監督機制,讓公眾參與到公共安全監督中。雖然,一些數據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但可通過“脫密化”和“脫敏化”處理后公開相關數據。
第七,危化品應急技能動態培訓。墨菲(Murphy)的研究發現非線性動態管理能有效監督應急管理過程及提高應急效率[31],同樣這也是提高消防員應急技能的基本途徑。德州大爆炸反映應急救援人員缺乏危化品專業應急技能,2013年8月,美國聯邦政府發布了《關于硝酸銨的儲藏與管理的指導意見》,共有19頁,這是美國首次發布專門針對硝酸銨安全管理文件。美國國土安全局和環境保護局也加大了對地方政府、消防機構及公眾危化品安全培訓和宣傳。在天津大爆炸中,如果事先建立較為完善的應急機制,災前建立了專門危化品安全管理法制,并且得到嚴格執行,同時通過報紙、雜志、電視和網絡等途徑進行相關教育,這一慘案或許就不會發生。2017年5月31日天津港又發生了火災,為了控制火勢,消防隊員在貨場四周架起了數臺高達十幾米的機械臂,利用機械臂的高度從上往下噴水滅火,這明顯吸取了2015年大爆炸教訓,在不明原因情況下沒有冒然派消防員直接滅火,這與相應的應急技術培訓、知識宣傳及經驗總結的努力分不開。此外,應急管理需要擺脫“人禍論”思維,因為這會導致人們不太關注安全文化、為何會引起爆炸、如何處理爆炸事故以及總結相關經驗教訓以避免類似悲劇重演,而這是目前應急管理亟須解決的重要議題。
我國災害風險與公共安全形勢非常嚴峻。通過深入探討中美應急管理的結構趨同與趨異,有利于從“結構回歸”角度健全我國應急管理體系。比較研究表明,我國應急管理需要從“表面問責”向“結構反思”、從“應急危機”向“變革契機”轉變,以克服跨界治理、制度結構、行動結構、認知結構和信息結構等應急“結構固化”的局限,最終從“系統思維”層面促進我國從第一代分災害應急管理體系*這是指根據不同的災害類型及不同部門建立的應急管理體系,例如根據起因分成人為災害或自然災害的應急管理體系,或者根據原因、發生部位和發生機理劃分成的地質災害、天氣災害、環境災害、生化災害和海洋災害等成立的應急管理部門,導致應急管理分散、重疊、沖突及低效等現象出現。、第二代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向第三代應急風險治理體系的積極轉變。
[1]郭太生.美國公共安全危機事件應急管理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J].2003(6): 16.
[2]王宏偉.美國應急管理的發展與演變, 國外社會科學[J]. 2007(2): 53.
[3]閃淳昌,周 玲,方 曼.美國應急管理機制建設的發展過程及對我國的啟示[J].中國行政管理, 2010(8): 100-105.
[4]游志斌,薛 瀾.美國應急管理體系重構新趨向:全國準備與核心能力[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5(3): 118.
[5]劉 霞,嚴 曉.我國應急管理一案三制建設:挑戰與重構[J], 政治學研究,2011(1):94.
[6]陶 鵬.中國應急管理縱向府際關系:轉型、挑戰及因應[J].南京社會科學, 2015(9): 91.
[7]王光星,許 堯,劉亞麗.社會力量在應急管理中的作用及其完善——以2009年部分城市應對暴雪災害為例[J].中國行政管理,2010(7): 67.
[8]張海波,童 星.中國應急管理結構變化及其理論概化[J].中國社會科學, 2015(3): 58,67, 58-68,24,67.
[9]TIERNEY K J.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mainstream? disaster research at the crossroa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J]. 2007, 33(2): 503-525.
[10]STALLING R A. Weberian political sociology and sociological disaster studies[J]. Sociological Forum , 2002, 17(2): 281-305.
[11]ROSENTHAL U. Future disasters, future definitions[Z]. In QUARANTELLI E L. (Ed.), What Is a Disaster? Perspectives on Ques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232-254.
[12]COOMBS W T. West pharmaceutical’s explosion: structuring crisis discourse knowledge[J].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04, 30(4): 467-473.
[13]QUARANTELLI E L. Where we have been and where we might go[Z]. In QUARANTELLI E L. (Ed.), What is a Disaster? Perspectives on Ques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370-382.
[14]BOIN A& HART P. Public Leadership in times of crisis: mission impossible?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3 63(5): 544-553.
[15]REILLY A H. Are organizations ready for crisis? a managerial scoreboard [J].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87, 22: 79-88.
[16]NUNAMAKER J F J. et al. Organiz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systems: planning for intelligent Ac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989, 5(4):7-31.
[17]ROUX-DUFORT C. Is crisis management (only) a management of exceptions? [J].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2007, 15(2): 105-114.
[18]BRIEN G O. UK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6, 59(2): 63.,
[19]盧文剛, 黎舒菡.中美省、州級政府間應急管理協作比較研究——以“泛珠三角”和EMAC為例[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 2015(5):28.
[20]周利敏.“離災優于防災”:國際災害治理政策創新及對中國啟示[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 2015(1): 7-14.
[21]COOMBS W T& HOLLADAY S J. Communication and attributions in a crisis: an experiment Study in crisis communication[J].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996(8): 279-295.
[22]KREPS G. Disaster as a Systemic Event and Social Catalyst[Z].// QUARANTELLI E L (Ed.),What is a Disaster? Perspectives on Ques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153-167.
[23]周利敏.災后重建中非正式制度的非正式功能及類型化分析[J].人文雜志, 2016(2): 102-104.
[24]LOUISE K. Comfort, Rethinking Security: Organizational fragility in extreme event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2, 62(2): 98-107.
[25]ROBERT B &LAJTHA C. A new approach to crisis management[J] .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2002(10): 181-191.
[26]張海波,童 星. 公共危機治理與問責制[J]. 政治學研究, 2010(2): 50-56.
[27]LEE B K. Audience-oriented approach to crisis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Hong Kong consumers’ evalu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crisis [J].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4(31): 600-618.
[28]FORTUNATO J A. Restoring a reputation: The Duke University lacrosse scandal [J].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08, 34(2):116-123.
[29]CASTILLO C.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 at Boeing: An integrated model. Journal of Facilities Management, 2004, 3(1), 8-26.
[30]COMFORT L K, SUNGU Y. JOHNSON D &DUNN M. Complex systems in crisis: Anticipation and resilience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J].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2001, 9(3): 144-158.
[31]MURPHY P. Chaos theory as a model for managing issues and crises [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1996,22(2): 95-113.
(本文責編:辛城)
BeyondAccountability:AStructuralContrastStudyonDisasterEmergencyManagementbetweenChinaandUSA——ACaseStudyonExplosionsinTianjinandTexas
ZHOU Li-min, LI Xia-yin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ofGuangzhou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A contrast and comparison study on explosive disasters in Tianjin and Texas show us that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of emergent management. They are similar in structure solidifying,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system of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aster and shock and similar in response to disaster, mistakes in rescue,procedure structure and ways on emergent occa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ponse and rescue. However, they differ in such aspects in structure as speciality and coordination, system driven and law driven, control from cooperation and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professional system and full time system, prevention and consequence orientation, emergent response and relative slow, social reaction and limited participation, systematic reflection and lack in reflection and so on. In order to change the system from accountability to structural reflection and turn crisis into opportunity, we’d better overcome such shortcomings as failure in classic management, false and cross-border management, underlying rules for emergent management by reforming such structures as accountability system and emergent pre-arranged plans for dangerous chemicals, information broadcasting system, overall cross-border governance, administrative system for emergency, dynamic data base, training skills in dealing with dangerous chemicals in emergency and so on, thus overcoming the inflexibilities in system, action, cognition and information to positively transform our emergent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first stage of separating emergent system for disasters to the second stage of overall national emergent system and finally to the third stage of emergent risk management system.
explosion of dangerous chemicals; emergent management; emergent laws; emergent pre-arranged planning; disaster.
2017-01-16
2017-08-20
2015年廣州市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面上重點課題“特大城市應對突發性災害的社區教育研究”(1201522893)階段性成果。
周利敏(1977-),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廣州大學南方災害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博士。
D668;C916;D638
A
1002-9753(2017)10-0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