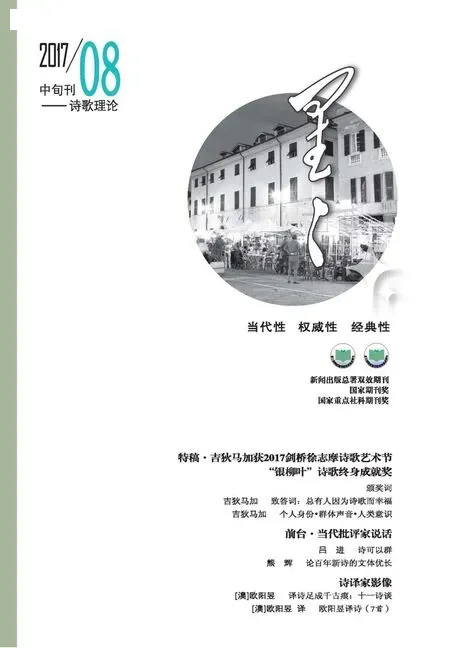在時(shí)間中沉潛的詩(shī)歌
楊東偉
每月詩(shī)歌推薦
在時(shí)間中沉潛的詩(shī)歌
楊東偉

在海德格爾那里,時(shí)間構(gòu)成了“此在”的一切境域,人類(lèi)需要在“此在”的時(shí)間線中展開(kāi)自我的體驗(yàn)與生存,并據(jù)此向“存在”發(fā)出追問(wèn)。這樣來(lái)看,正是時(shí)間建構(gòu)了人類(lèi)賴(lài)以生存的根基,也塑造了我們自己。我們活在時(shí)間之流中,且需要不斷地解決和回答時(shí)間對(duì)我們提出的問(wèn)題,才能最終獲取生命的價(jià)值與意義,而在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寫(xiě)詩(shī)也是一樣。真正的詩(shī)人并不沉迷于“虛度時(shí)光”,或是在消費(fèi)主義的泡沫里玩弄語(yǔ)言游戲,而是應(yīng)學(xué)會(huì)在時(shí)間里沉潛,在對(duì)時(shí)間的深度體驗(yàn)中加深對(duì)自我、對(duì)他者、對(duì)世界的理解和認(rèn)知。時(shí)間對(duì)于這些詩(shī)人而言就是生命的饋贈(zèng),或者說(shuō)是米沃什意義上的“禮物”,詩(shī)人在和時(shí)間的對(duì)話與相互贈(zèng)予中,也獲得了生命應(yīng)有的厚重感。
如果將一刻的“停頓”納入到整個(gè)生命的時(shí)間之流中來(lái)觀照,它只是如博爾赫斯說(shuō)的那樣是“孤獨(dú)的一瞬”,既微妙如塵,也不可把捉。代薇的詩(shī)卻將能將這“停頓”放大和提煉,變成一種詩(shī)意的綻放。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和閱歷的豐富,詩(shī)人的內(nèi)心越發(fā)纖細(xì)而敏感,她甚至清晰地記得“夜晚的唱片,金屬?gòu)澢?漸失的體溫”,也愈發(fā)覺(jué)得在這個(gè)世界上有太多我們無(wú)法撼動(dòng)和改變的事物,比如“世界的方向”,這是一種 “無(wú)能的力量”。在這種撒旦之力的籠罩下,詩(shī)人既“執(zhí)迷”而“痛心”,卻又無(wú)能為力。而她乘坐的生命火車(chē)就像時(shí)間之流中那既短暫卻又“漫長(zhǎng)的停頓”,這“停頓”也如荒野中無(wú)助等待的戈多,充滿著無(wú)限的荒誕感,此時(shí)她記起了“你的眼睛/像一個(gè)傷口挨著另一個(gè)傷口”。詩(shī)人向我們展示出生活中必然存在的某些莫名的無(wú)可奈何,同時(shí)也揭示了時(shí)間帶給我們的創(chuàng)傷和疼痛。這種生命內(nèi)在的疼痛無(wú)法被治愈,就像一個(gè)“永恒的停頓”一樣,詩(shī)人只有帶著它繼續(xù)上路,隱忍地生活。
窗戶(hù)的《身體里漸漸有木質(zhì)的東西》一詩(shī),則展現(xiàn)出80后詩(shī)人精神成熟的過(guò)程。伴隨時(shí)間與經(jīng)驗(yàn)的累積,80后詩(shī)人身上那些漂浮感和浮躁之態(tài)在逐漸淡去,更多了一些生命的沉淀,這是時(shí)間在他們身上的刻痕。詩(shī)人感覺(jué)“身體里漸漸有木質(zhì)的東西”,但這“不是因?yàn)樗ダ狭恕保羌由盍藢?duì)生活和生命本身的理解。這些隨時(shí)間而增長(zhǎng)起來(lái)的“心靈溝壑”,“更像蕩漾的水面/靜靜容納所有投影”,更具包容之力,也更蘊(yùn)含著詩(shī)人對(duì)生活本身的領(lǐng)悟與參透。詩(shī)人反思自己以前的生活:年少輕狂之時(shí)熱愛(ài)樹(shù)葉和花朵,喜歡女孩子的襯衫,憧憬一切“充滿陽(yáng)光與歌聲”的事物,因?yàn)槟窍笳髦啻号c活力。但“現(xiàn)在只剩回憶了”,詩(shī)人卻并不后悔,因?yàn)闀r(shí)間帶給他的并不是流逝與遺憾,同樣帶給他對(duì)生命更深刻、更內(nèi)在的把握,使他領(lǐng)悟到“生命和心靈”會(huì)隨著時(shí)光的淘洗“越久越堅(jiān)硬”。詩(shī)人在時(shí)間中成長(zhǎng)與修行,也在時(shí)間中“得道”;同時(shí),時(shí)間也反過(guò)來(lái)拓展了詩(shī)人生命的厚度與容量。
十九歲的90后詩(shī)人余真有著超出一般同齡詩(shī)人的天賦與成熟,這是時(shí)間讓她迅速成長(zhǎng)的結(jié)果。在她身上極少能看到青春寫(xiě)作的稚嫩,更多的是成年詩(shī)人的洞徹與睿智,她那首小有名氣的《情書(shū)》如此,這首《動(dòng)搖》也一樣。在這首詩(shī)中,詩(shī)人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廣闊的視覺(jué)空間,隨著她鏡頭的推進(jìn),我們看到了“大雁們?cè)谀媳遍g奔波,經(jīng)過(guò)秦嶺、密西西比河/在死海之岸看到低頭吃草的羊群,遠(yuǎn)處豹子正產(chǎn)下自己的孩子”,原始自然中那些互不關(guān)聯(lián)的生物群種在詩(shī)人跳躍的詩(shī)意中被聯(lián)系起來(lái),顯出一副生機(jī)勃勃的生命圖景,充滿著蓬勃旺盛的元?dú)狻5祟?lèi)自己卻生活在被規(guī)訓(xùn)的城市中,看似是身處“在廣闊的河岸”,卻感受不到自然之風(fēng)對(duì)我們的吹拂,因而我們也看不到“蘆葦”與“水流”搖曳的風(fēng)姿,更失卻了“對(duì)生命恍惚的敬畏”。這也驗(yàn)證了本詩(shī)的開(kāi)頭:我們筑了一條“為了通向他方”的路,卻成了“攔住了自己的去路”的路。這首詩(shī)隱含了一個(gè)人類(lèi)與動(dòng)物、自然與城市的二元對(duì)立結(jié)構(gòu),詩(shī)人指出了人類(lèi)作繭自縛的困境,看透了我們內(nèi)心的封閉與荒蕪,而她內(nèi)心的“動(dòng)搖”或許也指向了對(duì)我們生活方式的某種詰問(wèn)與質(zhì)疑,也滲透著對(duì)現(xiàn)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
在一個(gè)浮華的年代,只有像上述詩(shī)人一樣“抱著時(shí)間”沉到我們時(shí)代的“底部”,去領(lǐng)悟時(shí)間本身的力量,才有可能在詩(shī)歌中讓時(shí)間發(fā)芽和開(kāi)花,也才有可能成為一個(gè)被時(shí)間銘記的詩(shī)人。這是他們的宿命,也是他們的責(zé)任。
(作者單位: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