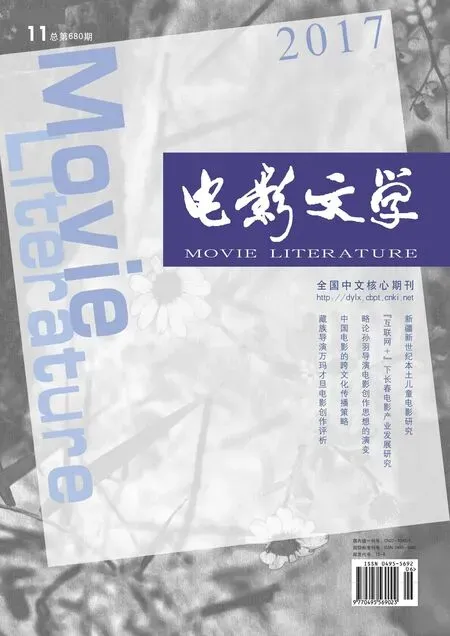“關系”視域下《歸來》的“留白”策略
任慧群(邢臺學院,河北 邢臺 054001)
新中國成立一年后出生的張藝謀,在拍攝《活著》20年后,又以《歸來》顯示了其重新反思新時期前30年歷史的期待:“希望能讓年輕人看到那段歷史。”[1]此時,年過60的他呈現歷史的視角已與不惑之年不同,他“不要直接描寫波瀾壯闊、撕心裂肺”,而是“走入尋常百姓家”,把“時代濃縮到細節中表現”[2],采用“刪繁就簡”[3]、“留白”[2]的方式。在張藝謀看來,這不僅是“技巧”,更是“故事呈現的意圖和態度”[4]。那么,《歸來》中“留的某一句話、某一個形象、某一個處理”[5]“冰山一角的拍攝方法”[3]留下的“細節”[2]又處于何種關系中,發揮著何種作用?由細節留下的空白與“繁”的關系、與“故事”的“意圖”的關系如何?或者說,細節與特定歷史書寫的關系如何?具體地說,借助“細節”留下的空白,影片在尋常百姓家庭故事中主要建構了何種關系?其呈現歷史的方式與人物行為的動機和情感的關系如何?在多層面關系中,填補這些空白時的召喚力量如何實現?
從這一思考出發,可以說,《歸來》主要講述了三口之家在1973年和1979年的故事,并以夫妻、父女、母女等關系為切入點,展示了人物之間“人之常情”“歸來”的過程。影片留下的“細節”,包括與人物情感具有內在關系的音樂等,與揭示人物言行的動因相關的事件及其敘述角度的選擇,召喚著觀眾感受它們與人物、人物與時代、人物與他人、人物與自己等的關系,填充細節留下的空白。由觀眾帶入的“關系”產生的力量,是影片運用留白策略書寫新時期前30年歷史的希冀,即使它有不合理之處。
一、“關系”視域下1973年敘事的留白與歷史書寫
嚴歌苓說《歸來》的表現方式“像一滴水見太陽”[3],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對“一滴水”和“太陽”之間關系的理解,就像理解影片留下的細節與新時期前30年歷史的關系一樣,需要把細節放到特定的時代和人物的關系中,其意義才可能被感知到。
在處理方式上略顯單調(幾乎都以不完整的形式出現)、出現在不同空間的標語,召喚人們填補它們與社會語境的關系。舞蹈學校排練房間墻上的條幅,工宣隊辦公室走廊墻壁上字體不一、層層疊疊的標語和大字報,雨夜大街上街道主任領著農場同志匆匆行走時后面掛著的條幅,主人公家的春聯,女兒雨夜回來放車子時墻上、樓道口及墻壁、母親趕公交去火車站時道路兩旁墻上、女兒騎車追趕母親時路邊墻壁上、火車站里等各處的標語,時而清楚、時而模糊的廣播聲(起到標語作用)等,填補其中留下的空白,是人們走入1973年的重要媒介,也是理解人物情感和行為動因的重要途徑(當女兒說出其中一部分詞語作為評價父親的依據時,保留它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影片的具體場景顯示了特定時代氛圍與人物行動、情感的關系。舞蹈學校訓練室,舞者整齊劃一的足尖、舞步、眼神,配合音樂等,把時代氛圍具體到了普通青年的精神特征上。把演員所演故事中留下的細節,與影片要講述的母女命運、與1973年故事的最后場景相聯系,滿含淚水演群眾的女兒,主角演員對女兒挑釁的眼光,滿場演員和觀眾的行動,配合并不完整的音樂及舞臺側幕上的標語等,構成了人物與他人、與自身、與時代的特定關系,提供了反思1973年歷史的一個視角。16年前的“老右派”的“逃跑”成為工宣隊領導確定主演名單、判定“罪加一等”的依據;農場同志的嚴厲態度說明“政治立場”的重要性,農場指導員“大義滅親”的勸導、毫不動搖的抓捕行動等,把特定時代的政治氛圍通過具體場景中的人物關系呈現出來。
丈夫歸來的原因,首先有工宣隊人員、妻子、街道主任、舞蹈老師等視角的補充,但他為何處于這一境地,這一留白需要觀眾在人物與時代、與自己、與他人的關系下才能理解。影片減速處理丈夫雨夜歸來時的一系列細節:啃生紅薯、臉孔的顏色、拴在腰間的繩子、轉動門上鎖子的手、肩頭的補丁、磨破膝蓋的褲子等,都意在引發觀眾對人物16年來的經歷與時代的關聯。但作為教授的丈夫,以其勞改16年的人生體驗,不會想不到自己這一行動對妻女的影響,既然抱著“來生”的念頭(1979年丈夫歸來后看到1973年留給妻子的字條時顯示)回家,難道僅僅因為女兒的敵視和妻子的不開門,就放棄了進門的愿望,或者說人物與自己的關系中的矛盾心態是影片要側重展示的部分?或許這些不合理之處也是影片留白策略的又一表現:讀者在“關系”視域下參與解讀和反思歷史的過程就是其處理相關情節的期待。
對丈夫的歸來,妻子和女兒在態度和行動上始終形成一種對照。女兒對父親“階級敵人”的評價,不免使人想象16年來妻子是如何對女兒言說丈夫的。而坐在臥室為女兒擦拭舞鞋的母親,聽到女兒再次評價丈夫時把舞鞋扔到桌子上。從母親的反應來說,她好像是第一次在家里聽女兒對丈夫的這一評價。妻子從箱子里給丈夫拿出被子,聽到敲門聲后走到門前的過程,影片減速處理人物的動作與情感,意在展示其內心的掙扎和矛盾。從父女關系看,老師的視角、決定主演者的堅決,都可以說明女兒在此情境下對待父親的態度的原因。狹窄的樓道里,女兒在驚慌中走向樓口,又退回樓道,上樓梯后又下樓,走向農場指導員,對能跳主角的關注等,顯示了女兒在多重關系下選擇告密的動因和艱難過程。
女兒的這一行動似乎是母親的態度由猶豫到決絕見面的唯一動力(填補這一空白的是雨夜丈夫留給妻子的紙條),也堅定了母親本來出于女兒前途的猶豫,面對農場人員抓捕的危險,她做出了與之前簡直判若兩人的動作,而這些似乎都與妻子16年來的人生經驗無關。但坐在堵住門口的椅子上睡了一夜的19歲女兒,醒來發現身上披著毛巾被,母親怎么走的?這些問題,顯示了影片留白中的疏漏之處。
二、“關系”視域下1979年敘事的留白與歷史書寫
較之1973年的敘事,影片1979年的新時期前歷史書寫中的留白更為含蓄、節制。張藝謀提及影片的主題之一是“重建和追求美好”“更期待‘文革’后的意義”[1]。要實現這一目的,需要讀者填補1979年敘事中留下的細節與時代、人物之間的多重“關系”,才能部分解除之前敘事中夫妻感情鋪墊和積累太少的質疑,“人之常情”的“重建”和“美好”才能在觀眾的填補中實現。
具象化的細節顯示了人物與其對自己生活評價的對比:行動僵直、遲緩的失憶妻子對生活“都好”的評價,與丈夫字條留言中對自己處境的評價、丈夫的信中對生活的認識形成呼應,但后者信中表達春天到來的心情又與1973年留言“來生”之間充滿矛盾。街道主任、女兒等多重視角揭示了6年來妻子的生活狀態以及她與丈夫、方師傅的關系。但方師傅與妻子這一關系的建立,不能不說存在漏洞:既然二者關系始于“前幾年”,也就是說,1973年前方師傅與這一家庭還沒有關系,并且1973年丈夫已經被抓回農場,那么為了丈夫的事妻子為什么“沒少找過”方師傅?失憶的妻子憤怒地與“方師傅”的對話,似乎部分回答了“找過他”的原因,但丈夫與家庭所在地的革委會之間有何關聯?二者關系的這一設置合理嗎?而女兒在1973年時已經19歲了,為什么還說“那時自己還小”?
醫生視角提供了妻子失憶可能的病因,這是對妻子6年來經歷的含蓄而節制的書寫;丈夫標準的法語發音,標志著人物的身份和過往,與丈夫從箱子里拿出的呢子大衣(20年來的勞改一直帶著50年代的衣服?)、妻子對丈夫“教授”身份的記憶(50年代如此年輕的教授應該可能意在說明其成就?)等形成呼應,更與1973年丈夫歸來時的服裝和相關道具的呈現形成對照。夫妻年輕時候好友的丈夫自殺,從另一個角度呼應了1973年敘事的巨大空白。妻子車站接丈夫過程中的一系列動作,實現了其壓抑20年來對丈夫的情感的歸來,影片富有變化地呈現了失憶人物反復進行的這一動作,形象地展示出這份“堅守”“思念”“期盼”[2]及其“歸來”的艱難。
作為醫生提供的治療方法之一,女兒拿來很多本相冊,呈現在觀眾眼中的被剪掉或涂黑的父親頭像等,不能不引發人們對影片處理照片方式的注意。可以說,到父親翻看這些照片鏡頭出現時,影片已是第六次顯示有關畫面。妻子在丈夫1973年歸來時從箱子里往外拿被子,妻子和丈夫(被剪掉頭)的合影清晰地展示在墻上。而從這次呈現相關照片時說明女兒在1973年父親歸來前已經剪掉他的照片,而母親對女兒這一行動似乎也沒有什么不原諒之處。但此時當女兒評價父親是“階級敵人”后母親把舞鞋扔到桌子上,并且女兒告發父親的行為在丈夫1979年歸來前一直未能得到母親的原諒,因此,母親對女兒的態度和行為的合理性可以處理得更有說服力。從這一角度說,對于被剪照片時如何梳理清楚母女關系及其變化,影片其實可以表現得更合情理。
《漁光曲》音樂片斷“早晨太陽里曬漁網,迎面吹來大海風”引發夫妻情感的劇烈反應,引發人們有關夫妻以前的美好生活與現實處境的酸楚的對比。一箱子不同紙質的信件顯示了20多年來丈夫對妻子的深情,從丈夫所處環境與對妻子的情感對照中,從妻子急切讓人讀信的動作中,從妻子20年前對丈夫的意見的順從中,從丈夫歸來后對妻子實現其照顧的諾言中,影片實現了夫妻之情的歸來(這種情感延續至90年代后的畫面,直至影片結束,同時伴隨著《漁光曲》的旋律)。母親對女兒回家的反應(包括行動和語言的重復),是6年來母女關系實際狀態的呈現,丈夫的信件直接引發了妻子與女兒關系的改善,所有這些也構成夫妻情感回歸的襯托。而女兒在家中的舞蹈似乎是其未實現的舞臺夢的歸來,此時她鞠躬的對象已經不再是革命者(1973年敘事中本應屬于女兒的主演的最后動作),而是自己的父母,這也是“人之常情”歸來的另一種呈現方式。
總之,影片《歸來》主要講述了20世紀70年代一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的故事,由此展示了新時期前30年歷史中特定社會里有著“純愛”因素的最小單位的生存狀態,但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中的諸多關系,這一單位之外的那段歷史巨大的復雜性和豐富性等,所有空白都等待觀眾去填補。而由觀眾帶入的“關系”所具有的力量,是影片運用留白策略書寫新時期前30年歷史的希冀,即使有諸多的不合理之處,也可視為其留白策略的另一種表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