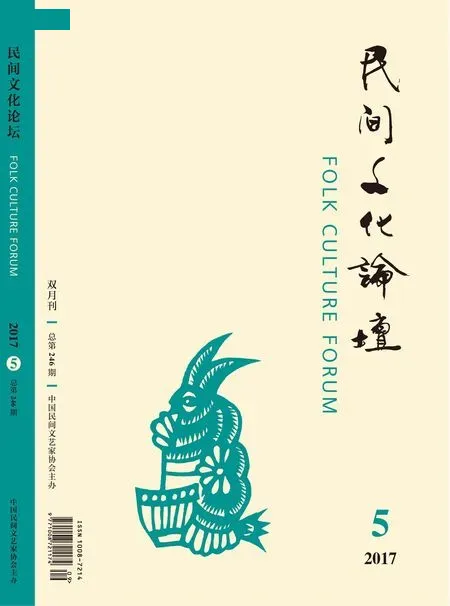都市的認同感
——浴火重生的城市文化
[德]沃爾夫岡?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著 吳秀杰 譯
民俗研究
都市的認同感
——浴火重生的城市文化
[德]沃爾夫岡?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著 吳秀杰 譯
城市的興起是工業化、現代化的伴生現象;大量人口密集居住的大都市生活造成的環境惡化、人際關系疏離、犯罪與暴力頻發等問題,使得都市成為20世紀現代性批判的靶子,逃離都市一度成為現代人向往的生活方式。20世紀70年代以后,都市文化被重新發現和塑造,再度煥發出多樣性、包容性、具有多重文化品位的魅力。在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都市在打造自我身份認同中再度成為宜居之地,為外來者的社會融合和身份認同形成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本文勾勒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城市文化變遷的進程:從單調平庸的灰色水泥林,到五彩繽紛的各種社會與文化理念的實驗場。
都市文化;身份認同;移民;社會融合;社會實驗場
這件“I love New York”紅心T恤衫成了一個象征性的宣言,傾訴了人們對一個城市的熱愛。它原本敘述了另外一段完全不同的歷史,一段慢慢被遺忘的歷史。1972年,當一個藝術家小組設計出這個T恤衫時,紐約這個大城市遠遠不像今天這樣為億萬人所傾慕。它似乎要宣告自己的末日降臨:交通堵塞、霧霾、投機和犯罪橫行,城市人口在減少。那一句“我愛紐約”是當時尚且留在城市里的人發出的最后求救呼聲:“讓我們別拋棄這座城市!”

圖1 “我愛紐約”T恤衫(攝影 Wolfgang Kaschuba)
我愛……我們!
不過這早已是陳年舊事。如我們今天所見,紐約這樣的大都會理所當然地被看作充滿多樣性的文化空間、消費空間和感受空間。令人難以忘懷的歷史景觀和建筑景觀遍布城市各處,了不起的技術裝備與旅游業基礎設施,令人嘆為觀止的藝術和文化活動。它們為不同人群所居住、所使用,這其中有當地人、外來移民、流動人員、旅游者。獨有的自我意識與別具一格的精神風貌塑造了這個城市,文化多樣性和社會整合讓它變成了世界之都,變成了某種標記。這種獨一無二性給紐約人帶來一種身份認同;同時,它又反過來迫使紐約人持續性地擴建城市,從基礎設施到文化,從娛樂活動到娛樂價值,以便能讓自身具有國際競爭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也要求城市不得不適應全球趨勢,其代價是建筑學上的標準化和文化上的同一化。城市競爭越來越帶來自我摧毀的效應。
這一發展模式早已遍地開花,哪怕在中等都市也是如此,連老城區也經常讓人覺得是可以替代的、毫無特色。隨之而來的是,對于公司、媒體、旅游者以及當地人來說與地點有重要關聯意義的地方認同感陷入危險之中,即那些特殊的體驗和設想:在柏林生活會有別于在慕尼黑或者博登湖畔的康斯坦茨,因為各地的歷史、建筑、風光、精神風貌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
因此,今天的城市推廣計劃才如此集中而深入地考慮這一問題:如何讓城市最終變得不能被錯認,什么是它的特殊風格、它的特殊顏色,以及它獨此一家的標志。在晚現代時期以及在全球背景下,這些就顯得尤為有價值:強調和維護那些真正刻寫在該城市中的個性特征,讓居民感受到這是“地方精魂”,由此出現一種都市的“我們”認同感。
這些為形成地方性認同感和定位的努力,在最近一些年當中發展成為一種真正的城市特征。這是一種文化“地標”,城市推廣活動和文化專欄是其推手,它們也出現在旅游手冊和互聯網博客中,也通過電視系列劇和城市流行歌曲、通過圖片相冊和導游傳播出去。城市被當作集體性的行動主體,成為地方性共同體和文化,它們的居民變成了同樣的“生于斯長于斯”的本地人,成為都市部落中的一員:他們從先前廣袤的都市獵場回撤到隱蔽的保留地,以便能躲開房地產大鱷和建筑修復,躲開追名逐利之徒以及旅游者。人們要形成一個“自己的”和“他人的”世界,移民風格也好,巴伐利亞風格也好,只是為了再度贏得距離和安靜。可惜這經常徒勞無益,因為正是這種回撤到“獨特方式”的街區和居住區,讓觀光者和投資者變得更為好奇,因為這種氛圍讓這些當地人具有都市本真性以及亞文化的殊異性。這些做法讓當地人不情愿地掉進了旅游-經濟犧牲品的模板中:文化很容易帶來自食其果的效應。
赫爾曼廣場——柏林
柏林有一個赫爾曼廣場(Hermannplatz)。直到不久以前,這并不能讓人感到有什么可激動的。其他德國城市也有同樣的地名來紀念不同的“赫爾曼”,有的是榮譽市民,有的是市長,或者是日耳曼部落的首領。柏林赫爾曼廣場的存在開始于1885年,那還是有皇帝的第二帝國時代,紀念的是那位舍魯克人或者日耳曼人,他原本是一位德意志-意大利移民,在羅馬名叫阿米尼烏斯,在那里被訓練成士兵。直到他似乎對毫無愛意的意大利歡迎文化感到失望,又再度移居到日耳曼,剛好在兩千零五年以前,在離奧斯納布魯克不遠的沼澤地中將羅馬軍團連同他們的統帥瓦魯斯打得一敗涂地(即通俗說法中日耳曼部落擊敗羅馬軍團的“條頓堡森林之役”)。不過,赫爾曼廣場今天引起關注并非由于這一歷史背景;更多是因為一件T恤衫,上面印著漂亮的字母“你害怕赫爾曼廣場”。這件T恤衫連同同名的互聯網博客反映了這一廣場的特殊象征意義,展示的是“新”柏林的社會地貌和文化地貌。它正好位于草根多元藝術文化的舊重心“十字山”(Kreuzberg)與新重心“十字科爾恩”(Kreuzk?lln)地帶的交界點,是通向熱點社會問題區“新科爾恩區”(Neuk?lln)的過渡地帶。在20世紀20年代,這里還是都市現代性的核心地點:當時歐洲最現代的百貨大樓Karstadt坐落在這里,這里是地鐵和公交車的換乘站,貧民區和城市區的交匯地。直到今天,這個廣場的外貌雖然保持著都市特征,不過標記的是另外的內容:這是一個由失業者、移民、毒販子和涂鴉者構成的社會問題焦點地區。在這件T恤衫上,這些特征都被反映出來了:這是一個經典的“危險地點”的圖標和象征,是大都市中那些不要去的地方之一。在依靠媒體化和奇異化存活的柏林“感受圖景”中設定一個這樣的“險地”,便是利用這一地點的傳統并使其變為一種帶有挑釁性的、自我感覺良好的游戲。
這樣一來,一句“你害怕赫爾曼廣場”也帶有雙重含義:這是一種傲慢的挑戰,也是向前往這些地區的人如旅游者以及新老柏林人發出的邀約。與之相隨的隱含文本在說:“本色的”“真實的”城市,活在這些草根多元文化的街區,活在街區的共同體當中,他們將自己及其藝術、音樂和生活格調看作是特別的、先鋒的:就是要與其他人的不一樣。
同時,與新都市性的關聯也就此產生出來。在新都市性中,似乎什么都能被變成文化,也就是說一切都足以、也有意愿被用于展示文化闡釋,其象征性會被提升。在這種關聯背景下,文化上的價值提升同時也能經濟化和高端化:空間和地點、地產和房租、格調和特色都連在一起。考慮到文化效應與經濟效應這種既富有創意、又不乏風險的共舞,今天的大城市——具有不同的空間政治和空間主體——正可以提供一個完美的實驗室,來進行那些意圖明確的或者“無心插柳”的高端化試驗。“你害怕赫爾曼廣場”本身就是最好的例子:這個圖標的知識產權屬于當地的一家完全商業化經營的廣告公司。
文化化——都市
柏林的這一例子要說明的是,調停自我認知與他人認知中的形象、平衡多側面展示與刻意而為的奇異化圖景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對話過程,而這一過程在今天打造“城市標識”與“社區建設”中都不可小覷。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城市背景下“品牌”與“市場”的交互作用是多么緊密:這里指涉到城市中心的住宅和空間以及人們害怕其高端化。在很多城市,這早已經是頭號的日常話題,因為城市中心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對居住者和投資者都是如此。他們都在意、也都力圖打造“都市認同感”:展演都市的個性與共性,讓都市生活世界中的經濟威脅和社會威脅成為話題。

圖2“我愛紐約”T恤衫(攝影 Wolfgang Kaschuba)
盡管有這樣的模棱兩可性,城市空間重獲社會質量和文化質量這一事實,使得今天的城市,尤其是市中心又成為整個社會的渴求之地。在1900年,馬克斯?韋伯已經在最初的現代城市當中看到,人們充滿渴望地感受到自由空氣在城市中吹拂,生活格調的多樣性以及生活方式的開放性讓人興奮得目不暇接。今天似乎我們又可以有類似的感知,我們的城市中心不再是一個純功能性的工作與交通世界,即經典的由工業生產和消費組成的“福特式”地點。我們也從中看到生活世界的空間在日益增加,這要求城市有特別的文化質量,能夠對當地人和旅游者、對老年人和年輕人、對單身者和家庭都同樣有吸引力;對于那些新的生活方式——有生態或者能源、道德或者享樂的特定取向——都有發展空間。
在我們今天的渴望與馬克斯?韋伯的渴望之間,是一段長長的城市危機時代。尤其是在1939年和1945年以后,城市因為戰爭的后果、汽車交通、鋼筋水泥的現代建筑以及快速發展變成了那種“類屬城市”(generic city),這是荷蘭建筑學家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ss)自20世紀70年代就激烈抨擊的:城市變成了沒有生活質量和都市魅力的疲乏之地。庫哈斯呼應了亞歷山大?米切利西(Alexander Mitscherlich)斷言的“城市的不適合人居性”的畫面,他在此前十年將這一現象診斷為都市的單調性、社會匿名性以及愈演愈烈的逃離城市行動。1972年的德國城市聯席會議發出了這樣的呼吁:“救救我們的城市——現在!”“我愛紐約”的T恤衫也在同一年出現,這絕非巧合。
在城市經歷著深度的國際性危機之時,有一些來自國家的和地方上的反向計劃出臺,開始將城市發展和城市規劃作為主動的、系統性的“文化化”來推動,作為有目標的文化上細胞再生舉措。這些舉措首先“來自上面”、經由城市發展政策而啟動。法蘭克福的文化負責人希爾瑪?霍夫曼(Hilmar Hoffmann)提出的“給所有人的文化”這一口號變成了都市戰斗號角。這在七十年代首先是一個城市文化“節慶化”的理念,其方式是要長期地設立音樂周、戲劇周,設立文學節、電影節,設立青少年之家以及文化中心。在八十年代接踵而至的是城市文化“機構化”,其方式是上千個博物館和藝術場館,老城的修復和重建。在九十年代,還增添了將城市文化項目“盛舉化”:完備地舉辦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從大型古典音樂會和通俗音樂會,到藝術展覽以及街頭游行,這些“盛舉”與國際性城市旅游熱與都市形象政策結合在一起,讓城市觀光客的數量迅速推升。

圖3 奧斯陸的歌劇院,2014(攝影 Wolfgang Kaschuba)

圖4 被包裝起來的柏林國會大廈(攝影 Wolfgang Kaschuba)
在最近的十年,市中心地帶則出現了不折不扣的“地中海化”:系統性地讓棕櫚樹和沙灘出現在城市中,城市沙灘、街頭咖啡館、躺椅、吊床、實況轉播場所、晚會舉辦地等設施讓城市的一部分慢慢地成為露天舞臺和度假地。許多人雖然在話語中不無自我解嘲的意味,卻帶著極大的樂趣加入到這一新的都市表演中:這出戲叫作“現在我們來表演蔚藍海岸(里維埃拉)!”盡管高緯度的地理位置以及比較低的氣溫,人們依然樂此不疲,必要時也可以用上通過公平貿易渠道購置來的毯子(柏林)或者不那么環保的電暖器(巴黎)。
公民社會——烏托邦
與“自上而下”的城市改造并行不悖,自20世紀70年代也開始出現了一種“自下而上”的文化都市化。都市項目和公民運動經由新的社會網絡和政治活動而出現,人們占據城市空間、重整其原有的形式、賦予這些空間以新含義和新功能。一種遍及全球的“城市性”(citiness)從中脫穎而出:這是一種普適性的城市知識,它將新的都市生活格調與新“烏托邦”連接在一起,其組織方式是通過互聯網或者街頭,在這里聚樂晚會與政治的界線似乎終于被抹去了。我們的城市風景終于不再讓人感到如庫哈斯斷言的那樣毫無生氣,相反是活生生的、有魔力的。至少對于那些有意在文化上發掘城市世界這一充滿魔力的一面、并且也有充足財力的居民和觀光者來說,的確如此。在這兩個群體當中有這種愿望和能力的人,其比例如今都在快速增長。

圖5 柏聯邦總理府旁的沙灘,2013(攝影 Wolfgang Kaschuba)
都市空間作為文化實驗場的功能并非全新現象,而是有著悠久的歷史。若干世紀以來,歐洲城市的發展主要靠人口流動和移民,也就是說,人、理念、物品、價值的移入和交換。在跨入現代社會的進程中,城市終于變成了“移民”地,成為社會相遇的空間,成為文化混合的區域。城市、流動性、外來因素在歷史發展中彼此間的關聯作用,已經成為馬克斯?韋伯和格奧格?西美爾(Georg Simmel,1858-1918)思考的核心問題。尤其是西美爾曾經指出,要將外來者作為核心性的都市主體:與觀光者不同的是,他們今天來到城市,明天還會留在這里;在很多方面,明天他們也還會是“外來的”,不會走進當地人的世界、讓自己入鄉隨俗;他們也會不遺余力地嘗試著將自己的“不一樣”變成當地生活的一部分,其形式也可能是堅決不入鄉隨俗。我們慢慢地知道,這種情況似乎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流動性和移民是城市的系統性外在關聯因素,這在歷史上已經體現為兩種都市認同感:地方性的、容納性的城區傳統,以及同時存在的開放都市性,其根基在于城市社會異質性。這兩種動力讓城市的社會組合出現永久性的張力,這也給城市文化帶來特殊資本:社會差異與文化上的多樣性,給人們對于傳統與創新、順應與沖突、融入與隔斷的經驗帶來了富有產出性的諸多層面。
當下城市文化和城市社會的建設正是基于這一歷史資本,大城市變成了晚現代時期的某種特殊偶像,日益增多地匯集了開放的文化紋理以及通行的象征含義。這些具有偶像性質的晚現代世界大都會如紐約、巴黎、倫敦、北京、甚至也包括柏林,為許多二線、三線的城市所抄襲、所模仿,它們也嘗試將自己的市中心“都會化”“文化化”為某種有遠大抱負的新形式,其目的在于產生認同感效果,以利于造成形成共同體的社會效果。這種行動策略顯示出,在(德國的小城市)埃森或者巴登-巴登也不乏大都會的做法:舉辦大型的通俗文化活動、突兀的建筑物、將街區歷史化與展示化、都市海灘和都市花園。所有這些活動也許型號小一些、花費低廉些、更費力些,然而它們帶來的情感作用、在凝聚集體感以及提升認同感上的作用卻一點也不少。
無論如何,這一趨勢映射了全球文化交流的發展歷程。早在20世紀80年代,隨著城市文化國際化的日漸增加,當人員流動、移民、旅游業顯示出的可持續性交流效果已經初步凸顯出來時,國際性文化交流便開始了。如今,互聯網帶來的可能性又步入全球文化交流行列當中,并成為一個具有顛覆性的角色。認知與想象——開發城市文化有賴于此——有了全新的交流模式,這讓我們的時空坐標發生了極端改變。似乎一切都是無限的,幾乎都可以同時派上用場。“真正”生活在紐約或者巴黎,并不意味著能比在埃森和巴登-巴登能得到更多信息和知識,盡管在參與“本地的”活動和獲得本真性方面還仍然有一些小小的優勢。
實驗場——城市
都市空間、圖像以及網絡的全球化讓想象力提升,藝術和生活格調從中大為受益,因為城市空間越發強烈地被視為“公共”空間,一種誰都可以進入、可以當成舞臺來設置的社會試驗場地:街道被用作項目實驗室,城市廣場作為展示生活格調的舞臺,房屋的外墻作為藝術畫廊,餐館作為品嘗和烹飪的廚房。從中受益最大的是近年來發展起來的那種新“都市主義”——它經由不同的公民社會活動形式在我們的城市中迅速地傳播和形成,比如上千個獨立城市規劃倡議與租戶倡議,都市園藝和共有田園小組,維護學校與公園的活動,街區協會與跨文化溝通協會,環境與生態博客,圓桌聚會和社交聚餐,從南到北到處都有這樣的活動,給我們的城市以一種讓人“走進”的新方式。同時也有一些不怎么受歡迎的活動,比如針對難民居住區、建造清真寺和旅游者的敵意活動。“公民社會”成為一個越來越開放的概念,幾乎城市里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歸類到這個概念之下。另一方面,我們也能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在這一標簽下有很多私人利益,包括對外來者的敵意,被標榜成公共利益。這些也是我們在當下的都市生活世界中需要觀察和了解的內容。

圖6 城市街頭涂鴉中的觀光客形象,柏林,2013(攝影 Wolfgang Kaschuba)
盡管如此,城市文化發展帶來的后果肯定是利大于弊。原因在于,城市居民運動的討論、展示、反思、組織和設計,其所有形式和實踐都在重新磋商都市認同感設想和歸屬感,帶有高度的象征精準性和確證質性;城市的主體在這里展演自己,同時他們也把城市展演為主體。某些展演有著競爭性的、沖突性的形式,許多展演采取的形式是理念、價值觀和行動計劃,其中有些是普遍共有的,有些則是某些共同體所共有的:在不同的政治陣營與宗教教區之間,不同的族群與性別之間,在年輕人與老年人之間,在當地人與外地人之間。實際上,城市文化在運行“卓有成效的”社會融合政治和身份認同政治。
今天,我們的“公民”城市社會在精神上與政治上的更生實際上是都市“文化革命”。在戰后的危機時代之后,城市社會和城市文化首先如鳳凰一樣從灰燼中一躍而起,為自己創造了新的主導形象、文化世界和生活格調。如今它們將“大城市”這緊張的功能世界逐漸轉換成“城中心”這樣有吸引力的生活世界。在德國城市的市場廣場,人們露天坐在午后的陽光下,在大庭廣眾之下放松地喝上一杯意大利拿鐵瑪琪雅朵咖啡或者來一份威尼斯阿佩羅開胃雞尾酒,盡管在口味上未必如人意,但是在精神上的享受感卻是確鑿無疑的——這樣的情形簡直可以說是一種革命了。
市中心的開放氛圍以及城市對外敞開心扉的姿態,使得城市以一種新方式成為社會認同政治的核心資源。我們日益將自身、自我圖像、訴求、愿景和希望與城市的生活世界、空間、設施和形象關聯在一起。城市是社會發展的實驗場,也是展示文化意義上生活格調的舞臺:在行使這雙重功能的同時,在過去幾年和幾十年的公民社會更生中,城市也日漸贏得能給人帶來認同感的新面孔。當然,這一切也讓我們的城市感到不堪重負,因為我們想要從中獲得一切可能有的東西:要安全,也要冒險;要共同體也要多樣性;要聚會也要安寧;要消遣也要免費。這一切最好同時都有,而且最好在拐個彎就能到的地方;反正一切都要與我們近在咫尺觸手可及,同時還要遠得喧鬧之聲不會入耳。
城市要滿足所有這些訴求,這肯定不容易。不過,我們已經從城市生活以及城市發展中明白了一點:城市成為實驗場和舞臺,要比成為停車場和墓地好多了!
K890
A
1008-7214(2017)05-0071-07
沃爾夫岡?卡舒巴 (Wolfgang Kaschuba),曾任柏林洪堡大學歐洲民族學研究所教授、所長,自2015年起,擔任柏林社會融入與移民問題實證研究所(Berliner Instituts für empirische Integrationsund Migrationsforschung,簡稱BIM)所長。
[譯者簡介] 吳秀杰,德國馬普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研究人員,自由譯者。
[責任編輯:王素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