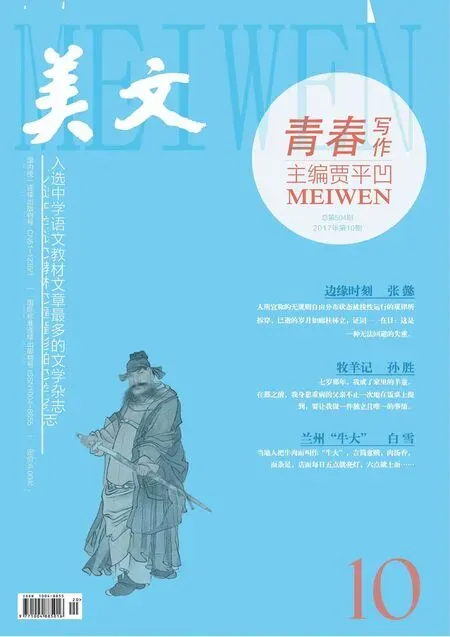蘭州“牛大”
白雪
蘭州“牛大”
白雪
也是在去年的五月,我正式告別了自己生活了四年的地方。
有時(shí)候不是我們選擇了城市,而是城市選擇了我們。蘭州第一次擁我入懷的時(shí)候,我還抗拒地想要推開(kāi)他。之前于我而言,蘭州不過(guò)是全國(guó)出了名的污染重地,還未踏足,就能想象得到漫天的陰霾和粗曠的空氣,甚至臨下車(chē)前,也不愿意抬頭望一眼天,只覺(jué)得在嚼舌頭難以聽(tīng)懂的方言之中行的舉步維艱。要不是為了完成學(xué)業(yè),我根本不會(huì)來(lái)到這樣的地方,身上承載的,也不過(guò)是別人的夢(mèng)想罷了。
起初,就連早餐,也是別人的選擇。按地理方位來(lái)說(shuō),學(xué)校處于北邊,位于方圓200米內(nèi)的東、西邊各有一家牛肉面店,南邊有兩家,就像食指和中指一樣緊緊挨著,卻從沒(méi)耽誤過(guò)生意,每家的生意都十分火爆。各家的牛肉面有各自獨(dú)特的秘方,成千上萬(wàn)家牛肉面店,有成千上萬(wàn)個(gè)獨(dú)特的配方,就如指紋一樣,是自家獨(dú)具的招牌,也靠此籠絡(luò)了很多相對(duì)固定的面客。當(dāng)?shù)厝税雅H饷娼凶鳌芭4蟆保院?jiǎn)意賅,肉湯香,面條足,店面每日五點(diǎn)就亮燈,六點(diǎn)就上面,人們?cè)谇宄砍鲎撸徽撘マk怎樣的大事或小事,多半都是從那醇厚濃郁的“頭鍋”牛大開(kāi)始的,出入在大街小巷的牛肉面店中,人們白臉進(jìn)紅臉出,火紅的辣子提起了一天的精神氣。直到中午一兩點(diǎn),伙計(jì)們準(zhǔn)備的面食全部告罄時(shí),才能迎來(lái)一時(shí)半會(huì)的疏通空氣。沒(méi)有冬旺夏淡季之分,牛肉面總是一個(gè)純粹的蘭州人的首選。我被身為本地人的舍友強(qiáng)迫著,終于還是踏上了漫漫追面的征途,從半碗面半碗湯的容量到一碗大“三細(xì)”加蛋夾肉加小菜的標(biāo)配,也不過(guò)僅僅兩月的光景。吃面總是匆忙的,等座的新客往自己旁邊一站,便沒(méi)有了舒坦享受的心思,仿佛自己浪費(fèi)的,不僅是自己的時(shí)間,經(jīng)常是滾燙地送入口中,又匆匆地飲湯而去,面客們?yōu)橥煌朊娑鴣?lái),奔向精彩或復(fù)雜的人生。
聽(tīng)聞曾有一位牛肉面館老板,想要把分店開(kāi)到上海去,花了重金請(qǐng)了資質(zhì)最老,手藝精湛的老師傅。整整籌備了半年,終于等到開(kāi)業(yè)迎客的這一天。剛開(kāi)業(yè)來(lái),顧客們都聞名而來(lái),生意自然是紅火,可老板中懷揣著一個(gè)只有行家才能意識(shí)到的憂慮,那就是這牛肉老湯,怎么都熬不出原來(lái)的味道。實(shí)驗(yàn)了百八十回,實(shí)在不知道是哪個(gè)環(huán)節(jié)出了問(wèn)題,索性將食材都從蘭州運(yùn)來(lái),牛肉、蘿卜、蒜苗、大料甚至辣椒,一樣不落。又試驗(yàn)了百八十回,依然與傳統(tǒng)正宗的味道差那么一點(diǎn)。老板祖上就是靠牛肉面發(fā)家,傳到他這,已經(jīng)是第三代,這煮湯拉面的手藝都是一絕,要求苛刻,趨于完美,不能容忍一星半點(diǎn)的瑕疵。最后,終于用一桶風(fēng)雨兼程從蘭州運(yùn)來(lái)的清水,揭開(kāi)了困惑許久的的謎底。原來(lái)蘭州的味道,原原本本的只能屬于蘭州,哪怕是做湯要用的水。時(shí)日不長(zhǎng),牛肉面過(guò)了新鮮的勁,似乎難以在上海人心中占領(lǐng)一席之地,加上長(zhǎng)途運(yùn)輸原料的花費(fèi)使得經(jīng)濟(jì)流通入不敷出,它就如過(guò)客一般,隱隱于市,退回故鄉(xiāng)。
為了改善當(dāng)?shù)氐目諝猸h(huán)境,政府是下了大工夫的。從清早到夜晚,抑塵灑水車(chē)總是不間斷的工作著。在吃一碗牛大的工夫,就已經(jīng)有兩三輛車(chē)嘀嘀吧吧響著音樂(lè),緩緩從眼前駛過(guò),留下從天而降的水滴和一層又一層的濕氣。因?yàn)橐?guī)劃修地鐵,公路變得更加狹窄,顛簸的讓人頭暈。據(jù)說(shuō)有一條地鐵線,是要從黃河地下挖過(guò)去的,想想都是偉大的工程。有時(shí)候會(huì)閑逛一整天。意料之外的是,街道被陽(yáng)光充滿(mǎn)的時(shí)候,都很溫暖,沒(méi)有太陽(yáng)的時(shí)候,空氣也沒(méi)有厚重的顆粒感,頂多是摻著些黃土罷了。許多事物,并不是你聽(tīng)到的別人口中的樣子。
蘭州吃行兩件寶,是誰(shuí)都挖不去的。第一件關(guān)于吃的,理所當(dāng)然的就是“牛大”,走在街上,即使原本計(jì)劃好了午餐,也會(huì)無(wú)端端被遍布空氣中牛肉面的香氣吸引了去,第二件關(guān)于行的,便這條霸道地把本就是東西走向的蘭州城又沿著東西走向劈成兩半的黃河水,獨(dú)特的地質(zhì)構(gòu)造讓兩岸的公路腰身更加纖細(xì),難免阻礙交通。蘭州沒(méi)有很多標(biāo)志性的建筑,但橫跨與黃河之上的橋梁卻不少,不論要去哪里,不過(guò)就是從這座大橋上來(lái),或是從那座大橋上去。小有名氣的有七里河黃河大橋、雁灘黃河大橋、城關(guān)黃河大橋,分別位于蘭州最繁華的三個(gè)區(qū),緊緊地?fù)е@蜿蜿蜒蜒的黃河水,這滔滔不盡向東流的黃河水。但凡給點(diǎn)光,黃河水就泛著星星點(diǎn)點(diǎn),尤其是夕陽(yáng)西下,太陽(yáng)剛剛掛在山頭,就閃耀的極為出彩。不知道這涌動(dòng)的淺浪里藏了多少金子,稍一翻身,就讓人忍不住去撈一把仔細(xì)探查。我總是站在中山橋上向西望,望著穿過(guò)這一條悠然的峽谷的金光,幻想著守護(hù)這一方水土的山神和土地,或者大鬧黃河的鬼怪,直到天黑。之所以鐘愛(ài)中山橋,不僅是因?yàn)橹猩綐虻拿麣猓奂饲皝?lái)參觀的游客和閑適散步的居民,最主要的,是能享受全城最撩人的夜景。站在橋上望,不覺(jué)就有了詩(shī)人的情懷。白塔山上的屋翎亮起來(lái)了,泊在對(duì)岸邊的客船亮起來(lái)了,中山橋的棱角也亮起來(lái)了,五顏六色交相輝映,坦露在黃河的倒影中,水動(dòng)影不動(dòng),很難想象粗狂的黃河水也有這般溫柔的時(shí)刻。即使已經(jīng)這么明亮,依然能逢上恰時(shí),絲毫沒(méi)有影響天邊群星捧的一輪月,不枉此景,亦不枉期盼。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時(shí)光、水波都不停地流動(dòng)著,他們帶走的事物,不止意味著喜,也不止意味著悲。隨后,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卻已被歲月化成了蘭州城中的一支獨(dú)白,舍不得離開(kāi)。
對(duì)于一座已經(jīng)化為他鄉(xiāng)的城,追懷起來(lái),總要想到他的好處;隨后再慢慢地想起起初踏入這里的埋怨和不滿(mǎn),所有的好處壞處,都變成了耐人尋味的紀(jì)念,更是對(duì)再見(jiàn)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