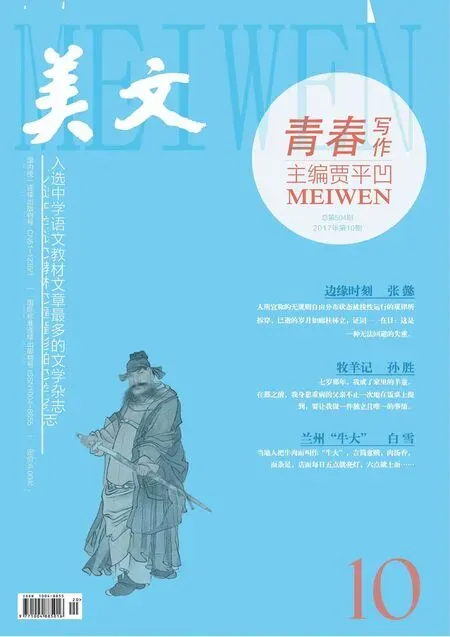食 味
柴新越
食 味
柴新越
人生冷暖,無非火鍋與酒
過了大雪節氣,天氣驟然變冷。尤其是下過一場鵝毛大雪,便分外想念吃一頓熱氣騰騰的火鍋。
入冬的北方,雪夜茫茫。若不是約了三五好友,若不是沖著火鍋,確實很少有出門的理由。
披厚衣、裹圍巾,踩著薄冰一路晃悠,深一腳淺一腳地穿過一條小巷,摸到一個熟悉的館子里。推門進去,寒風打著旋兒吹了進來,又被擋在了門外。一桌桌人大汗淋漓,大勺大碗大瓢正嘩啦啦地吃著。
汩汩滾開的火鍋里,肥牛肥羊舒展著身體,撒尿牛丸熱情地翻滾,黃喉毛肚唱起滾燙的情歌,鴨血鴨腸辣手摧花,菠菜茼蒿洗著一場酣暢淋漓的熱水澡。此時,若不圍爐涮鍋、詩酒趁年華,怎對得起這熱氣騰騰的冬夜?
朋友舉手招呼,落座,不等寒暄幾句,搶筷子夾羊肉下鍋燙,不等涼透趕緊進嘴,舌頭一燙,嘴里趕緊“吱吱”地喘息幾聲。推杯換盞,緊著涮緊著吃,手舞足蹈忙得一身汗。等吃完了,面色紅潤,渾身通透,胸襟開闊。
待到酒飽飯足,和圍爐的朋友一頭鉆進大雪里,嘴角隱約火氣繚繞,還不忘喊一聲:好雪。
那天,在網上看到一篇關于“火鍋”的文章,文字很平淡,只有最樸素的食材和味道的介紹。看完無感。其實,火鍋最像是人生,你很難在另外一種飲食中,找到愛恨情仇的全部交織。懂得了火鍋,就懂得這不再是一頓美食,而是一種情感,一種治愈。
就像夏日的一瓶啤酒,秋夜的一場燒烤。食物從來是撫慰人心的一劑良藥。
一人食的冬夜,眼淚在眼眶里打著轉兒。嗯,一定是,底料太辣了。
一個人端坐桌前,攪動著一個小火鍋。鍋周圍擺了白菜、土豆、豆皮、菠菜,還有半盤肥牛。呵,一盤對我來說,可是一場奢侈。一股腦兒將菜都倒了進去,心里憤怒地喊著:全都進去吧,全都進去吧,所有的不如意,都放馬過來吧,既然逃不掉,就連鍋一起端上桌。
有水有食材,有鍋有筷子,眼淚打著轉兒,嘴角卻倔強地揚起一道弧線。我記得那個冬夜,推開小飯館的木門,我對自己說,不準哭。過了好多年,無論生活扔給我什么樣的不如意,我照單全收,沒有掉過一滴淚。
昨天,我的媽媽說我,倔強得要命。仔細想一想,還真是這樣。
愛的人,就像火鍋里的涮肉,火候,要拿捏好。
吃火鍋,脾氣慢是不行的,急性子也不成。這和品茶、喝酒、下棋一樣,要懂得掌握好火候。脾氣慢的人往往會等到食材煮爛了,急性子的會嘩啦啦一盤底朝天地倒進鍋里。而燙菜涮肉時,火候更為重要。火候不夠,涮肉爛熟不透;火候太過,又會使肉的鮮味頓失。
在重慶吃火鍋時,店小二說,涮毛肚講究個“七上八下”,黃喉最多十下,牛百葉煮兩分鐘,海帶、冬瓜和尖筍要煮五分鐘。
我有個朋友,連食材燙多久都精確到秒,肉怎么涮才好吃,黃喉燙多少秒才有味道,分寸拿捏得極為到位。比如說起涮羊肉,他說在沸騰的清湯里滾兩下,外圈蜷縮泛白,內里還微微粉嫩時,入口,味道最鮮嫩。
這和愛情一個道理,愛情能否圓滿,就看火候和分寸的拿捏。
明知道是錯的,偏偏任性得要命,就像嘴皮都要辣翻,依然不肯停手。
年少時,和父親母親坐了一夜的火車,來到北京。第一次走出故鄉的小城市,第一次吃到炭銅火鍋,雖然最后頭暈目眩,有點兒中毒的征兆,但是不顧一切去遠方的念頭還是在心底扎了根。
和家人吵過、鬧過,任性地選擇遠方的城市、任性地選擇友情、任性地亂發脾氣,有時候明明知道自己錯了,還是不肯低頭。
深夜和朋友在街頭小館吃著火鍋,牛肉片被密密麻麻地裹上厚厚的一層辣椒,看著就讓人望而卻步,經過幾個回合后,還是沒能抵住誘惑,嘗了一片,灼熱的感覺停在嘴唇上,嘴里都是火辣辣的感覺。
舌頭比頭腦念舊,胃口比心忠誠,鍋里的食材熱熱鬧鬧,桌旁的親人說說笑笑。
小時候吃火鍋,沒有北京的大銅鍋,沒有重慶的九宮格,就是最簡陋的一張圓桌,一個電磁爐,一口鍋。
羊肉是必不可少的,然后是各種丸子,土豆和圓白菜是最常見的配菜,再泡一捆粉絲,抽一把掛面,然后就像過節一樣,轟轟烈烈地涮一頓羊肉。
醬料就是普通的麻醬,配著韭菜花和豆腐乳,還少不了炸些辣椒油。沒有海鮮醬、沒有沙茶醬、沒有牛肉醬。我最討厭麻醬那種濃稠的感覺,所以父親給我調上一大碗,我也只吃韭菜花和豆腐乳。
鍋底是最沒有看頭的。切上幾段蔥、生姜片,放上幾顆花椒大料,就成了。小時候只有幾種肉類,肥牛肥羊,去了不同的城市才知道,原來還有黃喉、撒尿牛丸、蝦滑、魚滑。鍋底也講究了起來。
待一切就緒,注入熱水,等開鍋。此時的等待最是難熬。不解風情的熱水,才不管饑腸轆轆的我們,不緊不慢地變熱,平靜的水面下開始上浮一串串的氣泡,水面的波瀾越來越洶涌,等到父親說一句“水開了”,肉嘩啦啦全都倒了進去,像是把一家人的歡聲笑語,統統倒入熱氣逼人的漩渦中。
那種滋滋冒泡的幸福感,就像一把溫柔的利刃,無論闖蕩生活,披上多么沉重的鎧甲,一筷子豐腴的羊肉,蘸上麻醬,都能戳中你幸福的軟肋。
家常與家
01
和朋友聊起最愛吃的菜。
絞盡腦汁想了大半天,憋出四個字:炒土豆絲。朋友不解,說這是很普通的一道菜啊。的確,這道菜沒有豬牛羊肉的鮮美、沒有紅燒、清燉、烹炸的百般滋味;缺少了南方菜系的精致,更少了西北菜的豪邁。但是它是我記憶里家鄉的味道,是母親的手藝。
小時候我特別挑食。不愛吃肉,尤其是肥肉。有幾次母親包餃子,放了很少的肥肉絲兒,都被我察覺到,哪怕嚼爛了即將下肚,也會吐出來。豬肘子白花花的油膩、羊腿上成塊成絲的膻味兒,都讓我厭惡。
很少吃青菜。芹菜有股怪怪的味道,茄子太軟潤,看起來像肥肉;白菜一年到頭吃不停,尤其是冬天,炒白菜、燉白菜,都要讓我反胃。
為此,母親沒少操心。母親總是變著花樣做好吃的,哪怕色、香、味俱全,也很難讓我垂涎三尺。后來母親給我炒了一盤土豆絲,放了一點點的辣椒,帶著點酸爽和微辣的味道,讓人胃口大開。
很長一段時間,母親都給我開小灶。
晚上給家人炒菜的間隙,母親會先給我炒上一盤土豆絲。就著米飯,狼吞虎咽地吃完了菜,甚至都會把湯喝掉,才會去寫作業。
02
老家除了疙瘩這道主食,還有一種食物,叫做大餅。放在爐里烤得金黃。剛出爐的大餅外酥里嫩,底兒、蓋兒、芯兒層層分離。
外層薄而且香脆,中間又很酥,軟軟的,帶著熱氣騰騰的面的香味兒。咬一口慢慢咀嚼,香味兒便溢滿口腔!
其實,大餅搭配炒土豆絲,非常普通。但是冬夜里要喝一碗羊湯,可真的是絕了。
有多少城市,就有多少種羊湯的味道。羊湯分紅、清、白三種顏色。老家的羊湯以白湯為主,盛到小碗的羊湯奶白色,不稠不凝,沒有油沫兒,羊肉、羊肚、羊雜碎都能入肚。尤其是切得極為精細的羊肉,吃多少,嘴中都不會殘留腥膻的雜味異味兒。
一碗羊湯,一個白餅子,胃的舒服很難用文字來表達。
因著朋友的一句話,想起一道菜,便想起幾件看似不相干,卻又能夠聯系在一起的食物,這時候才知道,原來每天能夠回家吃頓飯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以前,覺得“柴新越,你媽喊你回家吃飯”是一句玩笑,現在才覺得,熱氣騰騰的家常便飯,總能給我們最好的給養、最質樸的溫暖、最妥帖的慰藉。
03
而這種感覺,越長大,便越發真切。
家里的哥哥姐姐們過年回家,三番五次約了好幾次,每次都是因為各種忙,不能成行。每次發微信,總說著:好啊好啊,我忙完了就找你。每次總是沒了下文,時間成了未知數。
坐下來吃頓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這段時間,刻意地和網絡保持了一點兒距離。沒有關心娛樂明星的離婚,沒有關心一位父親募捐的瘋狂,沒有關心那些浮躁的八卦。忙忙碌碌的工作之外,深夜走在寂靜的大街上,心里想的都是回家吃飯的味道。
因為一些事情的煩亂,影響了自己的判斷。每次晚上回家和父親閑聊,他都是鼓勵的聲音,讓我這個男子漢去勇敢、去決斷、去面對、去戰斗。
這時候你就會覺得,無論外界多么浮躁,都不抵家人的一句關心;無論外界多么精彩,都不及家人一頓飯帶來的踏實。
04
人有時候,得藏著一點兒食糧。精神、肉體皆是。餓的時候,想到冰箱里有肉有雞蛋,柜子里有泡面,胃就會舒服些;焦慮的時候,想到還有家人可依靠,還有后路可走,心就會踏實些。
以前,急切地想離家千里,仿佛不離開家,都不足以談自由;現在,不想離家,放棄了刻意離家的念頭,人卻像是岸邊的船,隨著水波漂蕩,離岸越來越遠。
幸好,還有食物,回憶起兒時的味道,瞬間讓你回到岸邊。
我最近時常想起母親做的飯菜,它曾經作為我最大的精神樂趣,伴我度過了小學、初中。我時常想起餐廳里昏黃的燈光,在漆黑寒冷的冬夜里,像是一道光芒,指引著我回家的方向。
它溫潤了我整個青春期。將來,也勢必會在每個人生不如意的時刻,慰藉我。
05
看來,比人和脾氣更倔強的,是胃,是食物。
它對家里一盤炒菜、一個大餅和一碗羊湯的眷念,不需要刻意煽情,簡單卻動人。
若是食物知道,它能夠讓一個身處迷茫的人,在冬夜里念念不忘;讓他在浮躁的世界能夠穩得住一顆兵荒馬亂的心,食物也該驕傲起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