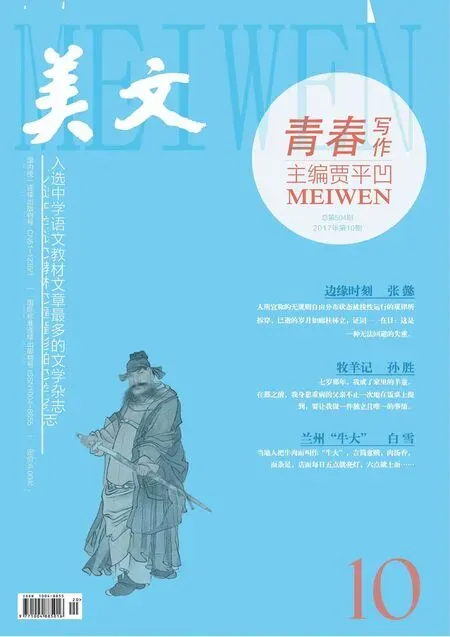姥爺的竹林
徐靜婷
姥爺的竹林
徐靜婷
每個暑假,姥爺都會托人帶信說:“回來吃筍呀。”
姥爺喜歡竹子,家里也種著一大叢青綠的竹林。下雨時,整晚都是雨打竹葉的聲音,屋子里外充斥著又重又涼的土腥味,第二天一早,林子中就冒出很多鮮嫩的竹筍,當然還有蟬洞,伸手就能摸到胖嘟嘟的知了猴。姥爺高興得臉上的褶子都皺在一起,招呼著鄰里來竹林里挖筍、挖蟬蛹,他自己則像只威武雄壯的大公雞,斜倚在大門口,一邊和人聊天,一邊指揮著年輕人和小孩子去更深遠的地方尋尋。就這樣忙乎完一晌午,等筍差不多挖盡了,蟬洞也差不多掏了一遍,他才樂呵呵地回去。回去了就讓姥姥炒一盤竹筍臘肉,煎個金蟬,又命令我快去村口打三斤黃酒,外加一毛錢跑腿費,用來賞我一根冰棍。每次,我抱著滿滿的酒瓶從村頭呼哧呼哧地跑回來時,前襟總是被酒打濕一片。姥爺拍拍我的頭,可惜地說:“哎,都灑了,得慢慢走路呀。”說完,從我懷里抽出酒來,步子很快地走向堂屋里——那里早等著三兩個談笑風生的酒友了。
姥爺喜歡竹子,這大概和他的經歷有關。年輕時,姥爺在永寧寺做俗家弟子,學了幾招防身的功夫和看病的本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他都是村里的赤腳醫生,扛著那只裝著器材和急救藥的舊木箱,走了很多路,救了很多急。后來,常跟著他行醫的大姨也成了赤腳醫生。姥爺曾在行醫途中從人販子手里救了個小孩,那孩子后來也成了挖筍的常客。姥爺說,永寧寺里有很多竹子,還說竹子用途很廣,能入藥,還能清心。他給舅舅起名叫“以竹”,希望舅舅能像竹子那般清朗挺拔,剛正不阿。女兒們的名字里都有草字頭,也是為了沾沾竹木的清氣。
姥爺的軟筆很好,也和在寺里抄過經有關。快過年的時候,村里人都找他寫春聯。姥爺家的堂屋正中掛著他臨摹鄭板橋的《竹石圖》。畫布的右上角從上到下,從右向左寫著:
四十年來畫竹枝,日間揮毫夜間思。
冗繁削盡留清瘦,畫到生時是熟時。
落款是:村野韓老叟。我曾誤將“叟”念成“瘦”,因為姥爺清茶素食,練功習武,清俊挺拔。
他卻擺擺手說:“不是‘瘦’,是‘叟’。‘老頭兒’的意思。”
“為什么不寫名,寫‘老頭兒’呢?”我問。
“老頭兒有老頭兒的好。你不知道,老頭兒有多好。”他微瞇著眼睛,搖頭晃腦,好像“老頭兒的好”就像睡在陽光里,撓著耳根的大花貓。
姥爺最開心的還是有人過來邀他喝酒。有一次,朋友如約而至,姥爺開心得不行,吩咐姥姥做幾個小菜,鐵了心地要喝一杯。姥姥勸他,他就跟孩子似的求了半晌,伸著一根指頭比畫著:“最后一次,最后一次。”那天,他灌了一斤白酒,整張臉都燒了起來,卻不成想真成了最后一次。
猶記得那年才入秋,連著下了好幾場雨,空氣清冷,竹筍發了好幾匝,鄰里都等姥爺招呼他們挖筍,可一直沒動靜,竹子也黃了不少。
姥爺不招呼客人是因為他病了:咳血嘔吐,整個人瘦脫了相。病的原因么,大家都說是姥爺喝酒抽煙太兇。可姥姥說,姥爺青年行醫時被人販子打斷過兩根肋骨,其中一根扎進肺里。那年頭醫療條件差,沒能根治,由是落下病根。在那個秋雨淅淅瀝瀝的晚上,姥爺裹著厚厚的毛絨毯子,走到門口,瞅著雨中蕭瑟的竹林呆呆立了半晌,輕聲嘀咕道:“怕是經不了冬了。”只不知這話是說竹林,還是說自己。
那時候,姥姥天天在廚房里熬中藥,院落里就很難聞到竹子的氣息了。她還在院子里、廚房里、客廳里來回穿梭,拿著抹布到處抹,不時地看著表,提醒姥爺又到吃藥時間了。姥爺的藥大概很苦。他這一輩子不皺眉、不嘆氣的“規矩”在吃藥時全都打破了:
“唉——”他長長地嘆著氣,面部肌肉奇怪地抽動著。
然后,他會端起一碗水,一口氣灌下去。面部開始舒展,他長地出了口氣,咂咂嘴,仿佛耗盡了所有氣力,身體也隨之深陷在那張哼哼唧唧的躺椅里頭。幫他解苦的是糖水,泡著冰糖和蜂蜜。當時蜂蜜還是奢侈品,是舅舅托人從外地帶回來的,但姥爺對這甜味似乎不買賬,說喝多了酸苦。這實在是個奇怪的道理。
我又想起另一件事來:姥爺曾有個“絕技”,能一眼分辨出糖水和白水來。我小時候問他是怎么做到的,他神秘兮兮地說:“糖水里有滑溜溜的絲縷,像風撕過的云彩片,清水透徹得厲害,陽光進去不打折。”我當真看了半天,說:“我怎么看不到呢?”姥爺就說:“你是小孩,眼睛還要進化,進化成老人家的程度才能看見。”我將信將疑。姥爺在我身后一邊偷著笑,一邊扯片竹葉放在茶里,一口一口地啜著,很得意的樣子。姥姥在一旁看不下去了,說:“他哪有這么厲害。兩個茶缸不一樣呀!”原來姥爺抽煙厲害,他的茶缸壁上自然印著焦黃的煙痕,都是無意中燒上去的。和茶杯一樣焦黃的是姥爺的手:指甲又大又硬,皮膚又粗又糙,上面密密排著皸裂的裂痕。姥爺因病戒煙的那段日子里,焦黃也褪去不少,轉成了青紫,似乎想要遮住松垮細瘦的手背上密密麻麻布著的針眼。
有一天半夜,姥姥聽到姥爺起床出門,院子里響起嘩啦啦的聲音。姥姥說,姥爺把幾株發黃的竹子連根拔了,也不知道他哪里來那么大的力氣。再后來,精疲力盡的姥爺回房間睡了。
他這一覺睡到大雪紛紛,睡到綠草茵茵。竹林依舊蔥郁地生長著,只是姥爺再也醒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