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動物大觀園
尚語
在接觸《中華大典·生物學典·動物分典》之前,對中國古代典籍中記載的動物,我們首先會想到《詩經》中“關關”叫的雎鳩和“食我黍”的碩鼠,《山海經》里銜石填海的悲情精衛和那些“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腳的鳥,生著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魯迅《阿長與〈山海經〉》),特別是《莊子》里那大得“不知其幾千里”的鯤、“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鵬、“搶榆枋時則不至”的蜩與學鳩、“翱翔蓬蒿之間”的斥饁、“不知晦朔”的朝菌和“不知春秋”的蟪蛄,等等。而翻開《動物分典》,隨著書頁在指間劃過,我們仿佛進入了一個奇大無比、畛域分明的“動物大觀園”,各式各樣、數不勝數的動物從歷史的褶皺里一個個躥出來,躍然紙上,讓人目不暇接,驚嘆不已。
《動物分典》是國務院批準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國家文化發展規劃綱要重點出版工程項目、國家“十一五”重大工程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重點支持項目《中華大典》子典之一《生物學典》的一個分典,由國內20多位平均年齡近8旬的動物學家歷時9載編纂而成,云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是一部大型動物學類書。全書共4冊近900萬字,內容依據現代動物系統分類學知識與古文獻資料情況設為52個總部,全面、客觀地反映了我國古代文獻對動物的命名、分類、形態特征、生存習性、地理分布,以及有益動物利用、有害動物防治等方面的記載和論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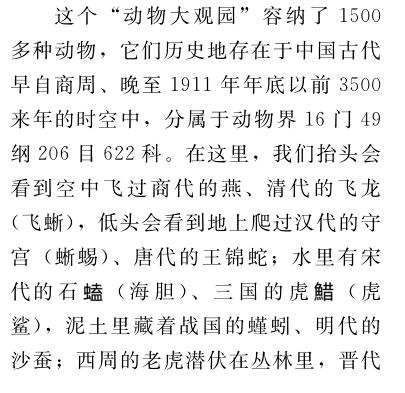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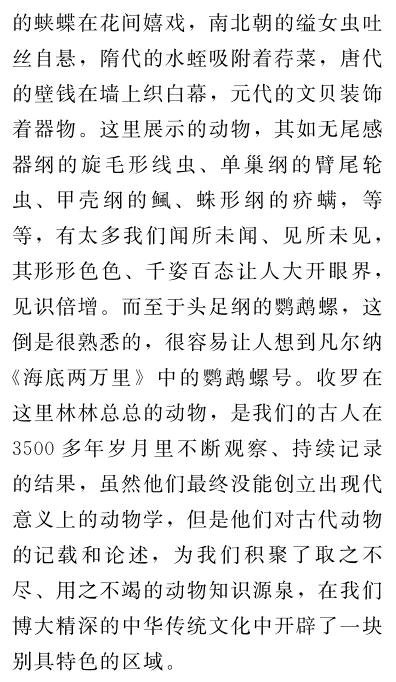
在這個“動物大觀園”里,我們除了能夠感受獅的威猛、蛇的陰鷙、狐的狡黠、虱的齷齪、猴的靈巧等,還能夠了解到古人對動物命名、分類、形態、解剖、生殖、生態、遺傳、進化以及物候、地理等方面的科學或不科學、合理或不合理、真實或荒誕的研究和看法,反映了古人對自然世界的觀察、認識和經驗積累。譬如關于鳥類:甲骨文、金文中便有“鳥”字,《說文解字》解釋說“鳥,長尾禽總名也”,又說“隹,鳥之短尾總名也”,將鳥分為兩大類,即長尾和短尾。這一區分,讓我們好像明白了在我們的漢語語境里,為什么同樣是鳥類,有的要叫作鳥,而有的要叫作雀。對鳥類的形態結構及其功能,古人觀察和描述頗為細心,如《禽經》曰“物食長喙,食物之生者皆長喙,水鳥之屬也;谷食短篋,鳥食五谷者喙皆短;搏則利嘴,鳥善搏斗者利嘴”,根據不同鳥的特性對鳥嘴的長短利鈍進行觀察和描述。對鳥類的物候特征與草木盛衰、季節變化之間的關系有明確的發現和記述,如《禽經》“颋?鳴而草衰,澤雉啼而麥齊”,《蠕范》“燕春社來,秋社去;?夏至來;雁仲春來,仲秋去。立春百舌鳴,雨水鶯羽,春分杜鵑北向,谷雨鵯?催起,霜降!"南翔,大雪脊令鳴,冬至伯勞歸”。對鳥鼠同穴的記述,反映了動物共生現象的存在,如《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為?,其鼠為駿”。而說到動物解剖,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莊子》里的“庖丁解牛”,庖丁那干凈利落、游刃有余的解牛表演實在令人稱奇。這應該算是兩千多年前的“動物解剖”了吧。《宋提刑洗冤集錄》載有驗骨的內容,說人的骨頭“有三百六十五節。男子骨白,婦人骨黑”“牙有二十四,或二十八,或三十二,或三十六”“左右肋骨,男子各十二條,八條長四條短,婦人各十四條”等,也不知道這樣的說法是否建立在人體解剖的實踐基礎之上。這些是古人在當時條件下獲得的知識,對此大可不必深究,倒是通過古人的記述,我們還知道了“三海豆芽”不是豆芽菜、“海百合”不是百合花、“泥筍”不是竹筍,這些看似植物名稱的詞語其實指的都是動物。同時,我們也不會相信古人關于“蟾蜍去月,天下大亂”“凡蛤蟆之類皆不交合,惟雌雄相對吐沫”“多年鼉入水化為龍”、兩頭蛇“是老蚯蚓所化”、“季秋之節,雀入大水化為蛤;孟冬之節,雉入水化為蜃”“鶴以聲交而孕。雄鳥上風,雌承下風則孕”等荒誕無稽的說法。
通過對“動物大觀園”的游覽,我們也發現,古人那么用心、持續地觀察、記載動物,有一個突出的用意是通過對動物的認識,來搞清楚動物在人類生產、生活中所能派上的用場,比如將動物納為食材、藥材以及用于觀賞、娛樂,甚至借動物之力來彌補或替換人力之所不及,于是便產生了狩獵活動,狩獵甚至成為古代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生產方式,并形成了四季狩獵的制度和禮儀,如“春?”“夏苗”“秋”“冬狩”,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狩獵規矩,以維護自然萬物的平衡。狩獵活動為歷代帝王所喜愛,常在冬季組織大規模的狩獵活動,并將狩獵活動當作習武練兵的重要手段。當然早在上古時期,古人在勞動生產實踐中,逐漸認識到自然環境與動物生存之間的關系,也認識到在狩獵時不可捕盡殺絕,應讓被獵動物有繁衍生息的機會,強調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如《逸周書》曰:“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則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不颬不卵,以成鳥獸之長。”古人此類野生動物保護意識,對我們今天保護野生動物,維護生態平衡,促進生態文明建設,仍具有其可資借鑒的現實意義。而在人類試圖將動物為我所用的同時,也不得不面對動物的攻擊和傷害,甲骨文中就有對蝗、鼠、虎等動物為害的記載,這是今天我們能夠見到的最早記載動物為害的文獻。對動物為害,古人是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的,所以古人不僅區分出了哪些是有益動物,哪些是為害動物,還總結、積累了一系列防治動物危害的方法。對虎的為害,我們在《水滸傳》中有所領略,但那是文學作品,不足為據。在古代中國,頻繁發生的蝗災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產生活和社會安定,甚至引起統治者的重視,大量文獻均有記載。譬如唐太宗痛感蝗之害民,取而生吞之。唐玄宗時宰相姚崇認為蝗災可治,創造了火邊掘坑,且焚且瘞,焚燒和掩埋相結合的治蝗辦法。如今,在我國,蝗災已很難大面積發生,但局部偶爾發生時,我們是否還可以從古人的治蝗辦法和經驗中獲得某種啟示呢?
《動物分典》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典籍中披沙揀金般地摘錄有關動物的資料,再將這些零亂龐雜的資料經考證、厘定,按現代動物學分類體系分門別類地編纂成卷,涉及的典籍多達4000卷(冊),差不多可以說把中國古代典籍翻了個底朝天。所以,在這個“動物大觀園”中,除了古代動物集體亮相外,中國古代典籍特別是動物典籍也來了個集體亮相,讓人們在大飽眼福的同時,還能更深切地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動物分典》的內容建立在如此深廣的典籍基礎之上,其分量之厚重可想而知。此外,書中還酌情引錄了明清時外國人在中國所著漢文著作及中國人譯編、譯述的著作,反映了中西文化在動物學界的交流與融合。根據動物學科的特點,對動物分類系統的綱、目、科、種中文名均標注了動物拉丁文學名,在動物物種正名下列出異名、地方名和俗名等,體現了新型類書的特點,對我們擴大認識、準確理解古籍中的動物知識將起到不可小視的作用。書中大量采自古籍的插圖,或簡潔,或細膩,無不展示著古代動物的生動形象,使我們能夠在“有圖有真相”的觀感中直觀地認識、了解古文說不清道不明的各種古代動物,尤其是《山海經》中那些稀奇古怪的動物。在昆蟲綱、鳥綱、獸綱三個總部中還配置了采自故宮珍藏的《清宮鳥譜》《清宮獸譜》中的動物彩圖。這些出自宮廷畫家之手,繪制精美、逼真,在深宮密院中封存了240多年的動物彩圖具有很高的史學、美學及科學價值。它們原來僅供皇室人員閱覽、欣賞,如今隨著《動物分典》的出版而公布于眾,讓紅墻之外的普通讀者也有幸一飽眼福,這稱得上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喜事。
《動物分典》的編纂出版,是建立在對我國古籍記載的動物資源進行全面調查的基礎之上的,其全面性、系統性、時空涵蓋性等多方面皆是空前的。它的出版,基本回答了1911年前古人認識多少種動物的問題,可為國內外讀者提供認識和研究中國歷史動物的渠道。這一成果不僅是古籍中動物資源記載的高度濃縮,也是對流傳至今、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掘、利用、傳承和弘揚,其積極作用和深遠意義是不言而喻的。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