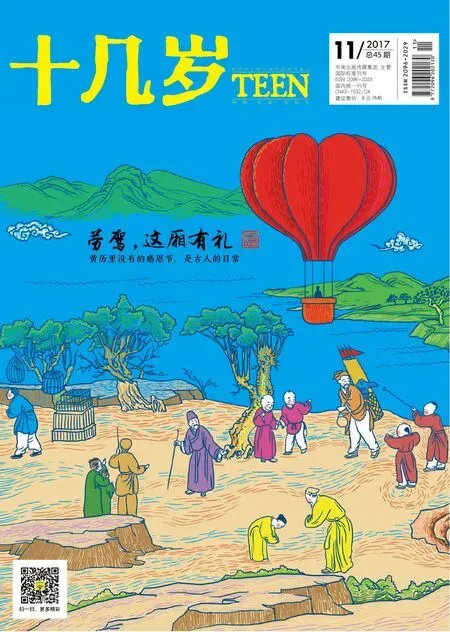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文/羅家偉(春芽文學社社員) 指導老師/鄧可成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文/羅家偉(春芽文學社社員) 指導老師/鄧可成

我羨慕那個悲愴的背影,能說出“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的豪言;我感嘆那個飄逸的身影,能吟出“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埋怨;我仰慕那個憔悴的面容,能懷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期許。
而今,奸佞當道,我才感“眾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獨;昏君不朝,我才覺“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的無奈;民不聊生,我才懂“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悲哀。
而我,難道只能空吟“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來荒唐度日?只能拿“五花馬,千金裘”換來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但,美酒入口,卻成苦酒;醉看離愁,更是離愁。
我所摯愛的一切灼燒著我的心,讓我在長醉中愈加清醒。是啊,正因為深知“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才不忍心拂衣而去,棄這江山黎民于水火;正因為明了“我輩豈是蓬蒿人”,我才不甘心披蓑戴笠,拋塵世悲歡于身后,獨釣一江冬雪;正因為我是那青蓮謫仙,盛唐最亮的那抹月光,我才寧愿在吶喊中瀟灑死去,也不愿在沉默中茍且生存。縱使世人都嘲笑我“縱酒狂歌空度日”,質疑我“飛揚跋扈為誰雄”,還有這一輪明月,溫柔待我。
于是我又舉起酒杯……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
所有壓抑的情感在此刻涌上心頭,我在醉意中高歌長嘯。倘若連吶喊的勇氣都已失去,那我何必在世上茍活!
朦朧中,我看見我的信仰,那樣模糊,又那樣清楚。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
于是我不再懼怕孤獨。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不再唯唯諾諾地茍且偷生,只用冷眼,予那諂媚阿諛一瞥不屑。我寧愿閑騎白鹿,漫步青崖;也不再摧眉折腰,不得歡顏。
翰林遭貶又怎樣,只管“仰天大笑出門去”,尋一酒坊,淺斟低唱;賜金放還又何妨,不過“一夜飛度鏡湖月”,行游山野,縱酒狂歌!不管前路是冰塞河川還是雪滿山巒,只要懷抱信仰,就能刺破黎明。
看不慣權貴的昏庸與暴戾,于是我憤然而去,重拾布衣,將富貴與功名拋卻天上。我只想回我的人間!可這人間,又成了怎樣的世間。愚昧遮住了人們的眼,讓他們沉默如傀儡,默然似行尸。悲哀,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我多羨慕那楚地的狂人,能高歌“鳳兮鳳兮”,質問孔丘“何德之衰”。而我,又能向誰訴說?
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
既然我的心容不下仕途的陰霾,何不另尋出路,在我的詩和遠方里大聲歌唱,用我歌吟,將這昏昏噩噩的愚民喚醒。
于是我一直走,一直走……
終有一日,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終有一日,我秀口一吐,成就半個盛唐。
終有一日,我會“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笑那“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
如果我遭逢失意,那只是因為我未成熟的羽翼尚且載不動我的意氣。只要懷揣著信仰,永遠不失去向生活宣戰的勇氣,終有一日,我會一鳴驚人。
問君何不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
寫作緣由
會逢十月,秋意漸濃。常見葉隨風落,滿目蕭索,頗感傷懷;又因近來諸事多有不順,郁懷于心,積久難發。可謂正是“人生在世不稱意”之際,只愁不能“明朝散發弄扁舟”。
于是提筆,題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借此高歌長嘯,暢抒我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