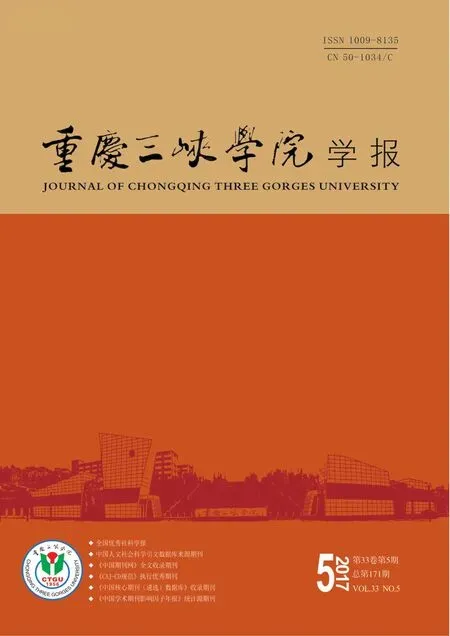甘寧將軍故里考辨
程地宇
?
甘寧將軍故里考辨
程地宇
(重慶三峽學院,重慶 404020)
甘寧壩、甘寧洞、甘寧村之名,載于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其地在“武寧縣北三十里”。武寧縣本漢巴郡臨江縣地,唐武德二年改屬浦州,即今萬州。正因如此,王象之將甘寧分別納入萬州及忠州“人物門”。說甘寧是“忠縣人”,是指甘寧故里曾經隸屬的武寧縣漢時為臨江縣轄地,而臨江縣治所在今忠縣;說他是“萬州人”,是指其故里甘寧壩、甘寧村在今萬州甘寧鎮。
甘寧;《輿地紀勝》;臨江縣;武寧縣;萬州甘寧鎮
一
萬州有個甘寧壩,甘寧壩上有個甘寧村,皆因三國東吳折沖將軍甘寧而得名。文獻記載甘寧是此地人,歷來人們也這樣認定。可是,近年來一種否定甘寧為萬州甘寧壩甘寧村(今屬甘寧鎮)人的說法卻悄然興起,在互聯網上廣為散播,流傳既久,漸成氣候。這種說法的代表作是陳仁德先生的《甘寧將軍是哪里人?》(以下簡稱陳文),陳文在網上發布并被多次轉發后,由作者本人提交給“重慶市三國文化研究會2013年會暨夔州文化研討會”,發表在該會會刊《白帝城》總第11期上。
陳文認為甘寧故里在今忠縣長江南岸甘家田,“甘寧應該是忠縣人”;對甘寧故里為萬州甘寧壩的傳統說法予以徹底否定,其文曰:
持萬州說的人所依據的主要資料是成書于民國后期的《萬縣志》。《志》載:“甘寧,字興霸,漢臨江人。后周析臨江置源陽,隋改源陽為武寧(治今武陵鎮),明省武陵入萬縣,故又稱萬縣人。”①這段短短的文字,幾乎沒有引起過人們的懷疑,但只要稍加推敲,就會發現其中的明顯疑點。首先是從臨江到源陽再到武寧(武陵)萬縣的建置變化的敘述,只是說明了武寧(武陵)原屬臨江(忠縣)后改屬萬縣的建置調整過程,而始終未有只字能說明甘寧是武寧(武陵)人。文中含糊其詞地偷換概念,將“臨江人”忽然偷換成“臨江”,然后一氣從臨江說到萬縣,又將概念偷換成“萬縣人”,給人的感覺是臨江人(甘寧)=源陽人=武寧(武寧)人=萬縣人。其破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應該是臨江人(甘寧)≠源陽人≠武寧(武寧)人≠萬縣人。古代臨江的范圍那么大,為什么其中一小部分后來劃歸萬縣,甘寧就一定“遷到”萬縣了呢?[1]
在作了這樣一番駁難之后,陳文直截了當地說:“甘寧鄉被附會為甘寧故里,是民國21年(1932)的事。當時萬縣縣長李某重修甘寧墓,請蜀中才子公孫長子題寫一碑樹于離墓約300米的河對岸,碑文為‘吳折沖將軍西陵太守甘寧故里’,以后眾口相傳,甘寧鄉便成了甘寧故里。”[1]

讀罷此文,人們不禁要問:“持萬州說的人所依據的主要資料”果真“是成書于民國后期的《萬縣志》”嗎?甘寧鄉被認定為甘寧故里,果真“是民國21年(1932)的事”嗎?
南宋時期,杰出的地理學家王象之就已在《輿地紀勝》里對甘寧故里在萬州作出了明確認定②。《輿地紀勝·夔州路·萬州·人物》云:“甘寧,字興霸,臨江人也。按:漢臨江縣即今武寧縣地。今武寧縣北三十里有洞有壩,皆以--(甘寧)名③,詳見忠州人物門。武寧、南賓皆漢臨江縣地,故甘寧亦附見二郡。寧佐吳為折沖將軍,開爽有計略,頗讀諸子,輕財敬士,事見《吳志》。”[2]卷一七七4601《輿地紀勝·夔州路·萬州·古跡》亦云:“甘寧洞,在武寧縣甘寧村,有洞曰甘寧洞。”[2]卷一七七4598
《輿地紀勝》中“武寧縣北三十里”之“甘寧壩”“甘寧村”“甘寧洞”的記載早于民國《萬縣志》715年,距今796年。此外,南宋著名地理學家祝穆所著《方輿勝覽·萬州·人物》也指出④:“甘寧,臨江人,即今武寧縣地。佐吳為折沖將軍,輕財敬士。”[3]卷五九1045
關于武寧縣的歷史沿革,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山南東道八·萬州》云:“武寧縣,本漢巴郡臨江縣地,后周武帝初分臨江縣地置源陽縣,屬南都郡。至建德四年改南都郡為懷德郡,又改源陽縣為武寧縣,取威武以寧斯地為名。隋開皇三年罷郡,以縣屬臨州,大業二年廢臨州⑤,以屬巴東郡。唐武德二年改屬浦州⑥,即今萬州是也。”[4]卷一四九2887
《輿地紀勝·夔州路·萬州·縣沿革》亦云:“武寧縣(下)⑦,在州西一百六十里、《圖經》云:本漢巴郡臨江縣,后周為源陽縣,又改曰武寧。隋以縣屬臨州;大業初又屬巴東郡。唐武德二年置南浦州,又改萬川縣,皆屬焉。”[2]卷一七七4590
南宋歷史地理學的權威著作《輿地紀勝》將甘寧列為萬州《人物》之首,《方輿勝覽》則把甘寧作為萬州《人物》唯一人選;二書皆認定甘寧為當時隸屬萬州的武寧縣人,《輿地紀勝》更是白紙黑字地載明“今武寧縣北三十里有洞有壩,皆以甘寧名”“甘寧洞,在武寧縣甘寧村”。可見“甘寧壩”“甘寧村”“甘寧洞”的地名在《輿地紀勝》成書之前就早已存在了,壩、村、洞皆以甘寧名之,其為甘寧故里無疑,豈是所謂依據“成書于民國后期的《萬縣志》”!又豈是“民國21年(1932)的事”!武寧縣(連同其轄地甘寧壩、甘寧村)隸屬萬州的始末,北宋《太平寰宇記》、南宋《輿地紀勝》均作了翔實的記載。由于甘寧壩所屬的武寧縣漢時為臨江縣地,而臨江縣治即為宋時的忠州,故王象之將甘寧其人分別列入萬州和忠州的《人物》門中,這是一種歷史主義的態度,也是一種圓融通達的記述方法。
《輿地紀勝》中有關忠州的記載已佚,今無從得見,但從《萬州·人物》門中有關甘寧的文字來看,在《忠州·人物》門里有關甘寧的文字當與之大同小異。岑建功于1848年據各書所引《輿地紀勝》的原文輯錄而成的《輿地紀勝補缺》(卷七)中,對《忠州·人物》門涉及甘寧的輯補文字即全抄《萬州·人物》門。
本來,仿效王象之將甘寧分別納入萬州和忠州《人物》門的做法,將甘寧說成“萬州人”或“忠縣人”均可——說他是“萬州人”,是指其故里甘寧壩、甘寧村在今萬州甘寧鎮;說他是“忠縣人”,是指甘寧壩、甘寧村曾經隸屬的武寧縣漢時為臨江縣轄地,而臨江縣治所在今忠縣。但陳文卻不能接受這種折中變通的說法,否定“甘寧是萬州人”而獨存“甘寧是忠縣人”之說。歷史人物故里的屬地問題,歸根到底是以當下的實際狀況為依據的,對于宋代當下,甘寧壩、甘寧村在“今武寧縣北三十里”,對于21世紀的當下,其名沿用至今的甘寧壩、甘寧村在重慶市萬州區甘寧鎮。這是不可改變的歷史事實和現實存在!
二
陳文指責民國《萬縣志》“含糊其詞地偷換概念,將‘臨江人’忽然偷換成‘臨江’,然后一氣從臨江說到萬縣,又將概念偷換成‘萬縣人’”。其實,民國《萬縣志》只不過是沿襲《輿地紀勝》等書的說法,并無別出心裁的文字,因而陳文指責的對象,即所謂“偷換概念”的主體,就不獨是民國《萬縣志》,而是包括《輿地紀勝》等書在內了。那么從《輿地紀勝》等書到民國《萬縣志》是不是在“偷換概念”?回答是完全否定的。這些著作中關于甘寧“是哪里人”的敘述,前后連貫,概念清晰,邏輯嚴密,并無“偷換概念”之嫌。
從事理上看,《三國志·吳書·甘寧傳》中“甘寧字興霸,臨江人也”,句中的“臨江”是個縣域大范圍,并未指明究竟在“臨江”何處。《輿地紀勝》將其指實為“漢臨江縣即今武寧縣地。今武寧縣北三十里有洞有壩,皆以甘寧名”則是對其具體位置及其在行政區劃演變中的隸屬關系所作的陳述,這不僅點明了“甘寧是武寧人”,而且還落實到“甘寧是武寧縣甘寧壩人”;而民國《萬縣志》只不過是綜合《輿地紀勝》等書有關敘述而成文罷了。
從形式邏輯的角度來看,這一表述是典型的對概念外延的逐級限定。在“甘寧是哪里人”的命題中,將地名與該地人分割開來是荒謬的,因為在此命題里,地名與該地人是統一的,說到某地,事實上指的就是某地人,這是題中已有之義,這也是常識所能判定的。陳文將二者割裂開,并將其對立起來,這才是真正的“偷換概念”。至于陳文中羅列的一系列等式和不等式,則無任何實際意義而顯得多余了。
陳文說:“據當地人講,甘寧鄉是因為境內有甘寧墓,而不是因為甘寧是當地人而得名。”這是作者“為了搞清楚個中原由,曾于上世紀末數次前往甘寧鄉實地考察”獲得的資訊。但其可信度如何委實堪疑。“當地人”是誰?何種身份?什么閱歷?是一人還是多人,其言論是否經過查證?凡此種種,皆語焉不詳,明顯帶有作者的主觀臆斷。
陳文將萬州甘寧鎮的甘寧墓斥為“偽冢”,匪夷所思。陳先生是一位長于古詩詞的文化人,理應知道所謂“衣冠冢”在古文化中的普遍性及其意義。萬州甘寧鎮甘寧墓是“衣冠冢”無疑,它是后人為紀念甘寧所建,并非為了以假亂真,欺世盜名。其實甘寧墓不止萬州甘寧鎮一處,見諸文獻的還有:
《景定建康志·風土志二·古陵》:“吳甘寧墓,在直瀆山下(今江蘇南京市)。考證:《伏滔記》:吳將甘寧墓,在直瀆之下,俗云墓有王氣。孫皓惡之,鑿其后為直瀆。”[5]卷四三第四八九冊,534
《湖廣通志·陵墓志》:“三國將軍甘寧墓:在興國州(今湖北陽新縣)東六十里軍山之陽。”[6]卷八一,第五三四冊,136
《四川通志·陵墓》:“甘寧墓:在通江縣(今四川通江縣)西百里露洛溪上,謂之甘谷。寧為吳將,歿歸葬于此。”[7]卷二九上,第五六〇冊,579
按照陳文的邏輯,只有甘寧真墓所在地才是甘寧故里。且不說陳文所指認的“甘寧故里”(今忠縣長江南岸甘家田)并無甘寧“真冢”,連“偽冢”也無!即便在上述幾座甘寧墓中,孰者為真,孰者為假?也恐怕難以分辨,甚至有可能皆為衣冠冢,即所謂“偽冢”。如此,豈不甘寧故里根本就不存在?當年萬縣縣長李某重修甘寧墓,并請蜀中才子題寫“甘寧故里”碑的行為,用今天的話來說,無非是一種鄉土文化建設。這一文化建設持之有故,并非憑空捏造,值得稱道,而陳文卻據此得出“甘寧鄉被附會為甘寧故里,是民國21年(1932)的事”[1]的結論,豈不有悖常理?
陳文說:“細考《三國志》……可以推知甘寧故里應該具備兩個特點。一是靠近長江邊,二是在縣城或者縣城附近。”[1]但就其所依據的《三國志》文字而論,殊難“推知”這“兩個特點”。陳文據《甘寧傳》注文“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住止常以繒錦維舟”等語就“推知”甘寧不可能“住在遠離江邊的地方”,因為這樣就不能“水則連輕舟……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其實《三國志·甘寧傳》的這段注文,不過是舉其水陸行止而泛言其行為方式及奢侈習氣,并未說甘寧只能在家鄉的陸地上車騎打轉,而不能跨出其故里輕舟泛波。何況甘寧壩距離長江并非遙不可及。陳文又以《三國志·甘寧傳》中“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至二十余年”等語就“推知”:“不可能想象,甘寧是離城很遠的地方的人而能常與‘長吏’交歡,至二十余年。”這就奇怪了,如此說來甘寧就只能在故里與“長吏”交歡,而不能走出去入城來與“長吏”交歡⑧!一位縱橫四方、隨心所欲的游俠,竟然被說成了一個足不出鄉里,身不離閭巷的土鱉!這種解讀未免牽強附會,更不能作為指認甘家田為“甘寧故里”的證據。
以忠縣甘家田為“甘寧故里”并非什么新見,而是載于清同治《忠州直隸州志》的舊聞⑨。仿《輿地紀勝》將甘寧分別納入萬州、忠州《人物》門之例,《忠州直隸州志》將甘寧納入其《人物志》本無可厚非,但該志又將甘家田指認為“甘寧故里”,這顯然與《輿地紀勝》《方輿勝覽》等歷史地理名著相抵牾。當然,如果有充分的證據,《輿地紀勝》《方輿勝覽》的結論也不是不可觸動,但可惜的是《忠州直隸州志》并未提出任何證據。而力主今忠縣長江南岸甘家田為“甘寧故里”的陳文,竟連《忠州直隸州志》這一出處也無只字提及。看來,陳文是落入了自己設定的陷阱。因為陳文一口咬定“持萬州說的人所依據的主要資料是成書于民國后期的《萬縣志》”“甘寧鄉被附會為甘寧故里,是民國21年(1932)的事”。并且說“公元二十世紀中葉的人在沒有明證的情況下去為公元三世紀初已定論為臨江人的甘寧作臨江人=萬縣人的推理,本身就是不科學的,不足置信的”。因而用晚清的地方志材料來為“今忠州長江南岸甘家田”為“甘寧故里”作證就底氣不足了——盡管《忠州直隸州志》成書早于民國《萬縣志》,但也早不到哪里去,與陳文自己設定的時間(《三國志》成書的年代)⑩相差也實在太遠了,從大的時間跨度而論,《忠州直隸州志》與民國《萬縣志》同樣“不足置信”,所以陳文干脆不提,這也算是一種策略吧。
三
甘寧并非完人,沒有必要回避或隱瞞其早年的行徑。《三國志·吳志·甘寧傳》云:“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眊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于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余年。”[8]卷五五1292
就是這段文字給甘寧留下了污點,以致招來非議乃至詈詬,對甘寧的歷史評價亦造成了諸多困擾。然而細讀這段文字即可發現,甘寧并非大奸大惡,不過是“輕薄少年”的“渠帥”而已;“奪其資貨”“有所賊害”者主要在“長吏界中”。因而稱之“游俠”,可謂恰如其分。同時,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不能局限于一時一事,而應綜合研判其一生的所作所為;更不能以偏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甘寧后來“止不攻劫,頗讀諸子”,正因發憤讀書,明理向善,終歸走上正途。
建安十三年(208)甘寧投奔孫權,開始其建功立業的人生歷程,官至西陵太守,封折沖將軍。民國《萬縣志》對甘寧的赫赫戰功作了簡明而又精彩的概括:“少好游俠,后歸吳,見用于孫權,破黃祖,據楚關,攻曹仁,取夷陵,鎮益陽,距關羽,守西陵,獲朱光,擊合肥,退張遼,迭著勛勞。事跡具《三國志》本傳。”《三國志·吳志·甘寧傳》對甘寧作了這樣的評價:“寧雖麄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8]卷五五1294孫權則云:“其人雖粗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8]卷五一1207《三國志·吳志·孫靜傳》附《孫皎傳》又云:“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8]卷五五1294在宋人看來,甘寧的地位當與黃忠、趙云輩相侔。程公許云?:“蜀將如關、張、龐統,吳將如周瑜、魯肅,志長命短,天下重惜之。而馬超、黃忠、趙云、費祎、呂蒙、程普、步騭、甘寧輩,皆智勇絕倫,足以當一面。”[9]卷一四第一一七六冊1049
宋人馮時行有詩詠甘寧廟云?:
豪杰自不群,俗眼蓋盲瞽。劉表既不識,那復論黃祖。
翻然脫霸銜,渡江得英主。唾手立功勛,雄名詫千古[10]卷六九第四七三冊474。
在馮時行看來,像甘寧這樣的豪杰,自然倜儻不群,與眾不同。不識英雄的俗物有眼無珠,如同盲人。劉表、黃祖者流就是這樣的睜眼瞎,而像孫權這樣的英明之主則獨具慧眼,使甘寧能順利地建立功勛,英雄威名令千古之人驚詫不已!
司馬光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他對甘寧也有嘉許之辭,其《寄題李舍人(偉)蒲中新齋》詩云:
隴上家聲勇氣殊,邊庭臥鼓欲安居。
非同王翦私求宅,更似甘寧晚好書。
劍倚寒窗風淅瀝,門無雜客柳蕭疏。
蒲州風土平生愛,為問旁鄰地有余。[11]卷六第一〇九四冊60
前引各家各書皆對甘寧持正面肯定的態度。而歷代民眾更是對之愛戴敬重,立廟祭祀,焚香禮拜。《明一統志·重慶府·祠廟》載:“甘寧廟,在巴縣。寧,三國吳將。”[10]卷六九第四七三冊474今湖北陽新縣富池鎮也有甘寧廟,當地有禱廟息風的習俗,與云陽張飛廟頗為相似。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沈遼睿達以書得名,楷盤皆妙。嘗自湖南泛江北歸,舟過富池,值大風,波濤駭怒,舟師失措,幾溺者屢矣。富池有吳將甘寧廟,往來者必祭焉。睿達遙望其祠,以誠禱之,風果小息,乃得維岸。乃述寧仕吳之奇謀忠節作贊,以揚靈威而答神之休,自作楷法大軸,以留廟中而去。其后乃為過客好事者取之。是夜神夢于郡守,使還之。明日,守使人訊其事,果得之,復畀廟令掌之。近聞今亦不存矣。”[12]卷九252
甘寧之靈還成為一方保護神。《湖廣通志·雜紀二》載:“富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建炎間,巨寇馬進自蘄黃渡江,至廟求杯珓?,欲攻興國。神不許,至于再三。進怒曰:‘不問何珓,必屠城!’乃自取擲,墜地不見,珓附著門頰上,去地數尺。進驚懼,不敢屠城。”[6]卷一一九第五三四冊934
1985年,湖北陽新縣富池鎮人民政府興建了甘寧公園,將甘寧墓遷至園內。園內一座高達5米的甘寧塑像巍然屹立。繞過塑像,有一泓清澈的泉水,名曰“甘泉”。甘寧墓在塑像后200米處,為公園的主體建筑。墓的東北面是十畝桂花,西南面是十畝翠竹,桂竹掩映,肅穆幽靜。墓前矗立著仿古六柱青石牌坊,云蒸霞蔚,雄偉壯麗;周邊青石圍壁上鐫刻書畫,琳瑯滿目,氣象萬千。甘寧公園游人如織。富池鎮甘寧公園的興建,對萬州甘寧鎮的鄉土歷史文化建設有著啟迪和借鑒作用。
八百多年來?,一直以甘寧為家鄉之名的萬州甘寧壩、甘寧村(今屬甘寧鎮)人民,任憑風雨晦明、世事滄桑,始終愛戴著這位英雄。他們不僅重修甘寧墓,立甘寧故里碑,還在蜚聲海內外的甘寧大瀑布(后改青龍大瀑布、再改萬州大瀑布)旁樹起了甘寧塑像。在一片如雷的濤聲和如夢的虹霓烘托下,甘寧騎著駿馬,手提長矛,回到了闊別的故鄉。但是,在萬州甘寧鎮歷史文化的建設中,至今仍然受到某些干擾。其中之一就是近年發生的“甘寧究竟是哪里人”的紛爭。此外,對甘寧的評價還有一種觀點,即“甘寧是蜀軍反將,人們早已將他遺忘”;甚至說“萬州人過高的抬高甘寧,可能在歷史界、文藝界引起混淆,也攪亂了外國人對中國歷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鬧出不必要的笑話而難以收場,再就是萬州人愧對了三國的蜀軍將士。”[13]此論調可謂糊涂到家,悖謬不倫。但是,這種觀點表露出的蜀漢正統思想以及狹隘本土意識倒是發人深思。
《三國演義》第一回云:“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并入于秦。及秦滅之后,楚、漢分爭,又并入于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后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14]1而三國又是走向新一統的歷史階段。從理論上講,魏、蜀、吳都有統一中國的可能性;三國之間為奪取天下進行的爭戰攻伐,從宏觀的歷史視角看,都是走向統一的進程。當代人對三國紛爭的格局,應當具備一種通透的、客觀的、科學的唯物史觀。但由于《三國演義》的巨大影響,一種以蜀漢為正統的歷史觀及其衍生的歷史情感深入人心,遂使民眾的心理產生巨大的偏移,親蜀仇魏排吳成為普遍的社會情態,尤其蜀漢故地表現得特別鮮明,歷久不衰。反映在對甘寧的評價上,就出現了所謂“甘寧是蜀軍反將”,“萬州人愧對了三國的蜀軍將士”等論調。把歷史道德化,把道德封建正統化,是這種論調的思想內核。這種論調不僅在理論上陳腐貧弱,在實踐上于文化遺產的繼承、旅游資源的開發百害無一利,也背離了萬州人民(尤其是甘寧故里人民)的意愿和權益。廣大甘寧壩、甘寧村(今屬甘寧鎮)人民并沒有將甘寧遺忘,而是世世代代不離不棄,珍之惜之。正是甘寧壩、甘寧村跨越時代的存在,甘寧故里人生生不息的綿延,方有幸在巴蜀大地上保留了一種獨立不羈的集體人格和超越世俗偏見的歷史意識。我想,今天的人們更應該珍惜文化遺產,敬重歷史名人,擁有一種大中華的文化情懷和歷史大趨勢的廣闊視界[15]。
[1] 陳仁德.甘寧將軍是哪里人?[J].白帝城,第11輯:33-34.
[2] 王象之.輿地紀勝[M].北京:中華書局,1992.
[3] 祝穆.方輿勝覽[M].祝洙,增訂;施和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
[4]樂史.太平寰宇記[M].王文楚,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
[5]周應合.景定建康志[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6]邁柱,夏力恕,等.湖廣通志[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7] 黃廷桂,張晉生,等.四川通志[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8] 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9] 程公許.滄州塵缶編[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0] 李賢,彭時,等.明一統志[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1] 司馬光.傳家集[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2] 張邦基.墨莊漫錄[M].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
[13] 余錫萬.求證青龍瀑布[J].巴鄉村,2001(1):17.
[14] 羅貫中.三國演義[M].長沙:岳麓書社,2001.
[15] 陳興貴,李虎.試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效果的評價[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1(1):27-32.
(責任編輯:李朝平)
①這段引文有三處錯誤:其一,民國《萬縣志》卷十三《人物志·甘寧》“明省武寧入萬縣”,陳文將“武寧”錯寫成“武陵”;其二,民國《萬縣志》卷十三《人物志·甘寧》“故又為萬縣人”陳文將“為”字錯寫成“稱”;其三,民國《萬縣志》卷十三《人物志·甘寧》“少好游俠,后歸吳,見用于孫權,破黃祖,據楚關,攻曹仁,取夷陵,鎮益陽,距關羽,守西陵,獲朱光,擊合肥,退張遼,迭著勛勞。事跡具《三國志》本傳”一節陳文漏引。這漏引的一節證明民國《萬縣志》是尊重《三國志》甘寧本傳的,并沒有否定《三國志》的說法。
②民國《萬縣志》熊特生序署為“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即成書于1936年8月。《輿地紀勝》成書于南宋嘉定、寶慶間,初稿約于嘉定十四年(1221)完成,至寶慶三年(1227)全書始成。后人以其詳贍分明,體例謹嚴,考證核洽,譽為南宋全國性總志中最善者。書中記載的內容當是發生在此前的既成事實。甘寧壩、甘寧村的存在就是如此。
③文中符號--,指代前文所列詞條,即“甘寧”二字。這是古書的慣例,目的在于減少重復刻字。這種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如《現代漢語詞典》的釋文中即用符號~代替所釋之詞條。
④《方輿勝覽》約成書于南宋嘉熙三年(1239),直至咸淳二年(1269)始有刻本流傳。甘寧壩、甘寧村的存在當在此前。
⑤《太平寰宇記》點校本卷一百四十九《校勘記》注:“隋開皇三年罷郡以縣屬臨州大業二年廢臨州:‘罷郡以縣屬臨州大業二年’十一字底本(金陵書局本)脫,萬本(萬廷蘭本)、庫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同,據宋版(宋槧殘本)補。《隋書·地理志》上載云開皇初廢懷德郡,大業初廢臨州,正合本書記載。”(中華書局2007年11月第1版,第2894頁)
⑥《太平寰宇記》點校本卷一百四十九《校勘記》注:“唐武德二年改屬浦州:按《舊唐書·地理志二》及本書萬州總序,唐武德二年于南浦縣置南浦州,武寧縣屬之,八年廢南浦州,同年復立浦州,則此‘浦州’應作‘南浦州’,才合。”(中華書局2007年11月第1版,第2894頁)
⑦武寧縣(下):“武寧縣”三字后的“下”字,表示武寧縣為下等縣。按:唐時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宋因唐制,縣亦分等級。縣分等級主要與賦稅掛鉤,也與縣官的品級相關。但劃分的標準各代不盡相同。《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志二·戶部尚書》:“六千戶以上為上縣,二千戶已上為中縣,一千戶已上為中下縣,不滿一千戶皆為下縣。”《宋史全文》卷一《宋太祖一》:“詔諸道所具版籍之數升降天下縣望,以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又,“武寧”今寫作“武陵”,據清同治《增修萬縣志·地理志·建置沿革·廢縣·后周源陽武寧廢縣》:“愚按:今武陵場即廢武寧縣理,萬縣西唯此為大鎮,計里與《寰宇記》《方輿紀要》不相遠。明有巡檢司,今廢。‘寧’曰‘陵’,傳訛也。”又據民國《萬縣志·輿地志·古跡》載:“按:今縣屬之武陵場,蓋即廢武寧縣,曰‘寧’,‘陵’字異,傳寫致訛。”這就是說,本當作“寧”,因人們在傳寫中錯為“陵”。
⑧請注意《三國志》卷五十五《吳志·甘寧傳》里“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等句中“接待隆厚者”一語。既言“接待”,當然是相逢之人或地方官員們接待甘寧,自然是甘寧前往與之“交歡”。
⑨《忠州直隸州志》,[清]侯若源、慶征總纂,柳福培纂修,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該書卷之首《方輿志第一·古跡九》載:“甘將軍故里:在治南二十里,俗名甘家田,為蜀漢吳將甘寧故里。”
⑩《三國志》最早以《魏書》《蜀書》《吳書》三書單獨流傳,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三書方合為一書。
?程公許(?—1251),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一說敘州宣化(今四川宜賓西北)人。字季與,一字希穎,號滄洲。宋嘉定進士。歷官著作郎、起居郎,數論劾史嵩之。后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又論劾鄭清之。屢遭排擠,官終權刑部尚書。有文才,今存《滄洲塵缶編》。
?馮時行(1100—1163):字當可,號縉云,祖籍浙江諸暨(諸暨紫巖鄉祝家塢人),宋徽宗宣和六年恩科狀元,歷官奉節尉、江原縣丞、左朝奉議郎等。后因力主抗金被貶,于重慶結廬授課,坐廢十七年后方重新起用,官至成都府路提刑,辭世于四川雅安。著有《縉云文集》四十三卷,《易倫》二卷。
?杯珓:占卜用具,即俗稱“打卦”。程大昌《演繁露·卜教》:“后世問卜于神有器名杯珓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或以竹,或以木,略斫削使如蛤形,而中分為二,有仰有俯,故亦名杯珓。”
?《輿地紀勝》成書于1221年。“甘寧壩”“甘寧村”“甘寧洞”之名首見于此書,距今已有796年。但其名之存在必定早于《輿地紀勝》成書之時間,取其整數,故稱800年,考慮到或許更早,故加一“多”字;究竟早到何時?尚待新材料之發現。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Hometown of General Ganning
CHENG Diyu
The names of Ganning plain, Ganning cave and Ganning village were first recorded inby Wang Xiangzhi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was described as “thirty miles northern from Wuning county”. Wuning county was firstly called Linjiang county which belonged to Han-Ba shire but then was included in Pu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which is Wanzhou nowadays. For this reason, Wang Xiangzhi recorded General Ganning in both Wanzhou Biography and Zhongzhou Biography. Therefore, the saying of General Ganning was Zhongxian people refers to his hometown Wuning county was once called Linjiang county, which belongs to Zhongxian nowadays; while the saying of he was Wanzhou people refers to his home town was Ganning plain in Ganning village which now belongs to Wanzhou district.
Ganning;; Linjiang county; Wuning county; Ganning town in Wanzhou
K878.2
A
1009-8135(2017)05-0001-07
2017-06-15
程地宇(1945—),男,重慶萬州人,重慶三峽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文藝美學、文化學。
三峽研究 欄目主持人:滕新才
主持人語:“鼙鼓聲喧震地來,吳師到處鬼神哀!百翎直貫曹家寨,盡說甘寧虎將才。”三國名將甘寧(?—220)故里何處?重慶市三峽文化研究會首任會長程地宇教授以古稀之齡,跋涉書海,甄淘文獻,確認甘寧將軍籍貫之臨江并非縣治所在地今重慶忠縣,而是今萬州區甘寧鎮,既有南宋地理名著《輿地紀勝》明文記載為依據,又有甘寧壩、甘寧洞、甘寧村等古跡為依托,言之鑿鑿,考辨精詳,所謂“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丑枝”是也。李俊教授深挖白居易忠州刺史任內所著詩文,無論勤政恤民的恪于職守,還是閑暇時光的種草賞花,都是其“外服儒風,內宗梵行”人格的真實反映,折射出一代詩人羈縻僻鄉的心路歷程。“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為學亦當如此恬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