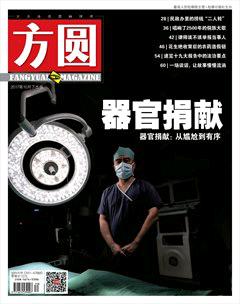等器官的人
毛亞楠
“等到了器官就有希望,等不到,一兩天的時間內,就是天上地下的選擇”,朱志軍告訴《方圓》記者。
“他還不是完全深度的昏迷”,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友誼醫院普外科肝移植病區的示教室內,病人家屬小聲對醫生說著,語氣里透著試探,她看著醫生,似乎是想從對方那里聽到些鼓勵和寬慰的話。
“我們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但確實,像病人病這么重的情況,做手術的風險會比較大,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七十,所以你們要考慮好”,主任醫師朱志軍這樣說。
“主要他還是有希望的”,病人的家屬又說,她指的是那個“已知的肝源”,通過聽醫生之間的討論,她判斷出這個肝源很可能來自河北石家莊。
但朱志軍心里清楚,手術到底能不能做,要視供體那邊的情況而定,而這個環節里變數太多。作為一名從事器官移植30多年的醫生,他太了解病人和病人家屬現在的這種焦灼心境了。
前段時間,朱志軍救治過一名來自云南的肝衰竭患者,病人50多歲,病情要比現在這個病例還重,“肝和腎的功能都不行了,當地醫院放棄了對他的治療”。但病人的家屬沒放棄,聯系到了這里來,聽到朱志軍說有一半的救治希望,不想再等下去的家屬索性花費50萬元包了架飛機,帶著病人從昆明一路飛過來。幸運的是,那個病人最終等到了救命的肝源,被救了回來。
“等到了器官就有希望,等不到,一兩天的時間內,就是天上地下的選擇”,朱志軍告訴《方圓》記者。
這種焦灼又殘酷的等待,發生在每一家可以進行器官移植的醫院里。
根據國家衛計委2013年公布的數據,中國每年大約有30萬人在生死邊緣排隊等候器官移植,但只有1萬余人能通過器官移植獲得新生,等待者和器官捐獻者之間的比例是30∶1。不僅如此,死神留給病人們的時間并不多,“腎衰竭患者尚可通過血液透析的方式多等一段時間,但肝衰竭患者在疾病嚴重時最多只能等2周,即使是病情穩定的肝衰竭患者,最多也只能等3個月”。
“活著真難”
2015年,一部名叫《活著》的電影獲得了第9屆FIRST青年電影展學生競賽單元的最佳紀錄片獎、二十三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紀錄長片以及第六屆中國紀錄片學院獎最佳大學生作品。片子記錄的是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腎移植科病房里那些等待腎移植的尿毒癥病人及其家庭的群像。該片讓人們了解到,腎衰竭病人對于移植器官的熱望及其焦灼的生存狀態。
2017年5月,在北京東城區Camera Stylo的小型放映室內,十幾名觀眾觀看了這部影片,并與導演馬倩雯進行了映后的交流。馬倩雯告訴《方圓》記者,她是在中國傳媒大學讀研拍畢業作品期間,看了一則有關器官移植的新聞,才打算走近這個群體的。
電影中,“希望與失望交替,絕望與振作循環”。新的一批腎源來了,護士站外排滿了準備抽血化驗的病人們。因為都了解那種難挨的心境,病友們會因為同伴配型成功而高興,同時也會因為自己沒能配上而沮喪萬分。
患者劉坤鵬表面堅強,實則被一次次配型失敗折磨得脆弱不堪。“掰著腳趾頭我都想不到我會到這一步”,劉坤鵬對著鏡頭說。沒得病前,他是躊躇滿志的創業青年,患上尿毒癥后,他親手將公司關門,流著淚把所有材料當廢品賣了,“說實話捅我兩刀都沒那難受”。“我終于能歇著了”,他這樣安慰自己。住到了醫院后,劉坤鵬和病房里的病友一樣,一邊做著透析一邊等能夠配得上的器官,從此過上了這種“天天盼望幸運之神降臨在自己身上”的生活。
未等到移植器官之前,做透析可以保命。可一位移友(已做完移植手術的人)曾如此感嘆,“那種看著血從管子里流進身體里的感覺,沒有經歷過,就從來不會覺得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是多么幸福的事”。
病人透析的痛苦,馬倩雯親眼見證過,“兩根很粗的針頭扎進去,通過一根針把全身的血液和其中的廢物從身體里抽出來,再通過另一根針把透析機過濾好的血液重新輸回身體內部。他們隔一天就要去透析一次,一透就透四個小時,這種頻率能把病人‘扎瘋,因此日常工作得不到保障,生活也都全部打亂。不僅如此,這個過程還伴有各種并發癥的可能。有的人透著透著就出現高血壓或心臟病,更有嚴重者透析時出現并發癥當時就躺在床上不行了。而換腎對他們來說也許是最好的選擇”。
可透析和換腎花費昂貴,能讓任何一個普通家庭“一夜回到解放前”。病人付強不忍母親年紀大了還要在醫院伺候她,故意和母親賭氣,從病房里出走,想讓她早點回家。傷心的母親對著眾人訴說,“我現在看見大街上要飯的人我都覺得可羨慕”。
14歲尿毒癥男孩宋萬里的媽媽和劉坤鵬一樣開朗愛笑,是病房里少見的暖色。可是夜深人靜的時候,心事重重的女人坐在醫院走廊里對著鏡頭笑著笑著卻哭了,她說她“不能倒下”,她的兒子聰明,怕拖累家里,已經好多次想要放棄治療選擇死亡,她必須在兒子面前強裝出輕松的樣子,以求兒子不要放棄自己。
病人元輝一家實在等不下去,在被醫生告知當時不是做手術的最佳時機的情況下,選擇在那個春節前做了親體移植手術,由父親捐腎給元輝。但術后,父親的腎在元輝體內出現了排異,面臨著被摘除的危險。這就意味著,如果不能重新激活,父親寶貴的腎只能從他體內摘除然后丟棄。在得知這個消息后,情緒崩潰的元輝母親傷心不已,她認為是自己的心急讓兒子陷入險境。整個家庭因兒子患病而灰暗,絕望的她曾跑到自己母親的墳前哭了整整一個上午。
“活著真難”,這話出自患者白潛鄖之口,換腎后肺部急性感染,白潛鄖再也沒能醒來。他終于結束了那段換腎后排異身體痛苦的日子,卻拋下了始終沒放棄自己的妻子還有可愛的兒子,以及換腎所產生的一大筆債務。endprint
馬倩雯知道白潛鄖去世的消息,是在一次紀錄片放映交流會上,有個觀眾問及這些病人的現狀,馬倩雯回說,“有一些已經做過了移植手術,情況都還不錯”。幾乎是同時,她感覺手機在口袋里震了一下,下場時一看,收到的是關于“白潛鄖追悼會”的通知短信,“當時整個人就蒙在了那里”。白潛鄖的去世對馬倩雯的打擊很大,“好幾個月都緩不過來”。
所以她現在很怕突然接到他們的電話,“不跟你聯系,就說明沒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對于他們來說,No news is good news(沒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馬倩雯說。
協調員的故事
“親眼看到一個人能救卻因為等不到器官而沒辦法救”,這是身為肝移植醫生的吳平最難接受的事情。2000年的時候,他的很多病人都因等不到救命的器官,而一個一個痛苦地死去。2003年,拿到一筆贊助基金的吳平選擇去美國匹斯堡大學器官移植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訪問學者,在那里,他了解到國外器官捐獻體系的運作。
吳平介紹,與國內器官捐獻主要做“因病死亡”的情況不同,美國做“因傷死亡”的情況較多,因為意外死亡的健康身體是最理想的器官移植源。而國外的駕照不僅是開車的執照,也是一份自愿的器官捐獻書。在美國,申領駕照時便會進行器官捐獻意愿登記,如果駕駛員遭遇交通事故,經醫生診斷死亡成立后,醫院便可按照死者的意愿處理器官。
然而在中國,考慮到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社會影響,剛剛起步的器官捐獻工作采取了比西方更為嚴格幾近苛刻的方針——一項捐獻行為的實施需要所有的直系親屬(公民父母、配偶及成年子女)的一致同意,哪怕捐獻者生前曾經在紅十字會登記成為器官捐獻的志愿者。
因此,親人家屬的意見成了影響中國實際器官捐贈的最重要因素。2010年,衛生部和中國紅十字會共同啟動了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首批人體器官協調員應運而生,肩負起了和潛在捐獻者的家庭進行溝通的核心工作,也承載著等候移植器官的患者們的希望。
2014年,吳平正式成為友誼醫院OPO(器官獲取組織)中的一員,擁有了除肝移植醫生以外的第二個身份——器官捐獻協調員。他開始與各家醫院建立聯系,期待各家醫院的醫生們能夠在發現潛在捐獻者的時候,及時通知到他。
“做起了器官協調員才知道,這活不好干,當醫生是人家請求著我做事情,而協調員卻是滿地求著人家,讓人家來同意捐獻。但不做這工作又不行啊,沒有肝源病人們怎么辦?”吳平向《方圓》記者坦陳。
吳平太了解肝移植的緊迫性了,“終末期肝衰竭病人的生死就在幾天的時間里,而慢性肝硬化的病人如果等不到器官,就只能看著他們一點點慢慢沒了,這個過程對病人來說太痛苦了”。所以吳平拼命地到處跑,“某個醫院的大夫一來電話,我們協調員就會過去,幾點打電話幾點就走,凌晨兩三點外出那是常事”。有媒體甚至計算過,器官移植協調員的車子一年下來有10萬公里左右,“在路上”是常態。
當現代醫療手段已無法挽救那個病人的生命,協調員們需要及時地介入,在合適的時間段里,慢慢開啟這個并不輕松的話題。“介入的時機很重要,太快了家屬們肯定接受不了,因為他們需要時間去接受這個事實。但也不能太慢,因為器官捐獻的各項手續都需要走嚴格的流程,太慢了則影響移植器官的質量。”
而在時機未到之前,協調員能做的只有等待,在這等待的每分每秒里,供體的病情變化、家屬的態度以及移植器官的質量,都是擺在協調員面前的變量。
“有死者的家屬7天內改了6次主意”,吳平感嘆說,而因為病情過重導致器官失效的情況,也不乏其例。印象深刻的一次,為等一個腦出血病人的簽字家屬,吳平從中午12點一直等到了第二天的凌晨,到最后卻只等來了一句“我們不捐了”。
這些年的器官移植協調工作,吳平總結,往往面對那些已知“器官移植概念”的人們,他們最后同意捐獻的可能性會更高。前些日子,友誼醫院一個來自貴州的3歲苗族孩子在等待肝源的過程中死亡,孩子的家屬在悲痛之余表示,“因為自己清楚等待中的那種煎熬的滋味,愿意將孩子完好的兩個腎捐贈出去,希望能救到別的孩子。也希望能通過這種方式,延續孩子的生命”。
“以生命為禮物,點燃他人重生的期待。從捐獻那刻起,按下‘停止的生命,開始重新啟動”,吳平告訴《方圓》記者,這是眾多等待故事里,最讓他受觸動的一個。
用親人的器官去救另一個親人的生命
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COTRS系統),是中國器官捐獻體系的關鍵系統。該系統嚴格遵循國家分配政策,執行無人為干預的自動供受者匹配過程,實現公平、公正、公開的器官分配。而當取到“公民死亡捐獻同意書”簽字的協調員將器官信息錄入這個系統后,系統分配程序啟動,一條或多條等待的生命將獲得新生。
但是,一個月前,在友誼醫院肝移植科病房內,因為血型不匹配,新來的肝源卻救不了燦燦(化名)的生命。燦燦的媽媽張巖(化名)心急如焚,決定自己給女兒捐肝,做親體肝移植手術。但是從準備倫理材料、提交倫理委員會到上交到衛計委等審批,完成這個流程最快也要一周的時間,可燦燦的病情卻已經不起等待。
張巖怎么也沒想到,先天性膽道閉鎖,這個每8000至14000個新生兒中僅會發生一例的可怕病癥會出現在自己的女兒身上。主治醫生告訴《方圓》記者,“膽道閉鎖的病因目前不是特別明確,得這種病的患兒最后的表現為肝功能衰竭,肝移植是最好的治療方案”。
等審批的那段時間,張巖感覺“女兒的生命像是在一天天燃燒”,因膽紅素過高,孩子身上已經有了出血點,且肝性腦病的癥狀也出現了,“意識不清,處于半昏迷狀態,即使她睜著眼睛也不看你,你叫她她也聽不見”。平日里,醫生不僅要給燦燦用藥,還需要給她灌腸,燦燦的肚子就脹著,特別大。已經渾身蠟黃色的孩子,從白天哭到晚上,難受地拼命含著張巖的乳頭,試圖在母親懷里尋找安全感。心力交瘁的張巖四天沒合過眼,精神也處于崩潰的邊緣。endprint
所幸3天后,通過醫院的加急處理,做親體肝移植手術的審批終于下來了。張巖和燦燦被推進了手術室,順利地做成手術。因為燦燦的情況比較嚴重,術后的她在ICU里住了半個多月的時間。如今,剛出來不到一個星期的孩子,又因抵抗力太低,感染上了肺炎。
7個半月的燦燦又瘦又小,體重從術前的14公斤,降到了現在的5.9公斤。除了咳嗽,她還在發著燒,為了給她降溫,張巖把病床上鋪滿了水袋。和做過肝移植手術的病人一樣,燦燦的腹部留下了兩道“奔馳標”一樣的疤痕,兩條管子仍插在她的身體里,一條是從腹部出來的引流管,另一條是從脖間穿到深靜脈里的輸液管。因為隔一天要抽一次血,燦燦的大腿和腳上已全是瘀青,小小的她現在還對痛覺不太敏感,但張巖總覺得,“有病的孩子要比正常的孩子懂事些,因為她一看到白大褂就哭”。
所有抗排斥藥物都要磨碎了沖水,再用喂藥器給燦燦喂進去。得了這種病,燦燦終生都要服藥。未來的生活是張巖能想象得到的,“孩子稍大一點吃藥肯定會哭,還會面臨各種并發癥的可能”。
術后的張巖一直肝區疼痛,在操勞孩子的同時,一起陪床的丈夫不忘每天給她后背按摩。因為孩子這病,這個家庭開始了“車輪戰”的生活,“倒班”休息的地點則是醫院對面的賓館。這種一直住賓館的狀態,要持續到孩子身體恢復好,能夠出院的那天。
燦燦鄰床的病友是一個從河北來的2歲男孩,最近因代謝病做的肝移植手術。肝移植術后,即便是出了院也要求每周一次復查,那些在北京沒有家的病人家屬們,幾乎都選擇了在醫院附近租房子住。家里人得了這樣的病,意味著一輩子都離不開醫院,比起那些日日都很艱難生活的人們,張巖感覺自己的情況要好得多,所幸自己和丈夫在北京有家、有體面的工作,孩子的病雖負擔沉重,但于他們而言還算能支付得起。
據《方圓》記者了解,雖然目前腎移植的術前和術后、肝移植的術后都已納入醫療保障,但這些費用對于貧困家庭來說,仍舊是不能承受之重。
幸運的人
兩年前,中國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獻成為唯一合法來源的政策令一些人感覺“中國器官移植的冬天來了”。有等不及的病人抱怨,“寫在紙上的法律反而簡單”,在紀錄片《活著》里,病人們也不止一次表達出這種不安的情緒。
“當然不能用樂觀的狀態去比較病人們的‘忍受”,吳平說,但他對中國的器官捐獻與移植現狀做出了客觀的評價,“大概在2003年的時候,一個外國人在國內死去,要求捐獻出自己的器官,我們這邊卻幾乎不知道這個概念,也不清楚是怎樣一個程序。而如今,在我們如此人口基數的大國里,每年器官捐獻的數量已經從開始僅有的十幾例,上升到了九千多例”。
“而比起以前,現在的等待者們等到器官的希望更大了。一方面,隨著器官捐獻宣傳工作的進行,國人對器官捐獻認知的提升,我國成功捐獻的案例幾乎呈每年翻一番的速度,且將來還會更多;另一方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造器官的功能越來越完善,未來會更好地解決人體器官短缺這個問題。”吳平告訴《方圓》記者。
在309醫院全軍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石炳毅的辦公室內,《方圓》記者了解到,國內腎移植率比2015年增加了28.1%,而截止到2017年6月30日,腎移植率又比2016年上半年上升了21.6%。這意味著半年內已做了4956例腎移植手術。“如果是呈這樣一個上升速度的話,今年也許有望達到1萬例左右”,石炳毅告訴《方圓》記者,近兩年器官移植在數量上發展迅速。
樂觀數據的背后,是幸運的降臨。在清華大學后勤部工作的呂宏杰,覺得自己就是那個“幸運的人”。56歲的他剛做完肝移植手術,“幾乎一天也沒有等”。
4月里的一天,呂宏杰住進中國人民解放軍302醫院,醫生告訴他需要等合適的肝源再做手術,“最多要等3個月的時間”。從醫院里回來,擔心等不到肝源的呂宏杰打算多去幾家能夠做肝移植的醫院排隊。可讓他想不到的是,下午4點多回到家里,他就接到了302醫院的電話,通知他當天晚上去住院,準備第二天一早的手術。
呂宏杰當時就有些蒙,“沒想到能這么快”。手術后他打聽,原來這個肝源本來匹配給另一個女患者,但女患者體重較大,供體器官的大小與其不匹配,此器官源又退回到網上做重新分配,而依據器官分配的“就近原則”,適合移植條件的呂宏杰最后做成了手術。“看來我和這肝有緣”,呂宏杰說。
現在,正在恢復身體的呂宏杰在家靜養。通過熟人的介紹,他加入了一個器官移植受者的微信群,經常和群里的“移友”們互動。移友們都來自北京肝移植受者聯誼會,聯誼會會長李祖澄,也曾在十幾年前接受過肝移植手術,到現在身體很棒,國慶節之前,李祖澄還組織了移友們去朝鮮旅游。
呂宏杰感謝這次人生偶然的饋贈,能夠讓他走向新生。但有時他也會“胡思亂想”,“怕術后會發生感染,也怕長期服藥的身體出現一些并發癥”。就在上個月,一個比他早一個星期做成移植手術的病友因膽管阻塞去世,這樣的消息時刻影響著他脆弱的神經,“還是一切看命吧,我如果能活得像李祖澄那樣,也就值了。”呂宏杰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