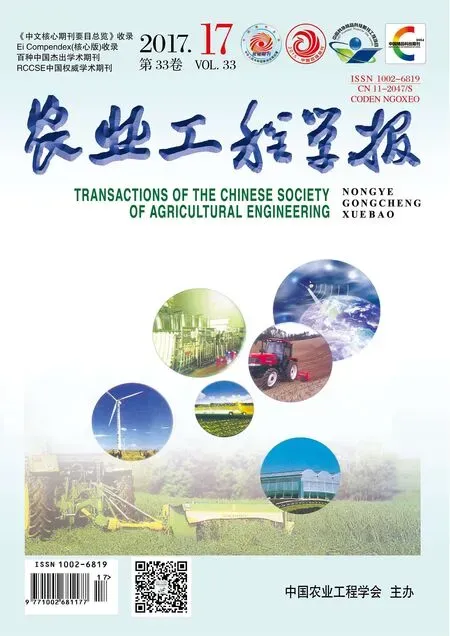陜北黃土區退耕前(1976—1997)坡面切溝發育特征
陳一先,焦菊英,,魏艷紅,趙珩鈧
?
陜北黃土區退耕前(1976—1997)坡面切溝發育特征
陳一先1,焦菊英1,2※,魏艷紅1,趙珩鈧2
(1. 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楊凌 712100;2.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研究所,楊凌 712100)
以陜北黃土區坊塌流域內7條大切溝及其谷緣上的小切溝為研究對象,通過ArcGIS和MATLAB從基于1976、1997年1:10 000比例尺地形圖生成的數字高程模型(DEM)上提取溝沿線,進而獲得1976、1997年大切溝的面積、周長和大切溝上小切溝溝頭前進距離,并結合當時的土地利用圖和植被覆蓋圖,定量研究了退耕前陜北黃土區切溝發育的速率,以及土地利用類型和植被覆蓋度對切溝發育的影響。結果顯示:在1976-1997年間,7條大切溝的面積、周長增長率分別為11.01%~180.46%和8.07%~86.75%,大切溝上小切溝溝頭年均前進速率為0.26~0.84 m;由溯源侵蝕導致的小切溝溝頭前進是研究區內大切溝上的主要侵蝕方式,大切溝溝谷拓寬和形成新的小切溝分別是對大切溝的面積和周長增長具有較高貢獻率的侵蝕方式;林草覆蓋能控制切溝發育,集水區內覆蓋度大于65%的植被能更加有效地控制大切溝內以溝谷拓寬為主的、多過程、多部位的綜合切溝侵蝕,覆蓋度大于45%的植被能更加有效地控制大切溝上小切溝溝頭的溯源侵蝕。研究表明基于GIS技術和不同年份的地形圖,可以確定切溝侵蝕的方式及速率,實現對切溝發育的動態監測。
土地利用;侵蝕;植被;切溝;溝沿線;退耕還林(草)
0 引 言
切溝是小流域中常見的溝蝕形態,主要發育于溝間地與溝谷地的過渡地帶上[1]。切溝的侵蝕過程復雜,朱顯謨[2]基于溝道的切割規模、縱剖面與所在坡面一致與否、溝床表面特征等指標,將切溝侵蝕劃分為小切溝、中切溝和大切溝三個發育階段。其中,大切溝寬、深均在20 m以上,其縱剖面與所在坡面有顯著差別,橫剖面呈U字形、V字形或梯形;小切溝以柵狀、放射狀或枝狀發育于大切溝的谷緣上,在三個發育階段中最為常見,其縱剖面與所在坡面基本一致,溝寬約1~5 m、深以2~3 m最為常見,橫剖面一般呈U字形或V字形[2-4]。切溝侵蝕通過溝頭溯源侵蝕,溝底下切與側蝕,溝坡沖淘、崩塌、滑坡、瀉溜等作用形式,不斷加劇土壤侵蝕[5],使土地變得支離破碎,造成土地退化[6],影響農業生產[7],惡化當地及下游的生態環境,是流域主要的土壤侵蝕方式之一[8]。黃土高原農地型小流域切溝侵蝕產沙量約占流域總產沙量的60%~90%[9]。然而,中國對切溝侵蝕的研究起步較晚[10],且當時監測技術手段有限,導致對坡面退耕前切溝侵蝕研究集中于切溝形態的描述和發育階段的劃分[2-4,11],而對切溝發育及其影響因子的定量研究很少,從而限制了切溝侵蝕方面的研究,導致對切溝侵蝕規律的認識不足,成為流域土壤侵蝕預報的瓶頸之一。
近年來,切溝侵蝕監測方法與技術不斷發展,從傳統的卷尺、插釬、地形測針儀等實地測量方法[12-14],發展到高精度GPS、遙感影像、三維激光地形測量、攝影測量等新興技術[15-18]。加之近年來DEM的廣泛應用,使得研究退耕前的切溝形態特征和發育速率成為可能。學者們通過GIS技術,基于DEM,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提取溝沿線。湯國安等[19]根據黃土地貌坡面坡度轉折特征,提出基于坡面朝向的溝沿線形態判別提取方法,該方法提取的溝沿線精度較高,能較好地反映空間溝沿線分布的真實情況。周毅等[20]依據黃土坡面形態特征及匯流特點,提出溝沿線柵格點約束上游匯水面積的正負地形分割方法,進而得到溝沿線,該方法人工干預少,提取的面積精度較高,在不同地貌類型區均有很好的應用適宜性。晏實江等[21]依據黃土坡面的坡度轉折性質,引入邊緣檢測算子,提取并連接溝沿線候選點,同時借助數學形態學方法濾除細碎線段,獲得精度較高的溝沿線。溝沿線提取方法的不斷改進,為準確、深入地研究退耕前切溝發育提供了數據基礎。同時,切溝發育受到一系列影響因子的作用,包括地形地貌、土壤性質、氣候、土地利用和植被覆蓋等[22-23]。其中,土地利用通過影響切溝集水區的產流特征來影響切溝發育[23],不同土地利用類型對徑流的攔蓄作用不同[24],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會導致土壤滲透性降低和徑流流速增大,從而增加地表產流和增大徑流剪切力,加速溝蝕進程[23,25]。植被對控制切溝發育的作用可歸納為:一方面,地表植被和枯枝落葉通過攔截降雨,減輕濺蝕[26],同時,降低徑流速度,減小其剪切力[27];另一方面,根系通過改良土壤,增加入滲,減少徑流,同時,根系固結土體,增強土壤抗蝕性[28]。因此,土地利用和植被覆蓋被看作評價切溝侵蝕的關鍵因子,其作用甚至被認為比氣候對切溝發育的影響更為重要[29]。為此,本文通過收集早期的地形圖、土地利用圖和植被覆蓋(NDVI)圖等資料,基于GIS技術提取切溝1976和1997年的溝沿線,估算切溝發育速率,分析土地利用類型和植被覆蓋度對切溝發育的影響,以期為研究區的切溝防治及退耕還林(草)工程的生態效益評價提供依據。
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位于陜西省安塞縣坊塌流域,地理位置為109°14′42″~109°16′59″E、36°46′21″~36°49′30″N,流域面積8.67 km2,平均海拔1 210.9 m。屬于暖溫帶半濕潤氣候向半干旱氣候的過渡地區,年平均氣溫8.8 ℃。根據安塞縣氣象站的觀測數據,1976-1997年年平均降雨量為520.54 mm,其中年降雨量最大值為668.9 mm(1983年),最小值為275 mm(1997年);1978、1983、1990和1996年降雨量均超過600 mm;6-9月降雨量占全年的70%以上,以暴雨為主。植被屬于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區向草原區過渡的森林草原植被[30]。土壤類型主要為黃土母質上發育的黃綿土,顆粒組成以粉粒為主,土質疏松,極易被分散和搬運[31]。流域呈現出溝谷密集、地面起伏率大和土壤侵蝕劇烈的典型梁峁狀黃土丘陵地貌特征。土壤侵蝕以水力侵蝕為主,其次是重力侵蝕。梁峁坡以片蝕、細溝侵蝕和淺溝侵蝕為主,溝坡以切溝侵蝕、沖溝侵蝕、懸溝侵蝕和滑坡、崩塌等重力侵蝕為主[32]。
本研究利用樣帶法在坊塌流域內隨機設置一貫穿整個流域的樣帶,從樣帶上選取7條大切溝(圖1),以大切溝及其谷緣上的小切溝作為研究對象。大切溝的基本信息見表1,其中,溝谷區為溝沿線所圍成的閉合區域,集水區為溝沿線以上至分水嶺間的區域[1]。

圖1 大切溝在研究區內分布圖

表1 大切溝基本信息
2 材料與方法
2.1 數據源及預處理
本研究所用的數據源包括來自陜西省測繪地理信息局的1976、1997年1:1萬比例尺地形圖,來自黃土高原科學數據共享平臺的1980年30 m分辨率和2000年1∶10萬比例尺土地利用圖,來自中科院水利部水保所的1978-2000年分辨率為30 m的多年平均植被覆蓋圖。其中,1980、2000年土地利用圖分別根據Landsat4-5MSS和Landsat4-5TM、Landsat7ETM遙感影像,通過室內監督分類解譯,結合野外實地調查編制而成;植被覆蓋數據基于Landsat1-3 MSS(1978-1983年)和Landsat4-5 TM(1984-2000年)遙感影像計算得到,選用1978-2000年間每年8月20日前后的影像代表研究區當年度植被覆蓋最大的時期[33],對影像進行輻射校正、幾何精校正、大氣校正等預處理后,計算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進而得到1978-2000年多年平均植被覆蓋(NDVI)圖。雖然1999年開始全面退耕還林(草)導致坊塌流域土地利用和植被覆蓋逐漸發生變化,但2000年處于退耕早期,可認為當時流域內的土地利用和植被覆蓋與退耕前相比尚未發生明顯變化,且因為退耕前的基礎數據缺乏,能收集到的與本研究起止年份(1976年1997年)最接近的數據就是1980、2000年的土地利用圖和1978-2000年多年平均植被覆蓋圖,因此,本文通過1980、2000年的土地利用圖和1978-2000年多年平均植被覆蓋圖來反映研究區研究期間的土地利用和植被覆蓋特征。
利用ArcGIS 10.2軟件對所有圖層數據進行WGS 1984坐標系轉換和橫軸墨卡托投影;之后在ArcGIS 10.2中對地形圖進行幾何變換,再對等高線進行數字化和賦高程值,并在完成后檢查和糾正可能存在的漏線、串線、斷點、未賦值、賦錯值等情況,以確保數字化的精度;然后由數字化的等高線生成不規則三角網(TIN),再由TIN生成空間分辨率為5 m×5 m的DEM;最后,對DEM進行填洼處理,得到無洼地的DEM,用于提取切溝溝沿線。
2.2 切溝參數提取
考慮到生成的DEM空間分辨率為5 m×5 m,難以用于準確提取小切溝的溝沿線,所以本文以大切溝為單位提取溝沿線,研究其面積和周長變化。同時,因為小切溝發育于大切溝的谷緣上,其溝沿線是大切溝溝沿線的一部分。雖然大切溝溝沿線上呈現的小切溝可能存在誤差,但其為基于相同規格的基礎數據,并由同一技術人員在相同工作環境中利用相同的技術提取得到,因此可認為其具有近似的系統誤差,所以本文在研究大切溝面積和周長變化的基礎上,還研究了大切溝上小切溝溝頭前進的相對距離。
2.2.1 大切溝溝沿線提取
參考晏實江等[21]的DEM邊緣檢測溝沿線提取方法,利用ArcGIS 10.2和MATLAB R2010a軟件對溝沿線進行提取。首先,調用MATLAB軟件中的高斯-拉普拉斯(laplacian of gaussian,LOG)算子對填洼后的DEM進行邊緣檢測(設定閾值為0.001)[21],提取突變邊緣;然后,在ArcGIS軟件中基于地形圖結合目視解譯識別出突變邊緣中屬于溝沿線的部分,并對其進行連接和數字化,初步得到切溝的溝沿線。為進一步提高溝沿線的精度,對于少量存在的邊緣檢測未能提取出溝沿線、提取結果較破碎或存在偏移的部位,參考當年度地形圖上等高線的走勢進行手動勾繪和校正,得到完善后的溝沿線。在ArcGIS中根據溝沿線劃分出大切溝的溝谷區和集水區兩類面狀圖層[1,34-35],分別用于計算大切溝的面積、周長和從土地利用圖層上裁剪出各集水區范圍內的土地利用情況。
2.2.2 大切溝面積和周長變化及小切溝溝頭前進距離計算
利用ArcGIS 10.2,分別計算1976和1997年各大切溝溝谷區的面積和周長,進而得到各大切溝的面積變化和周長變化。根據大切溝溝沿線上蜿蜒的形態、規模和分布,結合朱顯謨[2]對小切溝的定義,判別出其中屬于小切溝的部分。然后在ArcGIS 10.2中將2期大切溝溝谷區圖層進行疊加,根據2期圖層上小切溝的位置和輪廓相似程度,判別不同時期的2條小切溝是否為同一切溝,然后利用Measure工具測量兩期溝谷區圖層上同一小切溝的溝頭頂點間距離作為小切溝溝頭前進距離。
2.2.3 土地利用類型和植被覆蓋度獲取
在ArcGIS 10.2軟件中,利用大切溝集水區圖層對土地利用圖層進行裁剪,獲得大切溝集水區的土地利用類型,分別計算各集水區內各土地利用類型的面積比例。考慮到土地利用圖中只劃分出林地、草地和耕地3種土地利用類型,為進一步獲得土地利用的具體信息,于2014年7月對大切溝集水區研究期間的土地利用情況進行了實地走訪。
借助ENVI 5.3軟件,基于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計算大切溝集水區內每個像元的植被覆蓋度,公式為[36]

式中f為植被覆蓋度,%;NDVI為每個像元的NDVI值;NDVIsoil為裸土的NDVI值,即無植被像元的NDVI值;NDVIveg為植被的NDVI值,即純植被像元的NDVI值。
為了消除NDVI數據噪聲所固有的誤差,取5%分位數對應的NDVI值為NDVIsoil,95%分位數對應的NDVI值為NDVIveg[34]。計算出各集水區的植被覆蓋度后,參考Li等[37]對植被覆蓋度分級的方法,利用ArcGIS將其按≤10%、≤15%、≤20%、≤25%、≤30%、≤35%、≤40%、≤45%、≤50%、≤55%、≤60%、≤65%、≤70%、≤75%、≤80%、≤85%劃分為16個等級,統計各等級的像元數量,并結合像元的空間分辨率(30 m×30 m),計算各等級植被覆蓋的面積,進而得到其占大切溝集水區面積的比例。
2.3 數據分析
利用SPSS 18.0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用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比較不同大切溝上小切溝溝頭前進距離的差異。各等級植被覆蓋占大切溝集水區面積比例、大切溝面積增長率、大切溝上小切溝溝頭前進距離之間的關系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進行分析,差異顯著性水平為=0.05。
3 結果與分析
3.1 切溝發育特征
1976和1997年研究區內7條大切溝的面積增長和周長增長見表2。其中2、4、7號大切溝的面積增長率相對較大,分別為50.70%、119.72%、180.46%;3、6號大切溝相對較小,分別為38.07%和11.01%。2、3、7號大切溝的周長增長率相對較大,分別為58.99%、46.32%、86.75%;1、6號大切溝相對較小,分別為18.69%和8.07%。1、4、5號大切溝的面積增長率大于3號大切溝,但周長增長率小于3號大切溝。

表2 1976-1997年大切溝的面積和周長變化
將1976和1997年2期大切溝溝谷區圖層進行疊加(圖2),可以看出1976-1997年期間,7號大切溝同時存在溝谷拓寬、小切溝溝頭溯源侵蝕和形成新的小切溝3種侵蝕方式,1、4號大切溝則以溝谷拓寬和小切溝溯源侵蝕為主,2、5、6號大切溝以小切溝的溯源侵蝕為主,其中5號大切溝也存在微弱的溝谷拓寬。3號大切溝以形成新的小切溝為主,因此其周長增長率大于1、4、5號大切溝,而其面積增長率小于1、4、5號大切溝,是因為1、4、5號大切溝均發生溝谷拓寬。綜上所述,小切溝溝頭溯源侵蝕是研究區內大切溝上的主要侵蝕方式,而大切溝溝谷拓寬和形成新的小切溝則分別是對大切溝的面積和周長增長具有較高貢獻率的侵蝕方式。

圖2 1976-1997年大切溝溝谷區變化
根據疊加分析的結果,1976-1997年1~7號大切溝內因溯源侵蝕而發生溝頭前進的小切溝數量分別為28、24、14、12、27、29和4條,溝頭前進平均速率分別為0.35±0.20、0.68±0.66、0.39±0.44、0.56±0.77、0.36±0.27、0.26±0.22和0.84±0.16 m/a。如表3所示,2、4、7號大切溝上小切溝的溝頭前進距離明顯大于其他4條大切溝(0.05)。

表3 1976-1997年大切溝上小切溝溝頭前進距離
注:不同字母表示小切溝溝頭前進距離有顯著差異(P<0.05)。
Not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head forward distance of small gullies (<0.05).
3.2 土地利用變化對切溝發育的影響
選定的7條大切溝1976和1997年集水區各土地利用類型面積比例如表4所示。

表4 1976和1997年集水區土地利用類型變化
在1976年至1997年間,1、6號大切溝集水區內草地面積比例減少,2~5號大切溝集水區草地面積比例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增加,但其中2~4號在1976年時均沒有草地,7號大切溝集水區則在研究期間一直沒有草地。林地方面,7號大切溝集水區的林地面積比例增加最多,2號次之,3號最少,其他大切溝的集水區在研究期間均無林木覆蓋。1、5、6號大切溝的集水區在研究期間始終具有一定比例的草地,相應地,其面積增長率低于2、4、7號大切溝。雖然3號大切溝集水區的林草地面積增加比例很小,但通過實地走訪得知,研究期間該集水區的耕地類型主要為梯田,可有效減少坡面徑流產生[38],從而減輕徑流對溝頭的沖刷,所以3號大切溝上小切溝溝頭前進距離小于2、4、7號大切溝,但高于1、5、6號大切溝,是因為梯田僅分布在梁峁頂部,對整個坡面上徑流的攔蓄作用有限。然而,3號大切溝的面積增長率稍低于1、5號大切溝,是因為研究期間1、5號大切溝均發生了溝谷拓寬。
根據實地走訪得知,退耕還林(草)工程正式實施以前,研究區的耕地已開始逐漸撂荒,待其自然演替,當時還未全面栽種刺槐、檸條、沙棘等水土保持喬灌木樹種,導致所選大切溝的集水區內林地普遍較少,這期間草本植物便為影響切溝發育的主要植被類型。同時,可以看出,梯田也能控制切溝發育,但其作用大小視梯田規模及其在坡面的分布位置而定。
3.3 植被覆蓋對切溝發育的影響
將各等級植被覆蓋占大切溝集水區的面積比例與大切溝面積增長率和大切溝上小切溝溝頭前進平均距離分別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見表5。大切溝面積增長率和大切溝上小切溝溝頭前進平均距離分別在植被覆蓋度≤65%和≤45%的區間內,均與植被覆蓋面積比例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0.05),而當植被覆蓋度分別處于≤70%和≤50%的區間時,則均開始呈現顯著負相關(0.05),且此后隨著植被覆蓋度的不斷增大,大切溝面積增長率和大切溝上小切溝溝頭前進平均距離始終與植被覆蓋的面積比例保持顯著的負相關(0.05)。說明集水區內覆蓋度大于65%和45%的植被分別能更加有效地控制大切溝的面積增長和大切溝上小切溝的溝頭前進。結合上文大切溝面積增長主要由其溝谷拓寬引起,此外大切溝上小切溝的溝頭溯源侵蝕和溝谷擴張也有具一定的貢獻,而大切溝上小切溝的溝頭前進則主要由溯源侵蝕引起,可進一步得出集水區內覆蓋度大于65%的植被能更加有效地控制大切溝內以溝谷拓寬為主的、多過程、多部位的綜合切溝侵蝕;而覆蓋度大于45%的植被能更加有效地控制大切溝上小切溝溝頭的溯源侵蝕。因為涉及的侵蝕過程和部位更多,所以能更有效地控制大切溝內綜合切溝侵蝕的植被覆蓋度也更大。

表5 大切溝面積增長率和小切溝溝頭平均前進距離與集水區植被覆蓋度的相關系數(n=7)
Note: *,<0.05.
4 討 論
本研究通過比較由2期地形圖提取的溝沿線,估算陜北黃土區1976-1997年切溝發育的速率,其中大切溝面積年增長率為0.51~8.39%,均值3.21%;大切溝上小切溝的溝頭前進年平均速率為0.26~0.84 m,均值0.49 m。李鎮等[34,37]基于QuickBird影像估算出晉西北黃土區2003-2010年切溝年均面積增長率為0.07~1.35%,均值0.47%;溝頭前進年平均速率為0.36~0.44 m,均值0.40 m。本文結果明顯大于上述研究結果,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黃土高原地區自1999年實行全面退耕還林(草)以來,植被覆蓋度顯著增加,有效地控制了切溝發育。本文得出能更有效地控制大切溝內綜合切溝侵蝕的植被覆蓋度需大于65%,而劉斌等[39]發現,在黃土高原地區,植被覆蓋度大于60%時,其消減土壤侵蝕的作用明顯;李鎮等[34]得出晉西北黃土地區集水區植被覆蓋度大于60%時,其抑制切溝發育的效果更加突出。是因為上述2位學者的研究中林地面積比例占優,而本研究區內草地面積比例占優,但草地的攔泥蓄水作用不及同等覆蓋度下的林地[40]。這也解釋了為什么7號大切溝在研究期間初期可能因小流域治理(安塞縣1979年7月5日開始全縣推行小流域治理,進行飛播造林種草約7 000 hm2)[41]而進行了“退耕還林”的前提下,集水區林草地面積比例從1976年時均為0,增加至1997年林地面積比例高達99.88%,但其切溝侵蝕仍最為劇烈。是因為林木生長前、中期未能達到一定的覆蓋度,不能較有效地發揮徑流攔蓄作用[39]。本研究表明黃土高原地區坡面土地利用、植被覆蓋度影響切溝發育的速率,林、草覆蓋均能控制切溝發育,且集水區內覆蓋度大于65%和45%的植被分別能更加有效地遏制大切溝和其谷緣上小切溝的發育,這為實施退耕還林(草)等措施防治切溝侵蝕提供理論依據。
退耕前,由于技術手段有限、基礎數據缺乏,導致對切溝發育的研究很少,當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切溝形態的描述和發育階段的劃分[2-4,11]。本文利用地形圖定量研究了陜北黃土區退耕還林(草)以前1976-1997年間的切溝發育速率和發育方式,明確了退耕前切溝侵蝕特征,對于補充退耕前切溝侵蝕定量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隨著目前切溝侵蝕監測技術的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已開始定量獲得退耕后黃土高原地區切溝侵蝕的狀況[10,15,17-21,34,39],但沒有詳細的退耕前切溝侵蝕數據來與之進行比較,因而無法深入評價退耕還林(草)工程對切溝防治的生態效益。而本文對于退耕前切溝侵蝕速率與侵蝕方式的確定,能為退耕還林(草)工程對切溝防治的生態效益評價提供重要參考。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根據分辨率更高的DEM、遙感影像,結合實地測量,監測退耕還林(草)前、后不同時空尺度上的切溝發育速率,揭示不同地區切溝的動態發育過程。同時,根據本文的分析結果,由溯源侵蝕導致的小切溝溝頭前進是研究區內大切溝上的主要侵蝕方式,且不同大切溝間小切溝溝頭前進距離差異明顯,這可能與局部地形特征有關,如坡長、坡度、集水區面積的不同,導致產流特征及徑流能量不同[35,42],從而引起切溝發育差異。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這些地形因子對切溝發育速率的影響。此外,降雨是黃土區切溝發育的主要驅動力[22],土壤是切溝侵蝕的受體,土壤性質影響切溝侵蝕發生的臨界剪切力[43]。本研究7條大切溝之間的距離都在3.6 km以內,降雨、土壤性質等因素的空間差異較小,因而沒有考慮其對切溝發育的影響。但在未來的研究仍有必要根據黃土高原不同地區的降雨、土壤性質,結合地形、土地利用和植被覆蓋等因子,探明不同地區的切溝發育特征及其主要影響因子。
5 結 論
利用GIS技術和1976、1997年1:1萬比例尺的地形圖對陜北黃土區7條大切溝及其谷緣上的小切溝的發育速率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
1)1976-1997年,7條大切溝的面積、周長增長率分別為11.01%~180.46%和8.07%~86.75%,大切溝間小切溝溝頭前進年平均速率為0.26~0.84 m。由溯源侵蝕導致的小切溝溝頭前進是研究區內大切溝上的主要侵蝕方式,大切溝溝谷拓寬和形成新的小切溝分別是對大切溝的面積和周長增長具有較高貢獻率的侵蝕方式。
2)黃土高原地區林草覆蓋能控制切溝發育,集水區內覆蓋度大于65%的植被能更加有效地控制大切溝內以溝谷拓寬為主的、多過程、多部位的綜合切溝侵蝕;而覆蓋度大于45%的植被能更加有效地控制大切溝上小切溝溝頭的溯源侵蝕。
3)通過對比基于GIS技術從退耕前不同年份地形圖上提取的溝沿線,可以確定切溝侵蝕的方式及速率,結合當時的土地利用圖和植被覆蓋圖,可實現對退耕前切溝發育的動態監測及研究土地利用和植被覆蓋對切溝發育的影響。
[1] 伍永秋,劉寶元. 切溝、切溝侵蝕與預報[J]. 應用基礎與工程科學學報,2000,8(2):134-142.
Wu Yongqiu, Liu Baoyuan. Gully, gully erosion and prediction[J]. Journal of Basic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00, 8(2): 134-14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 朱顯謨. 黃土區土壤侵蝕的分類[J]. 土壤學報,1956,4(2):99-115.
Zhu Xianmo. Classification on the soil erosion in the Loess Plateau[J]. Acta Pedologica Sinica, 1956, 4(2): 99-11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 劉元保,朱顯謨,周佩華,等. 黃土高原坡面溝蝕的類型及其發生發展規律[J]. 中國科學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集刊,1988(1):9-18.
Liu Yuanbao, Zhu Xianmo, Zhou Peihua, et al. The laws of hillslope channel erosion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n Loess Plateau[J]. Memoir of NISWC, Academia Sinica, 1988(1): 9-1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4] 羅來興. 劃分晉西、陜北、隴東黃土區域溝間地與溝谷的地貌類型[J]. 地理學報,1956,22(3):201-222.
Luo Laixing. A tentative classification of landforms in the Loess Platea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56, 22(3): 201-22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5] 景可. 黃土高原溝谷侵蝕研究[J]. 地理科學,1986,6(4):340-347.
Jing Ke. A study on gully erosion on the Loess Plateau[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986, 6(4): 340-34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6] Eitel B, Eberle J, Kuhn R. Holocene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e Otjiwarongo thombush savanna (Northern Namibia), evidence from soils and sediments[J]. Catena, 2002, 47(1): 43-62.
[7] 于章濤,伍永秋. 黑土地切溝侵蝕的成因與危害[J].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39(5):701-705.
Yu Zhangtao, Wu Yongqiu. Causes and damages of gully erosion in black land[J].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03, 39(5): 701-70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8] Poesen J, Hooke J M. Erosion, flooding and channel management in Mediterranean environments of southern Europe[J]. 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 1997, 21(2): 157-199.
[9] Li Y, Poesen J, Yang J C, et al. Evaluating gully erosion using137Cs and210Pb/137Cs ratio in a reservoir catchment[J]. Soil and Tillage Research, 2003, 69(1/2): 107-115.
[10] 李鎮. 黃土高原切溝發育監測方法與侵蝕模型研究[D]. 北京:北京林業大學,2015.
Li Zhen. Study on Monitoring and Modelling Gully Erosion on the Loess Plateau[D]. Beijing: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201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1] 陳永宗. 黃河中游黃土丘陵區的溝谷類型[J]. 地理科學,1984,4(4):321-327.
Chen Yongzo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gully in Hilly Loess Reg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984, 4(4): 321-32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2] Capra A, Scicolone B. SW—Soil and Water: Ephemeral gully erosion in a wheat-cultivated area in sicily (Italy)[J]. Biosystems Engineering, 2002, 83(1): 119-126.
[13] Couper P, Stott T, Maddock I. Insights into river bank erosion processes derived from analysis of negative erosion-pin recordings: observations from three recent UK studies[J].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2002, 27: 59-79.
[14] Casal? J, López J J, Giráldez J V. Ephemeral gully erosion in southern Navarra (Spain)[J]. Catena, 1999, 36(1): 65-84.
[15] Wu Y Q, Cheng H. Monitoring of gully erosion on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 using a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J]. Catena, 2005, 63(2/3): 154-166.
[16] Vrieling A, Rodrigues S C, Bartholomeus H, et al.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of erosion gullies with ASTER imagery in the Brazilian Cerrado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2007, 28(12): 2723-2738.
[17] Li Z, Zhang Y, Zhu Q, et al. A gully erosion assessment model for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based on changes in gully length and area[J]. Catena, 2017, 148: 195-203.
[18] Liu K, Ding H, Tang G, et al. Detection of catchment-scale gully-affected areas using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 o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J]. 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2016, 5(12): 238.
[19] Tang G A, Xiao C C, Jia D X, et al. DEM based investigation of loess shoulder-line[C]//Geoinformatic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s and Photonics, 2007: 67532E-67532E.
[20] 周毅,湯國安,王春,等. 基于高分辨率DEM的黃土地貌正負地形自動分割技術研究[J]. 地理科學,2010,30(2):261-265.
Zhou Yi, Tang Guoan, Wang Chun, et al. Automatic segmentation of loess positive and negative terrains based on high resolution grid DEMs[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30(2): 261-26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1] 晏實江,湯國安,李發源,等. 利用DEM邊緣檢測進行黃土地貌溝沿線自動提取[J]. 武漢大學學報·信息科學版,2011,36(3):363-367.
Yan Shijiang, Tang Guoan, Li Fayuan, et al. An edge detection based method for extraction of loess shoulder-line from grid DEM[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11, 36(3): 363-36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2] Valentin C, Poesen J, Li Y. Gully erosion: Impacts, factors and control[J]. Catena, 2005, 63(2): 132-153.
[23] Chaplot V, Giboire G, Marchand P, et al. Dynamic modelling for linear erosion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 climate and land-use changes in northern Laos[J]. Catena, 2005, 63(2/3): 318-328.
[24] Galang M A, Markewitz D, Morris L A, et al. Land use change and gully erosion in the Piedmont region of South Carolina[J].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07, 62(3): 122-129.
[25] Lal R. Soil erosion impact on agronomic productivity and environment quality[J]. Critical Reviews in Plant Sciences, 1998, 17(4): 319-464.
[26] Torri D, Poesen J. A review of topographic threshold conditions for gully head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J]. Earth Science Reviews, 2014, 130(2): 73-85.
[27] Collison A J C. The cycle of instability: Stress release and fissure flow as controls on gully head retreat[J]. Hydrological Processses, 2001, 15(1): 3-12.
[28] De Baets S, Torri D, Poesen J, et al. Modelling increased soil cohesion due to roots with EUROSEM[J].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2008, 33(13): 1948-1963.
[29] Poesen J, Nachtergale J, Verstraeten G, et al. Gully eros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mportance and research needs[J]. Catena, 2003, 50(2/3/4): 91-133.
[30] 周萍,劉國彬,侯喜祿. 黃土丘陵區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土壤團粒結構分形特征[J]. 中國水土保持科學,2008,6(2):75-82.
Zhou Ping, Liu Guobin, Hou Xilu. Fractal features of soil aggregate structure under different land use in the Hilly-gully region of Loess Plateau[J]. Scienc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08, 6(2): 75-8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1] 姚文藝,陳界仁,秦奮. 黃河多沙粗沙區分布式土壤流失模型研究[J]. 水土保持學報,2008,22(4):21-26.
Yao Wenyi, Chen Jieren, Qin Fen. Study on the distributed forecast model of soil loss in sandy areas of Yellow River[J]. 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08, 22(4): 21-2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2] 鄭粉莉,高學田. 黃土坡面土壤侵蝕過程與模擬[M]. 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
[33] 鐘莉娜,趙文武. 基于 NDVI 的黃土高原植被覆蓋變化特征分析[J]. 中國水土保持科學,2013,11(5):57-62.
Zhong Lina, Zhao Wenwu. Detecting the dynamic changes of vegetation coverage in the Loess Plateau of China using NDVI data[J]. Scienc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13, 11(5): 57-6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4] 李鎮,張巖,姚文俊,等. 基于QuickBird影像估算晉西黃土區切溝發育速率[J]. 農業工程學報,2012,28(22):141-148.
Li Zhen, Zhang Yan, Yao Wenjun, et al. Estimating gully development rates in Hilly Loess Region of Western Shanxi province based on QuickBird images[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2, 28(22): 141-14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5] 張巖,楊松,李鎮,等. 陜北黃土區水平條帶整地措施對切溝發育的影響[J]. 農業工程學報,2015,31(7):125-130.
Zhang Yan, Yang Song, Li Zhen, et al. Effect of narrow terrace on gully erosion in Northern Shaanxi Loess area[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5, 31(7): 125-130.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6] Qi J, Marsett R C, Moran M S,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s of vegetation in the San Pedro River basin area[J]. Agriculture and Forest Meteorology, 2000, 105(1/2/3): 55-68.
[37] Li Z, Zhang Y, Zhu Q K, et al. Assessment of bank gully development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o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J]. Geomorphology, 2015, 228: 462-469.
[38] 姚云峰,王禮先. 水平梯田減蝕作用分析[J]. 中國水土保持,1992,3(2):40-41.
Yao Yunfeng, Wang Lixian. Analysis of effects of bench terraced field on reducing soil erosion[J].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1992, 3(2): 40-4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9] 劉斌,羅全華,常文哲,等. 不同林草植被覆蓋度的水土保持效益及適宜植被覆蓋度[J]. 中國水土保持科學,2008,6(6):68-73.
Liu Bin, Luo Quanhua, Chang Wenzhe,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ntage of vegetation cover and soil erosion[J]. Scienc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08, 6(6): 68-7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40] 焦菊英,王萬中,李靖. 黃土高原林草水土保持有效蓋度分析[J]. 植物生態學報,2000,24(5):608-612.
Jiao Juying, Wang Wanzhong, Li Jing. Effective cover rate of woodland and grassland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J]. Acta Phytoecologica Sinica, 2000, 24(5): 608-61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41] 陜西省情網,安塞縣志. http://www.sxsdq.cn/sqzlk/xbsxz/ sxdyl/yas_16203/asxz/.
[42] 陳永宗,景可,蔡強國. 黃土高原現代侵蝕與治理[M]. 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
[43] Smerdon E T, Beasley R P. Critical tractive forces in cohesive soils[J].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1961, 42(1): 26-29.
Characteristics of gully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Hilly Loess Region before Grain-for-Green Programme (1976-1997)
Chen Yixian1, Jiao Juying1,2※, Wei Yanhong1, Zhao Hengkang2
(1.,,712100,;2.,,712100,)
Gully erosion is a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 and the primary source of sediment loss on the Loess Plateau.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ed technologies and approaches for monitoring gully, most of the early studies focused on the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of gully morphology and the division of gully development stages, confining the advancement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for gully erosion and leading to insufficient knowledge about gully erosion.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quantitatively estimate the gully development rates as well as assess the effect of land use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in upslope drainage area on gully development over 1976-1997 period, after which the Grain-for-Green Programme had been completely implemented since 1999. The study area was in Fangta watershed in Ansai County (109°19’E, 36°52’N),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Shaanxi hilly loess region. Seven large gullies, as well as the small gullies which occurred along the large gullies, were selected along a transect placed randomly and throughout Fangta watershed. ArcGIS and MATLAB software were used to obtain boundary lines of the selected large gullies based on the DEM (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rived from topographic maps at the scale of 1:10000 in 1976 and 1997. By applying LOG (Laplacian of Gaussian) edge detection approach in MATLAB, the gully boundary lines were initially extracted;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boundary lines, visual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morphology reflected by contour line was conducted in ArcGIS. According to the gully boundary lines, the area and perimeter of large gully and the head retreat distance of small gullies within each large gully in 1976 and 1997 we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Details about land use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historical maps of land use and vegetation cover,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ates of area and perimeter development of the 7 large gullies from 1976 to 1997 ranged from 11.01% to 180.46% and from 8.07% to 86.75%, respectively, and the mean head retreat distance of the small gullies within a large gully varied from 0.26 to 0.84 m/a. Head retreat of small gully caused by headward erosion was the dominant erosion form presented within a large gully in study area. In addition, valley widening and forming new small gullies forming could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area and perimeter development of a large gully, respectively. Forest and grass coverage were both helpful to control gully development, especially when vegetation coverage exceeded 65% in upslope drainage area, which was more effective for controlling multiple erosion processes that simultaneously took place in a large gully, in which valley widening was mainly involved, as well as headward erosion and sidewall expansion of small gully. However, vegetation coverage exceeding 45% in upslope drainage area could only control the headward erosion of small gully effectively. Terrace could also control gully development and its efficiency depended on scale and position of terrace on the slope.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forms and rates of gully erosion can be determined based on GIS technology and topographic map, accomplishing the monitoring of gully dynamic development before implementing the Grain-for-Green Programme.
land use; erosion; vegetation; gully; gully boundary line; Grain-for-Green Programme
10.11975/j.issn.1002-6819.2017.17.016
S157.1
A
1002-6819(2017)-17-0120-08
2017-04-16
2017-08-31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41371280);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課題(2016YFC0501604)
陳一先,博士生,主要從事切溝侵蝕監測研究。楊凌 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712100。Email:chenyixian14@mails.ucas.ac.cn
焦菊英,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流域侵蝕產沙、土壤侵蝕與植被關系及水土保持效益評價研究。楊凌 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712100。Email:jyjiao@ms.iswc.a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