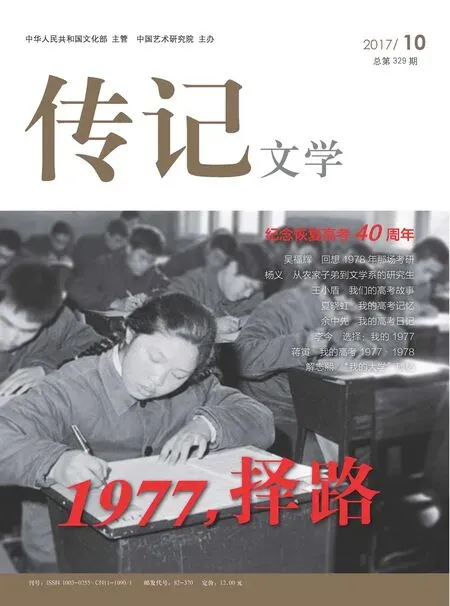我的高考1977·1978
蔣 寅
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我的高考1977·1978
蔣 寅
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上圖:2009年,作者在揚州大學正門前留影
人生總有一些改變命運的機會,很多情況下機會出現時我們都意識不到。但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1977年恢復高考,卻是大多數人都清楚意識到的一個機會。在農村插隊的,在農場務農的,在工廠上班的,乃至于游蕩在社會上的,所有年輕人都意識到,一個改變我們命運的機會正在降臨。
高考,上大學,雖然未來的前途尚不分明,但將擺脫目前的處境,走上一條充滿希望的路,則是確信無疑的。在所有不滿于現有處境、希望改變命運的年輕人面前,一扇門突然打開,一個通過考試獲得學習機會并進而實現各種理想的古老的歷史傳說再次成為現實。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像唐朝武則天推行科舉制時一樣,頃刻間被歡欣所激動,被夢想所陶醉。
我已記不起是怎么知道恢復高考招生的消息,當時似乎也沒有特別地振奮。因為我當時的境遇還算不錯。1976年高中畢業,適逢江蘇修改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規定。原本規定老大必須先插隊或插(農)場,下面的孩子才能留城,新規定改為家庭可以選擇先下或先留。我早已做好下鄉的準備,但臨了不知道是當時人們固有的對政策的不信任,還是父母對社會變革的先見之明,促使他們將我先留了下來。畢竟妹妹小我五歲,誰也不知道五年內會發生什么。這樣,我就在1977年5月參加工作,被分配到江蘇儀征造船廠工作。這比起插隊、插場來,已是很讓人羨慕的境遇,更何況我還很喜歡自己的工作。
造船廠屬于交通局,我的檔案材料經過局里時,被認為文字通順,書寫工整,有關部門想留我在局里做文秘。有人認識我父親,轉達此意,征求我的意見。在旁人看來,這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兒啊,但我卻不樂意。我生性好動不好靜,一想到成天坐在辦公室里,那多枯燥無聊啊,覺得還是船廠的工作有意思。檔案材料到了船廠,又出現同樣的情況,廠里也想把我留在廠部,做點文字工作。我再次要求下車間,最后如愿被分配到金工車間,做了一名鉗工。
和其他工廠的鉗工相比,船廠的鉗工是比較有意思的。平時工作沒多少高精尖的技術活兒,卻會旁通電焊、冷作、電工甚至開車、刨、銑床的本事,裝水管和拆裝、修理柴油機則是基本技能。日常工作主要是給拖輪安裝機動裝置,恰好趕上裝一條19米拖輪,每天跟隨師傅按圖紙加工零件,上船安裝,直到整條船裝完,開出去試航,周期差不多整一年。這種每天內容不同、不斷變化的工作顯然較適合我的性格。雖然寒冬酷暑、日曬雨淋,工作也相當辛苦,但并不覺得疲勞和厭倦,上班時一空下來就操練基本功。據說鉗工學徒三年滿師,要考銼六角,沒事就鋸一段圓鋼銼著玩。一年下來,我可以不用尺,光憑眼睛看,銼出極規準的六角,用游標卡量每邊差距在四絲以內——一根頭發絲是七絲左右!如果不讀大學,我相信三年滿師時我會是一名優秀的鉗工。當時我的理想確實就是成為一名像我師傅吳志軍那樣的技術最好的鉗工。
船廠的業余生活也很豐富,一起進廠的青工湊成了一支籃球隊。為參加縣職工籃球賽,我們自己平土拉碾,整出一個籃球場,每天下班后訓練。雖然第一次比賽成績欠佳,但我們的訓練熱情有增無減。我中學球隊的教練是縣體委工作人員,揚州地區職工籃球聯賽時還推薦我去擔任裁判,參加過二級裁判資格考試。應該說,以籃球為中心的業余生活是相當快樂的,工作中也沒有覺得知識不夠用——中學的工業基礎知識(相當于物理)課,已足夠應付一般鉗工能用到的簡單計算,甚至機械制圖也能對付(不知現在的中學生能否掌握)。無論從哪方面說,考大學對我來說都不是特別有誘惑力、特別令人鼓舞的事。但我獲知恢復高考的消息時,心頭還是涌起去試一試的沖動。因為我隱隱覺得文學是可以學習的東西。
青春與寫作是天然相連的。在那個年代,喜愛文學的青年更是無人不想當作家。許多人回憶高考經歷,都說在當時,讀大學就等于讀中文系,而讀中文系就是要當作家。我倒沒有這樣的意識,文學對我來說還是個很朦朧的東西,作家更是遙不可及的存在。
我出生在一個化肥世家,爺爺、父親都曾在南京化學工業公司工作,兩位姑姑和一些表姐表弟也都在化肥廠工作。因此我填家庭成分從來都是工人,其實我父親是高級工程師,雖然沒上過大學,卻能看英語資料,還懂點日語,那是讀中學時留學生任教和日據時皇民教育的結果。他是獲得化工部獎勵的對中國化肥工業有貢獻的技術人員。我母親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女中,曾是上海學聯籃球隊(相當于今天的青年隊)的控球后衛,可以保送上海體育學院,卻一心要考復旦新聞系,終因家庭成分的緣故不能錄取。她很喜歡看小說,從我記事起家里總有許多小說。即使在“文革”中,她也總能從不知道什么地方借來各種翻譯小說,多數是舊版的蘇聯和東歐作品,還有一些內部印行供批評用的材料,記得有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和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等。在中學時代,我已讀過很多中外小說,包括現代文學史上大量被定為“毒草”的作品,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歐陽山的《三家巷》《苦斗》,馮德英的三《花》,茅盾的《蝕三部曲》,至于《平原槍聲》《烈火金剛》《鐵道游擊隊》《林海雪原》《野火春風斗古城》《艷陽天》《金光大道》這些就更不用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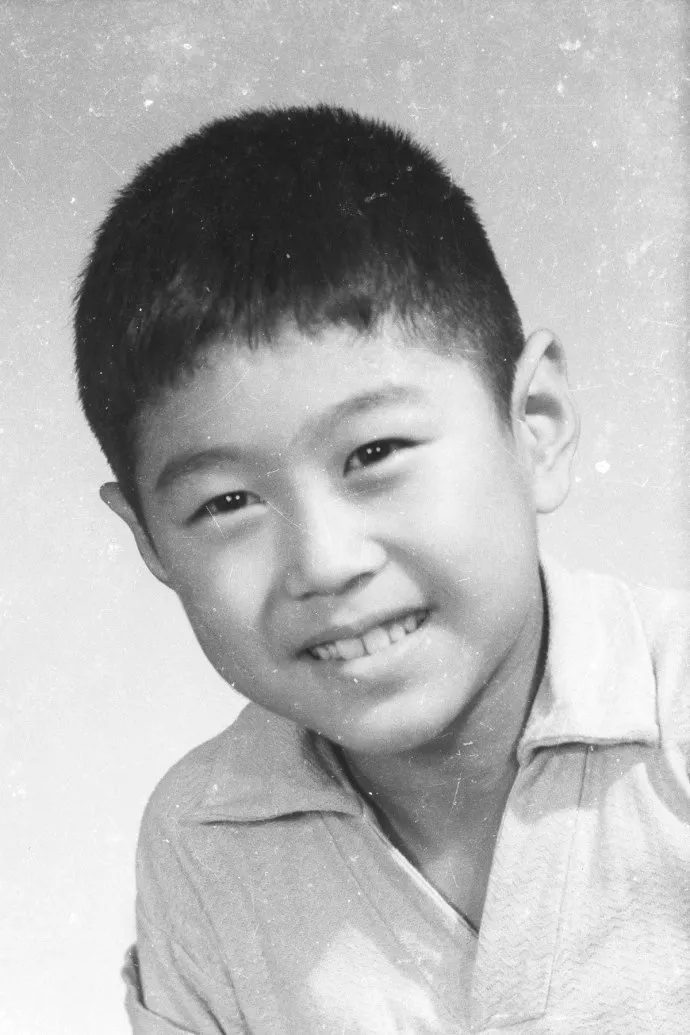
作者小學照片
我們這一代人的中小學教育,雖然很不正規,卻也有個好處,就是課余沒作業,有大把的時間自由閱讀,喜歡讀書的孩子也可以滿腹經綸。盡管缺乏真正的美育,但背誦毛澤東詩詞、老三篇、五篇哲學著作,唱語錄歌、樣板戲,看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聽鋼琴協奏曲《黃河》,總算也接觸到詩詞、文章、戲劇、音樂,不至于白紙一張。同輩中大概許多人都能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從頭唱到尾,比起現在的孩子也算了解一點京劇唱腔。對文學和藝術的這種非正常的接受方式,最終卻熏陶了我們對文學的興趣,這真是匪夷所思!
我從小除了讀小說外,也很喜歡聽故事。父母單位里有一位南京知青非常會講故事,夏天納涼時孩子們都圍坐聽他講當時流行的手抄本故事。他還是個紅學迷,常講《紅樓夢》的話題,我也因此將《紅樓夢》讀得很仔細。后來我雖不研究紅學,但有時與研究紅學的朋友聊天,故意問一些冷僻的問題,比如賈蕓的父親叫什么名字,他們也答不上來。
我對詩詞發生興趣,是在1976年高中畢業后,偶然在同學家看到一冊王力先生的《詩詞格律十講》,借回家照著詩詞格律作詩填詞。沒多久進工廠,午休時沒事,借一些詩詞方面的書來讀。第一部就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編的《李白詩選》,對李白的喜愛便從那時候開始。將近體詩格律弄清楚后,又將《考證白香詞譜》中的詞調都抄在一個小筆記本上,全部標畫出平仄,等于自己編了一本用⊙●○符號標記的詞譜。這么讀著讀著,對古典詩詞的興趣越來越濃。到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第一個念頭就是考中文系。中文系也是當時最熱門的志愿,就像王安憶說的:“我的那個年代,最好的人才都是讀中文系的。”我并不覺得自己是優秀人才,只是很想學文學。
可是沒想到,我填志愿卻遇到了挫折。由于父親在“文革”中歷經折磨,覺得文學就是舞文弄墨,搞大批判,寫大字報,堅決反對我報考文科,無奈之下我只得選理工科,第一志愿報大連海運學院的船舶設計與制造專業,這當然是出于對造船的熱愛。
儀征瀕臨長江,當時有兩個船廠,儀征造船廠隔壁還有一個南京航運公司的保養廠,俗稱南京船廠,后來成為著名詩人的唐曉渡就是南京船廠的工人。他是我小學籃球隊隊友的哥哥,認識但不熟悉,臨考試時在上班途中偶遇,交流了一點填志愿的信息。我很羨慕他報考了南京大學中文系。他畢業后分配到《詩刊》社任編輯,成為有名的詩人和評論家,我在七年后才成為他的系友。
1977年的高考,江蘇分兩次進行,初考只是語文、數學兩門,后來知道110分為及格線,合格再參加統考。我讀中學時數學成績雖也不錯,但畢竟沒學到什么東西。初考兩門總分勉強夠線,數學成績終究偏低。招生辦老師來電話,建議我統考時改考文科,正合我意,立即著手復習文科。不料臨近考試時,招生辦又緊急告知,文理不能轉科,我還是必須考理科。結果可想而知,統考數學成績更低,總分不夠線,名落孫山。
經過初試,我已確知數學成績不可能好,落榜實在意料之中,倒也不至于太氣餒,心里只想著如何補好數學。班照常上,復習都用業余時間,晚上和節假日。七七級入學甫定,七八級的考試又在眼前。那時考大學對全社會來說是個新鮮事兒,也是大事兒,全廠好像只有兩個人考,廠里對我倆也很優待,在臨考前一段時間準許我們休假備考。
這一次我決意不再聽家里的意見,非考文科不可,父親看我數學確實不行,只好由我。第一志愿填報復旦大學中文系,是要實現母親當年的夙愿。第二志愿是南京大學中文系。那時候中文專業可選院校很少,我又很怕當老師,只揀非師范專業的學校填,甚至報了遼寧財經學院師資班,其實也是師范性質,但我并不清楚。就這樣六個志愿還是填不滿,實在無可選,最后填了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鑒于去年歷史、地理兩門合一張試卷,題目也不難,我就沒怎么復習史、地,所有時間都花在了數學上。結果本年史、地分為兩張卷子,內容多出許多,我毫無準備,都只考了72分,數學拼命補習半年多,也僅得46分,總分343。語文和政治各考多少已記不清,語文更高些,應該是80多分。想想這個分數真不知道是怎么得來的,因為我記憶中從來沒好好學過語文課。
說起來,我的中小學義務教育,經歷頗為曲折,說是九年制,實際讀了十二年。因為父母雙職工,家里沒人照看,我5歲就上小學。“文革”開始時已讀二年級,所以全過程都記得很清楚。在江蘇六合縣讀到小學四年級,趕上學制改革,六年制改為五年制,本應升五年級的我們被退回三年級,結果重讀了三、四年級!這個匪夷所思的結果說起來沒人相信,連我自己也一度懷疑是不是記憶有誤,后來遇到一個在江蘇讀書的同齡人,證實情況確實如此。讀到五年級,隨父母調動工作遷居儀征,將要畢業又逢教育制度改革,夏冬畢業改為冬季,這樣我小學就讀了七年半!初二時冬季畢業再改回夏季,兩年制初中又多讀半年。到1976年夏天高中畢業時,我的中小學已讀了十二年,正好相當于“文革”前的老學制。為此我常覺得自己也等于是一個“文革”前讀中學的老三屆!
大概因為比別人讀書年頭長,我的中小學成績一直很好,主課考試經常都是100分,后來評分方式改為優、良、及格、不及格四等,就都是優秀。讀小學時我曾是“小紅花”宣傳隊里跑龍套的,當時讀書好點的學生本來就不多,宣傳隊里的文藝尖子更少有成績過得去的。考完試宣傳隊排練,紛紛晾成績單取樂,一蟹不如一蟹,隊長念一個笑一個。這讓我很不好意思晾自己的成績單,可越是忸怩大家越起哄得厲害。當隊長拿到成績單,驚呼:“這家伙三個100!”所有人都不相信,就差把成績單搶撕了。
其實我上課很少認真聽講,經常是看小說,下課看看黑板就知道老師講了些什么。數學有不明白的問問同學便了然,實在是課堂教學的知識量少得可憐。考試也簡單,初中數學課一度曾用口試,每人到老師面前抽三道題,口頭回答一下,我從來都是優秀。高考的數學題,超出我們課本知識很多,我完全不能應付;語文則靠讀了一肚子小說,作文能文從字順,而且卷面整潔無涂改。改錯改病句都無問題,但要說明理由往往講不清楚,因為沒怎么學過語法知識,只憑熟讀小說獲得的語言感覺,80多分怎么得來的只有天知道。
考完之后,自己的感覺還是不錯的,覺得數學沒那么難,很有希望及格;語文也沒什么大失誤,只有歷史、地理不太滿意,后悔沒有認真復習一下,本來可以考得更好一點。整個夏天是在漫長的等待、忐忑的期盼中度過的。每一串自行車鈴聲都會讓我豎起耳朵,屏息靜聽是不是郵遞員的來臨。
錄取通知書終于寄到。拆開招生辦的信函,當看到錄取通知書寫的是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時,我腦袋轟地一下仿佛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腦門上!怎么會是揚州師院中文系?我根本就沒報這個志愿啊!事實上我的總分只夠揚師的分數線,并且我也填了同意調劑。我亂轟轟的腦子稍微鎮定下來,第一反應就是放棄,明年重考。家里倒隨我,說重考就重考。可是父親很快獲知,招生政策規定,凡師范院校錄取不報到的要被取消高考資格。正在糾結中,鄰居一位浙江大學畢業、曾被打成右派的叔叔來串門,說:“本科讀什么大學沒關系,將來肯定要恢復研究生招生的。”這話很觸動我,覺得以后并不只是當老師一條路。于是,懷著對不可知未來的朦朧希冀,我走進了座落在瘦西湖畔的揚州師范學院,開始中文系學生的生活。那是1978年10月,只比七七級晚入學七個月。
后來知道,我們高中七個班,每班考取大學的只有一兩個人,我們班只有我一個。為此我像所有同輩人一樣,萬分珍惜這個機會,每天學習,學習,不倦不懈地學習。
后來將七七級到七九級這三屆稱為新三屆,與公認中學基礎較好的老三屆相提并論,不是沒道理的。新三屆和八○級以后,生源大不相同,風氣也截然異樣。新三屆的學生以往屆生居多,大都是從工廠、農村、農場考上來的,年齡相差也較大。以我們這個年級而言,年紀最大的36歲,最小的16歲。八○級開始以應屆生為主,一入學就談戀愛成風,讀書空氣也淡化許多。我們年級共有四個班,(一)班為老大哥班,年齡都在28歲以上,絕大多數都為人父母;其他三個班都是27歲以下,23歲上下的最多,應屆生沒幾個。同學之間水平差距也很大,(一)班同學中不乏小有名氣的作者、寫過不少劇本的劇團編劇、工作多年的機關干部、教學經驗豐富的中學老師……其他三個班則以知青、工人和民辦教師為主,很少上述成功人士。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都是以第一志愿被揚州師院錄取的。像我這樣沒報揚師而被錄取的,大概少而又少。知道了這一點,不僅沒讓我有半點自得,反而甚覺氣餒。
很快大家就知道,有許多同學是以遠遠高出分數線的總分入學的。雖然當時是先填志愿后考試,無法估量成績,但為求穩妥、以必中為唯一目標,是個重要原因。揚師340分的錄取線已是江蘇本科院校的底線,許多插隊、插場的同學只求考取以改變生活道路,根本就不考慮其他。因此,剛過分數線的我,不用說是班上基礎最弱的學生之一。聽到同學們這個說在寫評論,那個在寫散文,我連散文是什么都不清楚,感覺自己和同學們有不小的差距。不過話也說回來,大家對分數其實都看得較淡,起碼高分入學的同學并沒有表現出什么優越感,相反都一個賽一個地勤奮學習。新三屆區別于八○級以后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都埋頭讀書,不談戀愛,男女生之間沒什么交往,彼此間言語舉止都很拘謹;生活更是簡樸,上街除了買書,基本上沒有下館子吃喝的。
現在回想起來,那一代人的勤奮真是今天的學生難以想象的。
很少有人翹課,沒課時宿舍空無一人,都在圖書館或教室自習。宿舍晚九點五十熄燈,總有些同學在走廊就著昏暗的燈光讀書。雖然興趣各不相同,但似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愛好。有沉迷于哲學的,有熱衷于美學的,有喜愛寫作的,有耽于文學批評的,有用功練書法的,甚至還有對遺傳學感興趣的,經常捧一本《遺傳學報》在看。更多的則圍繞中學語文教學來看書和積累資料,他們多是從中學考來的公辦或民辦教師,將來的理想是成為特級教師。
我剛進學校時學習并無目標,只是瘋狂地讀小說。入學第一個月就看了40多種,大多是以前接觸不到的西歐小說。從雨果開始,司湯達、巴爾扎克、大小仲馬、羅曼·羅蘭、左拉、狄更司、馬克·吐溫……轉眼到二年級,我得知研究生恢復了招生。這點燃了我心底的愿望,同時在漫無目的的閱讀中,我也慢慢發現自己的興趣還是在古典文學方面。偶然看到社科院系統招聘助理研究員的消息,也曾怦然心動,但終究對外語毫無信心而作罷。
我中學時英文學得還算認真,曾擔任英語課代表,畢業后就再未看過。高考時外語只是參考科目,不計入總分,很多人都棄考。我考是考了,卻不曾復習,28分竟然名列班級亞軍,考38分的第一名是下鄉一直堅持學英語的一位老大哥。從獲知研究生恢復招生起,我就鉚足勁兒準備考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了解到日本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比較發達,便跟著電臺剛開播的日語廣播講座學日語。1981年秋,系里通知七八級可以同七七級一起報考碩士研究生,我們年級共有4個同學報考,最后3人考取。我第一志愿報考南京大學程千帆先生,未被錄取,調劑到第二志愿廣西師范學院,三年后再考程先生的博士生,終得立雪門下,從此成為一名古典文學研究者。雖然我從高中畢業后就自學詩詞格律并嘗試寫作,但進入揚師中文系才是我學習文學的正式開始,我對古典文學的興趣也是讀本科期間培養起來的,和老師們的誘導、鼓勵分不開。

1988年,作者博士畢業照
記得1990年,我和同事也是揚師中文系七七級學長汪暉同被遣往陜西山陽縣“鍛煉”,閑談中回憶起揚師中文系的老師們,好生感慨。那一代老先生的學問之好,絕不亞于任何名牌大學的教授。其中有現代漢語語法體系自成一家而講授古漢語課的李人鑒先生,以王國維美學研究名世的譚佛雛先生,與林散之、高二適、費新我并稱江蘇四老的書法家孫龍父先生,古典文學則有《張溥年譜》和《劉鶚年譜》的作者蔣逸雪先生,《新校元雜劇三十種》的作者徐沁君先生,《唐代揚州史考》的作者李廷先先生,至于任二北先生就更不用說了。我個人則更得趙繼武老師親炙,前幾年我寫過《我的第一位學術蒙師——趙繼武先生散憶》(《文匯報》2013年3月16日)一文,回憶從趙老師受業的往事。
當時我們還不懂得這些先生的學問,多年后自己成為學者,見識過各方前輩,這才知道我們那批老師的學問之好和學風之正。最難得的是他們還葆有舊日學人的風骨,勇于表明自己的學術立場,決不鄉愿趨時。如果說我們這一代學人,對學術還有那么一點信念、一點不隨流俗的崇高感,那是與老師輩的熏陶分不開的。
轉瞬高考迄今已40年,我也從一個文學愛好者成長為一名古典文學研究者和教授。回顧40年間最重要的經歷,高考仍不能不說是改變我們人生軌跡的第一個重要契機。沒有高考,我可能永遠不會走上文學研究之路,體會到職業和興趣合而為一的巨大幸福感。我確實覺得,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于職業能和興趣相重合,工作就是做自己有興趣的事,同時滿足了興趣和謀生的需要。為此,我也像所有同輩人一樣,發自內心地感謝鄧小平同志果斷恢復高考的偉大決定。這一舉措不僅改變了我們一代人的命運,同時也加快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速度。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三屆逐漸成為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并薪火相傳,成為思想、科學和文化上承上啟下的重要橋梁。站在現時回看1977年的高考,感覺就像打開了一扇自由之門,無數優秀人才由此走上社會的重要崗位,使古老的中國重新煥發生機,洋溢著年輕的活力。此后日益高漲的改革開放熱潮、思想解放新風,激發了巨大的創造力,帶來空前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進步,使80年代永遠成為讓人激動不已、深情懷念的時代。近年我越來越多地追懷80年代,那是屬于我們的青春,而對青春的回望只是意味著遲暮的到來。
懷舊從來是老暮的標志,也是過來人獨享的權益。若道未來的歲月無可展望,懷舊足以消遣短暫的時光;而如果確信時間的軌跡仍在延伸,則懷舊的激動也可成為天地回春的一股力量。

2009年,作者在揚州大學任二北先生紀念雕像前留影
責任編輯/崔金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