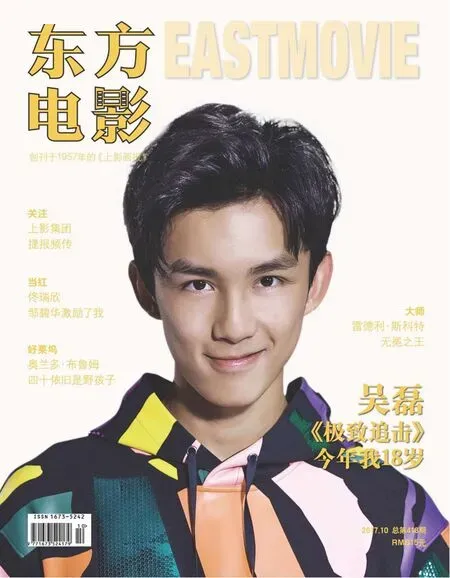雷德利·斯科特無冕之王
文/甘琳
雷德利·斯科特無冕之王
文/甘琳
花費30年才被世界影迷認定為科幻神作的《銀翼殺手》在2017年10月迎來了它的續集系列《銀翼殺手2049》。不再執導筒反而轉型幕后制片人的雷德利·斯科特將如何帶領新晉科幻導演丹尼斯·維倫紐瓦共同打造出一個具有警示意義的銀翼殺手世界,成了全世界影迷期待的焦點。在觀眾心中,雷德利·斯科特早已和《銀翼殺手》緊緊聯系在一起。從影40余年,貢獻了近50余部極富作者風格的類型電影,斯科特能夠當之無愧地接過觀眾獻給他的“無冕之王”的頭銜。
導演剪輯之父
2007年,《蝙蝠俠:黑暗騎士》在香港取景,拍攝前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給他的拍攝班底放的觀摩影片正是《銀翼殺手》。諾蘭給出的理由是:“這就是我們拍《蝙蝠俠》的路子。”1983年,當年輕的詹姆斯·卡梅隆開始制作令自己名聲大噪的《終結者》,他告訴團隊:“有必要或者必須參考《銀翼殺手》的風格。我們這一代導演,都受到了雷德利·斯科特的影響。”然而,在雷德利·斯科特的老家英國,類似肯·洛奇和邁克·李這樣的獨立藝術片導演卻并沒有對斯科特保持太多敬意。面對這樣的“差別待遇”,已經80歲的斯科特早已不再糾結:“如果我是一名喜劇演員,我的工作就是讓你笑。電影最重要的是娛樂性,在創造藝術性的同時,我并沒有忘記‘娛樂’的意義。”
在電影院遇見斯科特的方式有很多,可以在幽閉的宇宙空間站,可以在肆意的羅馬古戰場,甚至也可以在風光醉人的法國普羅旺斯。從業 40余年,斯科特執導的電影幾乎覆蓋了電影的所有類型,在他的電影圖像意識里,我們永遠不會覺得自己已經接近了世界邊緣:古老的埃及大地,摩西率領40萬希伯來朝圣者跨過紅海尋找新的家園;兩名叛逆女旅客駕著寶石藍的雷鳥汽車,在美國大峽谷完成了最后的末日狂旅;2019年陰雨霧霾的洛杉磯夜晚,一個在死亡前吟游的機器復制人重新讓人類認識了人之為人的意義……
不過,十年一個事業起落的斯科特也曾“享受”過被毒舌影評人寶琳·凱爾花費足足3個版面諷刺《銀翼殺手》的待遇,從此之后斯科特更是在媒體放言自己永遠不再看影評。這位更容易被稱作“匠人”而非“藝術家”的導演,總是能在公眾對他熱度減少甚至投之以江郎才盡的定論時反戈一擊,重新刷新輿論對他的認知。1982年上映的《銀翼殺手》是一部被眾多影迷、科幻迷忽略的老片,在拍攝時由于影片過于復雜的內容使他多次與攝制組發生沖突,上映時觀眾也很難接受這部氣氛壓抑、陰郁的影片。剛剛經歷了《星球大戰》這類強烈視聽沖擊的觀眾,很難對這樣一部晦暗的影片產生興趣,最終影片遭到了票房慘敗。直到90年代早期,這部影片在家庭市場中發行,才重新被公認為是一部科幻電影的杰作。2005年斯科特的鴻篇巨制《天國王朝》的上映也備受批評,輿論認為這是一部空有宏大場面的好萊塢膚淺故事。直到二十世紀福斯公司后來推出的導演剪輯版才再一次扭轉了影片的評論風向。多次不被看好,又多次逆轉口碑,“導演剪輯之父”雷德利·斯科特在注重電影娛樂性的情況下不介意人們把他當作匠人導演,但他更愿自謙為一位“用心的匠人”。事實上,每一次導演剪輯版的發行都足以證明斯科特在電影界具有作者論的權威,雖然沒有奧斯卡和“戛柏威”的獎項加持,斯科特在電影史上的地位也足夠被定義為“無冕之王”。

科幻世界的盡頭
人類的智識和好奇在工具理性的規劃和引導下,徹底蘇醒了。高速發展的工業文明讓人類在恪守工具理性的秩序中不斷膨脹自身的可能性,但是工具理性并非一個具有自我調節機制的自洽系統。人的主體性在與外物融合時,文化邊界和肉身邊界的模糊地帶總是會催生出無數的鬼魅的未知。
《銀翼殺手》改編自科幻小說家菲利普·K·迪克的作品《機器人會夢見電子羊嗎?》。菲利普本身就是一個具有中度妄想癥和精神疾病的作者,在他深度妄想、深度睿智、深度恐懼和深度風趣的作品里,偏好把狀況視為走下坡路,而非上坡。斯科特在改編他的作品時,深刻把握了其作品中關于齷齪、腐敗和黑暗面的描寫:每當科學或媒體科技創新延展了人類的感官中樞,它同時也創造了怪物作為人類自身的反面殘像以及魅影回響。銀翼殺手戴克在追捕人造人的過程中越來越喪失人性,而與此同時,人造人卻逐漸顯露出更加人性的一面。最后的人造人羅伊在片中為了抵抗生命流失帶來的痛苦,主動用鋼釘刺穿手掌,暗喻被盯上十字架的耶穌。當戴克即將墜樓時,羅伊用這只被鋼釘刺穿的手挽救了他,暗喻神為救世人而流血犧牲。羅伊代表了復制人的完美,一種遠超人類的神性,他以上帝的憐憫俯視掙扎逃生的人類。
一旦人無法從客觀世界中獲取自身存在的確定性時,這種尋求確定性的努力會發生方向性的改變,即從外部世界轉向了自身,人希望通過制作來塑造一個更加強大、更加可靠的自我,以抵消客觀世界的喪失帶來的不確定,抵御來自自然和宇宙的各種能量的侵襲。但是人又會因為機器在某一方面的優異功能遠超自己而產生強烈的焦慮感。純粹的科技特別是科幻作品里的人造人無法完美嵌合到蕪雜變動的社會生態中,銀翼殺手里的“復制人”只有4年的機器時間,他們的記憶都是被移植的,但他們卻比人還更珍視生命的意義。羅伊在死前的獨白:“我所見過的事物,你們人類絕對無法置信。我目睹戰艦在獵戶星座的端沿起火燃燒。我看著C射線,在唐懷瑟之門附近的黑暗中閃耀。所有這些時刻,終將流失在時光中。一如眼淚,消失在雨中。死亡的時刻到了。”羅伊在詩歌中描繪恢弘的境界,明明比地球上庸庸碌碌的人類更在乎真實的價值。
從《銀翼殺手》的結局看來,人們當時的觀念仍然是趨向于保守和中立的“人類中心”的舊調重彈,盡管對羅伊極盡美學化地造型,但所有的復制人在故事中都最終死去,人類仍然無法完全接受這個超人種賽博格的存在。2017年10月6日,在北美上映的由斯科特監制、《降臨》導演丹尼斯·維綸瓦爾執導的《銀翼殺手2049》延續了斯科特1982年的故事設定。時隔35年,人們是否愿意在社會倫理層面接受賽博格的生命形式,仍然取決于人的自我認知和哲學發展。瑞恩·高斯林飾演的新的銀翼殺手K會如何處理復制人與人類的關系,將會是沉寂了35年的科幻圣作《銀翼殺手》最值得讓人期待的地方。
早期的斯科特繼承了科幻電影與生俱來的“黑色情節”,對未來世界以及廣袤宇宙的外星生命抱有著更多的是恐懼而不是好奇的態度。曾經有記者問他為什么在《異形》里不設置宇航員與異形試圖進行溝通的橋段,斯科特苦笑:“試想如果船員們停下腳步來試圖和異形聊聊,那恐怖氣氛豈不是一下就散了?記住,諾斯托羅莫號的船員們逃命都來不及呢,誰會想著去找怪物溝通啊?而從一開始我們對異形的定位就非常明確—它不會與人溝通,也沒法和它講道理,它只為殺戮而生。”異形從出生開始就是為了無條件的生存,你也許看不到它,卻又絕對無法逃脫它的魔掌。
為了打造真正令人膽寒的異形造型,著重細節和道具設計的斯科特團隊苦尋了幾個月仍無法做出滿意的效果。最終,斯科特在瑞士超現實主義畫家H·R·吉格爾的畫冊《死靈之書》第65頁看到了一個惡魔的肖像:它的面部突出,有一個長長的腦袋。斯科特馬上意識到這就是苦苦尋覓的異形怪物。此外,斯科特還參考了英國老鄉著名畫家弗蘭西斯·培根的一系列作品。培根畫作里三個脖子上面長著大嘴的扭曲人像影響了《異形》最具恐怖色彩的“破胸”橋段,據此制成的破胸幼體模型扭曲丑惡到了極點,它長著滿嘴金屬利齒,可通過扯線和推桿進行操作。
1979年的《異形》里,斯科特設置了三組角色關系:人類、生化人和異形,人類是絕對的主角,影片所聚焦的是女主人公雷普莉如何在異形的攻擊和生化人的背叛下得以幸存下來。而2017年6月在全球公映的《異形:契約》中,斯科特顯然已經不滿足于三組簡單對立的關系,他把敘事的主導線索全部牽連在了邁克爾·法斯賓德飾演的生化人大衛身上。

生化人大衛類似于第一部里的機械人艾什,他們都是技術理性取得主導地位的產物。技術理性的背景下,人們的理性不再是充分地實現理性和真理、充分地發揮個體的潛能、實現真正的自由,而是如何與機器化過程實現協調一致。大衛和艾什都對異形這種在進化論上趨近“完美”的獵食生命體產生了由衷的親近感,這種令人不寒而栗的親切感追根溯源其實又會回到人類的欲望—人類渴望工業標準化“完美”的強力,強力的進化又會反噬人類主體性的特異。甚至,生化人大衛比艾什多出了一項工具理性之外的特性—創造力,他為了創造出完美的獵食生物體不惜獻祭自己的主人肖恩博士。

“工程師族創造了人類隨后又意圖毀滅人類,人類創造了生化人但意欲奴役驅使后者為其服務,生化人則培養了異形并幻想著自己能成為造物主,而處在鏈條最底端的異形卻最兇狠殘暴,可以回過頭來毫不猶豫地毀滅造物主和人類。”人類不再站在物種混戰的金字塔頂端,異形、生化人也不再是以被人類欺凌、奴役的受害者面貌出現。如果說早前《銀翼殺手》里斯科特對復制人的態度還算是曖昧不清,在新一版本的《異形》里,斯科特已經發展出了一個嶄新的宇宙觀:第一部里對霸權企業和科技對社會的完全支配的討論最多還限制在人類社會的生產交際領域,而2017年《異形》的命題已經上升到了關于生命的創造和毀滅的辯證互反關系中了。異形只有寄生人類體內才能生存,并且最終以對母體進行摧毀而完成自己的誕生,異形這個大IP輾轉35年又回到了斯科特的手里。斯科特明顯已經把具象化的異形抽象化,成了哲學概念,“科幻世界的盡頭”本質上是關于生命的反思—生命的創造必然跟隨著毀滅的殘暴。
視覺的意圖
曾經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專業學習電影藝術設計的雷德利,從童年就開始學習繪畫,功力深厚,堪稱是經營視覺風格的大師。這位左撇子導演每次都會親自繪制電影的分鏡頭腳本,在記者提問和采訪的時候,他甚至會一邊畫著畫,用繪畫的思路來進行語言的邏輯組織。《異形》還在進行前期策劃的時候,斯科特就親自繪制故事畫板,并將其提交給二十世紀福斯公司,正是因為導演精心繪制的這些故事畫板,才打動了福斯公司的高層,將原來450萬美元的預算至少提高到800萬美元。
60年代從倫敦皇家藝術學院畢業后,斯科特在BBC找到一份在劇組里做場景設計的工作,每年有1100英鎊的固定薪水,此外兼職拍攝廣告還可以讓他每年額外進賬14000英鎊。三年后他創建了自己的廣告攝制公司RSA,在業務巔峰時期,公司一年中拍攝了150條廣告。多年的廣告設計經驗讓斯科特的鏡頭語言極具視覺美學的奇觀。1984年,電腦界的大佬還是IBM,微軟才啟動了幾年,蘋果公司推出的新產品麥金托什系列機的廣告就是由斯科特執導。在這個概念性極強的廣告里,一群類似小說《1984》里被管制和奴役的人類因為一位個性的闖入者而突然獲得光明,“1984年因蘋果而不再1984”,整個廣告中科幻感極強的場景設置,就是斯科特視覺風格的一貫寫照。
拍攝《異形》時,斯科特對全片的每一個視覺細節都深究和細查,“在執導恐怖片的時候,你必須讓演員們與自己內心最深邃的恐懼產生共鳴,因此我將布景中的飛船艙室一再縮小,身材高大的亞非特·科托每次進出布景時都必須費力彎腰—我通過這種手法來向演員們傳達自己在狹小密室中的焦躁不安。”女主角甚至大發牢騷,抱怨導演關心他的道具甚至超過了他的演員。《異形》中許多看似無心的道具擺設,例如空啤酒罐、墻上的艷情海報、風鈴等等看起來凌亂不堪的道具都對劇情質量的提高充當了重要作用。明亮的環境里,死里逃生的凱恩就是在雜亂的空啤酒罐桌面上被破胸,生活道具營造的松懈感一下子形成了一種恐怖的反差。
有些影評家曾經建議美國歷史頻道將斯科特的《黑鷹墜落》作為美軍摩加迪沙之戰的參考歷史紀錄片;曾經的阿富汗前線,美國軍官們也經常把這部電影當作訓練士兵實戰的教材,因為在觀眾看來,斯科特在《黑鷹墜落》里提供的戰爭素材實在太過于真實。斯科特能夠全方位地解剖這場戰爭,提供整件事情的透視圖,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斯科特在創作時對影片真實性的負責。除了對于演員的嚴格要求(在正式開拍前,全體演員連同只有幾個鏡頭的小角色都分成三撥,分別在美軍的三角洲部隊、游騎兵部隊和黑鷹直升機基地參加軍訓。除學習部隊生活、武器操作和團隊精神外,他們還和摩加迪沙之戰中陣亡者的戰友和親友交談,對自己所扮演角色有更感性的認識),斯科特也死磕造型道具,“我有好幾個助手,包括李·馮·阿斯達爾和科爾,還有天天陪著我的湯姆·馬修斯,他們都是參加過區域實戰的專家。在拍攝現場,他們幫我確認每一個鏡頭的武器裝備都是對的,比如什么時候該用蘇聯的武器等等。”

史詩大作《角斗士》在人物的服裝設計上可謂煞費苦心,戰場上一閃而過的士兵的服飾都是經過精心的打造:弩兵腰間上的弩箭在木質箭身和金屬箭頭的連接處有深色的使用痕跡,士兵的金屬頭盔沒有一個是嶄新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老舊氧化的肌理質地。在打造《火星救援》時,一向熱愛實景的斯科特,用32臺GoPro攝像機實時拍攝主演馬特·達蒙在火星科考站里的所有活動,徹底把影片變成一場火星真人秀。而開篇時吹跑馬特·達蒙的大風暴,動用了6臺超級鼓風機,還加上大袋的煤灰粉塵、幾隊人馬上陣制造狂風牽引力。
斯科特在《銀翼殺手》里營造出的賽博朋克未來城市風格深深影響了后市無數音樂錄影帶、廣告、動作片以及商場百貨的設計。霓虹燈在80年代就已經遍布大街小巷,但是斯科特在《銀翼殺手》中卻把霓虹燈用出了一種未來感,這其中的關鍵就是霧霾。在霧霾的籠罩下,霓虹燈讓整個洛杉磯跨越了虛幻和真實的界限,整個城市仿佛陷入長夜,建筑的輪廓幾乎完全融化,霓虹燈發射出的冰冷艷麗的人造光令城市空間纏繞著光怪陸離的荒謬感。這種非自然光的造型設計可以追溯到德國表現主義的電影形式,黑暗、壓抑與陰森。在銀翼殺手戴克與女復制人瑞秋首次見面的場景里,空曠的房間里只放置了一條長長的桌子,后景是幾根柱子的天臺,少有的自然光射進室內,卻沒有營造出該有的溫暖,反而在室內肅殺的環境里被遏制和疏離。
類型多元的斯科特并沒有只局限于黑色基調的視覺設計,極具女性主義風格的《末路狂歡》就屬于斯科特作品中色彩比較輕松明亮的類型。兩位女主人公路易斯和賽爾瑪的服裝都是青春活潑的白色和牛仔藍,州際公路上亮眼的藍鳥汽車象征著兩位女性逃離男性權威后的自由和奔放。影片最后,大峽谷上藍鳥汽車一躍而下的浪漫鏡頭讓觀眾仿佛感覺兩位女主角不是奔向死亡,而是定格在了浪漫的光明瞬間。
色彩光線之外,對景別的風格化運用也是斯科特視覺設計的一大特色,在史詩巨作里,斯科特特別喜愛運用俯視全景的鏡頭,他經常會把人物身處之地或該年代特有的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用大全景鏡頭加以展現,給人以身臨其境的逼真感。《黑鷹墜落》在表現索馬里戰亂環境時運用了很多大全景鏡頭,從直升機上俯瞰地面成百上千的饑民涌向僅有的幾輛運糧車,盡管有暴徒在掃射平民,饑餓的人群仍源源不斷涌上前去,用幾乎喪失了為人尊嚴的難民俯視圖作為開場,也為后來影片表現戰爭的殘酷和無解打下了沉郁的基底。《天國王朝》里交戰的雙方在倒塌城墻處的拼死決戰也是用大全景來刻畫,此時的影片沒有環境音效,只有背景音樂,雙方簇擁混戰的身影慢慢幻化成累累尸首。斯科特用上帝之眼般的俯視鏡頭,傳達的卻更多是一種悲憫的情感。除了用大俯視全景表現抒情性的人文關懷,大全景在敘事層面上營造的恢弘壯闊的氣勢也在斯科特的電影中非常普遍。《羅賓漢》結尾部分有一組航拍鏡頭,俯瞰羅賓帶領的騎兵隊奔馳在通往海岸的群山之間,蒼翠的山脈、勇敢奔赴沙場的英雄配合著雄渾低沉的音樂,一種一往無前、無所畏懼的凜然情懷油然而生。觀眾在俯瞰山脈時能在一側山體上發現一匹奔騰的白馬的巨大圖案,在好萊塢,如此史詩氣質的俯瞰全景鏡頭,幾乎沒有人敢和斯科特叫板。
硬漢的人生哲學
雷德利·斯科特1937年11月30日出生在英國的諾薩布蘭。年幼時曾經歷二戰,“我們曾生活在倫敦郊區,二戰時經常有轟炸,當時我大概兩三歲的樣子,轟炸的時候就跟家人一起躲在樓梯下,我記得我拿著一盞小小的燈,大家在黑暗中一起唱歌,試圖暫時忘卻頭上的炸彈。”由于父親是軍人,青少年時期的他經常輾轉不定,搬過很多次家,父親因為供職于政府和軍隊而不能很好地照顧家庭,家庭的重任就經常落在母親的身上,雷德利·斯科特非常崇拜母親把三個兒子拉扯長大的堅毅品質。甚至,雷德利·斯科特認為自己之所以取得現在的成就,得益于自己是和一個“壓力應對大師”式的媽媽一起長大的。所以從《異形》到《火星救援》,他的電影中永遠不缺少那種強勢又有女性魅力的女性。除了那部宣揚女權的《末路狂花》外,他的《黑鷹墜落》就是送給母親的紀念作。“的確,我喜歡強勢的女性,比如我媽,一口氣生了三個男孩兒。我弟弟托尼·斯科特,是一個導演。我哥是個船長,在七、八十年代,他航行到過新加坡和中國南方,他當時還是在一家中國公司里就職。我媽一口氣養大了三條硬漢,所以我才對強勢的女人特別情有獨鐘。我有三個公司,一個在倫敦,一個在紐約,還有一個在其他地方……總之這些公司里都有女性在運營,我只能說,誰行誰上。”
除了對母親有著特殊情感,斯科特與已故弟弟托尼·斯科特的兄弟情誼也是一段佳話。斯科特在倫敦皇家藝術學院進修期間拍攝的第一部處女短片《男孩和自行車的故事》就是由自己的弟弟主演。影片里的弟弟飾演一名無所事事的男孩,他在學校玩鉤子,在海岸邊騎自行車。在被哥哥指使一個暑假之后,托尼也跟隨哥哥進入了電影行業。漸漸地,兩兄弟一起學習電影,斯科特介紹弟弟看大衛·里恩的《孤星血淚》,向弟弟介紹這是他第一部備受震撼的電影。然后,他們一起認識了約翰·福特、黑澤明、卡羅爾·里德和奧遜·威爾斯等世界著名導演,兩兄弟也形成了不同的導演風格。弟弟托尼·斯科特更青睞動作片類型,讓湯姆·克魯斯一炮而紅的《壯志凌云》就出自他的創作。2012年8月19日,托尼·斯科特從自己非常喜歡的加州第四大懸索橋文森特·托馬斯大橋跳下,自殺身亡,享年68歲。一向熱愛運動,喜愛登山攀巖的弟弟竟然自殺身亡,哥哥雷德利·斯科特將這一天視為史上最悲傷的周末。


看起來熱衷史詩巨作,喜愛描摹英雄事跡的斯科特實際上也很重視家庭的作用,或者說他所有的角色其實都是由最簡單的人文情感構成。由個人推至家庭,再由家庭上升到社會,暴力并不是目的,那些具有自我完善的人性觀才是斯科特電影的人文主題。《天國王朝》里的貝里昂在斯科特心中本質上并不是一個英雄和猛士。沒有宗教信仰的斯科特并不想把貝里昂打造成一個基督教的圣戰領導人。貝里昂在戰前動員的慷慨演講更想告知戰士們,自己守衛的不是圣城,不是宗教,而是耶路撒冷的人民,是自己的親人。貝里昂對人的信仰高于以往他盲目相信的宗教,貝里昂在伊貝林領地上帶領百姓打井灌溉,在漫天的黃沙之中開辟出一片綠洲。望著親手締造的和平生活,望著親手培植、護衛著的自然與生命,他找到了信仰,他知道了他守衛的是什么—對生命、人民、和平的尊崇與信念,高于世上的一切宗教。
和雷德利·斯科特合作過5次的羅素·克勞經常被斯科特安排飾演一些類似“角斗士”和“羅賓漢”式的宿命英雄人物,羅素·克勞和斯科特一樣都是擁有火暴脾氣的硬漢人物。不過,將羅素·克勞稱為一只稍顯自負的小狗的斯科特卻曾讓克勞在自己唯一的愛情喜劇《美好的一年》中擔任男主角。這兩個八竿子和浪漫打不著關系的大男人到最后反而超額完成了影片任務。優美恬淡的普羅旺斯讓一開始自私自負的男主角麥克斯轉變了生活的態度,陽光空氣,愛情美酒,與愛人在大樹下相擁的時刻才是真正的人生幸福。在斯科特和羅素·克勞所代表的硬漢直男的人生哲學里,一方面需要擁有敢與天下爭鋒的魄力,另一方面仍要珍視生活里的親情、愛情和浪漫,這大概也是兩位魅力男性從業多年依舊為人敬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