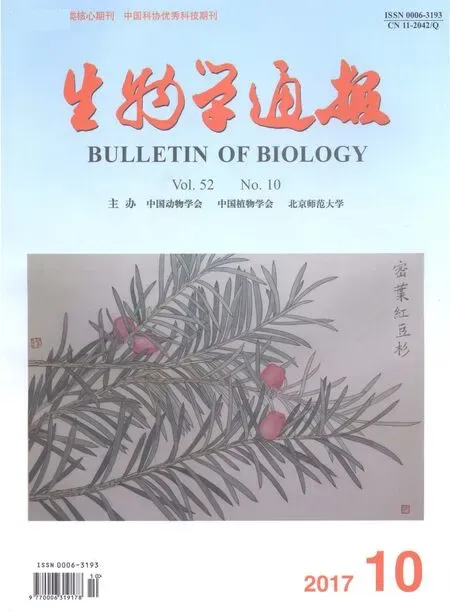不斷探索、不停奮斗的遺傳學家徐道覺
——紀念人類及哺乳動物細胞遺傳學的開創者徐道覺誕辰100周年
馮永康 (綿陽第一中學 四川綿陽 621000)
1 談家楨的得意弟子

圖1 徐道覺(1917—2003,照片由高翼之提供)
1917 年 4月 17日,徐道覺(T.C.Hsu)出生在浙江紹興的一個小山村。孩提時代的農家果園生活,使他自幼便養成了學會欣賞大自然、領略大自然之美的興趣。由于其父親的工作性質(河流工程師),屢屢需要奔波于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徐道覺也在不斷地隨之遷徙顛簸中,讀完了小學和中學。在父親豐厚學識的感染和探索精神的熏陶下,他不僅打下了中國歷史和文學方面的扎實基礎,喜好閱讀與詩歌創作,還利用課外時間走進學校附近的山區,在對昆蟲生活的觀察和標本的采集與制作中,了解了大自然的更多奧秘。這種探索大自然的旨趣,為他日后進入生物學的研究領域,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1936 年,徐道覺高中畢業選擇報考生物學專業,以優異成績考入了浙江大學農學院,主修昆蟲學。
1941 年,徐道覺獲得學士學位后,拜師于談家楨(1909—2008)的門下,攻讀遺傳學碩士學位。談家楨曾師從國際遺傳學大師摩爾根(T.H.Morgan,1866—1945)和進化遺傳學家杜布贊斯基(Theodosius Dubzhansky,1900—1975),于 1936 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在浙江大學建立了國內大學中第1個遺傳學專業。徐道覺加入到談家楨的實驗室后,不僅承擔了到廣西等地采集作為實驗研究材料的瓢蟲之任務,更重要的是能夠系統地閱讀到談家楨從美國帶回的所有遺傳學實驗研究的抽印本論文,從中了解到遺傳學發展的最新動向,獲取了豐富的遺傳學知識,逐步明確了自己為之奮斗的目標。在談家楨的悉心指導下,他還學會了用果蠅做實驗材料,用壓片法觀察唾腺染色體等遺傳學的實驗研究技術。
從攻讀碩士學位開始,徐道覺就完全醉心于活細胞中染色體的研究。他運用已初步掌握的遺傳學實驗技術,選擇一種搖蚊(Chironomus)作實驗材料,對其唾腺染色體進行實驗研究。他發現了在搖蚊第2號染色體的一個基因座上,泡(puff)的存在具有多樣性,即:無泡、雜合泡、全泡,并證明這些可遺傳變異出現的頻率,服從于哈迪·溫伯格(Hardy Weinberg)遺傳平衡定律。他將該研究結果用英文寫成的第1篇學術論文發表后,美國遺傳學家比爾曼(W.Beemann)用實驗研究獲得的遺傳證據表明,在第2號染色體那個基因座上無泡的搖蚊,不能在它們的唾腺細胞里合成某種蛋白質。
研究不同昆蟲的多線染色體,使徐道覺感受到成功的快樂。他與談家楨的另一個弟子劉祖洞合作,選用一種蝗蟲(Phlaeoba infumata)研究細胞的減數分裂,通過實驗觀察和統計,對得到的6個種群的實驗數據進行數學分析,完成了有較高學術價值的研究論文。1948年徐道覺留學美國時,他將論文完成稿交給進化生物學家邁爾(E.Mayr)指導。邁爾隨即寄給了群體遺傳學家賴特(S.Wright),請其為之審稿。賴特非常仔細地分析了論文中的實驗數據,并在專門給徐道覺長達7頁的回函中,提出了繼續研究的建議。
抗日戰爭勝利后,浙江大學由貴州湄潭遷回浙江杭州。談家楨因為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一年的經費資助,要再次赴美與杜布贊斯基合作研究。此時,徐道覺已碩士畢業留校擔任談家楨的助手,并承擔本科生的遺傳學課程。受導師的全權委托,他擔負起整個實驗室的工作安排和另外2名研究生的培養工作。
在一次給本科生講授遺傳學的課堂上,當徐道覺講到顯性性狀和隱性性狀,并舉例說明人群中有人會卷舌,有人不會卷舌時,生物學系的一位錢姓女學生告訴他,她的舌不但能卷,而且能上翻折疊,并作了現場表演。徐道覺馬上意識到,他遇見了一項從未被報告過的人類遺傳性狀——折疊舌(tongue upfolding)。以這項新發現的遺傳性狀為線索,徐道覺開展了系統的調查研究。1948年,他將該項研究結果,以“上翻折疊舌——一項新報告的人類遺傳性狀”為題撰寫成論文,發表在美國Journal of Heredity(第 39卷)上,并配有該錢姓女學生展示折疊舌的整版照片[2]。
1949 年,徐道覺與劉祖洞合作,將在人類中已發現的屬于隱性遺傳的折疊舌和屬于顯性遺傳的卷舌這2種性狀,從群體遺傳學的角度,在對調查所獲數據做了統計學的處理,測定了基因頻率后,以題為“中國人群一樣本中的折疊舌和卷舌”之論文,再次發表在美國Journal of Heredity(第40卷)上。
上述2篇論文是中國遺傳學家在人類遺傳學領域最早的研究成果,顯示了徐道覺等人深厚的遺傳學功底和所受到的科學研究能力的嚴格訓練。美國遺傳學家麥庫西克(V.A.McKusick)從1966年出版他所編寫的巨著《人類孟德爾遺傳》第1版起,還專門收錄了徐道覺發現的“折疊舌”這一條目至今(MIM 189300)。
2 并非遺憾的“偶然發現”
1948 年,談家楨利用在美國作學術訪問研究之便,為徐道覺爭取到了赴美國德州大學帕特森(J.Patterson)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同年4月,徐道覺暫別妻子和即將出生的孩子,來到異國他鄉,開始了為期3年的博士研究生學習生涯。
初到美國時,面對生活的艱辛、語言交流又不太自如的處境,徐道覺首先接受到的是導師帕特森教授安排給他的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研究任務——搞清楚“果蠅virilis種群內各個種的關系”。在研究生院內的青年同事瓦格納(B.P.Wagner)、惠 勒 (M.H.Wheeler), 特 別 是 懷 特 (M.J.D.White)教授的幫助下,徐道覺參加了3次以采集果蠅為主的徒步旅行,每次為期1個月,足跡幾乎遍布整個美國大陸。通過實地考察與研究,他以果蠅遺傳學家格里芬(A.B.Griffin)繪制的唾腺染色體圖譜為基礎,構建了更加完整的、為后來的研究者所延用的果蠅virilis種群新圖譜。
1951年6 月,徐道覺順利通過畢業論文答辯取得博士學位后,舍棄了自己從事的果蠅遺傳學研究,來到位于加爾維斯頓(Galveston)的德州大學醫學院,進入波米拉(C.M.Pomerat)實驗室接受人類和哺乳類組織培養的博士后訓練。在最初的大約6個月時間內,他學會了如何建立人體組織細胞培養物,拍攝相差顯微鏡照片和縮時電影等技術。他也曾嘗試觀察人體組織細胞中的染色體,卻發現它們總是擠成一堆,什么也分不清楚。研究進程的停頓,讓他感到十分失望和沮喪。度日如年的悲觀情緒,縈繞在他的心頭。
正當徐道覺的學習與研究處于猶豫徘徊之際,“奇跡”突然出現了。
1952 年初的一天晚上,徐道覺照常到實驗室做研究。他在對幾個來自人工流產的胎兒組織(皮膚和脾臟組織)培養物固定后用蘇木精染料染色,放到顯微鏡下觀察時,被眼前的情景驚住了。在顯微鏡下的視野中,他清楚地看到了玻片標本上一些分散的染色體,竟然鋪展得如此勻散 。
徐道覺在后來的回憶中寫道:“此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是獨自默默地繞著實驗樓走了一圈。當我再次回到實驗室,在顯微鏡下觀察那些玻片標本,舒展分散的染色體還清楚可見。我知道它們是真的了。我試著研究那些玻片標本,并制備了另外一些新的人體胚胎組織細胞培養物,想重復這一‘奇跡’。但是,結果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有絲分裂的圖像又回到了前面那種擠成一堆的‘糟糕’狀態。我連續重復了2次,都沒有看到分散的染色體。我開始思考,那批不同尋常的人體脾臟組織培養物一定是發生了什么‘差錯’,才使有絲分裂的染色體能如此均勻分散開來!”[3]
這之后,徐道覺花了大約3個多月的時間,嘗試著改變可能想到的每一種因素:培養液的成分、培養的條件、培育的溫度、秋水仙素的添加、固定的步驟、染色的方法等。每一次他都只改變眾多因素中的一個因素,結果還是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
直到1952年4月,當徐道覺將蒸餾水和平衡鹽溶液相混合以降低滲透壓時,“奇跡”再一次出現。在顯微鏡下,玻片標本中分散排列很開的染色體,又重新出現在他的眼前[4]。
此時,他已能作出肯定,3個多月之前出現的“奇跡”,一定是實驗室中的某一位技術員在配制平衡鹽溶液時,讀錯了刻度標尺,以致誤配成低滲溶液的緣故。
1952 年,徐道覺在美國Journal of Heredity(第43卷)雜志上發表了題為“體外哺乳類染色體:人的核型”之論文。低滲溶液預處理技術的首次發現,使徐道覺清楚地意識到,現在已經有了一種強有力的研究手段,可使細胞膨脹并使其中的染色體鋪展開來。這種技術不僅僅適用于人體細胞,并對所有生物和所有的細胞培養物一概都是適用的。
當時擔任德州大學校長的佩因特(T.S.Painte)是一位對果蠅遺傳學做出過卓越貢獻的學術權威,是徐道覺極為尊重的細胞遺傳學家之一。正是佩因特在1923年發表的研究論文中,對人類染色體的數目得出了2n=48的錯誤結論,隨后“48”這個數字,便一直充斥于所有的生物學著作乃至百科全書及生物學教材中。
本來可以成為世界上首位確認并發布人類染色體正確數目為2n=46的遺傳學家徐道覺,在身處德州大學和享有盛名的遺傳學大師佩因特的光環籠罩下,作為還在為生計發愁的年輕博士生,不敢輕易冒犯學術權威。直面顯微鏡下視野中清楚的“46”,他沒有繼續再做確證性的實驗觀察,而是選擇了對佩因特關于人類染色體數目為2n=48的沉默。
徐道覺與確證人類染色體數目為46條雖然失之交臂,但是他對人類染色體制片過程中采用低滲溶液預處理技術的發現,卻直接導致3年后,華裔遺傳學家蔣有興(J.H.Tjio)對人類染色體數目的再次準確地計數與公開發布。
1955年12 月,在瑞典隆德大學萊文(A.Levan)實驗室做研究的華裔遺傳學家蔣有興,選用人體胚胎肺組織為材料,利用徐道覺發現的低滲溶液預處理技術,分別在顯微鏡下和照片中,觀察了來自4個不同人類胚胎組織的261個肺細胞,清清楚楚地計數出了使他自己都難以置信的人的染色體數目,不是佩因特的2n=48,而是實實在在的2n=46。根據這一確定的觀察結果,他以“人類的染色體數”為題迅速撰寫成論文,發表在1956年1月出版的斯堪的納維亞Hereditas雜志上,從而擯棄了在整個細胞遺傳學界長達30多年無人質疑的佩因特的錯誤結論,使全世界的遺傳學家對人類染色體數目達成了2n=46的正確的共識。
徐道覺未能確認自己所觀察到的人類染色體為2n=46這一事實,國內遺傳學界的某些學者曾經給予了“對徐道覺來說,實在是一個莫大遺憾”的評論。
難道這真是遺傳學史上的一個“遺憾”?答案是否定的。
作者通過再次研讀徐道覺于1990年代撰寫的《我是怎樣成為一個遺傳學家的》自傳,并有機會訪談到徐道覺本人,在查閱了大量文獻獲取信息的基礎上,覺得有必要通過史料的再次論證,還原對徐道覺20世紀50年代初期首創低滲溶液預處理技術并觀察到人類染色體這一科學事實的客觀評價。
徐道覺在自傳中,曾多處提到了他對這段研究經歷的回憶。他寫道:“我已經發現了低滲溶液對染色體的作用。這是一次意外‘錯誤’的結果。低滲技術促成了人類細胞遺傳學的大發展。由于這個發現,我決心繼續做細胞培養的研究工作。因為真正的科學家關注的是下一步。”[1]
他還寫道:“我永遠都是探索者。探索者是會犯錯誤的。我也一樣。發現低滲技術,在我的科學人生中僅僅是一個小插曲。但是這個偶然的發現,的確是一個有意義的貢獻,不然人類和醫學遺傳學就會延遲不知多少年。事件的發生雖然是‘偶然’的,但追溯可能起作用的因素,則需要堅韌不拔的決心。在這個‘偶然’的發現中,我是在幸運之神向我微笑時,緊緊地抓住了機會。”[1]
徐道覺后來在接受作者訪談時也說道:“較之我一生具有挑戰精神的學術研究經歷,較之我大半生對人類和哺乳動物細胞遺傳學所作出的貢獻來說,1952年的那次發現,僅僅是我科學人生的一個很小的片斷。我并不認為當時沒有確定并發布第1次觀察到‘人類染色體為46條’這一發現,而感到有什么遺憾。因為正是有了這一次的小小發現,自1950年代初期開始,才奠定了我從事人類細胞遺傳學的實驗研究方向,堅定了我畢生為之不停追求的科學研究目標,也最終確立了我在人類和哺乳類細胞遺傳學研究中的學術地位。”
在這次訪談中,徐道覺還向作者簡要地談到他與蔣有興結為摯友的一些往事。由于蔣友興利用徐道覺創立的低滲溶液預處理這一技術,再次觀察得出“人類細胞中的染色體數目為46條”的正確結論并予以公開發布,他們2人從此成為了密切交往的學術摯友。
3 不停奮斗的科學人生
1952 年,徐道覺所發現的低滲溶液預處理技術是人類和哺乳動物細胞遺傳學史上的重要轉折點。他的導師波米拉為他的出色工作而感到驕傲,并說服醫學院的教務長給了他一個助理教授的資格。但是,具有不斷探索精神的徐道覺,仍然想通過更加出色地努力,實現創建一個屬于自己的遺傳學實驗研究室的學術夢想。
1955 年,徐道覺終于如愿以償,進入到德州大學安德森(M.D.Anderson)醫院和腫瘤研究所(后來改名為安德森癌癥中心),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人類和哺乳動物細胞遺傳學的實驗研究。
在安德森癌癥中心這樣一個充滿信任、激勵而又合作的學術環境中,徐道覺的科學生涯開始步入一個“黃金時期”。他用幾年時間重點研究了小鼠的L系細胞長期培養時數量的變化,也嘗試從其他正常的動物組織培養中,建立他自己擁有的細胞系。從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末期,徐道覺率領的研究團隊經過大量的實驗觀察和結果分析,在多種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以“體外哺乳類染色體”為總題目的系列研究論文(包括從1952年的之1到1963年的之16)。這期間,他們還通過收集來自世界各地實驗室的各種哺乳動物的組織樣本和淋巴細胞,經培養固定進行染色體的分析,在獲得大量實驗數據基礎上,主編了極其精美的《哺乳動物染色體圖譜》(從1967年出版第1卷到1977年出版第10卷)。該圖譜共收集了現存常見和罕見的哺乳動物的染色體圖片及其核型分析,為哺乳動物細胞遺傳學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資料[5]。
1980 年代初期,徐道覺利用人類細胞遺傳學的研究成果,開始實施一項“研究環境誘變劑同癌癥易感性關系”的宏大計劃。他與實驗室中的年輕同事,先是收集并查證了大量的文獻資料,然后從一個為之孕育和辛苦工作了8年的實驗體系中,極其巧妙地設計了一個反其道而行之的實驗構想:將染色體作為度量誘變劑敏感性的工具。他們將人的淋巴細胞放在含有被公認為的擬輻射物質的博來霉素(bleomycin)的培養基中處理一段時間,由這種誘變劑誘導斷裂的染色單體的頻率,作為誘變劑敏感性的定量評估。為了獲得足夠多的人體血樣(包括正常個體和癌癥患者),他們從實驗室的每一個來訪者身上抽取10 mL血液,分類作好記錄,以用于論證假說的實驗測試。到1987年,徐道覺實驗室已經收集了豐富的實驗數據,既有正常的對照者血樣,也有各類癌癥病人的樣本。他們從概念的形成到論文的發表,前后用了8年的時間,初步得出了癌癥患者對博來霉素的敏感性(即出現較高的染色單體斷裂率)較正常人高的結論。實驗數據也有力地表明了引起癌癥的原因是環境與遺傳的相互作用[1]。
徐道覺創立的用博來霉素誘導染色單體斷裂的頻率,作為誘變劑敏感性的定量評估之實驗研究方法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很快引起了學術界更多同行的興趣。不同地域、不同科系的臨床醫生和研究者,紛紛來到徐道覺實驗室學習,并嘗試擴大這種測試方法的臨床范圍。安德森癌癥中心外科學系的香茨(S.P.Schantz)運用該實驗測試方法,在臨床醫學上發現了對博來霉素高敏感性的患者可能產生第2次原發性癌癥的機會,是低敏感者的4倍。癌癥防治系的施皮茨(M.R.Spitz)將自己的流行病學數據同香茨的臨床信息綜合起來,發現了在上消化道系統獲得腫瘤的幾率與吸入的煙草和飲用的酒精量成正比。當將博來霉素敏感性參與分析時,對博來霉素敏感個體的消化道上腫瘤的比率顯著升高。香茨和施皮茨的臨床實驗與分析結果,促使徐道覺與他的助手雪莉(L.Shirley)、弗朗(C.Furlong)等,進一步用實驗論證乙醇是否有誘變作用的研究。他們選取博來霉素等多種誘變劑分別與乙醇共同作用于細胞,實驗結果證實了乙醇有加強博來霉素等誘變劑的作用。通過進一步的實驗,徐道覺等人還證明了乙醇作用的機制:它不僅能阻斷正常的DNA復制,也可能抑制一些與DNA修復有關的酶的活性[1]。
基于這一系列的實驗研究結果,徐道覺向公眾提出了健康生活的忠告。他告誡人們:吸煙有害健康,是因為它能引起細胞輕微的遺傳損傷。雖然只要給以足夠長的時間,大部分遺傳損傷可以被修復,但是當又抽煙又喝酒時,DNA的修復就受到了乙醇的抑制,由此引起癌癥的發生。
在長達50年的遺傳學實驗研究中,徐道覺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他領導的實驗室成為人類和哺乳動物細胞遺傳學的“麥加”。世界各國的細胞遺傳學家(包括施立明等中國遺傳學家),都紛紛慕名來到這里,學習制備有絲分裂染色體的新技術、新方法,進行細胞遺傳學的學術進修與實驗研究。徐道覺本人被國際遺傳學界尊崇為“哺乳動物細胞遺傳學之父”(Father of Mammalian Cytogenetics)。
在徐道覺的整個科學研究生涯中,他于1953年被聘為美國德州大學的助理教授;1955年升任成副教授,并成為安德森癌癥中心細胞生物學研究主任;1961年晉升為正教授;1973年被選為美國細胞生物學會主席(該學會第1次選出的華人主席)。1980年成為安德森癌癥中心第1個“特聘首席”(endowed chair)教授。他的一生發表了近400篇論文及12本專著),可稱之為碩果累累。徐道覺的原創性貢獻,正如他在自傳中所總結的主要有3個方面:
1)發現低滲溶液預處理技術,為精確確定人體染色體數目及其他哺乳動物染色體數目,提供了有效的技術手段與研究方法[6];
2)創建了顯示組成型異染色質的方法,即染色體C顯帶技術的發現;
3)提出了誘變劑敏感性與環境致癌作用相關的假說,并用實驗證明了這一假說。
2003年7 月9日,徐道覺因癌癥病逝于他所工作過的德州大學安德森醫院,享年86歲。他對遺傳科學研究的興趣與挑戰精神,不停奮斗的學術人生,不僅為學界同仁所景仰,還將繼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后來人,朝著未知的遺傳奧秘,不斷地向縱深探索。